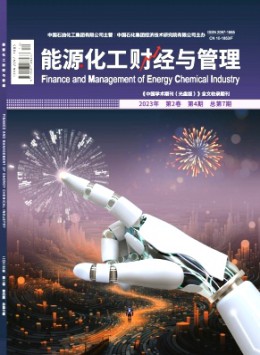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一、词的比较,体会匠心
作者在写文章时,常常通过比较揣摩,选用最恰当的语言文字来表现事物,表达感情。词语教学在阅读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让学生通过比较了解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特定含义,真正体味到文章作者遣词造句的独特匠心。
1.交换词语
教学《推敲》一文,当同学们读到这一句“贾岛去郊外拜访一个叫李凝的朋友”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这里的‘拜访’能否换成‘访问’?”显然不能,虽然“拜访”和“访问”是一组近义词,但是,它们还是有区别的。“访问”的意思是有目的地去探望人并跟他谈话,而“拜访”含有尊敬对方的意思。文中写贾岛去拜访朋友,已经深夜了,路很难走,一路摸去,足以看出贾岛对朋友的诚心诚意。通过换词进行比较,学生能较好地体会到作者用词的准确性,体会出语言文字的妙处,还可以培养学生反复推敲的阅读能力。
2.增删词语
课文中有很多词语用得准确生动,教学时紧扣这些词语进行品味,学生就能较好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教学《春笋》一文时,出示“它们冲破泥土,掀翻石块,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一句,问学生:句中的加点词能删除吗?学生通过阅读感悟,觉得加点词不能删除,虽然删除后的语句依然文通字顺,但表达效果完全不一样,“冲破泥土”“掀翻石块”生动表现出春笋顽强的生命力,“一个一个”形象地表现了许许多多春笋连续不断、你追我赶、破土而出。通过增删比较,足以体会作者的独特匠心。
二、句的比较,加深理解
运用比较法进行句子教学,常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学《小露珠》一文时,出示下面两组句子:
第一组:
(1)“早哇,像钻石那么闪亮的小露珠。”蹦到大荷叶上的小青蛙对小露珠说。
“早哇,像水晶那么透明的小露珠。”爬到草秆上的小蟋蟀对小露珠说。
“早哇,像珍珠那么圆润的小露珠。”落在花朵上的小蝴蝶对小露珠说。
(2)“早哇,小露珠。”小青蛙对小露珠说。
“早哇,小露珠。”小蟋蟀对小露珠说。
“早哇,小露珠。”小蝴蝶对小露珠说。
第二组:
(1)霞光中,小露珠光彩熠熠,把所有的植物都装点得格外精神――金黄的向日葵,碧绿的白杨树,紫红的喇叭花,还有数不尽的鲜花嫩草,都像俊俏的小姑娘戴上了美丽的珠宝,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2)霞光中,小露珠把所有的植物都装点得格外精神――向日葵,白杨树,喇叭花,还有鲜花嫩草,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出示后,让学生读句子,引导思考:“你们看,两组句子中,分别是哪一句表达的效果更好?请结合文章说说你的理由。”学生必然静心思考、认真讨论。最后很容易就达成共识:每组中第一句表达的效果更好。第一组中“像钻石那么闪亮的”“像水晶那么透明的”“像珍珠那么圆润的”三个比喻句既形象地表现出小露珠“闪亮”“透明”“圆润”的特点,又写出了小动物们喜欢小露珠的原因。句中“蹦到大荷叶上”“爬到草秆上”“落在花朵上”形象描写出小青蛙、小蟋蟀、小蝴蝶活泼可爱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生活习性。第二组中“光彩熠熠”是植物变得格外精神的原因,“金黄的”“碧绿的”“紫红的”写出了向日葵、白杨树、喇叭花的颜色特点,“数不尽的”表现鲜花嫩草的多,“像俊俏的小姑娘戴上了美丽的珠宝”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表现小露珠的美丽……阳光下的小露珠给所有的植物带来精神、生机和美丽,那么植物当然喜欢小露珠了。实际上,这是告诉我们露水有着滋润万物的作用,正如谚语说的“雨露滋润禾苗壮”。
这时,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则水到渠成,课文的重点也就很顺利地突破。
三、段的比较,提升语感
理解段的主要意思,了解构段方法及段之间的关系,是段教学的主要任务,也可以运用比较方法进行。
如《泉城》一文的第2~5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分别介绍了“珍珠泉”“五龙潭”“黑虎泉”“趵突泉”的不同特点:珍珠泉约一亩见方,清澈见底;五龙潭由五处泉水汇注而成;黑虎泉的泉口是用石头雕成的三个老虎头;趵突泉名列七十二泉之首,面积大,水清,如三堆白雪。从教材特点出发,指导学生看图读文时,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理解这四个自然段的主要意思后,引导学生再读、比较,发现这四个自然段是并列关系,它们的构段方式相同:都是先介绍泉的位置,后描绘泉的特点。
教学《在大海中永生》,第三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写由奔腾不息的浪花联想到骨灰的去向:万里海疆、澳门香港、宝岛台湾、三大洋……赞美小平同志的影响之大。引导学生理解内容后,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把这四句话的顺序打乱好不好?学生说,打乱顺序不好,因为骨灰去向的地域渐次增大,暗含他制定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方针影响之深远,缅怀其丰功伟绩之意尽在其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用比较的方法了解自然段的构段方式。
四、篇的比较,探索规律
篇的教学中运用比较方法,可以使学生深入体会文章的立意、思想内容、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
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有《菩萨兵》《少年王勃》等四篇课文,通过比较,就能发现这是一组写人的文章。四篇课文,篇篇写人,但表现手法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四篇课文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例表现人物。《菩萨兵》通过主人公的语言和行为,以及藏胞人民的赞扬,表现人物品质;《李广射虎》虽是文包诗,但却是具体的场景的描述,如将军的动作和神情,刻画将军的神勇;《少年王勃》的重点是正反对比描写相结合的方式,让人物在对比中高大起来;《大作家的小老师》通过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萧伯纳的胸襟和谦逊。
再读这四篇课文,揣摩其脉络。《菩萨兵》一文中有一些表示时间的词,根据时间来理清课文的脉络是一种方法。可以告诉学生写人和写事的文章,我们大都可以根据时间顺序和事情发展的顺序来理清课文的脉络。于是引导学生进行学法的实践。学生很快对课文《李广射虎》和《少年王勃》《大作家的小老师》进行实践。《李广射虎》一文中既有鲜明的时间概念,又有潜藏在文字中的事情发展的线索,学生很快找出文章线索,层次也分得较清楚。
第2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一、再现画面,理文握情
对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歌教学,大家运用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叙事诗,如果只依靠教师语言的描述是不够的。那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往往效果不好,学生学起来感觉无趣。但是通过课件动画再现出来,使课件变得具体可见,教学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利用网络中的信息资源,调用素材库中现存的资料(有影片、音乐、录音、动画、图片等),解决教学难点。
比如我在执教如《鹅》这首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有鹅的色彩、形象、动作等等,由于课堂条件有限,如此丰富的信息仅凭口头讲解是不易表达完整透彻的,故此根据诗意我制作了多媒体动画课件。画面上:亭台楼阁,杨柳依依,岸边一位老翁嘻嘻地持着胡须,一个儿童正在不断地向湖里那群“嘎嘎”欢叫的大白鹅抛撒谷粒。图中的白鹅伸着长长的脖子,高昂着头朝天欢叫。红红的脚掌在绿绿的水波中悠闲地划着。教学时诗画对照,相映成趣,为学生想象活动提供了丰富、鲜明的表象信息,学生很轻松地踏入了诗的意境之中。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结合画面说说生动活泼、天真可爱的白鹅形象,学生就不难表达了:那长着一身洁白的羽毛,有看两只红红的脚掌的鹅,在清澈浅绿的湖水中悠闲自在地拔掌前行,欢快的引颈高歌。此时水波荡漾,荷叶轻摇,荷花飘香…… 这意境是多美啊!为了引发学生们的参与意识和创造兴趣,也为了更好地理解诗意,体会诗境,我从二年级上学期起就鼓励学生根据诗意大胆想象,自己动手在白纸上为古诗《所见》、《绝句》、《小池》等配画,然后在视频上展示。一张张充满重稚的画面,展现了他们对诗意的理解程度,也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更让他们在诗的意境中受到了美的熏陶。通过为诗作画,反馈出他们对诗词的理解,调节了教学气氛,使学生学中有趣,趣中有美,美中有物。
二、品词赏句,体味诗歌的语言美
诗歌用词非常精炼,一字一词都经过作者的千锤百炼所至,因此抓住重点字词分析理解句意是古诗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传统的古诗教学采取的大都是“串讲法”。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解,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为之窒息,智力因而枯竭,学习成为负担。而多媒体能克服时空限制,通过形、声、光、色等形式,将抽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直观、形象、具体的视听文字,这样有利于学生抓住诗中的诗眼或者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词语,反复推敲、理解、体会语言文字的妙处。
三、运用多媒体帮助理解诗句的意思
由于古诗文的文字凝练,小朋友很难理解着背出,如让小朋友连大概意思都不知道死背出来,小朋友不仅背得吃力而且容易遗忘。适当的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帮助小朋友轻松的理解诗句的意思再背诵出。
如我在教苏教版一年级上册《江南》时,发现小朋友理解后五句有些困难,为了让小朋友能够轻松的理解其意思,在教学过程中我运用多媒体出示了一段这样的画面:一个长满了莲叶的池塘,池水清澈见底,池里的小鱼儿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一会儿游到了东边,一会儿穿到了西边,一会儿钻到了南边,一会儿又滑到了北边。通过引导学生观看多媒体动画,小朋友很快理解了古诗中“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后五句的意思且能很轻松的背诵出这首古诗。
四、运用多媒体指导练习朗读,对提高学生朗读诗歌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古诗虽然短小精悍,但意境深远,音韵和谐,读来琅琅上口,回味无穷。再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反复的诵读中,学生对诗的含义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和意会。而恰当地运用电教手段,则能有效地指导学生在感情地朗读古诗,并熟读成诵。
如我在教完《望庐山瀑布》后,播放了一段庐山瀑布的录像,让学生亲眼目睹了庐山瀑布的雄伟气势,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然后再让学生听配乐的课文录音,跟着录音练读。这样,学生读起来既感情真挚,又抑扬顿挫。最后,我把学生的朗读录下来,再放给他们听,让他们跟课文录音比一比,自己评一评。学生找到了差距,练得更欢了。而学生对这首诗的气势和内涵也在一遍遍的诵读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领会。
五、运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提高古诗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
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古诗教学,根据教学目标精心设计多媒体课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多媒体课件的精心设计和准备却极大地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课堂上,教师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在极短的时间里使学生看到清晰的画面、形象直观的视频、古诗的解释等。教师有步骤,有秩序地教学,从而避免手忙脚乱或顾此失彼,赢得了大量的教学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利用多媒体教育技术,教师在一堂古诗教学课中,既完成了诗句的理解、朗读、背诵和训练,又对学生介绍了作者的生平事迹和古诗写作的背景等,使学生提高了朗读水平,增强了审美情趣,也使学生对诗人、作品、古诗的风格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要想提高古诗的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就需要教师把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应用到古诗教学中。这样我们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
六、电教多媒体在古诗教学中发挥的其他的优势还很多
第3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关键词:“十大金曲”;“大”;语法化;量词特征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14-03
作者:王兴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重庆。万州,404000
“十大金曲”之“大”,就其词性来看,学界同仁迄今仍是看法不一,各持一端:有偏重于表达式中“大”所表示的形容词意义,而认为其词性仍归属于形容词者;但也有论者认为,该表达式中的“大”带有量词的一些基本特征,它有向量词发展的趋势。“数词+大+NP”表达式,在现代交际中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和习用。我们认为,在这种习用而特定的句法结构里,“大”不可能兼属两种不同的词性,而且学界各持一端的看法让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因而再次探讨表达式中“大”的词性问题,仍显得十分必要。
“数词+大+NP”表达式,其产生的历史较为悠久。许光灿《“十大金曲”之“大”不应看成量词》一文认为,“两汉之交,伴随着佛教文化的输入,形成了汉语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引进,为传播佛教思想,译者们在对译中尽量使梵文汉化,使之成为符合汉语习惯,‘数+大+名’格式正是这次梵汉对译中产生的一种意译外来词的重要格式。”大家知道,古印度的梵语(Sanskrit)被认为是一种只有名词没有形容词的语言,其修饰名词的属性词都是名词,具有名词的各种形态。而表属性的词与表属性的主体的词不但具有相同的形态标记和句法成分,而且在语序上也是自由的。“数+大+名”既然是梵汉对译中产生的一种意译外来词的重要格式,那么这种格式也就模拟和反映了外来词的一些基本特征,“数+大+名”中的“大”,也就对应地复制了梵语中“大”这个具有属性意义的名词。在类型学家看来,只有名词和动词两大类的一些语言里,不存在名―形―体或形―动―体的词类。属性概念常常是由语法上的纯名词或纯动词来表示。按照形态一句法标准看,梵语表示“黑”的词就象一个名词,表示“黑的东西”。同样,表示“大”的词也象一个名词,表示“大的东西”。因此梵语被认为只有名词词类,没有名―形同一的词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大”表示属性概念,但这种作为意译外来词的格式,其“大”就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形容词。
即便如许光灿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数+大+名”格式是“数+形+名”结构而不是“数+量+名”结构,那么我们认为这种表属性概念的“大”,其语法功能也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语法是不断地发展并进行着动态性变化的。功能语法的代表人物P.Hopper《浮现语法》认为,语法是动态的,是在使用中逐渐成型的。语法不是事先就存在的,而是在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中一些经常性的用法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产生或“浮现”的。语法的“浮现”观告诉我们,语言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大量异质的“构式(construction)”的集合,每个构式都是跟其使用的语境密切相关。“数词+大+NP”自汉代产生到现在的大量运用,其间历经了各种不同的时代。经过不同时期人们的反复运用和不断实践,这种格式中“大”的功能与属性也并非恒久未变。在认知、语用等诸要素的作用下,其悄然进行着语法的动态性变化,也经历着向量词演变的语法化过程。
语法化过程离不开语法化的主要机制。语法化的机制有两种,一种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一种是类推(analogy)。从认知的角度看,重新分析是概念的“转喻”。类推是概念的“隐喻”。二者遵循的原则有所不同:邻近(contiguity)是转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相似(similarity)则是隐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认为,“数词+大+NP”表达式中“大”所进行的语法化,其背后有人们认知动因在不断地起作用。在“大”向量词演化的过程中,人们的重新分析最为关键。所谓重新分析,是指一种改变结构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并不对表层结构作直接或本质上的修正。从根本上说,重新分析完全是听者(或读者)在接受语言编码后解码时所进行的一种心理认知活动,听者(或读者)不是顺着语言单位之间本来的句法关系来理解。而是通常在一定的诱因作用下,按照自己的主观看法作另外一种理解。这样一来,原有的结构关系在听者(或读者)的认知世界里就变成了另一种结构关系。拿ABC这样的语言组合来说。假如它本来的结构关系是A(Bc)。那么重新分析后,它的结构关系可能就是(AB)C。同样,“数词+大+NP”表达式,原来的结构关系是“数词+(大+NP)”,而通过人们认知解码便可变为“(数词+大)+NP”。我们对“大”与数词组合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大”更多地是与数字十以内(包括数字“十”)的单音数词组合。而十以内的数词与“大”恰好构成一个双音节的音步。受双音化的影响,两个经常邻近出现的单音词成分,就很容易地融合成一个复合体。这样一来,“大”与前面数词组合,时间一长便在人们心理认知上获得了一种“完型”的概念。此时的“数词+大+NP”结构,人们很难将“大”看作是后面NP的修饰成分,而更容易把“大”看作是被前面数词所修饰的词语。重新分析是“大”赖以演变为量词的前提基础和必由之路,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已经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量词。重新分析以后,“大”处于一个临界点上:前与数词结合构成一个复合体。而后又能与NP进行语义上搭配。这种特殊的句法环境,为“大”进一步向量词演化提供了条件。而我们知道,“数词+量词+NP”是汉语偏正结构的基本语义类型之一,其早已成为人们所习用的表达形式。受“数词+量词+NP”长期使用的影响,人们便以此为基础而对“数词+量词+NP”结构进一步类推和隐喻,于是与“数词+量词+NP”同形的“数词+大+NP”的结构,“大”就更容易被语法化为量词。类推和隐喻必须有比较具体的“意象――图式”,而这“意象――图式”的获取来自于已有的句法结构。如果没有汉语中“数词+量词+NP”结构的映射(mapping),“数词+大”结构的“大”便不会进行量词的语法化。
邵敬敏、吴立红《“副+名”组合与语义指向的新品种》一文曾分析了“副+名”的组合。认为副词在唤醒名词的属性特征时,其语义指向主要采用了语义斜指法、语义内指法、语义偏指法、语义深指法和语义外指法等途径和方法。其中的语义斜指法主要是针对“形语素+名语素”,所构成的偏正结构而言。这种偏正结构名词的语义核心,本来应该是中心语素,所以修饰语的语义原则上应该指向这个中心语素。例如“小红花”,“小”的语义应该指向“花”,而不是指向“红”。一旦当程度副词 跟名词组合时,却可以指向名词的非中心语素(即修饰语素)。如“很柔情”。“很”的语义指向不再是“情”而是“柔”。我们认为,这种语义斜指法也可以移植到“数词+大+NP”表达式的分析上。如“伤心事”,数词“八”以及后面的属性词“大”、“伤心”本当都将其各自的语义指向到了后面的中心词“事”,但由于数词“八”与“大”的长期组合和共现,使得二者在人们心理认知上获得了“完型”概念,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八”的语义指向就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其意义由指向中心词“事”而转为主要“斜指”在其后的“大”之上。这样一来,数词在语义上的斜指就有可能使得“大”获得量词的一些属性和基本特征。以此观之,一个词语是否发生语法化,很显然与该词语所处的句法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㈨。
英国的语义学家利奇曾把语义分为七种,把撇开“主题意义”剩下的六种语义分成了两大类:理性意义和联想意义。所谓理性意义是语言交际的核心意义,它是静态的,是其他语义的基础。如“大”的属性意义亦即利奇所指的理性意义。而联想意义包括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和搭配意义等多种意义。某个词的联想意义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可变的,是的意义,受到时代、社会、文化、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只能在与不同词语匹配构成的句法结构的组合中才能显示。随着“数词+大+NP”运用的日益增多,也随着“大”与数词长时间的组合和共现,受人们认知心理及交际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大”的理性意义之外便会自然地产生一些联想意义(笔者以为主要是搭配意义)。“数词+大+NP”中的数词,因与“大”长期组合便会唤醒“大”的一些量词特征,并使其逐渐吸收量词的一些词义。因而语法化以后的“大”。既有作为语义基础表属性的理性意义,又有了作为量词用法的联想意义。它既有“个、位、首、座”等专职量词的意思,又有“排名在前的”、“主要的”等属性意义。这时候的“大”由于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语法化,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形容词,而以量词对待为妥。我们认为“大”作为量词,其意义是量词意义做基本意义和属性词作附加意义的结合。比如“两个杀手”与“两大杀手”相比较,“大”除了量词功能外,还因为其具有“排名在前的”、“主要的”的含义而对其后的成“杀手”进行凸显和描写,而且在句法上对“杀手”还进行限制,形成偏正结构即“主要的杀手”。而象“个”、“位”、“首”、“座”等来自于名词的量词却没有这样的功能。“大”作为量词还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它几乎囊括了所有量词的词义属性和特点,避免了因称量对象的不同而对量词所进行的选择。如“四大佛教名山”,若不进行缩略表达应是“四座大的佛教名山”;“2000年十大金曲”,若不进行缩略表达当为“2000年十首排名靠前的金曲”;“十大年度词汇”应是“十个主要的年度词汇”;“我最喜欢的十大人民警察”当为“我最喜欢的十位主要的人民警察”等,象这种完全式表达往往需要依照不同的指称对象――“名山”、“金曲”、“词汇”和“人民警察”而分别选用专职量词“座”、“首”、“个”和“位”。而让“数词+大+NP”中“大”充当量词,就省却了选择专职量词这一过程的繁复。而且“大”作量词具有其他量词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会使“数词+大+NP”表达式信息量大,表达更为精练。这样既不影响人们对句意的理解,也更符合人们普遍遵从的经济达意原则。
语法变化是一种意义类型的转换,意义失去的同时也伴随着意义的获得。我们知道,一个词不管它原来的词性如何,一旦它进入量词队伍,它都要或多或少地会失去或改变原有意义而发展出概括性更强的语法意义。一方面,用作量词所表示的意义与原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另一方面也仍然同原词义有着或显或隐的一些联系。量词队伍更多地是由名词演变而来。大多数量词由于源于名词,因而这些量词本身仍然带有同本义有关的一些语义信息,如“一张纸”的“张”,含有延展的、平面的意思;“一条路”的“条”,有长形的意思。“一位学生”的“位”,也还有保存在“位置”里作为名词性语素的含义。而汉语中源于形容词的量词同样也保留了原来词义的一些信息或一些语义成分,而且这些形容词在充当量词以后,其所保留的原有语义信息要比名词用作量词以后所附带的原有信息要凸显得多。如“一弯月亮”的“弯”除称量记数以外,还保留有“弯曲、亏缺”的意思;“一碧秋水”的“碧”还含有“青绿”之意;“一丛图书”的“丛”还有“聚集”的含义;“五曲音乐”的“曲”还“婉转”的意思;“两团毛线”的“团”还有“会合在一起”的意思。“三方腊肉”的“方”还有“方形的”意义。这些量词因本身由形容词转化而来,其原来描写事物性状的功能在充当量词以后仍然在起作用,它们对“数词+量词”结构后面所跟的NP成分在语义上进行修饰和限定。如“弯弯的月亮”、“碧绿的秋水”、“聚集的图书”、“婉转的音乐”、“会合在一起的毛线”、“方形的腊肉’,等等。这表明由形容词转变而来的量词,不象由名词演化而来的量词那样在量词属性和特征方面显得更加纯粹。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弯”、“丛”、“碧”、“曲”、“团”、“方”等词具有量词属性而将其归入其他词类。
第4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从文化的角度讲,比喻的民族性与文化的相对性有关,文化的相对性又承认文化的多元性,特定的文化有其固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民族透过同一喻体的梭镜,会看到不同的价值折光。以“牛”为例,汉语中“牛”用作喻体时大多含有褒义。是“埋头苦干,勤勤恳恳”,“诚实”的象征。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做人民大众的老黄牛”等等。而在维吾尔语,以下简称维语中,“牛”具有“笨蛋”、“傻瓜”的负面象征意义。如:“Kali?aox?a?qarapturmaq(像牛一样看着)”、“Kalid?kd?tik?n(像牛一样笨)”等,显然两个民族心目中“牛”的比喻趋向及涵义不大相同。这种对同一喻体的褒贬态度天壤之别的现象,既反映了两族人民认识和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又折射出了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
比喻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本体相同、喻体不同
不同的民族立喻时,“用心有别,着眼因殊”,在表现相同的本体时,却使用不同的喻体。这主要是因为选择喻体的侧重点不同和思维或联想方式不同。不同的民族在表现相同的本体时,用不同的词语、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例如:维语中的“ti?a???pk?(铁锨帽)”在汉语中是“鸭舌帽”。对相同的本体,维语用“铁锨”,而汉语用“鸭舌”作为喻体,在两种语言中使用了不同的喻体;微长而窄,上部略圆,下部略尖的面庞,汉语形容为“瓜子脸”,维语形容为“atjyz(马脸)”;脚掌或脚趾上增生而形成的小圆硬块,汉语比喻为“鸡眼”,而维语比喻为“qadaq(疙瘩)”;女人特有的器官,汉语是“子宫”,而维语是“balajatqu(子位)”;山的接地的地方,汉语是“山脚”,而维语是“ta?ba?ri(山胸)”;下雨的感觉对任何民族是相同的,但对比较轻而细的雨,汉语比喻为“毛毛雨”,而维语比喻为“sim-simjam?ur(噌噌雨)”,不难发现,汉语比喻的侧重点为雨的形状,维语比喻的侧重点为雨的声音。再比如汉语的“窗口”,维语相对应的词语是“d?riz?k?zi(窗眼)”,比喻联想的差异在于“口”和“眼”之间的差距。人体器官设为喻体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描写同一种事物或现象时,语两种语言不一定选择同一种器官为喻体,汉语选择“鼻子”,而维语可能是“耳朵”。
汉语中的“日光灯”,相对应的维语是“no?u??iraq(面杖灯)”。相同的本体,两种语言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上建立起了不同的比喻联想。前者为“日光”,突出灯光的效果像阳光;后者为“面杖”,突出灯的形状像面杖。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可以窥见:维语比喻较之汉语的比喻,在喻体的选择上尚大忌小,尚直观忌抽象,或许这正是维吾尔民族朴拙大气的特点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无论是形象的选择,或者词语的理据性方面,两种语言在表现相同的本体时,具有独特的民族比喻特色。
二、喻义相同、喻体不同
比喻的民族性是与不同民族的生活经验、风土人情、习俗风尚、宗教、地理、历史、美学趣味等诸因素密切相关的,因此,不同民族在不同的事物中看到了相同价值的折光。对于相同的喻义,各民族人民“用心有别,各取所需”,从上述因素中寻找本民族不同的喻体来表示。例如:形容一个人胆子小,汉语用“胆小如鼠”,即“鼠”为喻体,而维语选用的喻体为“鸡”,“toxujyr?k(鸡心)”;汉语中形容某人特别瘦,比喻为“像猴子一样”或“骨瘦如柴”,而维语是“jin?jigenitt?k(像吃了针的狗)”或“j?ttiniky?ykli?anqan?iqt?k(像生了七个狗崽子的母狗)”;表示杳无音讯,很长时间见不到人,汉语是“杳如黄鹤”,维语是“altin?iajnipaqisid?k(像六月里的青蛙)”;表示多此一举,汉语是“画蛇添足”,维语是“pajpaqqanalaqaqqand?k(袜子上钉掌)”;比喻人的才能或仪表很出众,汉语是“鹤立鸡群”,维语是“??k?arisi?akiripqal?ant?gid?k(站在山羊群中间的骆驼)”;形容生活状况非常糟糕,汉语是“过着牛马生活”,维语是“itnikyninik?rm?k(过着狗的日子)”;形容记得非常牢固,汉语是“入木三分”,维语是“ta?qam?hyrbasqand?k(像石头上盖章子)”;形容铺张浪费,汉语是“挥金如土”,维语是“pulni?azaniornidax??lim?k(把钱当作树叶去花)”;表示不让任何人知道,汉语是“人不知,鬼不觉”,维语是“my?ykbalisinijiw?tk?nd?k(像猫儿吃小猫)”;形容一对夫妻门当户对,汉语是“龙配风”,维语是“altunyzykk?yaqutk?zmask?lg?nd?k(像金戒指配红宝石)”。又如,形容某事遥遥无期,不可能实现,汉语说“猴年马月”或“等太阳从西边出来”,而维语却使用迥然不同的比喻形象,“toxu?irim?a?ili?and?k(等到鸡啃树苗时)”。再有,汉语用“非驴非马”比喻什么也不象,不成样子,而维语用“jaaq?m?s,jak?k?m?s(即不是白的,也不是绿的)”来表示。从以上所列举的比喻中可以体会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性和文化渊源。汉语比喻中,“牛”、“马”、“鸡”等家禽畜类词汇较多,且对弱小的动物表现出爱怜、怜惜之情。维语比喻中,“骆驼”、“猫”、“狗”等与戈壁有关的词汇较多。在汉语中描写爱情,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鸳鸯”,而在维吾尔文学作品中,作为爱情喻体的还有杜鹃、百灵鸟、则纳甫,雀鹰等。
三、喻体相同、喻义不同
比喻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本体相同、喻体不同上,更多的是表现在相同的喻体所引发出的不同喻义。喻体相同、喻义不同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同一事物可构成性质不同的多种比喻,因为每一事物都有着多种自然属性。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利用该事物某种属性,生发出这个或那个相似点,使之与同一事物相联系,因而出现喻体相同、喻义不同的现象。上面“牛”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再以“公鸡”为例,在汉语中“公鸡”做喻体时一般比喻十分吝啬的人,如“铁公鸡”。而在维语中“公鸡”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却是“好斗”和“色鬼”的象征,如“?tidink??ki??xorazd?ksoqu?upjyrm?k”(整天像小公鸡一样和别人打架)”、“xotunki?inik?rsilaxorazd?kbazlapbaqqusikelidu(见到女人就像公鸡一样想调戏)”。再比如“火”,汉语用以比喻愤怒这似与五行之说有关,因肝属木,木生火,由此有“大动肝火”、“肝火正旺”等说法。而在维语中一般把爱情或热恋的气氛比喻为“火”,因此,汉语中的“火气大”与维语的“otujaman”虽然是同一词语的对应形式,但完全表示不同的意思:汉语比喻为暴躁的脾气,而维语比喻为爱情的魔力。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比喻作为一种能使语言更真切、更生动的修辞手段,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郁的民族特点。由于两种语言所蕴涵的文化、地理环境及语言体系大不相同,使用这两种语言的民族在观察事物和表达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表达手段——比喻,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研究这些特点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文化内涵,对于双语教学和互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新世纪汉语规范词典》编委.新世纪汉语规范词典(增补本)[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新疆大学中国语文系.词典[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3]王振本.艾力·阿比提.维吾尔成语词典[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4]陈许.英汉比喻的民族特点初探[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04).
第5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一、课堂生成的资源化
课堂是一个五彩的世界,是一个千变万化的阵地。农村学生的思维虽然不如城里学生那么有条理,但其中也不乏智慧的火花,只要教师善于把握,一样会让课堂出现耀眼的光环。如果我们认真地把它们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来处理,会为语文教学挖出一个宝藏。在教学《隆中对》一文时,我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所了解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小学学过《草船借箭》这篇课文,主要讲诸葛亮忽悠了周瑜。”一语既出,满堂哄笑。我当时眼前一亮:这个学生不一般,这个答案不一般,这个“忽悠”不一般,不能仅仅一笑而过。细究之下,“忽悠”这个词这几年很流行,学生受社会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不过,这个词一般是用在开玩笑的话语中,不能用在一些庄重的场合,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位同学用一种自己的独特理解来活用生活中的语言,是一个积极学习语言的好例子,一定要保护这个同学学习语言的积极性,但又得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首先对这位同学进行表扬:“不同凡响,匪夷所思,思维活跃。但同学们为什么笑你呢?”这位同学回答不上来。我便让那些发笑的同学来说说意见。终于有一位同学说:“‘忽悠’这个词含有玩弄的意思,用在这里有些贬低了诸葛亮。”这位同学想想,也自觉不太恰当,笑了笑,脸上有些微红。我提示他,能不能把“忽悠”这个词换换。后来他就想到用“制服”。大家都觉得比较满意。这样处理,既保护了这位同学的积极性,又让大家学习了语言的使用,明白了语言文字的感彩,可谓“一箭双雕”。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仿写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学生仿写往往思维受局限,这就要指导学生从生活中取材,让学生活学活用,有的学生就能学以致用,为其他同学开辟一种新的思路。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课,文章中有一个关联句:“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我让学生用关联词“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造句。一个学生造了这样一个句子:“不必说巍峨的崂山,也不必说具有国际化大城市气派的东部,单是那小小的百花园,就有无限趣味。”我听了后,大加赞赏:“能把课堂学过的内容结合实际生活恰当的用关联词联起来,这是一种高明的创新。”从此以后,我经常让学生针对课文的具体情境进行仿写。有了前面的经验,学生仿写起来就游刃有余了。
二、教师角色的多重性
什么样的课堂受学生的欢迎,什么样的课堂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是课堂教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语文教学是一台戏,教师只有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提高这台戏的质量,然而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往往越俎代庖,代替学生思考或代替作者言论,这不是语文教师应扮演的角色。语文教师应在学生与教材之间扮演桥的角色。在阅读上教师应做打开学生阅读视野大门的钥匙:1.培养阅读兴趣,要给学生阅读自由。2.做好阅读指导,如怎样选书,怎样看书等都要做认真指导。3.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如每天定时阅读的习惯,记读书笔记的习惯,阅读中提问题的习惯等。在学生人文精神的渗透上教师要做艺术感染的天使:首先是情感上要丰富而真诚,其次在言行上要有风度,最后语文教师要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在创新精神上,教师做学生的开路先锋。
三、词语的具体形象化
无论是谁,都应当承认学生学习语言时的个体差异,但学生对具体的事例都怀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中国的历史悠久,典籍典故浩如烟海,即便是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教师,也为我们让词语具体形象起来提供了足够的来源。讲革命先烈的乐观主义精神时,我为了让学生明白什么是乐观,讲了这样的事例:“有一个石学士,此人心胸宽广,做事不拘小节。有一次,他乘车外出,由于他的车夫不小心,马惊了,把他一下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车夫心惊胆战地扶起他,请求他饶恕自己。这位石学士说:‘幸亏我是石学士,要是瓦学士,这会可惨了。’”同学们听了后都哈哈大笑。我进而告诉学生,乐观就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仍然开朗笑对。
四、每篇课文都有一个亮点
这种想法,源于我自己的一次教学实例。在讲《精彩极了,糟糕透了》这篇文章时,我当时设置了一个句子的重点理解:“七点一刻。七点半。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表现出很纳闷的样子问学生:“只有一个词,作者却都用了句号,作者是不是用错了标点符号?如果没有用错,那么哪位同学能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在我的引导下,一个学生补充道:“我在客厅里等着父亲,一看表,已是七点一刻,但是父亲没有回来。又等了很长时间(这是作者的感觉),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我又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七点半了。”其他同学也是类似的答案。我紧接着问:“从这几句话你体会到什么?”学生用本课的成语“迫不及待”来回答。我又让学生读这几句话,学生的兴趣明显地高涨。读书的热情高涨。几遍下来,几乎人人能熟读成诵。紧接着我又出示了两篇文章《诺曼底号遇难记》《地震中的父与子》,让学生找出与此相似之处,以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我们期望语文教学能立竿见影,学过的好东西能成为学生的东西,那么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必然指日可待。这节课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鼓舞:抓住课文的一个亮点,让学生在幡然醒悟中欣喜地发现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这样他们就会过目不忘,就乐于学着应用。
在后来的教学中,我就尽力在每课中找出一个有特色的地方,让学生思考,研读,体会,做到“质疑——豁然开朗——喜爱——成诵。”
第6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一、课堂提问的作用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是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的重要场所,所以教者应以课堂为着力点,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针对性。因此,教师应注意课堂提问的技巧,做到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良好的教学提问技巧能增强课堂的凝聚力,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如在教学《故乡》时,针对开头写景部分,笔者创设了以下问题情境: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是什么样的景象?那些传神的语句映射出什么境况?描写故乡的词语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情?这种提问环环相扣、切中关键,使学生对文中的理解更深入。由于设问自然、层层递进,学生的注意力会集中指向对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从而有效提升了课堂教学的实效。
教师潜心研究教材,精心设计新颖的、有挑战性的教学问题,可以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我的老师》一文时,分析蔡老师写信援助了“我”这件事的详细原因时,笔者问学生:大家发挥聪明才智想象一下,假如你是蔡老师,在信中对受委屈的小魏巍可能说些什么话呢?话音刚落,学生就开始热烈讨论,他们学习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想象的闸门也打开了。然后学生从各自的体会中解释了为什么对此终生难忘,表达了这件事要详写的道理。在教学中,教师让学生感受到所提问题蕴含的趣味,就能激发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欲望。
二、课堂提问遵循的原则
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其受益者是学生。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师生角色互换,设计问题应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充分体现课堂提问的针对性、系统性、桃战性。具体来说,课堂提问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难易适度。教师设计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问题的难易程度,设计的问题难易适中,要避免过难或过易。如果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不假思索就能对答如流,这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也会使学生养成浅尝辄止的不良习惯。
2.有系统性。人的认识活动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即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所以教师提问也应如此。如在教学《捕蛇者说》时,我设计了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既然永州的蛇其毒无比,永州人为什么还争相捕蛇呢?二是蒋氏捕蛇,三代遭难,为什么还不愿“更役”“复赋”?三是从永州捕蛇民众的悲惨境遇中可以看到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这三个问题能让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课文内容,得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结论。这种提问就像一个链条,环环相扣、步步深化,能够有效地训练学生思维的系统性,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课文。
3.富于启发性。优秀的提问必定含有启发性,对于所提的问题,学生经过认真思索,总会有所收获。富于启发性,就是要求教师设计的问题能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他们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对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课堂提问的形式
课堂提问作为教学的一种手段,是灵活、复杂而多样的。因此,教师的课堂提问要因文而异、因人而异,在方法上力求灵活多变,不能通篇使用一种固定模式,这就是“大体须有之,定体则无之”。下面概述一下课堂提问的几种常见形式:
第7篇:含有绿的意思的词语范文
关键词:性质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有界 无界
名词的界限特征凸显事物的空间界限,动词的界限特征凸显动作的时间界限,形容词的界限特征凸显事物的程度界限。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一般认为两者的界限特征呈对立状态。形容词在量上有量幅和量点之分。性质形容词表示量幅,具有无界特征;状态形容词表示量点界限,具有一定的有界特征。(,2007:428)
性质形容词的界限特征和状态形容词的界限特征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无界的性质形容词可以转化为有界的状态形容词。如:
重 叠:长长的 高高的
带后缀:火辣辣 红通通
程度副词+形容词+的:挺漂亮的 非常脏的
通过添加附加成分,无界的性质形容词可以转化为有界的状态形容词。有界的状态形容词也可以通过去掉附加成分转化为无界的性质形容词,如:“雪白”可以转化为 “白”。
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的界限特征的对立,直接影响到二者的句法分布和语义特征。
句法上,状态形容词如“雪白”“绿油油”等,不可以受“很”“非常”等程度副词的修饰,也不可以加“不”等否定副词;性质形容词则相反,可以受“很”“非常”等程度副词的修饰,也可以加“不”等否定副词。如:
*很雪白 很/非常白
*不绿油油 不白/绿
“很”“非常”“不”等副词具有无界倾向,和无界成分同现自由,限制条件少,与有界成分同现不自由,限制条件多。“雪白”“绿油油”等状态形容词具有有界特征,与“很”“不”等无界成分同现不自由。并且,状态形容词本身已经表示一定的量点界限,不需要再借助程度副词表示量点界限。“白”和“绿”等性质形容词具有无界倾向,可以自由地与无界成分同现。此外,性质形容词加上“很”“不”以后,如“很白”“不白”,便在认知心理上具有一定的量点界限,与普通的“白”区分开来,具有弱式有界倾向。“不”对性质形容词的否定,并不是否定形容词所表示的性状没有出现,而只是表述该性状的程度尚未达到某性状主观或客观的标准。如:“这个西瓜不甜”表示“甜”的程度不高,没有达到说话人主观预想的“甜”度,并不代表“西瓜是苦的”。
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都可以作定语和谓语,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沈家煊曾论证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充当句法成分时的特征。他将形容词和句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标示为如下的关联标记模式:
定语 谓语
性质形容词 无标记 有标记
状态形容词 有标记 无标记
据此,沈家煊得出结论:性质形容词更倾向于作定语而不是作谓语,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更倾向于作谓语。(沈家煊,1997)
关于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作定语和谓语的区别,同样也可以用“有界―无界”的概念来解释。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性质形容词的匹配度高于状态形容词。这主要是因为“定语的典型语义特征是时间、空间、程度量的零赋值,具有无界性;凡是句法上时间性、空间性和量性特征固化的有界词语均遭到排斥。”(张国宪,2000)因此,无界的性质形容词作定语比较自由,有界的状态形容词作定语不自由,限制条件比较多。如:
凉水 冰凉的水
大眼睛 大大的眼睛
白羽毛 雪白雪白的羽毛
干净衣服 干干净净的衣服
性质形容词作定语可以不借助于助词,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而状态形容词需要借助助词“的”作定语,去掉“的”结构则不成立,不能说“*冰凉水”“*大大眼睛”“*雪白雪白羽毛”。
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修饰名词作定语时,加“的”可以使本来不成立的结构成立。如:
A B C
*大一双眼睛 大(的)眼睛 大大的一双眼睛
*脏一碗水 脏(的)水 脏的一碗水
*干干净净衣服 干净(的)衣服 干干净净的一件衣服
沈家煊(1995)曾指出,“的”的作用不可小看,它具有使无界变成有界的功能。A列结构不成立,是因为无界成分与有界成分直接同现,但是,句子同为无界成分(如B列结构)或同为有界成分(如C列结构)便可以成立。性质形容词“脏”是无界成分,“一碗水”是强式有界成分,二者不可以在直接成分中同现。要使结构成立,可以去掉数量成分“一碗”,这样无界名词“水”就可以同无界成分“脏”同现;也可以加“的”,这样“脏的”便成了弱式有界成分,可以与强式有界成分“一碗水”同现。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时,受到的限制条件不一样。如:
A B C
绿绸子 ?绿庄稼 绿油油的庄稼
脏衣服 ?脏糖 脏兮兮的糖
香花 ?香饭 香喷喷的饭
认为,这种差异与信息详密度有关。性质形容词所激活的信息是粗线条的,信息量比较低;状态形容词所激活的信息是细节信息,信息量比较多。B列结构不成立,是因为性质形容词信息量低,被修饰的成分表示的事物某方面的特征客观上不突出,显著度不高,那么这种结构就难以激活。而状态形容词的信息量多,被修饰的成分表示的事物某方面的特征客观上比较突出,显著度比较高,这种结构易于被激活,如C列结构。(,2007,428-433)
张国宪认为,性质形容词直接作定语所受的限制既不是意义上的,也不是语法上的,而是与交际功能有关。性质形容词的主要交际功能是区别,区别是以具有分类的可能为前提的。如“庄稼”一般都是绿的,“绿”便不具备区别作用;而“绸子”有不同的颜色,“绿”只是其中一种颜色,此时的“绿”便具有区别特征。状态形容词的主要交际功能是描写,表现个体事物的状态,是对状态的程度加细。如“庄稼”要凸出程度上的“绿”,便用状态形容词“绿油油”。(张国宪,2000)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同样可以用“有界―无界”的概念来解释。A列结构中,被修饰的成分是特指的,用来区别其他种类的事物,在认知心理上具有很强的有界倾向,影响到前面的性质形容词,便弱化了其无界倾向,结构可以成立。对于B列结构,被修饰的成分虽然也有特指意味,但不能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被修饰成分的有界倾向不能弱化性质形容词的无界倾向,整体结构不符合认知心理习惯,不能成立。把B列结构转换成C列结构之后,认知心理上感受到的不是与其他事物区分开,而是被修饰成分程度的加深,这主要归功于状态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具有很强的有界特征,其有界倾向又加深了被修饰成分的界限特征,“的”的使用也帮助加强了结构的有界倾向,有界成分和有界成分组合,符合认知心理习惯,可以成立。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作谓语时,状态形容词的匹配度高于性质形容词。这是因为,谓语的典型语义特征具有有界性,与状态形容词的有界性相吻合。沈家煊(1995)指出,性质形容词是无界的,不能单独作谓语,作谓语总是含有比较或对比的意思;状态形容词是有界的,可以单独作谓语。如:
人小心不小。 个儿小小儿的。
昨儿冷今儿不冷。 今儿怪冷的。
我比去年高了三公分。 我要长得高高的。
可以看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自身的界限特征造成了二者作定语和谓语的区别:具有无界倾向的性质形容词与定语的典型语义特征相吻合,二者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关联;具有有界倾向的状态形容词与谓语的典型语义特征相吻合,二者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关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界限特征呈对立状态,分别影响制约了二者的主要语法功能,性质形容词主要承担定语的功能,状态形容词主要承担谓语的功能。
总之,“有界―无界”这一概念是人们在一定的认知域上对词义的一种理解。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解读,能够帮助我们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句法分布和语义特征的对立。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4BYY1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沈家煊.“有界”与“无界”[J].中国语文,1995,(5).
[2]沈家煊.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J].中国语文,1997,
(4).
[3]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J].中国语文,2000,
(5).
[4]姚占龙.现代汉语状态形容词量级差别考察[J].语言研究,
2010,(4).
[5]李思旭.“有界”“无界”与补语“完”的有界化作用[J].汉语
学习,2011,(5).
[6]高笑可.“认知语言学”再思考[J].语言与翻译,2012,(3).
[7]胡振远,李浓.述评词的“有界”与 “无界”对语法结构的影
响――读沈家煊 《“有界”与“无界”》[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8).
[8]蒋岳春.“界”理论对词类的解释力[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13,(3).
[9]李劲荣.现代汉语状态形容词的认知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10]沈家煊.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11].认知语言学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