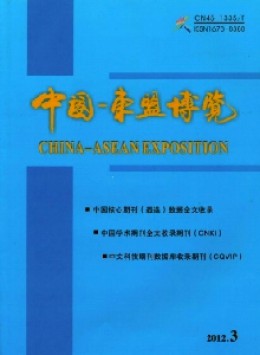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史论结合;教学实践;应用;材料论证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041
一、史论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看近6年全国卷第41题回顾:
2011年(课标卷)试题内容:欧洲崛起的方式。试题设问:“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2012年(课标卷)试题内容:中国近代化的动力。试题设问:“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2013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东汉、唐代地方行政区划方式的比较。试题设问:“在两幅图片中提取两项有关汉唐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太和殿与英国王宫、首相官邸建筑风格之间的比较。试题设问:“提取图片材料中的信息,从建筑和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2014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关于内容的教材目录,试题设问:“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理由”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关于世界近代史相关内容的两幅教材目录。试题设问:“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
2015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公式,试题设问: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公式进行探讨。”
(课标Ⅱ卷) 试题内容: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状况,指出其中我国节假日的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2016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启蒙思想及实践。试题设问: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论题并阐述。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试题设问: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史实加以论述。
从近6年的全国卷的41题中,我们发现对学科素养中史论结合的能力考查更加突出了史论结合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这种突出史论结合题型的小论文的能力呢?成为高中教学实践中的难题?
二、从高考真题实践演练探寻方法指导
例:(2011年湖南卷,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w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1. 了解试题类型,明确观点,有的放矢
选择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表态。如赞成第一种观点或赞成第二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既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2011年41题:我认为,西方的崛起首先归功于自身的创造,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其他文明的成果。故此,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原因的表述不完全正确,论据及说明如下:
2. 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的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我们熟悉的丰富的史实出发去论证观点,这样降低我们论述的难度。如近代西方通过自身的全方位社会革命而加速了崛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全球霸权的建立。通过大航海和一系列殖民扩张,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化。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3. 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结构。
4. 了解评价体系,分层论证,逻辑严密
5. 史论结合的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检测
(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
(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
(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 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
B. 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参考文献:
第2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
官方不重视数学教育,是数学发展停滞、数学知识难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周朝,数学曾被列为“六艺”之一,规定为贵族子弟在学校学习的必修课程。唐朝武则天时很重视数学,将九章和其他九部算经规定为国子学的必修课,并将数学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宋初曾效仿唐制,后因战乱,时兴时废。但是在唐朝中,数学虽被视为“通儒”的一项,但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8]有知识的人不能以数学为专业,这就大大妨碍了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
三、医学的传播
中国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传统科学。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论体系,至今还在医学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历代医学尊为经典的《黄帝内经》,仍然是今天中医的必读教材。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古代科学领域中,虽然中国医学作为硕果仅存,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当时“中医不科学”的贬辞也随处可闻,一些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声言不信中医,或者不请中医看病。
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特别是在它的基础理论中,确有不科学或不够科学之处;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发达的今天,继续发挥很好的作用。能否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种矛盾现象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呢?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阴阳、五行——在实践中可视为一种传播符号
阴阳本是古人解释自然现象的一对概念,进入中医学以后的阴阳学说,成为用来解释人体腑脏生理以及诊断、治理和处方用药的一种说理工具。春秋时期的医和认为,人致病原因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他还说,“阴寒疾,阳热疾”。意思是阴气太盛使人患寒病,阳气太盛使人患热病。这种理论很难用今天的科学原理来说明它,但它本质上是唯物的“气”一元论,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阴阳是一组对立的属性,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时还是互相消长的,即所谓的“阴消阳长”、“阳极反阴”、“阴极反阳”,可见,阴阳学说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矛盾的认识,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至于阴阳学说后来为儒、道家所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宗教迷信服务,则自当别论。
阴阳学说用到医学理论中,虽然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在诊断和用药归类上,起了至今仍然无法否定的作用。人体在生理活动过程中,物质与机能之间,必须经常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如果阳气(如热能)与阴质(如体液)在消长过程中不能保持这种平衡,就会产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从心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化。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就是这个意思,[9]治疗时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理论是阴阳学说具体运用到医疗实践中时用得最多的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阴阳,还是寒热,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现为对病理现象的分类,起到类似标记和符号的作用。虽然这种阴、阳、寒、热,很难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做细致的描述,更难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种相同特征的病理归为一类,如寒症或热症,然后对症治疗,就不能抹杀其科学性。与此相匹配的是,中药虽然多达数千种,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阴阳加以概括。中医药性分为寒、热、温、凉四类,温热药属阳,寒凉药属阴。所以,虽然阴、阳二词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热有时也难以区分,更难以定量,但它们作为一种符号,用以标识同一类病理,或同一类药物,这在医疗实践中是有意义、起作用的、这是2000多年的医学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中国医学还把古人的五行学说搬到医学理论中,五行即古人所认为的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搬到医学中来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别以肝、肺、肾、心、脾代表之。五行说在医学中的应用,不乏牵强附会和主观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机械循环论的成分,但其积极意义是,它强调人的脏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于医疗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医学中,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渗透一切的证明,没有带来多少新的实质性内容。剥去其神秘主义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脏,只不过是一套新的术语、新的符号而已。甚至于中医学中的肝、肺、肾、心、脾,也分别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号,它们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肝、肺、肾、心、脾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后来的解剖学证明,某一功能并不是这一种脏器所发出的。因为这个符号标识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确指某具体的脏器。比如,中医学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谓“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说法。而解剖学证明,心脏根本无此功能。
(二)药物学的积累式传播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被奉为中药学经典。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中国所使用的药物,绝大多数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为多,故中国古代药物学著作,几乎都称“本草”。自汉至清,“本草”传之不绝。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出现于汉代。该书共载药物365种,是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发现的药物又整理出365种加进去,编撰成《本草经集注》。唐、宋时期,朝廷曾组织专人整理修订中药学书籍。唐代苏敬等人编写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比西方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明代李时珍“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该书52卷,共载药1892种,绘图1160幅,这一巨著对我国医药学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清代的赵学敏又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补充药物716种,编成《本草纲目拾遗》,共载药2608种。[10]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的药物学,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断丰富补充前人的著作的结果。它靠知识积累,滚雪球式地传播到今天,堪称源远流长。
(三)借注经立言,严重妨碍医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也确立了它在中国医学中的经典地位。堪称经典的,还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等权威著作。历代著名医家,借经典立言,著书立说的比比皆是。这种注释经典的风气对医学界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认为,不注经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国医学虽然历史很长,学术争鸣空气却不浓,大多跟着经典走。医学史上的金元各家学术争鸣,对丰富和发展医疗方法颇有成就,但是这样的争鸣并不多见,特别是与经典著作争鸣更无勇气。明清时期,温病(属于急性外感热性病范畴)的研究比较热。一些医家,在总结既往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温热病的发病原因和诊治等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后来研究记性热性病的治疗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不过有的温病学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勇气申明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已经突破前人的论述,反而强调他们的见解,都是符合‘经旨’时,因此在某些论点上,难免出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个医家著书立说,都唯恐别人指责没有经典上的根据,就使得中国医学只能套着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国医学起步早,发展慢,基本理论体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国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几门科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为例证,研究了中国古代科学传播的状况及特点、从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难以存在,其科学就难以发展。
所谓逆向思维,就是传播跟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相左的看法与信息;对于科学的某一领域来说,就是传播与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或者权威性观点不同的意见与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阴阳五行这类官方意识形态,是不可以挑战的,学者总是试图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印证它们。中国天文学尽管历史悠久,积累的观测资料举世罕见,但始终笼照在神秘主义气氛中,出于对天的敬畏,不能客观地解释天文现象,所以除了为制定历法服务以外,就是把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作“预测”吉凶的根据,天文学差不多成了占星术的附庸,自然也就产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论。
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学科,逆向传播也常常困难重重。某一权威著作被奉为经典以后(特别是在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肯定以后),与之向左的科学观点就很难露头。中国传统文化有的注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者不敢偏离主流,另辟新径的表现。当然注经也有其必要的、积极的一面。有的学者有了真知灼见,却因与传统观点不同,也以注经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离经叛道者历来很难得到承认,还可能受到打击和迫害。
清朝有个医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他对经典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家、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与动物内脏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有不符,遂将42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他的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但是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却遭到冷嘲热讽,他被讥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对他的《医林改错》很长时间不予承认,幸得当时的西学东渐之风,未闻王清任受到迫害。
图为王清任在观察人体脏腑
毫无疑问,当一个社会中,学者随时心怀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之忧,就很难有划时代的科学理论提出,更谈不上爆发科学革命。
长期的封建专制秩序何封建正统观点,养成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学传播的困难。比如要学习西方数学,除了接受阿拉伯数字和其它一系列数学符号以外,书写形式上采取横写也是不可少的,这种书写方式在利玛窦来中国时已经带来,例如利玛窦、李之藻编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横写的汉文数字来介绍西方笔算的。但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像梅文鼎这样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还坚持使用老符号,并且又改横写为竖写。[12]只是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摧毁以后,中国才扫除了接受近代科学传播的障碍。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无、科学无国界等有利于科学传播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连载完)
注释:
[1] 顾炎武《日知录》。
[2]《史记·历书》。
[3]《史记·历书》。
[4]《史记·历书》。
[5]《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38年。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7]《颜氏家训》。
[8]《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290页、30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实用中医学》,第27-30页,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校编,1981年。
[10] 同上,第19页。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