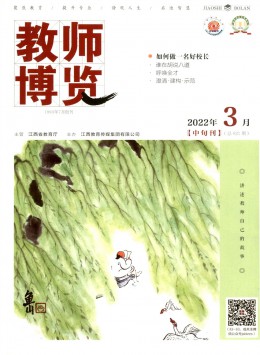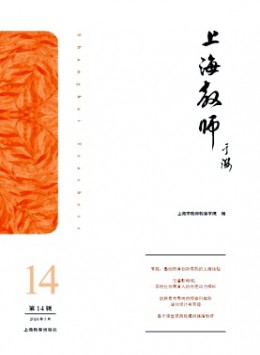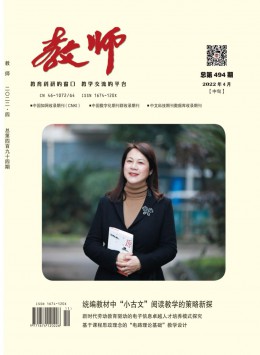教师节小短句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教师节小短句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教师节小短句范文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特征。消费者的“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是产生“阶段性消费”现象的微观基础;而“谦和、低调、面子、攀比、群体规范、风险厌恶、风险敏感、节俭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则又是“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形成的根源。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这样,一方面由于“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人们注重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另一方面“节俭”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美德,在这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形成了“过度自我控制”的认知偏差,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保守、谨小慎微,消费抱有负罪感/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的“保守消费”特征。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阶段周期,每一个阶段周期内都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低消费倾向”现象。
第2篇:教师节小短句范文
摘要:本研究通过课堂录音的方法,对六位综合英语教师课堂上的提问情况,即提问的类型、语言特征、交互方式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综合英语课堂教学仍存在某些问题与不足。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综合英语;课堂提问;问题;建议
一、引言
提问是英语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交流的重要方式。教师精心设计的高效课堂提问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为语言习得者的最大语言输出创造机会,使教师及时获取教学反馈信息,还可使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锻炼自身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熟练运用语言等能力。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六位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师。综合英语精品课为期五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品课建设项目之一。这六位英语教师都是课题组成员,担任本科英语专业综合英语的教学任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然调查法,即研究者在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对自然发生与发展中的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本研究借鉴了陈计庄、张菁的研究方法[1]。
研究者在综合英语精品课课题组十一位成员中,随机抽选了七位教师。并请他们各自所代班级的一位学生,在任课教师毫不知情时进行随堂录音。每位教师录音两小节课,100分钟,七位教师共计14小节课,700分钟。研究者对录音资料进行了编码及处理。
三、结果分析
(一)类型及分配比例
教师课堂提问是教师用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的口头回答、了解及评价学生的学习进展而进行的一个启发。Long 和Sato[2]经过系统研究,把教师的提问明确地划分为两类: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即限答式问题和非限答式问题[3]。展示性问题是用来检测学生知识的问题。教师在提问时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提问的目的是检测学生是否知道问题的答案。而参考性问题重在意义交流,教师在提问时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对于学生的回答也无法预料,学生可以自由发挥,各抒己见。
表1统计了六位教师在各自综合英语课堂上所提问题总量和不同类型问题的分配比例。统计显示,展示性问题平均占提问总量的536%,最高的一位教师占到862%,而参考性问题平均占464%,最少的一位教师只占138%。这些数字说明,课堂提问仍然以展示性问题为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桎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削弱他们独立思考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综合知识能力。
可行性建议:教师在做课前问题设计时,应该全面考虑,将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紧密结合,尽量少提展示性问题,多提参考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运用语言知识,表达自己思想,提高语言交际能力的机会。
(二)语言特征
本部分通过统计英语教师课堂提问时使用的汉语和英语的比例、教师问题的语法准确性、教师问题的平均句长,并对这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探讨英语教师是否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以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Krashen的“输入假设”认为,对语言输入的理解是语言习得最基本的途径。因此,语言教学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使语言习得者尽可能多地接受可理解的输入[4]。
1.汉英语比例
数字显示,课堂上英语教师主要使用英语,平均占问题总量的663%,最高的一位教师占971%。这说明课堂上英语教师有意尽可能多地使用目的语,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可接受输入。
2.语法准确性
表中数字说明,教师课堂提问时语法错误很低,仅占23%,最低的一位教师只占08%,教师为学生提供了有利的语言环境。Van Lair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应创设支持性的语言环境,以利于学生语言习得[5]。录音文字稿显示,教师课堂提问时大多使用短句,问题短,句法结构简单,这不利于学生的语言习得。
可行性建议:课前设计课堂问题时,在保证问题明晰并易于被学生理解的前提下,教师应有意识地增加问题中的语言难度,适当增长问句的长度,加大语法难点,为学生提供较为理想的语言习得环境。
3.长度
统计数字表明,最长问题有15个单词,最短为1个单词,平均为69个单词。分析结果说明,教师所提问题的句法结构简单,难度小。这一结果也解释了表3中的统计结果,教师所提问题的语法错误少,主要是因为教师所提问题的句法结构过于简单,这不利于语言习得,应引起教师的注意并加以改正。
(三)交互特征
本部分统计讨论教师课堂提问的交互特征和答问形式,旨在讨论综合英语课堂教师提问的交互特点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语言习得。
1.交互调整特点
课堂提问具有维持教师与学生交互的功能,是对话双方分享对同一事物的设想和辨别[5]。最重要的三种信息调整方式为:理解核实、澄清请求、确认核实。Long 和Chaudron给其定义如下(周星、周韵)[6]:
(1)理解核实:指说话者询问对方是否听懂了自己说的话。
(2)澄清请求:指说话者要求对方提供更多的帮助,使自己弄懂对方所说的话。
(3)确认核实:指说话者核实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表5中的数字显示,教师使用最多的交互调整方式是理解核实,占636%,而很少使用澄清请求,只占147%。综合英语精品课教学内容多,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只有使用理解核实才能控制整个课堂教学的节奏,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可行性建议:确认核实和澄清请求在课堂提问中必不可少,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意义协商机会,有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继续,并能给学生更多的可理解语言输入。短期内会影响教学进度,但坚持下去会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英语水平。
2.答问形式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答问形式主要包括:集体回答、指定学生回答、学生自愿回答、教师自问自答、没有回答。
表6中的数据说明,课堂上教师偏向使用学生自愿回答和集体回答,各占问题总量的345%和334%,整体情况比较良好。指定学生回答比例只占169%,教师自问自答达到12%,只有3%的问题没有回答。课堂上学生满堂吼和自愿回答可以为教师节省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但也说明教师没有很好地做到“因人施教”。
可行性建议:教师课前设计问题时,应当全面考虑,针对不同的学生设计多样化的问题,集体回答,指定回答,自愿回答,教师自答和不用回答交替灵活使用,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各取所需,扬长避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四、结语
本研究因为调查的样本较少,并只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定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说明所有大学综合英语课堂提问的情况。但通过本次定量分析研究,至少可以发现目前综合英语课堂提问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希望本研究及提出的可行性建议对从综合英语教学的教师有所帮助。(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本论文为新疆大学院校联合课题:“英语专业精品课课堂教师话语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Y080230
参考文献:
[1] 陈计庄,张菁.大学英语课堂教师提问特征调查研究[J].江苏教育研究(理论版),2008(5):58-62.
[2] LONG M, SATO C. Classroom foreigner talk discourse: Forms and functions teachers’ questions [C]// Seliger H, Long M. Classroom oriented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3:280.
[3] 赵晓红.大学英语阅读课教师话语的调查与分析[J].外语界,1998(2).
[4] KRASHEN, R.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in classroom language learn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1984(5).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