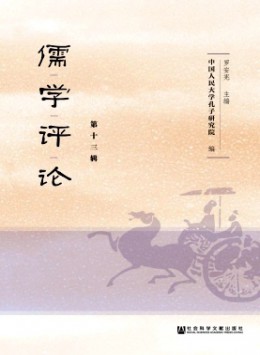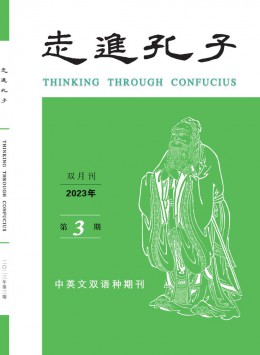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范文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论语・子路》),因而提倡“中庸”之道,实质是强调会通或贯通。孔子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见《论语・里仁》),用一个“仁”字将其贯通起来,这不仅指他对于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而且有他自己在春秋末期的独立创造。
中国早期儒家学说多处体现出“会通”精神。举一例:《礼记・礼运篇》(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著作)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也含有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主要源出于儒家,同时也吸收了墨家和道家之长,而非一家之专利,这就是会通精神的体现。
庄子认为诸子百家学说“多得一察以自好”而形成的主张。司马迁发挥了这个观点:“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各家各派立论不同,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于真理的探索,有助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面对西学东渐,明代学者徐光启在1631年上呈崇祯皇帝的奏折《历书总目表》中陈言:“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于是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就开始了。
重读中华文明史,不难发现会通精神表现出五大特点:会通致远、会通致大、会通致深、会通致精、会通致新。
会通致远。这就是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使之“与时偕行”。
道家在批评儒家过分夸大了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人学”有长处。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即所谓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方面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会通儒、道思想的特色。
会通致大。这就是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它,并吸收它的优点长处,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中,同时促进了儒、道、释的会通,由此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并不回避各种论点的相互辩论,如北宋时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就对当时关中学者张载提出的气与理的关系进行批评,认为张载把“太虚”和“气”视为世界的本原,是用有形的可感的东西代替了无形的不可感的本质,这种批评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会通致深。也就是说,“会通”需要有长期艰苦的研究,开拓学术视野,在不同思想观点的论辩中才能逐步达到这个境界。
这里不能不提到唐末五代出现的书院,书院经北宋初步建立,至南宋迅猛发展。这种由私人主持的讲学场所,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成为它的特征之一。由此,书院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智力资源和交流平台。南宋时期的朱熹理学学派,会通儒、道、释,以及产生陆象山“心学”学派,至明朝被王守仁发扬光大,都在书院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朱熹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将儒、释、道“三教”会通在以儒家为框架的思想体系里,成为所谓“新儒学”,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书集注》等著作中。
会通致精。就是要求人们对各种学说进行具体分析,认识到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必须寻求其精髓,在一定高度上寻求会通。
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会通中外各家思想的研究中开始把眼界扩展至天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这是难能可贵的。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天下”与君主的区别,实际上是对“朕即国家”专制思想的抨击。他将这种思想引申至学术方面,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公识”,其是非并不取决于个人和一家,应当由天下人来讨论,并决定其是非。
会通致新。也就是说,会通精神与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会通融合,也不会产生新思想;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当然不可能进行学术思想的会通。这个道理渗透在中国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值得我们深思。
我国古代与东南亚的文化的会通,在近现代的进一步交流,不但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而且有利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深化与华人社会的形成。世界上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各民族对人类的文明都有贡献;这种贡献只有在交流与会通中才能得到实现与提高。
对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理解不能扭曲会通精神。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西分割、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中华文明如实地看成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过程,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而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贯通。
事实证明:对世界文化了解得越多,对本国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在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将文化思想精华与古代文化中的糟粕加以剥离上越加科学化。同样,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得越深,对世界文化越有鉴别力,越能准确地吸收其优质,以补自身文化的某些不足。
第2篇: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范文
[关键词] 《论语》;异端;正统;经典诠释;儒学演进
[中图分类号] B22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1―0005―07
Abstract:Due to expounding on “heresy” for the first time, “Attack/Study Heresy” in The Analects got traditional scholars of th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concept of “heresy” was given many connotations by the traditional scholars accordingly, such as little man’s skills, insignificant things, preQin thinkers, Buddhism, Taoism, dissident, both sides. What is more, its borders got extended gradually, until the “heresy” was regarded as all the academic thought patterns what contrary to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many scholars in China's history, we can see the vei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all the past dynasties in China.we can also see that this chapter contains the various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Some scholars strongly rejected “heresy”. However, some scholars treated “heresy” gently; they denied the criticism of the “heresy” and even affirmed the value of the “heresy”.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ing contains the different thinking of the development ways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the Analects;heresy;the orthodoxy;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
《论语・为政》篇载孔子之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据出土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本,此章“攻”作“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另据传世的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此章“已”后多“矣”。([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一《为政》,《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自汉代开始,以此章“异端”为核心的诠释甚多。大体而言,历代歧解,均以如何看待“异端”为核心;以“正统”为基准,强调“异端”之害,可以说是其主流原则。当然,其中又存在明显差异。从诠释面向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训“攻”为“治”,以“斯”指代学习异端,视“已”为虚词,认为学习、专攻异端是有害的,因而反对士人学习异端;其二,是训“攻”为“击”“辟”等,或以“斯”指代异端而视“已”为虚词,或以“斯”指代攻击异端而训“已”为“止”,认为应攻击消灭异端以避免异端之害;其三,是训“攻”为“击”“辟”等,以“斯”指代攻击异端,视“已”为虚词,反对攻击异端引起更大的祸害,而主张昌明儒学则异端自不能为害。以时间为纵轴看,历代学者对“异端”的诠释,又有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相应的“正统”则特化为儒家正道,甚至程朱之学。
对“攻乎异端”章诠释史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论语》诠释与不同时代的文化环境、学术风尚以及诠释者个人的学术旨趣、学术理念之间的关系,在儒学演进的整体脉络中理解经典意义的生成,理解历代诠释中的时代内涵。
一将此章诠解为反对学习异端:历代
“异端”内涵的变化与儒学演进
至西汉,先秦时期关于《论语》的授受及其诠解,时人已不甚清楚;而两汉《论语》传本、注本虽众,今亦多不存。
两汉时期,《论语》即有《古论》《齐论》《鲁论》《张侯论》等不同的传本,又有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等人的注本,然今皆无完本。相应地,两汉儒者对于“攻乎异端”章的诠释,我们难以获知。不过,东汉初年的经学家范升对此章的引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儒对此章的理解。据载,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视《左氏春秋》为异端,反对韩歆、许淑等意图置《左氏》博士,他说:“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六《范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28-1229页。这里,范升是将“异端”与“本”对立了起来。所谓的“本”,即与孔子有明确渊源的儒学正统,也就是今文经学;而《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
《后汉书》卷三六《范升传》,第1228页。,范升自然要将之排斥在经典诠释的体系之外,反对儒生们学习它。这种以《左传》为中心的今、古文之争,实乃对经典诠释权威的争夺,代表了两汉今文经学家排斥古文经学,以垄断经典诠释权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范升的理解仅局限于经学之争,那么何晏(公元?-249年)的诠释则扩展了此章的意涵,他说:“攻,治也。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
《论语集解义疏》卷一《为政》,第20页。在这里,“善道”指儒家六经,“统”即“本”,也就是儒家圣人之道,在何晏看来,《诗》《书》《礼》《乐》虽教化路径不同,但同归于儒家圣人之道;“异端”不本乎此,故旨趣不同。这是将“异端”与“本”,也就正统儒学相对待的。不过,何晏又说:“虽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道者也。”
《论语集解义疏》卷五《子罕》,第129页。在诠释“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时,何晏更指出,“小道,谓异端也”。
《论语集解义疏》卷十《子张》,第267页。在这里,何晏不仅不排斥“异端”,反而认为“异端”有可取之处,所反映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对此,学界多认为这才是何晏的真实思想。何晏热衷于探求玄理,在诠释《论语》时也不免表现出以道释儒的学术旨趣,“此处他就是借用老庄‘小大之辩’的道理来诠释‘异端’。强调‘异端’虽‘小’但也‘可观’,力图对魏晋时期党同伐异的风气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此说明显带有其‘重大不忽小’的玄学色彩。”
施仲贞:《中“异端”研究史考辨》,《人文s志》,2009年第3期,第33页。尽管如此,何晏的这番诠解尚显隐晦,他提出的“异端即小道”虽为后世诸多学者所继承,但多被引申至强调异端之害。
南朝梁皇侃(公元488-545年)对何晏的诠释作了进一步的疏解:“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杂学诸子百家之书也。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故书史载人专经学问者,皆云治其书,治其经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为害之深也。”
《论语集解义疏》卷一《为政》,第20-21页。这就很明确地诠释了此章的具体内涵,即:学习诸子百家等杂书,这是有害的。唐代经学统一,皇《疏》为官方采用;宋初邢m(公元932-1010年)《论语注疏》对此章的诠释也与皇《疏》大体一致。至少在宋学兴起之前,“攻乎异端”章的内涵通常被如此理解。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尚未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状况,将“异端”诠释为诸子百家等杂书,显然不合此章的历史语境。但这种不顾历史语境的诠释倾向,到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回应佛、老二氏的挑战,复兴儒学,已经成为儒家学者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纷纷对此章义理进行疏解,以资对佛、老之学的排斥。程颐(公元1033-1107年)即阐发此章说: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宋]程颢、程颐,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20页。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第187页。
显然,他与前述汉唐古注的作者们在此章诠释的面向上是一致的,都以儒家之道为本位,反对研习小道异端。他们痛心地看到,当时有不少儒家学者,为佛老之学中某些精致的理论成果所迷惑,混淆了儒学与佛老之学的界线。在对本章的诠释、发挥中,程颐强调,异端虽“有可取”却偏离了儒家正道,要彰显儒家圣人之道,就必须摆脱异端之惑。这一阐发,反映了在佛老之学挑战日益严重,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善待完善、儒学复兴尚未完成的时代环境中,儒家学者对佛老之学的高度警惕与排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与佛老之学的紧张与对立,体会到程颐内心的焦虑。
与程颐同时而稍后的著名学者、王安石的高足陈祥道(公元1053-1093年)对此章也有诠释。他说:
天下之物,有本有末。本出于一端,立于两。出于一则为同,立于两则为异,故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异端”也。……董仲舒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进。”此之谓知本者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一,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儒藏》精华编1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5页。
这一诠释,立足于本末关系进行阐述,将相关的阐发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但透过抽象的理论论证可以看到,其主旨很明确,那就是以“先王之教”为标准进行衡量,“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异端也”。对待异端的态度也很坚决,他高度肯定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进”之说,认为如此方可谓是深明学术之本。陈祥道是荆公学派的重要成员,从其对于异端之学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到在《三经新义》颁于学官,荆公新学挟官学之威独行于世、科场士子“咸宗其说”的历史情境中,儒家学者对于儒家之外的各家学术加以排斥、抑制、禁罢的事实。当时,荆公新学虽然取得了官学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课题远未完成,儒家学者非常需要借助其政治优势,确立儒学在思想学术界的垄断地位,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自然得到了他们的高度称颂。
南宋时期,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承袭了皇侃、程颐等对“攻乎异端”的诠释,认为“攻者,是讲习之谓,非攻击之攻”
《朱子语类》卷二四,[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册,第854页。“异端者,杂杨、墨、诸子百家而言之”
《晦庵集》卷五二《答都昌县学诸生》,《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74页。“范氏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论语集注》卷一,《朱子全书》,第6册,第79页。同时,朱熹对异端之学也持激烈的排斥、批判态度,强调正道与异端水火不容、互为消长:“正道、异端,如水火之相胜,彼盛则此衰,此强则彼弱。”
《论语或问》卷二,《朱子全书》,第6册,第652页。而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朱熹特别关注的,是具有较为精致的理论体系、对儒学产生最大威胁的佛学。他引用程颐之言说明了这一点:“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VV然入于其中矣。’”
《论语集注》卷一,《朱子全书》,第6册,第79页。就朱熹而言,他在自身思想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对佛老之学的思想资料与理论思维成果借鉴、吸取甚多,这是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共同的学术取径,是儒学更新、复兴的必然选择。但在此过程中,朱熹牢固坚持儒家的价值立场,从价值层面对佛老之学进行激烈的批判,划清与佛老之学的界线。从朱熹对“攻乎异端”的诠释、发挥中,我们可以看到严格辨析儒佛之异、严防受到佛学诱惑而沉溺其中,仍然是许多儒家学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字里行间,充满着紧张感、警惕性。
但同时代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的诠释则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他说:
今世类指佛老为异端。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却指那个为异端?盖异与同对,虽同师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不同,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有人问吾异端者,吾对曰:“子先理会得同底一端,则凡异此者,皆异端。”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2页。
与程、朱不同,陆九渊反对将孔子所言的“端”与佛老之学直接联系。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扩大了“异端”的范围,将“所学之端绪与尧舜不同”作为划分“异端”的依据,“虽同师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不同,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这就大大地扩大了“异端”的范围,被纳入其中的,已经远不止佛老,而是同时也包括与之“同师尧舜”却偏离尧舜之正道的其他儒家学派。但是,陆九渊所理解的“与尧舜不同”或者“同”,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按照陆九渊的说法,在于自己“理会”,与此心之理不同的自然就是“异端”。显然,在陆九渊这里,学术的排他性更强了,不仅佛老之学、诸子百家,与其观点、路径不同的其他儒家学派也同样可以被贴上“异端”的标签。南宋中期,儒学呈现出繁荣之势,学派分化严重,不同学派学者相互质疑论辩,不同思想观点激烈交锋。陆九渊对“异端”的诠释就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陆九渊对“异端”的诠释已经被他作为排斥其他学派的工具。这也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经过长期的理论建构之后,儒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已经初步完成,陆九渊等儒家学者充满理论自信,不再对佛教的威胁深感焦虑、深怀恐惧,进而把关注的重点转向在儒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其他理论路径、致思方向的排斥方面。
对“异端”的这种宽泛理解,在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在这里,王阳明提出了衡量正统和异端的标准:即思想理论是否与愚夫愚妇的要求、愿望相背离,能否使得未经教化的民众也能致其良知。他最为关注的是学术能否贴近民众,融入其日常生活。对当时学界热衷于记诵词章的习气,“言之太详、析之太精”的学风,王阳明进行了批判:
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辞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辞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
《王阳明全集》卷七《别湛甘泉序》,第257页。
显然,在王阳明这里,对杨、墨、佛、老之学的排斥已经成为退居其次的问题,他所谓的“异端”,所指的正是某些儒家学者。按照王阳明的标准,当时很多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圣人之道,成为远离愚夫愚妇的“异端”。在王阳明这里,“异端”指向的范围更为宽泛,甚至成为用以明确其学术边界、凸显其学术旨趣的一种工具。王阳明所倡行的“致良知”之学,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平民大众,也可以感发遵行。清代学者焦循概括阳明心学的特点说:“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小人。”
[清]焦循:《雕菰集》卷八《良知论》,《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页。。王阳明“异端”观,反映了其学术旨趣,彰显了其特色,也反映了明代儒学的平民化转型。
到清代,尤其是随着考据之学的兴起,清儒逐渐深入此章的历史语境,结合字词训诂与孔子的思想体系,在这一面向的“异端”诠释上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如: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将据传的孔子删订《六经》的行动均视为孔子对“异端”的排斥,认为“异端”即“洪荒幽眇之说”,涵盖了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等。
李光地认为,“那时异端颇多,所以删《书》,断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说,芟除个尽……”([清]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二《上论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8页。)程廷祚(公元1691-1767年)则依据《论语》文本佐证,取何晏“小道”说来解释“异端”的内涵,将之具体化为农、圃、医、卜等学问。
至于孔子为何不直接说“攻乎小道,斯害也已”,程氏认为,“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异,起端则殊途而不同归矣。曰‘小道’,人或犹以为道之绪余,攻之无害;曰‘异端’,而后天下皆知其不可攻。呜呼!圣人所以一儒之统者,严矣。”([清]程廷祚:《论语说》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册,第459a-460a页。)也就是说,这蕴含着孔子告诫后人的深意,因为“小道”毕竟仍在“道”的范围之内,不易使人廓清,仍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而“异端”则表明小道自一开始便与大道歧途,更易使人清醒地认识到小道之害而不再去学习。此类诠释尽管内容各有偏重,但总体而言,都力图回到孔子所处的历史环境,学风朴实。从中不难看出清代考据之学的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叶学者戴震(公元1724-1777年)等独辟蹊径,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释。戴震将“异端”诠释为“两头”,所谓“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言业精于专,兼攻两头,则为害耳。”
[清]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第16a-16b页。宋翔凤(公元1779-1860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发挥,他借助《中庸》的“执两用中”,将此章内涵与儒家的“中道”价值观相联系。他说:
执者,度之也。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过或不及,即^之异端。攻乎异端,即不能用中于民而有害于命,如后世杨、墨之言,治国皆有过与不及,有害于用中之道。……孔子知之,故于《论语》言一以贯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
[清]宋翔凤:《论语说义》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第274b-275a页。
与戴震一样,宋氏也将“异端”诠释为“两端”,并且将戴震的诠释进行了充分的展开。在宋氏看来,“执其两端”是权衡利害,会以中道为准而能专一,不再有过与不及的偏差;“攻乎异端”则是不加审视而兼治两头,导致过与不及,产生危害。在这种以“中道”价值为取向的诠释中,所谓的“异端”与以往所谓的小道、诸子百家、佛老邪说等“异端”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这种诠释,已经上升到了方法论的层次,所探讨的是如何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把握“中道”,避免过与不及之害,从中可以略窥清代学术中方法论意识的端倪。
二将此章诠解为攻击异端或反对攻击异端:
历代学者对儒学发展方式的思考
在“攻乎异端”章诠释史上,还存在着攻击异端和否定攻击异端两种面向的诠释,而这两种面向,都包含了儒家学者对儒学发展方式的思考。
在上节的诠释中,“攻”一般被训为“治”。但是,《论语》中“攻”字的使用,除了此章外,还有“小子鸣鼓而攻之”(《先进》),以及“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两处,皆取攻击、攻伐义。因而在有些学者看来,此章也不应例外,此章“攻”字应训为“击”,相应地,“斯”或指代“攻乎异端”,而“已”为虚词;或指代“异端”,而“已”为“止”。这一面向的诠释,其主旨在于攻击乃至消灭“异端”,以避免“异端”造成危害。
在这方面,宋儒孙奕的诠释最为直截明白,他说:“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杨、墨,则欲杨、墨之害止;韩子辟佛、老,则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四《经说》,《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页。
元儒朱公迁更将所谓的孔子作《春秋》也视为对当时异端的批判攻击,他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元]朱公迁:《四书通旨》卷四《异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4册,第617页。
这里所谓的“异端”明确地指向当时的“邪说暴行”“乱臣贼子”,基于异端和正道对立的思维,他必须要确立孔子是攻击异端的这一基调。在他看来,孔子忧虑当时的异端之害,因而作《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而异端之害息。
以上的理解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的认可,他以帝王姿态将“攻”解释为攻击,“已”解释为停止,强调对异端的排斥打击,并对一些宋儒的诠释提出了批评,所谓“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已甚,岂不谬哉”
[明]黄佐:《翰林记》卷九《御前讲论经文》,《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0页。。在他看来,大概将“攻”解释为学习专攻,不能突出孔子对异端邪说的严厉态度。将之解释为攻击,则能表明孔子必欲消灭异端邪说的取向。
然而,以上这种二元对立的诠释,所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只要与圣人之道相异的东西,就是有害的,必须加以排斥、打击,消除其危害。这一观念,带有极强的文化专制意味,也是与孔子强调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相`的,因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虽将“攻”解释为攻击,但以“斯”指代攻击异端而“已”为虚词,将此章内涵理解为:攻击异端,这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可见于历代学者对此章的诠释之中。
北宋大儒张载(公元1020-1077年)曾诠释此章说:“攻,难辟之义也,观孔子未尝攻异端也。道不同谓之异端,若孟子自有攻异端之事,故时人以为好辨。”
[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张子语录中》,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0页。他认为,“异端”只是不同道者,孔子并未攻异端。甚至对孟子批判异端,张载颇有微词。在他看来,不必花费精力攻击异端,只要坚守、彰显儒家之道,就可以从根本上破除异端对世人的迷惑:“诸公所论,但守之不失,不为异端所劫,进进不已,则物怪不须辨,异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胜矣。”
《张载集・答范巽之书第一》,第349页。张载的这一认识,与他对历史的反思有关。唐代韩愈(公元768-824年)曾要求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页。的激烈措施对待佛、老,宋儒石介(公元1005-1045年)也曾著《怪说》来攻击佛、老对儒家伦理纲常的破坏,倡言“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
[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集》卷五《怪说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页。;此外,还先后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但这些行动并没能阻断佛、老等“异端”的兴盛与发展。北宋中期以来,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转变策略,不再一味辟佛,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加强儒学自身理论建设方面来。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即著《本论》,指出“修其本以胜之”
[宋]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七《本论上》,[宋]欧阳修著,李之亮点校:《欧阳修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41页。作为复兴儒学、维护儒学正统的根本途径。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我们也许能对张载的观点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他的诠释,实际上包含了他对儒学发展思路的认识。
在宋代,在此章的诠释、阐发中表达反对攻击异端主张的学者不乏其人。南宋学者郑汝谐(公元1126-1205年)就说:“圣人之所辨者,疑似而已。若异端之于吾道,如黑白,如东西,夫人皆知之,何必攻也。后世好与释、老辨者,盖未识圣人之心也。”
[宋]郑汝谐:《论语意原》卷一,《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这一观点,与张载之说是一致的。罗泌(公元1131-1189年)也曾从修本和攻击异端有害两个层面进行他的诠释,钱时(公元1175-1244年)也有同样的看法。
罗氏言:“夫异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圣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则害有甚也。……大抵天下之事,大过则反伤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门、毁像事,至与安而复;建德之毁经像、还僧道,至大象而复及;会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复。夫亦岂知《易》道之变通哉?曰:然则终不可攻邪?曰:正其义不忧。”([宋]罗泌:《路史》卷三四《发挥三・道以异端而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第498页。)钱氏也认为:“攻即攻击之攻,异端非正道而别起一端以诬民者也。正道昌明,异端自然衰止,不必攻也。求以胜之,反为害耳。”([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第586-587页。)宋末学者黄震(公元1213-1280年)更依据孔子身处的时代语境,彻底否定了对异端的攻击,他说:“孔子本意,似不过戒学者它用其心耳。后有孟子辟杨、墨为异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异端目之。……然孔子时未有此议论,说者自不必以后世之事,反上释古人之言。君子又何必因异端之字与今偶同,而回护至此耶?”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张伟、何忠礼主编:《黄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册,第10页。孔子时既然尚不存在对于异端的排斥,那么后儒在诠释此章时,于正道和异端之间显然就失去了合理性。这不光是反对从反面的排斥异端来彰显儒家正道,甚至连从正面的修本以彰显儒家正道也为他所反对。此外,黄氏还指出了此章历代诠释的要害,即“因异端之字与今偶同”,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异端”与后世学者所谓的“异端”只是字面上相同,在内涵上却是存在差别的,不能用后世的境况来诠释孔子所言的“异端”,而应深入当时的历史与文本语境去诠释其真义。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时代变局使学者们对学术的同与异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们以更为宽阔的视野与胸怀、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思考学术的发展问题。如明儒章世纯(公元1575-1644年)认为攻击异端之举很不明智,甚至从正面对异端存在的价值进行了肯定。他说:“徒以异己而攻之,失其所济,丧己之利矣。……鸡鸣狗盗,智者犹或存之,为有济于一旦也。故善用道者,不弃恶,恶且不弃,况或俱美者乎”
[明]章世纯:《四书留书》卷三《论语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7册,第734页。,异端很可能是自身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不仅不应攻击,而且应该善待之,甚至与之俱美。这一看法,在否定攻击异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肯定异端的价值,颇具保持学术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反映出当时学者对学术发展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正统与异端二元对立的藩篱,正在走向深入。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更为否定对异端的攻击提供了理论论证。他说:
天地有阴阳、虚实,而无善恶、真伪。阴阳分而流为善恶,虚实分而流为真伪。实行则真,虚名容伪。愈高则愈伪,愈伪则愈遁,固其所也。知其遁而容其遁,圣人合天地之道也。有杨、墨而后孟子显。孟子辨孔子时之杨、墨,而不辨同时之庄子,谓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不亦可乎?不得已而辨,辨亦不辨,虽辨之而仍相忘也。仁者仁,知智者知智,百姓安其不知,君子之道虽鲜而无不相成者,错行之道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言当听其同异,乃谓大同;攻之则害起耳。立教者惟在自强不息,强其元气而病自不能为害。
[清]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容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7。
在这里,方以智借阐发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语,明确表达了其学术理念。他认为,学术应当保持对于不同立场、观点的宽容,保持有同有异的状态。正如在先秦学术史上,有杨、墨而后孟子之学才得以彰显一样,立场、观点相异的学术,往往能收相反相成之效。他甚至认为,“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孔子、孟子有意识地留下对立的学派,以保留学术发展的空间。相反,如果一味攻击异端之学,就会产生很多弊害。在他看来,学术要发展,依靠的是“自强不息”,完善自身理论体系,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使自己能够抵御“异端”之学的挑战。方以智的论述,从辨同异的层面对攻击异端进行了否定,在学术发展方面表现出一种相当宽容、开放的态度。“当听其同异,乃谓大同”,无疑是学术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
三结语
第3篇: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范文
关键词:先秦诸家;义利观;当代中国;启示
义与利及其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的话题。自先秦以来,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
一、义和利的含义
“义”(繁体为“義”)从汉字结构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捍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慑力的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最高道德。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中庸》解释为“宜也”,即“适宜”的意思。《札记?祭义》也说:“义者,宜此者也”。“义”又和“宜”相通,行为的适宜性在通过一定的“礼仪”表现出来。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循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责任。
“利”,也是一个会意字,由“刀”与“禾”组成, 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从刀,和然后利。”意为以刀割禾,即用农具收割庄稼而有收获,获得利益、好处。所以“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笔者认为义利关系实质上是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公义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义利观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思想观点。
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为主,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价值标准,认为义为君子的内在价值与固有本质,君子是取义,重义轻利;小人则趋利,见利忘义。孔子的观点为儒家学派确立了“重义轻利”的基调。继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孟子说:“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他在回答梁惠王时也曾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义利关系发生冲突时,孟子的思想是“取义”为先,甚至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孟子思想任然坚持义为先,甚至为义而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重义轻利,甚至重义轻生。荀子作为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受孔孟的影响,也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义与利者,人所两者有也,”(《荀子?大略》).但在义与利之间,他并非完全排除利,而是坚持义为先,利为后,提倡先义而后取利的价值导向。总之,在儒家看来,义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有益,提倡“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道德原则,即强调“义”的第一性。见到“利”要先想到“义”,符合“义”的行为才是应当做的行为。而“轻利”不等于不言利。在“利”和“义”的关系上,在两者相比较时,“义”先而“利”后,并不等于说要“义”就不能要“利”。但孔子和孟子所指的“利”从总体上讲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在“义”和“利”的关系中,孔子、孟子强调“义”的第一性,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也指出追逐“利”的正当性,但他们又有安贫乐道的意思。
三、道家的义利观
道家主要以老子为代表,老子主张取消义利,从道德上超越了义利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了解老子对“德”的划分,他把“无为”之德称为“上德”,把“有名”之德称为“下德”,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义利之辨就不能适用于老子的义利观。老子认为“下德”会使人失“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所以只有由“下德”转变为“上德”才能实现其“道”的回归,在他看来仁义是世界变坏的一个象征,进而主张无为, 既没有任何仁义的社会模式,“无为之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甚至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所以才有了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 。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利而不用利,有仁义而不知仁义。所以道家的义利观虽然是完全否认义利,但是从他们超越仁义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道德的更高追求,有其积极的一面。
四、墨家的义利观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认为:“义者,利也”(《墨子?大取》),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求利即是谋义,取利即是尚义。
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原则, 所谓“兼爱”,就是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墨子强调人们要爱人如己,人们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能这样爱人如己,就会“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在此基础上的“交相利”原则是“兼相爱”原则的具体反映和实施,“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从而进一步强调利不但不非义, 而且义利并行,即“义”与“利”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墨家的义利观上升为治国方略则认“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乐》) ,这里的“利”是“公利”也即“义”,所以墨家的义利观是建立在把利国利民之利视作义的基础上的, 把个人私利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把“利天下”的公利与义等同起来,把道德评价的标准与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结合起来,它强调忘我无私,利人利国,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大同的社会道德理想。
五、法家的义利观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崇法尚利,承认因阶级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利”,强调统治阶级要明于公私义利之分,举公而不纵私。韩非子指出“古者仓领之作书也, 自环者谓之私, 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领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子?五蠢》)所以,“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韩非子?八说》),真可谓“ 君臣之利异”(《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为此,统治者“必明于公私之公,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韩非子?饰邪》),同时韩非子又指出追求义利是人之本性,人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利者, 所以得民也”《韩非子?诡使》,“利之所在, 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在上》。而利有“大利”、“小利”之分,因为“顺小利, 则大利之残也”《韩非子?十过》,所以,人不能“苦小费而忘大利”《韩非子?南面》,而要“出其小害计其大利”《韩非子?八说》,并进一步“虑其后便,计之长利。《韩非子?六反》。所以他们求利之心比任何一个学派都强烈,而且在法家这里的利就是一种具体的利益,法家义利观是对道德精神价值的放弃,对物质利益的高度重视,甚至把人物质化,这样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看来,必然会把社会的道德引向陌路,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义利观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强调重义而轻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否定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带有浓厚的道德蒙昧主义色彩,但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了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适应了自汉代以后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需要;道家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可以看作是一种“绝义弃利”的义利虚无主义;而墨法二家强调是义利上的一致性、平等性,认为利他即利天下,义是整体利益的要求也是利人的最终目标,所以儒家与墨家法家义利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尽管各有侧重, 具体内容不同, 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体与整体、个人私利与社会公义的关系, 都是为解决现实社会义利矛盾而提出的道德对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借鉴的思想文化遗产,就某些方面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六、先秦儒道墨法家义利观的现代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处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私利和公利,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都显得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活动的趋利性刺激和强化了人们的利益意识和利益追求,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取向呈多元性,这就决定了道德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复杂性,由此导致主体的利益价值追求与道德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激烈,甚至发生冲突。因此,正确理解和继承先秦家诸家义利观的义利思想,对于现代义利观的形成,对于当下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4篇: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范文
《论语》是儒家学派重要的经典着作,阐述了孔子重要的文学思想观点,对后代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分析孔子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着作———《论语》,总结出孔子重要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并为政治外交服务“仁”是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孔子一切学说的重要出发点,因此,孔子在文学思想中强调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对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是这样阐述的,“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见,孔子将道德置于与文学同等的位置,而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服务的。另外,孔子也认为,文学与道德修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说到,“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文学的创作必须把道德始终放在第一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学创作应该为政治外交所服务。孔子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作者的志向,即反映作者内在的想法,特别是政治上的愿望,因此诗歌的创作必须满足作者本人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理解诗歌,解读诗歌的重要意义所在就是要实现政治外交活动的顺利完成。
(二)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思想目的性的重要体现。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社会作用上,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兴”就是指“兴于诗”,它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修身的第一步必须要学诗,诗歌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将各种形象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内在的精神修养,达到培养人格修养的作用。“观”就是指“观察”,即要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去感受外在的事物,就是指诗的内容应该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群”就是指将不同的人的观念结合起来,通过相互的交流切磋,以达到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提高人们的思想修为。“怨”就是指文学作品应该批判现实的黑暗社会,为政治服务,达到教化人的目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表述了文学的认识作用、对人的教育作用以及审美作用等。
(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协调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一直十分强调诗乐的和谐美。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质彬彬说”。“文质彬彬”一词主要用于形容人的精神品格,“文”主要是指人的外貌,而“质”主要是指人的品质、内在的修养等,即外貌的修饰必须要与人的内在的品格相统一。在这里,孔子引申为,在文学的创作上必须达到文学创作内容与文学形式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孔子并不是将内容与形式放在同等的位置,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他认为内容应该重于形式,即内容决定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他更加强调“质”的重要作用,而“文”应该随着“质”的变化而变化,与“质”相统一。
二、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重要启示探析
孔子许多的思想至今为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为我国物质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其文学思想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现代教育应该以德为本“仁”是孔子学说的灵魂,而品德与文学并重是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认为,品德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位于首要的位置。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我国教育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即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目的,可见,德育应该放在首位。德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孔子认为,德的内涵包括孝、义、忠、恕、勇、信、诚、勤、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直、中庸等多个方面。在儒家的教育思想里面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人最核心的素质应该是人的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的重要途径,学生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孔子的文学思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但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教育的核心主要偏重于学生“智”的发展,而忽视了学生“德”的培育,严重地制约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现代教育应该为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服务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的创作的目的在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观群怨”学说则更加地突出了文学的社会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教育更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所在。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可见,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的教育也应该贯彻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服务的宗旨。[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对于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我国现代教育的改革应该紧紧地围绕这一需求进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现代教育应该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孔子认为,文学的创作应该反映现实,这主要体现在孔子“观”的学说上。笔者认为,教育更应该促进理论知识与实际的结合,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应试教育占据着主导地位,老师们都只是一味地追求学生考取高分,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我国许多学生的综合素质较低。“哑巴英语”现象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一些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弱,连一些基本的实验都无法独立完成。“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较低,因此现代的教育必须要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全面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地提高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四)现代的教育应该注重“文质”的结合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而中国也素来重视品质与行为举止的统一。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强调了“文质”的重要性,认为文艺要从属于礼,要为礼所服务。人在社会交往中,也必须注重行为举止与礼貌内在修养的统一。因此在现代的教育中,除了要树立“德育”的理念外,也必须注重社会交往的各种行为举止的教育,使学生在交往中做到“文与质”的结合。孔子的“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外在的礼貌修养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商业交往的各种活动中。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教育却是相当薄弱,从小学到大学,除了大学某些学校开设相关的专业之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开设这类的课程,导致我国很多大学生在求职、商业社交中,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外貌修饰,使自身达到“文质”的协调。
三、结语
第5篇: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范文
摘 要:在宋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与陆九渊领军的“心学”是其中两个主要学派,朱、陆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共扶名教,同植纲常。为此,两人进行了十余年的学术争辩与互动,试图在儒学的框架中实现“理学”与“心学”的融合,终因双方学术之路迥异而难以实现。考察朱陆的思想差异,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层面:“理”本体的外在支配性与内在能动性,人性的差异性与平等性,道德修养的内求与外索以及对佛教文化的正统与异端判定。
关键词:理;本心;差异;平等;正统;异端
中图分类号:B244.7,B24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10-0034-04
朱熹,字元晦、仲晦,晚年号晦庵,尊称为朱子,他承接、吸收“北宋五子”的理论并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朱子“理学”体系以“理”范畴为核心,以“理”为体,以“气”为用,形上之“理”对于形下之“气”及万物具有逻辑先在性和支配性。从“理”与“气”的关系映射到社会和人生层面,外在的强制性的“理”就转化为社会规范的内容和道德实践的目标,这个寻求合乎于“理”的过程需要通过格物致知和知行相须的途径来完成。
陆九渊,字子静,自称象山居士,人称象山先生,是南宋“心学”的开创者。相对于朱子“理学”较为复杂的由理、气及人的结构,象山的“心学”比较简明,他通过“心即理”的命题把“理”定位为“本心”,明确指出“理”不在身外,而是在人们心内,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不是面向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去格物,而是要面向内心来格心,做“剥落本心”的工作。
朱、陆二人思想体系完备,虽然同纳于儒学之门,但是两人各行一路。因二人殊途而进,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认识的差异,两人多次的学术争辩与互动影响巨大,史称“朱陆之辩”。其争辩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易简与支离、尊德性与道问学、发明本心与格物致知、太极与无极、融佛与排佛等多个问题与范畴上。加以归纳,可以从这样四个层面来考察:
一、本体论之异:外在的“理”与内生的“本心”
“宋学有两项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建构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理’的世界;二是发展了种种关于精神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指点人如何‘成圣成贤’。”[1]朱子的“理学”以形上本体之“理”为核心这无须多言,陆九渊的“心学”虽然以“心”为标识,但是此心即是此理,同样以本体“理”为核心。所不同的是,朱子的“理”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先验存在,具有绝对的支配性和约束性,而象山的“理”是内在的,它存在于人们“心”中,因而主体人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在朱子看来,“理”是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它超越时空,是宇宙的本源,同时,也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的社会都统一于“理”,受“理”的制约和支配。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2]1他在《答黄道夫》一文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3]
象山也把“理”作为形上的本体。象山说:“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岂可言无?若以为无,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4]28“‘此理在宇宙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顺此理而无私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顾此理哉。’”[5]196与朱子把“理”作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外在总根据不同,象山认为此“理”也存在于人的心中,即人之“本心”。象山通过“心即理”的命题,把“理”与主体人进行了关联,给予普通人也可以明心见理的信心,为人积极追寻“理”的道德实践打开了自主性和能动性之门。
需要指出的是,象山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并非是说“理”由人心所生。“‘充塞宇宙’表示理在宇宙间的普遍存在。理既存在于人心,又普遍存在于天地之间,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这都是强调内心的道德准则与宇宙普遍之理的同一性,而不是指宇宙之理是人心的产物。理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可知性是陆九渊所不否认的,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5]196
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中,也有“心”这一范畴。在他的“心统性情”理论中,朱子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认为合乎理者为道心,落于人欲者为人心。对此,象山评论说:“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4]475他还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4]396由此可见:“盖象山紧承孟子性善之说,形色即天性,撇开了伊川所加的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这一纠结,在根源上不承认有理、气之对立,及天理与人欲之对立。”[6]朱子把心置于形而下者气的层面,认为心为理所支配与制约,这种观点与象山把“心”归为本体的主张显然不可调和,自然会引发象山的不满与批评。
二、人性论之异:人性的等级性与平等性
作为形上本体的“理”是朱、陆理论的起点,但并非他们理论的最终目的。从“理”出发,为社会的秩序和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依据和指导道德修养实践,才是朱、陆最为关心的内容。对于个体来说,朱子和象山对他们的道德起点设定是不一样的,朱子认为人性是不同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而象山则基本相反,认为人性大体相同,具有平等性。
朱子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2]61朱子认为,就理而言,它是至真至纯、无善无恶、无贵无贱的,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属于形而下的世界,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构成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问:理无不善,则气胡为有清浊之殊?曰:才说著气,便自有寒热,有香有臭。二气五行,始何尝不正。只衮来衮去、便有不正。气升降,无时止息,理只附气。惟气有昏浊,理亦随而间隔。”[2]63
严格地讲,朱子上面的回答并不令人信服。既然理是体、气是用,那么就应该是由理来决定气而不是相反;再者,不管气是何种形态,只要理是同一个理,又何来理亦随而间隔之说?
朱子对气质之性的界定完成了他对人性差异性和等级性的预设。他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一个人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2]2686很显然,坚持人性差异性的朱子断然不会同意象山所坚持的生而平等的人性观。在“本心”面前,象山认为人人平等地拥有一个相同的“本心”,在“发明本心”的过程中,在完美人性的回归之途中,只有是和非的差异,并不存在高低、尊卑的区别。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4]483在此,象山认为“本心”是一种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绝对存在,也是人性和道德的本源;其在宇宙为一,于古今为一,具有唯一性。因而,这唯一的“心”还为每一个人所拥有,不分圣、凡,不分贵贱。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4]149“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4]4他说:“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故曰‘周公岂欺我哉’?”[4]13这样,象山坚定地赋予了人们在道德起点上的平等性。
正是存在着对人性认定的差异,朱子对象山的人性生而平等的看法颇有微辞。朱子说:“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功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2]2688又曰:“从陆子静者,不问如何,个个学得不逊。只才从他门前过,便学得悖慢无礼,无长少之节,可畏!可畏!”[2]1338更进一步,朱子不但认为象山错了,而且还认为其害甚大。他说:“他(指子静)学者是见得个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说,实是卒动他不得,一齐恁地无大无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若我见得,我父不见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见得,便是兄不似我。更无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后世,即今便是。”
三、功夫论之异:道德修养进路的内求与外索
从人性的起点出发,朱子和象山提出了“内圣”功夫的不同方法。朱子主张格物致知、知先行后,象山主张发明本心,尊德性而后道问学;朱子主张向外探索,做加法,进行量的积累,知众多分殊之理而最终明一理;象山坚持向内寻求,做减法,通过逐层剥落而直达本心。
“朱熹与小程一样地认为,人之成德,是在认识的基础上才可以确立,且亦唯有建基于认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与可靠的。”[7]148朱子的功夫论以知识论为前提和基础,他认为道德功夫首先在于格物致知,然后再去行,即知先行后,应该由知来分辨、判定行是否具有确当性,在合于“理”之知的指导下去行,进行道德实践追求。朱子所主张的格物对象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2]259“格物,是逐物格将去;致知,则是推得渐广。”[2]353“‘积习虽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2]408朱子认为,格物的目的在于明“理一分殊”中之“一理”。显然,只有不停地格物,反复积累“分殊”之理,虽不一定要格尽万物,但总要有非常多的积累为基础,对“一理”的认识才有可能豁然贯通,最终体认到万物普遍之理。
朱子主张的外向型累积性道德修养功夫受到了象山的批评,这源于双方本体论上的分歧。朱子之本体“理”外在地支配主体人,故而人须外向而寻“理”;象山之本体为“本心”,为主体人生而所有,道德修养自然应该向内探索,直接从主体省悟中探求与“本心”的自同,达到心、理合一的目标。象山判定:“知识论的进路只会使心逐物于外而使‘本心’失却,故陆九渊甚至直认其成德功夫即在‘减担’与‘剥落’。”[7]148他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4]427因此,象山主张的道德功夫是“切己自反”、“发明本心”,而不是格物致知、知先行后;是逐渐剥落遮蔽“本心”之外在事物,而不是不断积累与道德修养并无多少关联的问学之知。正是这个原因,象山宣称自己的道德修养方法为“易简”功夫,而把朱子的方法称为“支离事业”。
在鹅湖之会上,象山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4]458在诗中,象山认为人道德之“本心”是本来自有,千古不变,始终同一。他认为自己开创的心学是“易简功夫”,直指人心,是真功夫,可以永恒长久;而朱熹的所主张的则是“支离事业”,会陷于繁琐之末节而疏远根本,是伪功夫,只会浮沉不定。象山认为,既然“本心”或者说是“理”为每个人平等拥有,那么道德功夫的结果只能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如果说不同的人德性存在差异,那是主体自身不作为的原因,而并非其不能为也。他说:“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4]64只要不断地剥落本心,一旦明理,则人皆可为尧舜。
四、文化观之异:判定佛教的正统与异端身份
对处于强势地位的佛教文化进行批判和检讨、重振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朱、陆所处时代的儒家学者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有感于当时儒学影响减弱而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张之势,朱熹感慨地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2]408在儒学萧瑟的现状和颓势面前,朱熹和陆九渊自觉地担负起复兴儒学的使命,如何对待佛教这种与儒学异质的文化就成为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本体论到功夫论所体现出来的等级性与平等性物质来看,朱、陆二人对佛教的态度也继续体现出这样的差异。
朱熹对于佛教持反感的态度,因而缺少了对异质文化的平等意识和包容胸怀。他立儒学为正统,把与儒家价值伦理相异的佛教定位为异端。如果仅从认识判断的角度而言,不相同则相异,把相异者称为异端本没有价值层面的褒贬、善恶之意。但是,朱熹的目的在于把“异”归之于“邪”,把“同”、“异”之别上升为“正”、“邪”对立的价值层面,这样一来,就为他坚决地反对和排斥包括佛教在内的异质文化提供了伦理基础。朱熹说:“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2]2719朱熹还说:“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论道者,安得不辟之乎!”[2]3963更进一步,朱熹把异端归入邪说之伍。他接着说:“释氏生西竺,汉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汉窦后始好尚之。自晋梁以及于唐,其教显行,韩公力排斥之,然后大道得不泯绝,有识之士谓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识高明,熟知其害而务去之乎”[8]
事实上,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创造和财富,多元文化中不同文化主体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用现代的观念来说,唯有不同民族所创造的差异性文化的存在,世界文化才显得丰富多彩和充满生命力。因此,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通过有选择地吸取和扬弃的过程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宋代新儒学在本质上正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们所宣扬和主张的并非如此。
与朱熹把佛教归于“邪说”的文化观不同,陆象山较为客观地从认知层面把佛教划归为与儒学不同的“异”,表现了他对佛教文化的尊重与平等意识。象山虽然也排佛,但不是如朱熹那般以“邪”视之、攻之、灭之,而只是以“异”视之,认真审视和与之辨理。象山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佛教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取舍多是依理而非情感之喜好。象山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今世类指佛老为异端。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却指那个为异端?”[4]402在象山看来,所谓“异字与同字为对,有同而后有异也”[4]177。象山进一步解释说:“盖异与同相对,虽同师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不同,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有人问吾异端者,吾对曰:‘子先理会得同底一端,则凡异些者,皆异端。’”[4]402可以看出,象山对儒学与佛学只是作学理上的分别。不仅如此,象山更是认为儒学与佛学平等地具有社会功用和价值。
据《语录上》记载,刘淳叟参禅,其友周姓者问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参禅?”淳叟答曰:“譬之于手,释氏是把镢头,儒者是把斧头。所把虽不同,然却皆是这手。我而今只反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头处明此手,不愿就他把锄头处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谓善对。”[4]402这段话不难看出:“在象山看来,如果儒学可算是把斧头,那么佛教也算把锄头,都是可以使手‘明’(使手发挥更大作用)的工具。而若有人只从斧头处‘明’此手,不要从锄头处‘明’此手,象山也表示理解。由此可见,佛教在象山的观念中不是毫无价值的。基于这样的立场,象山对那种随意指认佛禅损人心害圣道的行为极为反感。”[9]291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先秦到唐宋时期的儒学并没有紧随时展的脚步及时地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因而导致了儒学的衰弱。因此,隋唐时期佛教的勃兴与繁荣从现象来看是对儒学主流地位的乘虚而入,从实质上说却是合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自然选择。在复兴儒学的时代任务面前,与朱熹过多地把目标和着力点放在消除外在因素上的做法不同,象山勇敢地直视儒学理论自身的欠缺,直指根本。
概言之,正如李承贵在对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中对象山的评价时指出:“象山对于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平等尊重超越了同时代众多儒士的等级意识,在儒学阵营里,犹如一盏明灯,闪耀炽烈而异样的光芒。其中所显示出的学术思想观点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光大。那就是‘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唯理是准’的平等判学原则,‘客观公正’的为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9]297-298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5.
[2]朱熹.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
[3]洪修平.儒佛道哲学名著选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1.
[4]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9.
[7]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