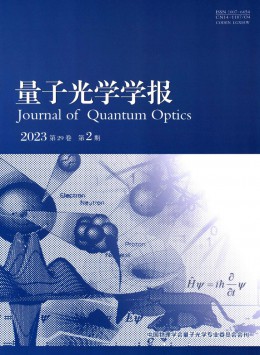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人们通常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如何理解量子力学的争论,看成是继地心说与日心说之后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就像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整个认知图景一样,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争论也蕴含着值得深入探讨的对理论意义与概念变化的全新理解以及关于世界的不同看法。有趣的是,他们俩人虽然都对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爱因斯坦在最早基于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并运用光量子概念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以及运用能量量子化概念推导出固体比热的量子论公式之后,却从量子论的奠基者,变成了量子力学的最强烈的反对者,甚至是最尖锐的批评家。截然相反的是,玻尔在1913年同样基于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了半经典半量子的氢原子模型之后,却成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奠基人。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反对,不是质疑其数学形式,而是对成为主流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深感不满。这些不满主要体现在爱因斯坦与玻尔就量子力学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的三次大论战中。他们的第一次论战是在1927年10月24日至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索尔未会议上进行的。这次会议由洛伦兹主持,其目的是为讨论量子论的意义提供一个最高级的论坛。在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第一次听到了玻尔的互补性观点,并试图通过分析理想实验来驳倒玻尔—海森堡的解释。这一次论战以玻尔成功地捍卫了互补性诠释的逻辑无矛盾性而结束;第二次大论战是于1930年10月20日至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并由朗子万主持的第六届索尔未会议上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关于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仍然是许多与会代表所共同关心的主要论题。爱因斯坦继续设计了一个“光子箱”的理想实验,试图从相对论来玻尔的解释。但是,在这个理想实验中,爱因斯坦求助于自己创立的相对论来反驳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关系,反倒被玻尔发现他的论证本身包含了驳倒自己推论的关键因素而放弃。
当这两个理想实验都被玻尔驳倒之后,爱因斯坦虽然不再怀疑不确定关系的有效性和量子理论的内在自洽性。但是,他对整个理论的基础是否坚实仍然缺乏信任。1931年之后,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质疑采取了新的态度:不是把理想实验用作正面攻击海森堡的不确定关系的武器,而是试图通过设计思想实验导出一个逻辑悖论,以证明哥本哈根解释把波函数理解成是描述单个系统行为的观点是不完备的,而不再是证明逻辑上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第三次论战的焦点就集中于论证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观点。1935年发表的EPR论证的文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从写作风格上来看,EPR论证既不是从实验结果出发,也不再是完全借助于思想实验来进行,而是把概念判据作为讨论的逻辑前提。这样,EPR论证就把讨论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问题,转化为讨论量子力学能否满足文章提供的概念判据的问题。由于这些概念判据事实上就是哲学假设,这就进一步把是否满足概念判据的问题,推向了潜在地接受什么样的哲学假设的问题。例如,EPR论证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对于一种物理理论的任何严肃的考查,都必须考虑到那个独立于任何理论之外的客观实在同理论所使用的物理概念之间的区别。这些概念是用来对应客观实在的,我们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描绘出实在的图像。为了要判断一种物理理论成功与否,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两个问题:(1)“这理论是正确的吗?”(2)“这理论所作的描述是完备的吗?”只有在对这两个问题都具有肯定的答案时,这种理论的一些概念才可说是令人满意的。”〔3〕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这段开场白至少蕴含了两层意思,其一,物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运用物理概念来描绘客观实在,是因为物理概念是对客观实在的表征,由这些表征描绘出的实在图像,是可想象的。这是真理符合论的最基本的形式,也反映了经典实在论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二,如果一个理论是令人满意的,当且仅当,这个理论既正确,又完备。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理论与完备的理论呢?EPR论证认为,理论的正确性是由理论的结论同人的经验的符合程度来判断的。只有通过经验,我们才能对实在作出一些推断,而在物理学里,这些经验是采取实验和量度的形式的。〔4〕也就是说,理论正确与否是根据实验结果来判定的,正确的理论就是与实验结果相吻合的理论。但文章接着申明说,就量子力学的情况而言,只讨论完备性问题。言外之意是,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即与实验相符合,但不一定是完备的。为了讨论完备性问题,文章首先不加证论地给出了物理理论的完备性条件:如果一个物理理论是完备的,那么,物理实在的每一元素都必须在这个物理理论中有它的对应量。物理实在的元素必须通过实验和量度来得到,而不能由先验的哲学思考来确定。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又进一步提供了关于物理实在的判据:“要是对于一个体系没有任何干扰,我们能够确定地预测(即几率等于1)一个物理量的值,那末对应于这一物理量,必定存在着一个物理实在的元素。”
文章认为,这个实在性判据尽管不可能包括所有认识物理实在的可能方法,但只要具备了所要求的条件,就至少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方法。只要不把这个判据看成是实在的必要条件,而只看成是一个充足条件,那末这个判据同经典实在观和量子力学的实在观都是符合的。综合起来,这两个判据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物理量能够对应于一个物理实在的元素,那么,这个物理量就是实在的;如果一个物理理论的每一个物理量都能够对应于物理实在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物理学理论就是完备的。然而,根据现有的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当两个物理量(比如,位置X与动量P)是不可对易的量(即,XP≠PX)时,我们就不可能同时准确地得到它们的值,即得到其中一个物理量的准确值,就会排除得到另一个物理量的准确值的可能,因为对后一个物理量的测量,会改变体系的状态,破坏前者的值。这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关系所要求的。于是,他们得出了两种选择:要么,(1)由波动函数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量子力学的描述是不完备的;要么,(2)当对应于两个物理量的算符不可对易时,这两个物理量就不能同时是实在的。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概念阐述之后,接着设想了曾经相互作用过的两个系统分开之后的量子力学描述,然后,根据他们给定的判据,得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结论。EPR论证发表不久,薛定谔在运用数学观点分折了EPR论证之后,以著名的“薛定谔猫”的理想实验为例,提出了一个不同于EPR论证,但却支持EPR论证观点的新的论证进路。出乎意料的是,爱因斯坦却在1936年6月19日写给薛定谔的一封信中透露说,EPR论文是经过他们三个人的共同讨论之后,由于语言问题,由波多尔斯基执笔完成的,他本人对EPR的论证没有充分表达出他自己的真实观点表示不满。从爱因斯坦在1948年撰写的“量子力学与实在”一文来看,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的论证主要集中于量子理论的概率特征与非定域性问题。他认为,物理对象在时空中是独立存在的,如果不做出这种区分,就不可能建立与检验物理学定律。因此,量子力学“很可能成为以后一种理论的一部分,就像几何光学现在合并在波动光学里面一样:相互关系仍然保持着,但其基础将被一个包罗得更广泛的基础所加深或代替。”显然,爱因斯坦后来对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问题的论证比EPR论证更具体、更明确。EPR论证中的思想实验只是隐含了对非定域性的质疑,但没有明朗化。但就论证问题的哲学前提而言,爱因斯坦与EPR论证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本文下面只是从哲学意义上把EPR论证看成是基于经典物理学的概念体系来理解量子力学的一个例证来讨论,而不准备专门阐述爱因斯坦本人的观点。
二、玻尔的反驳与量子整体性
玻尔在EPR论证发表后不久很快就以与EPR论文同样的题目也在《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反驳EPR论证的文章。玻尔在这篇文章中重申并升华了他的互补观念。玻尔认为,EPR论证的实在性判据中所讲的“不受任何方式干扰系统”的说法包含着一种本质上的含混不清,是建立在经典测量观基础上的一种理想的说法。因为在经典测量中,被测量的对象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可以被忽略不计,测量结果或现象被无歧义地认为反映了对象的某一特性。但是,在量子测量系统中,不仅曾经相互作用过的两个粒子,在空间上彼此分离开之后,仍然必须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被测量的量子系统与测量仪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将会在根本意义上影响量子对象的行为表现,成为获得测量结果或实验现象的一个基本条件,从而使人们不可能像经典测量那样独立于测量手段来谈论原子现象。玻尔把量子现象对测量设置的这种依赖性称为量子整体性(whole-ness)。
在玻尔看来,为了明确描述被测量的对象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希望把对象与仪器分离开来的任何企图,都会违反这种基本的整体性。这样,在量子测量中,量子对象的行为失去了经典对象具有的那种自主性,即量子测量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量子对象的行为表现,既属于量子对象,也属于实验设置,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量子测量中,“观察”的可能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突出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不仅不能离开观察条件来谈论量子现象,而且,试图明确地区分对象的自主行为以及对象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玻尔指出,“确实,在每一种实验设置中,区分物理系统的测量仪器与研究客体的必要性,成为在对物理现象的经典描述与量子力学的描述之间的原则性区别。”〔8〕海森堡也曾指出,“在原子物理学中,不可能再有像经典物理学意义下的那种感知的客观化可能性。放弃这种客观化可能性的逻辑前提,是由于我们断定,在观察原子现象的时候,不应该忽略观察行动所给予被观察体系的那种干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之打交道的那些重大物体来说,观察它们时所必然与之相连的很小一点干扰,自然起不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作用量子的发现,揭示了量子世界的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观念的确立,又相应地导致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根本问题。首先,就经典概念的运用而言,一旦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或词语,不再以连续性的观念为基础,它们就会成为意义不明确的概念或词语。如果我们希望仍然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量子现象,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限制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和精确度。对于完备地反映微观物理实在的特性而言,描述现象所使用的经典概念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这是玻尔的互补性观念的精神所在。有鉴于此,玻尔认为,EPR论证根本不会影响量子力学描述的可靠性,反而是揭示了按照经典物理学中传统的自然哲学观点或经典实在论来阐述量子测量现象时存在的本质上的不适用性。他指出:“在所有考虑的这些现象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那种以任意挑选物理实在的各种不同要素而同时牺牲其他要素为其特征的一种不完备的描述,而是那种对于本质上不同的一些实验装置和实验步骤的合理区分;……事实上,在每一个实验装置中对于物理实在描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方面的放弃(这些方面的结合是经典物理学方法的特征,因而在此意义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彼此互补的),本质上取决于量子论领域中精确控制客体对测量仪器反作用的不可能性;这种反作用也就是指位置测量时的动量传递,以及动量测量时的位移。正是在这后一点上,量子力学和普通统计力学之间的任何对比都是在本质上不妥当的———不管这种对比对于理论的形式表示可能多么有用。事实上,在适于用来研究真正的量子现象的每一个实验装置中,我们不但必将涉及对于某些物理量的值的无知,而且还必将涉及无歧义地定义这些量的不可能性。”其次,就量子描述的可能性而言,玻尔认为,我们“位于”世界之中,不可能再像在经典物理学中那样扮演“上帝之眼”的角色,站在世界之外或从“外部”来描述世界,不可能获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知识。玻尔把这种描述的可能性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对自我认识的可能性进行了类比。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知觉主体本身是进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这一事实,限制了对自我认识的纯客观描述的可能性。用玻尔形象化的比喻来说,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因此,量子描述的客观性位于理想化的纯客观描述与纯主观描述之间的某个地方。
为此,玻尔认为,物理学的任务不是发现自然界究竟是怎样的,而是提供对自然界的描述。海森堡也曾指出,在原子物理学领域内,“我们又尖锐地碰到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即在科学方面我们不是在同自然本身而是在同自然科学打交道。”爱因斯坦则坚持认为,在科学中,我们应当关心自然界在干什么,物理学家的工作不是告诉人们关于自然界能说些什么。爱因斯坦的观点是EPR论证所蕴含的。这两种理论观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不仅是有没有必要考虑和阐述包括概念、仪器等认知中介的作用的分歧,而且是能否把量子力学纳入到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当中的分歧。EPR论证以经典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为前提,认为正确的科学理论理应是对自然界的正确反映,认知中介对测量结果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玻尔与海森堡则以接受量子测量带来的认识论教益为前提,认为量子力学已经失去了经典科学具有的那种概念与物理实在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认知中介的设定成为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基本前提。第三,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而言,EPR论证认为,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界线。这意味着,所有的主体都能对客体进行同样的描述,并且他们描述现象所用的概念与语言是无歧义的。无歧义意味着对概念或语言的意义的理解是一致的。而对于量子测量而言,对客体的描述包含了主体遵守的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描述条件的说明,从而显现了一种新的主客体关系。为此,我们可以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类:其一,能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所有的主体对客体的描述都是相同的,EPR论证属于此类;其二,能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属于此类;其三,不可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包括了对测量条件的描述在内,玻尔对EPR论证的反驳属于此类。显然,EPR论证隐含的主客体关系与玻尔所理解的量子测量中的主客体关系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EPR论证是沿袭了经典实在论的观点,而玻尔的观点代表了他基于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总结出来的某种新的认识。在这里,就像不能用欧几里得几何的时空观来反对非欧几何的时空观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观反对量子意义上的理论观。因此,可以说,物理学家关于如何理解量子力学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他们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假设之间的争论。
三、实验的形而上学
EPR论证不仅引发了量子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哲学讨论,而且还创立了“实验的形而上学”,提供了物理学家如何基于形而上学的观念之争,最终探索出通过实验检验其结论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过程与寻找量子论的隐变量解释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量子力学的隐变量解释的最早方案是德布罗意在1927年提出的“导波”理论。1932年,冯•诺意曼在他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中曾根据量子力学的概念体系提出了四个假设,并且证明,隐变量理论和他的第四个假设(即,可加性假设)相矛盾,认为通过设计隐变量的观念来把量子理论置于决定论体系之中的任何企图都注定是失败的。冯•诺意曼的这一工作在为量子论的隐变量解释判了死刑的同时,也极大地支持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有意思的是,曾是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支持者与传播者的玻姆,在1951年基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精神出版了至今仍然有影响的《量子理论》一书,并在书的结尾,以EPR论证为基础,提出了“量子理论同隐变量不相容的一个证明”之后,从1952年开始反而致力于从逻辑上为量子力学提供一种隐变量解释的研究。
玻姆阐述隐变量理论的目标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试图用能够直觉想象的概念为量子概率和量子测量提供一种可理解的说明,证明为量子论提供一个决定论的基础是可行的;二是希望从逻辑上表明,隐变量理论是有可能的,“不论这种理论是多么抽象和‘玄学’。”玻姆的追求显然是一种信念的支撑,而不是事实之使然。在这种信念的引导下,玻姆在1952年连续发表了两篇阐述隐变量理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用经典方式定义波函数,假定微观粒子像经典粒子一样总是具有精确的位置和精确的动量,阐述了一种可能的量子论的隐变量解释,最后,用一个粒子的两个自旋分量代替EPR论证中的坐标与动量,讨论了EPR论证的思想实验,并运用量子场与量子势概念解释了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影响第二个粒子的动量的原因。
贝尔在读了玻姆的文章之后,认为有必要重新系统地研究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贝尔试图解决的矛盾是:如果冯•诺意曼的证明成立,那么,怎么会有可能建立一个逻辑上无矛盾的隐变量理论呢?为了搞明白问题,贝尔首先重新剖析了冯•诺意曼的关于隐变量的不可能性的证明和EPR论证中设想的思想实验,然后,抓住了隐变量理论的共同本质,于1964年发表了“关于EPR悖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贝尔引述了用自旋函数来表述EPR论证的玻姆说法,或者说,从EPR—玻姆的思想实验出发,以转动不变的独立波函数描述组合系统的态,推导出一个不同于量子力学预言的、符合定域隐变量理论的关于自旋相关度的不等式,通常称为贝尔不等式或贝尔定理,然后,用归谬法了量子力学的预言和贝尔不等式相符的可能性,说明任何定域的隐变量理论,不论它的变数的本性是什么,都在某些参数上同量子力学相矛盾。贝尔还假设,如果所进行的两个测量在空间上彼此相距甚远,那么,沿着一个磁场方向的测量,将不会影响到另一个测量结果。贝尔把这个假设称为“定域性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贝尔指出,如果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测量结果预言第二个测量结果,测量可以沿着任何一个坐标轴来进行,那么,测量的结果一定是已经预先确定了的。但是,由于波函数不对这种预先确定的量提供任何描述,所以,这种预定的结果一定是通过决定论的隐变量来获得的。贝尔后来申明说,他在“关于EPR悖论”一文中假设的是定域性,而不是决定论,决定论是一种推断,不是一个假设,或者说,贝尔的这篇文章是从定域性推论出决定论,而不是开始于决定论的隐变量。从逻辑前提上来看,贝尔的假设更接近于爱因斯坦的假设,他们都把“定域性条件”看成是比“决定论前提”更基本的概念。因此,贝尔的工作比冯•诺意曼和玻姆的工作更进一步地推进了关于量子力学的根本特征的理解。贝尔的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成为20世纪下半叶物理学与哲学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而且为进一步设计具体的实验来澄清量子力学的内在本性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粒子物理学家斯塔普(HenryStapp)甚至把贝尔定理的提出说成是“意义最深远的科学发现。”
同EPR论证一样,贝尔的这一发现也不是从实验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基于哲学信念的逻辑推理的结果。此后,量子物理学界进一步推广贝尔定理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验方案的探索工作并行不悖地开展起来。而这些工作都与EPR论证相关。就实验进展而言,物理学界承认,阿斯佩克特等人于1982年关于“实现EPR-玻姆思想实验”的实验结果,支持了量子力学,针对这样的实验结果,贝尔指出:“依我看,首先,人们必定说,这些结果是所预料到的。因为它们与量子力学预示相一致。量子力学毕竟是科学的一个极有成就的科学分支,很难相信它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我也认为值得做这种非常具体的实验。这种实验把量子力学最奇特的一个特征分离了出来。原先,我们只是信赖于旁证。量子力学从没有错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即使在这些非常苛刻的条件下,它也不会错的。”
虽然EPR论证的初衷是希望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还没有提出量子测量的非定域性概念,但是,物理学家则通常运用EPR思想实验的术语来讨论非定域性问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具体的实验结果使EPR论证失去了对量子力学的挑战性。一方面,这些实验证实了非定域性是所有量子论的一个基本属性,要求把在同一个物理过程中生成的两个相关粒子永远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不能分解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其中,一个粒子发生任何变化,另一个粒子必定同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相互影响与它们的空间距离无关;另一方面,这些实验也表明了EPR论证提供的哲学假设不再是判断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有效前提,而是反过来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玻尔在反驳EPR论证的观点中所蕴含的哲学启迪。总而言之,EPR论证尽管是基于哲学假设,运用思想实验,来驳斥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但在客观上,物理学家围绕这一论证的讨论,最终在思想实验的基础上出乎意料地发展出可以具体操作的实验方案,并且获得了有效的实验结果。这一段历史发展不仅证明,无论在哲学假设的问题上,还是在物理概念的意义理解的问题上,量子力学都不是对经典物理学的补充和扩展,是一个蕴含有新的哲学假设的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家玻恩得出了“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的断言。
四、认识论的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EPR论证—玻姆—贝尔这条发展主线是把对物理学问题镶嵌在哲学信念中进行思考的。这一历史片断揭示出,基于哲学信念的逻辑推理在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认知作用。一方面,在这些探索方式中,不论是EPR论证的真理符合论假设,玻姆的决定论假设,还是贝尔的定域性假设,它们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把量子力学纳入到经典物理学的概念框架或哲学信念之中。另一方面,检验贝尔不等式的物理学实验结果对量子力学的支持和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依旧固守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假设来质疑量子力学,而是应该颠倒过来,积极主动地揭示量子力学蕴含的哲学思想,以进一步明确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假设的适用范围。
但是,这种视域的逆转不是简单地倡导用量子力学的哲学假设取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假设,也不是武断地主张用玻尔的理论观替代EPR论证所蕴含的理论观,而是提倡摆脱习以为常的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确立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希腊延续下来的,追求概念与实在之间的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忽视或缺乏对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认知中介和理论框架的考虑。从起源上来讲,这种无视认知中介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源于常识,是对常识的一种延伸外推与精致化。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与巩固了这种思维方式。EPR论证也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使经典科学蕴含的哲学假设以具体化的判据形式呈现出来。然而,与过去的物理学理论所不同的是。量子力学不再是关于可存在量(beable)的理论,而是关于可观察量(observable)的理论,“是理论决定我们的观察内容”这一句话,既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感想,也为海森堡提出不确定关系提供了观念启迪。就理论形式而言,量子力学的理论描述用的是数学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用数学语言描述的微观世界是一个多位空间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类,很难直观地想象这样的世界,更不可能直接“进入”这个世界来“观看”一切。人类感知的这种局限性是原则性的,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微观世界的知识的全面获得。用玻尔的话来说,我们对一个微观对象的最大限度的知识不可能从单个实验中获得,而只能从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实验安排中获得。用玻恩的话来说,在量子测量中,观察与测量并不是指自然现象本身,而是一种投影。
第2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关键词: 科学实在论 内在实在论 带人面的实在论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作为科学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原本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实在论者,然而由于受到自尼采以来兴起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即非理性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经过80年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激烈争论,使他开始逐渐对科学实在论立场产生怀疑,并最终由强实在论转变为弱实在论,由科学实在论向人本主义实在论退让。《带人面的实在论》一书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根本立场的动摇。那么,普特南又为什么仅仅表现为一种立场上的转变,而不放弃实在论,却坚持捍卫一种内在实在论,并进一步从人的立场给予阐释呢?
一、从科学实在论立场退却
众所周知,W.塞拉斯作为美国科学实在论的创始人,因受其父R.塞拉斯的物理实在论的薰陶,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正是这一基本立场对普特南的强烈影响,使他成为继W. 塞拉斯之后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的科学实在论者。概括普特南的哲学,主要在如下方面突出了“科学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
在科学观上,他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近于真实,前后相继的理论拥有共同的指称,这证明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种客观实在性,他反对库恩的范式信念、不可通约性和科学革命的理论;坚持认为科学知识通过逐渐累积的方式而增长是科学的基本特征。库恩所反对的传统累积观的错误在于:原来用于辨认一个实体或自然种类的那些属性不必一定属于该实体或种类;人们也许会在后来发现那些属性并不是决定性的;也可能在其它的实体或自然种类中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拒绝认为最初给某一实体或自然种类所指定的属性就构成了指称它们的那些名词的“意义”。实际上,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的连续性中和不同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可比较性中,以及不同概念的变化中保持的某些共同的东西,不是传统理论所主张的构成名词或概念的不可改变的意义,而是固定的指称。换句话说,尽管人们对于一个事物所说的话不同,但都是谈的“相同的事物”。这是根据最初一次“命名”的因果关系得到的逻辑保证。以后所谈的有关属性便都必然地归属于那个最初指称者。另外,既然科学是逐渐累积而增长的,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因此科学进步也是无可怀疑的。新的科学理论总是比旧的科学理论能提供更正确的预言、更好的控制自然界的方法和更接近于科学真理。
在本体论上,虽然他声称自己的实在论既不是唯物主义实在论,也不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而是趋同实在论,但是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说:“如果给出适当的条件(包括适当语言的其它方面),‘有电子流经导线’这个陈述可以和‘房间里有一把椅子’的陈述,或‘我头痛’这个陈述同样在客观上是真的。在椅子(或感觉)存在的任何意义上,电子都存在着。”(〔1〕,第848页)即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科学术语都是有所指的,即便是“电子”这样的术语也如同“椅子”一类的词汇一样具有客观实在的指谓对象。
在认识论上,普特南坚持“真理符合说”;强调科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表述外部世界;决定科学陈述的真假,既不是人们的主观感觉,也不是人的内心结构或语言,而是外部事物。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描述性术语有所指谓,那么在理论科学中,真理的概念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也许所有的理论句子都是‘假的’;或者当谓词无所指谓时,就代之以为指定真值所作出的某种约定。总之,对于包括理论术语的句子来说,‘真值’概念会变得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也就无所谓真理了。”([2],p.25)为此,他认为只有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才能把科学研究 引上正确轨道。只是这种符合不是绝对的符合,而是存存一种趋同现象,即较新的理论总比较旧的理论更逼进真理。
但是,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尤其是面对反实在论的激烈挑战,使他逐渐发现自己的科学实在论立场中存在许多疑点。一是“词和特定客体之间”、“表达与实在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他认为自己过去把追求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吻合与一致看作是实在论的目的,认为概念或符号表达式可以通过指谓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而获得意义,是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这种“一致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的常识观念,而“常识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二是如果人们仅仅从反对“证实原则”的角度来批判分析哲学,那只是简单地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实在论者。事实上,具有组织信息功能的大脑,所能够熟练操作和把握的只是对某物的“感觉”、有关某物的“信息”、“符号”等等,而不是某物本身。换句话说,人的认识只能局限于感觉和影像方面,而与客观性无关。这个长期存在的、而且从未被真正解决的主体和客体、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矛盾性是动摇实在论的基础。三是当代的科学观不在于研究所谓的“主客观相符合的真理”是什么,而在于真理的价值、真理的意义,如何产生真理,如何从事科学发现、科学应用,即主要是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的问题,是生活、行为惯例和社会实践的问题;方法、实践和价值问题不解决,“真理”问题就不能够解决。他说,他提出有关真理的合理性标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如何才能够认识到真理,以及如何才能够理解这个世界。这种反思的结果使他从早期的强实在论立场撤退,力图以弱实在论的形式来摆脱科学实在论面临的困境。其具体做法是:
1.他以纠正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证实方法为前提, 从以客观实在为基础的本体实在论转向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认识实在论。由于比早期更自觉地注重逻辑问题,更倾向于对真理概念进行逻辑思考,故他从注重本体论上的“一致性”立场转变到认识论上的“逻辑性”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真理。在转变后的普特南看来,真理主要是语言、意义和实用价值的问题;一切概念和符号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不论它们是个人心理的还是公众性的,“它们本身如果不被使用就不是概念。符号本身并不内在地指称什么。”([3],p.18)只有在人们进行认识活动时,才能够将它们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在这里,普特南实际上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实用主义观点,突出了“指称问题上的语境的重要作用”;暗示了符号和概念的意义都是社会地和历史地被确定的,因而也都是变化的和相对的,确立了一种文化上和概念上的相对主义观点。
2.他放弃了“真理符合说”,提出了真理是理想化的, 是逻辑地被证实了的可能性的思想。他说,真理是在理想化的证实意义上与证实相一致的。它与靠现存证据的证实是对立的。这种理想化的证实和真理发展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那种机械的和僵化的真或假的“二价原则”只能是对具有各种可能性的真理发展的约束和限制,因为真理在本质上不是直观地、外在地可参照的,而是理性范围内的、逻辑的、抽象的、内在的相互关系。真理不涉及。直接外在的经验证实。比如一位具有实在论思想的科学家,如果他拥有某种逻辑,他就会认为有某种行为在保护着真理。这样,“如果他认为理论T1是真的,而且认为理论T2也是真的,那么从逻辑上,他就会认为T1和T2,即T1和T2的结合也是真的。”([4],p.90)为此,他非常欣赏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不可知论的观点,认为康德是最先提出内在真理观的人,认为“康德不仅放弃了我们的观念和物自体之间的相似的概念,甚至还放弃了任何抽象同构的概念。这就意味着他的哲学中不存在真理符合理论”。他说,从康德的著作中能够引出的唯一答案是:“一种知识,即一个‘真陈述’,是这样一个陈述,它能够在一和我们的本性实际上可能具有的充分的经验基础上被有理性的东西所接受。而在其它任何意义上,‘真理’都无法为我们接受和理解,真理就是最完善的适合性。”([3],p.64)这也就是普特南的有关真理的“合理性”的构想。
3. 他认为真正具有逻辑性的真理概念是概率的或非决定论的实在论观点,即非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观点。传统的所谓“与实在一致”是一种非认识论关系。为此他表明:在经典逻辑和决定论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实在论者。他说,传统的两分法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开来是太绝对了。判断是不是事实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接受它是不是合理的。“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都预设了价值。”([3],p.128 )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事实和世界。“我们必须具有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才能有一个经验的世界,这些标准展示了我们理想思辨的理智概念的一部分。简言之,我主张‘实在世界’依赖于我们的价值,当然后者也依赖于前者。”([3],p.134)再一方面,他也反对在多种现象之后, 总存在一个反映共同的和终极本质的单一的“实在”的形而上学假定。他认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意向性现象的一切情形共同具有的可以科学地描述的性质。因此,也不要企图探察现象背后的实在和本质。但是,在量子力学所展示的非决定论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他仍然坚持自己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
4.在坚持真理是一种极限,因而具有趋向性的基础上, 他又进一步把真理看作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真理不是已经达到,而只是趋向,而且可能有多种趋向。因此一个陈述被证实,只是说它有成为真理的可能性,不等于它就是真理。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以及根据这一理论所作出的一些预言,虽然已经多次得到证实,但并不等于说它就是真理,因为“这里的困难是,起到真理作用的谓词,即导致成功预测的谓词并不具有真理的性质。”([4],p.90)再一方面,一个命题或句子的证实条件总是随着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它不可能永远被固定。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现在认为被已经证实了的一些命题或理论是错的,而且可以发现现在认为是正确的程序也是不正确的,而其它的程序则更好。所以,当下被证实的命题或理论可能是假的,而导致我们相信这个命题或理论的检验也可能是非常不可靠的。既然真理只是一种可能性和理想化的证实,而非完全现实的证实,所以真理是多维的。这种多维性能够更好地反映世界复杂的内在结构。只坚持一种真理的观点是狭隘的和站不住脚的。
二、保卫内在实在论
面对反实在论的不断冲击,普特南并没有完全退出实在论的阵地,相反在1990年出版的《拥有人面的实在论》一书中又公开提出“保卫内在实在论”的口号。那么究竟何谓“内在实在论”呢?普特南解释说,以前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主要有三种:其一主张世界是由总量恒定的非精神客体构成的,即朴素的唯物主义或客观主义;其二主张只存在一种有关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形的真实而完整的描述,即经验主义或真理一元论;其三主张真理只涉及一致性,即观念与实在之间的符合论或一致论。这三种观点除了拥有一套华而不实的东西外,并没有什么清楚明白的内容。离开一种哲学传统,所谓“客体”、“总量恒定”、“非精神的”、“有关世界的唯一真实而完整的描述”都没有确切的性质与含义。所以,依照内在实在论的观点,这三种形而上学实在论,实质上都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并依赖于各种进一步的假设和概念,否则必将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如果他承认“存在一种构成世界的总量恒定的非精神物质”,那么他就不能不接受真理符合论;如果他说,“存在一种构成世界的总量恒定的非精神物质”,但这种物质只有在“内在真理”的意义上,即在构成认识主体的一部分的意义上,才可以被当作真,这样,也就等于否定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而内在实在论既不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不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它认为“真理是一种性质,这一性质不同于论证、或现存证据的或然性;它不是仅仅取决于说话者的现存记忆和经验,而是我们不应该抛弃的对实在的一种洞察。”([5],p.32)
那么在内在实在论看来,应该怎样理解抽象层次上的词和概念的指谓或理论描绘的世界图象呢?普特南说,一般科学上的术语、概念都有确定不移的指谓,从而显示了它们的客观实在性。比如最有争议的“电子”,反实在论者总是否定它的真实存在,然而科学家们却坚信其存在已经得到证明。否则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玻尔在1900年和1934年使用的同一个词“电子”是合理的,并认定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是描述同一个对象?
“虽然玻尔在1900 年的主观概率度规(subjectiveprobability metric)并不是他在1934年的主观概率度规:但这并不是说,在玻尔的习用语汇中‘电子’这个词,或是任何其它的德语词,是否改变了它的指谓(reference)”。([5],p.33)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为真的原理告诉我们,应当采纳玻尔一贯指称过的那个被称之为电子的东西。我们应该说,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相同实体的不同理论,而不应该说,有多少种理论就有多少种实体。所以不论是词和概念,还是理论的辩护和解释都存在客观性。
当然不能否定解释具有主观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指谓也是主观的;不能说只存在“理性重建”或“经验建构”的事实,不存在有关科学和日常实践中说话者所指谓的客观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拥有一种独立于一般程序和实践的指谓概念;我们一直是通过这种程序和实践认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信念背景的人们,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涉及的是同一事物。”([5],p.34)以人类对植物的认识为例,毫无疑问我们都会认为200年前人类称作“植物”的东西, 与今天人类叫做“植物”的东西是一类(或近似于我们今天叫做“植物”的东西)。尽管我们不同意200年前人类对植物的本质特征持有的观念,因为200年来人类语言中绝大多数的常用词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们的指谓含义,但是如果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主观的,如果翻译实践也是主观的,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任何有关指谓和真理的理论之间或语言之间的概念能够完全保留下来。
但是如果认为所有的指谓都是客观的,那么又怎么样为客观辩护?是否在大家都作了一致理解的情况下就是客观的,在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主观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决定于人们确立的“多数”一致的标准有多高,也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文化。比如在宗教领域,教皇的一贯正确性,早就被作为客观证明了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必然使人想到这一点,“证实了的东西不一定是指人们实际上说已得到证实的东西,而是人类中某种理想的有‘能力’的成员所要说的东西得到辩护。”([5] ,p.35)这种为客观性提出的论据, 实际上与街上那些把所有哲学当作主观的东西的人们所提出的论据并无二致。因此,为客观辩护的标准也不应是大家认为的“一致”,客观就是指指谓对象的实在性。不论是翻译的概念、解释的概念还是辩护的概念,只要拥有指谓对象就具有客观性。
所以,“我相信存在一种真理的概念,或说得普通一点,存在正确的概念。这种概念,我们经常使用,而且完全不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者用以描述‘符合’本体事实状况的概念。”([5],p.40)比如从日常生活与理智实践的观点上看,把点作为个体的理论和把点作为极限的理论在适当的环境中,两者都是正确的。根据超距作用描述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根据场的概念描述同样情况的物理学理论,两者也都可以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包含着真理的认识;在精确的理性思维和实践中也包含着真理的认识;在科学的、数学化的认识形态中有真理,在非科学的、非数学化的认识中也有真理。对象是一个,而承担真理的知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普特南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为自己构绘出一幅有关外部世界的哲学概念图,这并不是件坏事。坏的是忘记它们是图,并把它们看作就是“这个世界”。与其他哲学家一样,普特南也有一幅概念图,在他的图中,从理论的两种不相容的本体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体论都可以是正确的意义上看,客体是与理论相依赖的。说这些本体论都是正确的,并不是说存在着与拥有广延性的实体一样的“在那里头”的场以及逻辑建构意义上的场;也不是说同时存在绝对时空点和仅仅作为界限的点。而是说各种表述和各种理论在一定场合下都同样是适宜的。在实用主义的传统中,它是说,各种手段在其为之设计的关系中,如果功能是相同的话,那么它们在我们所能控制的各方面都是等效的。
既然客体是与理论相依赖的,所谓真理是根据某一语言中各分项间以及固有的非理论化实体中各分项间的“对应联系”而定义或解释的思想就必须被放弃,而确立这样一种观念或认识论的图景:“真理不过是观念理性化的可接受性。”那些被认定为“真”的东西,在赋有“理性和可感觉性”的生物拥有的经验与智力的基础上,应被认为是有保证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草拟一种有关“实在”的保证理论(即一种有关保证的“本质”的理论),更不用说一种观念化的保证理论了。在实践中,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建构起一种有关世界的独一无二的理论,只是建构起各种不同的理论,而且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等效的。因为我们实践的多元论必然导致理论的多元论。所以在普特南的概念图中,存在许多个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作为描绘的对象当然有客观性,但也有多面性和模糊性。不过模糊的谓项并没有什么错误,错误的是在特定场合中太模糊,这常常是一些实在论者忽略或错误表述的另一个事实。
三、人本主义倾向
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激烈争论中,普特南虽然没有完全抛弃实在论,并力图保卫它,但是在实在论的内涵方面,他已从早期的客观实在的立场转向客观实在对人的依赖性立场,即从外在实在论转向内在实在论;从科学知识的独立性转向对认识主体、认识工具的依存性;从科学理论的辩护和证明转向科学理论的解释;从真理的趋同性和符合论转向真理的多元论和实用论;从欣赏唯物主义转向欣赏唯心主义和操作主义;从注重本体论研究转向到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继而又转向到注重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研究。而所有这一切,尤其是他的内在实在论立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实在论日益带有人本主义色彩。这种带人性的实在论色彩可以从如下方面证明:
首先在对待科学和世界的态度问题上,他对尼采所谓的“随着科学范围的日益扩大,它所触及的悖论的地方也就越多”的观点表示欣赏,并进一步考察:是否随着科学知识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和这个世界本身也变得愈来愈自相矛盾。以只有少数人理解和熟悉的量子力学为例,一方面,它与经典物理学相区别的独特性就在于:有关这一理论的任何应用都需要没有被包括在这一理论系统之内的“科学仪器”或“观察者”的存在;另一方面,“原则上又没有关于整个宇宙的量子力学理论”。许多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都已经注意到:在理论系统和观察者的切面之间,用来测量和检验理论应用的仪器最终是靠在观察者一边的。以至玻尔在他的所谓“哥本哈根解释”中明确表示:“只有与特殊的实验场景中的特殊的测量仪器相联系,该系统中的每一种性质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和存在的。”([5],p.4 )这也正是许多人认为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不可比较的原因所在。然而要想利用测量仪器获得满意的描述和结果,就必须利用同样存在于经典物理学中的语言和数学公式。这样,在玻尔看来,量子力学又没有简单地使经典物理学废弃不用。
从上述量子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关系上看,这好象是足够悖谬的,但是普特南却证明:量子物理学对于经典物理学的依赖性却不是悖论。在他看来,所谓的量子力学理论只不过是“牛顿的想象力所要求的一部分”。因为牛顿的物理学拥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它对几个世纪以来的神学、哲学、心理学、乃至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给予我们的是“上帝的视野”,是上帝对整个宇宙的洞察。这个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如果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就会认为我们自身就是这架巨大机器的一个分系统。如果你是一个二元论者,就会认为只有我们的身体才是这架机器的一部分。迄今以来,我们对于这架机器的测量、观察和物理学上的描绘,只不过是整个事物内部的相互作用。这幅完美的宇宙图的梦,即实际上包括描绘这个宇宙的理论家—观察者在内的宇宙图的梦,既是物理学的梦,也是形而上学的梦,甚至象笛卡尔这样的二元论者也梦想构绘一幅完美的宇宙图。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梦想绘制一幅宇宙图的人都感觉到需要一门额外的基础科学,即一门与描述“灵魂、思维或智力”的心理学有关的基础科学,以实现自己的美梦。自十七世纪以来,整个西方文化一直在做着这种美梦,而且凡是借助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利用实验或数学方法从事过这种工作的人都一定感觉到这是一场梦。
但是,玻尔的哥本哈根解释却恰恰放弃了这种梦想。象康德一样,玻尔感觉到这个世界“本身”是超越描绘它的人类思维的能力的。即便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即我们的经验的世界也不能只凭借一幅图就实现其完整的描绘,而常常需要的是不同类型图的互补。在一些实验场合中必须绘制一幅波动图,在另一些实验场合中又必须绘制一幅粒子图。要放弃只利用一种描绘来说明所有场合的观念;要确立物理学概念与实验场合相互依存的思想;要认识到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即整个宇宙系统之间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量子力学的核心,是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本质所在。但是,却不能由此说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是完全对立的。只能说量子力学在本质上涵盖了经典物理学的应用。比如冯诺依曼(Von Neumann )的经典著作就向我们表明了如何利用纯粹的量子力学术语来分析测量的案例。所以,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之间具有一种依存关系和包含关系,并不相互矛盾。只是经典物理学认为它所描绘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量子力学则认为人类只能描绘包含自身在内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因实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理智无能力认识一个“自在”的世界。
这是不是说,普特南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可知论者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关于形而上学,普特南说,“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事实,在一种意义上,哲学的任务是克服形而上学;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的任务又是持续形而上学的讨论。每一个哲学家都会一面在叫喊,“这项事业是徒劳的、轻薄的、疯狂的——我们必须说:停止!”,而另一面又叫唤,“这项事业完全是最一般、最抽象层次上的反映,停止它将是对理性的一种犯罪。”当然,哲学问题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正如S.卡威尔(Stanley Cavell)曾经论述的,“存在有关它们的或是更好或是更坏的思考方式。”不论有多少人认为哲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如何的无益和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失败,但“我还是想展示一些原理,这些原理在我们面对一些叫做形而上学的事情以及一些叫做认识论的事情遭受失败而感到失望的时候不应当抛弃。”([5],p.19)哲学虽然不能构成存在、知识和文化得以确立的基座, 但是作为一种讲话和思维的方式对于人类的实践和精神无疑有着重要价值。当然哲学的重要性不在于说“我拒绝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的争论”,但是它却可以表明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歪曲了我们借助概念而生活的生命。一场争论是无益的,并不意味着相互竞争的图象是不重要的。因为哲学所编造的幻觉属于人类生活自身的本性,而且需要进一步阐明。
那么普特南究竟展示了哪些不应当抛弃的哲学原理呢?1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所作的陈述不管是否有根据,都是事实,但是其中多数事实都是“价值事实”。2 )一个陈述的意义不管是否有根据都不取决于处于一种文化中的多数公民的口头评判,而是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实际功用。3)有根据的断言的规范和标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们是随时间而演变着的。4 )这些规范和标准总是反映我们的兴趣和价值,而我们的理智兴趣图通常只是人类兴趣图的一部分。5 )一切事物(包括有根据的断言)的规范和标准都能够改变。存在着更好或更坏的规范和标准。这五条原理概括到一点:评判一切陈述和命题都取决于人们的兴趣和价值;人们的兴趣和价值观念变了,一个陈述或命题是否有根据和理由也就变了。这既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哲学观点。一切有无、真伪、好坏都以人而论。
既然如此,普特南虽然一再强调要保护内在实在论,然而他的“实在论”已经完全人本主义化了。这正象他自己所陈述的,“如果说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实在论者’,那么我们最好都是实在论者——用小r代表这类实在论者。 但是关于‘实在论’的形而上学说法却超出拥有小r的实在论之外,而具有某种哲学幻想的特征。”([5],p.26)对于小r的实在论来说,它不需要回答形而上学实在论者渴望解答的问题。诸如:“一个具体客体(空—时域)的存在怎么可能是一种约定?A(椅子)和B(空—时域)的同一性怎么可能是一种约定?”等问题。在小r看来,这些恰恰是生活中的一种事实。他能够感觉到它。 那对于其他人是一种压力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东西。而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基本特征则集中体现在这一观念中,即主张“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是构造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的世界图景”([6],p.107)为此他们总是竭力描绘一幅巨大的先验论的图画; 在这幅图中存在一套固定的“独立于语言”的客体(其中一些是抽象的,另一些是具体的),以及术语与它们的附加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普特南认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宇宙图景只是部分地与它意欲解释的常识观点相一致。从常识的观点上看,形而上学实在论所描绘的图象是非常模糊的。“我们抓牢哲学家们的拥有小r的实在论,放弃拥有大R的实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完全没有任何错。”([5],p.28)
作为结论,普特南所描绘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图象是:“一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之辩护,只能够通过成功来证明它正当;而成功又要通过人的兴趣和价值来判断,而人的兴趣和价值不仅在进化着,并同时获得改造,而且与我们的有关这个世界本身的进化着的图象相互作用。正象必须抛弃‘约定和事实’的绝对两分法一样,基于类似的理由,也必须抛弃‘事实和价值’的绝对两分法。另一方面,它又毕竟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图象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也不是我们以某种方式讲话的气质的产物。”([5],p.29)换句话说,既不是我们制造了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语言或文化制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从无中生有的;它不是一种产品,而是:“世界就是世界”。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却是与理论相依赖的,是与我们的兴趣、价值观念和最后的审视紧密相关的。
参考文献
[1] 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
[2] Hilary Putnam,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1978.
[3]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1.
[4] A.Baruch,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ed,New Jersey,1989.
第3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然而,三维目标的提出已历时多年,笔者通过对十几所高等学校物理学师范生的培养计划的调查了解到,我国不少高等学校物理学师范生的课程设置还是跟不上基础课程改革的步伐,尤其在西部,有的一般综合大学物理学师范生的课程设置还停留在学科知识本位的传统课程观上。本文将选取西部某一般综合大学(以下简称X大学)与东部某985大学(以下简称D大学)2012年物理学师范生的教学计划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以期给落后的课程设置以良好的启示。
一比较分析
从整体上看,不含学校统一的公选课,D大学共开设68门课,共210.5学分,共4843学时,大于4年的总学时4320学时(每周按30学时计算),学生有选择的空间,由于实行了完全学分制,学生必须修满160学分;X大学共开设48门课,共150学分,共3148学时,小于4年的总学时4320学时,由于未实行学分制,学生只要修完安排的课程考试及格就行,除学校统一的公选课外,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
1通识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两大学通识课程开设情况如表一。学生处理社会关系及交往合作的能力的培养是由通识课程来实现的。D大学与X大学在这一模块的学分比例分别为36.9%和32.9%,主要区别是X大学开设了“某省省情”的课,它是地方政策,对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计算机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只开了三门有关计算机的课,共计144学时。现代人称不懂电脑不能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是文盲,而大多数学生进大学时所具有的计算机知识不多,有的甚至是零,D大学正是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共开了7门有关计算机的课,共计414学时,加强计算机方面的能力培养。
2学科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两大学学科课程开设情况如表二。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必备的学科知识能力的培养是由学科课程来实现的。D大学与X大学在这一模块区别最大,学分比例分别为40%和51.3%,X大学学分比例超过了一半,偏重学科知识的培养,折射出课程设置者的学科知识本位思想,反映了课程设置者固步自封、懒于改革的落后思想。D大学则根据基础课程的改革,勇于探索。首先,D大学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实验整合为便于管理、分层次教学的《大学物理实验》,它比传统的按知识板块划分实验课程更有利于知识板块之间的横向联系,有利于学生对物理学知识整体的全面认识,有利于学生全面看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它针对传统实验课程中经典物理实验偏多而缺少综合性、设计性等实验而增设了这几方面的实验,有利于学生的综合能力、独立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而《近代物理实验》重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从实验技术型向实验研究型方向转型,相比较,X大学在这一点的培养力度显得不足。其次,当代社会需求的是知识面广、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教师,学校的教育和课程设置要为学生毕业后不断的进行知识和能力的更新打下宽厚的基础,能力全面的要求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教学内容不断的增加,而教学时数有限,这一矛盾也是课程设置所面临的问题。D大学不仅将《理论力学》、《热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整合为一门《理论物理》课,缩短了教学时数,从各类大学的师范专业主要是向社会输送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点来说,这种整合是合理的,同时也将《力学》、《电磁学》、《热学》、《光学》、《原子物理》的学时相应的减少。而X大学按知识板块开设四大力学的主要原因是有学生要考研,但X大学物理系自建校多年来总共才考上了5个硕士生,为满足少数学生考研的需求,应用开设选修课的方法,而不应用一刀切的方法重小头失大头。从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来看,尤其是X大学这类层次的学生,由于数学知识的缺乏和理解能力的不足,让他们分知识板块的对这四大力学更深层次的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学了一学期的《量子力学》,半点也不懂!”这是X大学的一个学生对《量子力学》学习的感叹,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将四大力学整合为一门《理论物理》课,即重视了理论物理不同于普通物理的研究方法的培养,也降低了知识内容的难度,这种整合对层次较低的学生来说也是有必要的。另外,不少教师在教学中感觉到学生的数学知识掌握得不牢固,根据这一具体情况,D大学增加了《高等数学》的学时数。还有,D大学开设了23门选修课供学生选学,以拓宽学生学科知识面。
3教育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两大学教育课程开设情况如表三。组织有效的物理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的培养是由教育课程来实现的。D大学与X大学两大学在这一模块的学分比例分别为23.1%和15.8%,区别也很大。
(1)必修课的比较分析
D大学与X大学这部分的学分比例分别为20.6%和5.1%。组织有效的物理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包涵了教育内容的编制能力、分析教材的能力、表达能力、应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研究能力、集体指导能力、沟通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等等。从表三可看出,D大学通过开设有关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组织有效的物理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而X大学除了教育实习、毕业论文,没有其它教育专业的必修课,这是十分不合理的,有什么样的课程设置就有什么样的学生,X大学这样的课程设置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组织有效的物理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方面先天不足。
(2)选修课程的比较分析
首先,D大学开设了3门选修课,共6学分,选修4学分;而X大学开设了9门选修课,共17学分,选修17学分,学生没有选择的空间,选修课不是让学生选修的,而是由管理者选开的,有些课尤其是选修课被随意停开,例如09级第七学期的《物理学史》就没开,甚至《教育学》也被停开过。其次,虽然说选修课与必修课同样重要,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选修课被受轻视,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课程设置具有导向性,《教育学》、《心理学》、《物理教学论》等这些物理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得不到X大学学生的重视。另外,“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斯宾塞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课程编制论的首要问题。X大学有些课的开设不是最有价值的,例如,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为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D大学开设《教师口语》,X大学开设《普通话》,诚然,普通话是教师口语的基础,但这应是小学阶段要完成的培养任务。因此,在学校学时数有限的情况下,对师范专业开设《教师口语》更合理更有价值。
二抛砖引玉提建议
1整合物理课程,整改物理教材
一方面将内容重复、研究方法相同的物理课程进行整合;另一方面重建概念,建立物理学知识的统一结构,从根本上解决物理知识总量不断增加,而教学时数有限的矛盾,这一点,德国已走在了前面,值得借鉴学习。
2重视专业英语,实现英语分层次教学,增设其它语种的外语课
在中小学受到良好的英语教育的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听、读、写、查能力。提高词汇量,学习《专业英语》应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任务。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中小学英语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学生进大学时的英语能力良莠不齐的实际情况,将英语分层次教学,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不同需求。同时,增设其它语种的外语课程供学生选修,外语学分控制在4至6学分。
3取消必修与选修之别
从根本上同等重视每一门课程。必修意味着强制性,取消这种强制性,让学生根据自身的需求、兴趣爱好、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的影响力度来自主选择课程修满所规定的学分。为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平衡发展,可将总学分按通识课程、学科课程、教育课程模块平均分配,即限制学生在每一课程模块上所要修满的学分即可。
4加强物理教育教学能力及其研究能力的培养力度
增设师范性、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以提高学生物理教育教学能力及其研究能力。例如将师范性不强的《心理学》改为《物理教学心理学》,强调物理学习的心理过程和特点以及社会心理对物理教学的影响;增设《物理教育研究方法》提高学生撰写物理教育教学论文的能力,等等。
5科学分配开课时间的先后次序,进校开始做毕业论文,实习分两阶段进行
传统的一通二学三教四实论的开课时序,同类课程开课时间太过集中,使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缺乏,学习效率不高。将通识课程、学科课程、教育课程根据课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搭配,科学分配开课时间的先后次序,提高学习效率。例如,第一学期就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工作,这样学生有较长的研究时间,更重要的是可以促使学生改变“中小学不做探究,大学也就不习惯研究”的不良习惯;勒温说:“没有无研究的行动,也没有无行动的研究。”教育实习可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安排在二年级,第二阶段安排在四年级。第一阶段结束后,在《中学物理实践教学技能研究》教学中实施“课程行动研究”,学生在“课程行动研究”中检讨教学过程的实际问题,并加以反思、评价、改变对问题的先前理解,改变教法,改进教学品质,从而使学生的教学能力、研究能力得到切实的培养,相信再经历第二阶段的实习后学生可自信的走上工作岗位,学校为社会输送的是合格的人才。
参考文献
第4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关键词:数学建模;力学实践;科学思维;创新能力
数学模型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是将数学应用于力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桥梁。数学建模不仅是数学走向力学应用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科学思维建立的基础。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力学问题,将数学应用于实际的尝试,亲历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可以取得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无法获得的宝贵经验和亲身感受,不断深化科学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数学建模对力学教学思维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数学建模与数学建模教学的发展
数学建模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得所写的《几何原本》为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构建了数学模型。可以说,数学模型与数学是同时产生的。数学建模的发展贯穿近代力学的发展过程,两者互相促进,相互推动。开普勒总结的行星运动三大规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电动力学中的Maxwell方程、流体力学中的Navier-Stokes方程与Euler方程以及量子力学中的Schrodinger方程等等,无不是经典的数学建模。
1985年,美国开始举办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至此数学建模的教育开始引起广泛的重视。数学建模在我国兴起并被广泛使用是近三十年的事。从1982年起我国开设“数学建模”课程,1992年起举办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现在已经成为我国高校规模最大的课外科技活动。2002年,开展“将数学建模的思想与方法融入数学类主干课程”的教改实践,2012年,《数学建模及其应用》杂志创办。
二、数学建模对力学教学的指导作用
1.数学建模是将数学应用于力学实践的必要过程
数学建模(Mathematical Modeling)是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抽象、简化,建立起变量和参数间的数学模型,求解该数学问题并验证解,从而确定能否用于解决问题多次循环、不断深化的过程。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是指为了一个特定目的,对于一个现实问题,发掘其内在规律,通过积极主动的思维,提出适当的假设,运用数学工具得到的一个数学结构。
数学建模几乎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用数学来解决的实际问题,都是通过数学建模的过程来进行的。而力学是应用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种力学理论往往和相应的一个数学分支相伴产生,如:运动基本定律和微积分,运动方程的求解和常微分方程,弹性力学及流体力学和数学分析理论,天体力学中运动稳定性和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等。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力学应该也是一门应用数学。
2.数学建模是培养科学思维的基础
科学思维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化、最优化的思维,是科学家适应现代实践活动方式和现代科技革命而创立的方法体系。科学思维的其他重要研究者Dunbar立足心理学视角指出,科学思维过程是建构理论、实验设计、假设检验、数据解释和科学发现等阶段中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与数学建模完全吻合,因此数学建模是培养科学思维的基础。
许多的力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他们在力学研究工作中总是善于从复杂的现象中洞察问题本质,又能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数学模型,逐渐形成一套特有的思维与方法。数学建模不单单是对某个问题或是某类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的培养。科学思维的培养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是科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3.数学建模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数学建模是一个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从数学理论到应用数学,再到应用科学,它为培养学生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能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数学建模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数学建模竞赛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发挥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创新可以是前所未有的创造,也可以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改进,即包含创造、改造和重组等意思。数学模型来源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没有现成的答案和固定的模式,因此学生在建立和求解这类模型时,从貌似不同的问题中抓住其本质,常常需要打破常规、突破传统。可以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始终贯穿在数学建模的整个过程。在数学建模的过程中体现了知识的创新、方法的创新、结果的创新和应用的创新。
三、数学建模在力学教学中的现状
数学建模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本科、专科和高职学院开设了数学建模课程,但普及率并不高,并且大部分学校只针对特殊专业开设,如中南大学物理升华班,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等。
在学习力学之前,学生对数学建模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高校对数模竞赛的宣传,所知有限。教师应在本科第一堂力学课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建模概念,将数学建模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数学建模思维的培养,联系实际力学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孙琳.浅析数学建模[J].大学数学,2007,23(05):129-134.
[2]米广春.科学思维培养的实证研究:MBD教学模式的建构及其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11:28-35.
[3]晁增福,邢小宁,周保平.数学建模对大学数学教学的影响[J].大众科技,2011(06):179-182.
[4]李大潜.从数学建模到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J].数学建模及其应用,2014,3(03):1-9.
[5]杨四香.浅析高等数学教学中数学建模思想的渗透[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3):89-95.
[6]刘唐伟,熊思灿,乐励华.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与创新能力培养[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01):77-79.
第5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意识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众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与神经科学家在此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使用计算方法试图让机器装置拥有意识能力。这类研究逐渐被称为“机器意识”的研究。早期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比较初步,研究工作较少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甚至早些年提到“机器意识”还有不合时宜的顾虑。
尽管哲学上关于“机器意识”有着不同观点的争论,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学者开始充分认识到开展机器意识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专门撰文进行了精辟论述。比如,英国皇家学院电子工程系的Aleksander教授根据学术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对机器意识态度的转变,指出机器意识的影响与日俱增,并预计了机器意识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改变人们对意识的理解、改进计算装置与机器人概念等方面的贡献尤为重大。
无独有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Haikonen教授则专门撰文强调机器意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机遇,他认为新产品与系统的发展机会起因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现有的人工智能基于预先编程算法,机器与程序并不能理解其所执行的内容。显而易见,不考虑意识就没有对自身行为的理解,而机器意识技术的涌现可以弥补这一缺失,因此机器意识技术可以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Chella教授则指出,开展机器意识不仅是一种技术挑战,也是科学和理论上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新途径。最近,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的Gök和Sayan两位学者进一步认为,开展机器意识的计算建模研究还有助于推进对人类意识现象的理解,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意识理论。
上述这些学者的论述,无疑说明,机器意识研究不但对深化人工智能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从科学上解释神秘的意识现象也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因为机器意识研究有着如此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推动未来信息技术革新的潜在价值,随着最近十年的研究发展,该领域已经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和实验系统已逐步形成,有些成果已经被运用到实际机器认知系统的开发之中。机器意识研究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最为前沿的研究领域。
机器意识研究的现状分析
2006年之前的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状况,英国皇家学院电子工程系的研究团队已经做过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因此,我们这里主要就在此之后国际上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据我们的文献检索,截止到2015年底,在机器意识研究领域发表过的学术论文超过350余篇,其中最近十年发表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归纳起来,由于对意识的哲学解释不同,目前机器意识方面的主流研究往往是以某种意识科学理论为出发点的具体建模研究和实现。由于涉及到的文献过多,无法一一列举,我们仅就一些影响较大的典型研究进行分析。
在意识科学研究领域,一种较早的理论观点是用量子机制来解释意识现象,这样的出发点也波及到有关机器意识建模的研究。利用量子理论来描述意识产生机制的有效性并不是说物质的量子活动可以直接产生意识,而是强调意识产生机制与量子机制具有跨越尺度的相似性。近年来,意识的量子模型发展又有了新的动向。比如,作为量子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高山(Gao Shan)提出了意识的一种量子理论,研究了量子塌缩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假定量子塌缩是一种客观的动态过程。日本Akita国际大学的Schroeder另辟蹊径,在构建统一意识模型中不涉及量子力学的量子相干性方面做出了全新的探索,主要目标是说明现象意识能够依据量子力学的物理解释,用量子力学的形式化代数性质来描述。此外,俄罗斯Lebedev物理研究所的Michael B. Mensky利用意识的量子概念提出了一种主观选择的数学模型,说明意识和超意识的特性如何能够通过简单的数学模型给出。当然,更多的是有关意识量子机制描述的可能性争论,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有。特别是在2012年的Physics of Life Reviews第9卷第3期,以Baars和Edelman所著论文“Consciousness, biology and quantum hypotheses”为核心,10余名相关领域的学者分别撰文对是否能够通过量子机制来描述意识现象展开了多方位的辩论。最近,Susmit Bagchi从分布式计算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讨论了生物演化与量子意识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在机器意识研究中,第二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就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workspace theory)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经科学研究所的Baars研究员1988年提出的意识解释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由Baars、Franklin和Ramamurthy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长达20多年的机器意识研究工作,最终开发完成了LIDA认知系统。
LIDA(Learning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Agent)是在该研究团队等人早期开发的IDA(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Agent)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依据Baars全局工作空间理论,采用神经网络与符号规则混合计算方法,通过在每个软件主体建立内部认知模型来实现诸多方面的意识认知能力,如注意、情感与想象等。该系统可以区分有无意识状态,是否有效运用有意识状态,并具备一定的内省反思能力等。从机器意识的终极目标来看,该系统缺乏现象意识的特征,比如意识主观性、感受性和统一性均不具备。
指导机器意识研究的第三种重要理论观点是意识的信息整合理论。意识的信息整合理论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精神病学的Tononi教授1998年提出的。自该理论提出以来,不少研究团队以信息整合理论为依据,采用神经网络计算方法来进行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其中,典型代表有英国Aleksander教授的研究团队和美国Haikonen教授的研究团队所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工作。英国皇家学院的Aleksander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长期开展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早期的研究主要给出了有关意识的公理系统及其神经表征建模实现,比较强调采用虚拟计算机器来建模意识。最近几年,Aleksander研究团队采取仿脑策略,强调信息整合理论的运用,建立了若干仿脑(brain-inspired)意识实现系统,更好地实现了五个意识公理的最小目标。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Haikonen教授的研究团队则主要采用联想神经网络来进行机器意识系统的构建工作。自1999年以来,该团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Haikonen教授在所提出的认知体系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实验型认知机器人XCR-1系统。应该说,虽然Haikonen所开展的机器意识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揭示意识现象本性,但他的成果却是目前机器意识研究领域最为典范的工作之一。
在意识科学研究中,也有学者将人类的意识能力看作是一种高阶认知能力,提出意识的高阶理论。在机器意识研究中,以这样的高阶理论为指导,往往会采用传统的符号规则方法来建立某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系统。其中,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工程就是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Chella教授用10年时间开发的Cicerobot机器人研究项目。该机器人实现了一种自我意识的认知结构机制,该机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亚概念感知部分、语言处理部分和高阶概念部分。通过机器人的高阶感知(一阶感知是指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高阶是对机器人内部世界的感知),就形成了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机器人。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将逻辑形式化方法与概念空间组织相结合,强调对外部事物的一种心理表征能力,并对外部环境进行内部模拟。在高阶认知观点的自我意识建模研究方面,另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Samsonovich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该团队经过10余年的研究,开发了一个仿生认知体系GMU-BICA(George Mason University-Biologically Inspired Cognitive Architecture)。在该系统中定义的心理状态不但包含内容,还包含主观观察者,因此该系统拥有“自我”意识的主观能力。系统实验是利用所提出的认知结构模型来控制虚拟机器人完成一些简单的走迷宫活动,机器人可以表现出具有人类意识所需要的行为。相比而言,与Cicerobot机器人强调自我意识是反思能力的概念不同,GMU-BICA系统则将自我意识理解为“自我”的意识。当然,不管是Cicerobot还是GMU-BICA,这样的高阶认知模型往往对心理扫视、主观体验与统一意识等意识本质方面的表现兼顾不足。
除了上述介绍的这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外,对于机器意识研究而言,还有如何判定机器具有意识能力的检验问题,这是目前机器意识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显然,要判断开发的机器意识系统是否真正具备预期的意识能力,就需要开展相应的意识特性分析、评判标准建立以及检测方法实现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由于目前对意识现象的认识存在许多争议,对于意识评测特性分析方面也难以有统一的认识。因此,目前的机器意识特性需求分析也比较零散。倒是在评判标准的建立方面,西班牙卡洛斯三世马德里大学计算机科学系Arrabales教授的研究团队做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该团队自2008年开始就在这方面开展意识特性分析,给出了计算人工意识的一种量化测量方法ConsScale以及对感受质的功能性刻画。之后,该团队又进一步提出了ConsScale的修订版,并讨论了在机器中产生感受质和现象意识状态的可能性。最终,该团队成功构建了CERA-CRANIUM认知体系(采用意识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建模)来检验产生的视觉感受质以及实现的内部言语。所有的这些成果为机器意识能力的初步检测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标准。当然,也有将镜像认知看作是机器拥有自我意识能力的一种检测标准,该理论的依据是人类和其他一些动物能够在镜子中认出自己,这一能力被看作是拥有自我意识的明证。因此,Haikonen认为在镜像中的自我识别,即镜像测验,也可以用来确认机器潜在的自我意识能力。于是,在意识能力检测方法的研究中,许多研究工作都是通过镜像测试来确定意识能力的。但也有研究认为,镜像测验并不能证明意识能力的存在,要证明机器具有意识能力还需要通过更加复杂的测验。比如,Edelman就提出三种意识检验的途径,即意识的语言报告、神经生理信号以及意识行为表现。
总而言之,机器意识的研究主要围绕量子涌现机制、全局工作空间、信息整合理论、意识高阶理论以及意识能力检测这五个方面展开的。从研究的策略来看,主要分为算法构造策略(Algorithm)与仿脑构造策略(Brain-Inspiration)两种途径。从具体的实现方法上,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采用类神经网络的方法;二是采用量子计算方法;三是采用规则计算方法。虽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机器意识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人类意识表现方面,目前机器意识能力的表现还是非常局限的。根据笔者以及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的Gök和Sayan发表的论文,目前机器意识系统主要具备的能力都是功能意识方面的,偶尔涉及自我意识和统一性意识(很难说是否真正实现了)。可见,意识计算模型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关于内省反思能力、可报告性能力、镜像认知能力、情感感受能力以及主观性现象等,这些方面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人类意识能力的唯识学分析
人类意识能力的基础是神经活动,尽管神经活动本身是意识不到的,也不是所有的神经活动都能产生意识,但神经活动却能够产生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这便形成了人类的意识能力。
根据现有的相关科学与哲学研究成果,人类意识的运行机制大致是这样的:物质运动变化创生万物,生物的生理活动支持着神经活动,神经活动涌现意识(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意识感受生理表现并指导意向性心智活动的实现,从而反观认知万物之理。除了心理活动所涉及的神经系统外,主要的心理能力包括感觉(身体感受)、感知(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能力,包括视、听、味、嗅、触)、认知(记忆、思考、想象等)、觉知(反思、意识、自我等)、情感(情绪感受)、行为(意志、愿望、等)、返观(禅观、悟解)等。
必须强调的是,迄今为止,对有意识的心理能力最为系统解析的学说体系并非是现在的脑科学研究,而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唯识学。唯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心识问题,相当于本文界定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如图1所示,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五蕴八识的心法体系。
第一,前五识归为色蕴,对应的心法称为色法,相当于当代心理学中的感知,其意识的作用称为五俱意识(所谓“俱”,就是伴随)。如果这种感知是真实外境的感知,则其伴随性意识称为同缘意识;如果是有错觉的感知,则称不同缘意识;如果这种感知活动产生后像效应,则称为五后意识(属于不相应法)。一般而言,色蕴对应的心理活动都是有意向对象的,因此属于意向心理活动。
第二,受蕴是一种心所法(具体的心理能力),主要是指身体与情感状态的感受。注意这里要区分身识中的身体状态感受与色蕴是完全不同的心理能力,身识相当于触觉,是一种感知能力,而身体状态的感受不是感知能力,而是感受身体疼痛、暖冷等的体验能力。受蕴的心理活动,虽然具有意识,但不具有意向对象,因此不属于意向性心理活动。
第三,想蕴是另一种心所法,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话讲,就是狭义的思维能力,如思考、记忆、想象等,属于认知的高级阶段,显然是属于意向性心理活动。
第四,行蕴也是一种心所法,主要指一切造作之心,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话讲,如动机、欲望、意愿、行为等。唯识学中的“行”,与“业”的概念相互关联,一般分为三种,即身业(行动)、语业(说话)和意业(意想),但都强调有意作为的方面,因此行蕴也属于意向性心理活动。
第五,识蕴是整体统一的心法,更加强调的是后两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的心法,现代西方的认知科学尚无对应的概念。主要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特别是返观能力,即对根本心识的悟解能力。
总之,色蕴是色法(感知能力),受蕴、想蕴、行蕴都是心所法(具体的心理能力),它们本身就是具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统归于心法),其中色法的意识作用是伴随性的五俱意识,其他三蕴的意识作用与伴随性的意识则又有不同,称为独散意识(受蕴、想蕴、行蕴所涉及的意识,是一种周遍性意识活动)。
当然,如果所有意识作用出现在梦中,唯识学中则另外称之为梦中意识(做梦时的意识活动,属于不相应法)。在唯识学的五蕴学说中,识蕴比较复杂,它是唯识理论特别单列的一种根本心法,除了强调自我意识的末那识“我执”外,更是强调达到定中意识的阿赖耶识“解脱”,属于去意向性心理活动。
总之,从意向性的角度看,我们的心理能力可以分为无意向性的受蕴,意向性的色蕴(前五识)、想蕴、行蕴,元意向性的意识以及去意向性的识蕴。其中,识蕴是一种特定的禅悟能力,对其性质的认识与禅宗的心法观有关。
机器意识研究面临的困境
对于目前的人工智能研究而言,我们涉及到的心智能力,如果按照五蕴分类体系来分析,那么大致只有色蕴、想蕴与行蕴中的部分能力。如果考虑目前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也仅仅涉及到五俱同缘的伴随性意识、想蕴与行蕴中的独散意识、识蕴中的自我意识以及意识活动本身的机制问题,其他意识比如不相应法的梦中意识、五后意识、定中意识、五俱不同缘意识等都没有涉及。
根据上述有关心识能力的唯识学分析,对于机器而言,真正困难的机器意识实现问题是受蕴性独散心识(体验性意识能力)与识蕴性心识两个方面,一个涉及无意向心理活动的表征问题,一个涉及去意向性心理活动的表征问题,这两方面都是目前计算理论与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讲,机器最有可能实现的心智能力部分应当是那些具有意向性的心识能力(色蕴、想蕴与行蕴),即唯识学心法中的色法与若干心所法。
很明显,意向性心理活动一定伴随有意向对象,于是就有可能对此进行计算表证,并完成相关的某种计算任务。因此,反过来说,我们认为意向性心理能力是人工智能的理论限度(是上界,但并非是上确界),机器实现的人类意识能力不可能超越意向性心识的范围。这也就是本文观点讨论的基点,并具体给出如下方面论据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心智机器的成功标准。从我们的立场看,如果要构建具有人类心智能力的机器,成功的标准起码应该通过图灵测验。主要理由是,由于“他心知”问题的存在,行为表现可能是唯一的判断标准,此时图灵测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测试途径,关键是“巧问”的设计。原则上,图灵测验通过言行交流,这是人类之间默认具有心智能力的唯一途径。再者,根据摩根准则,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宁肯选择比较简单的解释。因而,对图灵测验的解释中,也必须注意摩根准则,诸如机器思维或者机器经过思考的行动这类有关心智能力的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丢弃。
现在我们就来一场图灵测验,看看机器到底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为了看清本质,我们的提问异常简单,就是进行如下提问(所谓“多大年纪”思想实验,参见笔者以前的文章“重新发现图灵测验的意义”):你多大年纪?此时会发生怎样复杂的情形呢?当提问者一而再、再而三不断重复这一问题时,机器很快就会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不可预见性反应能力。那么,面对这么简单的提问,机器为什么会无所适从呢?其实这跟机器形式系统的局限性有关。众所周知,图灵机是个形式系统,而哥德尔不完全性说明足够复杂的形式系统不能证明某些真命题。这是否说明人的某些知识是计算机器永远不能得到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否说明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形式化呢?这样就引出了如下第二个论据的讨论。
从形式系统角度看,确实存在不可计算(证明)的问题,而且是大量的,但这些问题对于人类同样也是不可计算(证明)的。比如图灵停机问题,如果换成了人,结果是一样的。至于知识,可能首先要分清知识的含义与性质,知识是动词还是名词,要不要考虑元知识?如果这样看待知识,那么肯定不是所有知识都可以形式化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问题不在于形式系统是否有局限性,而在于对于意识现象能不能给出一致性的形式描述。
那么,我们可以对人类的意识现象给出一致性描述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人类的意识现象中,存在着意识的自反映心理现象:我们的意识活动是自明性的。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系统允许自涉,那么该系统一定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无法对该系统给出一致性的形式化描述。其实,人类的心理活动本来就是建立在神经集群活动的自组织涌现机制之上的。因此,出现意识的自明性现象是必然的。这也就是美国哲学家普特南给出“钵中之脑”思想实验所要说明的道理。比如,对于“我们都是钵中之脑”命题,在事先并不知晓这一事实的前提下,使用知道逻辑的反证法,可以明确加以否定。因此,我们人类的意识能力,显然不可能为机器所操纵。这样,由于计算机器形式化能力的局限性,靠逻辑机器是不可能拥有人类全部意识能力的,起码意识的自明性能力不可能为机器所拥有。
进一步,作为第三个论据讨论,我们再来看人类的意义指称能力问题。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机器能处理符号,但它能真正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吗?如果人的概念依赖于人类的躯体和动机(涉身性认知),那机器怎么可能掌握它们呢?这个问题主要是指机器是否能够拥有指称能力。塞尔的“中文之屋”提出了反对意见。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弄清什么是“意义”?如果意义是指所谓抽象的“概念”内涵而非表征形式,那么就必然存在一条语义鸿沟,因为机器内部能够处理或变换的只是不同的形式语言而已。但如果意义是指“行为表现”,那么这个问题就回到了上面图灵测验的第一个论据上去了。
人类语言表达意义不在语言形式本身,而在于意识能力。正因为这样,才会有许多超出常规的意义表达方式。从根本上讲,我们也不必一一列举机器难以拥有的指称能力,诸如矛盾性言辞、元语言表述以及整体性语境等难以一致性描述的状况;而只需指出,机器不可能拥有人类的终极指称能力即可。那么什么是终极指称能力呢?宋代临济宗禅师惠洪在《临济宗旨》中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源、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其中所谓的“心之妙”者,就是终极指称。由于超越了概念分别,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这就为形式化描述带来了根本的困境。
第四个论据的讨论涉及到所谓预先设定程序的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机器只能遵循给定的程序运行(预先设定的程序),这样的话,机器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也许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要让机器的“计算”更加“聪明”,但目前预先设定程序的机器不可能是灵活的,更不用说创造性能力了。显然,事情越有规则,机器就越能掌控,这就是预先设定程序的界限。比如对于表面复杂结构的分形图案,由于可以靠简单规则加以迭代产生,机器就可以靠预先编程规则自如产生。但是对于人类常常出现的出错性,由于毫无规律可言,机器便不可能预先加以编程,机器也就不可能拥有出错性了。人是易于犯错误的,而机器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行,永远不会出错,这就是预先编程的一个致命弱点,这也是第一个论据讨论中机器无法通过图灵测验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出错性表面上似乎是一个负面品质,但其实质上则包含着灵活性和创造性,是一切新事物涌现机制的基础。如果没有生物基因的出错性,自然选择就没有了作用的对象,繁复的生物多样性也就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没有了思想模因的出错性,文化选择也同样没有了作用的对象,博大的思想多样性同样无从谈起。可见,出错性是机器难以企及人类心智能力的一个分界线,而这一切都归结为机器的预先编程的局限性。
同样的道理,由于预先编程问题,也带来了机器不可能真正拥有情感能力的新问题,这也构成了机器难以拥有人类心识能力的第五个论据。我们知道,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常规理性活动过程中的“出错性”,是非理性的,但基于逻辑的机器是理性的。也许人们会说,非理性的情感在心理表现中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起作用的。但我们要强调,即使是理性思维,情感和其他非理性因素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倾向性指导作用)。如果说理性的认知能力是前进的方向,那么非理性的情感能力就是前进的动力,人类的心理活动中岂可或缺情感能力?!而对于机器而言,缺少了情感能力,机器怎么能够像人类一样思维?!
机器是逻辑的,难以体现情感本性,目前有关情感的计算只是实现了情感的理性成份。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理智是方向性的舵手,情感是驱动性的马达,在航行中情感与理智相互依存。因此,如果情感不能计算,那么也谈不上实现人类意识的计算,因为情感难以计算的本质就是意识的感受问题。
机器能拥有意识能力吗
通过上述对机器实现人类心智能力所面临的困境的讨论,就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机器是否能够跟人类一样拥有意识能力的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信念之争,笔者认为学术辩论主要应对事实或可能事实开展分析讨论。由于计算机器的概念相对明确,争论的焦点多半会聚焦到有关人类“意识能力”的界定之上。所以,下面先给出笔者所理解的人类“意识能力”的分析描述,然后再围绕着我们讨论的主题,展开观点的陈述。
意识包括功能意识、自我意识和现象意识,其中功能意识大体上涉及到意向性的心理能力,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五个论据外,似乎并不存在特别的新困难。但自我意识和现象意识则不同,由于涉及到去意向性和非意向性的表征问题,这便构成了机器心识的最大困扰。首先,我们要清楚“自我意识”不是关于“自我”的意识,而是一种自身内省反思能力。因此,自我意识是意识的核心功能。其次,我们必须澄清所谓的“体验意识(qualia)”到底指什么?是精神的本性,还是虚构的对象?这涉及到哲学基本问题,非常复杂,观点纷呈。机器能否拥有意识能力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在于此。
由于涉及到心灵的一些本质问题,机器意识研究一开始就引起了哲学领域的广泛关注,有专家专门讨论机器意识研究的哲学基础,也有学者讨论机器意识会面临的困难,包括像意识(consciousness)、感受质(qualia)和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这些回避不了的、显而易见的困难问题,以及一些与意识相关的认知加工,如感知、想象、动机和内部言语等方面的技术挑战。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延续早期对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对机器意识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涉及到强弱人工智能之争、人工通用智能问题、意识的难问题、“中文之屋”悖论的新应用、人工算法在实现意识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蛇神机器人不可能拥有主观性、现象意识等众多方面的争论。
那么机器能够拥有这种现象意识状态吗?对于现象意识的存在性问题,有截然相左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神秘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神经生物系统唯一共有的就是主观体验,这种现象意识是不可还原为物理机制或逻辑描述的,靠人类心智是无法把握的。另一种是取消论的观点,认为机器仅仅是一个蛇神(zombie)而已,除了机器还是机器,不可能具有任何主观体验的东西。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还存在各种不同偏向的观点,如还原论、涌现论、唯心论、二元论,等等。其实,依笔者看来,无需做上述复杂的讨论,只须从意向性的角度来看,便可以澄清机器意识的可能性问题。笔者观点是,凡是具有意向性的心理能力,理论上机器均有可能实现,反之则肯定不能实现。因为一旦缺少了意向对象,机器连可表征的内容都不存在,又如何形式化并进行计算呢!
通过上述分析讨论,可以发现,机器意识难以达成的主要困境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形式化要求,特别是一致性要求导致的局限性,使得机器智能局限于具有意向性的心识能力,如色蕴、想蕴、行蕴。第二个则是机器缺乏不预见性的反应能力,只能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来应对环境。第三个就是无法拥有终极指称能力,无法实现去意向性的识蕴能力。最后补充一点则是,对于涉及到现象意识的感受性能力(受蕴),由于没有意向对象可以作为形式化的载体,因而对其进行的计算完全无从入手。
于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意向性就是实现机器意识能力的一条不可逾越之界线。用数学的术语说,机器能够拥有的意识能力的上界就是意向性心识能力。当然这并非是上确界,因为不可预见性的反应能力也属于意向性能力,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基于预先编程的机器仍然无法拥有不可预见的反应能力。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更为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器来突破预先编程能力,但意向性心识能力的边界,依然是无法突破的。
因此,当我们把目前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分为面向感知能力实现的、面向具体特定意识能力实现的、面向意识机制实现的、面向自我意识实现的以及面向受蕴能力实现的这五个类别时,就可以同唯识学中意识的五蕴学说相对比,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其中的本质问题所在。我们的结论是,对于机器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应当搁置有争论的主观体验方面(身心感受)的实现研究,围绕意向性心识能力(环境感知、认知推理、语言交流、想象思维、情感发生、行为控制),采用仿脑与量子计算思想相结合的策略,来开发具有一定意向能力的机器人,并应用到社会服务领域。
机器意识研究未来展望
围绕着上述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我们认为,未来机器意识的研究,主要应该开展如下5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首先,构建面向机器实现的意识解释理论。由于意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目前存在众多不同的意识解释理论,其中只有部分理论用于指导机器意识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开展机器意识研究工作,取得更加理想的机器意识表现效果,必须直接面向机器意识实现问题本身,综合并兼顾已有意识解释理论,提出一种更加有利于机器意识研究的、有针对性的、全新的意识解释理论。提出的新理论应该不但能够清晰地刻画各种意识特性及其关系,而且应该符合机器意识实现的要求,更好地用以指导机器意识的开展。为此,具体需要开展现有意识解释理论的梳理研究、机器意识限度与范围的分析研究、意识特性刻画标准规范的构建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次,探索机器意识的计算策略与方法。过去的研究表明,要想让机器拥有意识能力,传统的人工智能方法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寻找全新的计算方法。因此,机器意识的深入展开,需要有不同于传统人工智能的计算策略和方法。就目前机器意识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言,在计算方法方面起码需要开展亚符号(神经信号)表征到符号(逻辑规则)表征之间的相互转换计算方法、在非量子体系中实现类量子纠缠性的计算方法,以及神经联结与符号规则相互融合的计算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在计算策略方面则需要开展仿脑与算法相结合策略的研究。只有确定了行之有效的计算策略和方法,才能真正推动机器意识进一步深入发展。
第三,构建机器意识的综合认知体系。作为机器意识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构建具有(部分)意识现象表现的机器认知体系。给出的意识机器认知体系应该满足一些基本需求,起码应该包括:实现具有感受质和外部感知对象的感知过程;实现过程内容的内省反思;允许各模块无缝整合的可报告性以及配备本体感知系统的基本自我概念。因此,这部分的研究内容应该结合机器意识计算策略与方法的探索,参照已有各种机器意识认知体系的优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构建工作,以期满足基本的意识特性需求。
第四,开发实验性的意识机器人系统。在已有智能机器人开发平台的基础上,嵌入构建好的机器意识综合认知体系,形成具体的意识机器人系统,并开展具体的系统实验分析研究。通过各种意识特性的实验,检验机器意识综合认知体系的性能是否满足基本的意识特性需求,最终给出一种实验性意识机器人系统的范例。
第6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关键词:物理教学;思维能力;科学精神
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期,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纷纷改革教育,研究教育思想,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方法。顺应时代的变化,我国教育模式也在转变,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核心。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研究性、探索性。因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在物理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物理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思维能力、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等,其中思维能力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物理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有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有助于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利用已有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1.1 启发式教学是打开学生思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钥匙
启发式教学的优点可归纳为两点:
(1)能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启发过程中,向学生提出的应是围绕教学重点,能唤起学生积极思考的关键问题,可以使学生处于紧张的思维状态中。这样,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也为一堂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2) 可以培养学生的正确思维方法。启发式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教学的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因此,要使启发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在课前精心设计,切不可掉以轻心。例如在示波器实验中,一般教材上只是说明示波器的基本原理,不可能把每一型号的示波器面板操作都写出来,学生第一次接触这么多旋钮,很难一下子调出稳定的波形,往往都是调了半天,显示屏上什么都没有。教师可以先接好两个通道的信号线,调出信号,再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可以限定学生每次只动一个旋钮(按钮),这时屏幕上的波形也会随着变化,学生就很容易理解这个旋钮(按钮)的作用,然后再把这个旋钮转(按钮)的位置还原。依次去改变其他的旋钮(按钮),这样,学生很快就可以学会示波器的基本操作。
1.2 加强物理方法的学习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进行科学创造需要掌握深厚的物理学知识,需要产生各种联想、想象和设想,更需要加强物理方法的学习。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认识、融会在书本中的方法论思想,逐步建立理想模型,设计理想实验,掌握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类比等方法,学会进行科学假设和建立简单数学模型。方法是活的知识,它能够为学生进行科学探索提供启示。例如在学习流体力学时,我们首先忽略了流体的可压缩性和粘滞性,提出了理想流体这模型,才导出连续性原理和伯努利方程。同样当我们考虑流体粘滞性时,也是先引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流动状态-层流。然后导出了泊肃叶公式和斯托克斯公式。
2 在物理教学中注意介绍杰出物理学家对物理学发展的作用,利用物理学史引导学生学习物理学家的科学精神
物理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含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工作,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物理学家的主要作用表现为:
(1)前人的错误论断,建立科学的概念,开创科学的新纪元。如伽里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落得快”的错误观点,提出匀速运动和匀加速度等概念,奠定了力学的基础。
(2)创造性地综合已有理论,集科学之大成,建立完整的科学体系。如牛顿在伽里略、开普勒等人的基础上,对力学理论进行创造性的综合,提出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动三定律,完成物理学的第一次大综合。
(3)在科学实验中的重要发现。在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重要的实验往往能深化人类的认识,将物理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勒耳发现物质的放射性,1897年汤姆生发现电子,正是这三大实验发现揭开了现代物理的序幕。
(4)突破前人的思想方法,创立新的科学思想。物理学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需要新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例如玻耳兹曼和吉布斯在麦克斯韦之后将统计方法彻底地引入物理学,突破了牛顿等人的因果决定论思想。
(5)提出科学假说,构建新理论,如在解释黑体辐射问题时,普郎克提出能量量子化假说,为量子力学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
(6)进行重要的验证性实验。如赫兹实验证实了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并使之很快得到应用。杰出物理学家能够对物理学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他们非凡的智力和优秀的性格特征外,还与他们处在物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关,同时他们还受益于前辈科学家已有的成果和经验。
3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学生要学好物理,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习惯,建立良好的知识结构,摆脱死记硬背的倾向,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性。强烈的学习动机是有效学习的推动力量,所以教师应结合物理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第一,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物理学研究的内容很广,大到天体,小到基本粒子,各种电器、无线电装置都与物理知识有关,这会给学生产生一种自发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光凭这点还是不够的。教师还要常常用物理学史中精彩片断、高质量的演示实验(教师自制的演示实验更好)、物理学的新进展、物理学在其它领域中的应用等吸引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第二,让学生保持学习的良性循环。学习动机是学习的原因,又是学习的结果。增强学生学习动机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让学生学懂,学生从成功的学习开始,可以增强和保持强烈的学习动机。如果学习的压力过大,学生心理上就难以承受,就得不到学习成功的愉快体验,从而减弱学习动机。第三,让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尽量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对学生的进步给予及时的鼓励。
4 寓德育于物理教学之中,培养学生先成人,后成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德育为本。物理学科中蕴含着大量的德育因素,对于促使学生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责无旁贷。
4.1 在物理概念,定律,原理的讲授中,注意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
每一个物理概念、定律、原理都是对物理事实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概括、总结和升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作为教师,不仅要讲清楚物理学的概念、定律和原理,而且要让学生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如上复习课时,教师要善于发掘教材内在的统一性,使纷繁复杂的现象、概念、公式、定律、原理等物理知识,在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原理的指挥调度下,组成一个井然有序、简单明了的物理体系。通过正确的讲授方法,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树立学生的世界观。
4.2 在物理实践课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作风。
物理学知识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让学生在实践中去不断接触各类物理现象,远比单纯让学生在书本上学习抽象的物理规律效果好。在物理实践课中,教师要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的教育,比如通过物理实验,让学生亲身体验探索研究物理原理的过程,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二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使学生不仅学会物理基本原理,而且能运用这些原理去解释和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物理现象和物理问题。三是培养学生的组织观念、集体现念、道德品质,增强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协作精神。四是培养学生从事经济建设的本领,物理教学活动要紧密联系工农业生产实际,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实习,参加物质生产劳动,使他们掌握一定的从事经济工作的本领和有关的基本操作技能,为将来走向社会、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启发式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刻苦的科学精神、优秀的思想品德也是不可缺少的,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参考文献
[1]窦建波.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J]. 广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7).
[2]李松岭.物理教育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教育理念和策略[J].物理教师.2004,(7).
第7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16岁时就曾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在《自传注记》中,爱因斯坦回想起自己在梦中追逐着一道穿行在空间里的光线。他由此推想到,如果自己能以光的速度移动,那么在他眼里,这道光就是静止的,就像是一个空间振荡却又保持静止的电磁场。
该实验与当时的“以太”理论相矛盾,该理论认为光的传播需要一种看不见的介质。如今,人们已知道“以太”理论并不正确,但爱因斯坦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确证了自己的理论。这个思想实验就像一粒“胚芽”,最终让他结出了“狭义相对论”的果实。
“猴子与打字机”又称“无限猴子定律”:如果在无尽的时间里,无限多的猴子可以随意敲击无限多的打字机,相信它们总有一天可以“创作”出莎士比亚全集。20世纪早期,法国数学家埃米尔·博雷尔提出的这项定律曾流行一时。
猴子可以写出《哈姆雷特》?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从数学角度进行论证,只要考虑到它的无限性,则完全可以论证成功。在现实世界,这个实验似乎无法开展,但仍不免有人想尝试。2003年,英国的科学家们试图在一个动物园里验证这一定律。他们将一台电脑及其键盘放到一个灵长类动物围栏内,不幸的是,猴子们可没兴趣写什么十四行诗,除了满篇满幅的“s”,很难在该“作品”里再找到其他字母。
“电车难题”是十分有名的伦理学思想实验,它的内容如下:一个疯子将5名无辜的人绑在一条手推车轨道上,而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向他们冲去。此时,你可以拉动操纵杆将电车转至另一轨道,但那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你会如何选择?
哲学家菲利帕·富特之所以提出这个难题,目的在于批判伦理学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功利主义。根据功利主义哲学,牺牲1个人可以挽救5个人,毫无疑问应该拉动操纵杆。然而,如果拉了操纵杆,你就成为杀死1个人的同谋,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有人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有所作为,不作为就会被视为不道德。
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不做、怎样做,都无法让自己在道德的世界里无懈可击,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很多哲学家都以“电车难题”来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通常会让自己的道德标准不断妥协,因为真实而完满的道德,并不存于世。
在“定时炸弹”实验中,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藏于某处,更糟糕的是,距离爆炸的时间越来越近。若你正监管着一个知晓该装置藏于何处的人,你会对他严刑拷打以逼问信息吗?
跟“电车难题”一样,“定时炸弹”也是一道伦理学难题,它逼迫人们在两种不道德的行为上做选择。这个实验常用来批驳“在任何情况下,刑讯逼供都不可原谅”这一论调。
“忒修斯号”这则非常古老的思想实验源自希腊作家普卢塔克的作品,以“充满悖论”闻名于世:有一艘船,经过不断修补,已在海面上航行了数百年。终于有一天,这艘船上的所有配件都被换了一遍。那么,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忒修斯号?如果这艘船不是原来的忒修斯号,那么它是从何时起成为另一艘船的呢?
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这个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如果有人将换下来的旧配件收集起来再做成一艘船,与那艘由新配件组成的“忒修斯号”相比,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
哲学家们常用“忒修斯号”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属性。世人常将事物的本质等同于其物质或现象,而这个实验归根结底就是逼迫人们质疑:事物的本质是否仅止于此?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赛尔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将一个只会说英语的人关进一间密室,只在门上留一条投信口那么窄的缝,房内有一份英文版的计算机中英翻译程序打印稿。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一些便笺纸、铅笔以及文件柜。从门上的“投信口”将一些印有中文的纸片投入该房间。在赛尔看来,这个人可以借助这些资料进行翻译,然后将回复用中文写好后递出。尽管他一句中文也不会讲,却可以让房间外的人误以为,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为了电脑以及其他人工智能仪器能具有理解及思考能力,赛尔构想出“中文工作室”这一思想实验。房间里的人完全不会中文,因而也不可能用中文进行思考。但借助某些特定工具,即使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也会觉得他的中文很好。赛尔认为,电脑也是这样。它们并不能理解所获取的信息,只是通过运行程序来存取信息,从而让人们觉得,它们仿佛拥有了人类的“智慧”。
薛定谔的猫是一则关于量子力学的著名悖论,由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提出,其内容如下:将一只猫关在一个密闭的盒子内1小时,盒子里同时放有某放射性元素以及一个装有致命性毒气的小药瓶。在这一小时内,该放射性元素发生衰变的可能性为50%。如果发生衰变,则用于计量衰变的盖格计数器就会触发开关,让一把小锤子将装有毒气的药瓶击破,从而把盒子里的猫杀死。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为50%,因而薛定谔断定,盒子未打开以前,猫同时处于既死亡又活着这一双重状态。
这则复杂的思想实验引发了大量的解说与讨论。其中最为古怪的一个莫过于“多重世界”学说:既然猫可以同时处于既死亡又活着这一双重状态,那么也就存在两个互不叠加的空间来容纳这只猫。
论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非“桶中人脑”莫属。从认知科学、哲学到通俗文化,它的“身影”简直随处可见。它说的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将你的大脑从你的身体里取出,放入一个装有生命维持液的桶内,然后在你的大脑上装载电极,让它与一台能够产生图像与感觉的电脑装置相联。由于你获知的所有信息都来自脑部,所以这台电脑足以让你过上“日常生活”。
第8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关键词:意识;心身问题;突现论;泛心论
作者简介:威廉·西格(William Seager),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心灵哲学、意识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陈巍,心理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心理学系讲师,浙江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认知科学与哲学心理学研究。
校者简介: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心理学史与理论心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的意义”,项目编号:10YJC720052;南京师范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神经现象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BS0003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3-018-012
一、问题的提出
一旦触及意识问题,就不可能逃避回答这样一个基本的疑问:何为意识?但是总体而言,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如果有人真的缺乏任何关于何为意识的想法,那么将难以想象如何将任何信息传递给他们(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曾经说过的那样,当询问什么是爵士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意识”(consciousness)这一术语包含了大量的心理现象。有时它指对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的复杂的反思鉴别,就像我们体验这些心理状态一般。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意识有时也仅仅等同于觉醒(wakefulness)或感觉的觉知(sensory awareness)(这是麻醉师所采用的定义)。大概动物(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会比较受用于这类意识,同时很可能只有人类才能反思其自身的心理状态。意识状态的最鲜明的例子的确可以算是感觉状态:一个成熟番茄的炫目红色、小号的尖锐声、炎炎夏日里品尝一杯冰啤酒的滋味,以及所有经由这些感觉形式体现出的东西。但是,意识的分类也应该包括有意识的思维(conscious thought),及其牵涉我们思维的内容与更朦胧的认知层面,诸如当我们忽然认识到我们理解了某物的时候的感觉,一种典型的意识状态超越了我们所能把握的内容。至于我们有意识思维的内容,其保留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要么是否所有涉及意识的思维均需身披某些感觉的外衣(它可能以如下形式出现,心理意象,或者听觉的,或视觉的),要么是否存在着某些“纯粹”的智力理解(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s)。进一步地,意识的分类需要包括意识的基本感情状态,其范例是疼痛和愉悦。这些状态的动机性力量使得它们与众不同,而它们遗留下来的重要性也许甚至使人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意识状态的原初形式。情感超出了简单的刺激-反应式的疼痛与愉悦。这体现出了一系列意识的情绪性状态。诸如愤怒、爱或恐惧等情绪组成了一些我们最强烈的有意识的经验,并且由于涉及了这些状态,所以它们超出了裸的情感、感觉或智力形态。
有人可能对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心理状态名单中发现任何核心或共同的特征感到绝望。意识那多少有些捉摸不定的本质是主观性的(subjectivity),在那里使用的是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著名表述方式:成为一个拥有意识状态之主体所是之物。1火箭或者烟灰缸不具备主观的方面,也没有“内部”(interior)的生命。撇开所有构成意识的不同类型的心理状态的细节,意识的核心问题在于理解主观性本身的性质与起源。
我们必须感谢意识问题是作为一个更普遍的议题的一部分出现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这便是所谓的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既然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意识是心理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它将心理从其他自然物中分离出来,因此,人们不会期望存在着任何关于心灵的问题可以从意识问题中脱离出来。由于意识是一种属性,从而产生了大量问题——意识是某物的一种特征,并且这种“事物”可以被称为心灵。这个主题与真实的古老问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一问题是:当身体遭到明显的摧毁之后,是否仍然有一些东西幸存下来,这种最终能被人类所认识之物将会给他们的尘世生活(earthly existence)带来一种必然的终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趋势去相信(或希望)我们是以某种方法幸免于死的,并且为了这种幸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它不得不保留意识且将它想当然地视作一种在类型上与身体截然不同的事物。
尽管意识问题的现代形式是一种相对的近期发展,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与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兴起以及随后对世界的科学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意识使得我们不同于(其他)自然的物质。因此,为了理解意识问题,理论哲学家建议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顾心身问题的悠久历史。
二、早期历史
身处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哲学家的观点通常被世人视作令人怜悯的荒谬而加以嘲讽与否认:万物由水构成(everything is made of water),万物皆不动(nothing can move)。但是,就提出世界应该依据自然力量和理性探究而予以解释的想法而言,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置于一场广泛的讨论之中。这些知识先驱的积极观点错得离谱并不令人感到诧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呈现的观点为科学革命奠定了早期的基石。
前苏格拉底的准自然主义者的观点指引他们去询问一个关于世界的结构与组织的根本性问题,他们遗留下的答案至今仍在争论之中。这就是突现(emergence)与我们所谓的(因为缺少更好的术语)内在性(inherence)。世界包含了大量的不同事物,这些事物展示出一种令人惊愕的复杂特征与交互作用。但是,很明显的是,这种复杂性中的某些东西可以依据参与实体(participating entities)的交互作用而加以解释(这在我们所构想的人工产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并且有时忘记了手艺高度熟练的古代人是怎样设计工具和简单的机械的)。这种观察认为,也许世界中的万物可以借助少数拥有一些简单属性的基本特征而予以解释。这样的思路自然地招致反对者的挑战,某些事物是不能就这样被“还原”(reductively)而解释的。
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些关于世界的简单的基本特征,它们的基本属性和交互作用引起万物体现出一种突现论(emergentism)的形式。任一客体都有一属性,此属性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所不曾展示出来的。例如,太阳系展示出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这是其任何的组成成分均不(或甚至不能)具备的。但是,太阳系的组织完全是由其组成成分之间受规律支配下交互作用的产物,并由这些成分的属性而产生(例如,质量、位置、速率)。因此,动态结构是一种突现的特征。前苏格拉底时代最著名的突现论者是原子论者(atomist)德谟克利特。他坚持信奉万物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属性和原子的运动。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将某些特征认作突现是合理的,这并不意味着万物皆是如此。以颜色为例予以考量。假设原子是没有颜色的,那么,颜色又是如何从原子的交互作用中突现出来的呢?为了反对德谟克利特的突现原子论(emergent atomism),阿那克萨哥拉断然否定了突现的可能性,并选择了以所有特质内在于万物的观点作为替代:世界的多样性可以用任一具体事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混合属性加以解释。现代的原子论者——我们所有人——对颜色的例子没有留下多少印象。颜色仅仅是由根本上的非颜色属性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视觉系统而产生的。或许当德谟克利特晦涩地宣称“按照惯例是颜色……但事实上却是虚空(void)与原子”的时候,他已经预测到了这种回应。
在心身问题内部,这种基本的二分法产生了两个关于意识本质的理论:突现论和泛心论(panpsychism)。突现论者相信心灵和意识是由源自非意识先质(nonconscious precursors)的非意识的部分产生的,反之,泛心论者坚持认为心灵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万物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拥有一种意识的形态。当然,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述上述观点。一个泛心论者可能会强调这样的观点:意识不能从非意识的成分中突现出来,但也并非宣称万物绝对都有心理方面。
无论如何,在这种二分法的历史中形成了心身问题的背景。就此而论,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两位古代哲学先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完全缺乏前苏格拉底时代还原论者的精神,并且在《斐多篇》(Phaedo)中对此进行过攻击。柏拉图的替代性建议是心灵与身体不同,它多少是具有“活力的”(animated)。自然地,柏拉图提出了一些论据来阐明心灵是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的观点。这样的论点之一极其抽象并源自其著名的形式说(doctrine of Forms)。理念是完美的实体,而物质实在仅仅是近似于理念的,例如,在几何学中,我们证明一个物体是圆形的,但是在物质世界中不存在这样的事物。所有圆形的客体——并且在有的时候很明显是由几何学家所描绘的粗糙的图形——不可能是完美的圆形,因此,严格讲来,都算不上是圆形。然而,柏拉图怎么可能说我们的心灵为了进入到智力中需要与这些极端的非物质实体(nonphysical entities)发生联系?我们与它们在概念上的熟识使得我们认为心灵类似于非物质的。柏拉图也在其回忆说(recollection)中发展出该论证的一个不太抽象的版本。因为我们知道理念在知觉中从未遭遇其实体,我们的知识必须基于某些其他类型的觉知。柏拉图相信这只能借助我们的存在的非身体的状态(nonbodily phase)才能解释,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存在的朦胧回忆(事实上柏拉图甚至认可一种轮回学说[reincarnation])。虽然他的论证不是特别令人信服,但是这些论据确实指出了思维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特征:它具有将客体独立于其存在的能力(一种随后被称之为思维意向性的特性)。
乍一看,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主义者是站在柏拉图的对立面的。他否认了理念说,代之以客体可以用其在形式(form)和物质(matter)之间的区分来加以理解的观念。这里的形式(form),亚里士多德指的是某些类似于组织或结构的东西,而物质(matter)则是构成所讨论的客体的一切“非结构化的质料”(unstructured stuff)(因此,水的物质是氢和氧,蚁群的物质是蚂蚁)。亚里士多德将灵魂(或心灵)定义为“一个具有潜在的生命的自然化身体的形式”。这意味着心灵是一种作为我们特征的物质存在而不是某些缥缈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质料。然而,亚里士多德并非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就像柏拉图一样他也认为,心灵存在一些极其特殊之处,这种特征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心灵超越了物理物质。他有时把心灵之于身体的关系比作舵手之于船舶,并明确地坚持心灵至少在一个方面上——理性思维的能力,他称之为“主动理智”(active intellect),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亚里士多德是在对二元论的论证过程中展开其形式概念的。心灵可以思维任何事物,而且这是因为思维对象以其形式来告知心灵(例如,当你想到一头狮子的时候,狮子的形式告知了你心灵中的“物质”),这意味着心灵可以呈现任何的形式。但是,没有物质器官可以呈现每一种形式(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如下:眼睛只能够呈现视觉的形式,或者耳朵只能呈现听觉的形式)。因此,心灵不是物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非常有趣,就像柏拉图的回忆论证一样,关注心灵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使其进入到与其他潜在存在的联系之中(或者甚至非存在,当我们回忆时,我们能轻易地思考不可能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还引入了一个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影响的观念,即所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其本身的或是自我表征的(self-representing)。对此的论证是如果心理状态是经由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这是第一状态[first state])而引起觉知,随后就应该有一种第三状态将第二状态带入到觉知中去,以致产生了一种恶性的无穷倒退。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潜在地假设了所有心理状态都是那种我们能有意识地觉知它们的状态;否则,无穷倒退就会停滞在第一状态这种并非意识的状态中。这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吹毛求疵。因为,仅仅是将无意识心理状态的概念视作是清晰的之前,就需要花费我们很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将其视作一个严肃的猜想了。
三、科学革命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伴随一些值得注意的扭曲与挤压,服务于主导中世纪的教会约束下的哲学。在那里当然存在着有关心灵及其内容的本质与结构的诸多争论(我们将心理状态映射到客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或指向性[directedness]等重要概念归功于中世纪学者,心理状态是“关于”[about]某物的)。但是,这个观点在关于心灵与远离中央舞台的自然世界如何发生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并且心灵的概念需要用那些并非当时出现的自然主义的术语加以解释。当科学革命忽然降临欧洲的时候,这种对事物认识的自满视角被彻底地颠覆了。伽利略为区分首要特质与次要特质(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做好了准备。前者是物质在数学上便于处理的属性(mathematically tractable properties of matter),比如形状、质量和运动,而后者是在意识中所设置的首要特质的显现。次要特质是有意识的心灵的唯一属性。在伽利略撰写的《试金者》(The Assayer,1623年出版)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滋味、气味、颜色等只是我们用来将其锁定于客体的名字而已,它们均存在于意识之中。因此,如果生物体一旦改变,所有这些次要特质也必将被抹去或消失殆尽。
这种区分使得世界对科学变得安全。随后科学可以在这一范围内聚焦于物质世界的客观特征,并采用纯粹的数学理论加以解释。但是,有关次要特质本质的文本难题仅仅是暂时地被规避了而已。世界中生机勃勃的科学化图景,那些随后并且一直渴求的完满,不能再忽略室中巨象了1。
最著名的回应——来自笛卡儿——直截了当地在心灵和物质世界之间施加了一种完整的分割,并以一种迅速被命名为笛卡儿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的理论所阐述。如果有人赞同心灵是与身体分割开来的假设,那么,笛卡儿的观点就非常符合常识了。这种理论允许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因果互动,所以踢一下胫骨会产生一种疼痛的意识(这位于那些笛卡儿曾经非常感兴趣的甚至预言的物理学诡计之后),相反,一种愤怒的感觉导致手臂执行报复性的打击。笛卡儿二元论同样向天主教的灵魂不朽与身体复活学说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之中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时常火焚异教徒,例如,它曾臭名昭著地强迫伽利略撤回对哥白尼主义的辩护并宣判其毕生监禁于牢狱。
但是,笛卡儿二元论同样面临着大量精致的哲学难题。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因果互动威胁着世界的科学图景的完整性。心灵时常以某种方式干预或改变物理世界,这终究是物理上无法自圆其说的,并且使其在相当程度上违反了基本的规律,比如能量守恒定律。其次,在更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心灵(没有空间,没有位置)与身体这两个在根本上如此迥异的领域之间产生因果互动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一困境在笛卡儿刚提出他的理论时已经众所周知了。作为他的皇室读者,伊丽莎白公主在1643年坦率地质问他:“一个人的灵魂如何决定他身体的精神,以至产生自主动作(voluntary action)?”笛卡儿的正式回答是心身的联合是一种无理性的事实,由上帝所创立,这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畴。
为了回应这些困难,一大批可供选择的二元论者的理论被设计出来。斯宾诺莎提供了一种具有两面性的解释。在此种解释中,心灵与物质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无限的属性,潜在于他称之为“上帝”的那种实质之下(这种亵渎在于其暗指上帝拥有物质的属性)。虽然,并不存在不同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是它们却作为彼此的完美镜像矗立着,因此,呈现出一种因果交易的面貌。
莱布尼茨的理论通过假定一种无限的个别心灵(他称之为单子[monads])的集群,从而避免了斯宾诺莎那广受诟病的泛神论(pantheism)。这些心灵的知觉是由上帝(上帝是至高的单子)设立的,因此完美地与物理世界中的事件保持预定的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首次赋予某些心理状态是无意识的观点以地位,即他所谓的“微知觉”(petite perceptions)。
另一种对心身关系相当奇特的解释来自伯朗士的偶因论(occasionalism),该理论猜想上帝才是心灵与物质之间的仲裁人,所以任何意向性动作或感觉简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理论强有力地揭示了已认识到的心理因果关系的棘手性。
这种以反突现论者身份出现的二元论者对心灵的解释一度成为时代的主导趋势,但是依旧存在一些卓越的思想家,他们至少可以被贴上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s)的标签(例如,霍布斯、伽桑狄)。然而,他们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核心观点是拒绝一种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的分离的心理实体。他们甚至没有宣称心理属性是同一于物质属性的。例如,霍布斯认为人类是物质客体,可以借助微粒的运动得到充分的解释,这些微粒组成了大脑与身体。但是他补充道:“我们所称之高兴或烦恼即是那种微粒运动的显现或感觉。”这种显现属于意识的领域,并且在这些早期的唯物主义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有时被为属性二元论(property dualism)的主张(与之对立的是笛卡儿的实体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他们并未冒险超越早先已经存在的极端观点,即人类和灵魂都是彻底的物质客体。
四、科学哲学的兴起
当然,唯物主义在当时并未形成任何重要哲学发展的核心,哲学反而追求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idealism)的反突现论者的理论,这些理论宣称自然界中所有的存在从根本上讲都是心理的。多种唯心主义的形式被公之于众,肇始于贝克莱和康德,并且直至20世纪初,唯心主义一直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尽管它对哲学史的意义是广泛的,但是唯心主义并非是本文首要关注的,因为它将意识接纳成物理世界的本体论基础,这意味着唯心主义在相关意义上是不存在意识问题的。然而,一种由唯心主义者发展出来的被称之为现象学的衍生物却尤其值得关注(可以溯源至弗朗茨·布伦塔诺和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工作),这种学说力求借助内省检验(introspective examination)证明意识经验的精确结构和内部构造。
在意识问题的发展中更有意义的是在该领域所引发的惊人关注以及从笛卡儿时代到19世纪末的科学的解释能力。此外,科学的普遍延伸,使得其中的两类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以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为标志的进化生物学的诞生,以及心理学从哲学的一个分支转变成独立的科学学科。进化论希望假设复杂性是怎样从简单形式中突现出来的,其明确的意义处于有机体领域内,但含蓄的意义则来得更加深远——直至囊括生命本身从无机物的原始材料(nonorganic precursors)中的起源问题。这迫使突现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否认意识可以在缺乏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可能性。对从无意识到意识的不连续迁跃的讨论,威廉·克利福德(William Clifford)写道:“我们无法设想从一个生物到另一个生物的巨大跳跃应该发生在进化过程的任一节点之上。”这种反对突现的“基因的”(genetic)论证所保留的意见至今尚存。基本的问题源自对突现的正常模式的观察,进化论将新异能力产生自更高级组织的复杂性的认识奉为圭臬(例如手工计算器与超级计算机之间的差异)。论证进而宣称正常模式无法解释诸如意识等独一无二属性的出现。同时,这种论证具有一些直觉的力量,使得可供选择的方案变成接受心理是宇宙的一种基本特征的主张,并从一开始就直接建立在创世说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泛心论与在直觉上的可接受相去甚远——相反,我们的经验强烈地建议意识是伴随动物体内复杂的神经系统的发展而在某一时刻突现的。
19世纪后期的许多思想家信奉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泛心论者的说法(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威廉·詹姆斯)。但是突现论者,包括约翰·穆勒与C.劳埃德·摩根,以“摩根法则”(Morgan’s Canon)而闻名,同样发展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理论,即自然将被视为在突现层次中的有序等级。这种有序等级源于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自然法则,它作为潜在的复杂性的发展支配着这种突现。这种形式的突现从根本上打破了上述讨论的正常模式,并且常常被称之为激进突现(radical emergence),以区别于普通的突现形式。根据激进突现的理解,从潜在结构(submergent structure)中推演出突现,甚至在原理上也是说不通的,除非有人也将不可还原性的和不可预测的“突现法则”(laws of emergence)考虑在内。突现论者将物理领域中普通的化学过程当作激进突现的一个清晰而非争论性的例子,并将这个观点拓展到生命与意识。当然,这种观点撇下了意识的显现(appearance of consciousness)作为一种最底层的谜团,它甚至接受常识的观点,不是变形虫而是狗才具有意识。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坦言:“刺激神经组织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意识状态?就像阿拉丁擦拭其神灯时为何会出现精灵那般难以理解。”
激进突现的学说暗中与经典物理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量子力学的发展似乎完全颠覆了化学的关键性实例,即化学成分的基础早在1925年就已经基本上可以被解释的事实(从那时以来所有迹象均显示物质的化学属性完全依赖于物理属性,并且无须实施激进突现的魔法就可以排列其成分)。在生物学中,这种学说的发展以发现遗传的化学基础而达到顶峰,随后摧毁了生命作为一种激进突现现象的合理性学说,这遗留下意识作为突现的唯一候选物,没有其他任何例子可以为突现提供支持。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兴起,同样也反对激进突现的观点。在最初将意识视作一个特有的研究对象揽入怀抱之后,在20世纪初,心理学对心灵的内部方面感到厌恶,并陷入到一种奇特的和对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长期痴迷之中——行为主义的核心(或唯一的)观点是:在心理学中唯一合适的研究对象是被试可以观察的、客观的身体运动。
从一个行为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意识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太容易被解决了:意识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可以借助特定的物理身体(physical bodies)的运动而加以定义的(或者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特定的方法安置物理身体的运动)。在哲学中,行为主义获得了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ts)的某些形而上学和方法论学说的鼎力支持,尤其是他们提出的意义的证实理论(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证实主义(Verificationism)意味着任何陈述只要是无法被客观地观察或测量所公开证实,那么,事实上其便是无意义的(meaningless)或荒谬的(nonsensical)。这种荒谬的一个例子来自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关于“什么时候是太阳上的5点钟”的问题。当有人试图宣称并不存在可公开观察的方法来证实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意义时,证实主义者往往会表现得极为恼怒。
行为主义对心灵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本质上将除了可以借助可观察的行为而被明确定义的内部心理状态统统拉入了黑名单。同样的,意识的研究往好处说被视作非科学的,往坏处说则是完全无意义的或者类似于尝试研究独角兽或采访福尔摩斯。行为主义对哲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如果不是其官方的教条,那么,就是行为主义者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强烈地影响诸如维特根斯坦与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等哲学家。他们或多或少地共同发展了这样一种对心灵的解释观,这种观点将关于心理状态的词汇(像“机灵”、“疼痛”或“想象”)当作是行为的模式而不是被试的内部状态。然而,也许对行为主义而言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推动了随后的自然化的初始哲学计划(nascent philosophical project of naturalization)。
将某物自然化即是证明在没有对该世界观设置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将其流畅地融入到世界的科学图景之中。例如,在19世纪中,活力论(vitalism)也曾是一种享有盛誉的生命科学理论,并且像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这样的活力论者也在类似胚胎学的领域中进行了奠基性的工作。但是,活力论声明生命取决于一种神秘的和非物质的“生命冲动”(elan vital),这种主张无法与物理学化的心灵思想家(physically minded thinkers)所支持的唯物主义观相调解。20世纪生物学的一个伟大成就是与伴随有机化合物的化学物质和有机体过程的物理属性等大量发现一起发现的基因编码的化学基础,这一基础服务于自然化的生命。现在生命被视作一类化学过程(可以确信的是一种巨大的复杂体),这一过程既不违背自然规律,也没有将一种非物质的实体引入到自然之中。
行为主义提供了一种朝向自然化心灵的相似进路。如果心理状态真的仅仅是生物体行为的复杂模式,并且如果生物体本身就可以“还原”为伴随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纯粹物理的交互作用而在它们内部进行着的化学过程,那么,心灵将不会对世界的科学图景构成任何威胁。
虽然行为主义已不复存在,但随之而来鼓励自然化的做法却逐渐成为了意识的哲学理论的核心特征,直至20世纪中叶。在自然化运动背后,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是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广泛接受——该学说坚持假设性的实体是经科学所假定的真实存在,但其典型特征对人类感觉而言是不可见的。当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某些真正意义上对该观点的抵制。19世纪有关化学结构的早期工作被视作只是一种组织可测量的化学倾向(chemical proclivities)的有效方法。一般而言,原子理论也曾同样被视作一种有用但并非实际存在的模式,激起了诸如威廉·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等20世纪初期的杰出的科学家的一致反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简·佩兰(Jean Perrin)在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方面的工作在传统上而言常被引为反原子论(antiatomism)的致命一击。无论如何,自此科学有权利与能力宣称世界的不可见的深层结构变得可以被广泛地认识。尽管原子的存在符合激进突现论的主张,但显然在原则上将化学还原为量子力学的建议反而认为世界完全是在一种仅受量子层面上的规律支配的少量特异的量子实体(exotic quantum entities)的交互作用基础上运行的(在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合作关系[uneasy partnership]中与极其巨大物体的广义相对论原理相伴随)。
科学的显著能力宣告了存在于现象“背后”的世界的特征,澄清了并非是直接的可观察性才导致行为主义的狭隘看上去是不必要的阻碍甚至是愚蠢的,并且该学说的式微终究使其被一种巧妙地模仿其他科学并假设存在内部心理过程、状态与事件的认知心理学所替代。这种内部心理活动仅仅是间接地并与产生的行为相一致。此外,自动机的论证(automaton argument)也揭示了内部状态的重要性。如果对心灵归属(ascription of mind)而言,行为即是所有东西,那么一种被预编程序的、其动作看似好像拥有一个心灵的机器创造物,实际上也应该具有一个心灵。这种推断看似违背了一种强烈的直觉:即行为事件之原因的作用(在僵尸[zombie]与真正的人类之间存在着差异)。
五、近期的意识研究取向
为了回应已被日益接受的科学实在论和行为主义的衰落,哲学家(尤其是J.J.斯玛特[J. J. C. Smart]与U.T.普特斯[U. T. Place])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激进形式,该理论认为,不仅人类完全是物质客体,而且心理属性也同一于物理属性,特别是同一于大脑的属性(properties of the brain)(或状态)。这种中枢状态的同一论(central state identity theory)宣称意识的状态,比如对疼痛的感觉或颜色的经验只不过是在大脑中所处的状态或过程。这并非指大脑状态与心理状态相关或引起后者,而是激进地认为疼痛的属性仅仅是一种神经属性(neurological property)。非常明显,这样的观点充分地符合世界的科学图景(其目的即在于与之相符合),避免了行为主义者荒唐地否认存在着内部心理状态的做法,并且躲开了交互主义者的二元论(interactionist dualism)的所有问题。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交互主义者的二元论也是突现论的一种形式,但不是上述讨论的激进类型,而是遵循正常突现模式的一种温和的类型。在这种类型中,突现是可解释的新奇事物(explicable novelties)。世界的科学图景充斥着这种类型的突现(龙卷风、热力学属性等),并且同一论者能够利用其理论将这种突现类型添加到科学之中。
然而,不久伴随同一论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严肃问题。将心理与物理属性同一起来的概念在形而上学上看多少有些可疑,但是拥护者指出,在科学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属性同一,其中最频繁地被提及的是一种气体的温度同一于其构成分子的平均动能。反思这些由经验发现的同一性的启示引出了大量重要的哲学进展。但是,除了形而上学顾虑之外,更加坦率的反对同样得到了发展。“神经沙文主义”(neural chauvinism)就是问题之一(这一术语由内德·布洛克[Ned Block]创造,他是这种反对的早期支持者)。假设我们邂逅了一位外星人,从外表推断他是有智慧与意识的生命。随后我们发现他们的内部心理活动与我们自己的心理活动存在天壤之别——他们并没有我们熟知的大脑。那么,由此可以将他们从心理拥有者的队伍中排除出去吗?许多不同的内部系统可以产生意识,这在直觉上看似合理,但是这却直接违背了同一论。同一论的另一软肋在于,因为其将心理同一于物理状态,这在解释主观性本质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所有的物理状态都完全是客观的并且在原则上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是,有意识的状态的主观特质好像无法经由物理结构的知识和大脑的运作而被揭示(这一系列的论证在该领域内非常普遍,最初是由托马斯·内格尔与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提出的)。因此,为什么特定的物理属性是主观的,这一点似乎变得扑朔迷离(我们不能仅仅说它们具有主观特质或特征,因为同一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所有这些特征是严格同一于物理属性的)。
同一论的一个变种称之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它将同一论的核心问题归结为一种对特定的分析水平的错误同一(misidentification)。按照功能主义的理解,在神经硬件内部无法发现心理状态,作为替代的大脑的功能性架构(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brain)可以等同于心理状态。数字计算机的运作作为一个频繁的类比引领出功能主义者的口号:软件之于硬件犹如心灵之于大脑。正如相同的程序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计算机上运行那般(并且,在原则上,一台计算机可以由任何成分组成),心理状态也可以在许多不同的物理载体中执行或实现。全部所需的就是内部状态系统与合适的组织方式相互作用,引起内部的改变与外部的行为共同符合拥有一个心灵的状态。功能主义具有一种明显的吸引力:它利用当前的技术性类比(在解释心灵的谜团时常常通俗易懂),在没有诋毁脑研究的同时,还鼓励一种心理或认知架构的抽象领域,并且它允许一种朝向自然化心灵的相当清晰的可接受的进路。这在避免神经沙文主义反对同一论的同时,回避或至少在形而上学上消弭了同一论那令人不安的属性同一性(property identifications)特征。而且功能主义在适应当前科学理论方面,尤其是与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认知科学的跨学科领域保持互动上并不亚于同一论。认知科学含蓄地将功能主义者的观点接纳为其核心的视角。平心而论,以这样或那样形式遗留下来的功能主义逐渐成为有关心灵本质及其如何融入自然世界的诸多理论中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然而,功能主义依旧面临着其本身的一系列问题。不受任何特殊物理载体约束的优点却也潜藏着一种心灵太过自由式分布(liberal distribution)的缺陷的威胁。如果任何系统拥有合适的组织便可认识到有意识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可以正视某些非常奇异的实现形式。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由内德·布洛克率先发展而来的例子:组织一(非常大)群人来回反复地传递文本讯息以便模仿一个心灵承受剧烈疼痛的功能性架构。很难相信这样一个系统可以产生任何所承受的疼痛(除了参与者可能感受到的折磨人的厌倦)。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奇异的实现形式被排除出去,那么,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就像对同一论一样,对于意识主观状态的存在的解释究竟是什么?然而,忍受这种奇异的实现形式并未使得问题消失。正如在同一论中存在着为什么物质的特定组织结构应该拥有(或实现或执行)意识的主观特征这样的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功能主义也许会比同一论变得更糟。仅仅是一种组织如何产生彩色的现象?1
功能主义明确而不是隐晦地表达了另一种折回到笛卡儿时代的担忧。如果心理是一种组织特征,那么,它将不同于其物质载体,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其又如何被实现,均仰赖于物质并由物质所决定。既然如此就产生了有关心理因果性的另一个问题。组织依靠本身看上去无法引起任何东西,只能从任何可能是被组织起来的质料中“借用”因果效力(causal efficacy)。一个简单的例子,考虑一下飓风是如何导致死亡与摧毁的。飓风等诸如此类的现象是正常模式的突现。将这类突现看成大气的组织特征貌似合理,它完全依靠并由温度、气压等潜在的大气属性所决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飓风并不等同于地球的潜在属性——各种各样的气体配置能够产生飓风(例如,它们或者类似于木星中的漩涡扰动,其所形成的大气与地球上的大气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质问飓风的因果效力位于何处,又会怎样呢?显然不存在于飓风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其潜在的特征(如风速)之中。转而思考意识的情况,其担忧在于,例如疼痛只有借助潜在载体的力量,而无法借助存在疼痛去引起任何东西。这一点与直觉严重相悖。因为我们很难否认疼痛在其本身中拥有因果效力。当我们询问如此抽象的心理状态(比如对意义的觉知)可以拥有任何真正的因果效力时,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尖锐。
这种从高阶属性流向低阶属性的“因果疏导”(causal drainage)是自然化工作的一个普遍特征,并且它看似在远离意识的领域内完全无害。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一次飓风是如何借助其成分而肆虐的,但不太愿意承认我们的意识状态仅仅是借助完全无意识的实现这些状态的组成成分而起作用的。与感觉意识相对照,有意识的思维看似更糟。当前最受追捧的关于心理状态如何获取意义的哲学理论在本质上也牵涉外在于心灵的实体。因此,这些观点也被称为外在主义(externalism)。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介绍了一个著名的哲学思维实验,假设有一个遥远的行星,表面上与地球难以区分,但是一个特别之处不同于地球:我们的水(H2O)被孪生地球的另一相似的适宜饮用的液体物质(XYZ)所替代。根据意义理论的观点,外部关系是一种将内容分派给有意义状态的机制的本质部分,我们对于H2O的指称决定了“水”的意义,而在孪生地球上对XYZ的指称同样决定了在孪生地球上使用的“水”的意义。当我的孪生兄弟在孪生地球上思考“我想要一杯水”时,他所思维之物在内容上是与我相异的,不管我们在物理层面上可能有多相似(忽视与哲学不相干的不便事实——所选择的例子仅仅是思维实验的产物——我们主要是由水组成,而我们的孪生兄弟主要由XYZ组成)。此外,关于外在主义,还有一些由泰勒·伯吉(Tyler Burge)所倡导的极具诱惑力的论证。这些论证强调意义的社会维度,即主张我们的思维内容受惠于我们的语言环境。例如,我们可以思考合法契约,即便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承担一无所知。有人可能进行误导性的思考,比如,契约必须是书面文件。虽然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的思维的确与“我们”的合法契约有关。在孪生地球上,也许契约并非必须被书写下来,所以,我们的孪生子正在思考着一种关于“他们”的合法契约的真实姿态。
总之,外在论者关于思维的考虑是这样的,即如果两个物理层面完全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可以思维不同的内容(并且我要强调的是这的确应该是这样,即便环境的不同没有影响到参与其中的个体的心理状态)。对此可以想象一个粗糙的类比,两张相同的纸可以在它们的地位上存在不同,比如其中之一是“货真价实的美元”。可以争辩的是,因果力(causal powers)存在于执行其心理状态的物理结构之中,并且这些结构对于环境的差异并不敏感。因此,依赖其内容的内容——承载(content-carring)的心理状态并不是有效的(“存在一种货真价实的美元”的属性所具有内在的因果效力已经不存在),当我们考虑外在因果关系的力量时,即使内省化地通向我们思维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再一次严重地违反了直觉。
心理因果性的问题同样出现在D.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称为“异态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的著名理论中。该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革新形式——断言心理与物理领域并非且不能由任何科学的心理物理学法则连接起来,即便可以对事件进行心理与物理上的描述(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斯宾诺莎的身心两面观[dual aspect view])。戴维森承认心理与物理事件因果性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并非像看到的那样是由于事件的心理属性引起的,而是由于事件的物理属性引起的。同时戴维森注意以极大的怀疑态度讨论“由于……引发”(causing in virtue of),并将其视为我们理解因果性的一种极佳特征。例如,假设一块砖砸在你的脚趾上并且你感到疼痛,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由于砖的重量而不是其颜色造成的。所以在异态一元论中的担忧是,事件的心理属性在因果性上是无效的(至少在物理世界中是这样)。
最近,意识的问题、内容与自然化在某些令人激动的理论中被联系到了一起,这些理论将心灵的表征力(representational power)当作了意识的成分,因此,削弱了自然化意识带来的问题,并将其设想为是相对容易的自然化表征(naturalizing representation)的任务。其中的两大取向需要简单地提一下。其一是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亚里士多德,将一种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定义为作为另一种心理状态的目标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高级的心理状态。即,仅仅当某人正拥有一种思维以便使其处于S之中,那么某人的心理状态S才是有意识的(这种滞后的思维不必是有意识的,并在一般情况下将不会是有意识的,除非或直至已经出现了关于这种思维的高阶思维[higher-order thought, HOT])。显而易见,这类理论被称为意识的高阶理论(HOT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这类理论存在大量不同的版本,但是它们均共享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心理状态是通过成为另一个心理状态的目标而变得有意识的。我们所有的意识状态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似乎可以立即用来内省。高阶取向将这种特征作为一种意识本身的定义性特征。一个心理状态的本质对内省的“可用性”(availability)依旧处于争论之中——从将这种可用性等同于主动的内省(active introspection)(因就像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独创的高阶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到将其等同于潜在的内省(potential introspection)(正如彼得·卡拉瑟斯[Peter Carruthers]所改进的高阶理论),又抑或将其等同于描述控制语言产生系统的心理状态的获得状态(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解释中涉及的)。
反对高阶取向的论证在于否认对一种称为有意识的状态而言无须任何形式的高阶理论,而只需假设意识可以借助一阶表征(first-order representation)就可予以阐明(该观点的两位著名的支持者是雷德·德雷特斯基[Fred Dretske]与迈克尔·泰尔[Michael Tye])。我们意识到的仅仅是那些我们正在表征的心理状态。一个支持这种取向的著名论证源自所谓的心理状态的透明性(transparency)。透明性是意识的现象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意识的对象和我们的经验之间似乎一无所有。尝试一下实验。仔细注视一个邻近的咖啡杯。现在尝试将你的内省主义聚焦到看这个杯子的视觉经验属性上面。你将会发现在意识中除了杯子本身的特征并没有出现任何东西。因此,经验是透明的。这鼓励意识的一级表征理论拥护者去反思,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在知觉或思维过程中大脑如何表征物体,那么,我们就将有可能解决意识的问题。并且,当然,如果意识能够被还原为表征,那么,自然化视角的前景将会变得更加光明。较之主观意识,“表征”将被视作更加直截了当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一阶与高阶取向都同意),并且事实上当前大量自然化表征的理论正在兜售上述主张(尽管,作为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它们都饱受自身致命缺陷之苦)。该取向的一个问题是表征看似非常容易发现,若将其视为意识的本质则不免过于廉价了。如果有意识仅仅意味着去表征,那么,意识的出现岂不是随处泛滥了吗?我们可以凭借有意识的存在的约定将书籍、电影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视为衍生的表征(derivative representation)而不予考虑。然而,也许即便是原始的表征也过于宽泛,并且一种泛心论也会威胁侵入我们的信息负荷的世界。标准的回答是在认知系统中制定某些特殊的表征领域作为意识的归属地。然而,反复出现的解释问题恰恰是这些表征为何喜欢回归主观性。
拥护一阶理论并不重视内省在接近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这种接近正是意识的特点。恰恰相反,内省是一种“增添”的可选择的附件,只有生物才能以相当复杂的概念装备(conceptual equipment)来利用内省。意识本身是心灵的一种相对简单的、更初级的特征。因此,在两种取向各自面对动物意识的态度中可以发现一种有益的比较。在一阶理论看来,动物的意识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动物拥有表征其身体及其环境的不同特征的认知系统(最为显著的是,这种特征的相对生物性价值是在我们称之为疼痛与愉悦的信息源中的最基本的层次上被编码的)。因此,可以预料的是,我们与它们共同分享一种基本意识的根本性类型。高阶取向认为,动物的意识并不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予以解释。因为一种心理状态是有意识的,其必要条件是只存在一个关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思维,动物只有在掌握那些用以思考它们处于心理状态的概念的情况下才会是有意识的。换言之,仅仅为了感觉疼痛,动物将不得不具有心理状态的概念,至少具有那种将疼痛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概念。毫不夸张地说,动物要想掌握这些概念在直觉上是看似不可能的。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回答,从“温和”地宣称意识所需的概念归根到底并非真的非常复杂,到“激进”地认为概念的缺失恰恰显示了动物并非有意识的生物(这里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对笛卡儿学说的奇识,动物只是自动机让这种观点声名狼藉)。
综上所述,伴随这些近期源自对表征或意义的外在主义者解释的呼吁取向产生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在这种呼吁中表征的内容只有在适当地与其关指的状态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带出一种状态。一个直接的问题是:正如随意创造一张恰巧与美元钞票完全相同的纸并不会是真正的货币那样,太过随意地创造恰巧等同于人类的实体也不会拥有任何表征状态。如果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或者甚至只是依靠表征,那么,也可以得出这种随机创造的人类将会是完全无意识的。例如,表现在其行为(无法与我们的相区别)、神经过程(等同于我们的)、聪明的交流能力(从表面上看)方面等等,这一结论似乎非常值得怀疑。
第9篇: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范文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 上一篇: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范文
- 下一篇:想象力训练的好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