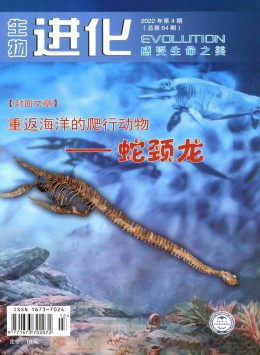生物多样性及其意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意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生物多样性及其意义范文
关键词:里山;新农村景观规划;E-CCP模式
一、“里山”的含义及其由来
关于“里山”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日本江户时期,是指村落周围山林及其环境的总称。实际上,里山是相对于深山而言的村落自然景观,是一种人里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有池塘、农田以及与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森林等。所以,里山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集合体,保护、管理和发展里山,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艺术”,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承[1,2]。 据有关文献记载[3],从1603年江户时期至今,“里山”的演变主要经历了江户、明治、二战后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四个时期。
表1 “里山”理念在不同时期的演变特点
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创伤,发展经济成为主要任务 经历十年经济危机后逐渐复苏
里山活动 狩猎、捕捞、采摘、砍柴、制木炭、水稻栽培等形式 石油、煤气等的使用,使里山中堆积的大量树叶、枝桠等缺乏管理,森林功能退化 石油、煤气等大量的使用,使里山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教育、发展特色经济为一体
里山理念 组成山村村落的景观林、薪炭林,与村民生活密切相关 福田氏提出里山由村落-田地-山野等配套组成 里山成为人类追求“自然生态”的代名词 村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包括森林、草地、农田、河流以及古建筑等
综上分析,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里山的含义已从单纯的薪炭林概念转变为复杂的村落自然景观层次,这种概念的扩展是基于人类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而确定。历史发展表明,对里山的认识过程大致是:自然生存下的简单认识――先进技术文化冲击下的认识――回归自然生态理念的再认识――生态景观层次上的新认识。
(一)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里山中的自然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里山的自然曾遭受到过度的人为干扰,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在此期间急剧下降,里山的自然景观受到严重破坏。此后,人类认识到里山的存在对生存环境的重大影响,开始通过改变管理里山的模式恢复其原生性,即通过人为管理加强里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降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强度等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里山发挥最大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
(二)注重生态文化价值
“里山” 的含义有人为干扰的因素,这种干扰大部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的,干扰的理想状态是科学的管理里山的资源,使里山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同时,里山大部分也是自然村落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带,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以及生态文化等。对居民们而言,里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让其享受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自然资源,而居民在这片土地繁衍并将文化元素不断融入里山文化中,丰富和发展了里山的文化。里山同时为生态教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围绕里山可以开展各种生态性的科普宣教、生态旅游等活动,让人类在自然中寻求更多的文化价值。
(三)延展乡村景观范围
从日本京都濑屋县内1970年至1995年的“里山”情况调查得知,当地的乡村景观范围从森林、农田、草地、溪流等扩大到商业种植园、耕地、建筑物等。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薪材、木炭的薪炭林减少以及对稻田、草地、芦苇田、人工针叶林和次生林的保护及修复所形成[4]。因此,乡村景观逐渐将人为自然景观也纳入其中。
(四)强化管理与社会参与
经过破坏的里山环境,需要借助各种技术与社会参与得到科学的恢复。而整个“里山”的恢复过程从人类意识到需要恢复开始直至后来得到良好的恢复,政府部门、各种环保组织与当地村民组成了一个有机、高效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里山恢复的时间与质量。相对于大众消费旅游视角而言,所提倡的少数人参与、志愿管理维护的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发挥社会各种资源来参与管理里山,丰富和发展乡土景观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5,6]。
三、当前我国新农村景观规划存在的一些误区
新农村规划在我国起步较晚,继《城乡规划法》、《村庄和计征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之后,对新农村规划有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依据。但对于新农村景观规划仍有不足,甚至有些地区认为新农村景观规划就是把原有道路、建筑、场地等拆除来建造高楼、广场、园林等,将大城市曾经有过的行为蔓延至新农村[7]。目前,主要存在以下误区:
(一)缺乏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认识
对于从事农村规划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资格要求不高,导致实际从事规划的人员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加上时间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使破坏性建设时有发生。如有些地区将蜿蜒曲折的自然河流填平或取直,违法建设占用基本农田,乱砍滥伐森林,“剥山”种植经济林等,均对原有的自然景观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8]。
(二)缺乏多维度的农村景观规划
采取城市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村规划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对于景观规划,不仅要从利益出发,注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更应注重其所带来的污染、噪音等问题,从时间、空间、文化等多维度综合考虑农村的景观规划。
(三)盲目城市化、忽视乡土文化
乡村的“破旧”不堪使得人类向城市看齐,由此改变了人类原有的价值观和对家园的认同感。乡土文化的消失不是新农村建设造成的,而是对农村历史发展、文化特性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关系缺乏认识导致的[9]。
(四)相应法律规范和公众参与制度不足
根据当地各个省、市、县及乡(镇)出台的规划体制来进行相应的新农村景观规划产生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在以往 “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中缺乏对农民自身意愿和当地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使在实际操作中显现出一定的缺陷[7]。
四、“里山”理念对新农村景观规划的启示
基于日本“里山”的核心理念中对生态的保护意识以及所采取的保护行为等,笔者认为我国新农村景观规划的方式可以借鉴“里山”理念中科学有价值的成分,形成以“生态”为中心,“意识”、“保护”、“发展”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模式,即E-CCP模式(如图1所示)。E-CCP模式重点在于:意识,对于新农村景观规划的参与机制问题,核心在于村民和政府两者对待农村景观规划上的主观和客观意识问题;保护,对于新农村景观规划中生产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历史环境等一系列人为、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延续问题;发展,是整个规划的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在于调节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有序发展。
图1E-CCP模式图
(一)新农村规划中的生态
生态(Ecology),是指整个村落生态系统。笔者认为整个村落生态系统包括可建设范围、不可建设范围和禁止建设范围。可建设范围,即居民的生活开发区域,可以根据相应的规划进行改造,例如房屋、集贸市场、排水渠等;不可建设范围包括天然池塘、河流、风水林等,但可根据相应规划进行适当修善;禁止建设范围包括农田、原始林、天然湿地、古文化建筑等,这些区域不允许人为过度干扰。所以,农村景观规划的主要区域为可建设范围和部分不可建设范围。
(二)新农村景观规划中的意识
意识(Conscious),是指在整个区域内的社会意识、自然意识,包括村民和政府两方面。里山能得到保护,离不开居住者的参与,也离不开政府对于保护的支持。从破坏到保护,人类经历过一个“反省”过程,逐渐开始关注环境、景观、资源、生态、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步确立开发与保护并举的规划理念,明确了居民参与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参与机制[10]。
(三)新农村景观规划中的保护
保护(Conserbation),主要是指对于整个生态环境、居住环境、人文历史遗产等的保护。目前,我国新农村景观规划缺乏地域文化特色。而查阅“里山”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几百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与生产生存方式在乡村中仍然延续着,这是故乡情结的体现,也是在现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原生态的最大保留。对“新”的认识是基于“旧”的定位,“新”与“旧”可以是对历史文化、建筑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的再认识,所以在规划建设中应该考虑不同群体的存在方式,为他们营造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一些具有自然状态与文化元素的存在物进行合理的保护。
(四)新农村景观规划中的发展
发展(Progress),是指各产业的发展。发展并不意味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以日本京都濑屋县内1970年至1995年里山内的主要土地和景观多样性为例,保护原始森林、分散土地使用、扩大人工林面积、恢复退化生态系统、营造人工景观等,从单一的自然景观扩大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形式。在保护和恢复村落生态系统的同时,也增加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显示出科学合理的村落发展生态理念[4]。
五、结束语
在我国的新农村景观建设中,不能单以经济因素来决定整个规划的走向及程度,应该坚持从生态、人文、经济等可持续的角度去把握规划的理念及开发建设的强度。在资源急剧短缺的今天,我们更要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在新农村景观规划中,以“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以发展特色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等为落实点,找准农村发展的定位,真正建设出“让政府得民心,让农民得实惠,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农村景观。正如张安所提出的“国民所期待的‘美丽农村景观’的内在意义在于‘与环境共生的农村景观’”[9,10] 。
注:本研究受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804100003)资助,特此感谢;*廖为明为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张玉钧.日本的里山[J].绿化与生活,2000,(4):13.
[2]章俊华.LANDSCAPE 思潮[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张玉均,北尾邦伸.日本的里山及其管理与保护[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23(1):90―92.
[4]Katsue Fukamachi, Hirokazu Oku and Tohru Nakashizuka.The change of a satoyama landscape and its causality in Kamiseya , Kyoto Prefecture ,Japan between 1970 and 1995 [J].Landscape Ecology, 2001(16):703-717.
[5]Hiromi Kobori,Richard B.Primack.Participarory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for Satoyama,the Traditional Forest and Agricultural Landscape of Japan[J].Ambio Vol.32 No.4,June 2003.
[6]周春光,刘建民.从日本“里山”现象看京郊民俗旅游[J].河北林业科技报.2006(1):30―32.
[7]寇建芝.当前新农村规划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报.2008,12(5):139―141.
[8]平,俞孔坚.新农村建设宜先做“反规划”[J].北京规划建设,2006,24(5):189―191.
[9]吴敏.对我国农村景观资源的再认识[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报),2010(1):35―36.
第2篇:生物多样性及其意义范文
一、艺术理论:一门居间的学科
说到艺术理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定位,而定位关涉定性。
从当代人文学科的知识系统来看,艺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没有问题。但是,它在人文学科中处于何种位置却很难回答。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知意情及其哲学三分,使美学有了自己的合法地位。②如果说的确存在着一种独立的艺术理论知识系统的话,那么,它与美学的关系显然最为密切也最为纠结。自黑格尔以来,美学几乎完全成为艺术哲学,许多美学家俨然就是艺术理论家,他们的著述大都集中于对种种艺术现象的思考,比如苏珊朗格或丹托等。如果说美学即艺术理论,那么艺术理论的合法位置在哪里呢?另一方面,艺术理论又和具体的门类艺术理论相互缠绕,比如造型艺术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等,这些具体门类的艺术理论界限不那么容易明确区分,尤其是造型艺术理论,它提出了扮演一般性的艺术理论角色。
定位艺术理论难免会揭示出它的两个困境。其一,艺术理论居间的尴尬地位,它好像介于天地之间的半空中,上有美学,下有各部门艺术理论向上延伸,艺术理论就进入了美学或艺术哲学的领域;向下深入,它就侵入各门具体艺术的领域。显然,艺术理论具有某种居间性特征,它一方面表明了它是一个延展性和关涉性很强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与其他知识系统相互交错。其二,居间性的知识系统往往容易被边界清晰和成熟的知识系统所‘‘殖民”。即是说,艺术理论不是被美学家所侵吞,就是被部门艺术理论所覆盖,好像它没有自己的家园而居无定所。由此推论说,艺术理论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非自主性。
如何定位艺术理论呢?我们需要拓展思路来考察。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在讨论现代主义绘画时曾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主义绘画所以有别于此前的绘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主义绘画具有一种自我批判性。他认为,这种自我批判源自康德哲学和美学,构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冲动。这一自我批判要做的工作是确立绘画有别于艺术的根基,它就是绘画的二维平面性。转向平面性是现代主义绘画的一次变革,它告别了文艺复兴透视法发明以来绘画一直与雕塑竞争的局面,抛弃了在二维平面上经营空间深度幻觉的把戏。格林伯格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绘画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批判为自己确立了更加安全的立足之地。只有当绘画有别于雕塑等其他造型艺术时,绘画才为自己找到了安全可靠的安身立命之地。③格林伯格分析现代主义绘画的方法对于我们反思艺术理论的定位有所启发。
我以为,对于艺术理论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居间性和非自主性,我们可以从更加积极的方面来探究,通过自我批判找到它的合法性根基。艺术理论居于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反过来看恰恰是艺术理论的优势所在。何以见得?第一,艺术理论在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及其艺术史之间,可以将哲学和美学关于艺术的资源引入艺术各个领域,对艺术的分析和解释提供更具理论性的观念和方法。其实,只要对当代各门艺术的研究稍加检索,就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门艺术研究的理论资源多半来自更为抽象和更具思辨性的哲学、美学、社会理论和文化史。缺少这些更具理论性的学科资源,各门艺术理论是难以自成一家的。即使是音乐和戏剧这两个非常技术性的研究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其他理论领域的深刻影响。因此,借助艺术理论这个居间学科的传递和渗透,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可以更加顺畅和有效地进入各门艺术的研究。第二,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同时又可以把具体艺术部门的各种现象及其特殊问题带入更高的理论层面,去激励艺术理论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甚至去叩响哲学殿堂的大门。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美学的兴起,抵制思辨美学的经验美学或科学美学开启了自下而上的艺术及其心理学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学自古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路径。这里不妨借这两种说法来描述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及其独特功能,即我们可以把艺术理论设想为同时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运动的知识系统。向上则进入哲学思辨领域,向下则延伸进各门艺术的肌理之中。
乍一看来,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好像正说明了它的局限性,没有属于自己地盘,就像一个‘‘倒爷儿”。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那么,不妨把这种居间性视为艺术理论的一个特点。在我看来,艺术理论的居间性突出地表现在它为各种艺术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提供某种丹托所说的‘‘种种理由的话语”。丹托晚年在关于‘‘艺术界”的重新界说中提出,艺术界中各种批评理论究其本质不过是有关艺术“种种理由的话语”(thedis¬courseofreasons):艺术品是符号性表达,在这种符号表达中它们体现了其意义。批评的意义是辨识意义并解释意义的呈现方式。照此说法,批评就是某种有关理由的话语,它参与了对艺术体制理论的艺术界的界定:把某物看成艺术也就是准备好按照它表达什么及它如何表达来解释它。
参照丹托的这一说法,我把这些‘‘理由的话语”视作艺术理论的基本工作。艺术界里各式角色都参与了这种“理由话语”的生产,从批评家到美学家,从艺术史家到策展人,从画商、经纪人到收藏家,还有各种艺术教育体制中的从业者。但是,艺术理论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立法者”和‘‘阐释者”(鲍曼语)角色。®即是说,艺术理论的基本工作就是关于艺术‘‘种种理由的话语”生产。用丹托早年的艺术界规定,那就是“将某物视作艺术需要某种眼睛看不见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的知识,亦即艺术界”(Danto“AW”40)。
没有这种“艺术理论的氛围”或“艺术史的知识”,可以肯定,任何门类艺术批评阐释或研究都难以展开。回到格林伯格关于自我批判的看法,或许可以说艺术理论就是通过‘‘种种理由的话语”而确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的。更具体地说,艺术理论就定位于为各种复杂的艺术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提供这种相应的原理、范畴、标准和方法等。接踵而至的问题是,美学不也同样是关于‘‘种种理由的话语”的研究吗?如何区分它们的差异呢?在我看来,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理由话语”各自所属的层次有所不同。美学通常是在哲学层面对有关艺术的种种理由所做的更加宽泛、更具有思辨性和更抽象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美学的讨论有时并不全然以艺术为焦点,而是更加宽泛,甚至是某一哲学观念的推证或延伸。艺术理论则有所不同,它关注的就是艺术这个焦点,是对艺术文本及其语境解释的根据或理由的探讨。因此,从美学到艺术理论有一个高低层次的区分,有一个焦点从宽泛到聚焦的变化,有一个远离艺术到切近艺术的发展。这正是艺术理论的居间性定位及其功能的体现,也是艺术理论自我批判所确立的自身合法性所在。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艺术理论居间性功能的自身合法化,并不是说艺术理论有赖于美学提供资源,然后再向具体艺术部门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和范畴,只起到一个‘‘二传手”的作用,而是说居间的定位要求艺术理论努力去建构属于自己知识体系的相关概念、范畴、方法和原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美学理论,同时又区别于门类艺术的具体理论。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艺术理论应该是一种相关性的话语,一定程度上与美学或门类艺术理论交叉,因而其知识系统是一种相对的区分。换言之,艺术理论在美学和部门艺术理论之间建立了自身的知识体系,通过与上位和下位知识系统的对话协商,逐步确立了自身独特的‘‘种种理由的话语”系统。
二、艺术理论:一个知识生产场域
丹托的“艺术界”虽说是一种模糊的描述,却也标明了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学科领域,而是一个包容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场域”,一个与其他知识领域相互纠缠的交界地带。后来,迪基把艺术界这一概念更加具体化了,把它设想为是由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组成的,包括艺术家、记者、艺术史家、批评家、理论家、美学家等。这批人的参与使得艺术界运转良好(迪基111)。仔细辨析这种说法,我以为它受到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影响或启发。
库恩在研究科学史演变时发现,科学知识的革命其实就是其知识范式的变革,而范式也就是科学家共同体所共有的学科规范:
—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得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所谓范式也就是由科学家共同体所组成的,而科学家共同体又是由背景相同、研究兴趣相近的人组成的。从共同体到范式到知识,科学知识的生产流程也就形成了。这个原理对于解释不同知识系统也具有普适性,用于说明艺术理论领域同样如此。
自从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目录调整后,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国内不少院系申报此学科并获得成功。于是“艺术学理论”便走上了历史前台。显然,不同的学校和学科各有不同的传统、理解、资源,对于如何建构艺术理论学也有不同的取向和看法,这就形成了多样化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稍加分析可以发现,构成当下中国这一学科学术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情况有点复杂。首先是来自综合性大学的一些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依据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以及所具有的理论学科传统,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上强调艺术理论的总体性和涵盖性。其次是来自专业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的从事具体艺术门类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是扬长避短地强调各门具体艺术门类的重要性,质疑在各门艺术理论之上的总体性艺术理论的合法性。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学中国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恰恰是艺术理论本身居间性所导致的,它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力量的抵牾所形成的。
我们知道,任何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演变,都依赖于从事这一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的协商。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概念的形成说穿了乃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其能指的选择是约定的,而其所指也是经过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的约定而形成,其意指也随着知识和时代而不断变化。®由此来看,所谓“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其定名也不过是特定学术或学者共同体的一种协商性的约定。晚近关于艺术理论的争议和论辩,也是这种约定过程必不可少的现象。由于参与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从业者背景和诉求有所不同,来源于的高校体制也有所差异,所以出现争论和不同取向是正常的。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理论研究倚重于以理论见长的学者,艺术专业院校的艺术研究倚重于特定艺术门类及其实践,两种取向的抵牾恰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理路的碰撞。
从更加宽泛的视角来说,艺术界才是艺术理论赖以生存的场所,参与艺术理论知识生存的不只限于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还包括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艺术研究院所、艺术团体、网络和杂志编辑、文化产业或艺术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等。这些人对艺术理论的知识建构亦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但他们也都是从各自专业背景和学术资源以及实践活动的特点出发,参与到艺术理论的建构中来,并对艺术理论学科的形成产生不同影响。
在我看来,艺术的专家共同体对艺术理论知识系统的约定,是通过各种话语的争辩和讨论而体现出来的,由此形成丹托所说的‘‘种种理由的话语”。当然,不同的学者会给出不同的“理由”,因而其艺术理论的话语形态也就呈现出不同面貌。这一知识生产的现状为我们反观它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为我们理解艺术理论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提供了依据。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艺术多样性及艺术理论生产者的多样性,决定了艺术理论形态、方法、观念的多样性。就目前而言,充分发挥不同学者的各自优势而不是强求一致,鼓励艺术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不同形态和研究的不同路径,这有助于推进这一知识的发展和深化。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每一知识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其中活动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彼此协商甚至冲突,进而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学术共同体。但是,每个场域中的象征资本是相当固定的,每一参与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学者及其体制,都无一例外地想方设法维护或扩大自己在这一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因此,艺术理论知识生产场域中就难免有象征资本的争夺,此一争斗具体化为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一般说来,象征资本大的共同体成员,其话语权也就更大,而边缘或弱势或初来乍到者就会努力捍卫自己的话语权,以便进入该场域参与知识生产。由此来看,无论是知名学者还是初出茅庐者,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当他们进入艺术理论场域时,都带有某种“工具理性”的潜在意图,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所以,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现有优势而占据一席之地,就成为艺术理论场域建设者们必然的策略。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综合性大学和专业艺术院校不同学者之间的理论取向冲突的原因,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现有的象征资本进入这一知识场域的,如果放弃自己现有的优势而改弦易张,那将会失去已有的象征资本而沦为“无产者”。
这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引向如下问题:艺术界中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的对“种种理由的话语”的话语建构,如何实现索绪尔所说的那种人为约定性呢?
如前所述,在艺术理论的场域中,由于存在着象征资本分配不均的情况,由于学术传统差异的原因,由于不同院校专业学术体制的关系,关于艺术的“种种理由的话语”讨论,必定存在着各说各话并据理力争的复杂局面。不同象征资本的拥有者的话语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不同的学术体制(如不同院校和专业等)会有不同的导向,加之中国特有的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更是家常便饭,因此有关艺术理论的讨论显得更为复杂。在艺术理论知识生产场内,存在着威廉斯分析文化时所指出的三种形态:主导的、残存的和新兴的三种艺术理论。主导地位的理论话语具有较多象征资本,往往与体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起作用;传统的甚至较为保守的话语,特别是有关古典话语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新锐激进的话语,它们不断地挑战已有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观念。这三种话语相互角力抵牾,形成了艺术理论场域的内在张力。
但是,我们知道,在学术领域,尽管象征资本的不同会导致话语权的差异,但是学术场域的游戏有自己的规则。特别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形成的规则,对于解释学术领域的游戏规则有所助益。强制的、权威的话语并不能压制其他话语,必须在理性论争基础上求得认同,学术研究有赖于学术共同体在理性论辩基础之上所达成的共识。换言之,学术争辩不看说话人的威望、地位和权力,而取决于他的话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或赞同。⑦当我们说艺术理论是艺术界的学术共同体人为约定的产物时,究竟如何约定形成艺术理论的知识体系呢?
其实,从学术史层面说,每门知识或学科的发展都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学术的发展和成熟。艺术理论也许是因为其居间性的特点,所以在当下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中更具争议性。但是,争议与分歧会通过协商,逐步转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共识,进而成为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知识系统。这里,我们选择‘‘协商的”或“妥协的”(negotiated)概念来描述人文的约定性。这一概念揭示了不同力量或话语之间的错综纠结的复杂状况,揭橥了学术领域中诸多力量达成的合力状态。在艺术理论场域中,任何一种理论取向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的状态一定是各种取向或力量的妥协,一种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状态。于是,张力在这个合力状态中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共识也就相对形成了。当然,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并不是全体一致同意,而是某种相对的、协商性的认可。在—个学术共同体内,完全一致是危险的,它往往是集权或文化专制的产物。
三、艺术理论:各门艺术的差异
艺术理论是关于各门艺术的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各门艺术的情况却又有所不同,_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是,有的艺术在一般性或总体性的艺术理论中被讨论得比较多,有的艺术则相对较少,甚至基本不涉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不同的艺术还有高低贵贱之分?
无论古今,亦无论中外,艺术理论好像总是比较青睐文学和造型艺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究。第一,文学和艺术的关系。严格说来,文学应该属于艺术的一个分支,18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巴托在为‘‘美的艺术”(finearts)命名时,就指出了五种“美的艺术”一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和舞蹈(Batteux102-05)。照理说,五门艺术本不分仲伯、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文学往往最具影响力或鹤立鸡群。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更是如此,文学一家独大,艺术则包含了文学以外的所有门类‘文学艺术”这一通常的表述足以证明文学对应于其他所有艺术的总和,就像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平起平坐一样。由于文学的独特地位和学科的强势,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艺术学各学科一直屈从于文学学科,直到不久前才单立门户。
文学的强势不仅体现在其学科的覆盖上,同时还呈现为长久以来文学理论一直在独领。20世纪作为一个‘‘语言学范式”主导学术的世纪,文学理论对各门艺术理论甚至美学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各门艺术理论中都可见到语言学或符号学的影子。这种状况从理论上反过来加强了文学理论对艺术理论的影响。当下发展艺术理论,一方面应该把文学重新置于艺术的名下,使之回归艺术大家庭之一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艺术理论本身对文学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在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的关系上,从事艺术理论的学者比较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反过来,文学理论的学者则不大注意艺术理论的进展。这种不平衡关系需要得到改善,而艺术理论需要努力完善自身并对文学乃至文化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除了文学的独特地位之外,在其他各门艺术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古往今来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似乎对诗与画钟爱有加。假如说艺术是一个大家族,那么,在艺术理论家或美学家的眼中,常常是诗与画更容易入他们的法眼。在历史上卷帙浩繁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思考中,诗与画是一个永恒的比较主题,无论古今或中外。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诗画一律”论,或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说即如是;而西方艺术理论的经典之作莱辛的《拉奥孔》,就是比较分析诗画异同的。更有趣的一个情况是,古往今来很多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画家(中国诗人王维或英国诗人布莱克等),或者著名的诗人作家同时又是重要的造型艺术批评家(比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等)。但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的就比较少见了,而既是诗人又是舞蹈家或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其诗与画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有某种内在相通性或共同性,所以诗人兼画家也就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其二,较之于其他各门艺术,诗与画所以更招理论家甚至哲学家们喜爱,也许它们更趋近于艺术理论的一般问题或原理。
这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艺术理论在其知识建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对某些艺术门类更为倚重。虽说各门艺术同等重要,但在艺术理论的知识结构中,对各门艺术的分析和解释会有一些差别。有些艺术类型接近艺术对一般理论和原理的阐释,有些艺术则较为远离。各门艺术的差异不仅呈现为与艺术理论的一般问题或原理的远近距离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专门性(或技术性)的差异上。相对说来,诗与画比较接近曰常经验,研究者也比较容易进入,而音乐、舞蹈、建筑和戏剧则需要更多的专业训练。所以诗与画,或文学与美术,就会成为艺术理论家们所青睐的艺术门类,他们无需像音乐、舞蹈、戏剧等经过专门的训练方可发表言论。
这一现象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到验证。我们知道,在英语世界,各门艺术除了造型艺术或美术之外,任何一门艺术都是用其门类概念来称呼自己,比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摄影等,至多使用“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或“舞蹈艺术”等概念。但惟独造型艺术,特别是绘画和雕塑(还包括建筑等)就直接称呼自己为art。所以,艺术史(arthistory)或艺术理论(arttheory)往往和造型艺术紧紧地关联在一起。比如著名的《詹森艺术史》实际上是美术史或造型艺术史,文杜里的《艺术批评史》是美术批评史,而巴拉什的《艺术理论》煌煌三大卷,也多半是造型艺术理论史和美学史的结合。⑧这启发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何造型艺术敢于垄断art这个概念的所有权,而其他艺术则没有这样的野心?
可能的结论是造型艺术的理论阐释有较大的涵盖面,可以说明一般艺术理论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历史现象,出身于造型艺术和文学的理论家往往更关心一般性的艺术理论问题,甚至美学和哲学问题。相比之下,其他门类的理论家则往往埋头于自己的门类问题。所以历史地看,艺术理论历史建构的主力军也是与文学和造型艺术关系密切的理论家、批评家和美学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造型艺术对总体的艺术理论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