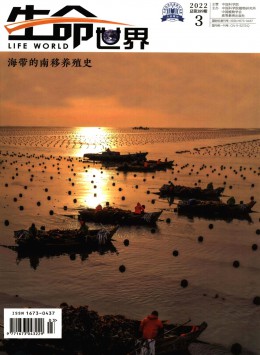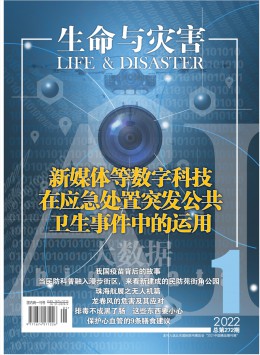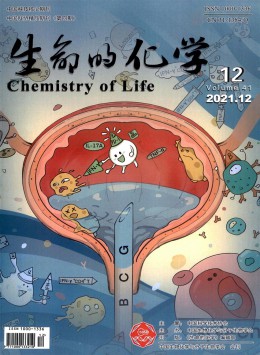生命存在的意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 生命思考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我们知道,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孔德)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发端,这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态度,也蕴含着科学主义思潮的走向。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受到人本主义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之后的科学哲学派别的批判。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同时指出科学也是尝试性的猜想和实验的反驳。因此可以看出,科学自身的基础和前提是可错的,因此科学主义如何永恒是一个问题。库恩的科学范式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发展历史模型的框架,强调文化心理因素与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理性没有秩序,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作为现代信仰。因此,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可以看出科学主义自身的问题,追求逻辑追求分析总有不可解决的方面。但是科学主义的探索对人类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唯科学主义。这值得注意和警惕。
西方现代哲学中,都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特别是以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为代表人物。海德格尔重点分析了特殊的存在,称为“此在”。将此在与时间结合为一进行分析,这样就会显示出人的本质价值地位尊严这些作为此在的意义。但是他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这样一来把人这样一种此在推向永恒,并且他有此在的死亡之意向。这都存在一些问题。萨特认为,人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自为的。人以外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这种存在是自在的。然而,存在主义确实表达了人的存在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生命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人本主义对人的生存来说,是有很多生命价值的。但是也要避免进入唯人本主义的境况之中,这样生命才有微调的空间。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力图为科学进行辩护,他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这样界定科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哲学要追问的是,关于“事实”的本质,科学家是怎样判断出来的?经验都是可靠的吗?即使获取了事实,那么科学知识是怎样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但是A.F.查尔默斯是这样界定科学家与哲学家各自的工作关系的:“科学家本人是最有能力从事科学的实践者,而且不需要哲学家的建议,但是,科学家并非特别擅长脱离他们的工作而对那种工作进行描述和表征。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科学家们通常是很出色的,但在阐明那种进步由什么构成方面,他们并不是特别出色。这就是科学家并不是特别善于进行有关科学的本质和地位的争论的原因。”这样为科学辩护,把科学奉为敬仰。这是值得反思的。
人类的生命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这并没有错。或许人类确实是这样一种存在,但是必须要警惕将一个学科作为信仰而凌驾于其他学科,这一定是不合理和不恰当的。如果一旦这种趋势上演,那么人类的生命长河一定是有问题的。人类的这种探索固然是好的,但是绝不能陷入一种独断论中,而否认其他一切。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兴起,我们更要值得注意和警惕。科学主义思潮决不能代替人本主义思潮,相反亦然。
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谈论的问题,而且也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演变而来的问题。不仅牵涉到横的因素,而且也关涉到纵的问题。从方方面面来看,生命所延伸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同样也是非常丰富的。生命不仅有着独特性,而且又有着圆融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生命思考,我们就会重新认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理解。
参考文献
[1] 林超然.现代科学哲学教程[M].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
[2]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叶秀山.哲学要义[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第2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今天是农历的十九,中午时分我和弟弟去看了卧床近一个月的外婆,可就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母亲打电话哭着说外婆不行了,,刹那间我懵了,此刻我才知道,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瞬间就会离你而去.
我和父亲立刻赶往外婆家,在车行驶的路上我的脑中一直是空白的,我始终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直到看到已经穿好寿衣躺在堂屋正中央的外婆遗体,她的表情很安详,好像睡着了一样,在她的嘴边放着一枚铜钱,镶着金边的帽子,灰色的围巾,蓝色的丝绵上衣,金黄色绣着龙凤的长裙,三寸金莲的小鞋,好像新娘出嫁一般,我抚摸着外婆的脸,泪水不自觉地从眼里滑落,心里无法抑制的压抑顷刻之间如洪水倾泻,号啕大哭起来.我已经不能再故作坚强了.
入殓那天,外婆家里似乎很热闹,很多的客人,外婆的儿女都戴着孝帽趴在外婆的棺木边哭泣,大姨的身体很不好,好像是在发抖,下午三点半,要封棺木了,我走过去,想再抚摸一下外婆的脸庞,那时她的脸冰冷的像那天的天气,可是她的表情还是那么的安详,母亲说人要走的时候好像都知道,会把身体内所有的垃圾都排出来,好像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因为外婆在饮食极少的情况下临死之前共排了三次大便,把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统统还给了这个世界)要封棺木了,我的心里一阵痛楚,这是最后一眸的永别,泪水在不自觉间挂满了整个脸庞.
第3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纵使有人逃避这个问题,渴望把自己变成绝对自利、专注于个人功名利禄的渺小生灵,也会在向着死流逝的时间面前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终究会发现无法逃避自私自利带来的失落感和空虚感。当一个世俗的自利欲望被满足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空虚,由此人陷入无休止的贪求之中,即使一时半刻不在外力的限制中遭遇挫折,也终将会被无魇的私欲折磨得精疲力竭。但意义的逼问是如此令人恐惧和焦虑,以至于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以各种方式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他感到死亡无可避免地临近之时,才意识到其一生的种种“追求”尽然是在努力搁置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已。
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教义带来了唤醒梦中人的呼声。“诸行无常”意味着自时间上观察,一切现象(有为法)皆在迁流变化之中刹那生灭,故无固定不变坏之物存在。佛教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所有存在者皆是由因缘(条件)和合而成,亦由因缘离散而灭,故此,从缘起法可推论出万物无常变化的法则。而由诸行无常,进而可推出无体或无我的法则。“法”,指事物、存在,通于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世间、出世间一切的总称。“我”指恒常不变的实体或主宰。佛教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假因缘和合而成,故而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此便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亦即所谓诸法无我。
不过,对于渴望逃避不存在的人而言,多少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意义似乎为人弥补甚至超越“存在的虚无化”结局提供了一种原发性的希望,使人隐约看到了生命在另一种层面上的延续甚至永恒。这是因为不论以何种存在方式生活,我们最终均能感受到,如果意义仅仅是就今生有限的自我而言,那面对着必然要终结的此生生命,“为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所承载的全部“意义”都将显得荒诞而空虚――不论当初付出多大的努力,取得多大的收获和喜悦。因此对人而言,比生命更长久的意义是对于“他者”而言的意义,“为了他者”使人突破了所谓的自我那荒诞、渺小的限度,使生命在存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因缘和合之假我的存在之中延续了下来。我们可以在古往今来无数令人动容的故事中发现,如果意义突破了自我那可怜的限度――当它被认为指向无限的终极存在者(神),或者指向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幸福时――其追求者甚至会为之牺牲生命却依旧感到幸福而无憾。
大乘佛教的出现,为不少信仰者面对存在之意义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大乘佛教的理想人格是菩萨。菩萨行意味着不满足于一己的离苦得乐,灰身灭智,它照耀到了人性之中一个被隐藏得极深的痛苦――一种对存在之意义的渴望而导致的痛苦。众所周知,大乘佛教倡导的菩萨精神之要义在于普渡众生,菩萨不住无为,不入涅,生生死死在六道轮回中去拯救无量的众生。菩萨之所以如此,并非不明世间之痛苦,不愿出离世间证入究竟佛果,其所作所为是悲悯无数尚且沉沦于世间的众生――虽处于火宅般的三界中却依旧浑浑噩噩,造业受苦,流转生死。
然而按佛教的说法,世间的众生似乎是度不尽的。佛教的世间论认为,三千大千世界本已是相当辽阔,但其数量是无限的,故而常说“十方微尘世界”、“十方恒河沙数世界”,因此众生的数量也应当是无限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菩萨行者的悲剧――为了那“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誓言,他们成为了“大悲阐提”――出于大悲之心而渴望普渡有情,在生死苦海中为了无量众生行无尽布施,使自己的超越生死轮回之解脱显得遥不可及。然而,正如一切伟大的悲剧所展示的那样,在这样一种抗拒命运的命运之中,人的存在不仅没有因为其无法改变之外部条件的禁锢而被遮蔽,恰恰相反,强大的外力和苦难的不可抗拒性非但没有使人下降为因果链条中完全受支配的物性的一环,反而使人之存在的尊严和崇高通过他在经验世界中的渺小和脆弱以及其受役的一面而凸现出来。这种凸现不是理性推理的产物,但却能从自己的生命之中去感受它。
反思此生的点点滴滴,利己和利他的往事为我们昭示了不同的意义。世俗利己的意义――即使有的话,在死亡面前便显得脆弱,而利他的意义却并未因此而逝去。因为,我们只能体验自己独自面对的死亡所带来的焦虑与空虚,却无法分享死亡对他人昭告,当我们将自己的意义分延至他人的福祉上时,我们不会像面对自己的死亡那样真切地感受他人的死对其所承载的意义的审判,当我们寻求人生意义所向之“他人”趋于无限时,意义便终极突破了有限性的牢笼,在救渡一切生命的宏业中延续下来。
第4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生命教育是指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欣赏生命,提高生存技能和生命质量的一种教育活动。近年来,大学生轻生、自伤事件时有发生,生命教育由此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中方兴未艾的话题。
当今社会受到急功近利的文化、应试教育的体制及升学主义的影响,学校、社会重视的是知识技能的传授与掌握,而轻视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与引导,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生命教育的缺失使许多学生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存在种种片面、零乱甚至矛盾错误的认识。高职学生是被普通高校淘汰的学生,这些学生学习动机不足,学习成绩不佳。当成绩成为评价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时,对于学业成绩不理想、不善于知识学习的高职生而言,学业的失败、人性的压抑使其看不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觉得生活是无趣的,生命是受压抑的。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高职生摆脱了高考的压力,开始自觉地思考人生,感受生命存在之价值。我是谁?我的存在有何价值?我努力奋斗为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成为他们经常拷问自己的话题。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部分高职生迷茫、困惑、挣扎、颓废,漠视生命乃至践踏生命。因此,对高职生尤其需要进行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人的一生,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笔者拟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探讨高职院校的生命教育。
高职院校生命教育的形式——体验式教学
所谓体验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积极创设各种情境,包括阅读、角色扮演、互动活动等多种形式,调动学生想象、移情、感悟等多种心理活动,引导学生对教育情境进行体验,通过师生间的分享与讨论,产生碰撞与共鸣,使学生学会转化、战胜消极的情绪体验和错误认知,发展、享受和利用积极的情感与正确的认知,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生命的意义因人因时而异,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学生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生活于宇宙之中、世界之上,要靠自己的实践发现生命之真,领悟生命之善,体验生命之美,不能靠他人的说教。学生的生命及其体验的生成基于学生生命活动、生命实践的永无止境的展开。只有通过学生切身体验获得的东西,才能入脑入心,珍藏久远。体验式教学以人的生命体验与发展为依归,尊重生命、关怀生命、拓展生命、提升生命,蕴含着高度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与传统的说教相比,体验式教学通过“创设情境——活动体验——互动分享——觉察反思——整合运用”的技术路线,由教师创设各种教学情境,学生通过对情境的亲历,产生内心的体验与感悟,通过师生间的分享和讨论,产生思想的碰撞,从而达到转变认知、改变行为的目的,其鲜明的亲历性和自主性、独特的个体性、丰富的情感性,使体验更容易深入学生的心灵。这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学生自我探索、自我选择、自我引导、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体验式教学是生命教育的必然选择。
高职院校生命教育的内容
人生包括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两个层次,因此,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生命教育应包括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两大层次。
(一)生存教育
生命存在是生命活动的物质载体,生命活动创造价值的前提是生命的存在。在传统教育中,往往只强调创造人生价值而忽视生命存在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加之当前的应试教育使学生陷入繁重的学业之中,根本无暇领悟生命之重、欣赏生命之美,因而漠视生命,对生命缺乏敬畏之情,进一步导致践踏生命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生命教育首先应是生存教育。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笔者认为主要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育。
生命意识教育生命意识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基础。生命意识教育的实质是热爱生命、敬畏生命。具体包括两个层面:(1)主体生命意识,即热爱、珍惜自己的生命;(2)客体生命意识,即敬畏、尊重他人乃至世间一切生命体。应通过生命意识教育使学生明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宝贵的,要热爱生命;生命来之不易,生命的诞生是个奇迹,要敬畏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世间一切生命体是共存的,要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珍爱他人乃至世间一切生命体。
死亡教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死亡”的话题一直是被避讳的,这种回避态度使得学生对死普遍缺乏科学认识,充满恐惧感或神秘感。有的学生将死视为解脱,碰到一点挫折就轻易选择轻生;有的学生则因为害怕死亡而导致各种神经症。因此,对高职生开展死亡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很有必要。死亡教育包括三个层次:(1)了解死亡及其意义,既明白死亡之重,又能正确面对死亡,懂得死是生活的终止,但生命可以永存,消除恐惧、焦虑等消极心理;(2)当面对重要他人死亡时要有心理上的准备;(3)向死而生,要为提高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质量而努力。
第5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生命问题;理性;绵延;此在;在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8-0000-00
对于人的生命形式,生物学可以给出一个令多数人信服的答案,首先人作为科学定义上的生物,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活动历程,从生长繁殖、新陈代谢,到遗传、进化,但作为对于生命现象的客观描述,显然不能穷尽生命本身。人作为有智慧的生物,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且能够将其自身拥有自在的生命上升为自觉生命的能力。那么这种智慧到底为何?这种能力又为何?
一、理性认识对于生命的局限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将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近代形而上学通过强调人的主体性来确立生命的价值,从笛卡尔开始,“我思故我在”,人的主体性确立,个人的理性成为通往一切的核心。康德将人的理性发挥到最大,康德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人的规定性就在于理性,通过理性去建立关系,从而得到有规律的关于世界的体系,“人为自然立法”。而在康德眼中的理性并不是个人的智慧,它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共同性,它源于个人又超越个人。从认识论上,康德看到了理性的问题,他认为理性作为认识的形式而无法作为形式去被认识。理性在对外的认识活动中可以发挥作用,认识活动必须在对象中进行,即产生主客体之间的分离,作为纯粹的形式的理性即先验的逻辑无法被认识,于是康德将物自体设立为其依据。那么,在对于生命问题的理性认识活动当中,“我”作为主体对于“我”的把握只能处于对象化的认识当中,“我”对“我”产生了一种空间性的分割,而生命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连接,是一体的不可割裂的,对于生命问题的追问不可能脱离“我”而存在,所以由理性认识活动出发得到的始终是关于生命的“假象”,是褫夺式的变式。由此得到的认识是我们离生命越来越远,却将这种认识无限扩大化,从而忽略了最为本质的关乎自身的生命问题。
二、生命问题的重拾与修正
亨利・柏格森为生命问题打开了一个视角,首先他指出:“我们的思维,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并不能阐释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阐明进化运动的深刻意义”, 而就生命问题而言,“我们思维的范畴,如统一性,多样性,机械的因果性,智慧的目的性等等,都不能准确地符合有生命的东西。”他否定了理性的万能,而并不是否定理性的全部意义,“认识理论和生命理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作为不间断的流动状态,柏格森将这种状态定义为“绵延”,“绵延是入侵将来和在前进中扩展的过去的持续推进”。柏格森提出了真正的时间与科学的时间的区别,真正的时间即为绵延,它是不间断的,科学的时间之所以会被分解是因为将时间空间化了,并不是流动状态而是出于静止状态。柏格森认为对真正时间即绵延的体验式把握是生命的独有形式,从中能够把握到生命的整体性。对于把握的方式,柏格森强调直觉,他认为直觉与绵延是不可分的,只有直觉才能体验到绵延的连续性,而运用理性得到的只能是分割的空间化的生命,无法把握生命的整体。柏格森无疑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生命的单一化解释,他将生命问题重新拉回生命本身,强调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对自身的创造,强调对自身生命的完整式体验而不是节点上的把握。海德格尔对生命哲学提出批判,他指出生命哲学的倾向领会得正确,“但生命本身却没有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海德格尔在谈论此在的问题的时候显然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首先海德格尔对于存在问题上认为“存在之为存在”即“去存在”,强调存在者在其存在的过程中获得其存在论上的价值和意义。在对于此在的分析中,“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其存在中这样那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海德格尔将“人”定义为存在,一方面避免了“人是理性动物”的成见即“其意义等于其他受造物的现成存在”,另一方面也将高高在上的人拉回了原地,我与世界没有二分,只有此在“在世”的状态。海德格尔以“在世”作为此在的基本建构,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平均日常状态为操劳,海德格尔陈述了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方式,从寻视,到触目,到指引,最后通过因缘来揭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并没有建立抽象的生命观念,而是试图透过复杂的的生命活动现象寻求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存在有着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之分”,虽然非本真状态的沉沦占据了生命的大多部分,但是正因如此本真状态才具有了价值和意义。
三、生命问题的缺失
当今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愈发地高,外界信息涵盖了个人对世界的全部认识,并且在不断地侵蚀着人对于自身生命价值的把握。众所周知,如今电子产品的功能愈发全面与方便,也催生出快餐文化与众多所谓的“智者”,人们试图通过这种便捷而又易懂的方式去理解生命的全貌,并试图从中为自己得到拯救寻求途径。然而,由于过分膨胀的理性培育出了残破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无限扩大化,而对于超越性的追求则满足于外界给予的答案,并不去探寻自身是否真正需要。这种始于答案又止于答案的行为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惊叹,并不会产生对于生命本身的深思,更很难对自身产生预期的功效。忽视对自身生命的整体把握,即从时间上去体验生命,将生命作为内在的,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去把握,在毫无精神约束的中国,其后果是可怕的。一方面会造成自我缺失带来的颓废感,缺乏对自身的支撑以及对“安身立命之本”求之不得的苦痛,人找寻不到自己的本真状态与面貌。另一方面,将生命的节点绝对化,刻意强调一方面的绝对性,而将生命无限化,幻象化,生命不再具有实存性而变成空泛的概念,没有具体体验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对生命问题的重提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 唐桂丽. “此在”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
[2] 刘敬鲁.论海德格尔对现代早期人学的扬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3] 谭裘麒.唯有时间(绵延) 真实――柏格森自我意识本体论初探[J].哲学研究,1998(5).
[4] 牟方磊.情本体与此在存在――论《历史本体论》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与改造[J].中国文学研究,2013(1).
第6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前一段时间读了本《教师人文读本》,很多的内容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与思考,其中,我最爱读的就是《读本》中——我为什么而活着这一章节.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我为什么而活着!"而他们也大都会用自己的一生去寻求这样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满足于上帝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拥有生命这样一种单纯的答案.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曾经问过大人,他们总是说:"活着呀,就是要快快乐乐的感受生命啊!"曾经品读他人,我的脑海中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活着的意义与目的,可是,最终我也没有弄明白"我为什么而活着!"
在《读本》中,收录了沈从文,史怀哲,罗素等一些诗人,作家,博士等名家的作品,初读此章节的时候,我还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收录在"我为什么而活着"这个章节中,不过由于自己也曾经苦苦思索过,不免反复咀嚼,体味其中真味.从沈从文给时间"画出的肖像"到史怀哲放弃已有的成就,甘愿去非洲丛林当一名乡村医生,其中的种种让我看到一个个在生命的长河中努力寻求生命真谛的身影.他们可以冲破种种既定的条款,做别人认为"特立独行"的事,尽管在与其他人比较时,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可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执着,努力的去冲破着什么.他们可以改变上天赋予的种种不公,用顽强的意志把生命诠释,尽管目不能视,但是却并不能阻碍他们想象,当我们的想象插上翅膀,即便身体不允许我们跑,跳,走,越,但谁又能阻挡想飞的心呢他们可以鄙视已经唾手可得的成就,只为了"敬畏生命"就可以把滚滚红尘抛于脑后,把功成名就踩于足下,用整个人生将"生命的意义"诠释得透彻.如果说,初读他们的时候是感动,那么在沉下心来仔细品味后,则是深深的震撼!自然界,生命的存在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对于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生命却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从昆虫界的短短几分钟的生命到其他几百年的生命,时间虽各有不同,存在却是相同的.也许有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繁衍下一代,使命完成便悄然而逝了;也许有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更长久的生存下去,所以捕杀,奔跑;也许有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维系整个生命系统的正常循环……
读史以励其志,也许,在这短短的篇章中,在这短短的思考中我并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想尽量把事做得最好,尽量让人生过得充实,也许当我白发髻首的时候,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可以得到"我为什么而活着"的答案吧
第7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摘要为了能透彻地阐释诗作的隐喻意义,本文以存在主义为哲学理论依据,对美国现代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些诗作加以评论,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研究评论过程,向读者展现诗人在其作品中对人生的哲学性思考、对人的存在这一特殊形式及其意义的理解与诠释。
关键词:存在主义 偶然性 自我 选择 责任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千百年来,受强烈欲望的驱使,人类努力地寻找,试图理解、诠释其赖以存在的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的运转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秩序,以期最终能够揭示所有相互关联的事物存在于大地上的意义所在。于是,作为具有创造力的物种,人类凭借各个领域的知识架构,通过复杂的洞察事物的方式界定时刻发生着的意义状态,包括生命现象、存在状态、“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及至具有哲学审美价值的“存在的意义”。
在这个不断探寻的过程中,人类创造出诗歌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情感、传递诸如其人生经验等信息。事实上,作为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模式,诗歌并不仅仅只是人们用以向其他人表情达意的意义形式,与此同时或者更多的是通过诗歌走进自己的内在,与自己交谈,让那个原始的、最真实的自己显现出来,在种种情绪中体验一己之存在,继而理解其自身价值。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大部分诗作向读者展现了人存在于宇宙间的偶然性、不确定性;进入“自我”的思索;以及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进行积极的抗争,为自己争得生命的意义,创造自己的价值。
一 存在的偶然性、不确定性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包括人的存在在内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偶然的,是偶然发生的、非决定的,所以存在也是不确定的。弗罗斯特的一首名为《熄灭吧,熄灭――》(“Out, Out――”)的诗作可作为强有力的例证来探讨个人之存在的不定、无常和空虚。
诗的开头部分就定下了不和谐的基调:一切似乎都是那么静谧,尤其是远处夕阳下的“五座绵延的山峰”,更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田园风光的图景;然而,随着具拟声意义的词汇“snarled and rattled”的侵入,这种视觉意象即刻被来自听觉的尖利刺耳的声音所破坏,而诗也随即转入诗人情感领域的最深处。在紧接着的第9-18诗行中,弗罗斯特详细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一切平平安安,一天活就要干完。/他们要早点说一天活结束就好了,/……此时那电锯,/……/突然跳向孩子的手――似乎是跳向――/但想必是他伸出了手。可不管怎样,/电锯和手没避免相遇。那只手哟!……”
紧迫感无疑落在此处的感叹号上,那一天很平静,终于到男孩十分看重的休息时间了,也许过于兴奋,也许转身过快,一刹那间他的一只手被锯断了。“可不管怎样”(However it was),这种弗罗斯特式的怪诞幽默恰好与萨特提出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偶然的、无目的的、荒诞的”这一命题相吻合。没有人预料到惨剧的发生,没有人预先规定就在这个时刻出现这一幕,更没有人说得清事情发生的原委,没有理由,无论怎样,在偶然的瞬间,锯与手必然地“相遇”!
随后此诗的叙述相对简洁,流畅地转向男孩的死亡。医生被请来了,但却于事无补。一切都难以预料,令人难以相信(No one believed),随着逐渐变弱的脉搏,男孩的生命就这样被毁掉了(spoiled),生命之火那么急促地熄灭了(out),死亡成为这一偶然事件的产物,而在诗的末尾那些转身去忙着自己事情的人们则进一步渲染了男孩死亡的悲剧性,加强了这一事件的“无意义和随意性”。
诗中近乎口语化的叙述非常流畅,除了两处感叹(“那只手哟!”和“微弱――更弱――消失!”),整首诗的语气似乎显得平缓,然而,诗的标题所内含的典故却正符合弗罗斯特所提出的“巧妙的隐喻和高雅的隐喻,适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深刻的思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麦克白》(Macbeth)中麦克白的经典独白将生命的短暂和无意义揭示得淋漓尽致:“熄灭吧!熄灭吧!转瞬即逝的烛火!(Out,out brief candle!)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路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述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诗中男孩的生命如此脆弱,脆弱得不堪一击;他的人生如此短暂,才刚刚“登场,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甚至还没能来得及留下“影子”。
二 进入“自我”
在阐述他的哲学思想时,海德格尔把“自我”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本,并对此提出了“亲在”的概念,即人的亲自存在,也就是“自我”的“存在”。他认为“亲在”是对一切不是“亲在”的存在的领会,通过领悟“亲在”,人才可以把握整个存在的意义,进而认识一切事物;可以说“亲在”是领悟存在的最好途径,并可能也是唯一的途径。关于此,萨特也提出存在是“人的实在”,即“自我”、“自我意识”,并且用“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两个概念来阐明人的存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弗罗斯特的诗作向读者展现的外部世界是偶然的、不定的、无常的,那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又如何使自己暂时远离这种混乱呢?且看他的诗作《进入自我》(Into My Own)中的“我”怎样努力通过涉入自己的内在来体验其存在的真实:
“我的愿望之一是那些黑暗之树,/并不如人们所想是纯粹的忧郁的面具,/……/我不会被拒绝,终有一天/我将悄悄进入它们的辽阔。”
第一诗行中的“那些黑暗之树”(those dark trees)令人费解,对这个意象的理解把握成为打开整首诗大门的钥匙。结合诗的标题,读者方能发现它的隐喻意义,况且“自我”是难以被看到或触摸到的,它完全利用它所创造、构筑的隐喻来表达,因为它隐匿在最深处,所以此处的“黑暗之树”自然而然地所指内在的那个“自我”。它将自己藏于最深最暗之处,甚至带着“忧郁的面具”,使人难以涉入。尼采认为“人类真正的动力在于黑暗、神秘的本能世界”,即使不易达到,诗中的“我”仍然坚持认为“我不会被拒绝”,而且一旦进入,“我”将感受到的是一片“辽阔”。也许生活总给“我”夹缝之感,经过那广袤深邃且无他人之境的洗礼,“我”似乎感悟到自己真实的存在:“我思,故我在”。因此,待到“我”再一次“返回”,开始面对外部世界时,“我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我变得更加确信”,即“我”更确定个人的是非观、善恶评判由个人断定。
在另一首名为《现在,关上窗户》(Now Close the Windows)的短诗中,叙述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己营造宁静:
“现在关闭窗户,让原野全都安静下来:/若是必须,就让树木静静摇荡;/现在没有鸟儿唱歌,如果有,/就让我错过吧。”
“我”在自我之真与外界之非真的冲突中主观地选择了将自己同其他一切隔开,给自己一个思索的空间,在沉静之中等待沼泽地再一次出现生命的迹象和第一只鸟飞过;不去听风声,但要远远地洞察“被风搅动的一切”。于是这里的相悖之处点名隐意:“我”虽然使自己远离外界,可同时又深处其中;当风吹过窗外的树木,给沼泽地带来生命,它更在“我”的心底激起波澜,尽管“我”外在的存在状态是与窗外分隔开的。
同样,在《梦中之痛》(A Dream Pang)里,叙述者“隐退至森林里”,让自己的歌声“被那飘扬的落叶淹没”,与它融为一体,“我”隐蔽得如此深远,以至于站在森林边缘的其他人认为“我”已经“走得太远”。针对这样的质疑,在第二诗节里,“我”为自己做出了解释:“不远,而且很近”;最重要的是,“我在此伫立,看到了全部”。这里的“it”一词实际上发挥了诗眼的作用,“我”进入森林所要寻找的正是“it”所指之物,到诗的最后一行它“苏醒了”,“我”不但看到了它,而且感觉到它为“我”停留,所以,“我”不孤独。“我”进入内心深处(forest),找到了“自我”(the wood, it),并且感受到“甜蜜的疼痛”(the sweet pang)。
三 积极的接受
存在主义哲学思潮被认为是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笔者认为它之所以毫不留情地揭示现代社会中渺小的个人之存在状态,强调个人为自己做出选择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为了阐明个人存在于世的意义,激励人们积极地面对并处理好自身与外界的矛盾冲突,创造自身的价值。作为诗人,弗罗斯特在他看似阴郁的诗歌语言背后,其实在向读者展示着存在之美。
人生充满着无数的选择,萨特的哲学命题之一即专论人的一个根本问题――选择,并提出具有主观意识的人拥有积极的“自行选择的权利与自由”,即使不选择也是“选择不选择的一种选择”。
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中,弗罗斯特一如既往地将隐喻寓于诗中,他有意不直言两条路所代表的意义,对选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任何暗示,只是叙说选择本身。全诗一共四节,前两节分别讲述“我”面临选择时“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的遗憾,以及经过复杂的心理过程之后“我”选择了“很少留下旅人足迹”的“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的“另外一条路”。到第三节,“我”感叹选择的存在使人生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且两者并存;“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选择使自己失去了可能性而获得了现实性。但是无论怎样期望能一睹“另外一条路”的美丽,在诗的最后一行“我”都坦然接受了现实,并向读者阐明了选择的本质:人的选择行为会影响、改变,最终“决定一生的道路”。
对于存在主义所言:“人是痛苦的”,萨特有这样的解释:
“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做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
含义隽永的《雪夜林边》非常明确地提到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羡,/但我还要守一些诺言,”无论怎样陶醉于这“林中积雪的美景”,尽管贪恋这寂静无声的平静,“我”仍然不敢卸掉自己肩头的担子――责任。而漫漫人生路上曾许下的诺言还等着“我”去实现,故而最后两诗行重复强调“路迢途远岂敢酣眠”,“我”必须承载生命赋予“我”的责任继续赶路,别无选择,如同守夜的人不能安眠。
《白桦树》(Birches)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绘:
“我真想暂时离开人世一会儿,/然后再回来,重新干它一番。可是,/别来个命运之神,故意曲解我,/只成全我愿望的一半,把我卷了走,/一去不返。你要爱,就扔不开人世。/我想不出还有哪儿是更好的去处。/我真想去爬白桦树,/……/爬向那天心,/……/把我放下来。去去又回来,那该有多好。”
显而易见的,“我”因为“厌倦于操心世事”,想躲避世俗的烦恼,可是为什么又对人世那么恋恋不舍,而且还想重新开始大干一场?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这段话恐怕是最好的回答: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四 结语
简而言之,生活是复杂的,生命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弗罗斯特诗作中所看到的晦暗、阴郁的一面,也不似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在他们的哲学论断中所讲的那么令人难以捉摸,而是寓于那些朴实的诗句中的深刻的思考,是存在主义思潮实际上要强调的对人存在于世这一事实应采取的积极态度。
注:本文系校青年科技基金,项目名称:存在的意义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研究,项目编号:QN0946;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名称:医学英语科研论文写作中的母语迁移现象研究,项目编号:09JK133。
参考文献:
[1] Brooks,Cleanth.And Warren,Robert Penn.Understanding Poetry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2]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胡开杰:《诗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尹星凡、詹世友、黄承烈等:《现代西方人文哲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第8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此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解释学循环:一方面,是生产(即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成为一种类存在;但另一方面,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生产者,又恰好是因为他具备类属能力。这一循环既不是自相矛盾,也不是理论缺陷,相反,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思考里的一个关键时刻。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实践与“类生活”( Gattungsleben)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写道“劳动的客体是类生活的客体化”,而“异化的劳动,因其剥夺了人类生产的客体,也就夺走了人的类生活,夺走了其实际的类属客体性(Gattungsgegenst?ndlichkeit)”。
因此,实践与类生活在同一个循环里彼此从属,互为起源和基础。正因为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彻彻底底地体验了这一循环,他才能跟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anschauende Materialismus)保持距离,把“感性”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也就是说,这一循环思想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源性体验。那么,类(Gattung)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是一种“类存在”(Gattungswesen)究竟意味着什么?
Gattung通常被翻译成“类”或“种”,两个词都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但Gattung的意思绝不仅仅是“自然物种”:马克思称正是“类存在”这一特质将人跟动物区分开,并把“类存在”直接跟实践,跟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非动物的生命活动)联系到一起。如果只有人类才是“类存在”,只有人类才具备类属能力,那么“类”这个词肯定具有比一般自然科学用语更深层的含义。如果不考虑它在西方哲学思想内部的位置和作用,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其独特的回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几乎用了一整卷的篇幅来解释几个名词。他把类(γ?νο?)定义为“连续的生成”(γ?νεσι?συνεχ??)。因此――他补充道――“只要人类存在”的意思就是“只要人类还在连续地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一般被翻译为“连续的生成”(continuous generation),但想让这一翻译成立,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生成”理解为“诞生”(origin),而且“连续”也不只是“紧凑、无间断”之意,而应根据其词源,将其解释为“维持统一的(συν?χει)”,“并立・ 结合的(con-tinens)”。γ?νεσι? συνεχ??的意思就是:在存在层面上维持统一性的诞生。“类”则是从属其中的个体(无论从“维持保有统一性”的能动意义上说,还是从“持续保有自身之统一性”的反身意义上讲)诞生的根源性大陆(con-tinente originale)。
因此,人具备类属能力,是一种“类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人而言,存在一种根源性的大陆,一条基本原则。在这条原则之下,作为个体的人不会觉得其他个体与自身是疏离的,相反,“类”在每个个体身上都直接并必然地存在,在此意义上,该原则使人成为“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可以说“人是一种类存在……因为他的行动对待现存的、活生生的类就像对待自身一样”,而“说人与其类属存在之间产生了疏离,也就等于说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产生了疏离或每个人与人类存在本身产生了疏离。”
从上文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从自然物种的角度,即与个体差异无直接关系的共同自然特征角度来理解“类”(genus)这个词的。为类存在这一人类特性奠定基础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内涵,而是实践,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更多是从“连续的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所具备的能动意义上,即从诞生(γ?νεσι?)的根本性原理上来理解“类”的概念。该原理在所有个体和行为中建立起人类存在的基础,从而使人成为彼此间保持统合的普遍性存在。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为什么启用“类”这个词以及具备类属能力这一对人类特性的定义为何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了极为关键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类”的定义。
当黑格尔谈及“类”在有机自然中的价值及其与具体个体性之间的关系时,他说道单个的生命体并不同时也是具有一般性的个体:有机生命的普遍性是纯粹偶然的。他还用了一段演绎推论作比:“两个极端,一边是一般性或作为类属的普遍生命,而……另一边则是作为一般性个体的普遍生命,”但作为中间项的具体的个体只要未能将上述两个极端包含在自身当中,就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斡旋调解,从而也就称不上真正的中间项。因此,黑格尔写道,与人类意识不同,“有机自然没有历史;有机自然是从普遍生命直接落入个别存在。”
统合黑格尔哲学系统的根源性力量解体后,“类属”与“个体”、“人的概念”与“人的肉身”之间和解问题就成为年轻的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左派思考的核心。他们之所以会对个体与类属的调解特别关心,是因为在一个具体的基础平台上重构人的普遍性也就等于同时解决了精神与自然、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之间的统一问题。
莫泽斯・ 赫斯(Moses Hess)1845年发表的一份小册子在德国社会主义圈子里引起了很大反响。莫泽斯在文中描述了“最近的哲学家”(施蒂纳[Max Stirner]和鲍威尔[Bruno Bauer])在调解黑格尔演绎推论里对立两项上所做的努力(和失败)。引文如下:
“没有人会主张熟知太阳系的天文学家跟太阳系是一回事。然而,按照最近德国哲学家们的说法,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自然和历史的知识,他就应该是‘类’(Gattung),是‘全体’。布希的杂志上写着,每个人都是国家,是全人类。‘每个人都是类,是整体,是全人类,是一切。’哲学家尤利乌斯最近这样写道。‘正如个体是自然整体一样,他也是类属全体。’施蒂纳如是说。”
“自从基督教存在以来,人们就一直试图消除父亲与儿子、神与人、‘人的概念’与‘人的肉身’之间的差别。但正如新教并未能通过打压可见的教会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最近的哲学家尽管消灭了不可见的教会,却反过来把‘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和‘类存在’推上了天堂的位置。”1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第六条里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正是他没能成功地调解感性个体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将存在单纯地理解为“类”(加了引号的Gattung),即“自然地连接起多个个体的沉默的内在普遍性(als innere, stumme, die vielen Individuen natürlich verbindende Allgemeinheit)”。对于马克思而言,作为能动的根本原理,即在生成(γ?νεσι?)意义上(而非作为不活动的物质普遍性)构成人类类属的中间项,是实践,是具有生产性的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构成了人的类属。也就是说,在实践中进行的生产同时也是人的“自我生产”。换言之,正是这种永远活动并在场的生成(γ?νεσι?)行为在类属中构成并包含了人类,同时建立起了人与自然,以及作为自然存在的人(man as natural being)与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的人(man as human natural being)之间统一的基础。
既然生成行为本身是人类的本质性起源,那么在其生产行为中的人类就突然进入了一个用任何自然科学年表都无法进入的维度。同时从神(最初的造物主)和自然(人与动物一样同属其中,却完全独立于人类存在的一切)手里解放出来的人如今在生产行为当中,将其自身树立成了人的起源与本质。2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生成行为也是历史的起源和基础。此处的历史是指人类本质(对于人类而言)成为自然以及自然成为人类的过程。这样一来,历史,作为人的类属和自我生产,便废止了“人类历史以前的自然,除了最近才刚刚成形的澳大利亚环礁以外,自然已经不复存在,”而且通过强调与自然的差异,历史将其自身定义为了“真正的人类自然史”。又因为历史与社会是同义词,马克思便可以做如下论断:所谓社会(其生成行为是实践),就是“人与自然本质上统一的实现,是自然真正的复活,是人类达成的自然主义以及自然达成的人道主义。”也正因为马克思是从这种根源性的原初层面上考察生产,并将生产的异化体验为人类历史上的首要事件,他对实践的定义才能到达人类命运的某个本质性的地平线(即人类存在在大地上的位置乃是生产性质的)。然而,尽管马克思把实践放在了人的根源性维度上,但他对生产本质的思考并未超出现代形而上学的覆盖范围。如果我们问他是什么赋予实践和人类生产以类属能力,使其能够成为人的根源性大陆,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特征使实践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就会让我们回到有关意志的形而上学。该形而上学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praxis)的定义,即:意志(?ρεξι?)与实践理性(νο?? πρακτικ??)。
马克思把实践跟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相比较后得出的定义是:“人将其生命活动本身作为其自身意志和意识的客体”,同时“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的类属特征。”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是一种派生特征(“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产物),而意志的根源性本质却在于作为自然存在、作为生命体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被赋予了逻各斯(λ?γο?)的理性动物(ζ?ον λ?γον?χων)。这个定义中必然包含着对生命体(ζ?ον)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对生命体(即有生命的人)本质特征的定义是意志,其中包含三层意思:欲求、欲望和意念。同样,马克思把人定义为“人的自然存在(human natural being)”也暗示着类似的解释,即:作为自然存在,作为生命体的人。
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其基本特征是冲动(T r i e b)和激情(Leidenschaft)。“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人被部分赋予了自然力(natürliche Kr?fien)和生命力(Lebenskr?ften),也就是说,人是活动的(t?tiges)自然存在;而这些力量在他身上以性情和能力,以各种冲动(Triebe)的形态存在。”;“因此,作为感性客体存在的人是被动的(leidendes),又因为他感受到了这种痛苦(Leiden),他也是充满激情的(leidenschaftliches)存在。激情,是积极指向自身客体的人类最为本质性的力量。”
实践的意识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退居到派生特征的次要地位,被理解为实践意识或与周围感性环境的直接关系。这时,被定义为冲动和激情的意志就成为实践唯一的本源性特征。人类的生产活动说到底就是生命力,是冲动、剧烈的张力和激情。如此一来,实践的本质,作为人性和历史存在的人的类属特征就退回到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这一自然科学式的内涵当中。有生命的“人”,进行生产活动的生命体,其根源性本质就是意志。人类生产就是实践。“人普遍地生产。”3
注释:
1. 莫泽斯・赫斯,《最后的哲学家》(达姆施塔特:Leste,1845),pp. 1 2。
第9篇:生命存在的意义范文
时间代表着金钱,也代表着价值,所以,人们珍惜时间,更珍惜着这代表价值和她的时间内涵。
一个人如果对追求没有价值,其生命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时间也如过客,没了留恋,更没了价值的存在。奉献生命,留住时间,就是奉献生命产出的价值,时间对生命才显得了重要,生命就有了存在着的意义和延伸。感谢××的每个员工,在匆忙的时间里,为××和自己生命的意义创造着价值和奉献。
企业是个生命体,企业的生存同样来自于对时间和社会所做出的价值和奉献。
企业最基本的价值在于对市场价值而满足于消费者,如果一个企业不能提供消费价值和社会价值,她也失去了存在着的意义。企业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失去价值或不能再创造社会价值,价值链形成本身就是企业品牌的延伸,并构成了企业的核心,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她、呵护她。
××是个大家庭,我们的兄弟姐妹很多很多,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并肩共同创造着和谐的情感交汇,共同演奏着“明天会更好”的大合唱。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