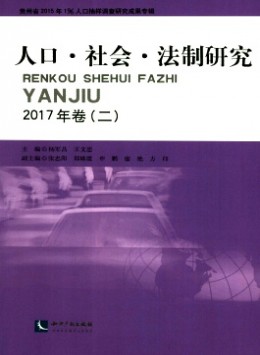流动人口的含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流动人口的含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该书从政治排斥的视角出发,对流动人口的政治处境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首先,对政治排斥的概念、含义和类型进行探讨,构建了一种政治排斥理论的分析框架;接着,对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城市政治系统确实存在对流动人口政治排斥问题的观点;然后,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群体自身因素等几个层面分析了流动人口中政治排斥问题产生的深刻原因,并从政治风险的角度揭示了流动人口中政治排斥问题的负面影响;最后,从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权利、能力和条件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性建议。我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拓展了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政治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他们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明显改善,特别是其政治处境基本没有改善,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的政治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其基本的政治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该书对流动人口政治排斥问题第一次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不少前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对策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缺失,就此而言,该书具有较高的创新性。
第二,引入并完善了一个分析社会弱势群体政治处境的新概念——政治排斥。作者通过对社会排斥理论兴起和发展的回顾,构建了一种政治排斥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流动人口的政治处境,从而对新的条件和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并在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同时,政治排斥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从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移植过来的,运用政治排斥理论分析问题,也可以借鉴西方学术界已经较为成熟的社会排斥理论的成果和西方国家在消除社会排斥方面的实践经验,提供有效化解这一问题的政策措施的新视角。正是运用这种分析框架,作者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政治问题的研究更富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也增强了该书的理论价值,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第三,揭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以期引起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由此,作者把流动人口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社会事实,以一种恰当的、简洁的语言形式揭示出来,以期引起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如同关注流动人口生存问题一样来关注流动人口的政治问题,并化解蕴藏于流动人口政治排斥中的政治风险问题。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2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许多家长都知道经常看电视对孩子不好。可到底有什么坏处,却一下子说不上来。近日,美国某网站总结了孩子少看电视的六大好处,提醒家长要减少孩子看电视的时间。
有利于减肥。研究表明,每天看2个小时的电视会增加孩子肥胖的几率,而少看电视,带着孩子外出散步、游玩等有助于帮助孩子将体重保持在标准水平。
睡得更香。孩子晚上看电视越多,越不愿意上床睡觉,入睡也更加困难。在睡前,和孩子做点放松的事情,如听听舒缓的音乐,读读小故事等不仅能陶冶孩子的情操,也有利于睡眠。
增加实践机会。一味接受电视里的信息不如让孩子亲身实践,给孩子一个增加经验的机会:玩玩具、认卡片、学画画等,更能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提高学习成绩。要想成绩好,看电视时间要减少。研究显示,小学生如果每天看电视或电脑2小时以上,那么他们在注意力、社交能力和情感表达上更容易出现问题,学习成绩也比其他孩子更差。喜欢电子游戏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贴近大自然。外出感受鸟语花香,看一看蔬菜水果是怎么长成的,体会一下农民伯伯的辛苦劳动……抛开电视走进大自然,孩子会更懂生活,也更珍惜生活。
提升社交能力。学会与其他人沟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非常重要。与其“孤零零”地看电视,不如给孩子创造社交的机会。
吃西兰花可预防关节炎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一种化合物可有效预防最常见的一类关节炎,并减缓关节炎导致的软骨损伤等。
这种被称作萝卜硫素的化合物能遏制一种可引发关节炎症的酶发挥作用,从而减缓软骨损伤并缓解关节疼痛。萝卜硫素普遍存在于西兰花、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在西兰花中的含量尤为丰富。
此前研究曾发现,萝卜硫素具有抗癌、抗炎症等功效,这项研究首次发现它还有利于关节健康。研究人员已开始在一些医院开展小规模临床试验,以验证多食用西兰花对于人类关节健康的积极影响。
一次运动1分钟也有用
美国现行保健指南建议,每周至少从事2.5小时中等强度健身运动,每次至少持续10分钟。研究人员发现,可将2.5小时化整为零,即便每次从事中高强度运动1分钟也有健身效果,有助于减轻体重。
研究发现,女性经常从事1分钟中高强度运动,身高体重指数会降低0.07,以身高1.63米的女子为例,体重减少约226克;男性效果稍逊,从事中高强度运动1分钟,身高体重指数降低0.04,以身高1.73米的男子为例,体重减少大约122克。
这项结果显示,就健身效果而言,一周150分钟的运动不是非得分成几大块时间,只要运动起来,“1分钟也有用”。健身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有一千种方法可以化整为零,轻松健身。譬如,一边听着欢快的音乐,一边精神饱满地打扫室内卫生,或者在室外洗车;在厨房,尽量少用小电器,自己动手切切菜、洗洗碗、和和面;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公交车或者地铁,多步行一段时间。
口渴时反应变慢
如果你正因为伏案工作而疲惫不堪,效率降低,喝杯水或许是个好办法。因为,口渴的时候,人的反应会变慢,喝一杯水能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英国东伦敦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试验:让34位受试者分两次完成一系列测试,早餐只吃一块饼干后做一次测试,早餐吃了一块饼干又喝了一瓶水后,再做一次测试。那些不口渴的人,在喝水和不喝水的情况下,大脑的反应时间一样。但是那些口渴的人,喝水后大脑反应速度比之前快。
研究人员说,人在口渴时,大脑处理口渴感信息占用了大脑部分资源。而在补水之后,这部分大脑资源就释放了,提高了大脑的整体反应速度。
一支口红含9种重金属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研究发现,女士都爱的口红中含有多种微量有毒金属,其中铝元素的含量最高。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4款唇彩和8个品牌的唇膏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除了人们熟知的铝外,还含有镉、钴、铝、钛、锰、铬、铜和镍八种重金属。其中铝、铬和锰在所有被检测到的金属中含量最高。此外,为了增加唇彩的亮度,制造商们经常在口红中添加天然矿物云母。云母通常含有铅、锰、铬、铝等金属,而且口红颜色越深,金属含量就越高。
虽然口红对健康的危害尚无定论,不过专家建议消费者应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识。首先,不要让幼儿玩口红,因为他们对重金属的危害更敏感;其次,爱美的女士每天只涂抹2~3次口红即可。因为如果每天擦多次口红,等于摄取过多的重金属,这可能会损害身体及神经系统。
个矮的人易得冠心病
一项研究表明,个子矮的人比个高者患冠心病的几率高50%。当然,与身高相比,体重、血压和吸烟习惯仍然是更重要的危险因素。
芬兰的科研人员总结了全世界52项有关身高和心脏健康之间的研究,总人数超过300万人。总体来说,矮个子(即男性低于165公分,女性低于152公分)患冠心病的风险是高个子(男性高于178公分,女性高于168公分)的1.5倍。研究人员认为,个矮者冠状动脉较细,一旦血液出现问题,很容易阻塞。此外,个头高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生前后的营养环境。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早期的发育受影响,不但个子矮,身体的总体健康状况也不如高个子。
不过,专家表示,个子矮的人不要因这项新发现而烦恼,身高只是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尽管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高,但他们可以调整其他重要的因素,即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不抽烟、不酗酒、平衡饮食和多运动。
沉迷流行音乐加重酒瘾
第3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大家好!我自2001年干计划生育工作已近五年了,回顾这五年来的工作历程,酸甜苦辣尽在其中,个中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味。
初干计生工作时,我主要分管流动人口计生工作,为了摸清辖区各片流动人口情况,我跟随各社居委、单位下去清查登记流动人口。因我辖区面积大、人口多、人员复杂,流动性大,流动人口较难管理,当时考核注重建档与持证,为了那一本小小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常常要对无证的经营户苦口婆心地进行政策宣传与督促办理,但却收效甚微,还要受到很多冷嘲热讽。也有一些不配合的人不给登记,挨骂受气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要动手打人。记得有一年,为了提高流动人口持证率,街道在区计生委的统一组织下,开展为三县流入人口代办证并送证上门活动,当我们把辛辛苦苦办来的《婚育证明》送给长江东路一卖化妆品老板时,她不但不领情,还当场把证撕烂扔在门外的下水道内,当时心里真是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既辛酸又伤心。
为了尽心尽力做好这项工作,我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我始终相信,计划生育工作是我的义务和职责,优质服务是我的愿望和追求,只要你以诚相待,终会取得流动人口的理解与支持。去年3月份,我和社居委主任上门查验长东745号一经营手机门面,之前社居委主任已上门多次索要《婚育证明》,每次去都说下次带来,这次说好今天一定带来。我和计生主任上门问其要证,他说又没带,计生主任正要发火,我想换个方式说,以退为进吧,我说:老板,今天忘带了没关系,你们做生意也忙,你说哪天带来,我们就哪天再上门,请也体谅一下我们的工作。他说下午带来,下午我们准时又登门,一见我们,老板满面歉意地迎上来,把证递给我们,说: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工作真是让人佩服,没想到你们这么有耐心,跑了这么多趟,耽误你们工作了……顿时我们感到无比欣慰,能听到他亲口说出肯定我们工作的话,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真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2003年2月的一次引产事件又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怀。因我辖区城乡交错、老旧小区较多,加之经济不发达等原因,住宅小区变动相当大,买卖房频繁、农村购房户口农转非、家庭情况复杂,这些人员的流入,势必成为计生工作中的极大隐患。天长路64号的许红就是农村购房迁入者,丈夫系农村人,夫妇双方均为再婚,且男方已有两个孩子,现女方又怀孕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非常重视,立
即行动采取补救措施。许红已是大月份,夫妇生育愿望很强烈,对其思想转变和说服教育相当难,在医院,夫妇抵触情绪很大,街道调动全体工作人员参与进来,轮流对其进行政策教育与心理疏导,当时的天气还很冷,我们又冷又饿,瑟瑟发抖,时间嘀嗒嘀嗒缓慢而沉重,我们的心理生理压力重重……经过一夜的双方沟通交流,夫妇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终于在早晨五点半签字同意手术,我们这才松一口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在医院照顾她的期间,以朋友的方式和她聊天,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安慰鼓励她重新站起来,面对新的人生。出院后,街道也从生活上给予其经济帮助,同时办理了低保,在街道的真诚付出和帮助下,许红来到计生办热泪盈眶地对我们说:谢谢街道、谢谢你们,你们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我一定会重新站起来,以后好好生活……我的内心真是百感交集,无比欣慰,既为我们能化敌为友,也为我们的工作得到居民的理解,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的真心付出感动了她们。
去年为了建立常注流动人口微机化管理模式,辖区近一万个育龄妇女和流动人口要上门核查和录入电脑,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计生办、各社居委紧锣密鼓地进行上门核查登记与微机录入工作。上门搜集资料是做好此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对于白天找不到人的住户,就利用晚上和双休日上门。我在做好业务与微机指导的同时,晚上把育龄妇女卡片带回家里录入,加班加点至深夜零点。居委会计生主任纷纷感慨:为了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和爱人,饱受工作、家庭不能两全的痛苦……我深深体会到这天下第一难事的真正含义,我更深深懂得,我踏上的计生路是一条充满风雨的坎坷之路。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街道、社居委的帐表、数据库完善齐全、信息准确、服务到位,我们的工作也得到大多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群众婚育观念也在逐步转变。
第4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2.048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opulation Float and Grain Yield In Anhui Based on VAR Model
DU Hui-yan,WANG Xu,ZHANG Yan,ZHANG Zh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total grain yield, floating population rat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1993-2014, a VAR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population float on grain y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short ter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ate had a good effect on grain yield, mainly due to the less pressure of the population-land contradiction and increased marginal benefit of land from the massive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the urbanization level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ain yield. In addition, the grain sown area, rural electricity power consumption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had promotion effect on grain yield in the short term.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to protect arable land, to improve the permanent protection area of basic good farmland an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 float;grain yield;VAR model;Anhui province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业发展稳定以及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来说是始终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1]。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工业化率不断提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必然[2]。人口流动是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做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根据人口流动的空间,可将其划分为县内的、省内的、省际的以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等类型。在当前城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成为人口流?拥闹髁?军。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农村人口加速迁移,表现在农村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二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包括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1]。另外,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省际劳动力流动不断增加,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占省际人口迁移的80%以上[3]。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代表的城乡间和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对粮食生产构成威胁。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使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出现弱质化、兼业化现象[4]。鉴于中国强大的人口基数,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民生的大问题[5]。当前,安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安徽也是重要的劳务输出大省,而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为保证粮食安全,须对农村人口流动和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促进农业发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2 安徽农村人口流动和粮食生产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步伐显著加快[1]。由于安徽农村人口流动相关数据缺失,本研究从安徽流动人口整体状况和城镇化率来探究安徽农村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安徽省际间流动人口从1993年121万上升到2014年1 053万,净增加93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85%;流动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例从2.06%增加到15.00%。另一方面,安徽城镇化率发展较快, 从1993年18.48%上升到2014年49.15%,年均增长4.77%;在城镇生活工作的人口总量从1 089.76万人上升到2 989.79万人,净增加约1 900万人。
1993-2014年安徽人口流动、城镇化率和粮食总产量情况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安徽省际间流动人口虽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但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且略有反复;而城镇化率自1998年开始,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
安徽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全省粮食总产量自1993年来整体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趋势。从1993年2 305.2万t增加到2014年3 415.8万t,净增加1 110.6万t,年均增加43.57万t。虽然安徽粮食总产量整体呈现不断增产的情况,但从图1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并不稳定,在1997-2006年10年间,安徽粮食总产量极不稳定,表现出不断起伏的特点,甚至在2003年达到2 214.8万t的历史最低值。
3 计量模型构建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选取1993-2014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GY,万t)、流动人口比例(FPR,%)、城镇化率(UR,%)、粮食播种面积(SA,千hm2)、农村用电量(REPC,万kwh)、农用化肥施用量(CF,t)等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粮食总产量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为自变量。所有数据均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7.0对数据进行分析。同时为减少数据的大幅波动及消除可能潜在的异方差对数据模型估计的影响,首先对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农村用电量、农用化肥施用量取自然对数,得到新的序列LnGY、LnSA、LnREPC、LnCF。
3.2 变量说明
流动人口比例(FPR):用地区内流向省外半年以上总人数与地区户籍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达。该指标能够说明当地人口向省外流动的程度和广度。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流动人口占比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农业兼业化、弱质化、老龄化、高龄化现象日趋严重。
城镇化率(UR):用地区城镇人口总数与地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达。该指标能够说明当地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程度和广度以及城镇人口的数量规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流向城镇的农村人口日益增加,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主体。
粮食播种面积(SA):指实际播种粮食的面积。凡是实际种植粮食的面积,不管种植在耕地上还是种植在非耕地上,均包括在粮食种植面积中。粮食生产最终来源于土地,因此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产量的根本性因素。
农村用电量(REPC):电力是一种现代化的能源。农村用电量的多少,标志着农村的生产率和农民的生活率。在农业生产上,用电力替代人、畜力乃至煤炭、柴油、汽油等,可以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提高。
农用化肥施用量(CF):指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数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化肥施用量按照折纯量计算。化肥是粮食生产的必需品,对粮食产量的稳定和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3.3.1 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是进行VAR模型分析的前提,在非平稳的情形下应用VAR模型可能会产生伪回归,使得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形严重偏离。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前,运用ADF检验方法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由表1可知,在所有被检验的变量中,对数化处理后的LnCF(农用化肥施用量)和LnSA(?Z食播种面积)仅在10%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另外FPR(流动人口比例)、UR(城镇化率)、LnREPC(对数化后的农村用电量)、LnGY(对数化后的粮食产量)4个变量无论在何种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其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时间序列数据FPR、UR、LnREPC、LnGY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LnCF和LnSA在1%和5%显著水平下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经ADF检验,在各个显著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序列FPR、UR、LnREPC、LnCF、LnSA、LnGY均是单整序列。
3.3.2 VAR模型的构建 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即变量间的关系并不依靠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它采用多方程联立形式,将内生变量对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期进行回归。VAR模型一般形式为:
Yt=A1Yt-1+A2Yt-2+???+APYt-p+B0Xt+???+BrXt-r+?着t
t=1,2,??,n (1)
式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Yt-i(i=1,2,…,p)是滞后内生变量向量,Xt-i(i=0,1,…,r)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或滞后外生变量向量,P、r分别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At是k×k维系数矩阵,Bi是k×d维系数矩阵,?着t是由k维随机误差项构成的向量。
序列FPR、UR、LnREPC、LnCF、LnSA、LnGY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但是在构建VAR模型之前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因为选择最佳滞后期是确定VAR模型结构的重要前提。运用Eviews7.0,依据AIC和SC最小原则,对序列FPR、UR、LnREPC、LnCF、LnSA、LnGY的滞后阶数进行判断,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因此建立VAR(2)模型。
运用Eviews7.0,构建VAR模型自回归向量方程如下:
LnGY=-1.016 1LnGY(-1)-0.154 5LnGY(-2)+1.909 3LnSA(-1)-0.798 5LnSA(-2)-0.040 8LnCF(-1)- 0.544 4LnCF(-2)+0.518 6LnREPC(-1)+0.086 8Ln
REPC(-2)+0.367 0FPR(-1)-0.437 4FPR(-2)-0.002 0UR(-1)+0.008 3UR(-2)+8.109 7 (2)
由式(2)可知,前1期的粮食产量对当期粮食产量的影响为负,前2期的粮食产量对当期粮食产量的影响仍为负,表明粮食产量的基础率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大,并且影响逐渐明显。粮食播种面积在滞后1期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在滞后2期为负,且系数之和为正值,表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减弱。农用化肥施用量在滞后1期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负,在滞后2期为负,且影响逐渐减弱。农村用电量在滞后1期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在滞后2期为正,说明农村用电量和粮食产量呈现正相关关系。流动人口比例在滞后1期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在滞后2期为负,系数和为负,表明流动人口比例和粮食产量之间在短期内可能有正相关关系。城镇化率在滞后1期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负,滞后2期为正,系数和为正,表明城镇化率和粮食产量在短期内可能是负相关,但长期看二者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3.3.3 脉冲响应分析 VAR模型的不足在于模型难以解释计量结果的经济含义,这要依赖于脉冲响应函数对有关模型的解释。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在误差项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带来的影响。与VAR模型的系数相比,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较好地反映序列之间的动态关系。基于已建立的VAR模型,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和粮食产量之间的动态响应。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前提是VAR模型具有稳定性。因此运用Eviews7.0对建立的VAR(2)模型进行检验,见图2。由图2可知,该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小于1,位于单位圆之内,表明模型稳定,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3是脉冲响应曲线图,模型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20期。
1)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响应情况。从图3a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对粮食播种面积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产生较大强度的正响应,且达到最大值,2~4期正响应开始下降趋近于0,5~15期出现负响应,16~20期出现正响应且在缓慢上升。这一现象说明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增加播种面积虽然可以实现粮食短期内增产;从中期来看,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影响并不明显;长期来看,粮食播种面积必须有一定的保证,才能确保粮食总产量增加。
2)农用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响应情况。从图3b可以看出,农用化肥施用量给粮食产量新息一定的冲击,粮食产量在第2期做出最高的正响应,到第3期迅速下降为负响应,随后在3~13期间不断在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间波动,在14~20期呈现负响应。短期来看,农用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有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化肥施用量的增长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确定。
3)农村用电量对粮食产量的响应情况。从图3c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对农村用电量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产生较大强度的正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程度的正响应,在4~9期粮食产量对农村用电量在正响应和负响应间波动,在10~20期表现出负响应。这一现象说明农村用电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短期看以促进作用为主,从长期看则对粮食产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4)流动人口比例对粮食产量的响应情况。从图3d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比例给粮食产量新息一定的冲击后,粮食产量在第1期立即做出最大的正响应,随后在2~3期,正响应缓慢下降,在4~9期呈现负响应和正响应交替出现的情形,第10期往后趋于稳定。总体看,人口流动对粮食产量有促进作用,减少了人地矛盾,有利于土地集中经营,提升土地的边际效益。
5)城镇化率对粮食产量的响应情况。从图3e可以看出,城镇化率在给粮食产量新息一定的冲击后,粮食产量在第1期做出负响应,随后在第2期立即做出较强正响应,第3期仍为正响应,在4~9期正负响应交替出现,第10期往后趋于平稳。
3.3.4 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分析函数刻画的是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情况,而方差分解则将VAR模型的一个变量的方差分解到其他变量上,进而计算出其对各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检验LnGY作为因变量的方差分解见表1。
从方差分解表看出,LnGY在第1期只有自身对预测方差有贡献,在第2期迅速下降到53.29%,随后整体保持下降趋势,大约在第11期左右,LnGY分解结果基本稳定。LnSA对LnGY有一定贡献度,在2~5期保持在23%以上,大?s在第11期左右分解结果基本稳定。LnCF对LnGY有一定贡献度,大约在第14期左右分解结果基本稳定。LnREPC对LnGY的贡献度从第2期的15.81%上升到第9期的22.60%,随后基本保持稳定。FPR对LnGY的贡献度从第3期的4.71%迅速上升到第4期的18.02%,随后大约在第7期左右分解结构保持基本稳定。UR对LnGY的贡献度很低,始终未达到0.50%。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综合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短期来看,流动人口比例增加对粮食产量产生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流动的增加有利于减缓人地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土地的边际效益;另外可能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兼业化的现状,对农业技术、新品种的推广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城镇化率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说明在当前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城镇化的推进是以占用耕地为代价的,这对提升粮食产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农业有更多资本、技术的投入,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可能被耕地面积减少抵消,导致城镇化对提升粮食产量的作用不明显。另外,粮食播种面积、农村用电量和农用化肥施用量在短期内对粮食产量具有推进作用。
第5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市人口;镇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03-09
一、导论
在中国,“城镇”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混沌的概念,其中至少包含着“城”与“镇”两层含义。但“城镇”显然应是一个组合词,是“城市”与“乡镇”词义的集合与重组。尽管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类聚落形态划分为“城镇”与“乡村”两种类型,却似乎难以将“城镇”内涵从“城市”概念中离析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遍布于乡村腹地的“镇”在一定程度上确已脱离了“乡”和“村”的属性与形态,初步具有了“城”的某些特质,因而可以将“镇”纳入“市”的范畴以“城”相待。此举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容易在认识上将“城市化”与“城镇化”两概念混为一谈,这种概念混淆不仅长期存在于国内学术界,甚至也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本中。
在西方,“城”与“镇”的含义本是泾渭分明的,“城”即City,亦即“市”,是以非农产业为主的人口聚居地,与传统的农牧生产和乡村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反差,其典型形式莫过于“都市”,英文叫Metropolis。同理,在英文中“镇”的对应词就叫Town,是指那些虽有“城”(City)的形态,但仍然与乡村(Countryside)和农牧业保持着较紧密联系的人口聚居地。两相比较,如果说,城(City)是非农产业及非农人口的聚居地;那么镇(Town)则可认为是农牧业区域中心,两者内涵有别、层次不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相关报告中,就是将“镇”(Town)单列出来,视之为不同于“市”(Citv)和“乡”(Countryside)的人口聚居类型。
如此看来,“城市化”作为一个泊来词,在其对应的英文Urbanization中,显然是关于“城市”(City)的表意,并无“镇”(Town)的蕴含。“城镇化”语境应是中国版的Urbanization,是本土化的“城市化”概念。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城市”与“城镇”分别指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两类城市化形态,前者已经明显脱离“农业”产业主导和农村生活方式,是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形态;后者作为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则依然与农业和农村联系紧密,尤其对于处在城市化初始阶段的“小城镇”,则更与农业和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独具“乡首城尾”特征的小城镇显然不宜与城市相提并论,两者所显现的人口学效应也不尽相同。
本研究拟根据人口普查设置的统计指标,将普查中设定的“镇人口”从“市人口”和“乡人口”中分离出来,视为小城镇人口,并确立如下三个对应关系:①“镇人口”指代小城镇人口;②“市人口”指代城市人口(不包括镇人口);③“乡人口”指代乡村人口。据此划分所做的分析,或许能为我们深入观察中国城镇化中的“市”“镇”人口状态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一些新认识。
二、“市”“镇”人口规模及其消长变化
人口规模作为反映既定时空条件下的人口状态,是我们观测区域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一个基本指标。城镇化演进的一个观察基准就是看人口规模的城镇集聚状态,因此,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及其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城镇化演进的具体表征。普查资料中的“城镇人口”是由“市人口”和“镇人口”两部分组成的,在既定时空条件下,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据此可观察两者在城镇化中的消长变化。
首先,在全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中,“镇人口”规模增长快于“市人口”。全国“镇人口”规模从2000年“五普”时的1.66亿增长到2010年“六普”时期的2.66亿,净增了1亿人,同期“市人口”规模从2.93亿增长到4.04亿,净增1.1亿。如此看来,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市镇人口规模绝对值的增长大体相当,但由于“市人口”基数近3亿,远高于“镇人口”1.66亿的同期值,因此,就市镇人口规模变化的相对值比较,“市人口”增长幅度仅为38%,同期“镇人口”增长幅度达到60%,表明这十年间“镇人口”规模增长明显快于“市人口”。
分省区观察(见图1),在“五普”至“六普”的十年(2000~2010年)间,全国及各省区“城”“镇”人口增长呈现两种变化态势。
一方面,“镇人口”增长幅度快于本省“市人口”的大多数是欠发达省区,共计22个。其中增长最显著的河北省,十年间镇人口规模从606万增加到1719万,净增1113万,增幅达183.66%,同期“市人口”仅增加289万,增幅仅为25.13%,表明河北省人口城“镇”化进程显著快于城“市”化进程。“镇人口”增幅超过100%的还有江西省(111.64%)、河南省(136.02%)、湖南省(127.68%)和青海省(105.36%)。另有山西、安徽、重庆、云南、陕西和甘肃等省区的“镇人口”规模增幅超过80%。
另一方面,“市人口”规模增长超过“镇人口”的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9个省区,尤其是天津和广东两省区的“市人口”增幅分别高达66.86%和73.13%,而“镇人口”规模不增反降,分别下降20.22%和3.09%,这种市镇人口增减的反差,表明这些省区的城“市”化进程快于城“镇”化进程。天津和广东两省“镇人口”增幅呈负值,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天津和广东两省区城市区域快速扩张,延伸到周边的乡镇,因而将原来独立存在的“镇人口”囊括其中,就地转变成为“市人口”,因此,才出现这两个省区“镇人口”减少、“市人口”增加的情形。
其次,在“五普”至“六普”时期,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36.92%提高到49.68%。这其中,由于“镇人口”规模的增长速率快于“市人口”,促使中国城镇化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镇人口”占市镇总人口的比重从36.21%上升到39.70%。意味着“镇人口”对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贡献率上升,“市人口”则相应下降,因此,在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构成中接近四成来自“镇人口”。
分省区比较,大部分省区“镇人口”占市镇总人口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五普”时“镇人口”占市镇总人口比重超过50%的只有三个省区,即江西省(50.67%)、云南省(53.03%)和(56.86%)。“六普”时期“镇人口”占市镇总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区增加到九个,即河北省(54.43%)、安徽省(52.37%)、江西省(61.52%)、湖南省(55.23%)、广西(54.65%)、四川省(50.59%)、贵州省(52.82%)、云南省(60.37%)和(59.99%)。与此同时,有十个省区的“镇人口”占比呈下降走势,下降幅度最大的天津和广东两省区分别为11.29%和12.09%(见表1)。
三、“市”“镇”人口聚居密度对比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城市功能的强弱之间存在较显著的一致性,因而形成不同层次的城市人口聚居密度。一般来讲,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由于大城市强大的吸纳能力与极化效应,单位面积内聚居的人口数量应多于小城镇,因而其人口密度往往更高。但在当代中国,现实情形则并非如此。
本文依据城市(市区)和建制镇(镇区)的统计数据,对比观察两类聚居区域中的人口密度,有以下三点发现。
一是发达省区的城市(市区)人口密度低于欠发达省区。如表2所示,城市(市区)人口聚居密度列前三位的并非经济发达的直辖市或沿海省区,而是陕西(6179人/km2)、黑龙江(5453人/km2)和新疆(4789人/km2)等经济欠发达省区。这其实折射出当今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偏向”——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二是建制镇(镇区)人口聚居密度较高的省区多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上海市(6621人/km2)、重庆市(4716人/km2)分别列居第一、二位,另如山西(4094人/km2)、江苏、海南、四川、福建等省区的建制镇(镇区)人口密度都在3000人/km2以上。这可能与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有直接关系。
三是大部分省区小城镇(镇区)人口密度高于大城市。如图2所示,在全国31个省区中,只有14个省区的城市(市区)人口密度高于建制镇(镇区),其余17个省区的城市(市区)人口密度都低于建制镇(镇区);而且观察人口密度相对差可见,“市人口>镇人口”的差值幅度显著低于“市人口
四、“市”“镇”外来人口构成状况
在开放的空间格局下,城镇人口增长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镇自身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城镇辖区外来人口的“迁移增长”。按照当下中国城乡人口统计标准,城镇人口可由“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部分构成,但城镇“常住人口”还可按户籍属性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两部分,前者就是传统制度安排下的城镇人口;后者则是当代市场经济驱使下,来自于城镇辖区以外的流动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乡村的农业人口,但是,“外来人口”作为流入城镇的一部分乡村人口,只有那些在城镇连续居住满半年(或离开原居住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才被视同为城镇的“常住人口”,纳入城镇人口统计(见图3)。
根据“六普”数据,本文确认,市镇总人口是由各自区域中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或称“外来人口”)构成的,两者之和就是城镇拥有的实际人口规模。
通过观察城镇人口中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构成,计算外来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的“分量”,即可发现,在201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城市的外来人口占比接近30%,小城镇外来人口占比虽然较低,也超过了17%。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城镇常住人口构成中,并不全是户籍人口,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外来(非户籍)人口。
分省区观察可见,在“市人口”层面,外来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一(33.34%)的省区包括北京、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海南及内蒙古7省区,其中大多是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东部及沿海省区,外来人口占比不足五分之一(20.00%)的省区只有黑龙江一省;相较而言,小城镇集聚的外来人口显然较少。如表3所示,在“镇人口”层面,外来人口占比超过1/3的省区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而外来人口占比不足1/5的省区却多达22个。这种市镇外来人口占比的差异说明,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越大,其占比也就越高。
五、“市”“镇”流动人口分年龄、分流向对比
年龄是影响个人迁移行为的一个主导因素。一般情况下,青壮年人口总是比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更具流动性,但不同的聚居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迁移流动取向。在此,我们依据2010年“六普”数据,以“镇人口”和“市人口”为对象,观察比较两个聚居层面(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情况的迁移流动人口(参见图4和图5),发现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全国“镇人口”层面的迁移流动显著偏向于省内,省内迁移(占75%)远远超过省际迁移(仅占25%)。同期在“市人口”层面,省内迁移与省际迁移大体上对等,省内迁移(占56.38%)略高于省际迁移(43.62%)。这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距离与聚居于其中的城镇规模相关,城镇规模越小,人口的迁移流动距离越短;反之,城镇规模越大,人口迁移流动的距离就越长。
二是“镇人口”层面的省内迁移人口年龄结构比“市人口”层面年轻。如图4显示,在“镇人口”层面,“六普”时15~19岁组省内迁移人口占比尤为凸显,其次是20~24岁组,两个年龄组人口合计,占到镇总迁移人口的25%;同期省际迁移占比最高的人口集中在20~24岁组,但也不过4.37%,其值仅与省内迁移10~14岁组和45~49岁组相当。可见在“镇人口”层面,省内迁移不仅主导着人口迁移流动取向,而且迁流人口的年龄相对较为年轻。
图5显示的是“市人口”层面的年龄别人口迁移流动格局,与图4“镇人口”比较,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在省内迁移与省际迁移之间的分布较为均衡,人口迁移行为主要发生在20~24岁组,省内迁移略强于省际迁移。其中只是在15~19岁组,仍然表现出省内迁移显著高于省际迁移的偏向,由此加强了省内迁移人口的年轻化格局。可见,在以“镇人口”统计的小城镇流动人口中,镇流动人口具有年龄结构较轻、迁流距离较短的特点。
六、结论及启示
人口城镇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深刻变革,亦是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一项重大实践。城镇化演进的一个显见标志就表现为既定区域的人口集聚。不同层次的城镇形态蕴含着不同的人口集聚效应,本文通过对普查数据的观测分析,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其一,总体观察,在21世纪的头十年间,虽然中国“镇人口”规模净增长低于“市人口”,但中国“镇人口”规模的增长速率明显快于“市人口”,由此促使“镇人口”在中国城镇总人口中的占比提升了近3.5个百分点。这或许意味着,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小城镇发展的低迷阶段后,中国小城镇人口集聚再次呈现的增长走势,预示着新一轮的城镇化有可能在小城镇层面展开。
其二,“五普”至“六普”这十年间,中国城镇化水平呈现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镇人口”对中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接近40%,表明小城镇人口在中国城镇化的人口格局中占有四成的分量。尤其是广大欠发达省区小城镇人口的加速集聚,助推着中国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可以预见,伴随国家产业布局的调整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人口城镇化中的小城镇“分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加码。这种格局变化有助于纠正“大城市”偏向,也印证了新近一份相关研究的观点:“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形态将由东部、大城市为主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分散转变”。
其三,无论是普查年的时期纵向观察,还是分省区的横向对比,也无论是城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构成变化,都表现出城镇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变化的关联性。这再次提示我们,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总是与不同的城镇化水平相对应。人口城“镇”化作为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是由乡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主导的。因此,人口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就是以人口的城“镇”化为主导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在辩证认识和适时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省区的发展条件,既要积极创造条件,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又要避免拔苗助长,片面追求城镇化的“一步到位”和“贪大求洋”,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促使区域城镇的健康发展。
其四,据年龄结构观察,“市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镇人口”和“乡人口”都低,这似乎背离现代化和城镇化对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规律,但其实不然。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乡城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情形下,大量乡村青壮年人口涌入城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镇人口年龄构成的“老化”程度。结果是,分省区观察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化”之间的变化关系并不一定同现,而且必将伴随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方向与强度而发生变异。
其五,人口聚居密度的高低变化取决于地域面积与聚居人口两者的互动结果。当地域面积扩张快于区域人口增长时,就会降低人口聚居密度;反之则将提升人口聚居密度。当代中国小城镇人口密度高于大城市,欠发达省区高于发达省区的现实表明,小城镇的人口聚居能效比大城市好。这提示我们,城市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与人口集聚密度的高低直接关联。在国土资源约束条件下,健康的城市化应该注重地域面积扩张与聚居人口增长两者之间的协调一致,寻求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高效组合。
最后,研究发现,城镇规模大小与人口流动空间距离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与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比较,中小城镇规模明显偏小,所以“镇人口”流动以短距离的省内流迁为主,而长距离的跨省流动人口主要发生在“市人口”层面。尤其是在京津沪、浙江和广东等省市,跨省人口流动更占据主导。这表明,不同的聚居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迁移流动取向,聚居在发达省区或中心城市的人口,由于信息更畅通、眼界更开阔,因而比聚居在边远省区和中小城镇的人口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意愿和更大的流动空间。
参考文献:
[1]Brunt,B,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2ed[M],Dublin:Gill&Macmillan,1997.
[2]World Bank,China Small and Medium Towns Overview[R],2012.
第6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测度方法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3日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概念界定
(一)新生代农民工。张雨林(1984)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词汇,随后“农民工”这一词汇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使用。王春光(2001)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差异明显,从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认为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刘传江、徐建玲(2006)则基于两代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各自文化、观念及行为上差异,从人口学和经济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认为其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具体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用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将其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虽然学者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上存在着差异,但绝大部分学者认同其是出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城市务工农民。
(二)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市民化”指农民、外来移民 (城市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这些均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市民化过程。广义“市民化”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使现有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些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农民市民化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市民化程度如何,采取什么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测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相比其他问题的研究文献而言不是很充分。构建一套全面、准确测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困难。现有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传江和王桂新两个学者的研究。
马用浩等(2006)认为完整的农民市民化是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相应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内容。但该文并没有进一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刘传江等(2008)构建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其中农民工个体市民化程度的综合指标由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中居住时间和自我认同这四者的几何平均数构成,结果显示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50.23%。王桂新等(2008)从微观主体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设立了一个指标评价体系,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5个维度。研究表明,在5个度量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中,居住条件的市民化水平最高,为61.5%,经济生活、社会融合和心理认同是农民工市民化的3个重要维度,而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但是,该方法的工作量相对较大,而且5个维度的权重赋值相等,这点有待商榷。
刘传江等(2009)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赋值测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558、0.258、0.096、0.096,这避免了王桂新等(2008)各个指标权重均等的缺陷。他们测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42.03%,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评价。
周密等(2012)采取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估计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市民供给的条件下具有市民需求的概率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1)市民需求,即农民工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的市民意愿;(2)市民供给,即打工者所在城市给予其市民身份。
三、不同测度方法比较
(一)几何平均方法。几何平均法最早由刘传江等(2008)采用,该方法采用微观调研数据,通过市民意愿与市民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测得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程度。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31.3%,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50.23%。
(二)指标评价体系法。王桂新等(2008)运用指标评价体系法对上海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他们构建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系统,分别从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5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别赋予每个指标的权重为0.2。结果显示,上海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达到53.9%。该指标评价体系法的工作量较大,而且赋予权重的主观性较强。该方法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于周密测度的市民化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测度的农民工群体包括了上一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是要高于上一代的,而且上海地区的生活成本较高,市民化程度低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AHP层次分析法。根据刘传江(2009)的研究结论,他们采用层级分析法(AHP)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他们选择了四个方面的指标,分别是:(1)生存职业指标;(2)社会身份指标;(3)自身素质指标;(4)意识行为指标。这些指标的数值都是在0~1之间,能较清晰地体现农民工朝着市民目标转变的进度,当其达到1的时候,便可判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四)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周密(2012)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了余姚和沈阳两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测得的余姚和沈阳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62%和81%。
周密的模型令y*s代表农民工市民供给意愿的隐含变量,ys代表农民工是否愿意供给的决策变量;y*d代表农民工市民需求意愿的隐含变量,yd代表农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决策变量;X1为影响农民工市民需求的解释变量,X2为影响农民工市民供给的解释变量。假设ε1和ε2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建立联立模型。
四、结束语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的测算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还比较薄弱,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如何?怎么选择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来测定其市民化水平?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其市民化进程中政府、社会机构、个人等不同层面宏观和微观主体应各自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开展相关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市整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3.
[2]马用浩,张登文,马昌伟.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初探.求实,2006.4.
[3]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5.
[4]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第7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计划生育与人的文化素质是紧密联系的,只有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能够充分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了,计生工作才会发生质的飞跃。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计生办站干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到“两基”工作,把“两基”工作融入到计生工作中,充分利用工作职能认真开展“两基”工作,为“两基”工作添砖加瓦,以尽快实现“两基”目标。现将其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大力宣传“两基”知识,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实现“两基”目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们充分利用人口计生工作点对点的宣传优势,每走到一户,在宣传计划工作的同时,把“两基”知识融入其中,向群众讲解两基的基本含义、两基包括的内容、在两基工作中每个人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应该做哪些工作等等知识,特别是对于有适龄儿童的家庭,反复宣传,动员其及时送子女到学校入学,对于厌学情绪严重有辍学可能的学生,就耐必细致地做其思想工作,必须好好念书,对于辍学到外打的学生,我们就给其父母下定硬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必须返回来入学,如果不返回,计划生育的有关证件一律不给办理。在人口学校,我们开设人口计划生育专题讲座,安排专人进行授课,使群众充分认识到教育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二、兑现有关优先优惠政策,切实为计生户的子女入学排忧解难。
在人口计生工作中,我们总是把“两基”工作放在首位,与两基有关的工作,我们先做,与两基有关的优先优惠政策我们先兑现。对于全乡的独生子女家庭和两女结扎家庭实行帮扶,对于子女让学有困难的,实行支助;对于积极送子女上学的已婚育龄妇女夫妇,列入计生“三结合”帮扶的重点对象;对因子女都在上学,因劳力有限忙于农业生产而未能及参加妇检或手术的对象,我们计生办一律免于处罚或从轻处罚;对因送子女上学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计生户,在办理计生证件时,一律免费。我们的多项优先优惠措施,为育龄群众自觉支持两基工作起到的一定的作用。
三、积极配合学校,认真清理辍学外出的务工青年,返乡继续完成学历。
我们根据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于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外出务工的青年进行认真的清理,通知其父母把子女叫回来上学,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回来的,一律停办该户成员的一切计生证件,并且还通过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通知流入地对其子女清查有关证件。对于子女及其父母都流出,而子女没有入学的家庭,我们严格实行“三代”人员责任追究制,对在家代看房屋、代耕土地的相关人员递发通知,限期将流出适龄入学青年通知回来上学。
四、积极配合,主动参与,搞好文化户口登记和核对工作。
第8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 人口迁移 势场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师塞罗达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 urbanization 的概念。Tisdale(1942)就认为城镇化概念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集中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
在国外,很多时候,人口迁移(migration)和人口流动(mobility)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是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经常居住地发生了改变,此时户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迁移;户籍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流动。本文中迁移和流动含义相同。与我国相比较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行的比较早,国外对人口迁移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理论主要有:推拉力理论。英国统计学家E.G.Ravenstein 1889年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法则,其中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966年,E.S.Lee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迁移者的个人因素四种。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说明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边际收益率高低所导致的。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建立了拉尼斯-费模式(Ranis-Fei model),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了农业剩余。但随后,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于1969年提出“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期望获得收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理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投资,所形成了人力资本,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物业学视角。国内外也有人以物理学视角解释人的行为,指出了人的行为同气体和流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可比性。Lewin(1951)认为社会场中的各个社会作用力是行为变化的操众者,Schwind(1975)提出人口迁移的流场理论。我国的肖周燕(2010)从人口迁移势能的角度尝试对人口迁移进行了解释。
目前,我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中来。根据以往的人口迁移理论,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势”,首次提出“人口势场”、“人口势差”等基本概念,并把“势”理论运用到人口迁移中去,以期以新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势差与人口迁移
物理学中,当某一能量场与位置有关系时,通常就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势”。自然界的物体都有自发地从高势向低势运动的趋势,物体的运动来自于能量差,社会中人口的迁移也不例外。本文中把人口与促使人口运动的能量以及人口所在的位置联系起来,提出“人口势场”的概念。当某一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聚集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而当某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低势位,富余人口具有自发地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态势。
我国长期存在着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的差别即是势差的客观表现形式,任何群体,越不平衡,变化的势能就越大,张福墀(2001)指出“势”是力的内隐形态。势差的存在使生产要素产生流动,其中经济性势差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杨满社,1994),主要表现为收入差异。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设Yu(t)为城市的收入水平,Yr(t)为农村的实际收入,Pt为劳动者在城市部门就业的概率。则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为:
其中,f?)>0进一步考虑迁移成本,则迁移行为取决于净收入V(0),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这里r为贴现率,C(0)为迁移成本。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除了以上收入差距等经济势差之外,还受到了原住地、迁入地、个人以及中间阻碍物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社会系统里面,迁移者都受到吸引力、斥力两种力量的影响,所产生的合力促使迁移者发生迁移行为。每个迁移者的合力都有所不同,故迁移路径也不尽相同。
不论居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利有弊,弊即对迁移者产生推力,推动其离开居住地,利即产生引力,吸引其留在居住地。见图1,图中“+”表示引力,“-”表示推力。在农村,有更多的推力“-”,导致了大量富于劳动力,处于势场的高势位,城镇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吸引力“+”,处于势场的低势位。“”表示富于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迁移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在阻挡着迁移。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城市的吸引力和推力见表1。
针对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李强(2003)指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前两位因素,同时指出户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大制度障碍。王敬贤(2011)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因之一就是存在经济势差,并把经济势差分为产业势差与地域势差。励娜等(2008)发现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主要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王德文等(2008)指出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综上所述,如果以物理中的重力势能来表示人口势能,则人口势能公式:Ep=mgh。这里m表示迁移者,g表示环境,主要是指迁移者所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条件、市民化程度及融入障碍等等。h表示经济势差,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这里可以用h上面的V(0)表示。
如果农村中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多的为人口势场高势位,则城镇中收入较高劳动力短缺的为人口势场低势位。由于势差的存在,则有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趋势。物理学中,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过程中,如果存在空气摩擦力,则有势能消耗,同样人口势能的转化中亦受到障碍因素的影响消耗能量,影响迁移效果。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点。
我国人口迁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城镇化格局不完善,人口势场高低不均衡。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经济势差很大,大城市统治支配着城市布局。由于大城市存在着大的规模经济,收入较高,劳动的供给弹性也较大,导致很多人涌入到大城市中,导致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许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弱,城市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格局不完善。
障碍因素多,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迁移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障碍因素,削弱了迁移的效果。障碍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这些使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主要使城乡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无法进行优化配置,农民的资产无法正常市场化,无法依靠资产的交易、转换和流动满足其工作、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需求;迁移者无法同城市人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最基本的保障;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迁入者生活成本大,无法承担较高的房价。
迁移者自身素质低,势能小。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小,素质普遍偏差,学历较低,掌握的技能偏少,城市生存手段少而单一等问题。在他们迁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无法融入到城镇中,将来这些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往往会返回居住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管理措施
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人口势场。促进人口迁移,就要解放农村人口。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口势场,增强农村人口推力,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使城市人口势场进一步降低。工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将走向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城镇规模经济的增强、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城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镇化提业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率,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能使城镇居民收入上升,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城乡一体发展,促进经济平衡,减少城乡人口势差。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城乡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融合发展,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障碍,提高“势能”转化效果。在迁移过程中,存在了阻碍人口迁移的许多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这些制度影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制约了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的障碍因素,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素质,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增加迁移者人口势能。城镇化中,人力资本素质是能否顺利迁移的很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素质高的能顺利进入城市,获得收入也较高。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中流动人口的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提高迁移者的素质,增强其在城镇中的适应性。还要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因此,要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积极鼓励和吸引农民落户扎根城镇,努力促进农民充分、稳定、体面就业。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中小城镇,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新型城镇化要探索“就地城镇化”模式,既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又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吸引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成为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条件成熟时,可以撤县变市,甚至“强镇扩权”。
参考文献:
1.张福墀.管理造势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3.王敬贤.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励娜,尹怀庭.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
5.王德文,蔡 ,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7(4)
第9篇: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作者简介:高一飞,女,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医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医学人文学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援引广阔真实背景下的论据,从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出发,论证和归纳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第一,同源性,即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会张力和社会结构驱动;第二,直接相互作用,即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会增加具体情境的艾滋病风险、社会易感性和脆弱性;第三,更微妙的间接相互影响与联系,即二者相互交织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应分别反作用于艾滋病防治与人口流动问题。
关键词:人口流动;艾滋病传播;医学人类学;社会医学
中图分类号:C913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089-06
关于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类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人口流动推动了艾滋病传播,流动的人口既是有更大机会接触传染源的易感人群,也是流动的传染源。[1](P259~267)其指导下的艾滋病防治实践虽然产生了短期的效果,但被认为无法触及和改善促成艾滋病传播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2](P177~185)在长期内更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果。另一类观点,试图从其他视角寻找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双向和复杂关系。比如,迁移性务工者更有机会接触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工具及公共卫生服务,有利于降低感染风险。[3](P753~754)艾滋病感染也可能导致人口流动,得知自己患病后,身处异乡的感染者或病人往往希望回到家乡度过临终阶段。[3]这些事实提示,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联系比单纯因果关系更复杂,但由于观点分散、证据零散,这类观点获得的关注不多,没能对艾滋病防治实践产生切实影响。本文从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出发,尝试寻找一种有较强解释力和实践意义的分析框架,尽量全面地理解、探究和审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
一、人口流动与艾滋病 “形影相随”的原因
如果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分别视为两个社会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场域中去理解,就会发现二者受到相似的社会张力影响。
(一)艾滋病是“获得性权力缺乏综合征”和“获得性金钱缺乏综合征”
1. 世界体系内的“获得性权力缺乏综合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球3500多万感染者和病人,超过90%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约70%的感染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年来,95%的新增感染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4]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艾滋病流行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不无关系。它们大部分有被殖民的历史,民族独立之后经济上和政治上仍极度依附欧美。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以时断时续的局部冲突为主要特征的“低强度战争”被认为是推高当地艾滋病风险的重要诱因。[5]战争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彻底摧毁公共基础设施,造成武装力量频繁穿越居民区、匪盗横行、大规模难民迁徙、强行征兵、乡村普遍凋敝等社会动荡,增加了商业性和多性伴的发生。同时,由于医疗卫生服务瘫痪,艾滋病预防知识和干预无法到位,性传播疾病蔓延,大大增加了感染风险。[6](P443~456)除了前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以外,以美国和西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挑起低强度战争的反叛势力的主要政治和经济支持,为的是促进它们在南非大陆和世界体系中政治目的的实现。
再以除古巴以外的加勒比海地区为例,这里是仅次于非洲的最为严重的艾滋病传播地区。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多巴哥、巴哈马等国家自15世纪起就是西方殖民者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中心之一。由于农业被摧毁、资源被耗尽,这一地区经济结构脆弱,民族独立后,仍处在一系列新殖民主义政策压迫下,最终沦为欧美人的廉价休闲胜地。大批破产农民从农村涌向城市,不得不以向游客提供商业性为生。流行病学报告表明,艾滋病病毒正是通过旅游业从美国传入专为欧美游客提供服务的红灯区,[7](P261)并因当地缺乏有力的疾病预防与控制系统而迅速蔓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艾滋病肆虐是国际和世界体系中政治、经济霸权的直接后果与反映。在国际政治中缺乏政治经济权力是艾滋病在当地蔓延的推手,艾滋病也是“获得性权力缺乏综合征”。[8]
2. 局部地区的“获得性金钱缺乏综合征”
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来看,也是社会底层的最贫困人群和社区首先受到艾滋病侵害。
以中国为例,1989年国内首例艾滋病病例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少数民族聚集的云南省西部偏远地区,此后大部分新增感染都出现在云南、广西、四川等西部不发达省份。2004年,又在河南、安徽等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发现了大批因既往非法卖血感染的农村贫困人口。[8]截止到2011年,中国758%的感染者集中在云南、广西、河南、四川、新疆和广东省,其中前5省均为经济欠发达省份,从感染的比例来看,受害最严重的是少数民族、农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10]这样的分布绝非偶然,研究发现,无论是少数民族地区静脉吸毒传播、城市商业性传播,还是非法卖血传播,贫困所致的艾滋病高危行为是最显著原因。[8] [11][12][13][14]
在美国,城市贫民区和少数族裔聚居区是艾滋病高发地。研究者分析纽约艾滋病分布情况发现,社会政策改变(如,公共服务的撤销)所引起的贫民区社会组织丧失是艾滋病高发的主要原因,这个过程被称为“城市荒漠化(urban desertification)”,指的是由于歧视性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中形成有如荒漠一般,政治和经济上极度匮乏的公共服务覆盖“盲区”[15](P801~813)(Wallace,1990)。美国的少数族裔社区(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常常面临贫穷、高失业率、无家可归、拥挤居住、营养不良、有毒环境、基础设施老化、卫生保健不均等威胁健康的状况,艾滋病也是其中之一。仅占美国总人口28%左右的非洲裔和拉丁裔人口,却构成了近一半确诊的艾滋病感染。[16]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17]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18]、移民和少数族裔[19](P72~114)、街头流浪儿童[20](P294~311)往往最先受到艾滋病风险威胁。他们中有的因贫困和缺乏其他生存技能而不得不从事高风险职业,有的因缺乏受教育机会、处于劣势地位而没有自我保护知识和能力,有的由于政策性歧视处于公共健康服务覆盖之外,还有的受社会歧视和排斥。社会经济地位低微是形成他们易感性的直接原因。在一个社会中,艾滋病是一种源于社会经济弱势的疾病,是“获得性收入缺乏综合征”。[21]
(二)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流动
自愿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根本动因就是追求生活条件的改善。[22]流入地(或目的地)的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形成“拉力”;流出地(或故乡)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形成“推力”,[23](P47~57)一拉一推两股力量驱动了所有的人口流动。经济发展不均衡及贫困所形成的推拉作用尤为普遍和显著。
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为例。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日益加大,[24]农村凋敝和贫困日益突出,[25]农村人口为了寻求收入更高、更体面的就业机会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极为普遍。中国的农民工大潮就是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开端,伴随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放开,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务工的潮流。中国的主要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民工流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农业收入太低。[26]由于耕地面积不足,农业收入得不到基本保障,据统计,全国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27](P2)再加上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农业人口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较城市人口偏低,一般城镇居民实际收入至少是农村居民的35倍以上,经济发达大城市和经济特区与农村收入差异甚至高达5-10倍。[28]经济因素的强大驱动还明显体现在人口流向上,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是超过2/3的跨省流动者的故乡,而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福建等东南部经济发达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吸纳了超过2/3的跨省流动人口。[29]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务工确实改善了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一部分农民工甚至在故乡获得了中上层社会地位。[30]然而,他们在城市社会仍处于最底层。[31]
分别审视人口流动和艾滋病传播两个现象,就会发现,它们的根源于且反映着相同的社会关系的“疾病”。所以,二者虽然看上去“形影相随”,却不是“形(原因)”与“影(结果)”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影”――都是类似的社会问题所投射的阴影。也因此,人口流动和艾滋病的传播常常同时发生,并被同时观察到。
二、当艾滋病传播遇上人口流动
(一)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意味着艾滋病传播
认为人口流动推动艾滋病传播的观点,其实是认为流动者直接参与了艾滋病病毒传播。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流动者输入地――他们的主要生活和务工地,应该观察到更高的艾滋病感染率。同时,流动者输出地的艾滋病感染也应该是由返乡的外出务工者“带回来”的。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和世界其他地方类似,中国疫情感染情况最为严重的云南、四川、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份,均为流动务工人员的主要输出地。[10]在劳工力大量输出的非洲农村,调研夫妻感染状况不一致(只有一方感染)的家庭,发现1/3的家庭是留守的农村妇女首先感染了艾滋病,而他们外出务工的丈夫还没有感染。[32](P2245~2252)男性外出务工者的妻子由于与伴侣长期分离,缺乏社会的、性的、经济的、情感的支持,而寻求短暂或者长期的婚外伴侣,是导致感染的主要原因。[33](P570~575)
人口流动现象确实可作为艾滋病风险警示信号之一,但并不是因为流动本身导致了艾滋病传播,而是因为促成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动因也会推动艾滋病传播。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相对弱势的群体,企图通过流动和迁移改变劣势、改善生活状况。“推、拉”他们流动的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同时也是增加和影响社会中艾滋病传播风险的因素。
(二)流动过程的情境因素加剧了社会易感性
人口流动和艾滋病传播之间也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多层面情境因素加剧了艾滋病社会易感性和脆弱性。[5][34](P65~80)[35](P142~151)[36](P1297~1307)
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来看,流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在输入地的社会缺乏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无法在公共服务决策中表达诉求,所能享受的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差、覆盖少,是社会中艾滋病病毒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从中观的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流动者远离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环境,脱离了熟悉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和约束体系,输入地对其而言又缺乏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社会控制和家庭控制对行为的约束锐减,客观上增加了高危行为发生的可能。[37](P1098~1101)同时,由于缺少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流动者缺乏社会心理资源来应对流动过程和输入地歧视性政治经济环境所造成的特殊生活压力,非常脆弱。从微观的个人层面来看,艰辛的流动过程使人面临一系列迫切且关乎生存的挑战、威胁和压力,容易产生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情境。首先,生活不稳定、与伴侣长期分离增加了发生婚外、商业性和更换性伴的可能性。[38]其次,相较食不果腹、工作朝不保夕、生存和生活条件艰苦、急性病痛等,艾滋病在流动者的生活中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倾向于低估或忽略生活中的艾滋病风险。[39]另外,一部分流动者采取酗酒、吸毒和其他高风险来缓解巨大生活压力,减轻窘境和忧虑,逃避孤独、压抑和社会孤立。[40]
(三)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交织产生的社会效应
艾滋病的传播涉及超出个人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复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它常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演化出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被称为“艾滋综合病(AIDS syngermic)”。[41](P931~948)艾滋病与人口流动问题的相遇也产生了一系列“化学反应”,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1. 放大驱动性社会张力
人口流动和艾滋病传播不仅受到共同或类似的不平等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所驱动,而且还能合力加强这些驱动性社会张力。人口流动虽然改善了流动者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但流动者在输入地又形成新的弱势群体,成为艾滋病的潜在侵害对象。感染艾滋病又导致因病致贫、歧视与羞辱、社会责难,加重了感染者和病人的弱势、恶化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相遇会启动所谓的恶性“累积因果循环过程”,[42]具有循环放大驱动二者的社会张力的倾向。
2. 产生制度性误解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同时发生容易导致制度性误解――把人口流动归结为艾滋病传播的推动因素,这是一种简单且方便的做法。一方面,如果忽略社会文化因素,单纯从生物医学视角看,有流动者作为载体,能促进病毒的散播,这一观点虽不正确,但简单、直接、便于理解,被广泛接受。制度性误解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将传播艾滋病的罪责归咎于流动者,恰迎合了人们把与自己生活方式相异的“他者”“外来者”作为危险代名词的思维习惯。[43]这种轻而易举的、看似“合情合理”的制度性误解会产生严重后果,会使艾滋病防治实践方向偏离、效果减弱,且会加剧对流动者的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一方面,制度性误解把流动者看作是传播艾滋病主体,防治干预就会针对流动者,专注阻隔艾滋病传播的生物医学路径。尽管能产生一定短期效果,但由于忽略了驱动性社会的结构因素,以及流动过程中造成脆弱性和社会易感性的具体情境,很难达成长久、切实的防治效果。另一方面,制度性误解会导致“贴标签”行为,流动者被贴上“高危人群”“病毒携带者”等标签,让本已倍受污名化和社会歧视的他们,[44]无辜背负与艾滋病相关的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等污名。这些既加深了社会对流动者的隔离与歧视,同时又将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对待“合法化”“合理化”,让其边缘地位进一步恶化、固化。
3. 增加艾滋病防治的难度
纵向来看,流动的多阶段性使防治变得复杂。人口流动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在地域上较分散的四个阶段:输出地(source)、中程(transit)、输入地(destination)、回流(return)。每个阶段的具体风险、脆弱性和社会易感性都有差别,如,输出地留守人口的社会支持真空、流动中程的风险情境、输入地的社会排斥、回流带动的性关系网络变化等。需要针对各阶段的特点来合理规划干预措施和分配防治资源,进行综合覆盖。横向来看,流动人口的内部多样性增加了防治难度。流动者和迁移务工者内部非常多样,由于从业特点、生活方式、性别比例、年龄结构、职业安全等区别,运输业工人、矿工、建筑工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人、家政服务员、非正规行业(包括行业)从业者、农业雇工、难民和国内流民等群体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和脆弱性的强度、种类都有很大差异。[45]要想实现经济而有效的干预,必须有区别、有针对、有侧重地开展防治。
三、启示与讨论
综上所述,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是多维的、多元的、多层次的。二者之间至少存在如图所示的三种关系。
第一种是同源性。由于在根本上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会张力和社会结构所驱动,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经常同时发生且并存于同一社会环境中。同源性的启示在于,无论面对艾滋病传播问题,还是与人口流动相关的社会问题,抑或同时面对二者,秉持整体观,从根源上解决驱动它们的结构与张力,能达到事半功倍、一举多得的效果。这种长远的、战略性的干预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速效,却是从源头缓解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二种是在具体情境中的直接相互作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会增加具体情境中的风险,加剧艾滋病社会易感性和脆弱性。这种关系提示,在进行应对和处理时,应在具体情境中识别充当“催化剂”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打破二者发生直接作用的机制,消除对彼此的负面影响。
第三种是微妙的间接相互影响与联系。这种关系通常存在于它们相互交织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应中。其中,较为明显的联系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合力再生产对它们具有驱动性的社会张力,并通过这种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对彼此产生间接的加强和推动。在实践中阻断和扭转这种恶行累积循环是防止问题恶化的关键。另外,更为复杂和微妙的联系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相遇产生的社会效应反过来作用于艾滋病问题与人口流动问题本身,让解决和应对更加困难。制度性误解会加深对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流动过程的纵向多阶段性和流动者的横向多元性使防治艾滋病变得更复杂。因此,当二者相遇时,社会政策须具有前瞻性和敏感性,注意预防或应对这种微妙联系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1] Prothero, R. 1977. Disease and human mobil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6.
[2]Anderson, A. F., Z. Qingsi, X. Hua, and B. Jianfeng, 2003.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potential for HIV transmission: a social behavioural perspective [J].AIDS Care, 15(2).
[3]Richard, G.W. 2003. Commentary: What can we make of an association betwee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prevalence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2.
[4]UNAIDS, 2013. HIV estimates with uncertainty bounds [R]. .
[5]Baldo,M. and A. Carbal, 1991. Low Intensity Wars and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HIV Transmission: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to Guide Research and Control of the HIV/AIDS Pandemic [A]. In Action on AIDS in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 Committee for Health in Southern Africa.
[6]Henry, D. 2005. The legacy of the Tank: The violence of peace [J]. Anthropology Quarterly, 78(2) .
[7]Farmer, P. 1992. AIDS and Accusation: 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 [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翁乃群. 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J].社会学研究, 2003, (5).
[9]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 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 [R] .2007.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 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R].2011. .
[11]潘绥铭.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12]潘绥铭. 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13]景军, 唐丽霞, 赵红心,等. 艾滋病与中国扶贫工作[OL]. 2002. http:///docsn/shxx/site/thaids/renwen/word/5.doc.
[14]景军. 艾滋病与乡土中国[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5, (2).
[15]Wallacek R. 1990. Urban Desertification,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Order: “Planned Shrinkage,” Violent Death, Substance Abuse and AIDS in Bronx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1.
[16]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1990. HIV/AIDS Surveillance: U.S. AIDS Cases Reported through July 1990 [R]. Atlanta: AIDS Program,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17]McGrath, J.W., D.A. Schumann, , Pearson-Marks, J., Rwabukwali, C.B., Mukasa, R., Namande, B., Nakayiwa, S. and Nakyobe, L., 1992.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Sexual Risk Behavior for AIDS among Baganda Women [J]. Medical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2).
[18] Symonds, P.V. 1998.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Logics of HIV/AIDS among the Hmong in Northern Thailand [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IDS, Merrill Singer ed.: 205-226. Amityville, New York: Baywood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Singer, M., C. Flores, L. Davison, G. Bruke, Z. Castillo, K. Scanlon and M. Rivera, 1990. SIDA: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AIDS among Latinos [J]. Medical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4(1).
[20]Lockhart, C. 2002. Kunyenga, “Real Sex,” and survival:Assessing the Risk of HIV Infection among Urban Street Boys in Tanzania [J].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6(3).
[21]Schoepf, B.G. 2001. International AIDS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risis [A].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Bogue, D.J. 1969.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M]. New York and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23]Lee, E.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J]. Demography, 3(1).
[24]Todaro, M. 197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ory, evidence,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M].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5]Mortuza, S.A. 1992.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Causes and effects [M]. Berlin: Berlin University Press.
[26]蔡, 都阳.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A]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经济社会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7]史柏年,等. 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8]高洪. 地区发展差距拉动: 我国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3, (2).
[2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30]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 1996, (4).
[31]赫广义.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32]Lurie, M.N., B.G. Williams, K. Zuma, D. Mkaya-Mwamburi, G. P. Garnett, M. D. Sweat, J. Gittelsohn, and S.S.A. Karim, 2003. Who infects whom? HIV-1 concordance and discordance among migrant and non-migrant couples in South Africa [J]. AIDS,17 (15).
[33]Nicolosi, A., M.L.C. Leite, M. Musicco, C. Arici, G. Gavazzeni and A. Lassarin, 1994. The efficiency of male-to-female and female-to-male sexu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 study of 730 stable couples [J]. Epidemiology, 5.
[34]Smith, C.J. 2005. Social geography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 China: Exploring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J].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6(1).
[35]Smith-Estelle, A. and S. Gruskin, 2003. Vulnerability to HIV/STIs among Rural Women from Migrant Communities in Nepal: A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Framework [J].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11(22).
[36]Soskolne, V. and R.A. Shtarkshall, 2002. Migration and HIV prevention programmes: linking structural factors, culture, and individual behaviour―an Israeli experience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
[37]Barnett, T., A. Whiteside,?and?J. Decosas, 2000. The Jaipur paradig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susceptibil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HIV [J].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 90(11).
[38]周盛平. 呼唤阳光――你不了解的艾滋病群落[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7.
[39]高一飞. 滇西某大型筑路工地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分析[J]. 人口研究, 2010, (2).
[40]骆华国, 莫国芳, 吴瑛. 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理论分析[J]. 思想战线, 2002, (2).
[41]Singer, M. 1994. AIDS and Health Crisis of the Urban Poor: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Medical Anthropology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9.
[42]Myrdal, G.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M].New York: Harper.
[43]刘有安. 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44]李建新, 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J]. 社会科学, 2009, (9).
[45]UNAIDS-IOM, 2003. Mobile Population and HIV/AIDS: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Region [M]. IOM-UNAIDS Reports on Mobile Population and HIV/AIDS, Vol.1., Geneva: IO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HIV/AIDS
GAO Yi-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510515, Guangzhou, China)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