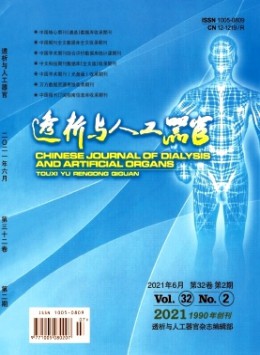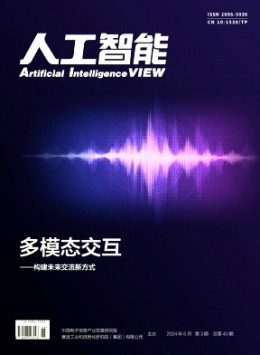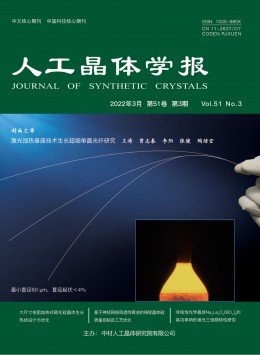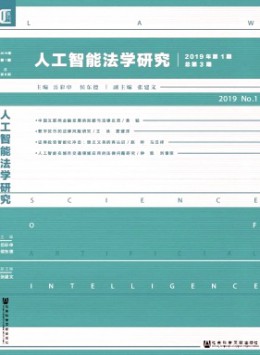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的好处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的好处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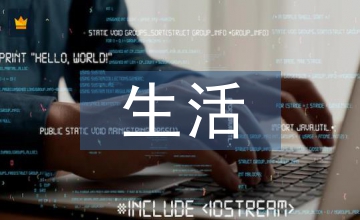
第1篇: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的好处范文
微信刚推出之时,很多人并未看出它与QQ的区分,认为只是多了一个语音会话功能罢了。与微博相比,微信的优势也不那么明显,朋友圈的发发帖子,怎么比得上各位大V的神神叨叨?马化腾是在玩双手互搏么?
然而,2013年10月24日,腾讯微信惊艳于天下,其户数量已经超过了6亿,每日活跃用户1亿。与此同时,微信海外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1亿名。
微信胜在何处?如果说微博走的是大众传播路线,微信走的则是社交直行路线。前者陷入了信息的大海,后者则充分让人在亲友圈里找到被关注被认同的喜大普奔。
再加上与内容提供商、新技术的无缝嫁接,微信更加无敌。由于许多有先见之明的传统老字号,纷纷转战微信平台,微信无形中,多了好多免费资源。微信还可以用来定位、打车、扫二维码买饮料、登录社区青年汇、团购低价电影票。风起云涌之势未成,却隐隐然,有秋风,起于青萍之末。
连社交网站的霸主Facebook也受到了冲击。11月,Facebook首席财务官戴维忧心忡忡地宣布:十几岁的青少年,在这个沟通平台上的活跃程度正在下降。对30个国家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后,Facebook发现,孩子们选择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服务。
看,这不仅是新旧媒体之争,连社交世界内部,也开始了相互扑杀。唯一可以肯定的一个趋势是:谁抓住了青少年的口味和消费style,谁就hold住未来。
余额宝
你的积蓄,还放在银行?那你就OUT了。马云新推出的余额宝拉开了互联网金融改革的序幕。余额宝,又称会赚钱的支付宝,用户通过把资金存入余额宝,可以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余额宝内的资金还能用于淘宝网上购物、支付宝转账等支付功能。可谓一举多得。转入余额宝的资金在第二个工作日由基金公司进行份额确认,对已确认的份额会开始计算收益,充分盘活了资金。
从开办淘宝以来,马云跨过前行路上大大小小的坎儿,创造了互联网经济的奇迹和电子商务的中国模式。余额宝,只是他又一次穿越“音障”之举罢了。2013年“双十一”当天,淘宝当天销售额突破350亿,其中,多少通过余额宝转账、支付,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未来是,这一理财+储蓄+支付模式,将来会吸引更多的小年轻,也将成为更大的蓄水池。
新能源
新能源这一词汇由来已久,但最近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却代表了这个概念正在获得的认同。2013年11月27日,页岩气概念股再度爆发,其中恒泰艾普(300157)开盘不到1小时便告涨停,据悉,这是由于重庆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进展,中石化涪陵焦石坝页岩气田日产能已突破150万立方米,今年可能形成5亿立方米产能,2015年总产能有望达到50亿立方米,2017年总产能有望达到100亿立方米。
页岩气是新能源界的新宠之一。由于与常规天然气相比,页岩气开发具有开采寿命长和生产周期长的优点,它正在成为搅动世界市场的力量。有“博弈改变者”之称。其迅猛发展,将改写世界的能源格局。
借新能源消除旧能源的垄断,是业界正兴起的破冰之举。如北京市最近尝试推出的电动汽车,就是对传统能耗汽车的突围。由于以车载电源为主要驱动力,对环境影响相对传统汽车较小,电动汽车的前景被广泛看好。北京市科委目前正力推电动汽车不参加摇号即可上路。
以页岩气和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寄托了消费者的无限期待。
3D打印
让我们假设一个诡异的情况。胳膊断掉之后,你可以做什么?
以下在不久的将来,将变为现实:
把断臂放在3D打印机中悬浮,打印机扫描后,打印喷头开始打印外骨骼。片刻过后,栩栩如生,几乎可以乱真的新的骨骼,重新生长于残缺的躯体。
这是科幻电影的一幕吗?
不,3D打印机出现之后,这一幕不再是梦。
这款专门制作外骨骼3D打印机是骨折患者的福音。其外骨骼材料质量轻强度大可清洗,由聚酰胺构成,并且根据患者不同情况而定制。打印机能打印出鲜活饱满的肌体。堪称打印机与生物医学最完美的结合。
尽管听起来匪夷所思,但3D打印在国外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人们可以用初级版本的3D打印机,打印出鞋子、手镯和包包。而一位自称“HaveBlue”的网友在3D设计分享网站上声称自己成功打印出手枪的部分组件,并结合真枪其他部件制作成一把枪。据HaveBlu介绍,“20英尺(约合6米)远的地方都能瞄得很准,累计射击200余次,枪身依然完好无损。”另一位3D打印的爱好者,业余枪械师迈克尔·格斯林克,则使用Stratasys3D打印机,成功打印出了AR-15步枪的下机匣。2012年10月,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工厂Shapeways在纽约开业,该工厂可容纳50台工业打印机,每年可按照消费者需求生产上千万件产品。
3D打印的原理,源于快速成形技术,它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合材料,通过逐层堆叠累积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即“积层造形法”)来生产出物品。如今,国外的珠宝、牙科、航空航天等领域,都用上了3D打印。
有些传统制造业的从业者为此变得悲观起来,他们担心制造业的被颠覆与转移。但3DRobotics公司CEO克里斯·安德森,认为3D打印机并不意味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到来,而只是推动器之一。
对年轻人来说,3D打印这四个字,则意味着无限创新与想象的可能。一个新的群体已经诞生,他们的名字叫做创客。他们也许头发蓬松,在金钱上捉襟见肘,但在新的工业革命中,这些家伙将创造了不起的未来。
大数据时代
扑面而来的滚滚资讯、避无可避的信息丛林、叫你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的信息,大数据时代仿佛在一夜间到来。
我们起初是从微博、然后是从微信上,知晓大数据的威力的。但这不是全部。大数据到底有多大?还是用数据说话:一天之中,互联网产生的全部内容可以刻满1.68亿张DVD;发出的邮件接近3000亿封之多;卖出的手机接近40万台,超过全球每天出生的婴儿数量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怎样的不同寻常的年代?如果说,以前的生活,更多的是建立在臆测、主观甚或情绪的状况下,那么现在,明确的标的物,参考系,出现了。以数据和以事实为准绳,显然比想当然的臆测,靠谱得多。
数据(包括文本、文字)为决策提供了依据。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那些商家们。沃尔玛曾经通过对交易记录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得出了消费者的消费倾好,并明智地在飓风天气来临之前,将手电筒与蛋挞放在一起,这两样商品的销量果然大增。
几乎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从大数据带来的量化分析中受益。券商可以通过分析众情绪抛售股票;投资机构搜集并分析上市企业声明,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医院、疾控中心、卫生部门,依据数据记录,分析疫病的传播状况;而政治家则可根据微博,分析舆情,决定竞选策略、施政纲领。
更多改变的正待开启,谷歌、苹果、亚马逊、TWITTER,年轻的创业者们正是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以及提供这份平台的重要性,推动自己走向成功。
对于那些年轻的网友来说,如果你知道自己留下的每一点痕迹,都可能被索引、被追踪,也许,对大数据时代也就有了另一个层面的认知,对一言一行哪怕是虚拟空间的,也就有了更深的警醒。
在线教育
自从小龙女龚海燕卖掉别墅,并把第二次创业的秒针对准“在线教育”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教育的又一轮变革或许悄没声地孕育了。龚只是嗅到敏锐的“狩猎者”之一。
早期,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局限于封闭性的大学、数十年不变的课程与老师,而一出围墙,即无心无时向学。校园啊,老师啊,一毕业就沙扬娜拉了。
自从哈佛公开课之幸福课被搬上网之后,我们才且惊且喜地发现:课,可以这样上。哈佛课,可以一线之隔。
“慕课”,是最新的在线教育模式之一。“慕课”,MOOC,“M”代表Massive,一门MOOC最多可达16万人;第一个“O”代表Open(开放),以兴趣导向,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不分国籍;第三个字母“O”代表第二个Online(在线),学习在网上完成,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C”代表Course,就是课程的意思。开放,降低门槛,分享、协作与传播,也符合教育的本义。“有教无类”,“敏而好学”,“学而时习之”,2000多年的孔子教育思想,仿佛也印证在今天的在线教育中。
《终结者3》里,阿诺德·施瓦辛格为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机器世界:由人亲手打造的智能机器,最终企图毁灭人类。人为生存与繁衍殊死一搏。
科幻电影总有如巫师般的咒怨与预言。当然,它遥遥领先于我们身处的时代。尽管有隐忧,现在的机器人“对手”显然还远远没有到颠覆人类的境地。人类,也继续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乐此不疲。
“深蓝”电脑击败了人类的世界国际象棋冠军,是人工智能的完美表现之一。1991年,美国军方则通过导弹系统和预警系统方面的运用,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军事方面的威力。苹果机和IBM的一些机器,也巧妙地介入人工智能的应用,如语音识别和文字识别。
“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甚至拥有人一样的智慧”,一代代人工智能科学家为此梦寐以求。一旦机器能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模拟人的思考,世界将会怎样?这种异想天开,使人工智能从一发端就处于计算机科学的前沿。
在我国,人工智能受重视日益倍增,并牢牢与实际应用、创新科技绑定。在2013年于安徽合肥举行的中国机器人大赛中,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等在内的206所高校参加角逐,最终西北工业大学在机器人舞蹈、救援、仿真机器人、家庭机器人、竞速机器人等项目的比赛中获得全国冠军七项,亚军两项,季军五项。而在上海,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科研团队通过沙粒尺度新型传感器技术、无线传感网络与传输技术、沙基机器人技术、沙漠新能源技术等一系列智能沙漠技术,形成一张可移动的无线传感网,形成了预测预报沙尘暴的有力机制,有利于缓解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的严峻形势。青年群体,成为推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生力军。
闭着眼睛也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智能机器可能继续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物联网
“把所有物品通过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用这样一句话,大概可对物联网做出一个浅显的说明。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对物联网的概念,做出天才而形象的描绘与预测:
用户遗失或遭窃的照相机将自动发回信息,告诉用户它现在所处的具置,甚至当它已经身处不同的城市。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零花钱,您可以从电脑钱包中给他转账5美元。此外,当您驾车驶过机场大门时,电脑钱包将会与机场购票系统连接,检验您是否购买了机票。
如果您计划购买一台冰箱,您将不用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推销员唠叨,因为电子公告板上有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价信息。
万物通过互联网连接。而不仅仅是信息和数据。互联网时代的2.0版。这就是物联网时代的全新意义。
如果对此还存在混沌不清,看看智能家居的应用也许我们就可以管窥物联网的内涵与奥秘:传统开关,也许你要依靠“纯手工”才能完成对电源的控制。但借助智能开关,你可以实现对家庭灯光的感光控制以及任意环境氛围和灯光场景的智能切换。
在安徽亳州涡阳县陈大镇禾景农业园区,物联网的运用更是到了极致。这里的大棚,安设有摄像头、“小黑匣子”、电线,它们构成一套灵敏的传感器,源源不断地把植物的各类信息传送到互联网上,如植物的温湿度、光照、化学条件等。由此,可以更有力地对植物的生长进行精确控制。农民看看屏幕就可以知道蔬菜大棚温度水分是否合适,动动鼠标就能给蔬菜浇水、施肥、打药,刷一下二维码就能知道它们从田间地头到卖场的全部信息农业物联网的运用,使这儿的作物产量提高40%,价格也提高了一倍。
预计到2020年全球会有200亿~500亿个IOT节点,更会由物联网应用催生80亿美元以上的商机。ARM商业及全球市场开发执行副总裁Antoni表示,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将使人与人、装置对装置、人对装置彼此之间的连接能力更富智慧化,并让每一个层级的连接更为紧密,“经由技术来缩短整个世界距离,虽是老生常谈,但这的确是现今与未来都必须共同实现的目标”。
太空探索
人类探索太空的雄心永无止境。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局)最近的一项计划,是这雄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学生、承包商以及志愿者组成的“月球植物生长栖息地”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咖啡罐大小的密封罐用于盛放植物种子,配上传感器、摄像头等可将信息传回地球的设备。这个密封罐有可能通过商业太空船被送上月球。一旦植物在月球上生长,那么,地球上的人类,将通过传感器了解生命在异类环境下如何生存,为下一步的太空探索打下基础。
在我国,2013年6月11日,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从酒泉卫星中心发射升空。与“天宫一号”实现两次交会对接,并成功完成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5个太空实验。近8万所学校、6000万名学生,目睹了这次太空授课。通向未来的太空探索之路,也许就此在小小童心中萌芽。
根据中国空间站的计划部署,我国将在2020年前后将建成规模较大、长期有人参与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智能电视的崛起
从2010开始崛起的视频之风,已经给传统电视媒体带来沉重打击,土豆、搜狐、优酷,个个不遑多让。但这只是第一波。新一轮攻势,又将袭来。这次的兵团,来自智能电视。
据目前市场研究机构的预测,至2014年,智能电视的出货量将达到1.23亿台,迎来爆炸式增长。三星、松下和LG等将成为智能电视角逐的大鳄。不过,最令消费者们期待的是苹果iTV的中坚力量。据说,苹果与时代华纳有线签订了合作协议,后者将为苹果设备提供电视内容。
智能电视将深受那些青年消费者的欢迎。他们希望的是更鲜活的电视内容而不是刻板的“老调长谈”。一键控制乾坤等更机动的掌控屏幕的方式,也令他们有真正做主人的感觉。
第2篇: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的好处范文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说过:“友谊是令世界团结的唯一胶合剂。”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胶合剂是否已经在快节奏、高科技、城市化的生活中失去了效力?
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中看出许多端倪。根据这项调查,在1985年至2004年之间,美国公民的好友(即有难时可以向他求助的朋友)人数从3个下降到了2个,而没有朋友可以吐露心事的人所占比例却从8%上升到了23%。在英国,独居的人数不断上升,社区的纽带也因为居民的频繁搬迁而削弱,这都造成了友谊濒临崩溃的“危机”。也有研究将社会孤立与互联网和手机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新技术虽然的确可能改变了传统的友谊,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它们对友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Facebook 2004年在哈佛创立的时候,目的是为了丰富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今天的用户也依然在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它。微软的高级研究员黛娜·波伊德(Danah Boyd)指出:“上网者的动机和以前并无不同——他们在网上交友,同样是为了有人能给自己情绪支持,能聊聊八卦,调调情,或者只是陪陪自己。”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还是那么几个,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最常和我们交流的人都是他们。“只是交友的方式变了,因为有了新的技术,也因为当代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文化。”
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我们持续交往的人数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普通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从2006年的137个上升到了2009年的440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发现,今天的典型美国青少年在Facebook上有大约300个朋友,在twitter上也有79名关注者——但这些人并不全是社交人脉,因为他们未必会反过来关注这些青少年。
这个数字已经大大超过了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演化心理学家)的计算——他认为我们的大脑受演化所限,能够应付的“真朋友”(meaningful friends)最多只有150个(参见《够聪明才会交朋友》)。这些多出来的人都是谁呢?他们都是所谓的“弱人脉”(weak ties),包括中学和大学阶段的朋友,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从前的伴侣,旅行中的相识,关系一般的熟人,朋友的朋友,有时还包括陌生人。社交网络使我们能和这些外围的友人保持联系——偶尔发发消息、看看他们的照片或状态更新之类。换作以前,我们在分手后就不会再和他们联系了。
社交网络扩展了我们的社交圈,原本那些分开之后不会再保持联系的所谓“弱人脉”,现在也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保持联络。
但是技术的功用还不止于此。最新的研究显示,Facebook甚至还能够改善那些远程友谊或脆弱友谊的质量。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杰西卡·维塔克(Jessica Vitak)对400多名Facebook用户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Facebook对于居住地间隔超过几小时车程的朋友特别有价值。友人之间住得越远,他们在Facebook上的交流就越是密切。维塔克指出,对这些朋友而言,Facebook或许就是一段记忆中的友谊和一段实实在在的友谊的区别所在。
与其他人在网上交流,比如在Facebook上回答问题或是祝别人生日快乐,在LinkedIn上称赞别人的技能,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下方留下“喜欢”或是评论,都是一种社会理毛行为,是我们祖先习惯的现代重演。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妮可·艾利森(Nicole Ellison)指出:“这些都是在表示我对你的关注。就像灵长类动物互相捉虱子,我们也期望自己的示好能得到回应——也就期望在将来也能得到对方的关注。”
艾利森和维塔克发现,脸书上的社会理毛行为对弱人脉的维持十分有效,而我们也的确有许多理由来维持这些人脉。那些体现重要关系的深切情绪纽带仍然需要面对面地培养,哪怕这些纽带是在网上产生的。不过弱人脉也自有其好处,这些人脉往往五花八门,并且分散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之中。他们可以提供新的看法观点,激励创新,带来工作机会,还能让你产生在社群之中的归属感。
要说明社交网络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我们会轻易地感染不怎么认识的人的情绪。这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相当常见——有人对你微笑,你也朝他微笑。但是在互联网上,这个感染效应就会成倍地放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领导的一个团队,分析了Facebook上的10亿多条更新,结果发现用户会不自觉地在自己写下的评论中传播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受众中甚至有居住在不同城市的朋友和熟人——也就是他们的弱人脉[参见《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第9卷,e90315页]。“在网络世界里,大规模的情绪感染是不久之前才成为可能的。”福勒说,“我认为将来还会发生更多全球情绪同步的情况。现在,我们和世人的同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高科技时代的社交网络,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友谊。图片来源:《新科学家》
人之所见,人之所为
人类的其他行为也会在网络上传播,包括喝酒、吃饭、还有节食的习惯,不过这些行为几乎完全是在强人脉——也就是好友和家人之间传播的。福勒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投票也是如此。
2010年11月2日是美国国会选举的日子,那一天,福勒的团队在6100万美国Facebook用户的信息流里了一则消息,敦促他们前去投票,并允许他们将自己的投票意愿在朋友圈里广播。结果,有大约6万名本来无意投票的人改变了主意,还带动了他们在Facebook上的28万名友人。研究者对这28万名投票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那6万名收到消息的用户的好友[参见《自然》(Nature),486卷,295页]。
福勒指出:“最要好的10个朋友促成了这场社会运动。这证明,如果想在人群中扩散某个行为,你就必须着眼于现实世界中的人际网络。这个发现非常激动人心,因为它开辟了利用网络世界改善现实世界的可能。”
友谊的形式显然已经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变化,但这变化究竟是好是坏,现在还在热烈的讨论之中。有研究显示,在网上与人交流的心理学价值和在现实中与人交流是一样的,都能减少焦虑和抑郁,并增加幸福感。在Facebook公司研究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莫伊拉·伯克(Moira Burke)发现,用户越是利用Facebook主动和朋友交往,他们就越是不会感到寂寞。不过,究竟是使用Facebook降低了寂寞感,还是本来就善于社交的人更多地使用Facebook,其中的因果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在网上维系友谊也有不少风险。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蕾切尔·格里夫(Rachel Grieve)指出:“由于电子通信的本质所限,人际交往中的种种细微之处可能在网上遗失。本来在喝咖啡时和朋友随口说的一句话,就算朋友误解也能及时澄清。可是一旦到了网上,那句话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许多人都会看到,并产生误会。”
此外还有一些更加微妙的风险。正如波伊德在她的著作《这很复杂》(It’s Complicated)中指出的,青少年如果和每一个旧熟人都保持往来,在进入大学之后就会难以建立新的、深入的人际关系。她说:“他们在第一个学期往往不太适应,于是都到过去认识的友邻那里去寻求安慰了。”
自恋还是需要?
对现代社交网络最严重的指摘,是说它助长了自恋和孤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发育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说:“情绪表达现在成了公共事件。”她还引用美国州立圣迭戈大学珍·特温奇(Jean Twenge)的研究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大学生在自恋特质上的得分就节节攀升。另有研究显示,自恋的人往往也是Facebook和twitter的积极使用者,而这两个网站都特别适合自我标榜。
但是也有人对此比较怀疑。新的研究显示,虽然常有人指责今天的大学生是最自我中心的群体,但是他们的自恋和他们对Facebook的使用之间并没有联系[参见《计算机与人类行为》(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第32卷,212页]。波伊德主张,学生们热衷使用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他们我行我素或者迷恋技术,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友情。“我采访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一次次地告诉我,他们宁愿在现实中和彼此见面,一起跨上自行车,不受拘束地出去游玩。但由于社会散播了大量关于陌生人的恐怖信息,这些年轻人已经很难在网络之外的地方见面交往了。”
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是迫切的,而要在今天的城市里做到这一点又是困难的。那么,我们距离跨出人类的圈子、踏入人工智能的世界还有多远呢?一个机器人又需要多么复杂,才能满足人类友情的核心需求,比如懂得回报和具备人格呢?
根据雪莉·图克尔(Sherry Turckle)在著作《一起孤单》(Alone Together)中的介绍,有些社交技术已经能够触到我们的“达尔文按钮”了。有的机器人已经能和人类目光交流、追踪人类的动作和姿势,并且留下“有人在家”的印象。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从机器人那里获得友谊。图片来源:《新科学家》
比如日本ATR智能机器和通信实验室的神田崇行(Takayuki Kanda)就开发了一个名叫“罗伯维”(Robovie)的人形机器人,它的基本交流能力已经相当成熟,足以令15岁的青少年相信它是一个具有情感的社会动物。神田表示,研究的一大难题是开发出可以随时与人为伴、而不仅仅是待在家里的机器人。据他推测,人和机器人相处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容易和它们建立“真正的关系”。
英国林肯大学的约翰·莫雷(John Morray)则主张,要造出合群的机器人,关键是要让它们犯错。莫雷和他的团队正在将人类的认知偏差引入机器人的电路,比如令它们的记忆产生故障,从而对人类的指令产生误解。“我们在试着开发不完美的机器人,也许人类会因此更加接纳它们。”他补充说,研究中的困难在于避开“诡异谷”(uncanny valley)——机器人在外形像人,行为却不怎么像人时,会尤其恐怖。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