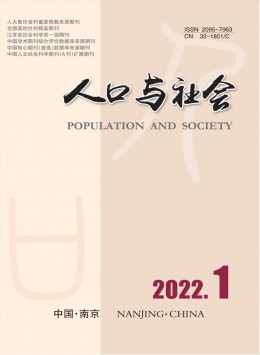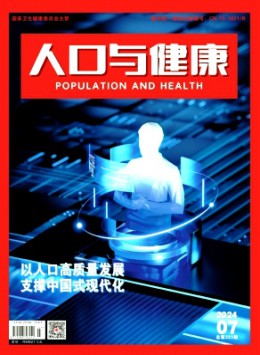人口红利的定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口红利的定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2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01-06;中图分类号:C061.2;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得到证实(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们更为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口转变结束之后,这个增长源泉(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陆D,蔡P,2014[7])?第二,在持续低生育率的老龄社会,人口变化是否还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会(World Bank,2016[8]),或者说,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带来的不利影响(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颖等,2016[10])?这两个问题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因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建民,2014)[11]。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丰厚人口红利的人口转变结束之后,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才能够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来源、结构和机制的深入认识。
一、人口红利的来源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给经济带来的一个增长源泉。有研究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1960―199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对人均产出提高的贡献率接近20%,在亚洲和欧洲这个贡献份额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一般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个体(家庭)经济行为变化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人口红利有三个直接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和劳动年人口比重提高,这种变化增强了人口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能力,进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这种“年龄结构效应”(Bloom et al.,2009)[12],也被称为“第一个人口红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美国人口经济学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个来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死亡率下降减少了劳动力的减损,而生育率下降则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仅从绝对规模上扩大了劳动供给,同时也强化了“结构效应”,使得第一个人口红利更加丰厚。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家庭面对因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变化而在决策和行为上(如储蓄、劳动供给、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被称为“行为效应”(Bloom et al.,2009)[12]。这种行为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激励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资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为父母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决策、储蓄决策和退休决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条件下,人们会主动调整自己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和风险应对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这些微观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增加储蓄、劳动力供给和对子女教育与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观层面上聚合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促进资本深化和创新。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效应”就是“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n,Lee,2004)[9]。
从来源上看,第一个人口红利与第二个人口红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个人口红利主要是一种结构效应,第二个人口红利则主要是行为效应。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也存在着行为效应,如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及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等。同样,在第二个红利中也存在着结构效应,如延迟退休可以推迟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终结时间和减缓负担比加重的速度。同时,两个人口红利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人口红利是对第一人口红利时期形成的有利条件的释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杨英,林焕荣,2013)[21],或者说,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已经蕴含了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机会。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积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是第二个人口红利期国民储蓄能力的重要基础;其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收益是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中对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再次,两个人口红利在时间上存在着一个交叠时期。由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长短取决于人口转变的速度,即人口转变的速度越快,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就越快,达到的负担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红利期就越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来说,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可以持续40多年,那些人口转变速度比较缓慢的国家的人口红利期甚至可以持续50年,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转变非常迅速的国家,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则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出生队列,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加入劳动力,他们接受了比父辈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这个人力资本增量实际上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就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从人口红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个概念,即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的生产性是基于人是生产者这一基本前提而产生的。人口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不同的人在劳动能力、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生产效率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有这些具有不同经济特质的个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产性,或者呈现出生产性的强弱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转变而带来的人口生产性的提高。其中,年龄结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可以提高人口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则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转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与人口转变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储蓄、劳动供给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的结构
人口红利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包括了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按照这个认识逻辑,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红利的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二是不同国家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做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此仅做理论上的探讨。
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是储蓄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红利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效应并非总是同时发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这种结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和发展的中期阶段,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因此,抚养比减轻导致的储蓄率提高就成为人口红利中的首要因素,因为储蓄率提高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所需的资本,而投资增长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剩余劳动力。从中国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绝大时段,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口红利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临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10)[22]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时候。
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来源主要是个人(家庭)的行为效应,因此,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更为鲜明。首先,因为每一个人(家庭)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因此,尽管每一个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行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微观行为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水平和结构。其次,相对于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第一个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的老龄化社会,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在规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劳动力的队列规模,如果要使整体劳动力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前提只有一个,即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一个队列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一个队列人口的劳动总产出并不会随着这个队列规模的缩减而成比例减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储蓄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稳定。以储蓄为例,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储蓄率提高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消费剩余,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出现了目的性储蓄,但基本上都属于短期储蓄行为。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人们的储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长的老年时期的生活做经济储备,因此是一种长期储蓄行为,这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终结?
对人口红利结构的解析和对人口红利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判断。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蔡P,2006[23];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续第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国外学者关于第一个人口红利终结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动态特征,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口红利就转变为“人口负债”(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人口红利期转变为人口负债期。也有学者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负担比”,即从有效劳动供给角度判断生产者与被负担者之间的比例关系(Mason,2007)[30]。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报告中把人口红利期的变化划分为4个阶段,或者说,把世界各国划分为4种类型:(1)处于前人口红利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4左右;(2)处于人口红利早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小于4,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3)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不快;(4)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较高并将继续提高。
国内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其中一派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王丰,2007[31];蔡P,2013[32]),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3年以来已经出现了持续减少的情况,而人口抚养比水平则持续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据分年龄的消费和生产曲线计算了有效劳动供给,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在2014年结束。还有一些学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尚在,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改革退休制度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从而延长人口红利期。另一派的观点是根据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如低于50)来判断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时限(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延续的时间更为乐观,认为它可以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远(田雪原,2006[33];刘家强,唐盛代,2007[34];陈佳鹏,2012[35])。笔者认为,以人口抚养比水平作为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标准是一种静态判断方法,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缺陷。例如,当人口抚养比的提高时,即使其仍处于50以下的区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也不可能给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判断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消失。首先,从年龄结构效应看,2012年以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2010年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结构效应)已经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条件下,生育率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不复存在,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国已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
四、第二个人口红利实现的机制
目前的中国人口和经济都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形态是人口转变的历史承继,随着第一个人口红利走向终结,第二个人口红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口红利将贯穿中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从人口红利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转变带来的第一个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和实现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丰,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人口转变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期,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国内外学者都高度重视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丰,2007[31];陈卫等,2015[39]),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红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或者说只是“数学上的红利”。对于中国而言,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全面启动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
第一,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老龄化社会,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和激励劳动力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机制。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真实地表达劳动力供求关系,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动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效应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是创造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Lee, Mason,2006)[13]。发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是中国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种激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供给激励,二是储蓄激励。这两个激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则。具有这两个激励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还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生产性,即可以有效地动员劳动供给和储蓄。只要人们在老年时期不是过分依赖公共或家庭转移支付,第二个人口红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负担比提高的不利影响(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伴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王丰,2007)[31],而资本市场是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重要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经济活动。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长期的角度看,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实现三个均衡:一是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均衡,二是劳动者的终生收入与终生消费的均衡,三是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均衡。具有这三个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和储蓄,因此是实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1]Bloom D. E.,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R].NBER Working Papers, 1997,12(3):419-455.
[2]Bloom D., Canning D.. cumulative caus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J].Population Matters, 2001:165-199.
[3]Kelley A. C., Schmidt, R. M. Evolution of recent economic-demographic modeling: a synthesis [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69,18(2):275-300.
[4]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J].中国金融论坛,2004,28(2):2-9.
[5] Lee R., Mason A.. Fertility,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10, 26(2):159-182.
[6]Gaag N. V. D., Beer J. D..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demographic burde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e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J].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4,106(1):94-109.
[7]陆D,蔡P.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3-29.
[8]World Bank. Leveraging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a world bank report [J].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2016, 42(1):155-161.
[9]Mason A., Lee R..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J].Genus,2004,62(2):11-35.
[10]王颖, 邓博文, 王建民.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产生机制及研究展望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37(2):12-20.
[11]李建民.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 [J].广东社会科学,2014(3): 5-14.
[12]Bloom D. E., Canning D., Fink G.,Finlay J. E..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9,14(2):79-101.
[13]Lee R.,Mason A. .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6,43(3):16-27.
[14]Coale A.J., Hoover E.M..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6-25.
[15]Angrist J. D., Evans W. 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exogenous variation in family siz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3):450-77.
[16] Agüero J. M., Marks M. S.. Motherhood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infertility shocks [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1,46(4):800-826.
[17]Becker G., Lewis H. G. .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84(2):279-S288.
[18]Becker G. , Tomes N. .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84(2):143-S162
[19]Acemoglu D. ,Johnson S. .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Life Expectancy on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7,115: 925-85.
[20]Bloom D. E., Canning D., Graham, B.. Longevity and life-cycle saving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05(105):319-338.
[21]杨英,林焕荣.基于理性预期的第二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J].产经评论,2013,4(2):113-125.
[22]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经济研究,2010(4): 4-13.
[23]蔡P. 人口红利终将成往事[J]. 中国社会保障,2006(3):22-23
[24]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J].人口研究, 2005(6): 21-27.
[25]刘怀宇, 马中.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J]. 人口研究, 2011(4):65-74.
[26] Ogawa, N.,Chen Qiulin. End of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ossible Labor Market Response i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J].China & World Economy,2013,21(2): 78-96.
[27]蔡P.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J].中国人口科学, 2009(1): 2-10.
[28]李稻葵, 石锦建, 金星晔.“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分析 [J].投资研究, 2015(12) :4-19.
[29]Van der Gaag N., de Beer J..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Demographic Burde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e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J].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5,106(1):94-109
[30]Mason 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Bush,2005,31(2): 81-101.
[31]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J]. 人口研究,2007, 31(6):76-83.
[32]蔡P. 人口红利拐点已现 [N].人民日报,2013,1/28.
[33]田雪原.21世纪中国发展:关注来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J].学习论坛,2006(11): 25-28.
[34]刘家强,唐代盛.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 [J].人口与发展, 2007,13(4):33-35.
[35]陈佳鹏.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内涵解读、定量分析及政策建议 [J].思想战线, 2012, 38(2):16-20.
[36]王丰, 安德鲁・梅森.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J].中国人口科学, 2006(3): 2-18.
[37]王德文,蔡P,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J].人口研究,2004,28(5):2-11.
第3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因为,在这个月里,据说有包括自定义为“中国Facebook”的人人网在内的近十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要登陆美国股市。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集中赴美挂牌的中国概念股几乎无一例外都被国内媒体围攻过,不是说亏损上市,就是指财报有疑点。似乎从美国资本市场和中国媒体两个角度,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似乎只是表面现象。那些中国概念股在上市之初就纷纷破发,其中包括人人网、世纪佳缘、网秦。
按照中国股市的逻辑,凡是没有盈利的公司,基本是没有条件上市的。但从早先的视频网站酷6网及优酷上市可以得知,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主营业务亏损上市是可行的,这似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五月份的几支中国概念股上市即破发的原因。但像世纪佳缘、网秦这样有盈利的公司,不也出现了破发的情况么,而且亏损上市的优酷网,后来股价反而涨势喜人。显然,仅仅依靠是否亏损上市来解释美国资本市场看空中国概念股是不准确的。
那么,是否因为这些中国概念股的商业模式普遍存在问题而被看空呢?似乎可以体现这种先兆的是自定义为“中国Facebook”的人人网,在上市前后,即被中美两国业内人士指认为非真正意义上的Facebook。假设这样的观点属实,那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投资者并不认为,在中国这一人口红利依旧存在的国家里,SNS网站模式能像在美国一样前途广阔。推而广之,类似世纪佳缘、网秦、凤凰网这些不同模式下的中国概念股,是否在上市后仍能够享受到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广告市场前景呢?如果美国股市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像凤凰网这一新媒体概念股,也应该会出现上市破发的情况,但实际上凤凰网在二级市场不但没有破发,股价反而表现得还很稳健。这也说明,美国资本市场看空基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商业模式的说法也不准确。
目前市面上,还有一种说法颇有市场,即中国概念股的投资人或投资银行人为做空所投资或协助IPO的中国概念股。最典型的事件是今年年初爆发的“李国庆大战大摩女事件”。事由是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在微博上埋怨IPO定价被投行人为压低,而“大摩女”则驳斥投行并没有多拿一分钱,还顺带攻击了当当的盈利状况以及李国庆的能力、人品和婚姻状况等。由此可见,即使作为同船人的中国概念股和帮这些中国概念股上市的投行,其实想法都不一致。
由此看来,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因为哪种原因使得红五月里几支中国概念股被看空。但也不可否认,这些原因都可以部分讲得通。不过,更有些意味的是,即使中国概念股似乎被集体看空,但还是有那么多中国公司打破脑袋要去美国上市。这里面的原因,似乎比为何被看空更简单些。
第4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王恩平(1988.05-),男,汉,河北秦皇岛,硕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金晶(1991.06-),回族,云南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多的来源于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体制不协调、不适应造成的矛盾。本文通过阐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厘清我国在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选择,旨在更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政策选择
十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不单是我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理好老龄化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的背景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7%,就称为人口老龄化。早在二十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因此我国早已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以及在经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而“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时期,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有所贡献,但是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我国的老龄化具有规模大,老龄化增速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老龄化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并且根据数据研究显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老龄化趋势在大体上是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将常态化。
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实现工业化,后进入老龄化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应该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模式下,根据自身特点提出更加可行的,适合本国发展的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人类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一段时期人口过度增长的结果,改变生育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作用,即使现在改变生育政策,也不会发生根本上的逆转。同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全是其本身带来的,更多是因为现有制度与人口结构不适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需要从公共政策方面进行改革,调节公共政策来协调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将是常态,需要提出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实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及商业人寿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但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1.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从现收现付制到统账结合制的转变阶段,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在现实实行过程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资金“混账管理”,社会统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因此形成大量“空账”运行,出现挪用个人账户的现象,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当前个人账户空账累计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到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2.5万亿,但是个人账户实有资金2703亿元,空账金额高达2.2万亿元。据社会保障国际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报告统计,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收支缺口达到767亿元。
2.养老保险金缺乏保值增值性
我国规定养老金在留足2个月的支付以外,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企业债券、投资股市,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目前我国养老金仍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银行储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无法满足老龄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并且,通货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过银行利率,存放银行只会造成养老保险金的贬值,是社会财富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养老保险的效率。
3.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加上保费欠缴的情况严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保费收不抵支,原有的积累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却不断减少。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二)、现行退休政策及其弊端
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规定:一般来说,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退休必须是男年满55周岁,女满45 周岁。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加上生活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国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有关专家预测我国2000年老年抚养比为10%,2010年为18.6%,2020年为26.3%,2030年为40.2%,2050年为58.7%,2060年为60.3%。
劳动年龄的上下限不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提高改变。我国现行的劳动年龄的上下限是50年代根据当时的条件确定的,已逐渐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全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比起世界平均年龄低了将近10岁。如果继续按原定的上下限执行,以后将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比、总供养比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上升的不利局面。
(三)、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弊端
1.“现收现付”为主的筹资模式使医疗保障面临未来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虽然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但个人账户积累能力有限,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积累。实际上,主要是依靠统筹基金的现收现付制,而对其他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等也主要是现收现付制。根据医疗保险理论,现收现付制需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而在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医疗保险基金主要依靠现收现付制筹集,每个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负担将不堪重负,最终将带来保险基金紧缺的危机。
2.服务提供上的问题
我国虽然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医疗机构、人员、床位数最大幅度增加。但仍然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势头。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出现的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住院难”问题已证明这一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
我国医疗资源不合理利用的表现主要为:(1)重治轻防;(2)病人不合理流向;(3)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特别是高新技术手段、药物的超标、过量使用。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我国医疗服务成本居高不下,且增长迅速。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加剧我国医疗资源和卫生费用的压力,甚至导致医疗保障体系的崩溃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选择
(一)、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35年前年轻人口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人口转变带来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支撑我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加上健康老年人口参与对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让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发掘老年人消费潜力,从内部发掘社会发展潜力。积极促进老年人健康宣传,树立健康理念,延长老龄人健康期,适当拉长就业和准就业年限。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寻找能充分发挥老年人特殊技能,丰富经验的工作机会。例如,退休老年人对年轻人进行特殊技术岗位的培训。不仅能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的机会,还能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高自我养老和消费能力。
人口红利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撑,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大就业参与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两次人口红利的对接。如果利用好人才资源,“第二次人口红利”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改变。
(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项基金存人银行或购买国家公债,这虽然是一条营运途径,但其保值和增值的程度大打折扣。要想使养老保险基金有效运营使之保值增值,可以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放宽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限制。政府应制定适当政策以引导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向低风险、高收益的领域投资,如住房贷款、基础设施、教育产业等。其次要积极推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从而提高基金投资效益。第三要坚持专业化运作,委托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作。世界银行的一份全面研究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由民营机构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门经营的养老金。
养老金入市也是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将养老金投资于市场,可以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也可以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由于养老金属于社会保障范畴,投入市场难免存在风险。广东省率先开始了千亿养老金入市的尝试。
(三)、完善医疗保险体系
目前医疗保险筹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企业和职工缴费,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职工与退休人员负担比的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有必要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的来源,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民间慈善捐款,从社会福利彩票所筹集的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老年人医疗保障事业,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也可以划拨一部分用于补偿医疗保险费用开支,也可以通过征收烟草税、发型彩票等方式增加医疗保险金的筹集渠道。
(四)、调整人口年龄结构
必须承认,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对策。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延长退休年龄会带来两个积极效应:一个是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一个是领取养老金总量的减少。这一多入少出,从整体上减轻了社会负担,有利于高度老龄化国家挺过老龄化危机。
虽然目前遭到多方反对和质疑,但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在相关政策的具体制定上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元化,多层次的弹性退休年龄结构。有的特殊行业,例如矿井工人,具有危险性的行业,由于挑战身体极限,若和一般职业一视同仁采取相通的退休政策,则显得有失公平和平等。有的行业例如律师,教授等技能、经验、智慧和阅历型的职业,没有受到年龄的限制,甚至年龄越大对社会越有价值,贡献越大,不能因为僵化的退休政策而使社会失去宝贵的社会价值。
(五)、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WHO曾经于1990年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提出,联合国也于1992年通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呼吁全球共同开展健康老龄化运动。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种体格,精神和社会活动能力上的完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老年人群不仅是社会的服务对象,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而要构建这种状态,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老龄化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尽管老龄人口的劳动力会随着年龄削弱,但却不会因为60或者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并且,人生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有不同的潜在可塑性,虽然老龄人口在体力上不如年轻人,但是在知识经验,阅历尚占有很大优势,所以说,老龄人口中蕴含着巨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尚未被人们充分挖掘的重要资源。老年人可以参与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应该充分发挥他们阅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优势,对年轻人进行指导和引导,推动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例如有经验的,在某个行业有成就的退休老龄人可以通过给年轻人上课,传授经验,不仅能大大提升社会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能使老年人得到社会认同感,提高晚年生活的意义和质量,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不仅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而且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也就是“生产性的老龄化”,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继续发挥余热。
第5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未富先老”与“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富裕国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因此,我们本来也不必担心变老。然而,中国的不寻常之处是“未富先老”。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加快赶超,人均GDP也在赶超。例如,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赶超,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但是,2010年我国老龄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发达国家的早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设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我们并不是很老,甚至还相对年轻一些。因此,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按照过去30年的速度预测,“十二五”结束时,将超过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还有一个概念,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讲得比较多的是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东西,如经济停滞、收入分配恶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经济学文献,看最早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机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许多相似的东西。说我们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是因为在文献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形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形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不过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挑战何在?日本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3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一比较。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5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未富先老”
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我想具体列举几个“先老”的表现,也就是人口转变早熟的表现。首先,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我们用的是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供给大概念。实际上,更准确地说,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0岁以上的人,按照我们退休规定其实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即使用16岁到64岁这个大概念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与这个相应,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观察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年以来上涨都十分迅速。例如,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农业中雇工工资上涨幅度更高。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就不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则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这个趋同导致一个结果,即对教育的负激励。如果做更细的计量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例如,我们以初中为参照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们的相对回报率在下降,而小学相对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相对提高。也就是说,工资趋同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对普通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来说,人们上学不仅要付出直接物质费用,还有推迟就业造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很可能导致在一定时间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未富”,即我们还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几个重要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所做的一个预测。由于我们的就业增长越来越慢,因此这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间会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时候变成负的,是压低潜在增长率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刺激性方案,而且区域发展战略都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支撑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它占的比重相当大,然而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人力资本贡献变化不是非常显著。再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未来不会有显著的提高。这里世界银行专家用的假设还是非常乐观的,许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认为,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至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还有人说这段时间是负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没法得到保障。除了我们的教育市场上出现负激励之外,我们看一看现有劳动力存量,随着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的禀赋显著下降,这同日本和美国在每个年龄段教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虽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中,中国竞争力指数被排在第27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规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则大多排位较低。例如,金融市场成熟度排在第57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在第60位,而技术准备仅仅排在第78位。这些表明我们在教育科技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延长比较优势
应对“未富先老”挑战
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面临的类似挑战,集中表现为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处于较低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保持既有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尽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对中国来说,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为此,我们提出几个紧迫的政策建议。
第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紧迫性何在呢?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美元-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第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谈判提高工资,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欧洲“梅佐乔诺现象”的发生。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第6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一、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了。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1][2]。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3],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4],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许多我的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蔡昉、杨涛、黄益平,2012)[5],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移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二、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6]。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约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7]。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争取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7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变;消费;投资;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3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其出生伊始直至死亡过程中一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人口因素成为考察宏观经济运行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又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因此,人口对经济发展可能会存在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影响。综合而言,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果,这或许正是早期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的研究依循这一思路,逐渐开始同时考虑人口总量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综合考察人口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逐渐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居于这类研究的中心。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并被认为在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起步较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因其“转变时间短、幅度大且总量规模大”而更为引人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又使得我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这一“中国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阶段所呈现出的“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似乎正好与我国同期高储蓄率保证和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相一致。不可否认,这一发展模式与我国政府试图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导向战略不无关系,但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促进出口的人口结构转变是否是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以至于同时期相伴随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期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但又值得深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1 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进展及其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
国内外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围绕着人口究竟是消耗资源(从而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消费者”)、还是提出(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辩与讨论,相关研究也因此大致可以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悲观论”(马尔萨斯派),或许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时间内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乐观论”(反马尔萨斯学派),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取决于诸多传导机制的综合效果从而净影响并不明确的“人口结构转变论”(中间学派)。由此使得人口、管理以及经济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进而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人口管理政策重心上也常常在控制还是鼓励人口生育之间徘徊。
早期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比于其人口而言是有限的,从而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过剩会阻碍人均产出的提高,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3月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堪称这一理论的代表[1]。但是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与人均收入均持续增长的现象使得马尔萨斯派的“人口增长悲观论”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人口增长乐观派认为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的讨论。例如Kuznets[2]认为人口增长使人类更容易获得知识发明和传播的规模效应,Simon[3]也认为人口增长在对资源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会对人类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人口增长也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实际情形是,从总量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4],但不同学者因为所关注的问题、数据或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存在较大出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或者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既有可能意味着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而言影响的净效果并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存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问题结论并不稳定。前者如Arrow[5]以及Mankiw[6]等的研究结论所示,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同时是提出的生产者也是消耗产出的消费者,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耗产出的净效果。后者正如Barlow[7]以及Kelley与Schmidt[4]等研究所指出的,通常而言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从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并不一定比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高或者低;并且早期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国家随后的人口出生率也通常比较高,而早期高出生率对应着随后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具有正向贡献的劳动力人口,与此同时随后的高人口出生率则意味着更重的少儿抚养负担因而消费更多的产出,从而意味着单纯从同期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其对同期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存在数据处理上的问题,因而结论也是模糊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开展的人口与经济互动影响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似乎才是考虑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关系的关键所在。
人口结构转变现象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共享[8],阐述的是在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源于对西欧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验分析的结论,最早可追溯到Landry[9]与Thompson[10]的研究,到40年代由 Notestein[11]等学者形成人口结构转变系统性理论,初步创立了“人口转型学派”,之后许多学者[12]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早期的人口转型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定义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但随后的研究[13]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而应该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转变过程的综合现象:包括流行病学转变[14]、生育行为转变[15]以及家庭组织结构变动[16]等。因而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人口特征变化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与Brumberg[17]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个体平滑其一生消费的动机使得其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以用于退休之后的消费,进而不同年龄个体的生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宏观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动将通过影响该国或地区总的产出、消费和储蓄水平等中介变量并最终传递到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上来[18]。随后,不同学者遵循这一逻辑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形:①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动从而影响劳动供给;②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下降或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发生改变,带来消费和/或储蓄变动从而影响投资,并进而影响物质资本存量;③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变动影响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投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④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还有可能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更进一步,如果该国或地区为开放经济体,则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存在差异时将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从而将通过进出口贸易等进一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之相对应,国内外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围绕其对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形成、通货膨胀率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等几个方面展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开始逐渐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转变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的研究也渐渐增多;其中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
2 人口结构转变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
尽管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体在其一生中经历从净消费者到净生产者继而到净消费者的角色的转变,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会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实际情形中这一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
从消费角度来看,Erlandsen与Nymoen[19]利用挪威近40年的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显著影响同时期挪威总消费的变动,李春琦与张杰平[20]也认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李文星等[2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1989-2004年间各省居民消费差异的解释极其有限。就储蓄而言,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重率先下降(从而少儿抚养比下降)可能意味着家庭或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并且研究表明资产价格将在人口红利窗口期被抬高而增加投资收益率[22-23],从而刺激居民储蓄行为。Leff[24]的经验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负相关,因而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抚养比率先下降和老年抚养比随后上升,将意味着国民储蓄率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Modigliani与Cao[25]利用我国的数据也发现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下降是我国同期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Cutler等[26]在新古典拉姆齐(Ramsey)模型中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在两国开放经济体模型中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比较。他对美国数据的动态模拟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将使得美国消费率在最初上升之后趋于下降,并最终达到小于初始值的稳态消费水平;储蓄率则在最初大幅下降随后上升,但仍小于初始水平,最终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Athukorala[27]发现台湾少儿抚养负担或老年抚养负担增加1个百分点,将分别对应着家庭储蓄减少25或0.10个百分点。然而,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可能跟少儿抚养负担负相关,但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居民增加储蓄[28]。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使得人们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本回报[29],并且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家庭对后代的预防性生育需求,从而使得家庭更有资源对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寿命变长、出生率下降、推迟生育和教育投资增加等相伴随出现的现象相一致。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时,寿命的延长是否必然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代表性个体更偏好子代数目还是更偏好后代的福利,但一旦引入社会保障后寿命延长会有利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 人口结构转变对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人口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机理在于: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相对丰裕的劳动力禀赋,进而带来较高的产出,以致出口更多;换到进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意味着进口国有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多的商品[30]。Taylor与Williamson[31]通过研究发现1960 年到2000 年间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从逆差到顺差的飞跃与同时期这些国家年龄结构的差异以及变动密切相关。Debelle与Faruqee[32]对1971-1993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发现人口结构对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Batini等[33]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他们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主要是: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将首先出现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相同的问题,而相对年轻的美国则将出现经常项目盈余。Bloom等[34]评价了中印的经济增长,认为健康状况改善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转变进程互换之后,至2006 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将下降超过30%,相对应地印度的出口总值则会上升超过30%。许多实现了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也是如此。其他经验研究[30,35]结论表明,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经济体选择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采取这个模式的时候,都处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劳动力供给的时期;从而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
与之相对应,当一个国家经历由人口结构转变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决定的大规模人口年龄构成变化时, 国际资本流动会随之变化[31]。这是因为人口年龄构成会影响国内总投资机会——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轻成年人,那么将出现投资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处于收入高峰期的较年长劳动力,那么将出现储蓄率高峰。从而经济体在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其人口年龄构成将会通过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峰的不同而影响其对国外资本的供给和需求。Higgins与Williamson[36]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相伴出现的生育率上升与死亡率下降从而总人口增加的情形使得亚洲国家减少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亚洲国家60年代以来储蓄大幅增加与同期少儿抚养负担大幅下降相对应,并利用1950-1992年的数据发现部分亚洲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以经常账户盈余相反数衡量的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在其少儿抚养负担最高时正好达到峰值。Feroli[37]模拟估算了G-7 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本在G-7 国家间流动的影响。他们从历史的G-7 国家人口年龄数据出发, 估计人口变动趋势的基本经济参数,用于预测未来人口年龄变化的状况。他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从2010-2030 年G-7 国家中的相对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其他的五个国家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祝丹涛[38]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认为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人口结构转变同时也可能对不同经济体间的汇率产生影响。Andersson与Osterholm[39]利用瑞典1960-2002年间的数据、Andersson与Osterholm[40]利用OECD国家1971-2006年间的数据均发现人口结构是实际汇率的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Aloy与Gente[41]发现日本人口结构转变后期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实际汇率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以上各小节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特征因素变动对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经济中介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24,42-46],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结构转变第二阶段“人口老龄化”阶段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压力。
就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而言,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一般先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呈现出“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之后的人口出生水平下降使得少儿抚养负担急剧下降,从而可能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47]:一是储蓄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趋缓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二是促进储蓄率的提高。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48-50]的结论基本与此逻辑相一致。与之相对应,人口老龄化则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43,51-56]:①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劳动力供需关系力量变化,并使得经济总产出下降;②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③人口老龄化会对公共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将面对养老金、医疗卫生等支出持续上涨的挑战,这在客观上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产生了上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将使税基缩减,税式支出增加。
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口抚养负担下降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从而转换为所谓的“经济增长红利”,而需要合适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使得“人口红利”有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的传导机制[57]: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得以持续。早期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表明这些国家国内环境以及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红利”转换为“经济增长红利”机制在这些国家得以实现[49]。与之相对应,学者也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但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如我国)而言,有可能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等来实现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49,58-60]。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态势的增强,行为人预期到自身寿命延长和负担增加,很可能会选择性地增加储蓄以削弱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额也将增加;从而意味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61-63]。这与Azomahou与Mishra[64]发现年龄别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高度非线性关系的结论相对照。因此现有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中所赖以检验的线性基础受到很大质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远比传统的线性假设复杂,从而进一步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
5 理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历经人口结构转变这一现象,人口和经济学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呈现出纵深化的特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转变的文献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并不单一,将通过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贸易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多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从而影响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情形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从而实证研究中因为各学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对引发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的设定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人口结构转变与这些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不同;因而考虑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既是一个国际化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应用探索,更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
致谢: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王丰教授为本文早期版本提出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丹尼斯·米都斯.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M]. 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Dennies L M.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M]. New York : Universe Books, 1974.]
[2]Kuznets S. Population Change and Aggregate Output, in 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eds.)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3]Simon J. The Ultimate Resour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4]Kelley A, Schmidt R. Aggregat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or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Componen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J]. Demography, 1995, 32 (4): 543-555.
[5]Arrow K.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s[A]. Nelson R R, ed.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BER, 1962:609-625.
[6]Mankiw N, Romer D, Weil D.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2): 407-437.
[7]Barlow R.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More Correlation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20(1): 153-165.
[8]Mason A. Demographic Dividend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R]. Paper for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21st Century COE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 of Kobe University and the Japan Economic Policy Association (JEPA), “Towards a New Economic Paradigm: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ization”, Awaji Yumebut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Near Kobe, Japan, 2005:17-18.
[9]Landry A. La R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1909) [M]. Paris: INED,1982.
[10]Thompson W S. Popula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9, 34: 959-975.
[11]Notestein F. Population:the Long View[A]. Schultz T W, et al. Food for the Worl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12]Coale A J, Hoover E.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 Income Population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3]Weeks J. Popu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Issues [M]. Belmont: Wadsworth/Thomason Learning, 2002.
[14]Olshansky S, Ault B. The Fourth Stage of the 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 [J]. The Milbank Quarterly, 1986, 64(3): 355-391.
[15]Ji J. An 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2003, 19(1): 1-25.
[16]Lloyd C, Ivanov S. The Effects of Improved Child Survival on Family Planning Practice and Fertility [J].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988, 19(3): 141-161.
[17]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A]. Kurihara K K,et al.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388-436.
[18]Dornbusch R, Fischer S. Macroeconomics, 6th Ed. [M].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4.
[19]Erlandsen S, Nymoen R. Consumption and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8, 21(3): 505-520.
[20]李春琦,张杰平.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4) : 14-22.[Li Chunqi, Zhang Jieping. The Eff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s[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9, (4): 14-22.]
[21]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 1989-2004 [J]. 经济研究, 2008, (7) : 118-129.[Li Wenxing, Xu Changsheng, Ai Chunrong.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 1989-2004[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8, (7): 118-129.]
[22]Poterba J.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Asset Retur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 83(4): 565-584.
[23]Krueger D, Ludwig A. On the Consequence of Demographic Change for Rates of Returns to Capit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Welfar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7, 54(1): 49-87.
[24]Leff N.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5): 886-896.
[25]Modigliani F, Cao S.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 145-170.
[26]Cutler D, Poterba J, Sheiner L,et al. An Aging Society: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0,(1): 1-73.
[27]Athukorala P. 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R].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2003/21, Division of Econom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8]袁志刚,宋铮. 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 2002, (11) : 24-32.[Yuan Zhigang, Song Zheng. The Age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Optimal Savings Ratio in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2,(11): 24-32.]
[29]KalemliOzcan S. A Stochastic Model of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0(1): 103-118.
[30]田巍,姚洋,余淼杰,等.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11015, 2011.[Tian Wei, Yao Yang, Yu Miaojie, et al. The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and World Trade [R]. Peking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C2011015, 2011.]
[31]Taylor A, Williamson J.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7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1994.
[32]Debelle G, Faruqee H.What Determines the Current Account? A CrossSectional and Panel Approach [R]. IMF Working Paper, 1996.
[33]Batini N, Callen T, McKibbin W. The Global Impa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R]. IMF Working Paper, 2006.
[34]Bloom D, Canning D, Hu L,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Demographic Change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1): 17-33.
[35]姚洋,余淼杰.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J].金融研究, 2009, (9): 1-13.[Yao Yang, Yu Miaojie. Labor, Demography, and the Exportoriented Growth Model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 Research, 2009, (9): 1-13.]
[36]Higgins M, Williamson J. Asian Demography and Foreign Capital Dependence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560,1996.
[37]Feroli, M. Demography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17(1): 11-16.
[38]祝丹涛. 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2): 27-32.[Zhu Dantao. 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Age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J]. Compa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2008, (2):27-32.]
[39]Andersson A, Osterholm P. Forecasting real Exchange Rate Trends Using Age Structure Data:the Case of Sweden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 2005, 12(5): 267-272.
[40]Andersson A, Osterholm P.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Real Exchange Rate in the OEC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006, 20(1): 1-18.
[41]Aloy M, Gente K. The Role of Demography in the Longrun Yen/USD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9, 31(4): 654-667.
[42]Attanasio O, Violante G.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losed and Open Economy: A Tale of Two Regions [R]. Working Paper No.412, Research Departmen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 C,2000.
[43]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 人口研究, 2004, (5): 2-11.[Wang Dewen, Cai Fang, Zhang Xuehui. Saving and Growth Effec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The Population Factor 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04, (5): 2-11.]
[44]Osterholm P. Estim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Structure and GDP in the OECD Using Panel Cointegration Methods [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13, Uppsala Universitet, Sweden,2004.
[45]Choudhry M, Elhorst J.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J]. Economic Systems, 2010, 34(3): 218-236.
[46]张琼, 白重恩. 抚养负担、居民健康与经济增长:影响我国县市经济发展的人口特征因素[J]. 财经研究, 2011, (7) : 17-27.[Zhang Qiong, Bai Chongen. Dependency Ratios,the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ffecting County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1, (7): 17-27.]
[47]Bauer J.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in East Asia,in Andrew Mason (eds.)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hallenges Met, Opportunities Seized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8]Bloom D, Williamson J.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419-455.
[49]Mason A.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hallenges Met, Opportunity Seized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0]Eastwood R, Lipton 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 Economic Affairs, 2012, 32(1): 26-30.
[51]Auerbach A, Kotlikoff L, Hagemann R, et al. The Economic Dynamics of an Aging Population: The Case of OECD Countries [R]. OECD Economic Studies, 1989.
[52]Peterson P. Gray Dawn: The Global Aging Crisis [J]. Foreign Affairs, 1999, 78(1): 42-55.
[53]Faruqee H.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R]. IMF Working Paper, 2001.
[54]付伯颖.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财政政策的选择[J]. 地方财政研究, 2008, (10): 25-29.[Fu Boying. Public Finance Policy Choice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Population [J]. Sub National Fiscal Research, 2008, (10): 25-29.]
[55]Zuo X, Yang X. Special Issue: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Ag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n the Chinese Economy of an Aging Population [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09, 30(1): 197-208.
[56]都阳. 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 (6).[Du Yang. Demographic Changes,Labor Market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0, (6): 136-148.]
[57]张茉楠. 由“人口红利”转型为“经济增长红利[N]. 上海证券报,2009 -12-09(7).[Zhang Monan.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Economic Growth Divided[N].Shanghai Securities News,2009 -12-09(7).]
[58]Mason A, Kinugasa T.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wo Demographic Dividends [R].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No.83, 2005.
[59]Lee R, Mason A.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06, 43(3): 16-17.
[60]Lee R, Mason A. Fertility,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10, 26(2): 159-182.
[61]Fougère M, Mérette M.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R].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Finance, Ottawa,1998.
[62]Faruqee H, Muehleisen M.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Demographic Shock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3, (15): 185-210.
[63]李军.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经济平衡增长路径[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8).[Li Jun. The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Path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06, (8): 11-21.]
[64]Azomahou T, Mishra T. Age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ing the Nexus in a Nonparametric Setting [J]. Economics Letters, 2008, 99(1): 67-71.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A Literature Analysis
ZHANG Xinyi1,2 ZHANG Qi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第8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一、近年来广州市社会管理所面临的形势分析。
近年来广州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虽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严重影响和冲击,但仍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紧紧围绕中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全省“三促进一保持”的中心任务,克服了各种困难,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继续改善,较好地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2]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广州社会管理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广州实际管理人口的压力不断加大。
据统计,2007年全市常住总人口为1004.58万人,比2006年末增加了29.12万人,增长3.0%。2008年全市常住总人口1018.2万人,比2007年末增加13.62万人,增长了1.4%。2009年全市常住总人口1033.45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了15.25万人,增长1.5%。由此可见,广州市全市常住人口连续三年均呈上升趋势。目前广东的实际管理人口已居全国第一位[3]。与此同时,广州市人口在省、市、区之间保持着迁移流动的态势。如2008年全市迁入人数为140927人,迁入率18.09%,迁出人数为75153人,迁出率9.65%。[4]广州市实际管理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迁移流动的常态化必然会给社会管理造成巨大的压力。
(二)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日趋明显。
据广州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广州市人口机会窗口打开时间是1983年。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预测,广州市常住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时间是2025年,户籍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时间是2021年。为此,广州市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如果外来流动人口保持现有状况,广州市常住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16年前仍是逐年增加。但至2016年便开始逐年减少,到2025年常住人口的总抚养比将超50%。[5]广州市如果不在“人口红利”期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那么当进入常住人口总抚养比超60%的“人口负债”期时,广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广州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思考。
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的定义,包容性发展指边缘群体(不论性别、种族、年龄、信仰、残疾或贫穷)能够参与并从中获益的发展。[6]在分析目前广州社会管理所面临新的形势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容性发展模式可以为我们思考广州市检察机关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一)包容性发展是检察机关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2007年10月,中央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09年11月15日,总书记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了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6日,总书记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再一次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包容性发展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一方面强调了增长的必然性,体现了发展的第一要义。另一方面强调了包容的兼顾性,反映了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要对社会各界群体利益统筹兼顾。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要充分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就必须在检察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检察职能的发挥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包容性发展是检察机关服务“十二五”规划的必然选择。
2010年10月27日,中央第十七届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五大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以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该建议凸显了包容性增长的主旨。表现在,五中全会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提出了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此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等。[7]为此,检察机关要切实发挥检察职能服务“十二五”规划,就必须将中央有关推进包容性发展的精神落实到检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三、构建检察工作包容性发展模式的几点建议。
包容性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二是包容。发展强调的是效率和效益。包容强调的是公平、合理、平等与和谐。[8]广州市检察机关要根据自身实际,通过有针对性、有步骤的措施加以探索。
第9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利用空间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自然等要素的地理空间分布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5~17]。标准差椭圆(Standarddeviationalellipse,SDE)是空间统计方法中能够精确地揭示经济空间分布多方面特征的方法[18,19],最早由Lefever在1926年提出,用于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20~24],已在社会学、人口学、犯罪学、地质学、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5~29]。SDE方法通过以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为基本参数的空间分布椭圆(见图1a所示)定量描述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整体特征。具体来说,空间分布椭圆以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为中心,分别计算其在X方向和Y方向上的标准差,以此定义包含要素分布的椭圆的轴。使用该椭圆可以查看要素的分布是否被拉长,由此而具有特定方向。SDE方法基于研究对象的空间区位和空间结构,可从全局的、空间的角度定量解释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空间形态等特征。椭圆空间分布范围表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主体区域,其中,中心表示地理要素在二维空间上分布的相对位置,方位角反映其分布的主趋势方向(即正北方向顺时针旋转到椭圆长轴的角度),长轴表征地理要素在主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SDE主要参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式中,(xi,yi)表示研究对象的空间区位,wi表示权重,(----Xw,-Yw)表示加权平均中心;θ为椭圆方位角,表示正北方向顺时针旋转到椭圆长轴所形成的夹角,~xi、~yi分别表示各研究对象区位到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σx、σy分别表示沿x轴和y轴的标准差。对不同椭圆的大小、方位等基本参数进行比较,可以提供不同空间分布之间的差异信息,而且空间分异系数可以定量刻画不同分布之间的空间分异程度(图1b)。例如,空间分布B相对于A的空间分异系数IB/A可通过以下具体表达式定量描述:IB/A=空间差异部分B的面积空间分布B的面积(5)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空间计算主要基于Arc-GIS10.0展开,空间参考为等面积的Albers投影坐标系统(中央经线为105°E,标准纬线分别为25°N、47°N)。
2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
倘若不考虑任何自然要素及社会经济要素的作用,社会经济、人口等在国土空间的分布应该是均衡、随机的,因而国土空间均衡分布是经济空间分异的起点。而实际上,在“第一自然”代表的自然禀赋差异的影响下,区域发展的起点并不平衡,同时,由于“第二自然”带来的区域发展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的空间差异,区域发展的过程也呈现不平衡的特征,这“两个自然”的作用共同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分异。本研究采用SDE方法分别定量刻画出国土均衡分布以及表征“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分异作用的相关特征分布,继而以国土均衡分布为基础参照,分别以国土空间“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相关特征分布为依据,在空间上定量刻画、分析中国的经济空间分异。2.1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作为国家的地理标志,具有特殊而复杂的几何特征,其国土尺度和形态对一个国家经济、人口、政治等的空间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学术界早就认识到国土的空间几何特征,使用重心、标准距离方法等统计方法来确定这些特征[30~33],但目前还未有学者应用SDE方法同时从从中心性、展布范围、方向趋势等多个角度精细地定量刻画中国国土空间的几何特征。本文研究以105°E为中央经线,对中国连续大陆空间(不包括海南、台湾等岛屿)进行30′×30′经纬度剖分,在国家几何轮廓内共确定了3048个剖分点来表征中国连续国土空间,继而以这些点的空间区位为基础,运用SDE方法在等权重的条件下(即将所有点的权重均设定为1或其他相同的值)计算得到完全均衡状态下的中国国土空间分布椭圆。中国国界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计算得到的中国国土均衡分布椭圆见图2,其中,中心在甘肃省兰州市(103.30°E,36.64°N),长半轴为1684.35km,短半轴为1161.88km,方位角为86.26°。从空间范围来看,国土均衡分布椭圆覆盖528.34×104km2的大陆国土面积,约占全国土面积的55%。该特征椭圆可为研究中国空间分异提供基本参照,从而反映经济、人口等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集中性。2.2国土地形分布椭圆Krugman所说的“第一自然”力量主要是指海拔、地形、水资源等决定空间经济演变起点的自然禀赋要素,在长期尺度下具有不变性,可以促进或限制经济的发展。在自然要素中,地形因素是人地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基础,其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控制和分异作用[34,35]。本文研究以地形因素为主要因素,通过中国连续国土空间地形分布椭圆刻画“第一自然”要素对区域经济空间发展起点的分异作用。研究主要针对上述3048个经纬度剖分点展开,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DEM,1:400万)提取出每个剖分点的高程信息。继而通过加权标准差椭圆方法计算连续国土空间地形分布椭圆——即基于3048个剖分点的空间区位信息,将每个点要素的高程信息作为权重计算得到国土地形分布椭圆。通过计算,中国国土空间地形分布椭圆中心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94.64°E,35.16°N),长半轴1327.89km,短半轴870.11km,方位角为89.22(°图3)。总的来说,国土地形分布椭圆覆盖358.40×104km2的大陆国土面积,约占全国土面积的37%。相对于国土空间均衡分布,地形分布椭圆中心分布明显偏西,长、短轴均显著小于国土均衡分布椭圆,这直接反映出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图3中国国土空间地形分布椭圆Fig.3ThespecificellipseoftopographydistributioninChina2.3中国人口分布椭圆Krugman将人类活动形成的交通条件、人口与资本聚集区位称为“第二自然”。经济活动最突出的空间特征是聚集,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如果需求和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完全均匀,所有的商品生产都将是当地性的,这时将没有空间分异[36]。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人的分布是人用脚在给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等投票,因而本文以人口分布为主要因素反映“第二自然”要素的分异作用,主要针对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开展研究。通过加权标准差椭圆方法计算人口分布椭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椭圆见图4,其中,椭圆中心在河南省南阳市(113.62°E,32.63°N),长半轴为1092.86km,短半轴为822.18km,方位角为28.83°。人口分布总体表现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分布主体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其覆盖252.97×104km2的大陆国土面积,约占全国土面积的26%。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而且具有稳定性[37,38],其东南方约40%国土面积上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线西方人口密度极低,主要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从图4中可看出,中国人口分布轴线(长轴)与胡焕庸线近似平行,且其绝大部分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方。图4中国国土空间人口分布椭圆Fig.4ThespecificellipseofpopulationdistributioninChina3
3结果分析与讨论
总的来说,中国国土空间均衡分布和地形分布总体表现为“东-西”空间格局,人口分布总体表现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图4)。相对于国土均衡分布椭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靠近东部地区,其椭圆长、短轴长度均显著减小,充分表现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聚集特征。如国土空间均衡分布的椭圆长、短轴分别为人口分布椭圆长轴、短轴的1.54、1.41倍(表1)。地形要素对人口分布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分异作用显著,其中,相对于地形分布椭圆,人口分布椭圆的空间分异系数为89.55%(即,与地形分布的空间重叠部分仅占人口分布椭圆面积的10.45%)。除了地形因素之外,水资源、气候等因素也对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胡焕庸线是通过人口表现出的自然,其与气象上的降水线、地貌区域分割线等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如,与作为中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分界线的400mm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结合胡焕庸线进一步分析“第一自然”要素的分异作用,经计算,人口特征椭圆的93%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方。在中国经济主体区域的内部,也存在着经济空间分异。城市作为集聚经济在空间上的体现,其经济产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聚集经济的空间分异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中国经济空间分异,本部分研究基于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39],得到中国地级城市体系人口分布和GDP分布特征椭圆,见图5。通过计算,城市体系人口分布中心与基于县域普查数据的人口分布中心基本一致(表1),且城市体系人口分布椭圆范围占县域普查人口分布椭圆面积的74%,因而研究城市体系经济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图5可看出,中国地级城市体系人口、GDP分布主体均完全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方,主要集中在约20%的大陆国土面积上,而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来说,基于地级城市体系的GDP-人口两个分布之间以东-西方向差异为主,GDP分布相对于人口分布的空间分异系数为15.45%(即,二者空间重叠部分占GDP分布椭圆面积的84.55%)。由于中国经济主体——沿海地带的狭长状分布特征,城市GDP空间分布,更靠近东部沿海地区,椭圆方位角较小,分布范围(长、短轴)略大。人口分布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主体,在GDP分布椭圆的西南方。综合以上分析,由于地形、降水、气候等自然禀赋因素是影响区域发展起点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因此从“第一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异和控制作用来看,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特别是西北侧地区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其总体以生态保护和恢复为主(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国22个限制开发区域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而且通过对比分析2000年第五次县域普查人口分布椭圆和2010年第六次县域普查人口分布椭圆,发现2010年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东南方向移动,西部地区有限的人口红利仍在流失,东、西部地区人口不均衡性在进一步加大,这也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产业的空间聚集是一种地缘现象,因而经济空间分异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确保空间发展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实现国土经济空间优化发展的关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靠近人口分布是判别区域空间公平的标准[40],而临近市场空间则更能体现效率,因而减小二者之间的空间差异将有助于兼顾效率和公平。目前中国城市体系人口分布比GDP分布略靠西南方,通过重点培育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中西部经济增长极可有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向西发展;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人口向GDP分布椭圆北部地区流动、聚集,发挥人口红利的拉动作用,推进经济增长由南向北发展。
4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