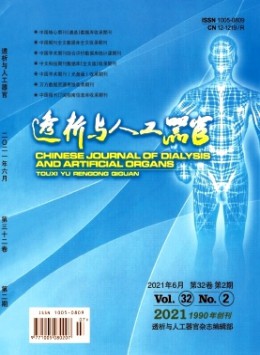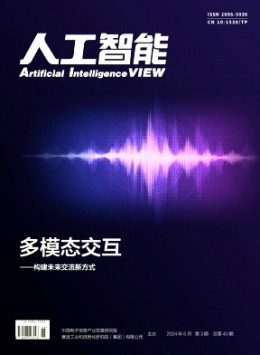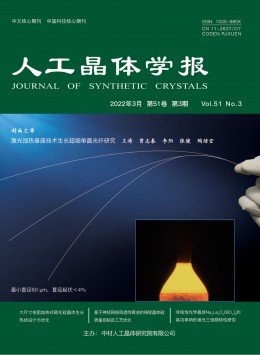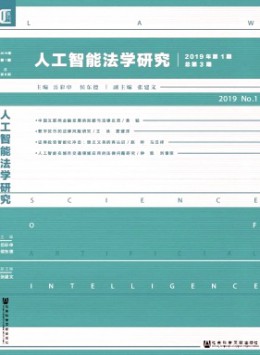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范文
【关键词】设计科学;基于设计的研究;干预;教育技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 (2008) 09―0052―04
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以下简称DBR)是一个国际性的前沿课题,国内学者对DBR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DBR属于设计科学的范畴,作为一种整合设计与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法论,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设计科学概述
1969年西蒙在《人工科学》中,将自然科学与人工科学加以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计科学这一门类。他认为要研究人类,在相当大程度上就要研究设计科学,因为它不仅是技术教育的专业要素,也是每个知书识字人的核心学科。同时指出设计科学是关于设计过程的学说体系,它在知识上是硬性的、分析的、部分可形式化的、部分经验性的、可传授的。
1994年Van Aken提出了一种更广泛的科学分类,他根据不同的研究范式,将科学分为三类:形式科学、解释科学、设计科学[1]。形式科学几乎没有经验性元素,它们的研究范式是测试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如数学、哲学。解释科学包括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学科,它们的研究范式是通过描述、解释现象,尽可能的预知该领域内可观察到的现象,如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设计科学是生产知识去支持设计、产品开发、系统建构,它们研究范式是开发出明确的适应性理论去适应实践的目的,如医药学、工程学等等。
1995年March和Smith在西蒙对设计科学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设计科学的六个特征:设计科学研究是由研究者发起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需要参与者之间的紧密协作;构造和评价是设计科学两项主要活动;通过建立行为,形成知识、使用知识、评价知识;设计科学产生四种知识:概念、结构 、模型和方法;产生技术人造物;通过价值或效用来评价产品[2]。
从关于设计科学的众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设计科学是以技术为基础,以创造新的知识、人造物去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实用价值为其产品的评价标准,最终在实践中建立解决问题的结构、模式、方法和实例。
二 DBR出现的背景及其内涵
尽管设计科学在工程学、医药科学领域论述的比较多,但在教育研究领域,人们对设计科学的认识相对较少,直到1992年,Allan Collins在有关“设计实验”的早期文章中,首次提出构建教育领域中的设计科学这一理念。他认为我们需要建立教育研究领域中的设计科学,从而研究不同的学习环境设计会怎样影响教与学的相关变量,进一步开发出情境化的理论,这也正是Ann Brown 与Allan Collins创生DBR方法论的初衷。
Ann Brown通过“设计实验”把实验室中对学习的研究与复杂的教学干预联系起来,在研究方案中,她致力于研究教室环境下的学习,她认为这种学习是丰富的、复杂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3]。与此同时,Collins提出了在教室环境下研究学习所需要的理论以及这样做所要面临的挑战,并且定义了“设计实验”的关键特征:(1)在与实践者的实际协作中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2)将已知的和假设的设计原理结合起来去合理的解决这些复杂问题。(3)进行严格的反思和调查去改进学习环境,同时界定新的设计原则[4]。
实际上DBR是由“设计实验”(Design Experiment)演化而来, 有关对DBR的界定,国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不同的DBR的专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5]。笔者认为,由Wang&Hannafin提出的DBR的定义体现了其内涵和本质:基于现实情景中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交互,通过迭代的分析、设计、开发、运用,产生情景化的设计原则和理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实践,是一种系统而又灵活的方法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种研究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团体,即由斯宾塞基金会(The Spencer Foundation)1999年发起的DBRC(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其中包括了来自认知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生物学、数学、人机交互学以及教学设计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一直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期推动该研究的发展。为了避免“设计试验”与“实验设计”(Experimental Design)、“试验教学法”(Trial Teaching Methods)相混淆,2003年DBRC用DBR代替了“设计实验”[6]。
三 DBR的设计科学特征分析
设计科学又称为设计方法论或设计哲学,它是从人类设计技能的本质上去探讨设计活动的规律,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论范式就是开发出情境化的理论、人造物,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DBR作为教育技术研究中的设计科学具有一些设计科学的特征:
真实情景性。设计科学是在自然的情境中解决存在的问题,DBR设计学习环境和开发学习理论或学习原型的目的在于干预,真正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所做的研究要能够解释在真实情景下设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迭代性。在设计科学中,评价要贯穿于研究的始终,只有通过不断的评价,才能改进最初的设计。在DBR研究中,开发和研究发生在设计、实施、分析和再设计直至理论形成这样一个持续的循环中。
创新性。设计科学与形式科学、解释科学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设计科学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DBR研究过程中,理论既是DBR的基础也是DBR的结果,因为DBR有一种“驱动理论”的特性,理论会通过研究过程不断发展、优化,同时现实世界情景中复杂的、真实的以及一些带有局限性的因素也会指导DBR研究,最终形成情境化的理论。
可传授性。DBR的研究结果是设计过程与研究的背景之间的连接,在DBR研究过程中详细地记录有关设计是否起作用,发生了什么样地变化,实践怎样被促进了等等。通过这些文档,其他研究者和设计者可以联系他们自己的背景和需要进行研究,来提高理论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同时,这也有助于理论共享,便于实践者与其他教育设计人员进行交流。
四 实施DBR的一般步骤
因为DBR在教育领域是比较年轻的,自身也有许多的变量,所以它不是简单得一步接一步地描述和指导DBR。尽管这些步骤是顺次的,但这些步骤经常是同时发生的,有时也会以不同的次序发生。
第一、知情探索
DBR最本质的不同方面是它强调阐述教师、学习者和其他人在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一般采用需求分析的方法来确定问题的领域,发现其中的问题。例如:中学学生对阅读没有兴趣;高中女孩子不愿意学习数学以及其它理科课程;大学生对学术研究没有兴趣;工人不能把培训的内容运用到工作中等等。同时,要确定来自社会、文化或者其他方面的约束有哪些,哪些是属于教育领域的问题,哪些不是。接下来,从现存的数据和研究中收集与问题相关的信息,例如:采用文献调查法查阅与问题有关的资料,从而确定问题的范畴;通过受众特征分析,了解受众的特点。最后,以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对解决问题的潜在方法进行系统的描述,例如:技术支持、理论框架,开发出最初的设计原型。
第二、开发、实施、修改干预
根据设计原型开发干预。开发干预是与形成性评价交互式作用的,在开发干预的过程中要及时的对形成性评价作出反馈,以开发出一种更精细化的干预,干预的形式可以是:人工制品、软件等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更加详尽的干预将会被运用到类似的环境中,从而使研究者能够描绘设计与多样的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DBR操作过程中,研究者需要积极的与其他参与者协作来设计,比如:教学设计人员、课程开发者、教师和评价者,协作者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在不同的层面:认知层面、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资源层面、机构或学校层面。如果没有这种协作,干预不可能在现实世界的背景中产生有效地变化。
通过迭代的循环,DBR不仅能够构建强有力的、适用于实践的理论,而且能够形成被实践很好的支持的教学设计的理论,同时还能够更深的理解学习环境的复杂性。有人曾经这样形容DBR的迭代过程:“DBR的迭代过程就如同人们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试着去理解世界”。
第三、评价干预的影响
DBR通过收集数据来揭示干预是否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问题是怎样被解决的;选择的理论能否能够解释教与学的过程和结果:哪些现象是由当时环境中的“当地性(local)”因素引起的[7]。DBR通常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来设计干预,因此通过干预,研究者们能够例示理论或者是有关教与学的假设。毫无疑问,设计是DBR中很关键的工具,正如Joseph所说,DBR解决问题不是通过形成理论来解决而是通过设计来解决。
第四、评价更为广泛的影响
以各种形式来形成DBR报告,其中包括什么因素会影响设计的推广;什么样的政策或文化适合采用这种设计;什么关键因素会影响这类设计的运用等等。这些报告将会对教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将会为他人的实践或研究提供一种平台,从而推动DBR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DBR的研究过程是从设计到实施到评价再到重新设计,研究者要揭示在现实情景中对于解决特定的问题来说,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特定的状态下怎样起作用。 因此,一定要注意特定研究实施的局限性或特定的条件,这种局限性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研究结论可能仅适用于研究情境或有类似特征的情境,而不是适用于更广泛的教学情境。
五 DBR与教育技术传统研究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众所周知,要理解一种新事物,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是通过把新事物与现存事物进行比较来理解,对于DBR也是如此,通过比较它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区别,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DBR。
1 DBR与实验研究
首先,DBR研究是在现实的背景下进行的,它要处理现实情景的复杂性和局限性,而实验研究通常只注重单一的决定性变量,没有其他变量的干预[8]。其次,由于实验研究者试图控制研究过程中的变量,因此他们的研究步骤是倾向于固定的。与此相反,DBR的研究者们试图对研究过程进行反复、灵活的修改来创造一种复杂的情况。第三,在DBR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要涉及到与社会的交互,因为它是在现实的情景中进行的,而实验研究它要试图阻止参与者与外界环境的交互。所以,对于DBR的理论研究成果很难在实验室进行验证。第四,大多数实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先前的假设,而DBR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现实的情景中形成新的理论或开发一种轮廓来运用于教育实践中,从而真正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
2 DBR与行动研究
DBR与行动研究的类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看成是伴随着一系列的行为发生的,研究的参与者比如教师都要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中。在DBR中参与者既是研究者又是设计者,研究者通常是研究过程的发起者,而在行动研究中,通常是实践者发起研究。
3 DBR与形成性评价
从某种程度上说,DBR与形成性评价有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关注过程、注重迭代的流程,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通过操作一种方法,检测一种现象,理解运用一种方法的一系列的过程,检测现存的理论,改善或者是提高某一种特殊方法或特殊设计的运用。而DBR通过设计开发更广泛的原型,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要,并且要扩展、揭示和确定理论之间的关系。然而,形成性评价在DBR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DBR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形成性评价对开发出的设计原型、人造物做出有效性评价,以利于设计的修改和问题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将DBR与教育技术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并不是摒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反,它是建立在形式科学、解释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例如,在DBR的研究过程中,要用到人种学中定性分析的方法与实验研究中定量分析的方法相结合,文献检索、观察法、实验研究方法、评价研究法等等都会运用到DBR的研究过程中,巴拉布(Barab)[9]曾经说过“与其说DBR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系列的方法”,DBR要与这些研究方法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使研究者更加理解他们的主张。例如,基于实验室的研究者应该自问他们的基于实验室的理论怎样通过在现实情景中的检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DBR的研究者应该思考他们的主张怎样能够在实验室中得到更精确的检测。
六 DBR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DBR通常是以教育工作者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为驱动,研究者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理解与解释教育现象,更多是要通过干预来改变和改善教育实践[10]。在研究过程中,也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情景”这一重要因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教育领域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而是与其它领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DBR真正地将理论与实践联系了起来。因此,DBR研究有更大的潜力来影响教育实践的进行以及教育产品的开发,同时使得DBR的结果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通过以上阐述,笔者认为DBR对教育技术的研究及其方法上可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
第一,目前国内教育技术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尽管目前实证研究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实证研究对于提高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水平,解决教育技术应用中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实证研究的目的并不能局限于单纯的验证假说,而要去研究这一假说在哪一范围内成立,对教育实践的哪些方面具有指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目前实证研究中的误差项中被排除在外的风俗、文化、环境、历史、社会等因素也必须包含进来[11]。
第二,强调研究不同情景下的学习活动,形成情景化的应用理论,这对促进教育技术的理论发展与应用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学习环境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创设多样的学习环境(其中包括创设多样的网络学习环境,创设丰富的传统学习环境),这是目前值得教育技术工作者去研究的问题。并且通过不同情景中的学习活动,真正地将理论“情景化”,同时通过形成性评价、反馈等手段迭代的改进设计、改进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真正的去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在研究过程中要客观、详细的记录研究过程,不仅要记录先前的设计或干预是否起作用,更要关注什么在起作用。科学的研究范式的特点是可重复性,通过对研究过程的记录,使整个研究过程清晰完整,这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共享,也有助于在相似的环境中的重新应用,同时增强了理论的应用性。
第四,促进教学设计的“本土化”研究。在教育技术领域,教学设计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领域,我国教学设计理论主要是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论的生存背景、实践应用,尤其是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了解不够,致使很多国外教学设计的理论和模式引入我国后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受到实践的排斥。中西方除了文化差异外,技术水平、教育条件、教育行政制度等等的差别都会导致设计需求的不同,“本土化”的核心应该把握住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实践中构建“本土化”的教学设计理论体系。
第五,要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持久性。多年来,教育改革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我们要认识到,一项成功的教育改革,并不是通过短时间、局部的改革功效来去判断成功与否,而是要从持久推广的过程中,认识到改革推广过程中的差异,例如东西部的差异、观念的差异,丰富教育改革的内容。
七 结束语
在教育技术领域,我们对有关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关注还比较欠缺,随着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深入,要使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取得发展,我们必须重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丰富和发展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当然,这并不是说基于设计的研究就是最好的研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运用传统的观点来看,DBR的客观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另外,由于研究的“情景化”,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适性[12]。然而,我们不得不关注这种研究方法论对某些问题有其独到的适应性,基于设计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自然情景下的学习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论范式。
参考文献
[1] Van Aken.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the design sciences: the quest for field tested and grounded technological rul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 41:219246.
[2] March S and Smith G. Design and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1995,15(4): 251266.
[3] Brown A.Design experiments: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eating complex interventions in classroom settings [J].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1992,(2):141-178.
[4] Collins Joseph & Bielaczyc K. Design Researc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004, 13(1):15-42.
[5] Kelly A. Research as Design [J].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3, 32(1):3-4.
[6] [DB/OL]省略.
[7] Philip Bell. On the theoretical breadth of design-bas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Draft, 2004 ,(1):1-36.
[8] Cobb P. &Schauble L.Design experiment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J].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3, 32(1):9-13.
[9] Sasha Barab&Kurt Squire. Design-Based Research: Putting a Stake in the Ground [J].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004, 13(1):1-14.
[10]The 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Design-Based Research: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Educational Inquiry [J].Educational Research, 2003, 32(1):5-8.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