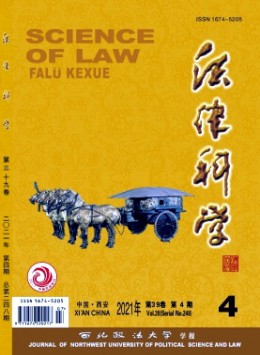法律规则的含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规则的含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可预见性规则;损害赔偿;建议
一 可预见性规则的一般问题
1. 可预见性规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学术界对可预见规则含义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人主张,当事人违反合同后,由其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一般以其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范围为准。还有人认为,可预见性规则只要是指订立合同后,承担的损害赔偿范围主要以违约方能够预见或者应该预见的范围为限。从某个角度来讲,可预见性规则是对“完全赔偿规则"的限制和补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订立合同后,赔偿损失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合理的预见范围内,并由违反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来承担。
2. 可预见性规则的构成要素
(1)可预见性规则的主体
对损害赔偿有合理预见责任的合同当事人,就是我们一般所指的可预见性规则的主体。关于可预见主体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就是,认为应该由双方当事人来共同确定可预见性规则的范围的双方当事人说。第二就是主张违约方说。同意这种学说的人认为,违约的当事人为预见的主体,而不包括受害方在内。第三,合理人说。这种观点主张的赔偿通常是指,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造成的损害赔偿事故引起的损失。
(2)可预见性规则的时间
我们应该以何时预见到损害为准,来由违约方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预见性规则的时间问题。针对预见的时间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主要是指“合同缔结时说”和“债务不履行时说”。然而我国有关学者对此提出了折中的看法,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把一般性的因素考虑进去,同时还有把一些特殊情况包括在内。经常在实践中经常看发生的就比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而在订立合同之后,合同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供了订立合同之前没有预想到的情况和信息,或者是在合同订立之后双方当事人又考虑了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情况和因素在我们确定可预见范围的时候也应该加以考虑。
(3)可预见性规则的认定标准
认定可预见规则的标准,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是“一般人"说、“理性人"说以及“理性加一般”说。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实践过程中,是否为可预见如果用一般人的标准来加以确定的话,可能会引起法律执行中的一些问题的存在,从而影响合同交易的正常进行。可见可预见规则在我国应当采取“理性加一般”说,以利于法官在司法实践审理案件的时候有合理的评价标准,同时还能充分的考虑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切身利益。
二.我国合同法上可预见性规则的缺陷
1. 违约方的过错问题上的不足
关于可预见性规则,我国目前合同法相关条款的有关规定,没有对主观过错进行区分,而是针对所有的违约情形都无差别的适用该规则。笔者认为通过这种方式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与合同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基本原则尤其是公平正义的原则相悖,这种情形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合同当事人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同时还可能导致违约情形的增加。
2. 完善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因为人的主观方面通常以人的内心活动为表现形式,可见主管过错也是以这种方式体现,于是从这种出发点来看,过错就较难把握和认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找一个使举证责任变得相对容易的行使机制,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审理案件的效率。
3. 守约方的信息揭示义务的缺位
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我国有关学者提出了守约方的信息揭示义务。因为在当事人没有告知,而对方当事人又不可能知晓的情况下,就很难对违约赔偿的范围加以确定,那么此时就产生了信息传递的必要性。可见能否知晓信息对违约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合同法上可预见性规则的建议
1. 完善相关立法
第一,明确立法相关规定。关于可预见性规则,我国《合同法》采取的做法和英美法系做法一致。也就是,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并不受违约方得主观过错得影响。所以实践中在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时候应当排除违约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
第二,统一法律表述。关于违约造成的损失,我国《合同法》做出了相关规定。根据该规定违约造成的损失,除了包括财产损失以外还包括可得利益损失。然而,有关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合同法》中相关合同条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统一,所运用的工具性概念也不一致,从而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2.健全司法制度
一方面,在司法的适用过程中应该将违约方的过错情形加以系统的考量。违约方的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在我国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中应当加以区分。对违约的发生,如果主观上存在过错的,确定的赔偿范围则以违约时的预见为准;如果主观上没有过错的,赔偿范围则以合同缔结时的预见为限。
另一方面,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与信息揭示义务相结合。在我国有的学者主张信息揭示的义务,这是一种影响当事人违约赔偿责任范围的理论。主要是促进当事人从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通过这种信息揭示义务来确定当事人的预见范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该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完善相关的司法制度,来达到具体的指导可预见性规则的目的。
结论
可预见规则的适用不仅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而且还填补了法律上的漏洞,能有利的保障合同交易的安全,增加交易双方的信心。由于可预见性规则在《合同法》中的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致使可预见性规则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不曾受到重视。本文从可预见性规则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针对我国司法实践提出了完善立法和司法的建议,希望能达到促进可预见性规则的细化和发展的目的。(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柴振国、何秉群:《合同法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2]何宝玉著:《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1999 年版
[3]李永军著:《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李响著:《美国侵权法原理及案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2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法律解释 基本范畴 解释方法 原则
一、法律解释慨述
法院的裁判是当事人最具体、最现实的“法律”
,而每一份判决都体现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任何一条规则未经法官解释都无法用在具体的判决之中。之所以需要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不仅因为法律用语多为书面语,而且有些术语本身极为抽象,比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更重要的是,规则皆有其法理基础,非经阐明,很难把握它的具体含义。加之法律规范常有冲突,当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不进行解释则不能直接使用。然而,什么是解释甚至如何解释,正如哈特所提出的一个恼人不休的问题一样,令人困惑不已。首先对一个现象进行理解,然后才能对其进行解释。“理解”与“解释”即是人们所说的进行解释时应该注重的两个步骤。法律解释的目的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立法文献及其他相关情况的解释,探究和阐明相关法条的确定含义。法律解释的主体既可以是立法者,也可以是法律执行者。但是在司法活动中,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法官。律师和当事人虽然也可以有自己对法律的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必须要让位于法官的解释。就对象而论,可以是法律、案例、合同、遗嘱、原则等等。只要是一个文本都可以被进行解释,甚至有时候不是文本也可以进行解释,比如法官的行为。可见,法律解释这个概念含义很广。
二、法律解释的对象
法律解释的对象只限于法律本身,而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对象可能包括对法律的解释,对法官的司法行为的解释,对法律程序的解释,以及有关法律解释的见解、学说和理论等等。可见,前者的含义比较狭窄。那么,法律又是什么呢?从经验的角度看,大体上法律主要存在于规则、案例和非规则标准之中。法律规则一般表现在专门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这种形式的好处在于法律能够系统化,相对明确,且便于查找和引用。缺点是由于语言的限制,规则无法反映其所赖以产生的背景,比如何时、何地、因何事、以何种方式及通过何种程序制定了该规则。非规则标准主要是以原则、政策、故事、警句等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以非常含蓄而又抽象的提示向人们站始发的基本精神和理念,甚至规则。对于法律规则的解释并不仅仅指某个词或者句子的含义是什么,它也指寻找法律规则的背景。人们通常所谓的立法者的动机和原初的意义指的就是背景方面的问题。当然,背景包括的要远比这更多。在判例法中,规则与背景之问的差距相对小一点,因为案例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判决程序、地点、时间、以及法官所做的选择都有明确的记录,这就相对减少了认识背景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在判例法中不勉励寻找背景的需要。因为一个案例虽然记载了上述种种原因,但法官为什么会做出一个决定的真正原因往往并没有反映在司法判决之中。
三、法律解释的方法和规则
培根说过一句话,“离开文本的解释不叫解释而叫算卦。”意在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解释必须以文本为依据。美国人注意一般意义,即按照文件的额原义来理解文本。另一些人则认为光依靠文本是不够的,法官必须考虑诸如立法意图,社会需要、经济、政治等因素,结合文本做出决定。有些研究法律解释方法的英美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应该有六种:第一种是历史解释,即根据立法者的意图进行解释。如何看待立法者的意图,可以通过立法委员会的报告,文件最后版本和以前版本之间的对比,立法者之问的争论,对立法的最后文本提出的修改等等来进行解释。第二种叫文本或逻辑解释,亦即萨维尼的语法要素和逻辑要素,就是严格通过文本的字面意思就行法律解释进而适用法律。第三种叫结构性解释,即将某一个规则拿到整个法律体系中予以解释,就是做一种前后连贯的解释。第四种就根据学说或者原理进行解释,也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学理解释,而这一般都是无权解释,即法学家的解释。第五种是根据道德伦理进行解释,即用某一文化的精神进行解释。第六种是根据谨慎原则进行解释,即权衡利益和成本进行解释。显然,第四、五、六种完全是出自法律以外的考虑,因为困难程度和随意程度都大得多。
从法官的角度看,西方法律制度中也形成了法律解释的一些基本规则或原则,即所谓“Canons”。根据《简明牛津法律词典》上的解释,大约有以下几种。第一,前后呼应。第二,根据字面意思解释规则。第三,黄金规则,即赋予一般词一般意义。第四,对所有不清楚的条款应以弥补纠正法律缺陷为目的而予以建构性解释,即所谓补救规则。第五,根据对同类事物的列举推断出未经列举的事物。
我国学者梁慧星主编的《民法解释学》对法律解释有着比较严谨的论述。按照梁慧星先生的观点,各种方法之间是有顺序的。一般适用法律解释方法,先以文义入手,如不奏效,再试试体系方法,如还不奏效,则可使用诸如历史的、社会的或其他方法等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面临的是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任务。无论何种方法,只要能解决问题,不一定要分先后,不一定非得要从文义入手;各种方法之间也不存在相对重要性。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拟解决的问题(问题中心主义)。该采取何种方式应以实际解决问题的要求为转移。
四、法律解释的原则
我国现行法律确认了法律解释制度,但对法律解释体例的界定过于粗漏,并且对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操作规程未能作出明文规定,这就造成了法律解释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根据有关法律解释的理论,结合我国法律解释实践,法律解释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法治原则的具体要求。在一切崇尚和追求法治的国家,一切法律活动必须合法,法律解释也不例外。遵循合法性原则要求法律解释首先应该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不得超越法律的权限或违背法律的程序。法律解释也是创造法律的一项活动,因而往往会扩大、限制或改变法律条文的含义,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因而,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有关解释的权限划分及解释程序的规定进行。越权或滥用解释权以及违背法律程序所作的解释无效;其次对法律概念、规则和法律事项的解释必须与法律原则,尤其是宪法原则保持一致。因为法律原则是一部法律的核心和灵魂,是法律规则之上的规则,是构成法律规则的基础,它统领法律规则,并使整个法律规则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没有法律原则的统领,整个法律规则就会像一堆没有组装起来的零部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抑或法律规则之问就会因为“群龙无首”而相互肘掣。
(二)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补充,也是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具体要求。它指的是法律解释必须符合情理、公理或符合一般的常识,不得作违背常理和常识的解释。遵循合理性原则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首先必须是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对法律所作的解释,离开了合法性,就没有合理性可言。因为法是大众理性的凝聚,而执法者和司法者所认定的“理”是因个人知识背景、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个人的“理”必须符合大众的“法”。其次法律解释必须符合社会公理,即符合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因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公正,至少是形式意义上的公正;再次法律解释要尊重公序良俗,即尊重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确定的,或者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秩序和风俗。最后,法律解释还要以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作指导,法律不是“独行客”,也不是“救世主”,它需要与其他社会规范共同承担起对社会的管理职能。
第3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英美法系对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的是一种两分法的思维程序,把因果关系区分为两类,一为事实上的原因(Cause in Fact),二为法律上的原因(Legal Cause),也称为近因(Proximate Cause)。其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也是分为两个步骤的,事实因果关系由陪审团认定,而法律因果关系由法官认定。[2]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涉及客观事实问题,即从客观事实的联系上找出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范围。一般而言,所有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的事实,都被作为该结果事实上的原因。但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是反映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上的联系,要使侵害人对其行为结果负责,除具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之外,还需具备法律上的原因。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法律的上原因”这一术语并未被英美法院广泛接受,习惯上仍然称为“近因”。[3]
按照英美法系对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其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也包括对于事实因果关系认定的规则和对于近因关系认定的规则,一般来说,对于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主要有必要条件规则[4] (But-For-Test)和实质要素规则[5] (Material Element or Substantial Factor Rule)。对于近因关系的认定规则主要有直接结果(direct consequence)规则[6] 和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规则。[7]
事实因果关系的两个认定规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侵权案件,两者是单向补充关系,且不会产生冲突,即首先以必要条件规则找出一切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原因,再以实质要素规则找出最主要的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相比而言,近因关系的两个认定规则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侵权案件,但两者不是补充关系,而且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冲突,即同一案件适用不同的规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所以,侵权因果关系的难点主要是近因关系的认定规则,以下本文将在对近因及其认定规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认识近因关系认定规则的难点及笔者对近因关系认定规则的一点认识。
一、近因关系及其认定规则的简介
近因是与远因(remote cause)相对的一个概念,以近因作为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首见于美国法院1866年在著名的纽约火灾案的判决,该案建立了这样一项法律原则,即如果被告因过失引起的火灾造成大片建筑焚毁,该被告仅对所引燃的首幢建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8] 法谚 “只看近因,不看远因”就是通常所说的近因。但是,这里的“近”和“远”怎么界定至今尚无定论。例如,《布莱克法学词典》认为:“这里所谓的最近,不必是实践或空间上的最近,而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最近。损害的近因是主因或动因或有效原因。”又如,美国著名的侵权法教授Prosser则认为,Proximate一词,系谓时间与空间上最近。再如,1918年英国上议院在Ley land shipping Co.Ltd.V. Nor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 Society Ltd一案中作出的判决认为近因是指效力上占主导地位(dominant efficacy)的原因。
由于英美法系没有关于侵权行为的成文规则,这就要求法官在审理每一个具体的侵权行为案件时进行法律和价值上的衡量和判断,考察是否存在近因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近因的判断至少应包含如下因素:第一、 这一因素实质上上造成了损害结果;第二、 这一因素自然地连续地发生作用,期间没有能够造成因果关系中断的其他因素的介入。从该理解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国家对近因关系的判断,并没有严格的高度统一的标准,其在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下,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个案的近因关系进行单独论证。
当然,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法官们对近因关系认定的某些问题已经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形成了一些的判案原则和规范,并通过法官与学者对这些原则与规范的不断修正和补充,创立了许多不同的规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直接结果理论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
(一)直接结果规则。
直接结果规则主张侵权人应当为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该理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侵权人只为其对损害结果有直接引发作用之侵害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只要侵权人之侵害行为直接导致之损害结果,不论该结果对侵权人而言有否可预见性,该侵害行为均称为损害结果发生之法律上的原因。[9]
直接结果规则系由1921年英国法院在Re Polemis 案件的终审判决中首次提出并创立。[10] 在该案中,被告乃一租船人,因其所雇佣船员之过失,摔落一块厚板,掉到船舱,触发火花,致舱内所装载之汽油引燃,整艘船烧毁沉没。高等法院认为虽然船之如此沉没并非被告所可预见,但其为被告过失行为之直接结果,因此被告租船人对于船之烧毁沉没应负赔偿责任。
直接结果规则是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的,即受害人遭受的由于侵害人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该得到赔偿。该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于认为,可预见性原本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侵害行为之确切后果根本就不是人们于事前可以断定的,行为之意义仅寓于行为的本身。[11]
但是,直接结果规则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该规则在实践运用中,对于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断过于简单、刻板,对法律所含蕴的正义理念感悟肤浅。[12] 1961年及1966年,The Judicai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于The Wagon Mound 及The Wagon Mound(No.2)两案中,先后排斥了Re Polemis 所确立的直接结果规则,而采可预见性规则,这一见解在嗣后的判决中履被肯定。[13]
(二)可预见性规则
可预见性规则是侵权行为归责理论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重要观念。以致埃德格拉曾经这样说,“除去有关侵权人存在故意之场合,没有哪一个理由能像可预见性这样影响着我们对事件的判断。” [14]
可预见性规则在本世纪初由英国法学家Goodhart和美国法学家Fleming James的倡导下逐渐形成的。1961年,英国枢密院首次将可预见性规则应用于审判实践,法官在The Wagon Mound案中指出,被告泄入河道的大量原油意外起火焚毁码头,因为通常原油泄漏的结果应为污染河道,所以火灾对被告而言不具有可预见性。被告据此对火灾不负损害赔偿责任。自此,可预见性规则一跃成为英美侵权行为法上近因关系认定的权威学说。
可预见性规则是从侵害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侵害人只应对其可预见的造成受害人的损失负责。该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人都应当和能够预先估计他可能承担的责任范围。换言之,行为人只能把他所预见的结果纳入其行为选择的范围,而不可预见的结果则无法影响其行为决策。对于可预见的标准,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主观上可预见标准,即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可预见。二是客观上可预见标准,即以一个合理的人在此情况下,能否预见作为标准确定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若一个合理的人能够预见,即使行为人不能预见,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亦具有因果关系。
二、认识近因关系认定规则的难点及解析
(一)直接结果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都可适用于任何侵权案件,如何看待二者的适用矛盾呢?
英美法系至今没有对直接结果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的案件适用范围作出明确归纳,所以从理论上讲,这两个规则可以适用于现在进行的任何一个侵权案件对于近因关系的认定。但是,从大量的文章和案例中都反映了现在一般的侵权案件大多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在《加拿大侵权法》中,Mr. Linden回顾了法庭对因果关系认定的不一致,认为“对于远因和近因的纠纷从来没有容易的答案”。他暗示了案例法是如此的令人费解,以至于无法对案件作出直接的预计。[15]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果一个行为是有过失且导致了损害,那么无论行为人对该损害是否可预见,他都应对由于其行为造成了损害负责。在1961年,英国的普通法院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在Overseas Tankship v. Mort‘s Dock and Engineering一案中认为“一个人只为他的行为可能(probable)造成的结果负责。对他要求太多是一个太过于苛刻的规则。”该案确立了“合理人预见”(the foresight of the reasonable man)的新规则。但是在1966,在一个名为The Wagon Mound #2的案件中,英国的高院(high court)将可能(probable)改变为可能(possible),又一次改变了认定的标准,扩大了了被告对其行为结果负责的范围。而加拿大的最高法院也在努力寻找认定的标准,在1974年它认为可预见不必指要一个人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有精确的预见。只要一个人能以通常的方式预见到可能发生的损害的种类和性质,就足够让他承担责任。所以,就侵权纠纷近因关系的认定而言,现在的核心应该是可预见性规则。[16]
造成我们大陆法系学生对认定近因关系的适用规则不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法系强调法律原则,而英美法系侧重法律规则。在大陆法系,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上位概念。一般来说,在同一个部门法里,法律原则是不能有冲突的,而法律规则是可以有冲突的。前者如在合同法中不能既规定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又规定契约法定的原则。合同法的法律原则只有契约自由,契约法定只是某些少量的特殊情况如格式条款的适用规则。后者如同样是侵权纠纷,一般侵权时适用过错规则,特殊侵权时适用无过错规则。但是,大陆法系又常常将规则也不加区分的表述成原则,如我们日常中一直把只适用于特殊侵权的无过错规则表述成无过错原则,所以当我们把直接结果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称之为直接结果原则和可预见性原则时,就产生理解上的难题了。事实上,英美侵权法是没有共同原则的,很少有著作或教材列单章探讨法律原则的问题,在大多数侵权法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世界,而不是纯粹理性的世界,而法律原则之类属于纯粹理性的范畴,不是实证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们认为法律原则渗透在具体的法律操作过程中,往往与法律规则混合在一起。[17]
直接结果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属于同一法律位阶,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笔者认为对于二者是法律规则的认定,既尊重了英美侵权法强调法律规则的传统,也可以从理论上解决大陆法系学生对二者在理解上的矛盾。只要我们认识到直接结果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是法律规则,就不难理解在英美法系二者可以共存于一般侵权的这个事实。
通过对于认定近因关系的适用规则的分析,给了我们大陆法系学生一个认识英美法的新视角,即不应单纯的从法律原则的角度去认识英美法的判例,判例产生的只是一项法律规则,所以后来的判例还可以推翻以前的判例。特别是在侵权法这个领域,一定要从法律规则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判例,这样才不会为前后迥然不同的判决而烦恼。
(二)可预见性规则为何把过失作为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前提?
可预见性规则把侵害人是否预见到损害结果作为标准来衡量侵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近因关系,进而推导出侵害人是否应对此损害结果承担责任。这么一个推理过程把过失认为是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确定近因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当一个人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时,他就有过失。例如,甲在其公寓的七层楼往下扔瓶子,造成楼下的乙受伤,甲就应当对乙的损害负责,因为甲应当知道公寓下一直有行人走过。但是,大陆法系将因果关系与过失区分的传统使我们无法理解英美法系把过失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
根据大陆法系的理念,除了特殊侵权(如环境侵权等无过失侵权)外,一般认为过失和因果关系是构成侵权的两个不同的要件。而且,在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体系中,因果关系是作为一种客观要件被考虑的,是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失的客观前提,即先考虑是否有因果关系,再考虑是否有过失,最后在二者兼备并符合其他要件的情况下才认定有侵权责任。所以,大陆法系认为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是考虑过失的前提。而英美法系则与大陆法系完全相反,可预见性规则将过失作为确定因果关系的前提。这就造成我们大陆法系学生认识上的疑惑,无法理解英美法系将过失作为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前提。
其实,造成我们大陆法系学生对于可预见性规则不解的根本原因在于英美法系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近因关系,而大陆法系则不加区分统称为因果关系。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体系中的因果关系仅指英美法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过失则相当于英美法系的近因关系。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英美法系把过失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因为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近因关系。
英美法系将过失与近因关系联系起来,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又有主观上的原因。从客观上讲,随着工业的大发展,各种不可预期的损失的极大增加,过失与近因关系都很难从其本来面目上予以精确认识,立法者或者学者的单纯的主观化过失与客观化近因关系也日益体现出局限性。从主观上讲,英美法系将过失与近因关系联系起来后,即在某种程度上将近因关系问题转化成过失的问题,随着过失认定标准客观化的趋势,使得近因关系的认定从主观趋于客观,有利于简化法庭对近因关系的认定,如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如汉德公式来认定过失。[18]
可预见性规则其实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路,即在侵权行为的归责中,不再孤立的看待过失和因果关系,而要有意的将两者相联系,通过从法律和社会对一般人注意义务标准的认识将过失与因果关系的认定结合起来。众所周知,普通法是强调程序的法律,从某种程度上讲,可预见性规则是人们追求不仅要实现法律的形式正义,也要努力实现其实质正义的结果。
三、结论
英美侵权法是英美民商法的一个难点,近因关系更是难点中的难点。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个观念,即以英美法系的视角去理解英美法。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侵权法这个领域有不少概念上的差异,但二者的基本原理都是一致的,作为我们大陆法系的学生只有在充分理解两大法系相关概念的差异的基础上,才能准确的理解英美侵权法对于近因关系的认定,才能正确地将英美法中合理、先进的规则引入大陆法的法律系统中来。
「注释
[1]《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王家福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2]《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研究》涂斌华 civillaw.com.cn
[3]《比较侵权法》 李仁玉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77页。
[4]该规则含义为若无行为人之行为,损害结果便不会发生,则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着事理上的因果关系;若无行为人之行为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事理上的因果关系。
[5]该规则意为当某一行为系某一结果发生的重要因素或实质性因素时,该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质要素规则是对必要条件规则的补充,为解决复合式因果关系并弥补必要条件理论的不足,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于1920年的Anderson v. Minneapolis案中创立了实质要素规则。
[6]该规则主张侵权人应当为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论该结果对侵权人而言有否可预见性。
[7]该规则主张侵权纠纷的被告仅就可预见之损害结果,且就该损害结果可预期发生之原告,负赔偿责任。
[8] See Ryan v. New York Central R. Co. (1866) 35 NY210.91 Am. Dec
[9]《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研究》 王旸 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第488页。
[10]See Re Polemis, [1921]3K.B.560 (C.A.)
[11]See John G. Flem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orts.P.119
[12]《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研究》 王旸 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第489页。
[13]See Harvey McGregor, McGregor on damages, fifteenth edition (1988),P.81。
[14]《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研究》 王旸 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第490页。
[15]See《Canadian Tort Law: Causation》 duhaime.org/Tort/ca-caus.htm
[16]有观点认为直接结果规则现在只大体适用于侵权人行为时有主观故意的侵权案件。《一般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和过错之关系初探》李小田 civillaw.com.cn
[17]《重新解释侵权行为法的公平责任原则》 徐爱国《政治与法律》杂志2003年第6期。
第4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非法证据;言词证据;实物证据
证据领域关于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效力与可采性问题,随着世界人权保障潮流的兴起与现代国家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也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关注的热点和证据制度的重大命题,这在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加以研究并建立适合我国的制度构想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一)非法证据的含义
证据具有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广义的非法证据,等同于不合法证据,指“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其范围包括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内容或表现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等因素不合法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而取得的证据,也即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有的学者称之为“非法取得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类型
1.收集或者提供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若由上述主体作证人提供的证据是为非法证据。
2.取证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如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的证据是为非法证据。
3.内容上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
4.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七种表现形式的证据材料。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产生于美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最初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于非法逮捕、搜查获得的实物证据,最终才运用于言词。美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较为严格,后根据需要有所松动,据此确立了①稀释原则②必然发现原则③独立来源原则④善意原则。
二、我国刑事诉讼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
1.立法司法现状。我国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取证行为都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但是非法证据能否在程序上加以排除、否定其证据资格,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特别是从程序法方面,没有明确的制度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执法现状。尽管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禁止非法搜查、扣押,但是未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因而在司法实务中违法法定程序而取得的证据基本都予以采用;我国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文禁止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律上的效力,但是刑讯逼供仍屡见不鲜。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
1.我国没有明确的证据法,现行诉讼法中虽然设有专章规定证据制度,但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粗疏、抽象,只有一个粗略、抽象的框架性规定,许多具体问题没有涉及。
2.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仅限于言词证据,而未纳人实物证据。
3.我国侦查机关的行为不规范。关于排除通过非法手段搜查、扣押所取得证据的规则在我国还尚未确立,并且在实践中我国有侦查权的机关常常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
4.有关非法证据问题的救济不健全。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构想
(一)观念更新。我们要打破传统观念,树立权利保障观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树立新的符合世界诉讼民主化潮流的观念,是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想基础。
(二)立法完善。
第一、要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涉及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应用,故它又是一个宪法问题。对此,我国宪法的相关条文虽也作了概括性规定,但不够明确和全面,我国宪法可以借鉴美国等宪法的规定,应增设专条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
第二、要从诉讼法上加以完善。宪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诉讼法对其精神更应进一步具体落实。①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可借鉴英国、德国的有益经验;②关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可借鉴美国和日本的有益经验;③关于“毒树之果”即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发现的其他证据的问题,美国实行有例外的排除原则;
(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配套制度。
1、证据来源保障制度。包括明确规定证据的范围和可采的证据种类;赋予有侦查权、取证权的人员取得证据的必要权限及必要的取证手段。
2、取证行为规范。包括严格规范各类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取证行为。
3、确定沉默权制度。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仅从协助司法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的角度考虑,回答有关身份等基本情况的问题,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的根源。
4、肯定在场权制度。确立言词证据收集时第三者的在场监督权,尤其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律师在场权。打破侦控过程暗箱操作的局面,从程序上制约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可能性。
5、强制侦查行为审核制度。检察机关是我国专门的法律实施监督机关。当侦查机关需要采取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原则上应先报检察机关审核决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由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自行决定。这样有助于减少非法实物证据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刘晶.非法证据排除诉讼价值的冲突与抉择[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12).
[2]何家弘,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88.
[3]刘善.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74-195.
[4]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9.
第5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客观解释规则 WTO 争端解决机构
一、引语
法律的存在天然与解释分不开,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离不开解释。实践中,我们很难以想象会有脱离解释的法律。因此,法律解释在法律的创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其都离不开法律解释;一般来说,在国内法中,较多称之为法律解释;而在国际法中,在很多情况下称其为条约解释。不论是法律解释还是条约解释,在解释之中难免会带有解释者的偏好--即解释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所遵循的解释规则。因此,对于采用何种规则对法律/条约予以解释,实践和理论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见仁见智。
在WTO争端解决中,同样会遇到对其涵盖协定的解释,纵观其近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发现,WTO争端解决机构运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⑴对WTO各协定的条款做出了许多颇具创造性的解释,总体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⑵然而,在解释的过程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应持何种解释规则为学者们所关注,其中有不少学者担心其会走向解释的能动主义。对此,笔者以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其采用较多的仍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对条约解释所坚持的客观解释规则,同时也会折衷采纳目的和宗旨解释。因此,客观解释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客观解释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的运用
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客观解释规则主要是规定在"解释之通则"的第31条之中。具体对该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该条对条约解释应遵循的一般规则有:善意解释原则、约文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嗣后实践解释方法和目的与宗旨解释方法。笔者认为,约文解释方法和体系解释方法直接体现了客观解释学派的观点,从而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中也是DSB对协定解释的首选,从而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根本出发点。
(一)约文解释方法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出发点与中心环节
条约解释的出发点与中心环节就是审查与阐释条约的约文。⑶因为探求条约文本的文义是条约解释的首要目的,条约的解释目的主要是阐释现存有效的条约文本的字面含义,以寻求妥当的结论,而并非探究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律。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约文解释也不例外,纵观其历史及其运行的具体实践,无论是以前的专家组还是现在的专家组以及上诉机构都特别强调约文解释的基础地位。归纳起来,在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对于约文解释方法的运用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第一,强调约文用语中通常含义。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报告中都强调首先要从约文的普通含义出发。对此,有学者认为,自从国际上出现WTO之后,设在日内瓦的上诉机构强调以文字取义为先,和尽在咫尺设在卢森堡的欧洲法院主张的目的论(Teleology),形成鲜明对照。⑷
例如,日本含酒精饮料税收案⑸是WTO上诉机构审理的第二个案件,在该案中,上诉机构根据国际法院的几桩判例⑹最后得出结论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的文字奠定了解释方法的基础。解释必须基于条约的约文。要按其上下文给条约规定以正常含义。在认定其规定的正常含义时还要重视条约的目的与宗旨。"⑺这段话在强调以约文的普通含义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对《公约》第31.1条的解释也十分全面与详细。⑻
第二,参照字典并重视用语的字典含义。WTO成立以来,上诉机构几乎在每一起案件中都引用《牛津英语词典》作为解释WTO规则的首选。⑼为了适用约文解释方法的需要,在WTO秘书处以及法律司,摆设了很多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权威字典。仅英文字典就有Oxford、Webster、Black Law Dictionary等版本,应有尽有。甚至有学者调侃道,查字典成了家常便饭。有些批评者讥讽地或者戏谑地说:"牛津字典(用得最多)变成了WTO的一个涵盖协定。"⑽
第三,适时考虑约文用语中的特殊含义。正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4条的规定,如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应使条约用语具有特殊意义。可见,如果要采用某一术语的特殊含义的话,并不是随意的,一般需要有相关当事国有特别"确定"的指向。在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也是如此,对于一些协定中用语的特殊含义,WTO争端解决机构也会赋予其该特殊的含义,当然这些也会结合缔约方所使用的协定术语本身隐含着该特殊的含义。例如,当涉及到农产品协定第5.1(b)条中"进口到岸价格"(the C.I.F import price)的含义时,由于CIF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在欧共体影响家禽类产品进口的措施案⑾中,上诉机构就采用了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CIF的界定来解释这一用语。⑿
(二)体系解释方法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有力支持
与国内的法律解释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一样,WTO争端解决机制运用上下文之体系解释方法解释协定术语含义的实践是十分普遍并且广泛的,当WTO协定中词语的含义出现较多时,WTO争端解决机构重视通过上下文来确定该用语的确切含义。如前文所述,就WTO协定而言,这里的上下文不仅包括该用语所在的协议,还包含其他协议的具体条文。当DSB解释某一特定协定时,WTO相关协定之间由于其内在联系可以被交叉引用,当然,这种引用还需要考虑不同条款之间联系的紧密型。
例如,在1995年美国棉织和人造纤维内衣进口限制案⒀中,针对美国对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产品追溯性地适用了过渡保障措施时,专家组指出:"由于《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对此未作出规定,我们应检视GATT1994的有关条款是如何处理的,后者和《纺织品和服装协定》一样都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GATT1994第10.2条就是这种相关条款。"⒁但是上诉机构对此并不赞同,其认为,《纺织品和服装协定》第6.10条己经做出相应规定。⒂由此,也许可以推导出:"在同一子协定中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参考其他子协定中的同类规范。"
整体来看,WTO的约文、序言与附件是争端解决机构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运用体系解释方法所依据的主体部分。约文、序言与附件包括了整个WTO法律体系。在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对WTO争端解决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首先就是将意义不明确的条款或语句放入其所在的段落、篇章乃至整个WTO协定中去加以解释。
综上,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几乎会在每个案例中都会运用上述客观解释规则。如前所述,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运用例如目的与宗旨的解释方法以及甚至会进行司法造法的情形,但是客观解释规则在很长时间扔会是它对协定解释的基石。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有其背后深层次的因素。
三、WTO争端解决机构运用客观解释规则的成因
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所具体采用的解释规则对争端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不断发展与增加,由于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建立的目的、宗旨、性质、管辖权、受案范围的不同,从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条约或协定进行解释时,会选择不同的解释规则。WTO争端解决机构已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特点,而在这些特点背后,也有其自身理由及其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DSB在管辖权上的强制性是其选择条约解释规则的根据。
管辖权是任何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争端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任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受理和审理案件的依据和前提条件。具体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而言,笔者认为,WTO协定在管辖权上的具体规定为其选择适当的条约解释规则解决各成员方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合法的根据。
WTO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主要在《WTO协定》附件2的DSU之中。专家组在实践中参考了国际法院的审案原则以及关于国际法院内部运行的理论或学说,确认自己有权决定是否对争端有实质管辖权;这种自裁权在实践中也基本得到了上诉机构的肯定。⒃
因此,专家组断案中确定和行使自裁管辖权,即是发挥专家组审案能动性弥补成文规定不足的例证,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WTO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⒄第一,专家组借助自裁管辖权,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需要,将一些附带非WTO涵盖协议明确的问题纳入发表建议范围;同时专家小组可以利用司法经济原则"避免对有关WTO法内部冲突问题作出明确结论"。⒅第二,专家组可以依据"管辖权之管辖权"原则,审查在更广范围内涉及非WTO诉请。WTO专家组有权决定听取和决定这一主张,尽管争端大部分包括国际法的其他原则。⒆专家组有权判定自己是否可以聆听有关附带WTO法方面的主张,判断此方权利存在的形态,而且开始时并不需要当事方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第三,专家组在以往案例中审查了投诉方诉讼请求中的有关双边条约,比如在"巴西向欧盟出口家禽制品案"的争端解决中,巴西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中提到与欧共体的双边协议,并称欧共体违反了该双边协议,但协议本身是否属于专家组的权限范围是一个问题,因为该协议不是DSU意义上的相关协议。专家组将该问题作为实质审查前的基础性问题来解决并决定在涉及欧共体在WTO协定下对巴西的义务的范围内审查油籽协议。⒇
其次,DSB的准司法性质是其坚持约文解释方法的出发点。
应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极富创意和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尽管其在诸多方面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但是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其是一个具有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构,还不是绝对的司法机制,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也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来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而作为准司法机构,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进行解释时,为了保证其权威性以及得到有效的实施,由此,其首选的解释规则就是约文解释规则,尊重条约约文的规定。进而去寻找相关的上下文以及嗣后相关的行为和做法。
当然,对WTO协定条款的解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套用的公式,但是有一定是肯定的,即在解释的过程中,需要维持协定的可预见性与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和动态发展等,同时更要平衡各成员方之间的利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解释要素和规则也没有一定的位阶。但事实上,坚持善意的原则,约文解释为出发点,即以条约用语通常含义为起点,从特定的含义到上下文再到目的和宗旨,一旦约文解释仍不明或造成显然荒谬时,在考虑从所采用的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与缔结情况在内的补充解释资料中进一步寻找证据,这无疑构DSB对协定解释的基本逻辑顺序。由此,对于具有"准司法性质"的WTO争端解决机构来讲,其坚守客观解释学派,更加青睐于上下文中的约文解释也就可以理解了。
最后,WTO协定"一揽子协议谈判方式"以及其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是DSB采用上下文解释方法的主要依据。
WTO以"一揽子协定谈判方式",即以其"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套餐方式适用于WTO的领域,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之一。纯粹从程序角度来看,它似乎只是一种立法方式。对于,"一揽子协定"谈判方式本身,虽然在实质上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获利益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趋强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依然会在相当时间内在国际贸易立法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WTO争端解决的过程中,面对WTO协定的错综复杂以及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现实,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其协定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各个协定之间的交错与交叉的关系,并且较多地运用各个协定作为解释"上下文"去确定协定中的"歧义"或空白中的含义,从而以平衡各成员方在WTO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
四、结语
综上,从目前WTO的司法实践来看,DSB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所进行的解释以及运用的解释方法是成功、有效的,这对于解决WTO成员间具体争端,澄清WTO协定现有规定模糊之处,确保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及WTO规则适用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前文的分析与论证我们知道,总体上,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实践中,其对协定的解释也遵循着《维也纳条约法》的条约解释的规则:即尽可能坚持上下文中的约文解释之客观解释规则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其协定解释的主要特点。
参考文献:
⑴DSU第3.2条规定:"WTO争端解决体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保护各成员在涵盖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BS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⑵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1页。
⑶陈欣:《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司法克制主义VS.司法能动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⑷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⑸Japan - 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WT/DS8, WT/DS10, WT/DS11, requested on 21st June and 7th July 1995.
⑹主要是指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之间领土争端(Libyan Arab Jamahiriya/Chad)和1995年卡塔尔与巴林海上划界案(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⑺See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p. 7, adopted on 1st November 1996.
⑻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⑼陈欣:《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司法克制主义VS. 司法能动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⑽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⑾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ation of Certain Poultry Products, WT/DS69, requested on 24th February 1997.
⑿WT/DS69/AB/R, p.51, footnote 89, adopted on 23rd July 1998.
⒀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Cotton and Man-Made Fibre Underwear, WT/DS24, requested on 22nd December 1995.
⒁See WT/DS24/R, p. 7.64, adopted on 25th February 1997.
⒂See WT/DS24/AB/R, p. 12, adopted on 25th February 1997.
⒃在1916年美国反倾销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中,上诉机构注意到一国际法庭有权主动地审查有关管辖权问题,并使自己相信对目前进入程序的任何一宗案件享有管辖权。在此上诉机构报告的脚注中列举了大量论据,包括国际法院案例法官的意见和个别法官的意见、著名国际法学者的论著、国际仲裁规则和实践等,以此作为专家组类似地享有此种权力的论据。See WT/DS162/AB/R, WT/DS136/AB/R, footnote30,P.17.
⒄赵秀丽:"世贸组织专家小组'自裁管辖权'初探"载http:///cacs/lilun/lilunshow.aspx?articleId=36272,2012年8月5日访问。
⒅余敏友、陈喜峰:"论解决WTO法内部冲突的司法解释原则(下)"载入《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 页。
⒆Joost Pauwelyn,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AJIL)2001, vol95, No.3, P556.
第6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理性化模式最佳化模式裁判规范
作者陈林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08)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是法律方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四十年来持续位居国际法律理论的研究前沿。德沃金和阿列克希为代表的法律原则理论,以基于“规则-原则”二元规范模型的整全性、融贯性和“权重公式”,展示了法律原则适用中“理性化考量”的方法和判准,但被批评为“难以信服”、“基本没什么价值”。①法律原则的反对者甚至认为,法律方法论只需两种类型的规范:正确的道德原则和实定化了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既无法律规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定性优点,又不具备道德原则具有的道德正确性优点,所以在法律方法论中并无一席之地。②不过,倘若否定法律原则的规范地位,那么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难案件的裁判中,法律推理是否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藉由对规则、尤其是原则之类别的进一步细分,能对法律原则的适用过程――尤其是规则和原则的关系――给出一个更清晰的结构性分析,并回应、澄清对原则理论的一些诘难和误解。
一、规则的两种属性:自主性和总括性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陈林林:法律原则的模式与应用
法律原则理论作为一个系统的规范理论,见诸于德沃金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通过描述原则在疑难案件中的裁判功能,并藉此确立原则的法律属性或法规范地位,德沃金意欲否定“法律是一个由承认规则保障的规则体系”这一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并据此重新划定法律的边界。在对Riggs v. Palmer案和Henningsen v. Bloomfield Motors案的解读中,德沃金论证了一种与法律规则全然不同的法律原则。具体说来:其一,规则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适用的。对于个案来说,构成事实要件一旦确认,规则就要么适用(规则生效),要么就不适用(规则无效)。由于原则并未清楚界定事实要件,因此对个案来说,并不存在一条确定的、排他适用的原则。一条原则只是支持这般判决的一个理由,同时却可能存在另一个更优越、更适切的原则,要求作出不同的判决;其二,原则在适用中含有一个规则所没有的特性,即“分量”或曰“重要性”。当不同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官必须权衡每一条原则的分量并择优录用,但这不会导致落选的原则失效。规则的冲突直接涉及效力问题,不予适用的规则会事后失效,并被排除在既定法律之外。③德沃金随后指出,形式取向的承认规则无法识别出法律原则,因为法律原则并非源于立法者或法院的某个决定,而是一段时期内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形成的公正感,需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才能得到识别。④法律实证主义的巨擘拉兹,试图否认规则和原则之间的“质的差别”,来化解德沃金的批判。拉兹指出,某些貌似法律原则的评价性标准,只不过是法律规则的缩略形式;法律规则在相互冲突之际,也存在分量上的比较。⑤所以,原则和规则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上的,而非逻辑上的。拉兹进而以社会来源命题为分析工具,强调了法律原则的事实属性。他主张即便法律原则是一种道德评价,那么它也是一种事实存在的公共价值标准。因此,“法律”的内容及其存在与否,仍可以参照社会事实、依据承认规则予以决定,而无需诉诸于道德权衡。⑥
德沃金和拉兹的争论,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各自可能存在双重属性或二元类别。法律规则作为一种一般化的规范性指示,由事实假设和行为方式或后果两部分组成。制定法律规则的理由或依据,是道德原则平衡或价值判断;换言之,法律规则是对各种道德原则进行通盘考虑之后进行理性选择的产物。法律规则一旦形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opaque)了规则背后的道德理由,即规则的适用不需要法官再行关注设立规则的一系列原则。判断规则是否可得适用,只涉及理解表述规则的文字,确认争议事实是否存在,并对照这二者是否一致。⑦当一条规则依赖若干相关的一系列原则的平衡得以正当化后,规则随后就排除或取代了那些原则――即所谓的一阶理由或基础性原则――直接适用于规则自己所涵盖的那类事实情形。这就是规则的二阶命令、排他性特征的来源。排他性理由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排除了理由的通盘考量这个实践原则,即规则不仅排除了其他理由的适用,而且自我界定为采取特定行动方案的一个理由。规则具有的二阶命令、排他性的特征,显现了规则在适用上的一个属性,即规则的“自主性”。
规则的“自主性”地位,来源于规则的另一个属性――“总括性”,即作为一种一般性规范的规则代表的是一些全局判断,是对各种一阶理由或一系列原则进行通盘权衡后所做的行动选择。规则的总括性特征,让法官“依规则裁判”时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减少偏见、避免自行权衡出现错误。但要注意到,可错、偏见与成本,是理性行动所固有的缺陷,作为总括性解决方案的法律规则,本质上仍是一种“次优”而非“最优”的解决方案。因为最优的行动方案至少建基于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拥有有关个人处境与行为后果的完整信息;二是发掘出适用于该处境的全部理由;三是对于该理由适用的推理过程是完美的。这些条件的结合,才使得“理性的行动”呈现出“在获得有关行为人所处实际境况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找到对行为人的行为最佳支持”这个基本含义。但这是太过理想化的看法,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⑧
德沃金和拉兹皆指出,规则最主要的逻辑特征是其“决定性”:当一个具体的事实情形符合规则的适用条件,那么规则就必须得到遵循。自主性意义上的法律规则,是排除一阶理由意义上的原则权衡的,或者说,在适用中是怠于或否定对一系列原则的权衡进行持续评估,因此其始终是具有决定性的。对于总括性意义上的法律规则而言,只要法院不改变对道德原则之间的基础性平衡的认识,那么它同样是具有决定性的。不过,当法院对基础性的道德原则平衡的观点发生变化时,总括性规则就会不断地得到修正。显然,较之自主性规则,总括性规则的“决定性”更弱而“内容性”更强。与规则适用中的自主性特征和总括性特征相对应的,是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⑨
二、原则的两种模式:理性化和最佳化
对于个案裁判而言,自主性法律规则必然是有拘束力的。当法官遇到了既有规则未予明确规定的个案时,如果要贯彻一致性和平等对待,那么依据德沃金的理论,法官能采取的合理方法是根据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能最佳地证成一系列相关的、有拘束力的自主性法律规则――来判决案件。如果所有这些法律规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那么法官可以认为,那些为规则提供正当性的法律原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当然,法官也可能认为,某些自主性规则在道德上也可能是错误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往往会主张,依据能从道德上正当化那些长期有效的自主性规则的次佳原则是合适的。次佳原则为道德上存疑的一些自主性规则做了最直接的辩护,藉此允许法官在判决新的案子时,能尽量与现行的那些规则保持一致。这种与规则自主性观念相辅相成的原则适用过程,因为仍然以一致性、可预测性等形式价值(次佳原则)为最优判决目标,被称为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⑩
前述分析表明法院(乙)认同先前判决设立的规则R,但支持理由却不同于法院(甲)。在这种情形中,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实际是重合的,因为最终的行动方案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纯粹基于法律原则的最佳化模式的分析思路,那么法院(乙)应追求个案相关的一系列相关原则的最佳平衡,因此不一定受法院(甲)的判决推理或结论的拘束,尽管法院在原则平衡时仍然要考量到可预测性、一致性等第二位阶的原则。换言之,法院(乙)在跨越适当的认知门槛后,可以法院(甲)的判决推理或结论,例如否定作为规则R之正当化基础的原则C2,修改规则R的事实构件,乃至否定规则R本身。当然,废弃规则R这样的重大法律变动,必须基于一些德沃金“整全法”意义上的整体性理由,即视为是错误的规则或判决,必然落在不能依最佳化证立予以正当化的那部分既定法律的范围之内。显然,基于最佳化模式的法律推理,还内置了罗尔斯式的审慎明智、协调一致的“反思性平衡”:在普遍性的所有层面上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其范围从关于个人具体行为的判断,到关于特定制度和社会政策之正义和非正义的判断,最终达到更普遍的信念。这意味着一条原则的法律地位部分地依赖于一种规范性标准,这个标准要求原则的内容和分量居于道德合理性的适当范围之内。法官必须诉诸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识别力,来判断这个标准是否得到了满足。换言之,法官们必须和自己进行道德论辩,而不单单是审查和以往其他人的道德推理相关的社会事实。藉此也再一次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因此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可以显现为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
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理论,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是有一定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但也难免于若干困惑。限于篇幅,此处只讨论隐含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A、法律原则的规范属性;B、适用法律原则的司法语境。C、原则适用的方法论。问题A所指的法律原则的“规范属性”问题,和反对法律原则的学者所提的问题相关却并不相同。亚历山大和克雷斯曾强调:法律原则既无法律规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定性优点,又不具备道德原则具有的道德正确性优点,因此在法律方法论中没有一席之地。前面的论述已指出,法律原则是独立于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但很显然,法律原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是不同于法律规则。这种“不同”的表面差异是行为指引上的确定性程度,实质差异是某个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则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但法律原则仅仅是一种“裁判规范”。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划分,可追溯至边沁的理论。边沁曾以刑法为例指出,“规定犯罪的法律与对犯罪施加处罚的法律,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它们管辖的行为完全不同;适用的对象也完全不同”。一条“禁止杀人”的规则,既是社会公众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杀人案件发生后法官必须考量适用的裁判规范,并且对于公众和法官来讲,“禁止杀人”都是一条明确的法律规则。相反,一条“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原则,尽管也是社会公众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但一般公众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并无恰当的能力(例如法律素养或法感)和信息(例如检索以往判例)――因此也无义务――去识别该原则是否是规范某一具体事项的一条法律原则。不过依据法律原则理论,一旦这类争议被递交到法官面前,法官就有义务去识别并适用与个案相关的法律原则;此外,判断一条道德原则是否是法律原则,取决于法官是否认定其得到了制度历史的支持,而与社会公众的认识或判断无关。换言之,法律规则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其适用对象既包括法官,也包括生活在某个法律体系中的社会公众;法律原则是一种裁判规范,它的适用对象仅仅是法官。
“法律原则的适用对象仅限于法官”这一命题无疑会招致批评,因为在适用法律原则进行判决的那类疑难案件中(例如泸州遗赠案、Riggs v. Palmer),当事人最终显然受到了法律原则的拘束。不过,这种批评只看到了裁判的表象。以泸州遗赠案的一审判决为例,纳溪法院实际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原则,针对遗产继承规则的效力设定了一条“第三者继承例外”的新继承规则。法云“一般条款不决定具体案件”,正是将《民法通则》第7条具体化为个案规则后,法院才否定了遗嘱的效力和第三者的继承权。因此一个补充性的亚命题是,“当法律原则适用于待决案件时,必须先具体化为一条个案法律规则;这条新创设的法律规则必然是可普遍化的,它既适用于社会公众,也适用于法官”。用阿列克希的“原则间的竞争法则”(Law of Competing Principles)转述之:当法律原则P1在C的条件下优于法律原则P2,并且,如果P1在C的条件下具有法效果Q,那么一条新规则R生效,该规则以C为构成要件,以Q为法律效果:CQ。
藉此转换到了问题B:适用法律原则的司法语境。一个已有的共识是,依据“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裁判纪律,唯有在“规则用尽”的疑难案件中,方得考虑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和“裁判规范”的定位,都表明原则裁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而是一种创设规则的准立法性法律实践。事实上,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引证的就是以法官为中心的普通法司法实践。离开普通法司法的语境,法律原则理论中的若干关键词――例如“制度性支持”、“先前判例”、“分量”、“”――的内涵就会引发歧义。因此,在司法体制和法官角色存在重大差异的大陆法系,尽管成文法中存在不少概括性条款或原则性规定,但法院是否可以根据最佳化模式进行规则创制并进行裁判说理,始终夹杂着诸多需澄清的问题,诸如法院的地位和功能、法适用和法创制的区分、法不溯及既往等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原则适用的方法论。法律原则的“分量”、“最佳化”等属性,从字眼上就表明原则裁判的关键,是用法政策式的权衡或类推去获得判决,其间必然诉诸对相关的不同后果及其可取性所做的比较和评估,即利益衡量。就如麦考米克所言,倘若判决所依据的那些相互竞争的类比、规则或者原则存在于法律之内,并表明判决为既有法律所支持――尽管不像明晰的强行性规则所提供的支持那般明确,那么法官有权作出相关的评估并使之生效。德沃金后期实际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整全性意义上的、向前看的结果导向论者。原则理论的支持者阿列克希,则进一步精细化了结果考量式的衡量方法,建构了一个复杂的“权重公式”:W1-i,2-j=(I1×W1×R1+……+ Ii×Wi×Ri)/(I2×W2×R2+……+Ij×Wj×Rj)。不过,所有这些努力――包括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理论――回答了一些问题,却又制造了一些新问题。
四、结语
哈特认为在法律规则不能给予判决以完全指引的案件中,裁量权的运用是在一些标准和政策指引之下进行的。不过,哈特对这些标准和政策存而不论,并否认其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恰恰是德沃金这样的法律原则论者所反对的。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为原则裁判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结构性分析,还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法律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裁判规范”。“裁判规范”的定位,保证了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案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尽管这种源于普通法司法的推理模式在方法论和制度环境上遗留了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
注释:
①See Brian Leiter, The End of Empire: Dorkin and Jurisprud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36 Rutgers Law Journal, 2004, p.165.
②Larry Alexander & Ken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ple’, ed. in Law and Interpretation, by Andrei Marm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6, 327.
③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4.
④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05-17.
⑤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9-30. 麦考密克认为,原则“实际是一种更概括的规范,是若干规则或若干套规则的合理化结晶”。See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232.
⑥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53.
⑦Alan H. Goldman, Practical Rules: When We Need Them and When We Do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7.
⑧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
⑨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2.
⑩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5.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
Richard Posner, ‘Pragmatic Adjudication’, in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Morris Dickstein ed. 1998. cited from Adrian Vermeule, 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7.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801.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0.
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3.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43.
斯蒂芬・佩里的分析较为繁琐,下述行文对其进行了概括梳理,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01。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430 (W. Harrison ed. 1948). Cited from Meir Dan-Cohen, Decision Rules and Conduct Rules: On Acoustic Separation in Criminal Law, 97 Harvard Law Review,1984, p.626.
Cf.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4.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73.
第7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保险条款,疑义利益,适用位阶,目的解释,限缩解释
保险立法史上,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援引与创设,初始系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进行司法调整以实现公平交易,并体现对保险交易中的弱势群体-被保险人倾斜性保护的价值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亦遵循了此一先进立法理念,移植并确立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该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然而,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在我国保险司法实务中,法院动辄适用该法第30条,作出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与判决,以致保险公司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有鉴于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法律适用上之位阶如何?其适用的条件是什么?范围又何在?等等,都有必要对保险契约的“疑义解释”规则作出解释,以利于公平合理地保护保险当事人双方的权益。
一、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法理基础及其目的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又称“不利解释”规则。此种解释规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1 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系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2 之所以当保险条款用语出现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学说和判例所持依据及其目的主要有四:
1.“附和契约说”。该说认为,保险契约所载之条款一般皆由保险人预先拟定,实际上虽多由投保人为要保申请,但在通常情形,其对保险单之内容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和契约。若保险人在拟约时,能立于公平正义之立场,不仅考虑本身,亦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契约之附和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绝大多数拟约人皆未能把持超然之地位,惟以契约自由之美名,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其相对人对此惟有接受或拒绝;别无选择。在此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则流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对于内容订定之自由完全被剥夺。因此,当保险契约之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制人之解释。3
2.“专有技术说”。该说认为,保险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商行为贯穿了几个世纪,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史诗。4 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危险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测定事故发生的比例(即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摊风险。根据概率论的科学方法,算定分担金要有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技术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共同特征。5 保险条款中所涉及术语的专门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若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条款之必要。但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因此,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3.“弱者保护说”。该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1)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业具有垄断性质,谈论合同自由是虚幻的;(2)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6 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当对保险单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4.“满足合理期待说”(honoring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该学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7 是在“附和合同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③该学说的主张者是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来阐述其理由的: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时至今日,保险交易类型繁杂,而保险契约类型有限及保险契约所约定之条文有限,以有限之保险契约类型承保日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即力有未逮;况保险契约之订定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保险人对保险契约内容固然具有“专业理解”,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日后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专业理解与要保人对保险契约之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只要要保人之期待合理,则此种差距之不利益应由保险人承受,法院应遵循“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9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学说与理论,前三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的法理依据及其目的,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附和合同说”和“专有技术说”从保险人的角度,揭示了疑义解释规则的归责原则,即因其为保险条款拟制人或使用人以及拥有专门技术与专业知识,在拟款措辞时,理应尽相当合理之注意义务和相当之诚信,以明确方式使相对人了解其义,否则应承担疑义之不利益;而“弱者保护说”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站在被保险人的立场,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价值取向,描述了保险交易中被保险人“弱者地位”的情形及其成因,从而阐释了疑义解释规则的旨趣,即疑义解释规则出于工具理性之目的,通过这种工具理性而为处干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上的救济。
笔者以为上述“满足合理期待说‘不仅不能成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理论基础与法理依据,而且是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背离。因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归责原理是:若合同条款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条款拟文人的解释。其隐含的前提是:若合同条款的语句或术语清晰而明确,法庭不能对合同术语进行强制解释。而现代英美保险法中的”满足合理期待学说“可以解释为:法庭重视并尊重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合理预期,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术语并不支持这些预期。10 这样看来,”满足合理期待说“是对传统合同法的背离。这种”背离“的弊端是明显的:首先,会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一方当事人会认为,法庭不应再解释明确而清晰的合同语言;而另一方则认为,除非清晰而明确的合同语言另有规定,法庭应授予投保人合理预期的权利。其次,保险人会认为法庭只考虑了投保人的合理预期,而没有考虑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产生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导致较高的保险费率。最后,某些被告知的投保人可以得到他们没有预期的保险保障,因为一般的投保人是会预期该保险保障的产因此,正如美国著名保险学者所描述的”满足合理期待说“在一定程度是”法庭判决的保险“。12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之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基础和目的,系基于保险合同为一种附和合同,保险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加之被保险人欠缺保险专业知识,且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为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当保险条款的用语有歧义或模糊时,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目前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一种对保险合同附和性的司法规制手段,以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救济方式。
二、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之适用位阶
适用于保险合同的具体解释规则很多,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判例中,“能够发现的解释规则大约达13个。”13 当保险条款文义有疑义时,解释上应否优先适用疑义解释规则,颇多争议。归纳起来,有下列三种学说:14
1.“肯定说”,又称“主观说”。该说认为由于保险条款都由保险人拟定,所以在享有选择符合其目的的措辞之权利同时,也负有将之清晰地表达出来以让对方了解的义务。如果有疑义,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以符合“如果有疑义,反对拟文人”的原则。支撑肯定说的理论基础为前述附和合同理论。附和合同与那些通过双方当事人相互磋商和妥协而形成合同条款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在大多数场合,当事人意思优先这一主要原则,建立在不正确的前提下,即保险合同是同等力量的当事人间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些当事人讨价还价,把他们的协议归纳成书面的。”15 因此,当保险人选定保单上的语言。书写保单,并将其卖给投保人后,如果该保单中含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解释规则,对此条款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
2.“否定说”,又称“客观说”。该说反对主观说的见解,认为主观说将疑义解释规则视为“优先原则”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它出自于个别保险合同的主观解释原则,而忽略了一般格式保险合同条款适用于危险共同团体内各成员的客观性。因此,该说主张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的疑义条款时,应当立于完全超然的地位,没有作不利于哪一方当事人解释的必要。支撑否定说的理论基础有二:其一为“团体契约说”。该理论认为,保险为一种分散危险的工具。危险的分散需要有一个遭受同类危险威胁的共同团体来承担,故任何一种保险均需以一危险共同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此团体由各个因某种危险事故发生而将遭受损失之人(被保险人)所组成,而保险人仅是负责集中危险及管理危险而赚取营业利润的组织。因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将有损危险共同体之根基。16 其二为“政府干预说”。该理论认为,一般定式合同保险条款并不是全部由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条款在应用前须先经保险监督机关的审查。由于不可能期待保险人具有将条款内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事先考虑清楚而表达出来的能力,所以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有违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原则。因此,“客观说”视已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查通过的保险条款具有和法律相同的效力,其解释方法应依一般法条解释原则,无所谓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必要。
3.“折中说”。折中说首先反对客观说的见解,其理由为:事实上无任何格式保险合伺条款的制定,由被保险人以同样的地位和保险人共同完成。即使其条款的应用需经保险监督机关的审查,但也只以保险人所提的稿案为案臼而已,并且审查机关为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不得将审查核准后的条款视为法律规定。这就要求保险人在拟稿措辞的时候基于其丰富的经验,应考虑各种可能产生的状况并付诸于文字,以明确的方式使对方了解其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并未违反平等对待原则,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不是只对一两个被保险人,而是对所有的被保险人都可适用。另一方面,对于不明确条款的解释,也不得纯就被保险人个人的利益而即刻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首先应顾及保险危险共同团体的概念及保险的真谛,参前该合同的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如果仍无法确定该有疑义条款的意义时,则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笔者认为,作为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特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有在适用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情况下方能得以适用。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17 之所以要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首先适用保险合同解释的一般解释原则,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原则”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为:首先得以适用的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意图解释原则。从保险单本身及任何附件(例如投保单等)中发现的当事人的意图应居于统治地位。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意图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保单条款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方为可能。18
三、保险条款是否疑义之判断标准
一般认为,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实质要件是保险合同中所载条款之用语“模糊不清”(ambiguity)。这一原则通常被叙述为“模糊规则”(ambiguity rule):如果标准的保险合同的某一条款意思模糊不清,法院将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条款解释。19 但问题是:是否所有的保险条款均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用语模糊不清之判断标准为何?等等,需要进一步探究。
1.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是否适用于个别议商性条款现代商业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通常由定型化契约条款与个别议商契约条款共同组成。《保险法》第18条、第19条对二者分别作了规定。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保险人名称和住所……”;第19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前条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作出约定。”其中,定型化契约条款均由保险人自行拟定,但需报保险主管机关核准方可使用。我国《保险法》第106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但由于保险标的不同、保险期间不同、保险条件不同等原因,定型化契约条款无法一一涵盖,更无法切合个案保险的需要。因此,实际上又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以个别议商方式,另行约定,此即个别议商条款。20 当投保人参与了保险合同的起草,或者保险公司不单独对合同的语义负责的时候,疑义解释规则很可能会不再适用。“ 21 依前述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利于条款拟订人“原理的实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当仅适用于定型化契约条款,而不适用于个别议商契约条款。个别议商契约条款的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
2.定型化保险条款是否“疑义”的判断标准
“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和前提,是保险合同的定型条款”模糊不清“(ambiguity)。”模糊不清“这一用语的本来含义,系指”一个词语具有两个以上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至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22 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方可适用。因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应为消除疑惑的目的而使用。据此,保单条款如不存在模糊不清,对保单的解释就无必要,此时该保单应依照其条款予以履行。
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将由审查案件的法院根据客观情况予以确定。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英美法院就此确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在考察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时,法院所使用的方法应当是能够“找到模糊不清”而非“制造模糊不清”的方法。23 其二,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将“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至于何者谓‘合同阅读者“,英美法院的确认标准各有不同: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两相比较,笔者以为,美国法院的标准显然更为合理。因为将合同阅读者确定为”正常的律师“对被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并
且“律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并非普遍接受的理解”。其三,英美法院除从正面对“模糊不清”的含义加以界定以外,还从个案中归纳出了许多不属“模糊不清”的例外情况,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条款不因其用语可以在字典中找到不同的定义而模糊不清,因为该用语的真实含义可能可以从上下文中清楚地推断出来;保险合同的用语不因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对其持不同的见解而必然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条款也不会仅因其难以解释、十分复杂以及保险纠纷的当事人对该用语诗不同的观点而模糊不清;即便是在保险合同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够阅读并理解该合同,该含同条款也不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综上,只有在经过全部考虑之后,法院仍认为无法解释,保险合同的条款才是模糊不清的。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如欲得到适用,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之处的产生不承担责任。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作为格式合同解释主要原则的“不利于制定人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体现。虽然保险合同的制定人通常均为保险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保险市场低迷、保险业务竞争激烈等),保险合同的某些条款也完全有可能由被保险人拟定。此时,如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就此条款产生争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不再适用,法院将允许当事人提交证据以证明谁应承担责任。
3.保险专业术语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保险单充满了“专门用语”,常常使未受训练的人迷惑。24 那么,当被保险人对专门术语按普通理解与保险人按专业含义理解不一致时,是否应当适用疑义解释规则,则无不疑义。这里涉及在解释该术语时是普通含义占优还是专门含义占优的价值判断问题。
对保险单文字含义进行解释时,一般应当首先按普通含义去理解词语,但在词语有“专门含义”时则不能按照普通含义去理解,这种情况下专门含义是优先的。25 保险单术语的专门含义优先于普通含义,主要有两种情形:26第一种情形是保险单中的词语“有专门的法律含义”。“有时,法律所要求的语言本身是不明确或者模棱两可的,则法院不会将此语言解释为对条款提出者或书写者不利。”27 第二种情形是保险单中的术语有“专门的技术含义”。“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表明其是在专门含义上使用某一词语的,则法院对该词语应解释为专门含义。”28上述情形出现最多的是那些规定责任或除外责任的词语。这些词语可能是刑事犯罪的名称,例如盗贼;或者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含义,例如保险危险中的“暴风”就有特殊含义,它并非普通含义上的“非常大的风”,而是专指17.2米/秒以上(相当于风力表8级以上)的风力,若小于这一衡量标准,就不是保险危险中“暴风”的正确含义。在上述情形之下,应按专业含义的解释从优原则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四、被保险人是否弱者之判断标准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创立,系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式予以诠释。”29 不过,由于在保险实践中,除了存在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保单以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有关的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
第8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法的渊源;国际法渊源;国际法的表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9-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分支部门,在发挥其维护国际秩序、协调国家间关系和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方面正逐渐显出它的强大力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国际法渊源内涵
同样在国际法领域,渊源的定义在不同时代也是不尽相同的。第八版《奥本海国际法》中,奥本海将国际法渊源比作水的渊源;而在第九版中,他又将此定义为:“行为规则得以产生并取得效力的历史事实。”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鲤生先生认为它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的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处所”。
而现阶段,国际法渊源的定义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英国的布朗利先生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存在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分:前者是为了制定具有一般适用性并对特定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后者为规则的存在提供依据,即一旦被证实,就具有一般适用的法律约束力规则的地位。
法律约束联合王国人民那样的方式来一般地约束各国的这种性质。因而布朗利先生认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不存在的,更难以维持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别。而王铁崖先生对此也表示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造法的宪法机构,因此,国际法不可能有所谓的‘形式渊源’”。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否定了形式渊源的第二种理解。
总而言之,国际法的渊源是特殊的,它本身不具有统一的宪法及立法机构。国际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不像传统的国内立法,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以某种国际法的法律表现的形式存在为依据,主要起到一定证明作用的法律渊源,而无论这种证明是历史的证明,还是法律的证明。
2国际法渊源的外延
在前文,我们已提到国际法渊源的外延非常广泛,至少包括:道德规范、正义观念、法理或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准条约(软法)、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国际习惯等。这里将其中争议较大、易混淆的三种(司法判例、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国际法渊源挑选出来,做一简单说明。对于司法判例,《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已明确规定:“法院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决只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从而使法院没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创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适用国际法时,总会对国际法律原则、规则、原理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常常会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国际实践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发展为一般法律原则、规则,因此判例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应为国际法渊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没有提到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可以作为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这可能与当时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没有现在重要有关。但是,国际组织本身是独立的国际人格者,其做出的决议属于单方面的行为,一般无法律约束力,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虽然它们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贡献,有的还成为缔结条约的基础。因此,它们是重要的国际法渊源。
3国际法因素
国际法因素是指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却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点在于:
第9篇:法律规则的含义范文
同许多含糊不清、令人生厌的概念一样,“法律渊源”(sourcesoflaw,fontesjuris,Rechtsquellen)这一语词让许多国际法学家头痛不已。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个用语的词义并非单一性的,而是如詹宁斯所言,大致包含四种意思:1.历史意义的渊源;2.作为识别法律规则的标准的技术意义的渊源;3.法律的可接受的和被承认的有形证据;4.制定、改变和发展法律的方法和程序。这种多义性导致的后果就是“法律渊源”与其他概念,诸如法律的起因、法律的依据、法律的形成过程等搅和在一起,使人难以看个清楚明白。一些学者为给“法律渊源”一个“名分”并进而厘清上述概念间的关系,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但其观点都不甚让人信服。如奥本海经典的“泉源”之喻受到了帕里(Parry)的批评;萨蒙德(Salmond)关于“形式渊源”(formalsources)和“实质渊源”(materialsources)的区分也遭到了布朗利(Brownli)的质疑。于是有的学者干脆说:“法律的‘渊源’一词的含混不清似乎使这个术语变得不具什么用处。人们应当不用令人误解的形象的措词,而应当采用一种明显地、直接地描述人们心目中的现象的措辞。”这种“一扔了之”的处理办法固然省了不少麻烦,但它同样抹杀了法律渊源作为一个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和沿用的概念的价值和意义。正如王铁崖先生所言,“尽管如此,国际法的渊源,作为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地方,还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故理智之态度乃是明确一个概念的使用语境,限定其用法而确定其含义,缚其多义之“翅膀”而令其难以自由飞翔.基于此立场,本文所称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效力产生的途径和过程;或者说“国际法效力的依据”。以此为前提,下面来探讨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国际习惯法。
二、国际习惯法的当下命运
习惯作为法律规则的渊源由来已久。罗马法将法律分为“成文法”(jusscriptum)和“不成文法”(jusnonscriptum),认为“不成文法是由经惯例检验的规则组成的;因为使用者的同意所核准的长期沿袭的习惯与成文法(statute)并无二至。”早期国际法学家和他们的先驱一样把习惯法描述为长期、不间断的惯例的不成文法。“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深受这个古典传统的影响,认为“万国法的证明与不成文的国内法相似;它可以在未遭毁损的(unbroken)习惯和深谙其中门道的那些人的证言(testimony)中被找到”。瓦泰尔(Vattel)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早期的主要国际法著作中把习惯法定义为“在长期的使用中被尊崇,并为国家在其相互交往中作为法律加以遵守的格言和习惯”。晚近,布莱尔利(Brierly)称之为“一种惯例,为其遵循者感到有义务的”。
对于绝大多数国际法学者而言,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渊源的两个主要形式。事实上,20世纪以前习惯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但是今天国际习惯法看上去有些时运不济:它在《国际法院规约》所列举的国际法渊源中仅居次席,而位于国际条约之后。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条约与习惯相比具有明确性,所包含的规则为国家的明示所同意,对国家有直接的拘束力,并且制定和更改更加灵活;相反,习惯确定的时间、内容和适用范围往往是不清晰的,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经过。另一方面,这也是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涌现,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些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看来,既有的国际习惯法渗透着传统西方价值观,因此坚决要求进行根本性的修订。国际社会整体规范的改变迫在眉睫,但习惯的不成文性质所隐含的不稳定因素和发展的时间上的拖延使它在与条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此外,与习惯法鼎盛时期相比国际社会成员规模大大增加(在一百年间,从40多个激增到170多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多,这就导致一项一般规则想要取得不同的国家的大多数支持变得“难于上青天”。国际习惯的“失宠”也就在所难免。
但若就此断言国际习惯法“穷途末路,气数将尽”,则为时尚早。首先,习惯同样具有条约所没有的优点。按照1969年《条约法公约》第34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也就是说,条约的效力仅及于缔约国,而不能逾越此范围对第三国产生拘束力(其同意除外)。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所有国家普遍参加的条约(《联合国》也不例外),且条约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它适用范围和涉及领域必然存在局限性。相对而言,国际习惯法则具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20年所作的判决一样,它通常被认为“(国际)社会的普遍之法”。当然,有些国际习惯可能只是区域性的,或者在一项习惯(即使是一般国际习惯法)形成过程中明白反对的国家被发现不受其拘束,但可以设想一下,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一道构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完备的法律体系。事实上,一套由条约和习惯法构成的法律规则仍然是不完备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习惯法具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
不但如此,习惯还是国际法以及一般法律的最古老和原始的渊源。因此,“虽然国际法院必须首先考虑对当事各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可适用的条约规定,但在发生疑问时,条约要以国际习惯法为背景加以解释,而且国际习惯法在它包含有一项强制法规则而条约与之相抵触的的范围内就将优于条约。”同时,在国际习惯法被收录(embodied)到公约后,它并不因此失去此后独立的有效性而仅仅依赖于相关的公约。也就是说,“当公约被拒绝承认或里边有条款规定听凭保留,拒绝或保留的一方可不再受其拘束”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国际法院明确指出:“法院不能驳回依据习惯的和一般的国际法原则所提出的主张,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被‘铭刻’(enshrined)进了所依据的公约的文本中……公认的,上面提到的原则已被编撰或体现在多边协议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停止存在和作为习惯法原则适用,即使是对公约成员国。”这样的习惯法原则包括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尊重国家独立和,等等。
最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尽然对国际习惯不利。应时代所需,国际习惯法在至少在三个方面仍将扮演重要角色。第一,由于在国家群体之间存在众多的的冲突和考虑所有紧密相关的因素的复杂性,迅速产生的新的经济需求经常不能及时被条约整理和调整。与此相对照,由一个或更多国家提出的有关一定争议的解决办法,最后可能满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并逐渐致使习惯规则出现。关于这点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新近出现的有关大陆架的规范。第二,在一些基本原则(fundamentals)领域,国际社会新显现的需求会导致在国家群体间发生冲突,并致使经由条约规则来加以规范变得极其困难。结果,国家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可能是出于给“广泛同意”的范围划定界限而非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目的,致力于复杂的磋商程序。联合国在此领域功绩卓著。各个国家可在这个国际讲坛上相互交换意见,消除隔阂,有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多数国家间最终消除对立,并在行为的一般标准上达成共识。后一种结果和起草条约一样,制定规范的核心(nucleus),形成此后实践的基础。这种“行为的一般标准”无疑在此前规范的真空和今后通过制定条约产生详细的规则间搭起了一座“桥”。而这恰恰是习惯法重要性的表现。在近几十年所形成的“禁止种族歧视和迫害”等习惯法规则可资为证。第三,新产生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对国际习惯法予以全盘否定。一些习惯法规则如果被新独立的国家认为或多或少具有可接受性,那么它在相关领域就会出现通过修订和细化而“茁壮成长”的态势。有关战争的规则、有关条约法的规则(“条约必须遵守”)等等习惯法都是如此。
三、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
在西方对习惯法的表述上,特别是在早先国际法学者的著述中,常出现“习惯”(custom)和“惯例”(usage)交混使用的情况。这同样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概念关系的认识,而常常用“惯例”替代“习惯”。严格来讲,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惯例代表了习惯的“混沌”时期,当习惯形成之日,即惯例终止之时。惯例只是一种行为的国际习常(habit),而没有足够法律的证明(attestation)。它可能是相互抵触的,而习惯必须前后一致,统一不悖。custom是《国际法院规约》明文正典记载的国际法渊源之一,“官袍加身”,具有法律拘束力;而usage相比之下只能算是“乡野村夫”了。
问题是,在概念上作内涵和外延的区分并不难,但在实践中如何加以识别就非轻而易举了。这就势必要明确“习惯”的构成因素有哪些,以此来判断特定场合是否存在一项国际习惯法。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往往殊途同归。如布朗利认为习惯的要素有四个:1.持续时间;2.常例的一致性和一贯性;3.常例的一般性;4.“法律和必要的确念”(Opiniojurisetnecessitotis)。前苏联有学者认为国际习惯具有三个要素:1.长期适用;2.普遍承认;3.确信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事实上,上述观点除了最后一个要素外都是对常例(practice)特征的说明。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二元概念(dualistconception),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有两个:“通例”(generalpractice)和“法律确念”(opiniojuris)。在“大陆架(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本质必须“主要的在国家实际实践和法律确念中寻找”。这种理解符合《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b)项的规定,具有成文法律依据,因而更加具有合理性。在这两个因素中,“通例”即国家的实践,是社会学的因素、客观的因素,而“法律确念”是心理学的因素、主观的因素;或者说,前者是数量的因素,后者是质量的因素。下面分别详细来论述一下这两个因素:
第一,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通例”,即国家的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时间性(temporality)、连续性(continuity)、一般性(generality)。只有当惯例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成为国际习惯的基本要素之一。
1.时间性。国际习惯的经典定义是“长期使用的不成文法”,强调的是持续时间的长期性。这是因为先前国际关系简单,国际交往有限,国家实践不足,导致惯例的形成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时间因素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活跃,形成惯例所需的时间也大为缩短。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1969)中认为:“仅仅一个短时间的过程不一定会妨碍或者其本身不一定会妨碍在原来纯粹为协定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一项新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承认1958年《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的等距离方法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形成了国际习惯法规则。这意味着国际法院在其有关判定是否存在国际习惯的司法实践中已不再将时间因素当作重点来考虑。有关外太空管理的习惯法规则的迅速出现也是一个例证。这一现象同样得到了学者的认同。童金认为:“时间性,换句话说,时间因素在国际法惯例规范的形成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时间因素本身并不能推定国际法惯例规范的存在。如果从法律上看惯例规则必须是‘古老的’或年代相当久远的,就更缺乏根据了。”布朗利说,“时间的经过当然的构成一般性和一贯性的部分证据,但当一项实践的一贯性和一般性被证明之后,特别的时间经过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说,他并没有将时间因素和其他因素作同等对待。郑斌提出的“即时的国际习惯法”(instantinternationalcustomarylaw)概念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但它同样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有意义的讯息:时间要素已经不成为国际法习惯形成的主要问题。
2.连续性,即一贯性(consistency)或划一性(uniformity)。“连续性”是一个评价问题,在许多案件中裁判者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完全的划一性是没有必要的,但要求有实质性(substantial)的划一。国际法院在“连续性”上的主导意见出现在“庇护案”中,“依据一项习惯的一方……必须证明这项习惯是以-它对于他方已经形成有拘束力-这种方式确立的;所引据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国家所实施的一项经常和划一的惯例……”接着法院从反面论证道:“法院所获知的事实显示,在行使外交庇护权的实践中和不同场合所表示的官方意见中,存在如此多的混乱和不一致,如此多的不肯定和矛盾;在为某些国家所批准而为其他国家所拒绝的迅速连续的各庇护公约中,存在如此多的不一贯性;以及在各实例中,实践受到政治意愿如此多的影响,故而是不可能从这一切中来辨明任何被接受为法律的经常的和划一的惯例的……”换句话说,在该案中阻止一项国际习惯规则形成不是重复的缺失(absenceofrepetition),而是实践中大量的不一贯性的存在。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并不期望在国家的实践中,对有关规则的施用应该是完美的,即国家应该以完全的一贯性戒绝使用武力和干涉别国内政。法院并不认为,对于一项规则成为习惯法,相应的实践必须完全严格地与该规则保持一致。为了推导出习惯规则的存在,法院认为国家的行为应在大体上与该规则保持一致就足够了。至于与特定规则不一致的国家实践的情况,一般应被视为是对那项规则的违背,而不是承认一项新规则的暗示。”
总而言之,实践中“大量的”不一贯(即相当数量的实践违反有关“规则”)将阻止一项习惯法规则的产生。而像国际法院在“英美渔业纠纷案”中声称的那样,“少量的”不一贯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实践违反声称的习惯法,似乎少量的实践也足以产生一项习惯规则,即使该常例仅涉及到小部分国家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3.一般性。一般性是指国家就一项惯例参加或接受的广泛程度要求,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1)广泛程度;(2)参加或接受的方式。对于问题(1),应该明确“一般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不能进行抽象的定义。它包含在所有国家-主要指有能力参与规则形成过程和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实践中。“一个常例可以成为一般的,即使它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并不存在既定的标准指示一个常例应达到何种广泛的程度,但它必须反映,在相关活动别有关的国家的广泛接受。”因此,对于有关海洋的国际习惯法而言,海洋大国和临海国的实践比内陆国的实践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无疑,“一般的”实践不等于要求“普遍性”(universality),即不要求是所有国家或其他国际主体无异议的实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受到其他国家通例的拘束,即使这违背它的意愿,如果它没有在该规则出现之时提出反对并坚持反对(persistentobjector)的话。问题是,按照“坚持反对者学说”(doctrineofpersistentobjector)的理解,“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习惯法的一项规则产生过程中坚持反对,就不受该规则的约束”,这很有可能为强国破坏国际习惯法规则提供可乘之机。国际习惯法本身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规范体系,因此应对其加以“小心呵护”而对阻止或妨碍行为作严格限制。基于此,一个国家坚持反对一项习惯规则,只有当这一行为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之后,才能脱离该规则的拘束。反之,如果其反对行为未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则仍然受该规则的拘束。当然,如果多数国家反对一项习惯规则,则该规则无从产生,不发生对有关国家有无拘束力的问题。
对于问题(2),从“一般性”的内涵可知,它的形成要有国家的参加或接受行为。法律上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关于不作为能否产生习惯法曾构成“荷花号案”(1927)的争论焦点之一。但现在一般已不再视其为问题。正如童金教授指出的那样,“不仅国家的积极作为,还有一定情况下的不作为,都可以导致国际法惯例规范的产生。”国家积极的作为即直接表明了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但国家的不作为,什么情况下可理解为“沉默即默许”,什么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国家对该主题缺乏兴趣还有疑问。在后一种情况中,国家的不作为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意思表示,即既不意味着同意,也不意味着反对。而“如果国家的行为不附有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是义务或权利,那么,所确立的是所谓‘惯例’,而不是造法的习惯。”因此既不能全盘否定不作为对于形成国际习惯法的意义,同时也不能一概认为不作为可以产生习惯法规则。在上述“荷花号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即使在已报告的案例中很少有司法判决足以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法国政府的人所认为的那些情况,这仅仅表明各国在实践中不进行刑事程序,而不表明它们承认它们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只有如果这种不行为是依据它们感到有义务的不行为,才可能说有一项国际习惯法”。法院虽然没有否认不作为可以成为惯例的一部分,但是表明不作为如果没有满足“法律确念”的要求就不能形成国际习惯法。
第二,当从国家实践中推断习惯法规则时,不仅要分析国家做了什么,而且要分析它们为什么那样做。这就引出了形成习惯法的心理学因素:法律确念,或者如《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2款所称的-“经接受为法律者”。
在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孰轻孰重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凯尔森认为习惯是一种造法事实,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上,“习惯,即各国长期确立的实践,创造了法律”。这事实上否定了“法律确念”的意义。卡特则直接说:“法律确念不是习惯的一个必需要素。但当它呈现时,它有助于将习惯和出于礼仪或其他理由采取的行为区别开来。”但如布朗利所言,“惯例是一种通例,只是不反映法律义务”。正是“法律确念”使“国际惯例”转成为“国际习惯”。现代分析哲学将“实在”分为“自然的、物理的实在”和“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两种形式。用来阐释制度性的实在的一个典型例子货币。为什么当我们捏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张的时候会获得拥有财富的满足感?而事实上这些染着某种颜色的纤维素构成物在物力上、化学上,并无神奇之处。为什么当我们设法制造出与它们一模一样的东西时,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假币”,甚至我们因此要受到刑事处罚?类似困惑的唯一答案可能就是:一种现象,当且仅当我们认为是货币它才是货币。类似的,国际习惯法作为一种“制度性实在”,当且仅当国际主体认为它是国际法它才是国际法。这就是心理学因素的意义,即国家承认惯例所形成的规则有法律拘束力,则这种“法律感”使国家受其拘束。不惟如此,就功能而言,“法律确念”可以被视为一种“溶媒”(solvent),将对国家实践实例在历史上的阐释(rendition)转换为一种更加流动的形式:一项国际习惯法可被应用到解决当下问题中。如果缺少了“法律确念”可能仅存在一个或多或少缺乏法律意义的历史经验。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惯例的时间性、连续性和一般性都是相对而言的。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的断层”(习惯通常只在争议时才浮出水面,而大部分时间则似有似无)和国家实践的模糊暧昧,而在不同的时空中作为法律规范得到应用,是因为它获得了国际主体的“法律信念”。因此,正是“法律确念”使国际习惯法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在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因素中,“法律确念”比“通例”更为重要。
“法律确念”常常被定义为“国家感到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乃国际法之要求的确信”。这一定义预示了所有的习惯法规则都是根据义务制定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它同样包含“许可性”规则,即允许国家以特定方式行动。例如,可在本土内对外国人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控诉。所以,对于“义务性”规则而言,传统的定义是正确的;对于“许可性”规则而言,“法律确念”意味着“国家感到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乃国际法所许可的确信”。对二者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在证明程度上加以区别。如果一些国家以特定方式行为(或者声称他们有权利以那种方式行为),而利益相关的国家没有对该行为(或声称)主张它们是违法的,那么一项许可性规则因此而得证明。但义务性规则就非仅限于此,还需要证明国家把行为看作是一种义务性的举动。
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判断这种心理学或主观的因素是否存在?事实上,它并不是抽象地出现的,而是产生自国家的行为所构成的实践。因此学者们有一点共识,即不是寻找国家心理学确信的直接证据,而是从国家的言行中间接加以推导出“法律确念”的存在,但在具体方法或进路(approach)上有所差异。如阿奎斯特认为,“官方言论并不需要;法律确念可以在行动或遗漏(omissions)中收集到。出于此目的,必须记住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支配国家行为的国际法规则;因此不仅需要分析一个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要分析其他国家如何反应。如果一些国家的行为激起其他国家主张该行为非法的抗议,这些抗议可以剥夺该行为作为习惯法证据的价值。”布朗利从国际法院的实践中总结出两种证明的“进路”:在一些案件中,国际法院乐意根据通例、文献著作中的一致性观点、国际法院先前的判例或其他国际性裁判所提供的证据推定法律确念的存在;但在很少部分案件中,法院采用了一种更加准确的方法,要求提供在国家的实践中承认系争规则效力更为确实的证据。至于选择那种进路,则取决于争论问题的性质。另有学者认为,“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法律义务感’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一种办法是询问国家,当它们以一种一贯的方式行为时仅仅是出于便利还是它们承认如此行为是因为它们感到受国际法的强制。但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难题。……国家可能经常以习惯的方式行为,却没有必要宣告它们这样做是因为某程度上感到了法律的拘束。事实上,与习惯法规则很好地被遵循时相比,国家有关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声明更可能在那些规则的冲突和疑惑情况下产生。”他接着说:“法学家和法官而非国家,对国际常例在一定阶段变成国际习惯法观点的表达而言是更有帮助的渊源。……法官们和国际法学家们对国际法作贡献的一种显著的途径是:通过对国家实践的解释和当这样的实践已经达到它可能真正地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时发表意见。经常地,不是国家而是法学家和法官成为那有魔力的一剂(potion)-法律确念-的有效酿造者。”从中不难看出,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可据以判断国家的实践中隐含“法律确念”,但它可以在相关证据中找到“踪迹”。
关于“法律确念”,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由“个别法律确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形成的特殊习惯(specialorparticularcustom)或区域习惯(regionalorlocalcustom)的效力问题。在“印度领土通行权案”(1960)中,国际法院明确表示这样形成的习惯对有关国家是有法律拘束力的。但作为国际法的渊源的习惯必须是一般性习惯,或者严格地说是普遍性习惯,而特殊习惯或区域习惯不能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规则或规章,除非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承认或默认。注释:
Jennings,inBernhardt,Vol.Ⅱ,p.1165.转引自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48页。日本学者广部和也指出“法律渊源”是一个多义词,大体有四种含义:①给予法律以拘束力的事物;②法律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③法律的存在形式;④认知法规的资料。(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参见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分册,第17-18页。但詹宁斯、瓦茨修订的第九版《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把该部分内容删去了。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50页。
“语言一旦长上了翅膀,就自由飞翔。”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个体的理解中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
See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Little,Brown&Company.1993.p.164.
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ClarendonPress.Oxford,1986.p.181.
《联合国》对于缔约国没有拘束力,它“仍然是一项多边条约,不过是一项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多边条约而已。”(参见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册,第19页。)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4.
同上,p.165.
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册,第15页。
L.C.Creen,InternationalLaw:ACanadianPerspective.2ndEd.TheCarswellCompanyLimited,1988.p.60.
See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p.181-183.
有关著作有周鲠生的《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台湾学者沈克勤的《国际法》(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增订五版),等。我国外交文件和国内法规用“国际惯例”代替“国际习惯”的例子可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68-69页。
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p.142.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ClarendonPress.Oxford,1990.p.5-7.
「苏联科热夫尼克夫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页。
ICJRep.1985,29.See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LondonandNewYork.1997.p.39.
HiramE.Chodosh,“NeitherTreatyNorCustom:TheEmergenceofDeclarativeInternationalLaw”,inTIlJ,Vol.26,No.1,p.99.note1.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2页。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7.
ICJReports,1969.p.43..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5页。
「苏联格·伊·童金著:《国际法理论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SeeRodolfBernhardt,EncyclopediaofPublicInternationalLaw,1995.p.902.SeealsoG.J.H.vanHoof,RethinkingtheSourcesofInternationalLaw,1987.p.36.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6页。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ICJReports,1950.pp276-7.Seealso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6.
Nicaraguav.US(Merits),ICJRep.1986,p.98.Seealso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1.
UKv.Norway,ICJRep.1951.116.p.138.
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2.
TheRestatement(Third),Vol.1,para.102,25..Seealso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2.
「苏联格·伊·童金著:《国际法理论问题》,同前注,第74页。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257页。
PCIJPublications,SeriesA,No.10,p.28.转引自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78页。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257页。
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p.144.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美约翰·塞尔著:《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See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p.166-7.
See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4.
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5.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7.
郑斌认为“法律确念”有“一般法律确念”(opiniojurisgeneralis)和“个别法律确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之分。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83页。
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84-85页。
参考书目:
中文
l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周鲠生著:《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台)沈克勤:《国际法》,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增订五版。
4「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5年版。
6「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美约翰·塞尔著:《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8「苏联格·伊·童金著:《国际法理论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9「苏联ф·и·科热夫尼克夫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l0「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英文
l、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ClarendonPress.Oxford,1990.
2、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LondonandNewYork.1997.
3、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Little,Brown&Company.1993.
4、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ClarendonPress.Oxford,1986.
5、L.C.Creen,InternationalLaw:ACanadianPerspective.2ndEd.TheCarswellCompanyLimited,1988.
6、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
相关文章阅读
相关期刊推荐
精选范文推荐
- 1法律意见书
- 2法律法规思想汇报
- 3法律意识淡薄的反思
- 4法律知识不足整改措施
- 5法律典型案例
- 6法律伦理案例
- 7法律法规学习情况汇报
- 8法律专业研究方向
- 9法律逻辑学论文
- 10法律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