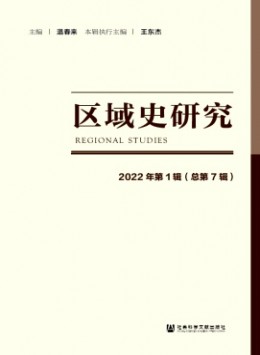微观环境的概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微观环境的概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环境成本; 计量; 披露; 关联会计
引言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环境系统作为由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组成的开放系统,其核心的环境成本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环境成本的成因及属性均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成本或经济成本。为此,环境成本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广泛关注与探讨的议题。目前,研究者对环境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计量方法和口径尚未统一,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成本的信息披露也并不充分。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在成本核算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成本补偿制度,同时将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引入到会计系统中,上述相关规定将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全面地反映会计信息,并为环境成本的计量与信息披露指明发展方向。鉴于此,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信息的不同需求,以及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迫切需要,文章从关联视角入手,拓展成本计量和信息披露的概念范围、主体范围、内容范围、计量范围、方法范围、披露范围等,试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进行环境成本的计量与环境信息的披露研究。wwW.133229.cOm
一、关联法与社会关联会计
环境成本确认、计量、披露标准及方法的变化需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基础。本文选择的关联视角源于会计关联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会计理论体系。
所谓关联,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法,其本质就是从事物的内在特征出发,基于客观规律及客观现实,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使不同事物关联于一个有机系统之内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在我国,以关联为主要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社会关联会计的学者是王晓东。将关联思想应用于会计领域即产生会计关联法,主要是指在会计研究的过程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原理,从会计事物的本质出发,建立不同会计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会计事物产生的根本因素及关键影响因素,进而通过理论设计、制度设计、方法设计等引导会计事物的发展方向,实现企业目标或社会目标。
在会计关联法下关联会计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关联视角下,以传统的财务会计为基础,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增值会计等新兴的会计领域都被纳入到社会关联会计的研究范畴,而社会关联会计模式下的成本核算,将是传统生产经营成本基础上的完全成本,是包含了环境成本、社会责任成本在内的全部外部性成本。将关联思想应用于环境成本问题研究,其核心是拓展传统环境成本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企业主体边界,对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报告进行关联视角下的重新界定。
二、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界定环境成本的已有定义
(一)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的定义
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以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日本环境省及荷兰国家统计局(cbs)等为代表。
其中,isar的定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阐述了环境成本包括的主要内容。首先,在isar1998年第15次会议上,isar通过了《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与财务报告》(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environmental cost and liabilities)立场公告。在立场公告中,isar提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而付出的其它成本。”这一定义从微观角度限定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主要内容;其后,isar在《环境管理会计:政策与联系》中,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成本定义,将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全部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纳入环境成本范畴。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将环境成本分为环境措施成本与环境损失成本。本质上来说,cica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同样是微观的企业环境成本。cica将企业主动对环境进行保护而产生的成本定义为环境措施成本,即企业保护再生或不可再生资源而采取的行动成本或为减少、修复已造成的环境破坏而采取的行动成本;环境损失成本则是指企业因为环境问题而发生没有任何利益回报的净损失,比如,因违反环境法规或破坏环境而支付的罚款、赔偿金等。
日本环境省称环境成本为环境保全成本,主体界定仍然是企业,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将环境保全成本定义为企业为保全环境而付出的费用和投资。环境保全是企业为降低环境负荷而采取的一种环境保护活动,该成本定义类似于cica定义中的环境措施成本概念。此外,荷兰国家统计局(cbs)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与日本环境省类似,同样将环境成本定义为环境保护成本,即“出于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所发生的成本”。
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一般基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目的,因此,主体界定为企业,是一种微观的环境成本。与此同时,环境成本内容多以环境保护为主,是一种积极的环境成本定义。
(二)我国会计学界对环境成本的定义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环境成本的界定以郭道扬、陈思维、朱学义等为代表,以上学者对环境污染控制成本以及污染本身造成的损失进行分类和计算,认为环境成本主要包括: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环境机会成本等。
近年来,有关学者对环境成本的定义有所拓展,但本质上仍然围绕企业微观的环境保护和维护成本展开,如黄蕙萍、成(2000)将环境成本分为三部分,一是正常的环境开发成本,二是环境净化和环境损害成本,三是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即因环境资源使用而对后代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成本。惠尚文(2003)进一步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损耗、保护、恢复所支付的成本费用,归纳分类为耗减成本、损失成本、恢复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及替代成本。
我国学者对环境成本的定义较国外会计机构更为细化,但从本质上来看,我国及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定义的立足点都是企业,其界定都是针对微观环境成本而进行的。
论文 联盟
(三)关联视角下对环境成本的界定
基于不同的主体视角,环境成本的界定有所不同。上述概念的差异即体现了不同主体视角下的不同概念范围。综合来看,会计学界对环境成本的界定是立足于企业主体的微观环境成本,根据主体的计量目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微观财务成本和微观经济成本。李明辉(2005)将企业的环境预防、维护和发展成本,环境的治理成本以及因遵循环境法规而导致的环境成本等纳入微观财务环境成本的确认范畴,从财务确认、计量的角度将企业承担的、影响企业财务成果、与环境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支出定义为微观财务环境成本。而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和定义为微观经济环境成本,其实质是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微观经济成本包括了企业活动可能对外部环境造成的全部货币性或非货币性损失,其中货币性损失可量化,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在会计核算系统中予以反映,而非货币性损失,如因企业污染而造成的周围居民寿命降低、水质下降等等则无法在会计核算系统中量化反映,因此,在目前的会计体系下,微观经济成本不计入企业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因而对企业的财务成果没有影响。
由于当前能够进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主要是微观财务成本,因此,环境成本的计量和披露范围在会计系统中被限制和缩小了。为了全面反映企业与其所在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环境交互关系,首先要拓展环境成本研究的主体,即在关联视角下,重新界定环境成本。
关联视角下,企业的本质从社会契约转变为社会价值链中的一个节点,称为社会关联体。每一个社会关联体都存在于社会关联网络之中,通过不同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关联体交互,同时负有向所有利益关系的关联体提供信息的义务。在关联视角下,企业本质的转变要求对成本的界定从整个物质世界循环的角度进行,即成本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耗费的补偿,而且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耗费、破坏的补偿及更新或复原的补偿,从而使自然界保持其原有的良好状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应该反映人们为制造该产品所付出的全部代价,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经营成本,也包括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社会成本。这种反映生产某产品或提供某种劳务人们所付出的全部代价的成本称为完全成本。因此在关联视角下,微观层面上研究的完全环境成本,是指包含了微观财务环境成本和微观经济环境成本的环境成本总和。
此外,当所有企业都成为社会价值链中的社会关联体时,由于负外部性而产生的微观经济环境成本在整个关联网络中可以被整合为社会视角下的净损失,即宏观环境成本。关联研究法允许将研究的主体范围拓展到关联体及其关联关系,于是,内含于整个关联网络之内的每一个社会关联体,可以作为环境成本的动因,与此同时关联体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成为环境成本的驱动因素,整合了关联体及其关系的关联网络作为主体,环境成本的范畴便从微观拓展到了宏观,在单一的微观财务环境成本计量的基础上,微观经济环境成本及宏观环境成本的计量和信息披露成为可能。
三、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
(一)传统环境成本计量模式
会计学中使用的狭义成本计量是指运用一定的计量单位,选择被计量对象的合理属性,确定应予记录的各种经济事项或交易活动及其影响的数量,进行成本归集和分配的处理过程。成本计量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时间维度上看,分为传统成本计量模式、现代成本计量模式和未来成本计量模式。
传统环境成本计量模式嫁接于会计账户系统之上,是以微观财务环境成本计量系统为核心,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封闭系统。其成本计量过程如图1所示。
由于传统的环境成本计量系统依赖于会计的账户系统,因此,在结构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无法很好地满足多目标、多层次、综合性的信息要求,对于信息使用者而言,面临着相关性消失的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在拓展的环境成本主体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式。
(二)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式
会计的关联法将环境成本的计量主体拓展到社会关联体及其关联关系,由此在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需要建立新的计量目标、对象、系统以及相应的方法。
1.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目标
环境成本的起因与产品成本不同,它以环境负荷的发生和消减为起因,而所谓环境负荷,概括地讲就是指社会关联系统中,社会关联体(包括个人与组织)对其系统内的环境所产生的负担影响,包括社会关联体直接利用环境资源所产生的负荷以及对环境造成损害所形成的负荷。因此,企业的环境成本就成为企业为减少环境负荷而付出的资源投入,这是传统环境成本进行计量的目的。与此相区别,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以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帕累托最优为目标,为社会关联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关联体(包括社会大众)提供利益相关的信息,为国家、企业、个人的战略、规划及发展决策提供有用信息。
2.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对象
以关联为基础,环境成本对各个社会关联体的环境负荷进行计量;同时计算关联网络上由于外部性而造成的环境经济成本;最后,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计量整体的宏观环境成本。
3.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系统及计量方法
多层次、多维度、复合结构、开放性是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计量系统的主要特征,操作中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建立环境成本计量系统。
(1)基础层:各社会关联体自身的环境成本计量
该层次的环境成本计量是实现环境成本关联计量的基础,是在吸收借鉴现有财务环境成本计量模式的基础上,突破会计账户框架,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将成本计量与企业的战略层、管理层、作业层相结合,满足“不同目的,不同成本”要求,将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目的的环境成本纳入微观成本计量框架,建立多层次、复合结构的开放式成本计量系统,以此为不同关联体之间建立关联关系奠定基础。具体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生命周期成本法、完全环境成本法等。
(2)网络层:关联体之间的环境经济成本计量
经济环境成本发生在关联体的关联网络之间,引起负的外部性从而使其关联网络中的其他关联体产生外部成本。外部成本,又称负外部性,是指由受益人之外的主体所承担的成本,即某种不良的环境后果由主体a引发,但相应的损失却由主体b来承担。这些不良的环境后果主要有:未得到补偿的健康影响、自然资源的折耗、当地生活质量的变化、噪音和美学的影响、长期废弃物的处理、残余气体和水的排放等等。当前理论研究中主要观点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但在关联视角下,该外部成本可以单独计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净损失予以反映,可以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意愿调查法等。
(3)宏观层:社会综合环境成本计量
全部关联体的有机整合成为宏观环境成本的计量主体,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环境成本不是微观社会关联体环境成本的简单累加,因为在网络层面外部环境成本的作用下,经济关系之外的价值体系被纳入宏观环境成本的计量范畴之内,即宏观环境成本还需考量承担的社会环境责任成本。在社会环境责任成本中,除因外部性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如处理废水、废渣、降低能源消耗、对社会环境治理、居民身心健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外,还包括因对社会福利的贡献而付出的社会环境责任成本。对企业在全社会范围内付出的环境责任成本确认和计量的难度较大,当前较普遍采用的计量方法有:调查分析法、支付成本法、成本收益法、替代品评价法、社会公正成本法、影子价格法等。
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综合计量系统如图2所示。
四、关联视角下的环境信息披露
与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相对应,为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也应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由国家统一规范,并将信息汇总为一份综合报告。
(一)定量披露
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应首先包括定量信息,如微观环境成本费用、外部环境成本费用。环境成本报告可以采取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比较型模式(如日本富士通公司)或环境成本与环境负荷比较型模式(如日本理光公司)。
(二)定性披露
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有关的信息可采取定性披露为主的方式,在定性披露部分,可直接采用文字表达法进行叙述性反映,即以非正规形式或用文字说明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承担了哪些环境社会责任等,或者以附注形式反映。
(三)综合披露
以关联整体作为报告主体,还需要披露宏观环境成本信息,定量计算绿色gdp等或定性分析整个社会的环境责任履行现状。
五、结论
成本动因的特殊性导致对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与披露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成本。当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焦点问题之一时,对环境成本的量化必然突破单一的企业边界,需建立起多层次、多维度、综合性的开放计量系统。会计的关联法恰恰契合了这一需求。为此,本文从关联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与环境成本有关的要素及其影响关系,在关联视角下重新界定了环境成本的范畴、计量主体,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环境成本计量系统,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主体为各关联体、关联体间关系及内涵了价值体系的整个关联网络;
第二,关联视角下构建的环境成本计量系统,其计量目标、计量对象、计量方法均有所变化和拓展,整个计量系统分为基础的微观环境成本计量层、多维交互的外部环境成本计量层以及整合的宏观环境成本计量层;
第三,与三层次的环境成本计量系统相对应,对环境信息可采用定量披露、定性披露以及综合披露等不同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晓东.企业社会关联会计问题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 isar,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environmental cost and liabilities[m],1998.
[3] 黄蕙萍,成.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内在化问题[j].武汉工业大学学报,2000(6):97-100.
第2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学前教育;专业认同;时空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5-0039-03
尽管学前教育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和教师们一直极力倡导和宣传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科学知识,但学前教育专业近二十年来被社会更广泛地了解和认知还是基于中国教育部门官方的推动,包括政策出台、经费支持、师资培养等政府行为。同时,在大学生社会就业压力日益吃紧的情况下,早期教育机构却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呈现上扬的趋势,这也使得政府推动学前教育师资培养的政策获得了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与认可。高考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人数大幅增长,更多的全国各级院系近年来也开始增设学前教育专业,这些院系也为此专业毕业的硕博学位获得者提供了一部分新的教职,因此国内整体大环境使得学前教育专业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发展。这发展本身自然有经济的因素,然而教育毕竟不具有纯粹商品经济的性质,加之学前教育工作的对象是儿童,因此从事该领域工作的学生、教师以及研究者们必然会遇到“教育”所包含的比从经济生活层面获益更为复杂的问题。笔者发现到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们关注了学前教育师资培养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学前教育专业认同”的问题,这问题从教育层面说便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观察点,使我们的眼光跨越当下“学前教育热”,冷静地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这个专业更为深层次的发展。
一、从环境角度看“学前教育专业认同”
(一)“学前教育专业认同”作为环境的组成部分
从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承认对人有影响的两大因素是“遗传”与“环境” [1]。“遗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我们要探讨的是环境。在教育学领域,“教育”有时候被独立出来作为影响人的另一个因素,这其实是一个“自然”或“使然”的哲学争论。如果教育被理解为广义上的对人的“影响”,它是偏向自然的、经验的;如果教育被理解为狭义的“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是偏向自然的,包含了人的理性的部分[2]。从环境的层面看,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分,如果教育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与环境联系起来,那么自然的环境与教育的广义概念有着更深的渊源,社会环境与教育的狭义概念则有更显著的联系,总之教育是可以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然而,教育领域这些年来对生态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看到,不能轻率地将教育划分到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概念下。事实是,在“生态”这个问题上,既然人与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影响、彼此互动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依这个逻辑推理――教育不应当被狭义的理解。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曾试图从教材、教学方法等微观的因素来影响受教育者,我们也曾通过改善环境的办法影响受教育者。作为后者,我们可以把“学前教育专业认同”这个概念考虑成环境作用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二)“学前教育专业认同”的不稳定性
“学前教育专业认同”既是个体微观上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认知、理解、信念、预期系统,也是行业群体对这个专业所形成的基本价值观,个体的态度看法等构成了群体的价值观,反过来群体价值观对个体又形成意识层面的“环境”,有时候这“环境”甚至表现为“文化迫力”。就像本文在开篇提到的学前教育在国内的整体趋势一样,从专业领域到社会民间都承认这个专业带来了经济生活层面的影响力,使更多的大学生愿意加入到这一行业,但这并不是基于“专业认同”水平上的表现,而是一种趋势所带来的“迫力”。如一些基于心理层面的研究者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已经就读该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的选择并不基于了解和兴趣,而是与高考录取制度相关[3]。对大学生将来是否愿意从事幼儿园教师或与之相关工作的调查显示他们更倾向于再次选择新的工作领域[4]。还有一些大学生认为这个专业更容易毕业之后找到工作,所以对专业体现出积极的情感取向[5]。这一类的研究都印证了我们之前对学前教育大学生专业认同感的既有印象,即出于外在的环境迫力产生了对专业的认同,但是对专业本身的课程设置、学科内容、研究对象、工作领域等属于专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并没有带来对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坚定信心。从此类研究的结论看,部分的因素在于整体对学前教育专业技术性认知不够,这样将在未来长远的时间里造成专业认同上的不稳定,而当下基于政策提倡和就业趋势的热潮是短暂的。
二、学前教育专业认同的时空环境影响
专业认同的问题既然属于环境的一部分,环境总包含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下面我们从这两个维度来思考学前教育专业认同的问题。
(一)空间角度
笔者参考了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6],梳理了学前教育专业认同环境里所包含的空间有三大方面:其一,大学生当下所从事学习工作领域范围内的空间环境,这个空间环境是微观的,虽然横向范围很大,但其集合由众多微观环境构成,包含各个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系、学院、学前教育研究所等;其二是由各个高校以及研究所等教学科研单位所构成的学术教育层面的环境,环境内部的微系统彼此交流形成一个中间系统,它是建立和稳定大学生对此专业认同的重要部分,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三,是前文提到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外部环境,即国家政策、社会就业等所形成的外系统,当下这个外系统正在起作用,拉高了该专业认同的曲线;其四,就是国内文化环境、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所造就的大系统,它影响着教师职业选择、价值取向等诸多的问题。
这几个环境系统正在用不同的力量作用于学前教育专业的认同,尤其是这个专业由过去中专、大专学历层次被普遍提高到本科层次,系统中的个人、单位群体对“专业认同”的期望更迫切了。短期内这种迫切可以在外系统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使得学生个体增加了对专业认同感,但这种认同感会随着外系统作用的变化而变化,一旦政策、社会就业有所冷却,这种认同感又会随之降低,它是不稳定的。真正能够建立其专业认同感的力量来自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因为它是学前教育专业科学技术层面的支持,一旦这种技术支持得到深入的发展,形成具有系统的、人文的、科学的专业性质,并为大学生所认知,它将提升专业认同内部的自信,形成坚固的专业认同价值观。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系统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到最大的限度,所以要提高专业认同感,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工作。至于大系统,那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且并不能通过具体的某项工作加以直接影响,此处不深入讨论。
(二)时间角度
任何的空间都有时间维度作为量度的依据,前文所述空间的系统是随时间的变化而相互作用、改变的。比如,当下被拉高的专业认同是由外系统作用的,那么要在更长时间内稳定和继续增进专业认同就需要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的支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调查研究描述的是当下时间维度的现状,假如不进行理性的、主动的作为,那么未来的专业认同发展我们很难预期四种环境作用力会如何朝着我们的期待变得更坚固。同时我们并不能突破时间维度的界限来解决问题,比如短期内制造大量的研究成果、技术手段,但我们可以通过拓展大学生在此领域学习工作的空间范围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效率,那么就相当于我们部分地延伸了时间维度给予建立专业认同的条件。通俗地说,将学生从专业院系学习的空间环境拓展,延伸到幼儿园、早教机构、社会领域、家长群体、幼儿群体、社区、儿童福利组织等,建立大学生对此领域更广泛的认知;再如密切学前教育院系、研究所的学术交流,夯实中间系统的环境,这对稳固专业认同科学层面的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微系统和中间系统的作用力被激发,专业认同内在的引力就会形成。长远看,我们就不必完全依赖外系统甚至大系统来提高专业认同感。
三、建议
(一)学前教育专业认同是动态的过程
学前教育专业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总是处于变化的环境中,它也属于环境的一部分,现在这个专业认同的确比过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这个专业规模上的扩大,但我们不能说这种扩大肯定会朝向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从笔者对诸研究资料的观察来看,专业认同并没有形成中间系统科学性、专业性的引力,虽然在行业内的学者看来这个专业并不乏科学性和专业性,但如果要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将之渗透下去,并把这种认同渗透到微观系统,进而建构一个良好的中间系统环境,是需要从长计议的。
(二)调整课程结构与人才培养方向
目前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大多侧重培养幼儿教师、教研人员以及从事本专业边缘领域工作的从业人员,类似于职业培养。但我们对儿童教育问题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空间并不大,这个特点从很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结构上可以看出来。比如艺术类技能课程计划,并不是以本科室通识教育(EDUCAITON)课程的身份而存在,而是职业技能训练(TRAINING)的角色。又比如大量大学生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能有机会进入早教机构、幼儿园做独立的、小范围的观察研究型学习的机会却与招生的人数不成比例。这些实际的问题都需要微观系统中的每一个小系统进行调整。
以此,只有稳住基础研究、大学教学,才能让“专业认同”从求职热潮走向学前教育专业自身存在的应有状态,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大学生对这个专业的认同与肯定。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卢乐珍.学前教育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9:27.
[2]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16.
[3]杨继英.高师院校学前教育大学生专业认同状况的个案
调查[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8).
[4]陈妍,梁颖,强丽君.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情况
的校别比较[J].学前教育研究,2008,(3).
[5]王杰,薛钰川.学前教育大学生职业认同现状的调查与
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1,(1).
第3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景观学;艺术设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7-058-01
客观地讲就目前的中国景观艺术设计学科正处于探索阶段,从学科概念、学科性质到学科实践范围均缺少系统性、明确性和指向性。那么什么是景观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与景观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景观学体系中它的实践主体是什么?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从景观学的引导、多元系统设计以及景观艺术设计的实践主体进行系统的论述。
一、景观学引导下的艺术设计
景观艺术设计依托景观生态学,通过对自然的尊重、表达、展现生态环境的和谐优美,依托景观建筑学创建城乡宜人的环境,依托景观人文学,表达人类行为心理的精神寄托及愿望,景观艺术设计成为景观形象高品质化生成的驱动力。
就景观学而言,景观艺术设计是景观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狭义的景观定义,是微观层次意义上的景观设计,在体现景观形象的创作上常常成为景观形象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景观艺术设计也涉及到景观学内容本身,但它更多的是遵循景观学的引导,关注景观形象要素对各景观环境系统空间进行艺术化处理,其核心任务是协调人与环境空间视觉形象的关系。景观艺术设计在景观学的引导下,构成了一个交叉融合的设计系统,它是运用艺术融于景观科学的手段来协调景观形象在环境空间的发展关系问题,并使之达到最佳状态。它融合了园林学、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成熟经验,以其艺术的视野,从系统、和谐优美的角度,解决城乡发展中的景观创新问题。
二、多元系统设计含义的艺术设计
景观艺术设计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聚居环境空间艺术的二个方面。环境艺术设计从改善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室内设计起步,以室内室外环境一体化设计为核心,注重环境空间的自身形态,以及环境艺术的具体样式。而景观艺术设计更强调环境空间的综合形态、环境艺术的复合样式、环境表述的多层空间,具体表现在多元系统设计下的互融与综合。
1、综合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是将城市、广场、街道、园林、建筑、壁画、广告、公共设施等环境空间看成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有机综合体,虽然它们有时是以几组形式出现,有时是以相对单一的个体出现,然而解决上述问题却要求兼顾到整体的环境,是在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造环境空间基础上实现的二次创造,景观艺术设计涉及到园林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造型设计、平面设计以及生态学、材料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并将这些知识纳入到景观艺术生成的总体设计系统之中。
2、复合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是在景观学的引导下所构成的复合设计系统,由于景观艺术设计的综合性特点,因此常常表现出设计内容界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基于景观空间形态的视觉系统设计,融于区域景观精神的形象系统设计,反映区域文化特征的风格样式系统设计,以及关注人的行为、心理的人文关怀系统设计等等。
3、多层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的设计空间呈现为多层性的表述特点,表现在从微观意义层面上的景观设计为主体到中观意义上的景观规划、宏观意义上景观策划的多层与协调。
4、广泛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的设计观念呈现出广泛性,《亚太景观》一书在导言中谈到现代景观设计带来的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宏观的观念、生态的观念、构成的观念、文脉的观念、民众参与的观念等等。其次是创作方法上,所有这些凝结成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极简的、高技的,为景观设计师提供了广泛的创造可能性”。
三、微观景观为实践主体的艺术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景观艺术设计学科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其实践范围广泛,内容综合而庞杂,既涉及到景观空间各个层面又融合了环境要素的全部内容。但是如果只是从广义概念出发而缺乏具体目标的限定,景观艺术设计学科建构将一直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这是目前很多高校增设景观艺术设计专业方向后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庞大的景观学科中,景观艺术设计的实践范围或者说它实践主体是什么的问题。
1、宏观层面——景观策划
宏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是建立在经济、旅游、生态等专业的基础上,包括进行大规模的景观生态保护、治理改造、景观资源开发、旅游策划规划等。这类景观实践主要侧重于景观前期的策划。核心是协调土地的利用与管理。是在大规模、大尺度上进行景观体系的把握,具体项目有区域控制性规划、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等。策划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2、中观层面——景观规划
中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是指有一定的规模,涉及到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生态及地方特色整体风貌内容的较大型景观规划,包括与人类社会、文化相关内容,以及生态、历史等多学科的应用。规划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第4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
关键词:模型;化学学习;符号;表征
文章编号:1005–6629(2014)1–0003–05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1 前言
学生进入学习场域前所先存的特定想法往往与科学社群认可的科学观点有所差异,因而造成学生日后科学学习的障碍。研究发现,化学学习的困难之一在于学生无法为巨观的实验现象与符号搭起联系的桥梁(Johnstone, 1982, 1991, 2006; Talanquer, 2011; Treagust, Chittleborough, & Mamiala, 2003)。学生时常只记忆特定表征形式所建构的化学理论、实验的结果以及特定的化学反应,殊不知割裂的、片段式的学习无法统整与理解化学符号与巨观现象的关联。因此,为了改善学生的学可以从教师教学专业素养与学生学习特性着手外,更应该提供结构良好且具认识论观点的教科书。优质的教科书不仅提供教师设计教学的内容与过程,亦能够帮助学生发展与修正其素朴概念。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说明模型观点在化学学习与教科书编写上的意涵,以作为教科书编写方向与化学教学的参考。
2 化学学习中的模型观点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为三位研究动态分子模拟的学者-Martin Karplus、Michael Levitt和Arieh Warshel,瑞典皇家科学院主要表彰三位学者在建构模型思考的模拟架构以提供分子动力学面向理论与实务的卓越贡献(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除了模拟之外,化学学科中许多概念都会以模型作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因此教科书与教师如何利用模型的认识观点促进学生的化学学习极为重要。
2.1 模型的意涵
模型一般被视为具体可形塑的实物,大都为实体的缩小版(如玩具模型),但有时其亦可作为表达设计者对于所设计实体的抽象想法,以呈现出物件之间的关系,而后再透过具体物件与内在想法交互作用完成更好的成品。在科学上,此设计者可视为科学家,而其成品可以是实验结果的数据、数据间的关系或是所产生的理论。因此,模型除了具体实物外,尚可以呈现抽象的想法、关系或是一个事件(Buckley & Boulter, 2000)。事实上每个人每天都会透过既有想法与外在环境或刺激物进行交互作用,从而建构内在心智表征与外显模型,再借助建构出来的模型进行学习与迁移。当学习与迁移顺利时,则会强化其既有的心智模式,反之,若无法顺利学习与迁移,则会出现对新讯息忽略、搁置、修正与重建等认知行为(如图1)。
2.2 模型与化学学习的关联
化学知识的组成包含现象观察的结果与其蕴含的科学理论,化学家透过文字与符号对现象或是抽象的观点进行阐述以形成化学理论。学生经由教学过程或是依据实验的操作进行现象的理解,再经由符号的解释以了解巨观现象所发生的原理机制。学生在学习时通常会将情境的问题加以解构,把知识内容拆成片段来理解而非以模型的系统观点组织自己已经习得或是正在学习的内容。为了促进学生进行有效的化学学习,多位学者尝试从巨观、符号、次微观、中观、人的因素以及语言等面向及其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以下介绍几位学者所提出的化学学习应该着重的面向之观点。
2.2.1 Johnstone的三面向学习观
Johnstone认为化学学习应该着重巨观(macro)、表征(representational)以及次微观(submicro-)三种面向之间关系的连结(Johnstone, 1982, 1991, 2006),亦即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应该注重此三个面向及连结关系,才能提升学生的化学知能(见图2)。此观点已被广泛讨论与应用于教学上(Gilbert & Treagust, 2009; Talanquer, 2011; Treagust et al., 2003)。其中巨观包括现象与具体的实验操作,例如:将染料滴入水中,染料逐渐扩散。表征即指使用到的元素符号、化学式以及化学方程式等,例如:HCl(aq)+NaOH(aq)H2O(l)+NaCl(aq)说明盐酸与氢氧化钠的酸碱反应。而次微观则指以原子、分子以及离子等说明巨观与表征之间的关联,例如:H+(aq)+OH-(aq)H2O(l)指出溶液中氢离子与氢氧根离子是以1:1的数量关系形成水分子。
2.2.2 Mahaffy增加“个人特质”面向
学者Peter Mahaffy认为前述学者的观点虽然可以帮助学生专注于化学学习,然而却忽略了个体对于学习化学重要性的论述,意即忽视了具备不同特质的学生对于化学学习如何产生意义的连结。Mahaffy认为化学教学需要从学生的生活情境与文化背景中去帮助学生找寻学习化学的意涵,并且经由真实生活的经验发掘化学知识中巨观、符号以及分子层级(取代次微观)间的关系,而唯有找出化学学习对于不同个体的学习价值,才能让学生透过其余面向进行有效的学习(Mahaffy, 2006)(见图3)。
2.2.3 邱美虹增加“语言”面向
本文第一作者根据过去研究的结果认为化学学了巨观、符号、次微观以及人的因素之外,还需要考量不同文化特质的语言特征对于学习化学的正反面影响(见图4,Chiu, 2012)。语言的双刃剑效应可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以正面影响而言,如金属以“金”字旁、液体以”水”字旁、气体以”气”字头来构字命名,皆有助于学生认识物质的本质以及命名的原则;但负面的影响则如常见的强酸与强碱进行中和反应后,溶液为中性其酸碱度(pH)为7,由于中文的「中字即具有中间之意,因此学生常易误以为中和反应后便达到中性而忽略酸碱物质的本质。又如碳酸钠和碳酸氢钠其命名中有“碳酸和氢”,因此学生直觉地认为这两种化合物都具酸性,或是以物理静态平衡来认识动态的化学平衡概念,这些都是常见的因语言所造成的另有概念。此现象在英语系国家亦有相似的研究成果(Watts, 1983),如:美国小学生对于能量守恒(conservation of energy)的想法会从字面意义将其看成小心使用而不要浪费能源,而非是科学上的总量是固定的概念。另外日常生活中常用英制单位,使得学生在科学学习上使用公制单位时造成困扰。除此之外,邱美虹(2012)亦认为次微观的观点宜以中观(meso)来说明教学或学习时所使用的表征方式是介于巨观与微观之间的表征关系。有鉴于语言的特征有时能够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科学概念,但是有时却阻碍学生的学习以及以中观取代Johnstone的次微观或是Mahaffy的分子,因而本文提出金字塔型的解释架构(图4最右边的图)。图4说明这些模型的转变。
3 教科书中模型的使用情况
教科书是多数教师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然而研究显示,如果教师仅着重于教科书中的知识结构来计划教学活动,教学过程中学生难以发展以模型为主的认知想法(刘俊庚和邱美虹,2010;Gericke & Hagberg, 2010),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3.1 分别强调巨观现象与符号,缺乏连结巨观现象与符号的桥梁
化学概念的复杂性使得教科书内容多分开独立说明巨观现象及其化学反应式,强调反应面向的巨观解释以及相关的数学演算,而忽略如何运用粒子说明化学反应的历程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Chiu & Chung, 2013;Levy & Wilensky, 2009)。例如:当教科书解释波义耳定律时通常描述体积与压力的乘积为一定值(PV=K)可以解释潜水员在海面下吐出的气泡会随着海水深度的减少而体积变大,但却没有再以粒子观点说明体积的增加的原因,藉此搭起连结巨观现象与符号的桥梁。因此有时学生只会计算,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学生并未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甚至会误以为是粒子本身的体积变大而非其所占有的空间变大。
3.2 大都使用单一表征或类比,忽略多重表征与多重类比的强化功能与互补特性
研究发现教科书说明单一概念时多以单一表征或是单一类比形式进行说明,缺乏针对相同概念以多重表征或是多重类比的形式从不同面向进行探讨(Ainsworth, 1999; Spiro, Feltovich, Coulson, & Anderson, 1989)。使用得当的多重表征或是多重类比并不会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而学生可以经由不同表征形式与类比的介绍而有效地消除特定的另有概念(林静雯和邱美虹,2005);同时透过多重表征结合巨观、中观、符号之间转换的机制以促进学生的化学学习。
3.3 着重学科结构特质,忽略不同形式模型之间迁移的过程
大部分教科书以陈述科学事实与概念为主,忽略概念间的连结关系。以原子结构的发展为例,教科书时常先介绍汤姆生的西瓜模型再说明卢瑟福的原子模型,最后以轨道或是轨域的想法说明原子结构,而教科书的内容强调科学模型建构的结果,却忽略当时科学家建构科学模型发展、检验与修正的轨迹(刘俊庚和邱美虹,2010;Clement, 2000)。
3.4 强调科学理论的建构,忽略联系学生生活经验
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教科书多以工作分析的方式进行编写,也就是依照学科结构逐步加深与拓宽,然而却忽略学习化学与学生生活经验的关联性(Levy & Wilensky, 2009)。例如,学生会知悉最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即为四面体结构的甲烷分子,其可作为燃料;然而却无法统合理解甲烷分子作为燃料时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
4 模型观点对于教科书编写与教学的启发
模型即为说明物件以及物件间的关系的具体或是抽象的表征,透过教科书可以呈现科学模型内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模型的发展与修正历程。因此模型的认知观点可以提供教科书与教学的启发包含以下几点:建构适切的概念学习顺序,强化连结巨观、中观与符号表征之间的关系,注意语言使用在科学学习上的影响及提供学生反思与修正既有模型的机会,以帮助学生建构完整且融贯的科学模型。详细说明如下。
4.1 依据学习原理建构适切的概念学习顺序
模型涵盖内部物件与物件之间的关系,而科学模型亦由特定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组成,因此教科书呈现科学模型时需要考量科学模型的本质与建构历程,说明组成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再从中建构出完整的科学模型图像,最后形成适切的教学序列(林静雯和邱美虹,2009;Méheut, 2004; Méheut & Psillos, 2004)。例如,引入概念时需要引起动机并与生活经验结合,接着进行实验,再透过多重表征与多重类比形式建构出科学理论架构,并透过多样性的建模活动再精致学生建构出来的概念模型(Snir, Smith, & Raz, 2003)。
4.2 着重巨观、中观现象与化学符号之间的连结关系
根据学科呈现的外显模型(expressed model)以及学生内部的心智模式进行模型本位的学习方法,让学生透过表征的操作(manipulation)而对学习的概念进行融贯性地建构(钟建坪,2013;Chiu & Chang, 2013; Treagustetal., 2003)。例如,动手操作实验、提供具体分子模型并与模拟动画交互说明相同概念,让学生能够获得不同巨观、中观与符号间的转换。
4.3 注意语言在化学学习上的功能
语言是认知历程中将经验转化成知识的条件与过程(Halliday, 1993)。语言特征包含语句(syntax)、语意(semantics)以及语用(pragmatics)。化学学习中学生不仅应该理解化学教科书与科学社群书写的语句以及含意,更应该理解如何正确地使用陈述的科学语言。因此教科书应该提供适切的语言表征、理解学生生活情境中的语言限制、强化语言可能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以帮助学生概念顺利发展(Chiu, 2012)。
4.4 强化学生反思与修正既有模型以建构完整的科学模型
依据学习原理与知识建构的历程在教科书中明确地提供模型本位的课程,让学生可以将模型的素朴想法经由建构模型的历程逐步建构、检验、分析、运用以及转化既有模型为科学模型,并提供学生反思科学模型的转变历程,以及自身模型的限制,以进而转换自己既有不完整、不融贯的模型成为符合科学社群认同的科学模型(钟建坪,2013;Chiu, Chung, Lin, Liaw, & Yang, 2013; Jong, Chiu, Chung, 2013)。
4.5 着重模型的系统性思考以连结学生相关的生活经验与所学的科学理论
学习不该是片段的组成而应该有系统性的认识论架构作为统筹的依据,因此提供学生组织心智模式与外显模型的模型认知观点是必要的。透过模型观点将学生个人生活情境、先前知识与将要学习的科学理论连结,而学生也才能在学习之后将所学到的相关科学知识类推应用到自己的生活情境之中(Hofstein & Kesner, 2006; Pilot & Bulte, 2006),而非只是学到割裂的、片段的内容。例如,当介绍有机物时会说明提炼原油的技术,也提供生活当中可能运用到的产品,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化工产品使用的优缺点,让学生针对有限的资源思考生活周遭的问题。
5 结语与建议
化学概念的学习常因概念的抽象与复杂的特质,使学生在学习上常产生教学上非预期的结果。因此透过连结化学知识中巨观、符号以及中观三个面向与其交互作用的关系,并考量学生个体因素以及教学环境中所使用的语言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如图5所示,图5显示教科书应该提供学生转变自身素朴模型的环境以说明化学知识巨观、符号以及中观的连结,而教师根据个人特质及语言等方式协助学生透过感官知觉与学习环境产生交互作用(包括教科书与身处情境),并且监控(monitor)学生暂时性模型的转变(从M1、M2至M3)与需要建构特定模型时所需要的能力,让学生在学习历程中建构出完整且正确的概念模型以达到系统性的理解。
最后基于上述论述,本文针对教科书编写与教学提出如下建议:
5.1 教科书编写应该透过适切的语言连结巨观、中观与符号之间的关联
教科书通常提供教师教学活动设计与规划的依据,因此教科书编写应该考量如何使用适切的语言说明化学知识中的巨观现象、符号以及微观的特质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藉此提供学生明确的学习准则以建构出适切的心智模式。
5.2 针对不同特质学生,教师提供适切的学习特征帮助学生逐步建构正确的化学模型
教科书除了提供学生良好的阅读范本之外,亦应提供教师概念教学的依据,为使具有不同学习特质的学生都能够从学习中获得意义,教师需要针对不同学生提供多元表征(如类比模型、图表、示意图等),唯有透过适切的学习特征(如:语言、巨观、符号、中观等)才能够让学生产生意义的连结,也才能够从中获悉化学知识里巨观、中观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从中逐步修正既有的心智模式使其更趋于正确的化学模型。
参考文献:
[1]林静雯,邱美虹.整合类比与多重表征研究取向探究多重类比设计对儿童电学概念学习之影响[J].科学教育学刊,2005,13(3):317~345.
[2]林静雯,邱美虹.探究以学生心智模式为设计基础之教-学序列对学生电学学习之影响[J].科学教育学刊,2009,17(6):481~507.
[3]刘俊庚,邱美虹.从建模观点分析高中化学教科书中原子理论之建模历程及其意涵[J].科学教育研究与发展季刊,2010,59:23~54.
[4]钟建坪.模型本位探究策略在不同场域之学习成效研究[D].未出版博士论文.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2013.
第5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景观设计;多元系统;目标;实践主体
客观地讲就目前的中国景观艺术设计学科正处于探索阶段,从学科概念、学科性质到学科实践范围均缺少系统性、明确性和指向性。那么什么是景观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与景观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景观学体系中它的实践主体是什么?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从景观学的引导、多元系统设计以及景观艺术设计的实践主体进行系统的论述。
一、景观学引导下的艺术设计
景观艺术设计依托景观生态学,通过对自然的尊重、表达、展现生态环境的和谐与优美,依托景观建筑学创建城乡宜人的环境空间,依托景观人文学,表达人类行为心理的精神寄托及愿望,景观艺术设计成为景观形象高品质化生成的驱动力。
就景观学而言,景观艺术设计是景观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狭义的景观定义,是微观层次意义上的景观设计,在体现景观形象的创作上常常成为景观形象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景观艺术设计也涉及到景观学内容本身,但它更多的是遵循景观学的引导,关注景观形象要素对各景观环境系统空间进行艺术化处理,其核心任务是协调人与环境空间视觉形象的关系。景观艺术设计在景观学的引导下,构成了一个交叉融合的设计系统,它是运用艺术融于景观科学的手段来协调景观形象在环境空间的发展关系问题,并使之达到最佳状态。它融合了园林学、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成熟经验,以其艺术的视野,从系统、和谐、优美的角度,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景观形象的创新问题。
景观艺术设计在景观学的引导下,依据艺术和谐原则干预协调各景观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均衡关系时,更强调景观生成时对人精神上、视觉上、生理健康上的基本需求,通过景观环境空间艺术的创作,用以提升、陶冶公众的视觉审美经验,可以说景观艺术设计也是一种改善人们使用与体验户外空间的艺术创造活动。
二、多元系统设计含义的艺术设计
景观艺术设计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聚居环境空间艺术的二个方面。环境艺术设计从改善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室内设计起步,以室内室外环境一体化设计为核心,注重环境空间的自身形态,以及环境艺术的具体样式。而景观艺术设计更强调环境空间的综合形态、环境艺术的复合样式、环境表述的多层空间,具体表现在多元系统设计下的互融与综合。
(一)综合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是将城市、广场、街道、园林、建筑、壁画、广告、公共设施等环境空间看成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有机综合体,虽然它们有时是以几组形式出现,有时是以相对单一的个体出现,然而解决上述问题却要求兼顾到整体的环境,是在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造环境空间基础上实现的二次创造,景观艺术设计涉及到园林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造型设计、平面设计以及生态学、材料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并将这些知识纳入到景观艺术生成的总体设计系统之中。
(二)复合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是在景观学的引导下所构成的复合设计系统,由于景观艺术设计的综合性特点,因此常常表现出设计内容界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基于景观空间形态的视觉系统设计,融于区域景观精神的形象系统设计,反映区域文化特征的风格样式系统设计,以及关注人的行为、心理的人文关怀系统设计等等。各系统之间相互融合与交叉,共同构建起景观艺术设计的复合设计系统。
(三)多层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的设计空间呈现为多层性的表述特点,表现在从微观意义层面上的景观设计为主体到中观意义上的景观规划、宏观意义上的景观策划的多层与协调。
(四)广泛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的设计观念呈现出广泛性,《亚太景观》一书在导言中谈到现代景观设计带来的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宏观的观念、生态的观念、构成的观念、文脉的观念、民众参与的观念等等。其次是创作方法上…….所有这些凝结成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极简的、高技的……为景观设计师提供了广泛的创造可能性”。广泛的设计观念构成了景观艺术设计多元系统设计的哲学基础。
三、微观景观为实践主体的艺术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景观艺术设计学科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其实践范围广泛,内容综合而庞杂,既涉及到景观空间的各个层面又融合了环境要素的全部内容。但是如果只是从广义的概念出发而缺乏具体目标的限定,景观艺术设计学科建构将会一直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也是目前很多高校增设景观艺术设计专业方向后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即在庞大的景观学科中,景观艺术设计的实践范围或者说它的实践主体是什么的问题。
(一)宏观层面——景观策划。
宏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是建立在经济、旅游、生态等专业的基础上,包括进行大规模的景观生态保护、治理改造、景观资源开发、旅游策划规划等。这类景观实践主要侧重于景观前期的策划。核心是协调土地的利用与管理。是在大规模、大尺度上进行景观体系的把握,具体项目有区域控制性规划、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等。策划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二)中观层面——景观规划。
中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是指有一定的规模,涉及到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生态及地方特色整体风貌内容的较大型景观规划,包括与人类社会、文化相关内容,以及生态、历史等多学科的应用。规划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三)微观层面——景观设计。
微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主要指规模尺度较小,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景观环境设计。包括城市地形、水体、植被、建筑、构筑物以及公众艺术品等等。设计对象是城市开放空间,包括广场、公园、商业街区、居住区环境、城市街头绿地以及城市滨水地带等,其目的在满足景观环境功能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提高景观的艺术品质,已此丰富人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要求。设计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近年来,景观艺术设计伴随着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快速推进,以及人们对城市景观艺术形象期望值的不断提高,短短几年已发展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设计门类,然而与“遍地开花”的景观艺术实践工程项目相比,其学科发展与理论建构显得相对滞后,正因为这一缘故,景观艺术设计面临着许多课题,从学科观念、支撑专业、人才培养、实践主体,都有待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景观教育的发展与创新——2005国际景观教育大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6)
[2](美)约翰•o•西蒙兹《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2000
[3]郑曙旸《景观设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杭州 2002
第6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预防、处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问世以来,我国政府亦高度重视低碳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指导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应看到,由于部分低碳经济政策的内容尚不够合理,致使政策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政策并有效实施,以此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透视
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作为尽可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以最大限度地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制定并实施的低碳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逐渐摆脱传统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战略目标。但是,实践中却时常出现政策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偏离而不能有效推行国家意愿或政策传递与交接过程出现断层而不能有效传达政策意志的情况,由此导致了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根据政策全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将政策失灵分为政策制定失灵、政策执行失灵、政策评价失灵和政策监督失灵,[2]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政策制定失灵方面的问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根据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同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由于受“有限理性人”的限制无法考虑到政策目标的方方面面,因而在决策时可能无法做出真正反映现实需求的决策,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因受到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而偏离目标。从这一点上说,低碳经济政策失灵有其客观原因。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探究在这些客观原因背后是否有其他的可控因素导致了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低碳经济政策的贯彻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从规划低碳经济发展方向的宏观层面,到发展低碳城市与低碳产业的中观层面,再到对企业、个人行为规范的微观层面,层层推进。然而,尽管低碳经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概念,但它的政策效果却是基于企业和个人这一微观层面不断积累、传导和上升才能最终达成的。因此,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政策失灵的表现及成因,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低碳经济政策失灵问题。
在微观经济个体数目尚未达到饱和状态的范围内,自然环境可以被看作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公共物品,其对于微观经济个体而言既是基本不花费任何成本就能获得的资源要素,也是基本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破坏的环境要素。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破坏环境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微观经济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可能会罔顾政策法规和社会道德。而当大部分微观经济个体都采取高碳经营行为时,微观层面的高碳化将上升为区域产业、城市的高碳化,进而使整个国家的产业、能源、消费结构高碳化,[3]此时,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二、微观经济个体视角下低碳经济
政策失灵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高碳化运作收益与代价不对等导致的“公地悲剧”
第7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海水淡化循环经济路径战略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在针对资源节约,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解决的路径。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路径非常有助于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任务就是对垃圾的限制产生、合理利用及无害化处理。认为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合理和持久地利用所有物质,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实践中,如果仅从循环的角度研究生产过程的废弃物等资源的利用很容易陷入简单的“只要利用”就好的模式上。也就是说,只要能把废弃物利用上就具有循环经济价值,这种循环经济的认识就没有体现价值最大化原则,由此可能导致资源价值开发不够充分等缺憾。为了避免这一认识偏差,如果能把循环经济的活动范畴通过概念的细化和延伸,达到有效指导微观实践活动的效果,就利于实施循环经济时挖掘更具有经济价值的循环路径,使得投资和收益更好,实现循环经济价值最大化目标。
二、循环经济路径挖掘
鉴于当前循环经济缺少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不利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微观实践活动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有助于指导循环经济微观实践活动的四条路径。
1.从循环经济深度挖掘
循环经济深度是指延产业链上下游方向伸展的产业数量。如海水淡化循环经济过程中的上下游产业数量。具体表现为,相关上游产业提供的能源动力,即热电厂或大型钢铁行业中的企业提供的生产余热作为淡化海水的生产热能;下游相关行业中的企业对浓缩海水的开发利用,即晒盐场使用浓缩海水制盐、原盐用于下游的化工行业的企业生产原料,发展盐化工业等,这种循环经济发展方向代表了循环经济深度。见图1。
2.从循环经济宽度挖掘
循环经济宽度是指在产业链上下游方向延伸的过程中,在任何一个产业领域中可以分解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量。如海水淡化循环过程中使用某一中间排放物开发的产品品种数量。如在以原盐为原料的盐化工产业中,又可以分为工业品生产领域和生活用品生产领域,这两个方面就可以称为海水淡化循环经济宽度。另外,在海水淡化过程中,提取化学元素的种类、海洋生物制药,以及关联产业开发,如海水淡化装备制造业等都属于循环经济宽度,见图2。
3.进一步挖掘循环经济剩余
循环经济剩余是指在循环过程中是否仍然存在剩余排放物质或者虽然没有剩余,但是在循环开发中并没有实现某一排放物的价值开发最大化。如果没有实现价值开发最大化,我们仍然认为循环经济存在剩余。从经济活动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受内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如资金、市场、辅助资源等因素影响,可能无法一次建成循环经济体系,必然存在分阶段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循环剩余,或实现了循环,但循环不够充分,没有达到循环价值最大化的要求。如,仅把浓缩海水晒成原盐其价值开发就远没有达到最大化。
4.从循环经济相关性挖掘
循环经济相关性是指围绕循环经济的深度和宽度,凡是服务于循环经济体系的产业都称为相关产业,即与循环经济具有相关性。由此可知,循环经济体系越发达,带动的相关产业也会越多,循环经济价值越高,如图3。
从循环经济的深度、宽度、剩余及相关性四个微观概念看,它们对循环经济的价值最大化开发起到积极地引导和推动作用,能够促使循环经济参与者从循环经济的四个微观方面开发新的循环经济领域或新的产品,使得循环经济实现价值最大化。
三、基于循环经济路径挖掘的对策
关于循环经济路径挖掘仍以海水淡化产业的循环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发展海水淡化循环经济的思路和对策。
1.基于海水淡化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设计原则
(1)长远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发展海水淡化循环经济必须立足于发展多级产业链循环的目标。这种目标设置思路就要考虑循环经济的深度挖掘,追求循环经济价值最大化。实现这一目标不进行战略管理是难以实现的。同时,要认识到,围绕海水淡化循环经济要兼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创造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产业条件。
从实践看,实现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是一个战略过程,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阶段目标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到量力而行,掌控过程,有序发展。避免盲目的跃进式发展,贪大求快,造成投资失调,资源浪费,牺牲环境等问题。因此,在实施海水淡化循环经济过程中,要将战略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做到战略规划在先,有序推进阶段目标落实,为战略发展奠定基础。
(2)先易后难。实施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涉及到诸多的技术、管理、资金、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因此,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要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保证循环经济发展每一步的可行性,解决实际问题,有助于推动下一步循环发展。如,使用淡化海水是否被民众所接受,开发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循环经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等等。因为,就海水淡化来讲,如果没有民众的认识和支持,也就没有消费市场,淡化海水的使用和供应就会存在问题,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水淡化产业也就不可能,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更无法实现。所以,要考虑技术、管理、资金、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在兼顾和协调各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难易选择,推动海水淡化循环经济的发展。
(3)多目标市场开发。在规划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中,要注意循环经济的宽度和深度的路径挖掘与结合。既要注意研究循环经济的产业链上各产业的循环宽度,即本产业满足多目标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提升价值含量。还要立足于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战略高度,开发多目标的产业,搭建更宽度和更深度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只有实现海水淡化多目标市场开发,才能真正实现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价值最大化。
2.构建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体系
构建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体系是战略实践的基础。根据前文提出的循环经济的路径挖掘构建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体系,见图4。
从循环经济的宽度看,第一步可以有4种选择,即海水直接利用、海洋生物开发、海水淡化及伴随的余热利用。就这四个方面来讲,选择哪一个方面都涉及资源、技术、管理和投资等问题。因此发挥好资源优势,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就能够有效推动海水淡化循环经济的发展。如果当地的资源条件充足,可以同时考虑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达到提高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价值的目的。
从循环经济的深度讲,其深度开发更具有战略意义。淡化海水解决了陆地淡水的短缺问题,满足工业生产和民生的需要,同时利用循环经济路径挖掘的概念,可以深度挖掘浓缩海水的价值,而且这一阶段的价值开发可以有宽度和深度的多路径选择。如从宽度的的概念考虑,有化学元素提取和制盐。从深度概念考虑,有沿着提取的化学元素生产更多的化学产品;沿着原料盐开发,可以进入盐化工产业,并且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工业品产业链和民用品产业链。这种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深度开发和伴随的宽度开发能够极大地提高循环经济的价值。
从战略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看,在构建了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体系之后,就能清楚地看到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宽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可以明确制定长期战略目标,并进行战略周期划定,进而在战略周期内确定战略阶段目标和阶段划分。这种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战略目标与阶段目标结合的做法能很好地落实先易后难的策略,掌控循环经济开发的深度和宽度,更有效地利用和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从循环经济相关产业看,海水淡化循环经济有着广泛的相关产业与其共生。因为,该循环经济体系具有较宽和较深的循环经济特征,因此,该体系必然存在相关产业的专业设备和辅助设备制造,以及用于生产服务零部件的生产和供应,同时各产业对各种相关服务形成巨大的需求,从而随着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体系的发展,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出为海水淡化装备制造企业提供配套零部件和施工辅助用零部件,或专业用辅助设备等的生产,是考虑到产业分工规律和特点,以及这类零部件和专业辅助设备更适合中小企业生产加工,有助于形成产业集群。
提出循环经济路径挖掘的概念,对进一步开发循环经济领域,挖掘资源,杜绝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提高循环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
应当认识到,目前国内外关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指导方面,其原因是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是宏观经济,而循环经济的展开更注重于实践活动。因此,研究循环经济的微观理论更具有实践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董联党顾颖王晓璐:日本循环经济战略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亚太经济,2008,(2):68~72
[2]张东:天津临港工业区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战略研究.中国城市经济,2008,24 (10): 48~51
[3]我国瓶装水添新贵:中国食品科技网,省略 2009~4~14
第8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宏观国家形象;微观国家形象;认知形象;情感形象;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2-0062-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13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以往硬实力的竞争,发展到文化、外交、形象等软实力的竞争[1]。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资源,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更加直接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全面影响力的具体表现,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促进出口贸易,吸引海外投资、技术移民和国际旅游者[2]。
中国的旅游市场正在经历一个飞速发展并趋向于多元化的阶段[3]。中国出境旅游具有庞大的市场与巨大的消费能力,且中国出境市场仍处于与国情相适应的初步阶段[4]。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首次过亿,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17亿人次,同比增长8.96%;2014年韩国是中国旅游者出国旅游的第一大目的地国家,2015年韩国是中国旅游者出国旅游的第二大目的地国家[4-5]。由于潜在旅游者缺乏对旅游目的地的实际到访经历,对目的地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在选择目的地的决策过程中,目的地形象便成为一个关键因素[6]。目的地形象影响着潜在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和旅游地选择。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呈现何种特征和规律,是旅游目的地营销者和研究者欲加辨识又极力优化的学理与实践命题[7]。那么,目的地国家形象的感知对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有何影响?本研究选取中国潜在旅游者作为调查对象,研究中国潜在旅游者对韩国国家形象的感知,检验国家形象构成维度及其与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国家形象的概念与结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对国家形象概念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8]。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来自国际贸易和营销学领域。在国际贸易和营销学领域,原产国形象是消费者对一个特定国家的产品所形成的整体感知[9]。原产国作为信息线索不仅影响消费者对该国的整体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具有良好国家形象的产品[10]。国家形象是原产国形象概念的演 进[11]。Roth和Diamantopoulos在回顾原产国文献的基础上,将原产国形象(country-of-origin image)这一概念划分为3类:国家形象(country image)、产品-国家形象(product-country image)和产品形象(product image),其中,国家形象聚焦于国家的整体形象,产品-国家形象聚焦于国家及其产品的形象,产品形象聚焦于该国产品的形象[12]。Hsieh等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可分类为以下3组:整体国家形象(overall country image)、总产品国家形象(aggregate product country image)、特定产品国家形象(specific product country image)[13]。
国家形象是原产国效应的驱动力因素[10],当消费者购买一个特定国家的产品时,会将国家形象与该国的产品联系起来,便产生了原产国效应[9];原产国效应描述了国家形象对消费者决策的进一步影响[14],正面/负面的国家形象致使消费者对该国产品产生积极/消极的评价,进而会影响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消费行为。国家形象是消费者对与原产国相关联的各种要素,即宏观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技术等要素和微观层面上的具体产品品类,所选要素进行有效组合的创造性过程的结果[15-16]。
国家形象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3个成分,其中,认知成分是消费者对一个特定国家的信念,情感成分是消费者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情感反应,意向成分是指消费者对所要购买产品的国家的行为倾向。Roth和Diamantopoulos分析并总结了具体测量国家形象的量表,指出国家形象量表缺乏信度和效度检验,且量表中的题项内容主要反映了国家形象的认知维度,而情感维度的测量较缺乏,也有相关研究将意向成分纳入国家形象量表之中[12]。国内学者李东进等研究了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影响,构建了基于中国国情的兼具信度和效度的国家形象量表,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国家形象感知的6个维度分别是与中国关系评价、国家发展程度、整体产品评价、整体人民评价、交互意向和文化相似性,而产品形象的维度包括功能性评价和象征性评价[17];但该研究的国家形象6个维度仍属于国家认知形象,缺少对国家情感形象的测量。
1.2 宏观国家形象与微观国家形象
在国际贸易和营销学领域,有些学者将国家形象划分为宏观国家形象和微观国家形象两个维度,并认为二者内部具有关联性[16,18],这样划分便于克服以往原产国研究中偏向于宏观或微观国家形象研究的缺陷。Pappu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包括国家层面(宏观)和产品层面(微观)的构念[19]。宏观国家形象是指消费者对于一个国家所持有的描述性、推断性和信息性的信念的总和[20]。微观国家形象是指消费者对于一个国家的产品所拥有的声誉及印象[21]。如Pappu等从经济、政治、技术3个维度测量宏观国家形象,从创新、声望和设计3个维度测量微观国家形象[19];Pappu和Quester用工业化、经济发展、文化、自由市场体制、民主5个维度测量宏观国家形象,用信任、工作质量、创新、独立4个维度测量微观国家形象[16]。宏观国家形象量表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环境等方面的题项,而微观国家形象量表则包括创新、声望、设计、工作质量、信任等方面的题项。
旅游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关于目的地形象的研究,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一个特定目的地的知识、感情和整体印象的心理表征[22]。但以往研究对目的地形象概念化和操作化不统一,如不同研究分别用认知形象、情感形象、总体形象,或者三者的不同组合来表征目的地形象[23]。目的地形象构成的区域可划分为国家、省域、城市/乡村和景区[11,24-26],但目的地形象研究很少专门针对以国家为尺度的目的地进行特别讨论。Zhang等对国家尺度上的目的地形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国家为尺度的目的地形象结构主要是与旅游活动相关的方面(如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等),但具体的测量题项也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当地居民等,而这些内容也是国际贸易和营销领域国家形象概念中所包 含的[27]。
以往研究将旅游目的地对应于国家形象研究中的“产品”层面,国家形象研究中的产品主要为有形产品,而目的地是一种体验产品[11,24,28-29],这样,目的地形象就对应于国家形象研究中的产品形象[11,26]。由于以国家为尺度的目的地形象在内涵上与一般国际贸易和营销领域的国家形象有部分重叠(如政治、经济、环境、当地居民等),因此,以国家为尺度的目的地形象又不完全等同于产品形象或微观国家形象,在旅游领域需要重新整合国家形象和目的地形象两个概念,可以用国家形象表达国家尺度上的目的地形象[27]。而且,为了克服以往国际贸易和营销学领域国家形象研究偏向于宏观或微观国家形象研究的缺陷,可以采用宏观国家形象和微观国家形象相结合的视角进行旅游情境下的国家形象研究。本研究将旅游情境下的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尺度上的目的地形象即国家形象定义为国际旅游者对目的地国家的总体认知和情感的心理表征。
产品-国家形象聚焦于国家及其产品的形象,以一个国家的产品形象为基础,且衡量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维度是与该国的产品紧密相关的方面[24],如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工业化程度、劳动力状况等;而本研究的微观国家形象则是直接与核心旅游产品相关的形象,如旅游设施、自然与人文景观、整体氛围等,更强调核心旅游产品方面;本研究的微观国家形象与产品-国家形象的侧重点不同。本研究的宏观国家形象即国际贸易和营销学领域中的国家形象,是基于经济、技术、政治、两国关系、工业化程度、环境状况与管理、国民等因素而形成的形象。
1.3 国家认知形象与国家情感形象
国家形象包括国家认知形象和国家情感形 象[30-32],以往国家形象的研究缺少对国家认知形象与国家情感形象的区分,主要关注国家认知形象,但近年来,国家情感形象逐渐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Brijs等研究了比利时学生群体对西班牙和丹麦产品原产国的国家形象感知和态度,检验了国家形象的结构,结果发现国家认知形象正向影响国家情感形象[31]。
在旅游研究领域,Baloglu和McCleary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形象正向影响情感形象[22];张宏梅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检验旅游目的地形象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有显著正向影响[33];Elliot等运用地方形象的整合模型,研究分析韩国和加拿大的消费者对澳大利亚国家形象的评估,检验国家认知形象与国家情感形象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国家认知形象显著直接影响国家情感形象[34]。本研究将旅游领域的国家形象划分为宏观国家形象和微观国家形象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均由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组成,即宏观国家形象分为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和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微观国家形象分为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和微观国家情感形象。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a: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对宏观国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响;
假设1b: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响;
假设1c: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响;
假设1d: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对宏观国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响。
1.4 国家形象与旅游意向
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是一个人主观判断其未来可能采取行动的倾向,也是消费者对于产品或企业可能采取的特定活动或行为倾向[35]。消费者行为意向可划分为购买意向、再购意向、采购意向、支出意向和消费意向,而购买意向指消费者对该产品是否有购买意愿及意愿程度的高低[7]。国家形象影响消费者对该国产品和服务的评价,因此,在销售产品和制定营销战略方面,应充分发挥国家形象的作用[2]。
在国际贸易和营销学领域,以往研究表明国 家形象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和购买意向存在显著影响[13,17,36],消费者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评价越正面,就越有可能购买该国产品。李东进等研究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形象对购买意向没有直接影响,但国家形象通过产品评价、品牌态度、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购买意向[17]。Lala等检验国家形象、感知质量与购买意向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家形象通过感知质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购买意向[37]。Maher和Carter则指出国家形象中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对购买意向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他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国家认知形象而言,国家情感形象对消费者产品购买意向的影响更大[32]。Wang等将国家形象解构为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分析两者对购买意向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国家情感形象对购买意向有显著直接影响,国家认知形象通过产品形象间接影响购买 意向[30]。
在旅游研究领域,旅游意向(travel intention)是在指定时间内,旅游者认为将会去特定目的地旅游的可能性[38],旅游意向是购买意向的一种。由于旅游产品具有服务性、无形性和体验性等特点,潜在旅游者游前无法亲身体验当地的旅游产品,承担着较大的购买风险,目的地形象就会影响着潜在旅游者的出游意愿与目的地选择[39]。旅游意向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果变量,旅游者的旅游意向与实际旅游行为明显相关[40]。
Chalip等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为例,研究发现目的地形象与旅游意向显著相关,且因国籍不同影响旅游意向的形象因子也不同,安全、发展、自然环境因子与美国人的旅游意向显著相关,而新奇、便捷因子则对新西兰人更为重要[41]。目的地形象对旅游者行为意向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42]。白凯等分析韩国潜在旅游者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与行为意向,研究表明目的地形象认知与其行为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形象中的平和、愉悦特征对韩国潜在旅游者的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7]。旅游者对目的地的认知可以很好地预测旅游者的行为意向[43]。也有研究发现目的地认知形象对旅游者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不明显,但可以通过情感形象对旅游者行为意向产生间接影响[33]。
目前,关于国家形象对旅游意向影响的研究还较少。Elliot等将产品-国家形象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整合到地方形象模型内,分析韩国首尔的消费者对美日两国国家形象评估,检验目的地、产品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国家情感形象直接影响产品和目的地的接受能力(目的地的接受能力是由愿意去旅游、理想的国家和目的地整体很好3个题项测量)[44]。Nadeau等以尼泊尔作为案例地,把目的地形象放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国家形象情境之中,通过调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检验国家形象、目的地形象与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家形象通过目的地形象对现实旅游者的未来旅游意向产生间接影响[28]。Zeugner-Roth和?abkar研究国家形象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国家个性维度分别对行为意向中的旅游意向、购买意向、投资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国家认知形象而言,国家情感形象更能够影响消费者去该国的旅游意向[45]。张宏梅和蔡利平在整合国家形象与目的地形象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旅游者旅游意向模型和国家形象对旅游意向有显著直接影响的命题[11]。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a: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对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响;
假设2b: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对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响;
假设3a: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对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响;
假设3b: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对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响。
1.5 关于韩国形象的研究
关于韩国形象研究的视角主要来自传播学和旅游学领域。在传播学领域,对韩国形象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及原因[46-47],中国民间网络社区中的韩国国家形象[48]。在旅游研究领域,对韩国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韩流”效应,韩国举办大型事件对韩国入境旅游者形象感知,潜在旅游者对韩国形象感知方面。韩剧可以影响观众对韩国旅游形象的感知,增加他们对韩国的熟悉 程度和到韩国旅游的兴趣,影响旅游者的旅游意 向[39,49-50]。Lee等研究发现,旅游者对韩国形象感知中吸引力、舒适度、物超所值和异国情调4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并能够对旅游者的旅游决策、综合评价、现场体验以及行为意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51];2002年韩国世界杯的举办提升了韩国国家形象[52]。郭英之等探讨中国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市场竞争以及市场定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旅游者对韩国最具积极的感知形象为“旅游计划易于安排”和“购物的好去处”[53]。隋丽娜研究国内长三角居民对韩国旅游形象的感知,发现韩国干净整洁比较突出,对美食、完善的住宿和交通设施、自然景观、当地人民的亲切感的认同度较高,对语言障碍、旅行成本、节庆活动和陌生感的认同度较低[54]。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设计
现有的国家形象量表多是基于国家作为有形产品制造地和生产地的视角开发的,与旅游相关的内容较少。在分析已有的国家形象量表、目的地形象量表的基础上,参照Roth和Diamantopoulos[12]、Pappu等[19]、Nadeau等[28]、Knight等[55]、Martínez和Alvarez[56]等人的量表,把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分为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环境、国家关系和国民7个维度,宏观国家情感形象由“我喜欢韩国”和“我喜欢和韩国人在一起”这两个题项测量。参照Choi等[40]、Lee等[51]、Kim和Morrsion[52]、Beerli和Martín[57]、Lee等[58]等人的量表,把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分为自然、历史文化、旅游环境、旅游设施和购物5个维度,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则由3个题项来测量,分别为“去韩国旅游让我非常愉快”、“去韩国旅游感觉悠闲放松”和“去韩国旅游令人激动”。所有题项都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旅游意向用题项“在未来5年内,你愿不愿意去韩国旅游”来测量,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由于旅游者访问过旅游目的地后,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会被修正,从而形成更为“现实、客观、差异化和复杂化”的再评估形象[56,59-60],故本研究为了检验国家形象的感知与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选取未访问过韩国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并设置“你有没有去过韩国”该题项进行筛选。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于2015年1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在南京、合肥两地的机场、公园和大型购物中心进行。在发放问卷时,调查者简要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并询问一下被调查者“你有没有去过韩国”,若被调查者回答“没有”,则问卷现场发放给被调查者,被调查者做完后立刻收回。共发放问卷326份,去除无效问卷44份,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为282份,有效率87%。
使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进行初步分析。在样本的婚姻状况中未婚比例最高(60.6%);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年龄多集中于25~44岁之间(49.3%),次之为15~24岁之间(36.9%);在受教育程度上,大学本科所占比例最高(41.2%),其次为专科学历(30.9%);个人月收入在2000~4000元之间的最多(33.3%),其次为4000~6000元之间(24.6%);在职业上,有学生(23.6%)、公司职员(21.8%)、专业技术人员(12.9%)、其他(9.6%),分布较为分散;在获取有关韩国的信息来源中,韩剧/电影/音乐是最为主要的信息源(68.4%),该国产品(如三星/LG/现代)(41.1%)、网络(36.9%)、书籍/杂志/报刊(25.5%)、亲戚/朋友(23.4%)、旅行社(16.7%)、宣传册/旅游指南(12.8%);在地域分布上,安徽省居民(38.7%)、江苏省居民(34.4%)、其他省市居民(26.9%),调查样本涵盖了国内大多省市。
3 研究结果
3.1 国家认知形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3.1.1 宏观国家认知形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最初的宏观国家认知形象测量量表包括21个题项,首先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宏观国家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负荷大于0.5和共同度大于0.5,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通过5次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包括5个因子的由16个题项构成的宏观国家认知形象量表,5个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66.09%(表2)。
依据同一因子所包含题项的共同内涵,将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因子分别命名为国家特征、国家能力、国民特征、环境管理、国家关系。国家关系的信度值为0.47,因其信度值在0.5以下,信度偏低,故在后面的分析中将该因子删除。总体来看,受调查者对宏观国家认知形象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其中,对国家能力和国家关系评价最高(均值为3.54),其次为环境管理(均值为3.40),而对国家特征和国民特征评价较低(均值分别为3.29和3.28)。
3.1.2 微观国家认知形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微观国家认知形象测量量表包括17个题项,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微观国家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负荷大于0.5和共同度大于0.5,以及某题项负荷在某公因子下的内容效度等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按照以上标准通过8次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包括3个因子的由7个题项构成的微观国家认知形象量表,3个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66.29%(表3)。以往有些研究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采用的标准为因子负荷小于0.4、共同度小于0.4或者同时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都大于0.4者删除[7,37,60]。由于本研究的题项剔除标准更为严格,即因子负荷小于0.5、共同度小于0.5以及题项的因子负荷同时在两个因子上均大于 0.4[42,56],可能使较多题项被删除,但得到的3个因子基本上反映了微观国家认知形象的主要方面[27,29,51]。
将微观国家认知形象的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旅游环境、旅游设施、文化氛围。信度值大小与测项数的多少有关,当测项数少于6个,信度值有时可能会低于0.6[7,61]。微观国家认知形象的整体信度较低,可能是由于“旅游环境”、“旅游设施”和“文化氛围”因子的测项数均少于6个所致,除了文化氛围因子的信度值为0.57(在0.6以下),另外两个因子信度值均大于0.60,表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各指标能够较好地衡量相应因子。
调研发现,受调查者对微观国家认知形象中的旅游设施评价最高(均值为3.49),其次为旅游环境(均值为3.41),而对文化氛围评价最低(均值为3.26)。
3.2 国家情感形象
本研究将国家情感形象分为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和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宏观国家情感形象量表包括“我喜欢韩国”和“我喜欢和韩国人在一起”两个题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量表包括“去韩国旅游让我非常愉快”、“去韩国旅游感觉悠闲放松”和“去韩国旅游令人激动”3个题项。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和微观国家情感形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和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均为单维度变量。
潜在旅游者对宏观国家情感形象题项“我喜欢韩国”和“我喜欢和韩国人在一起”的感知均值分别为3.20和2.94;宏观国家情感形象的信度值为0.82。潜在旅游者对微观国家情感形题项“去韩国旅游让我非常愉快”、“去韩国旅游感觉悠闲放松”和“去韩国旅游令人激动”的感知均值分别为3.25,3.30和3.26;微观国家情感形象的信度值为0.81。总体来看,潜在旅游者对韩国有着积极正面的情感形象,且潜在旅游者对韩国的微观国家情感形象的评价要高于宏观国家情感形象。
3.3 国家形象对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的影响
此次问卷调查的样本中,在未来5年内,愿意去韩国旅游的潜在旅游者为220人,占总人数的78%;选择不愿意去韩国旅游的人数为62人,占总人数的22%;这说明样本中选择愿意去韩国旅游的人数所占比例很高。
为了分析韩国国家形象对中国潜在旅游者去韩国旅游意向有何影响,本研究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把“在未来5年内,您是否愿意去韩国旅游”,即旅游意向作为被解释变量,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形,分别赋值为1和0;以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作为解释变量;将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教育、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3.3.1 交叉分析
本研究对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交叉表分析与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特征中,仅性别通过卡方检验,卡方值为8.85,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中愿意去韩国旅游的比例为85.5%,男性中愿意去韩国旅游的比例为70.8%,女性比男性去韩国的旅游意向更强。在接下来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将性别变量纳入模型之中。
3.3.2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每个因子测量题项的均值进行回归分析,使用SPSS 17.0中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旅游意向的关系进行检验,采用向前条件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从第1个模型到第5个模型,每次均增加一个新变量进入模型。由于国家宏观认知形象维度中的国家特征和国家能力没有符合条件,均未进入模型之中。综上,用该方法得到的各模型的显著水平均较高,进入模型的各变量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5的-2Log Likelihood=186.88,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5的HosmerCLemeshow检验结果为P=0.408>0.05,统计不显著,也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5中的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和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假设3a和假设3b被支持,故国家情感形象对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的影响显著,呈正相关关系。潜在旅游者对韩国国家情感形象的评价越高,他们就越有可能去韩国旅游。
3.4 国家认知形象对国家情感形象的影响
从表4中的回归分析模型2和模型3易知,在没有纳入国家情感形象变量之前,国家认知形象对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是有显著影响的;如模型2中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变量的影响显著,模型3中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变量影响不显著,而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国家情感形象的纳入(模型4和模型5),国家认知形象对旅游意向的影响就不显著了。以上分析表明国家情感形象在国家认知形象和旅游意向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假设2a和假设2b被拒绝。
为了分析国家认知形象对国家情感形象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对国家认知形象与国家情感形象进行检验。使用SPSS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的选入方式采用Enter进入法,强制全部变量同时进入模型。检验国家认知形象各维度对宏观情感形象的影响,以及国家认知形象各维度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的影响,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知,各模型F值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01,说明表中的各模型的拟合效果都很好。模型1是检验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和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对宏观国家情感形象的影响,结果显示:宏观国家认知形象中的国民特征因子对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影响正向显著,假设1a被部分支持;微观国家认知形象中的旅游环境、旅游设施、文化氛围3个因子均显著正向影响宏观国家情感形象,假设1d被支持。模型2是检验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和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的影响,结果显示:宏观国家认知形象中的国民特征因子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影响正向显著,假设1b被部分支持;微观国家认知形象中的旅游环境、旅游设施、文化氛围3个因子对微观国家情感形象影响正向显著,假设1c被 支持。
4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中国潜在旅游者对韩国国家形象感知为例,检验国家形象构成维度及其与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整合了国际贸易和营销领域的国家形象和旅游领域的目的地形象概念,在旅游领域重构国家形象概念,将国家形象划分为宏观国家形象和微观国家形象,把目的地形象与国家形象的部分重叠内容(如政治、经济、当地居民等)归到宏观国家形象概念中,可以避免目的地形象和国家形象研究中出现重叠这一问题,解决在国家形象研究语境下讨论目的地形象可能出现的概念化和操作化问题。本研究对韩国国家认知形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得到5个因子分别为国家特征、国家能力、国民特征、环境管理、国家关系,微观国家认知形象得到3个因子分别为旅游环境、旅游设施、文化氛围,该结果与Zhang等[27]、Nadeau等[28]的研究较为一致。由于宏观国家认知形象因子中的“国家关系”信度值较低,故未纳入后面的回归分析中。本研究区别了国家认知形象和国家情感形象,以往多数国家形象研究仅关注认知形象,缺少对情感形象的研究,即使有的研究者测量了情感形象,但其测量题项实质上仍是认知性质的[12]。在预测国际旅游者的行为意向上,对国家认知形象或国家情感形象任何一个方面的测量都不能忽略。
使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国家形象对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的影响,得到以下结果:
(1)国家情感形象对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往对潜在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及其行为意向的研究表明目的地情感形象正向影响旅游者行为意向[7,33],本研究支持这一结果,并在旅游领域充实了国家形象与旅游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证明国家情感形象能够更好地预测国际旅游者的旅游意向。国家情感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以往研究很少将国家情感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的构成部分。国家情感形象是目的地国家给旅游者带来的情感收获,是影响旅游意向的最重要的成分,是旅游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在两个类似的目的地国家之间,旅游者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更为喜欢的目的地国家[45]。因此,本研究成果为韩国国家形象管理部门进行高效率的旅游形象宣传提供理论依据,管理部门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着重从国家情感形象方面进行,对目标市场潜在旅游者的情感形象进行培育、塑造和监测。
(2)微观国家认知形象显著影响国家情感形象,宏观国家认知形象中的国民特征因子显著影响国家情感形象。这一结果支持Brijs等[31]、Elliot等[34]的研究。国家认知形象通过国家情感形象的中介作用影响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相对于国家认知形象而言,国家情感形象能够更好地预测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这与Zeugner-Roth和?abkar[45]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仅用国家情感形象来解释潜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是不够的,需要结合国家认知形象来共同解释旅游意向,这样就形成了“国家认知形象-国家情感形象-旅游意向”的影响模式。如果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国家各属性的认知评价较高、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较为强烈,那么,他们就会产生去该国的旅游意向;反之,则不会产生去该国的旅游意向。而微观国家认知形象显著影响国家情感形象,因此让潜在旅游者了解韩国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和整体氛围,并对其产生较高的认知评价,进而导致积极的情感体验,就显得特别重要。此外,韩剧/电影/音乐、该国产品(如三星/LG/现代)、网络等是潜在旅游者获取有关韩国信息的主要来源,韩国旅游营销组织可通过这些非商业沟通渠道,从韩国的国民特征、旅游设施、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宣传,增进受众对韩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以上这些研究结果也为中国旅游管理部门提升国家形象,应对旅游市场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参与国际旅游竞争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没有将熟悉度纳入研究框架内,以往研究表明熟悉度会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感知[24,28,44],在以后的研究中可检验该变量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第二,潜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与实际旅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空 隙”[62]。对旅游者来说,影响其目的地选择的因素比一般产品的选择要复杂,许多旅游者对目的地印象很好,但由于时间、经济、同伴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或想游览更加偏好的目的地,而暂时没有游览或意向较弱[23]。第三,国内学术研究中一般采用方便抽样法[63],本研究采用该方法收集数据,所调查样本结构能够满足解决本研究问题的需要,即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的结果需要进行更多的验证。由于在合肥、南京两地进行的取样,故安徽和江苏居民较多,致使本研究的样本不能够很好地代表中国的潜在赴韩旅游者;又由于本次问卷调查是在1月份进行的,该月份在寒假期间,且调研地点为城市的机场、公园和大型购物中心,可能使得学生样本所占比例较大;因此,以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的地点和样本量,也需要注意收集数据的时间。第四,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因旅游者群体的不同而不同[64],后续研究还应进一步检验不同群体的国家形象感知与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
致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姜小云教授对本文英文摘要的修改润色。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ang Yi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ountry image building[J]. Around Southeast Asia, 2009, (9): 101-105. [桑颖. 论国际旅游与国家形象的塑造[J]. 东南亚纵横, 2009, (9):101-105.]
[2] Kotler P, Gertner D. Country as brand, product, and beyond: A place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02, 9(4/5): 249-261.
[3] Mccabe S, Li Chunxiao. This “new” tourists nor that new tourists: Challenges facing meet the needs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ts[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2): 5-8. [Mccabe S,李春晓. 此“新”游客非彼新游客: 满足中国出境游客需求所面临的挑战[J]. 旅游学刊, 2015, 30(12): 5-8.]
[4] China Tourism Academy. Annual Report of China Out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2015[M].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2015: 2, 16.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5[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5: 2, 16.]
[5] China Tourism Academy. Annual Report of China Out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2016[M].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2016: 2, 8, 156.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6[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6: 2, 8, 156.]
[6] Leisen B. Image segmentation: The case of a tourism destination[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001, 15(1): 49-66.
[7] Bai Kai, Chen Nan, Zhao Anzhou. Potential Korean tourists’ cognition of Chinese destination image and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J]. Tourism Science, 2012, 26(1): 82-94. [白凯, 陈楠, 赵安周. 韩国潜在游客的中国旅游目的地意象认知与行为意图[J]. 旅游科学, 2012, 26(1): 82-94.]
[8] Jin Zhengkun, Xu Qingchao.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The new task for China’s diplomacy[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 (2): 119-127. [金正昆, 徐庆超. 国家形象的塑造: 中国外交新课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 (2): 119-127.]
[9] Roth M S, Romeo J B. Matching product category and country image perceptions: A framework for managing country-of-origin effec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23(3): 477-497.
[10] Koschate-Fischer N, Diamantopoulos A, Oldenkotte K. Are consumers really willing to pay more for a favorable country image? A study of country-of-origin effects on willingness to pa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2, 20(1): 19-41.
[11] Zhang Hongmei, Cai Liping. Country image and destination imag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concepts and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9): 12-18. [张宏梅, 蔡利平. 国家形象与目的地形象: 概念的异同和整合的可能[J]. 旅游学刊, 2011, 26(9): 12-18.]
[12] Roth K P, Diamantopoulos A. Advancing the country image construc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7): 726-740.
[13] Hsieh M H, Pan S L, Setiono R. Produc-, corporate-, and country-image dimensions and purchase behavior: A multicountry analysi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4, 32(3): 251-170.
[14] Li Xiaohua. National marketing and the upgrading of “China Manufacturing”[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9(11): 36-39. [李晓华. 国家营销与“中国制造”升级[J]. 经济管理, 2007, 29(11): 36-39.]
[15] Keller K L.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3, 57(1): 1-22.
[16] Pappu R, Quester P. Country equity: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0, 19(3): 276-291.
[17] Li Dongjin, An Zhongshi, Zhou Ronghai, et al.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untry image on purchase intention of customers based on Fishbein’s model of reasoned action: The country images of America, Germany, Japan and Korea[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08, 11(5): 40-49. [李东进, 安钟石, 周荣海, 等. 基于Fishbein合理行为模型的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研究――以美、德、日、韩四国国家形象为例[J].南开管理评论, 2008, 11(5): 40-49.]
[18] Amonini C, Keogh J, Sweeney J C. The dual nature of country-of-origin effects--A study of Australian consumers’ evaluations[J].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 1998, 6(2): 13-27.
[19] Pappu R, Quester P G, Cooksey R W. Country image and consumer-based brand equity: Relationship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5): 726-745.
[20] Martin I M, Eroglu S. Measur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untry im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3, 28(3): 191-210.
[21] Nagashima A. 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US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product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0, 34(1): 68-74.
[22] Baloglu S, McCleary K W. A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4): 868-897.
[23] Zhang H, Fu X, Cai L A, et al. Destination image and tourist loyalty: A meta-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1): 213-223.
[24] Zhang Jingru, Chen Yingzhen, Zeng Qi, et al.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in a country context:A case stud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Beijing[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3): 13-22. [张静儒, 陈映臻, 曾祺, 等. 国家视角下的目的地形象模型――基于来华国际游客的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3): 13-22.]
[25] Bai Kai, Guo Shengwei.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ymbiotic image in scenic areas on tourists’ willingness of revisit and their words of mouth effect: A case study on Qujiang scenic areas with the theme of Tang culture in Xi’an[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 53-28. [白凯, 郭生伟. 旅游景区共生形象对游客重游意愿及口碑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西安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为[J]. 旅游学刊, 2010, 25(1): 53-58.]
[26] Mossberg L, Kleppe I A. Country and destination image:Different or similar image concept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4): 493-503.
[27] Zhang H, Xu F, Leung H H, et al. The influence of destination-country image on prospective tourists’ visit intention: Testing three competing model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21(7): 811-835.
[28] Nadeau J, Heslop L, O’Reilly N, et al. Destination in a country image contex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1): 84-106.
[29] Lei Yu, Zhang Hongmei, Xu Feifei, et al.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Chinese country image perceptions: A case study of China, UK and USA university students[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3): 23-34. [雷宇, 张宏梅, 徐菲菲, 等. 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跨文化比较――以中国、英国、美国大学生为例[J]. 旅游学刊, 2015, 30(3): 23-34.]
[30] Wang C L, Li D J, Barnes B R, et al. Country image, product image and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 21(6): 1041-1051.
[31] Brijs K, Bloemer J, Kasper H. Country-image discourse model: Unraveling meaning,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untry imag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12): 1259-1269.
[32] Maher A A, Carter L L. The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components of country image: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products in Kuwait[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11, 28(6): 559-580.
[33] Zhang Hongmei, Lu Lin, Cai Liping, et al.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structural model and visitors’ behavioral intentions: Based on a confirmatory study of localization of potential consumers[J]. Tourism Science, 2011, 25(1): 35-45. [张宏梅, 陆林, 蔡利平, 等. 旅游目的地形象结构与游客行为意图――基于潜在消费者的本土化验证研究[J]. 旅游科学, 2011, 25(1): 35-45.]
[34] Elliot S, Papadopoulos N, Szamosi L. Studying place im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holistic approach[J]. Anatolia, 2013, 24(1): 5-16.
[35] Folkes V S. Recent attribution 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 A review and new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8, 14(4): 548-565.
[36] Yin Shenghuan.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nsumer’ Selection of Korean Products[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05. [尹盛焕. 中国消费者对韩国产品选择的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5.]
[37] Lala V, Allred A T, Chakraborty G. A multidimensional scale for measuring country imag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009, 21(1): 51-66.
[38] Woodside A G, Lysonski S. A general model of traveler destination choice[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9, 27(4): 8-14.
[39] Liu Li. Screen-induced tourism: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age and intention to visit[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9): 61-72. [刘力. 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与游客旅游意向――基于影视旅游视角的综合研究[J]. 旅游学刊, 2013, 28(9): 61-72.]
[40] Choi J G, Tkachenko T, Sil S. On the destination image of Korea by Russian touris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1): 193-194.
[41] Chalip L, Green B C, Hill B. Effects of sport event media on destination image and intention to visit[J].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2003, 17(3): 214-234
[42] Chen C F, Tsai D C. How destination image and evaluative factors affect behavioral inten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4): 1115-1122
[43] Bai Kai, Ma Yaofeng, Li Tianshun, et al. An association study on tourists’ cognition, perceived value and behavior intention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A case study of inbound tourists in Xi’an Cit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2): 244-255. [白凯, 马耀峰, 李天顺, 等. 西安入境旅游者认知和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图[J]. 地理学报, 2010, 65(2): 244-255.]
[44] Elliot S, Papadopoulos N, Kim S 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place image: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stination, product, and country imag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5): 520-534.
[45] Zeugner-Roth K P, ?abkar V.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untry and destination image: Assessing common facets and their predictive valid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9):1844-1853.
[46] Tang Xiaojin. Changes and the reasons for South Korea’s country image in TV ads.[J]. Contemporary Manager, 2006, (8):192-193. [汤孝锦. 韩国旅游电视广告中国家形象的变迁及原因[J]. 当代经理人, 2006, (8): 192-193.]
[47] Wang Xiaoling, Dong Xiangrong. Changes and inspiration of South Korea’s country image[J]. Contemporary Korea, 2010, 2: 42-47. [王晓玲, 董向荣. 韩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及其启示[J]. 当代韩国, 2010, 2: 42-47.]
[48] Wen Chunying, Liu Xiaoye. Chinese folk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South Korea’s country image[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2012, (8): 54-56. [文春英, 刘小晔. 中国民间网络舆论中的韩国国家形象[J]. 对外传播, 2012, (8): 54-56.]
[49] Wang Yan.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s of Teleplays and Films on Tourist Image of Their Locations: A Case of the Influences of South Korean Teleplays and Films on Korean Tourism Image[D]. Nanning: Guangxi University, 2007. [王艳. 影视剧对其外景地旅游形象的影响研究――以韩剧对韩国旅游形象的影响为例[D]. 南宁: 广西大学, 2007.]
[50] Tang Daijian, Park ChangKyu. A trial elab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Korean Wave on tourism image of Korea[J]. Tourism Science, 2007, 21(2): 17-22. [唐代剑, 朴昌奎. “韩流”对韩国旅游形象的影响[J]. 旅游科学, 2007, 21(2): 17-22.]
[51] Lee C K, Lee Y K, Lee B K. Korea’s destination image formed by the 2002 World Cup[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4): 839-858.
[52] Kim S S, Morrsion A M. Change of images of South Korea among foreign tourists after the 2002 FIFA World Cup[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2): 233-247.
[53] Guo Yingzhi, Zhang Hong, Song Shuling, et al. A study of market positioning of China’s outbound travel destinations[J]. Tourism Tribune, 2004, 19(4): 27-32. [郭英之, 张红, 宋书玲, 等. 中国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市场定位研究[J]. 旅游学刊, 2004, 19(4): 27-32.]
[54] Sui Lina. An Apperceiving Model of Tourism Image and It’s Application[D]. Hangzhou: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2007. [隋丽娜. 旅游形象感知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以长三角居民对韩国旅游形象感知为例[D].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07.]
[55] Knight G A, Spreng R A, Yaprak A. Cross-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easurement scale: The COISC[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3, 12(5): 581-599.
[56] Martínez S C, Alvarez M D. Country versus destination imag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0, 27(7): 748-764.
[57] Beerli A, Martín J D. Touris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erceived image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A case study of Lanzarote, Spai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5): 623-636.
[58] Lee B K, Lee C K, Lee J. Dynamic nature of destination image and influence of tourist overall satisfaction on image modific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4, 53(2): 239-251.
[59] Selby M, Morgan N J. Reconstruing place image: A case study of its role in destination market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4): 287-294.
[60] Kim S S, Mckercher B, Lee H. Tracking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4): 715-718.
[61] Lu Wendai. SPSS Statistics Analysis (the 4th Edition)[M].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010: 512. [卢纹岱. SPSS统计分析(第四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512.]
[62] Kah J A, Lee C K, Lee S H. Spatial-temporal distances in travel intention-behavior[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57: 160-175.
第9篇:微观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波动性;波粒二象性;粒子性
近代物理学的研究表明,一切微观体系都具有波粒二象性,这是被实验结果所证实了的,是为人们所普遍公认的。然而,在量子力学或原子物理学的一些教科书中,在讲述微观体系或光的波粒二象性时,往往有如下一些说法出现:“既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波动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具有微粒性”。“光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波动性,在和物质相互作用时具有粒子性。”作者认为,类似的这种表述是不确切的,严格地说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不利于读者对整个量子力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一、关于波粒二象性表述的误区
(一)它否定了“二象性是一切微观体系的本质属性”这一基本事实
我们注意到上述引文“具有”一词的表述,言下之意是微观体系或光在“具有波动性”的情况下不具有粒子性;反过来,当它“具有微粒性”的情况下,就再也不具有波动性。或者说,“光在传播过程中”就不具有微粒性,而“在和物质相互作用时”就不具有波动性。
“波粒二象性”是光和每个物质体系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既然是本质属性,就是固有的、时刻存在的。过去已有许多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而最近瑞士科学家发现的光子以某种方式在10km距离相联系的实验证据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既然是本质属性,就意味着,它们既可按波行事,也可按粒子行事;究竟是表现波的行为,还是表现粒子的行为,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任何“本质”的东西都是与过程无关的,是不因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而改变的,只不过本质属性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来,而在某些别的情况下则被压抑而不表现出来罢了。毫无疑问,不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存在的、不“具有”的东西。
(二)容易引导读者陷入经典物理学观念的束缚中
在经典物理学中,所谓波动,指的是某一实在的物理量(例如力、位移、压强、电场强度等)在空间(通过介质)的传播过程,并且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干涉、衍射现象。而所谓粒子,则是一整份地出现在空间中的客体,这种客体具有确定的质量、电荷、动量等,并且在时空中有一条确定的运动轨道。在传统的经典物理学看来,波动性和粒子性是完全对立的,绝对不能统一,不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客体中。上述说法恰恰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并且似乎所说的粒子性和波动性就是经典意义下的粒子性和波动性。
(三)从哲学上说,是违背对立统一规律的,是形而上学的
这种说法实际上把“波动性”和“粒子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互不相容,采取“有此无彼”“有彼无此”或“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形式,彼此无法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因而与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是相违背的,是形而上学的。
(四)动摇了量子力学理论的认识基础
微观体系具有波粒二象性,这是量子力学理论认识的基础,或者说是量子力学理论的物理基础,由这个基础出发,才建立起整个量子力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微观体系的运动状态用波函数来描述,波函数(运动状态)的变化遵循薛定谔方程,微观体系的力学量用算符表示等。如果微观客体不是时刻具有波粒二象性,而是某些时候具有波动性,在别的不具有波动性的时候才具有粒子性;反之亦然,那么,量子力学就失去了认识基础。随之,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量子力学的理论框架也将倒塌。
二、量子力学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量子力学教学中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要彻底摈弃经典物理学观念的束缚
首先要明确,在微观领域,不可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给微观粒子拼凑出一个具体模型,历史上曾有过设想微观体系是粒子组成的疏密波,也有人设想粒子由波组成的波包等模型。但这些模型都因与实验事实不符而被否定。从逻辑上说,企图用从宏观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模型去套微观体系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要明确,我们仅仅是借用了经典物理学的“微粒性”和“波动性”概念(确切地说,是重复使用了这两个“术语”),然而,却与经典意义下该两个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所说的波动性,指的仅仅是客体在某些条件下会表现出干涉、衍射等相干性这些体现波动性的现象,而并不是说它是实在的物理量在空间的传播。我们所说的粒子性,指的是客体在与物质相互作用时是整体集中出现的,但并不存在轨道。“轨道”,对于经典物理学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在微观领域,却不能使用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观察到任何微观客体的运动轨道。换句话说,微观客体的运动不存在轨道。
(二)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反映的是客体内存在着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导致其行为的不确定性
海森伯以其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化了这种不确定性,即一对共轭力学量具有不确定度关系。其数学表达式为:
pq≥h/2
其中p、q分别为广义动量和广义位置。
这种模糊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摈弃了电子、光子等微观粒子在空间沿特定路径或轨道运动的直观概念。对于遵循一确定轨道运动的一个粒子来说,每一时刻它都必定具有一个位置(路径上的一点)和一个速度(路径的切矢量),但是一个微观粒子不可能同时具有二者。著名的托马斯・杨双缝实验最有代表性地显示了量子的模糊性。
(三)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理解“波粒二象性”
或许有人要问,电子“实际”是什么?光子“实际”是什么?这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至少,当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时,物理学家不可能给予回答,甚至量子力学的先驱者波尔也说过:“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例如,关于电子,我们常常谈论的是它的质量、电荷、自旋以及当它处于原子中时的分布情况(分布概率)等。如果确实要回答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比其他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微观客体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物质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我们认定“波动性”和“粒子性”是一对矛盾,或者说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话,那么,它们“既是波,又是粒子”“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它们是“波”和“粒子”的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是存在于客体之中的,是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波”和“粒子”,既不是经典概念中的“波”,也不是经典概念中的“粒子”。
甚至,按照哥本哈根的观点,“一个原子、电子,或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说是以其名词的完全与常规的意义而‘存在’的”。“由于‘原子’的概念从来就是只在对它实行观察的实践中才会碰到,所以,人们可以坚持认为:物理学家所必须关注的只是一致地关联各种观察结果”在经典物理学中,能量是一个纯抽象的量,只是以简单的方式将力学过程中各种观察联系在一起的一组数学关系中的一部分,于是,“像电子、光子或原子这些词,应该按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即它们是一些在我们想象中将实际上只是一组关联各种观察的数学关系固定起来的模型”。
最后,作者认为,对微观体系的波粒二象性这一本质属性应该给予如下全面、准确的表述:微观体系具有波粒二象性;在某些情况下波动特性表现明显,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微粒特性表现明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