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传故事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白蛇传故事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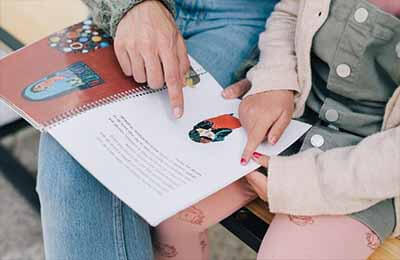
第1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从头说,《白蛇传》与镇江的渊源
人物,法海、白素贞、许仙等人名有案可查。
翻开《新编金山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唐代宗时,有位高僧叫灵坦,来到金山,就山洞(白龙洞)里参禅打坐,降伏毒龙,蟒蛇避走,毒气全消。”而灵坦是何许人也?灵坦,姓武,山西文水人,是武则天的侄孙。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来到金山,相传为金山开山第一代沙门。可见此人来头不小,佛法也了得。而白龙洞至今仍存,就在金山脚下东北侧,传言深不可测,直通西湖断桥。有趣的是我们在洞壁上还可以看到“此洞直通杭州西湖”八个字。洞口有一组白娘子与小青的塑像。再翻,该志还有一段记载:“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丞相裴休,笃信佛教。休作文送子出家,取名法海,行头陀行(故人称裴头陀)。”相同的说法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也可看到:“头陀……来润州金山,重兴殿宇。北岩有蟒,头陀入洞禅观,蟒遂去。得金数镒,助修建。寺成,竟莫知所之。”
为患,后有神僧以袈裟镇之始息。“再有就是《白蛇传》中“合钵”惨剧在金山的传说中似也遗有痕迹。”《金山志》载:“往有高僧呼龙曰:‘汝能现身乎?’龙即现一头如山。”“僧曰:‘汝能大,却不能小,能人吾钵中乎?’龙即入钵内。”僧曰:‘汝能出乎?’龙百伎莫能出”等等。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
“实名制”,《白蛇传》里对应的镇江地名。
以冯梦龙编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如“针子桥”,查《至顺镇江志》:“嘉泰桥,在市东紫金坊。宋嘉泰年间(公元1201-1204年)造,故名。俗呼针子桥。”该志又说:“紫金坊……以紫金泉得名”。而紫金泉就在今大市口附近,遗址保存完好。再如“五条巷”,即今天中山东路上的五条街,当年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街。又如“镇江渡江马头”,据学者考证就是西津渡,许仙和白娘子还在这里开了爿“保和堂”药店。至于“金山寺”就更不必说了。这不奇怪,《警世通言》的作者冯梦龙,明崇祯年间曾做过丹徒县儒学训导和教谕数年,相信他对镇江的风土人情应该了如指掌,创作起来定是信手拈来,得心应手。
传后世,催生形式多样的艺术之花
漂远流长,主题升华
《白蛇传》是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家喻户晓,流传久远,保留有古代图腾、神话和民俗信仰的痕迹,经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白蛇记》、南宋民间曲艺《雷峰塔》和宋、元时期的话本《西湖三塔记》等的再创作,并结合在江苏,浙江及四川民间广为流传的地方风物传说,渐成较完整的故事结构。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等均有相关记载,到冯梦龙编写《警世通言》方基本定型。后再经说书、戏曲,弹词等艺人的进一步演绎,到清黄图作《雷峰塔传奇》,才始有白娘子与法海打斗的简单情节,30年后,方成培改编了《雷峰塔传奇》,突破性地增加了“端阳”、“求草”、“水斗”、“断桥”和“祭塔”等内容,才使故事情节趋子完善。
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赵清阁还先后写出了通俗小说《白蛇传》。剧作大家“磨了它十二三年”,终于将《白蛇传》改编成京剧剧本。2006年镇江白蛇传传说又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让人欣慰的是,2007年6月,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收集整理出版了一套《白蛇传文化集粹》,分“论文卷”、“异文卷”和“工艺卷”三本,共收录230多篇文章,84万多字,另有图片近100幅,是建国以来50年间白蛇传研究之集大成者。千余年来,随着《白蛇传》故事情节的日渐演变,其主题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从原先人妖斗法、宣扬因果报应的旧主题,逐渐升华为自主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新思想。
形式丰富,影响深广
第2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关键词:互文性 文本 背景 读者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2)05-0095-02
作者简介:刘雪梅(1968―),女,北京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语文组教师。研究方向:阅读与写作。
刘以鬯是香港德高望重的多产作家,作品以反传统现实主义而著称,而尤以首创中国意识流的长篇小说为其突出成就。《蛇》笔者读了多遍,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意图,笔者还读了几部同题材的小说或文章,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赵清阁的《白蛇传》等。笔者发现,只有与传统的《白蛇传》进行互文阅读,《蛇》的意义才会凸显。
“互文性”的概念是由法国解构主义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在日常的阅读和教学中,我们总是会清楚地感知到“我们正在阅读的文本与以往阅读的某个文本的关联”。即“互文性”概念强调的“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
真正使“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获得应有地位的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中指出:“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本文将围绕这一理论,从《蛇》同其他文本以及同当时社会背景的互文性,读者的“互文性”三个方面对该小说进行“互文性”解读。
一、《蛇》与《白蛇传》的“互文性”
《蛇》取材于《白蛇传》,但又不同于《白蛇传》。笔者认为刘以鬯以“蛇”为小说题目的意图,就是让读者在第一时间内就联想到《白蛇传》,这样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主动调动自己有关《白蛇传》的储备,或展开联想补充小说中缺失的情节,或仔细对比、深入思考小说中相异的部分,从而达到解构小说、理解小说现实意义的目的。
小说《蛇》共分九个章节,在情节设置上基本沿袭了《白蛇传》前半部分的情节,即许仙与白素贞在西湖同舟避雨,既而结为夫妻,之后许仙开药铺,后来,许仙遇到法海,法海告之白素贞乃千年蛇妖所变,许仙疑心渐重,端午节劝白素贞饮下了雄黄酒。除此之外,作者还穿插了白素贞到昆仑山盗取仙草救活许仙这一情节,只不过将它由现实改写成了许仙的梦境。
《蛇》与《白蛇传》的情节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安排在形式上形成了互文关系。虽然《蛇》采用的是片段法结构文章,串连整个故事,而且在交代故事情节时用的都是极俭省的语言,甚至是一句话,或一个细节描写就交代了《白蛇传》中繁复的故事情节,但正因它根植于《白蛇传》,部分内容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所以读者就可以自然地将已有的阅读储备调动起来,填补作者有意而为之的缺漏,使它们完整丰富甚至是立体化。这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也是文本“互文性”特点给予作者和读者双方的好处。
“互文性”虽然强调“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互文”,但是也强调“任何一个文本又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合”。《蛇》实际上是借用了《白蛇传》中的部分故事情节,但是在表现其真正的主题情节或人物安排上却完全不同。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虽然都是善良、妍媚、体贴、细心的白娘子,但是前者是千年蛇妖贪恋人间爱情幻化成人的异物,而后者却是普普通通的弱女子,是真正的人,这就由《白蛇传》中的“人妖恋”变成了《蛇》中的“人人恋”,性质完全变了,这就为新小说的新主题奠定了第一层基础。其次,男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也有所不同,《蛇》中的许仙是个颠覆版的许仙,他自私、多疑,尤其是幼年时的一次经历,让他产生了终生的心理障碍。小说中说他“十一岁时因被白蛇所伤,从此,见到粗麻绳或长布带之类的东西,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小说中还有多处具体描写他的多疑,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的心理恐惧症。《蛇》中所加入的新细节将人性的自私、多疑、焦虑完全凸现出来。通过两篇小说的“互文性”解构,读者对“心魔,其实比真魔更可怕”的认识就更深刻了。
二、《蛇》与当时社会背景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中的文本并不单指文学文本或文字文本,同时还包括外部现实。根据德里达的观点,“文本”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哲学文本、神学文本,还涉及所有蕴涵文化意味的文本,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文本。《蛇》不仅与《白蛇传》有互文关系,同时也映射出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现实。
刘以鬯1948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以写作为生。1951年任香港《星岛周报》编辑及《西点》杂志主编。长期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工作。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正面临战后的经济萧条和生存忧患,一方面是身为殖民地大都市的华洋杂陈,与内地文化的隔绝;另一方面是“美元政治”“绿背文化”的绝对控制,文学的政治色彩和商业气息日渐浓厚,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现实和膨胀的物欲对人的挤压,加深了港人的生存困惑。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末期,香港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港人的生存压力逐渐加重,恐惧、惶惑、苦闷、焦虑、失落和无所归依成为了当时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
《蛇》发表于1978年8月,许仙挥之不去的焦虑紧张,不相信真挚的爱情,正是那个时代给港人留下的精神烙印。
许仙已经不是那个《白蛇传》中令人同情的、软弱的、心中有爱、眼中有情的许仙了,而是被生活中的创伤打压后,又被各种不明确的信息挤压着的,无法摆脱也无力摆脱负面情绪的港人的形象。
三、读者与文本的“互文性”
在“互文性”中,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对文本的重写。在“互文性”中,作者已死,代之的是读者的再生。读者将作者笔下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景一物,无限地放大、拉长,在想象中玩味文字,在思考中打量主题,得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体验。
《蛇》的最后一章写道:“许仙走去金山寺,找法海和尚。知客僧说:‘法海方丈已于上月圆寂。’许仙说:‘前日还在街上遇见他。’知客僧说:‘你遇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和尚。’”这飘忽不定的结局,加上一个疑虑重重,无法走出“心魔”的许仙,不禁带给读者一身冷汗,故事的结局注定不会美好。
小说虽然收尾了,但是由于作者写作技巧的高明,给读者留下了无数的想象空间。虽然心里是失落的、压抑的,也许还会长叹数声,但是那种参与创作的,那种纠结后的思考也永久地留了下来,这就是读者通过“互文性”凸显的《蛇》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房广莹.李碧华小说《青蛇》的互文性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4).
第3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镇江市。水漫金山的故事发生在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长江南岸的金山寺,出自于《白雪遗音·马头调·雷峰塔》。水漫金山的故事取材于我国著名的神话传说《白蛇传》。
《水漫金山》取材于我国四大神话传说之一的《白蛇传》,讲述了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这次以青蛇为主角,以青蛇的成长为主线,又演绎了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说,给人不一样的惊喜。
(来源:文章屋网 )
第4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星期一
昨日赏花,让我意犹未尽,望着袋中的梅花瓣,让我更十分期待今天的美景。
寒冷的天气,让我不禁打了几个哆嗦,但导游却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各位游客,冬天的杭州值得一看的东西还是挺多的,还记得《白蛇传》吗?现在我们就去看看这《白蛇传》中的断桥,瞧,我们到了。”
走下车,眼前有一片树林,“秋风扫落叶”让这些在秋天就落了叶子,但是现在一看。光秃秃的树枝,在几日白雪的“洗礼”之下,枝头结上了一层霜,洁白的霜晶莹透亮,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步行在小道上转了个弯便看到了一座桥,想必那就是白娘娘与许仙初遇的断桥了。可是白雪的覆盖,却让断桥上、下积满了雪,我不由觉得不能看到断桥的“庐山真面目”感到遗憾。但这时导游却拿起小喇叭大声说道:“各位游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杭州十大景之一的‘断桥残雪’。白雪给断桥换上了新面孔……”导游正绘声绘色地介绍着,其他游客也正听着入迷,而我一听是杭州十大景,便一股脑地奔向断桥。只可惜跑的太急了,脚一滑,差点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还好我及时“刹车”
第5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1、任嘉伦和杨紫合作的电视剧一共三部,分别是《天乩之白蛇传说》、《龙珠传奇之无间道》、《诛仙青云志》。
2、《天乩之白蛇传说》是由尹涛、刘国辉执导,杨紫、任嘉伦、茅子俊、李曼领衔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该剧由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改编而成,讲述了小白蛇白夭夭与药师宫宫上许宣前世今生、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
3、《龙珠传奇之无间道》是天意影视、悦视传媒出品的古装言情剧,由朱少杰、周远舟导演,杨紫、秦俊杰、任嘉伦 、舒畅、茅子俊、斯琴高娃、韩承羽、刘学义、孙蔚等主演。该剧讲述明朝公主李易欢偶遇微服私访的康熙,两人历经相知相许,但最终难敌家国仇恨的阻挡,决定相记于心相忘于世的故事。
4、《青云志》是根据萧鼎小说《诛仙》改编的古装仙侠剧,由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朱锐斌、刘国辉、周远舟、朱少杰执导,李易峰、赵丽颖、杨紫、舒畅等特别出演。该剧讲述了草庙村少年张小凡投身青云门下,与鬼王之女碧瑶、好友林惊羽,以及陆雪琪、曾书书等少年们一道,帮助良善,斩妖除恶,最终挫败鬼王阴谋的故事。
(来源:文章屋网 )
第6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1、电视剧《天乩之白蛇传说》的人物,白夭夭师从骊山圣母,初化人形之时与上仙紫宣相爱,得名白夭夭,后来紫宣为救白夭夭魂飞魄散。历经千年白夭夭重遇紫宣转世和许宣展开一段人与妖的虐心之恋师从骊山圣母,初化人形之时与上仙紫宣相爱,得名白夭夭,后来紫宣为救白夭夭魂飞魄散。历经千年白夭夭重遇紫宣转世和许宣展开一段人与妖的虐心之恋。
2、该剧由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改编而成,讲述了小白蛇白夭夭与药师宫宫上许宣前世今生、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第一部是布鲁塞尔皇家莫奈剧院新版亨德尔的《赛魅丽》。它以惊艳之姿亮相,无论是舞台创意和视觉效果,都令人耳目一新,更不必说它拥有的歌手好得几近奢侈。最高的敬意当然毫不吝啬地献给将《赛魅丽》演唱得活灵活现的韩国女高音徐艺俐。欣赏她的歌喉需要一点耐心与安静,但正是她夸张但不离谱的放松而妙趣横生的表演,才使得自始至终填满舞台的中国寺庙的斜顶与廊柱完全融于剧情,那些怪模怪样的比丘或比丘尼也不再显得隔膜。到了最后一幕,再看这栋来自安徽某地明朝年间的顶梁框架,简直要高呼此乃“神来之笔”了。
我还要把敬意献给指挥皮尔斯・马克西姆和中国爱乐乐团。我首先感到兴奋的是中国的乐团在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第一部巴洛克歌剧伴奏时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修养,年轻乐手们的才华和领悟力越到最后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真的让人感觉到对某些限度的突破。当然,成就这样一部亨德尔的名为清唱剧实为歌剧的制作,合唱队的水平至关重要。英国之声合唱团不仅在声音上维持了和全剧相匹配的高水准,而且在表演上也十分“搏出位”。
在令人开怀而轻松的亨德尔之后,观赏周龙作曲的《白蛇传》则显得有点累,这“累”不是源于对传统故事的颠覆,也并非不习惯导演理念和舞台实景与心理预期的错位。周龙的音乐还是用力过猛,包含的元素太多太杂,几乎令人耳不暇接。周龙写得累,我们听了更累。这种歌剧写法不仅属于资源浪费,也给演唱者和观戏者带来负担。颇感意外的是,周龙第一次做歌剧,居然就摊上一个非常好的剧本,不仅主题情怀充沛新颖,更难得戏剧结构平衡精当,而且剧词写得意境迷离,可以说完全达到民间传说“歌剧化”的升华高度。
《白蛇传》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和美国波士顿歌剧院共同委约的英文歌剧,但我仍愿意把它当做“中国歌剧”。当听到一句中国人简单的询问语被用英语唱出时,不禁哑然失笑。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不管是中国歌剧还是其他不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歌剧,以为用英语演唱就可以国际化、世界化,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当歌剧的黄金年代已在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和德国歌剧之外诞生了匈牙利、捷克、俄罗斯、波兰、西班牙等成功的民族主义歌剧时,英国以布里顿、蒂佩特、沃尔顿为代表的英语歌剧也在普赛尔和亨德尔之后再次崛起。中国歌剧创作便没有必要通过走英语之路而实现其国际化,它即使以西方舞台为表演重心,也只能用中文演唱,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中国歌剧风格。
说到用中文演唱中国歌剧,便到了“清算”作为国际音乐节闭幕式的歌剧《咏・别》剧本的时刻。首先,我向叶小纲无可替代的音乐灵性和色彩绚丽、技术精湛的管弦乐配器致以敬礼。如果这部刚刚“首演”的歌剧还有继续往前走的价值,我建议像瓦格纳歌剧经常被冠以“无词的×剧”那样,直接就做一个音乐会版的“无词的《咏・别》”。歌剧首先是戏剧,其次是“歌”。“歌”是什么?“歌”是“诗”。可是我们看看《咏・别》有哪怕是一点点的诗意吗?它有戏剧的尺度吗?有戏剧创作的逻辑性吗?有起码说得过去的戏剧结构吗?
巧合的是,《咏・别》也和《白蛇传》一样分“春夏秋冬”四幕。在《白蛇传》是与四季轮回、起承转合的中国叙事传统契合,而在《咏・别》则是取巧不成反添乱。本来因一部新戏的创作与排演而引发三角恋情的叙事内核具有一定张力,可以放在一个短促的时空内完成,却硬是拖拖拉拉地历经四季风雨,还跨到来年冬天。
第8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从小,我便对《白蛇传》无限喜爱,爱那刻骨铭心,爱那难分难舍,爱那明知结局却仍要尝试的抗争。自然,我也爱上了断桥,爱上了西湖美景。
六月的西湖,阴雨绵绵。白素贞与许仙在断桥上不期而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断桥借伞、断桥相会……浪漫如是。桥,真是个浪漫的地方。
爱情是浪漫的,浪漫到让人无法抗拒。可是,爱情,对白素贞来说,只是一场意外,一场美丽的意外。成仙路上遇到他,一把雨伞,让白素贞明白什么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最终让她许下“做人不做仙”的誓言。
断桥一见,让白素贞情根深种。终于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灰飞烟灭。
只是有时候,却是不懂的。白素贞对许仙的爱到底有多深,竟然能使她从成仙之路折回,走向那无尽的深渊。甘愿让雷峰塔,成为她的最终归宿。
她误了自己,也误了许仙。
可那又如何?毕竟白素贞无悔!许仙亦无悔!
可还曾记得断桥上的真情?“只羡鸳鸯不羡仙”,白素贞如是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许仙如是说。囚着白素贞的雷峰塔倒了,可见证爱情的断桥却依然未断——真情仍在,海誓山盟依旧!
第9篇:白蛇传故事范文
曹雪芹《红楼梦》
元春端午给宝玉赠扇在《红楼梦》中,端午节被正式描写的细节很少,只是在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提到过“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王夫人等也置酒席庆祝,同时在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中”提到节前的那天“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顽耍”。在其中对于端午节俗所提甚少,对于粽子只是用黛玉的一句话“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一笔带过。不过,对于“端午赠扇”的习俗,小说中倒是描写较多。《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贾元春“端午儿”前给亲人们“赏节礼”,给宝玉的便有扇子。
■教您一招端午结婚可赠扇给父母相传唐太宗曾于端午日送绢扇两把给他的“爱卿”长孙无忌和杨师道,上有他的“飞白书”亲笔题词。宋代人把“花巧画扇”列为“端午节物”(《东京梦华录》卷八)。至今,甘肃等地过端午仍保留着“蒸面扇”之俗;在福建,儿媳妇要送扇给公婆;浙江一些地区,学生给老师送粽子、馒头,作为还礼,老师以扇子回赠,故那里的端午又名“敬师节”。如果新婚夫妇在端午给老人家送扇子,不仅寓意驱赶蚊蝇,祈福、避邪赈灾,还能扇凉。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
充满“江苏味”的端午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中国味”,这篇《端午的鸭蛋》则充满了“江苏味儿”。“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着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除了怀念着名的“高邮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抹王字”、“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送符送扇”、“端午要吃十二红”等习俗均在文中有所提及: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
■教您一招用鸭蛋壳做“萤火虫灯”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汪老还不忘教大家DIY一下鸭蛋壳。不过现在南京市区已经抓不到萤火虫了,但聪明的孩子们,用荧光粉等可以在夜晚发光的物件来代替萤火虫,同样可以做出漂亮的“萤火虫灯”。
沈从文《边城》
在世外桃源赛龙舟捉鸭子其实,《边城》中虽有着小桥流水的清雅美,但不足以引人入胜。它最美得动人心魄的,是里面的风俗人情。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风景秀丽的一个湘西小镇——凤凰。
从一开始,沈从文就描写了边城端午节的热闹场面,继而补写了两年前端午节翠翠见到傩送的情景。端午节那天,所有的人围到岸边,早早地观看;而年轻小伙则在鼓声的节拍中向前奋划,四周一片吆喝助威……而龙舟竞赛的方式和捉鸭子的可爱场面,也不禁令人浮想联翩了。这便是湘西人民的独特的端午风俗了;所有的戍军长官也一起与民同乐,早早地围在税关前看热闹,并派遣士兵将大鸭子缚上红条放入水中,一起嬉戏。
边城在沈从文的笔下,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人间每天都在发生悲欢离合,这和时代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但撇开那些令人伤心的悲剧去看里面的每个人、每个风景、每个生活片断,去看端午赛龙舟,你会惊异地发现,沈从文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多么美丽的世外桃源。
吊脚楼最适合看龙舟“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很多人就是看了《边城》,又中了沈老这句话的毒,千里迢迢前往边城,只为在端午赛龙舟时,邂逅一个同样美丽的女子。
按照《边城》里的描述,临江的吊脚楼便是每年端午时分观看龙舟赛的最好位置。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的凤凰山,近处的虹桥,脚下的沱江,江上的观光船和对岸的繁华。只不过临江的吊脚楼可能会比不临江的住所价格要高些。
宋元话本《白蛇传》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