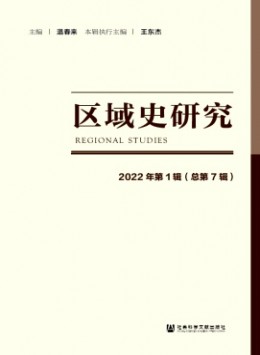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区别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区别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区别范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 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 。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 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 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 。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 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 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 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 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 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 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 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 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 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 )。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 ;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 ,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 [,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 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 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 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 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 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 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 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 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 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 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 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2篇: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区别范文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 旧区域主义 理论化 核心特征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58-64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欧洲再度引领的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区域主义研究回归到国际关系理论前沿。国际关系学界将之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并开始对之进行深入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研究。随着区域主义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兴起,“新区域主义”也进入我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然而,国内学者对“新区域主义”的探讨主要是从经验上或理论上、从国际政治学或国际经济学等视角分开研究;少量综合研究也局限于理论或个案,明显缺乏系统的、多学科的、经验与理论结合的综合性分析。所以,这些研究尚未真正反映出“新区域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所拥有的实际内涵,以至有学者对是否存在“新区域主义”提出质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揭示“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以期厘清国内学术界对之尚存的片面、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
一、“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的经验判断
目前,在国际关系学界,谈到“新区域主义”首先指的是区域主义实践的“新浪潮”,以区别于冷战背景下的“旧区域主义”。用诺曼•帕尔默的话说:“新区域主义不单单是旧区域主义的复兴,它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新因素。”[1] 然而,“新区域主义”的“新”还不仅限于此。它还明显地表现在理论层面的创新上。正如弗雷德里克•索德尔伯姆所言:“‘新区域主义’的‘新’主要是经验上的和理论上的,”它“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新的框架并有新的内容的新现象。”[2]
从经验上看,“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冷战背景下的“旧区域主义”通常表现为区域政府间组织,并以单一纬度的经济、政治或安全组织的形式出现。前者主要有西欧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洲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发展中国家间各种优惠贸易安排等;后者主要有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约、华约、欧洲安全会议等。尽管那些区域经济组织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安全目标,但其手段和性质是经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政府组织企图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但收效甚微,实质上只是一个政治或安全组织。例如,冷战时期的东盟,尽管它一开始被设想为一个追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的组织,实质上它是一个旨在预防战争和解决冲突的“外交共同体”。[3] 然而,“新区域主义”明显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一方面,一些原来功能单一的区域政府组织开始朝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纬度多议题的方向发展,并日益成为解决区域综合性问题的一支最重要力量。例如,欧共体过度到欧盟,并开始推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共同的社会与文化政策;东盟开始启动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始积极加入“新区域主义”的实践之中。以东南亚为例,90年代以来,在东盟框架外,各种“自然经济区”(又称 “增长三角”)迅速发展起来了。它们代表着一种“市场驱动的”、自发的、跨国的“微区域主义”,已被认为是东南亚宏观的区域主义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一种途径。东盟第4届首脑会议认定:“成员国之间或东盟成员国与非东盟国家之间的微区域经济合作安排,能够作为东盟总的经济合作的补充。”[4] 以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为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所发起的区域层面的会议(包括双边和多边会议),已形成推动东盟官方地区主义的“第二轨道”对话与协商机制。这一机制“给东盟增添了另一种成分,即从建立在国家组织需求之上的现代社会实体转变为在成员之间具有感情或精神纽带的‘组织化’实体。”[5]
二是区域间性。与“旧区域主义”基本上局限于一个既定的地理区域内不同,“新区域主义”开始出现一种超越传统地理范围的、以多层次区域间关系为特征的、跨大陆或大洋的“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它主要有3种形式,即区域集团间的关系、跨区域的安排以及区域集团与单个国家之间的混合安排等。典型的例子有:关系相对松散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欧亚会议(ASEM)、欧洲-拉美首脑会议、东南亚-拉美论坛(EALAF)以及关系相对紧密的欧洲-地中海国家间“伙伴关系动议”(即“巴塞罗那进程”)、欧盟-非加太国家集团间“伙伴关系协定”(即《科托努协定》)、欧盟与墨西哥、智利、南非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尚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拉美自由贸易区”等计划。[6] 与其他区域主义相比,这些“区域间主义”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以《科托努协定》为例。该协定确定:欧盟-非加太“新伙伴关系”有5根支柱,即政治对话、广泛参与、发展战略、经济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等,并明确规定:以通过一体化和发展消除贫困和边缘化作为基本宗旨;将经济贸易合作置于发展战略的框架之内;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在内的区域一体化作为实现其发展战略的具体工具;双方合作的角色包括政府角色(含地方、国家和区域政府)和非政府角色(包括私人部门、经济和社会组织等)。[7] 更重要的是,“区域间主义”大大超越了“旧区域主义”囿于发达国家之间(北北型)或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型)局面,而创造了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紧密合作的新型的区域主义模式(南北型),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三是开放性。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领域,“旧区域主义”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封闭的特征。前者主要表现为欧共体实施的共同关税政策、经互会内部的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战略与关贸总协定(GATT)多边贸易规则的矛盾性;后者主要表现为北约、华约和东南亚集体条约组织等对峙的军事联盟的存在。而“新区域主义”则显示出突出的“开放性”特征。经济方面,区域一体化进程开始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机制趋向一致。比如,“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 ”计划已明确规定该自由贸易区应尊重GATT谈判成果并依照有关协定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有关条款也都明确写进了欧盟-地中海协定和地中海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协定。欧盟也非常强调所有伙伴国家都成为WTO成员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地中海伙伴国家加入WTO当作推动该区域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
安全方面,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开放型的区域安全机制――“合作安全”。这是“一种广泛的合作取向,它在范围上是多维的,在性情上是渐进的;强调确保而非威慑;是包容的而非排斥的;在成员上没有限制;喜好多边主义胜于双边主义;在军事解决办法与非军事解决办法之间并非偏爱前者;认为国家是安全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也接受非国家行为者扮演重要角色;不要求但也不拒绝创立正式的制度。此外,强调在多边基础上形成对话的习惯。”[9] 合作安全机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是,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和国家、政府组织一起参与区域安全合作进程,从而出现一种独特的区域安全合作方式――“研讨会外交”或“第二轨道外交”。[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区域安全机制――欧洲安全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本质上都是“合作安全”机制。“新区域主义”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使之成为“开放的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m)的代名词。
四是主体化。与“旧区域主义”时期区域在国际舞台上被动的客体地位相比,“新区域主义”条件下,一些成熟的区域开始以一个“区域行为体”乃至“全球行为体”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强有力的主体作用。这就是区域作为一种经济或政治实体所具有的“角色性”。这意味着这些区域实体开始对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规则负责、能够制定连续的政策并适时运用政策工具、具有国际谈判能力、拥有决策进程的合法性等。[11] 由欧盟所主导的“区域间主义”便是这种“角色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显著体现。[12] 东盟也由于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10+3”合作机制和新启动的东亚首脑会议中担当至关重要的“推动者”的角色,已被参与各方公认为这些重要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领导者”。[13] 这表明,区域主体已成为推动“新区域主义”纵深发展的主角。所以,“对我们来说,新区域主义意味着该区域努力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政治主体。”[14]
五是趋同化。不像“旧区域主义”明显表现为西欧紧密的一体化(强制度建设)和发展中国家间松散的区域合作(弱制度化)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日益走上趋同化。这种趋同化既表现为它们共同拥有综合性、开放性等特征,还表现在其发展道路的趋向一致。宏观的区域主义多由区域经济一体化驱动,并显示出从创建自由贸易区开始,经由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最后到经济共同体乃至政治共同体的发展轨迹。现实的情况表明,在原已存在松散的区域合作或缺乏实质性区域合作的区域,“自由贸易区”(有时包括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前者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安第斯自由贸易区”、“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等;后者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洲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自由贸易区”建设已成为新兴的各种“区域间主义”的核心支柱和发展先锋,如“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欧盟-非加太互惠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APEC自由贸易区”等。一些区域开始从自由贸易区走向关税同盟或者共同市场,如南非发展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或者从后两者走上经济与货币同盟,如欧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建设开始成为许多区域近期和长期的目标,如“东盟共同体”计划、“东亚共同体”设想;一些区域组织开始用“共同体”来命名,如加勒比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等。[15] 同时,微观的安全区域主义也开始从冷战背景下以权力政治为工具、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均势”、军事联盟等传统的模式,走上“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主导下“合作安全”机制;一些区域开始形成或走向以区域一体化建设为核心保障的“安全共同体”,如欧盟和“东盟安全共同体”计划等。“安全共同体”已成为安全区域主义实践所追求的根本目标。[16] 总之,虽然这些区域主义形态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日益趋向一致的发展轨迹。
二、“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的理论分析
与“新区域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纵深发展相适应,“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成果也是层出不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这场区域主义的“新浪潮”;[17] 新的理论流派也迅速加入到这一研究的行列,从而推动“新区域主义”研究越来越具有明显而独特的理论色彩。[18] 具体而言,从理论上看,“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体系化。在“旧区域主义”时期,虽然理论界已将“区域”当作国际体系的“次体系”,但分析的焦点依然是民族国家,即强调区域内国家间联合和一体化在区域主义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他们“过分强调一体化理论”,而“相对缺乏对日益增加的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影响的考虑。”[19] 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体化理论家厄恩斯特•哈斯也承认,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外部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一个“主要错误”。[20] 同时,他们忽略了国内政治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占主导的一体化理论主要兴趣点是探讨如何实现突出集体决策能力的政治共同体,而“低估了当时许多国家的反多元主义、中心主义和政权建设的倾向。”[21]
“新区域主义”研究与之明显不同,它开始将区域主义置于全球化变革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即“必须在全球视野中去审视区域主义和区域主义者计划的复兴。”[22] 学者们开始采用体系的方法分析“区域主义”的发展和区域体系的变化。体系的方法首先表现在多层次的互动分析。最著名的有戴维•莱克和帕特里克•摩根使用的全球-区域-国内“三层博弈”分析方法、 [23] 比约恩•赫特纳等人采用的全球-区域间-区域-国家-地方“五层互动”分析方法[24] 和巴里•布赞等人采用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四层互动”模式。[25] 这种多层次互动分析不但提供了将区域内国家内部因素、单元间关系、区域间关系、区域动力与全球体互动等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区域主义和区域体系的变化既可以是自下而上(或由内及外)也可以是自上而下(或由外及里)的进程。体系的方法还表现在“新区域主义”行为主体的多元互动分析上。其中,最著名的是赫特纳等人提出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观点。他们认为,正是包括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在内的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推动一个有独立权利的区域角色的形成。[26] 所以,“新区域主义”事实上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合理性之间的妥协。[27]
二是社会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对“区域”和“区域主义”等概念的再定义相适应,“新区域主义”理论开始将区域主义和区域化视作一种社会建构的、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最有名的是赫特纳等人提出的“区域性”(regionness)概念和安德鲁•赫里尔提出的“阶段论”。“区域性”是指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从消极的客体向积极的主体转变,并能够将这个兴起中的区域的跨国利益联结起来的进程。它显示出一个特定区域不断发展的多维的区域化进程。“区域性”有5个不同的层次,即“区域空间”(元区域)、“区域复合体”(作为社会体系的区域)、“区域社会”(区域公民社会)、“区域共同体”(一种行为主体)和“区域国家”(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实体)等。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域性”共同构成区域化的自然演进史。[28] 赫里尔的“阶段论”把区域主义观念分为5种依次递进的类型,即区域化、区域意识与认同、区域国家间合作、国家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内聚体等。[29]
这些观点表明,区域主义呈现出从松散的“区域合作”到紧密的“区域一体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这就是区域主义的社会化进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本质上是区域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主导的、中心型的国家间合作,是一种“维持现状”模式;后者本质上是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共同体”观念主导的、区域政治实体化的“变革”模式。这正如乔根森•达尔所言,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的各个部分,一旦合作进程穿越一个门槛就会转变成为一体化的进程。这个“门槛”就是“由先前依赖于个体国家转向功能和权力的区域实体”。[30]
三是综合化。“新区域主义”理论的“综合化”既表现在区域主义动力的多层次和多元行为主体的互动分析,也表现在它所涉及议题的多纬度互动分析,更表现在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综合”上。在“旧区域主义”时期,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但局限于国家这一单一层次和单一行为主体,而且时常将政治与经济分开进行。约瑟夫•奈指出,当时人们在讨论着两类主要的区域主义活动:一方面是包括正式经济一体化的微观经济组织,另一方面是用以控制冲突的宏观的区域政治组织。[31] 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当时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主要以卡尔•多伊奇为代表的“交流主义”和厄恩斯特•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构成的、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一派是斯坦利•霍夫曼为代表的“政府间主义”构成的现实主义。他们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就欧洲一体化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32] 与之不同的是,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学者开始将区域主义视作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社会、文化等多个纬度的实践。赫特纳强调,在“新区域主义”时期,区域化进程表明从一种涉及不同纬度的相对异质性到不断增加的同质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安全、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这些纬度的变化成为区域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33] 布赞等人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5个领域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也就是说,各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每个领域仅仅被看作整体的一个纬度。[34]
在大理论上,“新区域主义”研究显示出日益深化的“综合化”趋势。首先是理性主义框架内的“综合”。主要成果是安德鲁•穆拉维斯克所代表的“自由政府间主义”。他在吸收国家偏好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讨价还价的政府间主义理论和强调可信的责任重要性的制度主义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于欧洲一体化的“三种组合框架”,即将一体化进程解释成国家偏好形成、国家间谈判和制度选择三个阶段。[35] 其次是反思主义框架内的“综合”。主要成果是赫特纳等人提出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他们将社会建构主义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的全球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并融入发展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内容,强调对“区域主义”的多层次、多元行为主体和多纬度分析以及区域化进程的社会建构。[36] 这样,“新区域主义方法”就“超越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和理论上的过分简约,而走上一种更综合的社会科学。”[37] 最后是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折中方法”下的“综合”。主要成果是赫里尔提出的“阶段论”。他强调,必须探索当代区域主义中不同逻辑之间互动的本质,即将物质刺激与主体间结构、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国家间合作与国内政治联合、国家与社会等新区域主义所依赖的互动形式概念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尤其是强有力的霸权)开始,经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利益与偏好),最后到建构主义(强调区域认同和共同体)来研究新区域主义的不同发展进程。[38] 这种方法就形成一种类似于亚历山大•温特等人所描述的、以物质主义(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底端、以社会学观点(包括建构主义、批判理论)为顶端的 “理论连续统一体”。[39]
四是秩序化。与“旧区域主义”研究孤立于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局限于实现福利、安全等目标有所不同,“新区域主义”研究承认区域主义(区域化)与全球化(全球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共存于同一进程之中,认为区域主义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持续的现实回应力量,它不但可以在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搭起一座互通“桥梁”,而且可以成为走上区域化的世界新秩序的有潜力的途径。[40] 赫特纳指出,“新区域主义”就是要通过良性的区域主义消除非对称的和极化的区域间结构性鸿沟,以创建一个平等的后霸权世界新秩序。主要由欧盟推动的“区域间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重要的努力。这种区域化世界秩序是一种挑战美国单边主义的“多中心”的世界秩序,是“我们所能够预期的最好的世界秩序。”[41] 所以,“新区域主义”理论“不能仅仅涉及兴起的区域本身,它必须是一种关于变革中的世界秩序和多层次治理模式的理论。”[42] 阿米塔夫•阿查亚强调,如果撇开“新区域主义”而“讨论21世纪之初兴起中的世界秩序就是不完整的。”[43]
三、小结
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已经彰显:经验上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和趋同化等;理论上表现为体系化、社会化、综合化和秩序化等。它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重要回应,是民族国家和其他行为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新区域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
注释:
[1]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1, pp. 1-19.
[2]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the New Regionalism”, paper for the XIII Nordic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Aalbog, 15-17 August 2002, pp. 3, 13.
[3] Michael Leifer,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2-6, 52-88.
[4] 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hancing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gapore, 27-28 January 1992, 省略
[5] Jusuf Wanandi, “The Future of ARF and CSCAP in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Jusuf Wanandi ed., Asian Pacific After the Cold War, Jar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p.231.
[6] 参见Heiner Hänggi et al.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7] 参见EC, The Cotonou Agreement, ec.europa.eu/development/ICenter/Pdf/agr01_en.pdf
[8] 参见 “The 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s Official Journal L097, 20/03/1998 P.0002-0183; “Survey on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European Commission, DG/BA.4, April, 1999.
[9] Paul M. Evans ed., Studying Asian Pacific Security: The Future of Research Training and Dialogue Activities, Ontario: University of Toroto- York University, 1994, p.38.
[10] 参见Emanuel Adler, “Seeds of Peaceful Change: The OSCE’ s 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8-142; Brian Job, “Track 2 Diplomacy: Idea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ving Asian Security Order”,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41-275.
[11] C. Brethereon and J. Vogler, Europe as a Global Acto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5.
[12] 参见Fredrik Sö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Special Issues: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2005.
[13] Yang Razali Kassim, “Minister: ASEAN will always have Driver’s Seat in Forum”, Business Times, 25 July 1994, p. 3; “首届东亚峰会签署吉隆坡宣言”, news.省略/w/2005-12-14/13347707371s.shtml, 2005年12月14日。
[14] Fu-Kuo Liu and Philippe Rognier,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1.
[15] 参见Robert Devlin and Antoni Estevadeordal, “What’s New i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merica?” INTAL-ITD-STA working paper 6, May 2001; Sheepoon Kim, “East Asian New Regionalism”,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 2003, pp.57-87; Candice Moor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African Initiatives”, Policy: Issues and Actors, vol. 17, No. 3, 2004, pp.1-17.
[16]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6-58.
[17] 参见Edward E.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 参见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2003.
[19]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11.
[20] Ernst B. Haas,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p. 9.
[21] Shaun Breslin, and Richard Higgott, “Studying Regions: Learning from the Old, Constructing the New”,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 335.
[22]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Introduction”, in Louise Fawcett et a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
[23]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19.
[24] 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örn Hettne, Andrάs Innotai 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p.11-16.
[25]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p.72.
[26]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44-45.
[27] Björn Hettne,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World Order: A Regionalism Approach”, in Sheila Page ed., Regions, and Development: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44-45.
[28]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pp.37-45.
[29]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et a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pp. 37-73.
[30] Arnfinn Jorgensen-Dahl,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25.
[31]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32] 参见Karl W. Deutsch and Sidney A. Burrell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1-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elus, vol. 95, No. 2, 1966, pp. 863-882.
[33] 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11-16.
[34]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Björn Hetnne et al.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p.1-25.
[35] 参见Andrew Morava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a to Maastrich,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pp.33-47.省略/conference-2004/paeprs/wunderlich-conceptualisation-regions.pdf
[38]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p. 37-73.
[39]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et al.,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52.
[40] 参见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20-23; Andrew Gamble, and Anthony Payne eds.,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41] 参见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en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3, March 17, 2003.
[42]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p.34.
[43]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Sovereignty, Autonomy, Identity”, in Shaun Breslin et al.,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