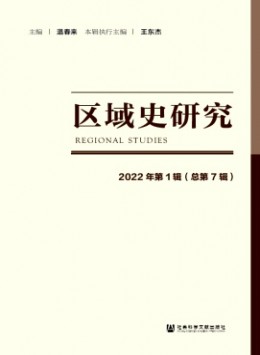微观经济分析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微观经济分析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微观经济分析法范文
1、经济指标分析对比:经济指标是反映经济活动结果的一系列数据和比例关系。
2、计量经济模型:它是表示经济变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授关系。
3、概率预测:它实质上是根据过去和现在来推测未来,广泛搜集经济领域的历史和现时的资料是开展经济预测的基本条件,善于处理和运用资料又是概率预测取得效果的必要手段。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微观经济分析法范文
关键词:危机管理;情境模拟;应用
一、情境模拟教学法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仿真训练方法,它通过创设教学内容所需要的接近实际工作或生活的场景,让学生在这种场景中分别担任不同角色,由教师在一旁进行指导、分析,并作出最后总结。作为一种虚拟实践性教学方法,情境模拟法认为人的主观心态、努力程度以及问题解决的方式会受制于不同的情境作用,因此,让组织者与角色参与者对环境保持动态的适应,对于切实改善学习效果、提高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在人才选拔和课堂教学中广泛应用的情境模拟法, 是在前人雄厚的理论基础上诞生的。认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境认知理论为情境模拟教学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前提出发,认为认识的内容来源于客观世界,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在教学中要遵循认识反映论的原理,根据客观存在对学生主观认识的作用进行情境模拟教学。通过对事件发生与发展的情景、环境、过程的模拟或虚拟再现,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扮演某种角色或进入某种心理状态,并和其中的人或事产生互动,以加深感受、深化认知。而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学习理论则主要是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提出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对人价值的再发现,强调学习者学习知识时主体认识特点的作用,它认为学生的学习不仅是对新知识的理解,而且是对新知识的分析、检验和批判。情境模拟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正是依托建构主义理论实现教学目标设置。①情境认知理论是与建构主义大约同时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它认为,实践不是独立于学习的。而意义也不是与实践和情境脉络相分离的,意义正是在实践和情境脉络中加以协商的。知识是个体与环境作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是一种人类协调一系列行为,去适应动态变化发展的环境的能力。知与行是交互的,知识是情境化的,通过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参与实践就会促进学习和理解。②这些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我们认识到情境在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和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作用,从而启示我们要明确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学习内容的设计要与具体实践相关联,通过虚拟人类具体生活实践的方式来组织教学,并将知识的获得与学习者的发展、身份建构等整合在一起。
二、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危机管理课程中的作用
危机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步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资源、环境、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日益严重,并不时引发出各种公共危机,如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2012年“毒胶囊”事件等。这些公共危机的爆发对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对政府应急体系的构建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应急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
然而,构建全面整合的应急体系、提升危机管理绩效,既离不开理论界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更离不开全社会范围内应急协防知识的普及和对日后从事公共管理的人才的危机管理能力的培养。因此,危机管理课程应以实践为导向,在重点介绍公共危机管理流程、危机决策模式、危机沟通机制、危机管理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分类阐述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控制等内容,并结合国外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的运行状况和经验教训,探讨建立与完善我国危机管理体制的制度措施与政策选择。
为了克服传统的教学模式“重知轻智”、“重灌轻趣”、“重教轻学”的弊端,使学生重点掌握危机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不同类型危机事件的处理方法,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危机观,培养学生的危机管理能力,采取情境模拟教学法对《危机管理》这样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都非常强的课程,有明显的优势:
1、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
现代教学论把学生的发展看作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情感需要为核心的一系列非智力因素,影响并制约着学生的学习与发展。③情境模拟训练着眼于学生求知活动中的情绪体验,满足学生求知过程中的情感需求,强化学生的感性体验在认知中的作用。通过强烈的现场参与感极大地触发和增强了学生危机管理理论思维的兴奋点,并缩短知行距离、促使知行转化,使学生在学习危机管理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得成功的满足和愉悦的情绪体验。
2、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大量的研究证明,只有当学生对正在学习的东西感兴趣,觉得富有挑战性并积极地参与其中时,学生的学习才真正有效。情景模拟教学法通过创设危机情境,进而让学生切实感知危机的突发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并在约束条件下,以管理者的身份做出危机决策、进行危机沟通、形成应急联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所扮演的是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在教师的引导下不仅能够极大地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3、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传统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比较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因而“高分低能”、学生实践能力弱化的现象十分突出。通过采用情境模拟教学法,既拓宽了授课教师的教学思路,也为学生打造了一个应用知识、锻炼技能的平台。在感知危机情境的基础上,学生能有意识地将所学危机管理论运用于对典型公共危机事件的分析中,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相关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
三、情境模拟教学法在危机管理课程中的设计与应用
为了确保情境模拟教学法在危机管理课程中的顺利实施,前提是创设危机情境。危机情境的创设是以危机的生命运动周期为基础的。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为了有效管理危机,学者们全面分析了危机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构建了危机运动的不同模型。其中,芬克(Fink)的四阶段模型、米特罗夫(Mitroff)的五阶段模型和基本的三阶段模型最为广泛接受。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危机的发生与发展简单划分为三阶段:潜伏期、爆发期、恢复期。相应地,危机管理的步骤可以浓缩为预警、应对、善后三步曲。因此,在危机管理课程中,教师可以围绕危机管理的流程创设不同的危机情境,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情境中的决策者、沟通者和执行者,让他们体会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的区别,通过多次模拟对比,使学生直接面对在约束条件下不同管理行为的结果和绩效。另外,学习该课程的学生毕业后可能成为危机管理的主体,但同时他们也极有可能成为公共危机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有必要让学生模拟公共危机的受众,检验学生应对不同危机事件的自救和协防能力。
在具体实施中,情境模拟教学包括以下阶段:
1、教学准备阶段
在准备阶段,教师首先要选择典型危机管理问题,如“毒奶粉”事件、“杭州飙车案”、“汶川大地震”等。并根据所确定主题,细化方案的设计,决定采取分组讨论、角色扮演、辩论等方式来进行情境模拟。对于每一主题进行情境模拟教学所需的条件、设备等,教学方案中应予以明确。其次,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来策划和准备相应场景,在物质条件配备的前提下,把应急决策、应急演练等情景,在课堂或者实验室中模拟出来,让同学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仿真的场景来帮助学生进行角色模拟。最后,教师要根据主题设计角色与分配角色。危机情景模拟的角色主要包括两类:危机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教师可以安排不同的学生扮演政府应急管理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媒体人员、危机受害者,让参与者做出符合角色特点的危机管理行为。
2、教学实施阶段
在实施阶段,学生要在课前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根据情景模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危机事件面临的管理问题做出现状分析和判断,并根据所学危机管理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实施方法。然后,学生根据事先安排的角色身临其境地按危机管理职责、危机管理流程等要求进行演练和操作。模拟结束后,由学生自由发言,就情境模拟中各危机管理参与者和危机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适当性、科学性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可请其他学生进行同一危机情境的再次模拟,通过相互比照,寻找问题冲突,进行深层次追问,从而使角色之间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更为科学。最后,教师要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科学的总结和评价。对于学生的角色扮演情况,教师要围绕主题对他们的语言表达、应变和解决问题等相关表现进行整体评价,也可由教师进行危机情境中相应角色的示范模拟,从而让学生找到不足,并启迪他们学以致用的创新意识。
3、教学总结阶段
在总结阶段,教师要充分听取学生对情景模拟教学法实施效果的建议和意见,不断修正情境模拟实施方案,创新教学方法。同时,将实施效果较好的典型实例进行总结和归纳,作为开展情境模拟教学的经典实例。学生也要在情境模拟教学结束后,总结经验和教训,掌握角色扮演的技巧和要求,以提高教学实效性。相关授课教师也可以在教学研讨活动中进行情景模拟教学法专题研究,针对情境模拟教学法在危机管理课程实施中的困境和难点进行探讨,以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能力。
四、危机管理课程情境模拟教学实例
危机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三大版块:危机及公共危机管理基本理论、公共危机管理实务、公共危机管理的变革与发展。其中,公共危机管理实务的教学内容是根据转型期我国公共危机的特点、性质、机理来分类设计的,包括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事故灾难危机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社会安全事件危机管理。在社会安全事件管理这一章中,选择的情境模拟实例是天津艾滋患者“扎针”事件。在这一案例中,存在多个危机管理参与者,包括市长、警察、医生、卫生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媒体人员、专家等。各参与者在危机管理中的职责、权限、作用是不同的。为了让学生深入把握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尤其是厘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不同职能,可以让学生在教师创设的天津艾滋患者“扎针”事件的情境中,进行角色模拟,身临其境地进行应急决策和应急沟通,以有效处置天津艾滋患者“扎针”事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设计天津艾滋患者“扎针”事件的情境模拟教学方案,确定情境模拟地点,参与人选、创设应急决策和应急沟通情境。
第二步:学生在熟悉案例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所扮演的角色,收集相关材料,结合所学危机管理理论,分析应急决策和应急沟通的方法、程序,尤其是要把握不同主体在危机管理中的职能定位和行为方式。
第三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进行情境模拟,由其他学生发言,就情境模拟中各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分析。也可请其他学生进行应急决策和应急沟通的再次模拟,通过相互比照,寻找修正各主体危机管理行为的总体思路和可操作建议。
第四步:教师对各位同学的在天津艾滋患者“扎针”事件情境中的角色模拟情况进行评价。并对应急决策和应急沟通的基本知识点及其应用进行总结和归纳,将学生的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识。
从实施效果来看,在危机管理课程中应用情景模拟教学法,强化了学生对危机管理理论的认知,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思辨能力。当然,情境模拟教学只是一种尝试,它还存在情境设计单一、教师组织引导能力不足的等问题,有待于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提高和完善。
[注释]
①齐磊.论情境模拟教育[J].学理论,2010(10),221页.
②程守梅,贺彦凤,刘云波.论情境模拟教学法的理论依据[J].成人教育,2011(7),44页.
③吴兆雪.创新思维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理论教学新视野[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5
[参考文献]
[1]胡德海.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李程伟.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2.
[4]戴子刚. 论情景模拟教学[J]. 中国校外教育, 2008(8).
第3篇:微观经济分析法范文
[关键词] 神经外科;重症医学;下呼吸道感染;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8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28-0034-03
颅脑外伤、脑出血等患者病情危重需要进行特殊的重症监护救治,患者生命体征的维持和监护需要实施多种医疗仪器进行无创或有创的治疗操作,患者意识模糊甚至处于昏迷的状态长时间卧床,且机体处于强烈的应激状态,免疫功能紊乱,下呼吸道是重症医学科最常见的医院感染部位,严重的肺部感染极易诱发患者呼吸障碍、全身感染、加重基础疾病和病情,结局不良[1]。本研究对我院重症医学科2009年2月~2013年3月收治的743例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进行分析,探讨影响患者并发下呼吸道感染和预后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降低感染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9年2月~2013年3月在我院重症医学科住院的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743例,男408例,女335例,年龄18~75岁,平均(63.29±10.83)岁,其中颅脑外伤382例,脑出血179例,颅内肿瘤术后82例,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ale,GCS)3~8分,平均(5.93±1.29)分,合并心脏病179例、高血压239例、高血脂159例、糖尿病209例、慢性肺部疾病126例,急诊手术307例,择期手术437例。
1.2调查方法
研究重症医学科住院期间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及预后,分析相关高危因素与下呼吸道感染发生及预后的关系,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年龄、性别、病情、合并症、GCS评分、营养状况[2])、治疗资料(手术类型、气管切开/气管插管/吸痰等侵入性操作、抗菌药物使用种类、激素使用、呼吸机使用)、住院时间、死亡等。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根据预后分为死亡组和对照组。
1.3统计学处理
数据应用SPSS 16.0软件包进行相应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P
2 结果
2.1下呼吸道感染发生情况及预后
73例发生下呼吸道感染,感染发生率为9.83%,经治疗处理好转55例为对照组,死亡18例为死亡组。
2.2下呼吸道感染及死亡单因素分析
年龄、心脏病、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营养状况、侵入性操作、抗菌药物种类、呼吸机使用、住院时间与患者发生下呼吸道感染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下呼吸道感染及死亡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侵入性操作、抗菌药物种类是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
3讨论
重症医学科收治的交通意外、工伤事故、脑血管意外、颅脑肿瘤等导致的颅脑创伤、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患者往往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稳定,机体状况极差,各系统功能出现紊乱或障碍,结局凶险,同时发生医院感染的风险极高,其中下呼吸道感染占比最大,患者并发下呼吸道感染后,加剧身体机能障碍,诱发基础疾病加重,引起多种严重并发症,直接危及患者生命,给危重症患者救治造成严重影响[3-5]。因而,防范下呼吸道感染是重症医学科医院感染控制的重点。本调查结果显示,743例神经外科重症患者73例发生下呼吸道感染,感染发生率为9.83%,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似,其中有18例死亡,说明神经外科危重症并发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预后差,死亡率高。
本研究中老年患者占比例较高,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率也显著高于较年轻患者,且死亡组和对照组比较也有显著性差异,但多因素分析则均不是独立危险因素,说明单纯的高龄并不决定患者并发下呼吸道感染和死亡的风险,而可能与高龄合并多种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更大有关。而合并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在多因素分析中均为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糖尿病对医院感染的风险被普遍认知[6],而既往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下呼吸道基础疾病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低下,对病原菌侵袭抵御能力低,病原菌感染风险极高,并发下呼吸道感染后,原有基础疾病可能诱发加重,从而使病情进展更为迅速,症状表现更严重[7]。心脏病、高血压等也是老年患者常见合并症,但在导致下呼吸道感染发生方面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心脏病在多因素分析结果中为患者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心脏基础疾病被肺部炎症诱发加重,形成多系统疾病的叠加,导致患者死亡[8]。营养状况是重症医学科需要关注的重要状态之一,尤其是神经外科危重患者往往处于昏迷状态,肠内营养难以补充,肠外营养达标也有难度,患者易发生营养不良,进一步降低机体抵抗力,发生感染[9],分析结果显示,营养状态与并发下呼吸道感染有关,但不是独立危险因素,而却对患者死亡起到了独立的影响作用,表明保证患者营养达标是危重症患者救治关键,不仅可降低感染发生,还有助于患者机体功能恢复,改善预后。侵入性操作和多种抗菌药物应用是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10]。呼吸机的使用和长时间住院治疗对并发下呼吸道感染及预后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本研究以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多数患者都需要实施人工机械通气,且住院时间都较长有关。
临床护理则可依据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的相关因素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重点人群为高龄、基础疾病多的患者;护理干预的方式则以患者具备的危险因素对症处理,保证患者营养达标,结合早期肠内营养,恢复患者胃肠道功能,促进身体机能逐步恢复,控制基础疾病,做好吸痰、机械通气调整,严格遵守无菌原则,保持患者皮肤、黏膜、呼吸道、导管等清洁,达到规避危险因素,降低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并发下呼吸道感染风险,改善预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Navoa-Ng JA,Berba R,Galapia A,et al. Device-associated infections rates in adult,pediatric,and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of hospitals in the Philippines:Inter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Consortium(INICC)findings[J].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2011,39(7):548-554.
[2] 宿英英,黄旭升,彭斌. 神经系统疾病肠内营养支持操作规范共识[J].中华神经科杂志,2009,42(11):788-791.
[3] Lili Tao,Bijie Hu,Victor D,et al. Device-associated infection rates in 398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Shanghai,China:Inter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Consortium(INICC) finding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2011,15(11):774-780.
[4] 沈雅舰,胡银燕,刘俏俊. 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呼吸道感染的预防及护理[J]. 中国临床保健杂志,2013,16(1):89-90.
[5] 耳思远,李卓杰. 早期气管切开对重型颅脑损伤并发肺部感染的防治作用[J]. 医学综述,2013,19(2):377-378.
[6] 郭魁,赵云龙,董全勇. 神经外科重症昏迷病人肺部感染的防治[J]. 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13,(1):42-44.
[7] 王鹏,王春生,齐震. 开颅术后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J]. 中国医药导刊,2013,(2):242-243.
[8] 温雅婷,沙丽艳,贾岩竹. 开颅术后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J].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2013,12(2):185-186.
[9] Helder OK,Brug J,Looman CW. The impact of an education program on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 incidence in an urba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n intervention study with before and after comparis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2010,47(10):1245-1252.
第4篇:微观经济分析法范文
【关键词】 微血管减压术; 发热; 颅内感染; 原因
Th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at the Patients of Postoperative Fever that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of the Trigeminal Nerve/SUN Yan-chun,LI Ping,ZHAO Chang-di,et al.//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6,13(20):135-139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of postoperative fever of the patients that was implemented of trigeminal neuralgia,hemifacial spasm and glossopharyngeal neuralgia,and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Method:All of cases in our department nearly five years that the trigeminal neuralgia were collected,hemifacial spasm and glossopharyngeal neuralgia 841 patients.All of the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group A(routine use of antibiotics),group B (temporary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group),the heat rate,infection rate were analyzed,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fever,explore treatment strategies.Result: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eat rate(P0.05).Conclusion:There is no obvious meaning that excessive use of antibiot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This is essential for the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ever positive lumbar punctur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laboratory tests.We recommend that early and aggressive use of antibiotics to intervene if you highly suspected intra-cranial infection.
【Key words】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ever; Intracranial infection; Cause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Ji’ning,Ji’ning 272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20.037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神经痛为常见病、多发病,由于其疼痛剧烈,故又被称为“天下第一痛”[1],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对于其治疗,多采用乙状窦后入路微血管减压术(MVD)[2],多数患者可取得良好的手术效果;但术后部分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严重者出现可怕的颅内感染,仍需进一步讨论;对此,笔者进一步综合分析其发热原因,针对不同的发热原因,探讨其防治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1月-2015年12月本科实施MVD术(或三叉神经感觉根部分切断术)的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神经痛患者共计841例,其中三叉神经痛患者511例,面肌痉挛患者326例,舌咽神经痛患者4例,其中男396例,女445例,年龄23~79岁,平均57.3岁。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其中2010年1月-2012年7月的患者为A组(常规应用抗菌药物组)425例,男201例,女224例,平均年龄(56.9±3.27)岁;2012年8月-2014年10月的患者为B组(临时应用抗菌药物组)416例,男195例,女221例,平均年龄(55.1±2.49)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实施MVD术(剔除复发后实施二次手术的病例),均置入涤纶棉减压(剔除仅实施感觉根部分切断术的病例),从打开硬膜至硬膜缝合完成,均不超过1 h;另外,对于开放乳突气房的患者,均采用骨蜡严格封闭,随后应用双氧水、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三遍,以免打开硬膜后造成颅内感染;污染的器械全部更换。A组在常规切皮前30 min静滴抗菌药物基础上,术后常规使用同一抗菌药物静滴5 d;B组常规切皮前30 min静滴抗菌药物,术后仅24 h之内临时使用一次抗菌药物。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字2检验,以P
2 结果
A组425例患者中,共97例(22.82%)出现发热症状;其中确诊颅内感染病例22例(5.18%),其中细菌性脑膜炎20例、脑脓肿/硬膜下脓肿
2例;术后吸收热64例;皮下积液4例;上呼吸道感染5例;肺部感染1例;泌尿系统感染1例。B组416例患者中,共132例(31.73%)出现发热症状;其中确诊颅内感染病例21例(5.05%),其中细菌性脑膜炎20例、脑脓肿/硬膜下脓肿
1例;术后吸收热97例;皮下积液3例;上呼吸道感染7例;肺部感染2例;泌尿系统感染2例。两组患者发热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8.4174,P0.05)。
3 讨论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神经痛的病因复杂,多数学者认为神经入脑干区域存在动脉血管压迫,是其主要因素,因此,多数患者实施微血管减压术有效。本科从80年代开始实施微血管减压术(MVD),有着丰富的手术经验,并且曾对MVD术后无效的原因曾予以分析[3-4],但在良好的手术效果之后,部分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术后发热,甚至合并颅内感染,从而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痛苦及负担。
笔者对841例实施MVD手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术后常规使用抗菌药物静滴5 d,与术后仅24 h之内临时使用一次抗菌药物组比较,颅内感染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发热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
3.1 术后吸收热 占据MVD术后发热比例第1位,可分为早期吸收热、晚期吸收热两类;发生时间分别为术后1~3 d、4~7 d;而对于术后晚期吸收热的正确诊断,至关重要,因为该时间段与颅内感染所致发热的时间段相重叠,与简智恒等[5]所得结论基本相同;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如头痛、头晕、恶心等)、体征(如颈抵抗、意识障碍、新发的神经系统体征等)以及影像学资料,无法做出正确诊断;应结合外周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降钙素原检查,以及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常规、蛋白定量等检查,综合做出诊断;其中,腰椎穿刺脑脊液实验室检查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但如果患者意识状态进行性下降,在腰穿之前首先行颅脑CT检查是有必要的;患者术后一旦合并发热,尤其对于术后第5天左右出现的发热,无法排除颅内感染因素时,均应该劝导患者行腰椎穿刺检查;根据脑脊液及外周血实验室结果,在排除颅内感染之后,无需使用抗菌药物,可多次腰穿释放脑脊液,从而使得患者临床症状(如发热、头痛、颈抵抗等)得以逐步缓解。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多采用每日一次腰椎穿刺,释放脑脊液,同时观察患者脑脊液性状、颅内压力、脑脊液白细胞数目等项目,指导患者临床恢复及预后,一般每次释放脑脊液不超过30 mL,脑脊液白细胞数目、多核细胞数目及脑脊液蛋白指标均进行性下降,从而初步估计预后良好。
3.2 颅内感染 术后颅内感染不太常见,但由于它可能对患者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于术后颅内感染的早期诊断,至关重要;单纯依靠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难与术后晚期吸收热相鉴别,应该结合外周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颅脑CT或MR检查,以及腰穿压力、脑脊液实验室检查,必要时需要予以细菌学培养,从而尽早确诊、尽早治疗;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候脑脊液细菌学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有时候难以培养出阳性结果;此时,如果患者的各项临床数据,无法排除颅内感染时,应该坚持宁左勿右的原则,早期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多采用三代头孢菌素或万古霉素药物,抗感染治疗;由于颅内感染的危害较大,严重时可能危及患者生活,因此,必要时可两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
3.2.1 细菌性脑膜炎 如果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以及腰穿脑脊液检查,均支持颅内感染的诊断,而颅脑CT或磁共振无异常改变,此时应确诊为细菌性脑膜炎。对于可能的感染途径,有助于选用抗菌药物:呼吸道细菌(如肺炎双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链球菌)可能通过脑脊液鼻漏或耳漏途径感染;而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细菌,多见于脑脊液切口漏途径感染。对于脑脊液漏的患者,是否应该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目前存在一定的争议[6];由于一旦合并颅内感染,将给社会及患者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因此,多采用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在应用抗菌药物的同时,积极的病因治疗必不可少;如果存在脑脊液漏,经保守治疗无效,应积极劝导家属行修补手术。
3.2.2 脑脓肿/硬膜下脓肿 术后脑脓肿、硬膜下脓肿多发生于年龄较大、体质相对较差的患者;可有伤口感染的迹象;文献[7-8]报道,脑脓肿或硬膜下脓肿的发生,多与革兰氏阴性需氧菌或皮肤菌群为致病菌;由于脑脓肿、硬膜下脓肿可不与蛛网膜下腔相通,因此,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可能不会升高[9-10];此时,积极的影像学检查必不可少。对于脑脓肿的治疗方案大致相同:如果脓肿较小,采用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即可,多采用三代头孢治疗,必要时可联合万古霉素治疗[11];如果脓肿较大、且局限,此时行脑在患者全身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早行脓肿清除术比较适用,术中留取合适的标本行细菌学培养,术后采用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待其培养标本回报后,根据结果再调整抗菌药物。
3.3 皮下积液 术后皮下积液的发生,多是由于缝合技术原因所导致;马玉召等[12]亦对皮下积液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首先硬膜应该做到无漏水缝合,若术后发生皮下积液,可采用局部加压包扎、腰椎置管降低颅内压的治疗方案[13],可降低脑脊液压力、减少脑脊液漏出、促进瘢痕形成等,从而促进硬膜、肌肉粘连、愈合;而术中硬膜的严密缝合(必要时可取肌肉筋膜修补缝合),以及肌层的无张力、严密缝合,对于预防皮下积液的发生至关重要。另外,如果为了降低预防脑组织水肿而在围手术期使用类固醇激素,则有可能对硬膜和蛛网膜的愈合产生不利影响[14]。另外,赵杰等[15]通过大量手术证实,对于全脑蛛网膜下腔包括的保护,亦可以有效地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并缩短治疗时间,减少患者痛苦。
3.4 术中乳突气房开放的处理 一旦乳突气房打开,均应采用骨蜡严格封闭,随后应用双氧水、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三遍,以免打开硬膜后造成颅内感染;污染的器械全部更换;另外,由于手术时间因素对发生感染亦可能为重要因素,因此,从打开硬膜,到缝合硬膜完毕,均在1 h内完成,从而减少术野暴露时间,减少感染率。
3.5 上呼吸道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患者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时机,多在季节交替、气温骤变的情况下;患者经历手术、全麻应激等因素,在全身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呼吸道病毒趁机大肆繁殖,从而导致上感发生。患者除了存在发热症状外,亦存在上呼吸道感染的表现,如流涕、咳嗽等症状;此时应积极针对性治疗。
3.6 肺部感染 上感患者一般情况进一步变差,则有可能发展至肺部感染;该病例亦发生在年龄较大、体征相对较差的患者;对于肺部感染的患者,积极的痰培养、痰涂片,同时行药敏试验,从而指导临床用药;在药敏试验结果出来之前,可应用广谱抗菌药物,防治肺部感染;待药敏结果回报后,根据药敏结果,及时调整抗菌药物。
3.7 泌尿系统感染 由于所有手术的患者,需要全身麻醉、术前留置尿管,从而增加了泌尿系统感染率;患者除了发热外,还可存在尿频、尿急、尿痛等膀胱刺激症状;因此,留置尿管前充分、仔细消毒,严格无菌操作,术后尽早拔出尿管,对降低泌尿系统感染率均有所帮助。一旦确诊泌尿系统感染,均应尽早拔出尿管,并早期应用抗菌药物,并嘱患者多饮水、冲刷尿道,均对治疗有帮助。
MVD术后潜在并发症很多,而术后发热的原因众多,均应积极找寻发热原因[16-17],无菌性脑膜炎亦是临床应该注意的问题之一[18];首先尽早排除或确诊颅内感染,从而进行相关治疗。另外,有学者认为,常规生理盐水+庆大霉素冲洗,对预防颅内感染有一定的帮助[19];而本科仅采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对此,笔者下一步也将进行进一步试验。楚燕飞等[20]亦大量分析了幕下开颅手术并发症,重点分析了发热的原因。一致认为,由于颅内感染一旦确诊,将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一旦高度怀疑颅内感染,建议坚持宁左勿右的原则,早期积极应用抗菌药物进行干预,尽量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参考文献
[1] Bennetto L,Patel N K,Fuller G.Trigeminal neuralgia and its management[J].BMJ,2007,334(7586):201-205.
[2] Obermann M.Treatment options in trigeminal neuralgia[J].Ther Adv Neurol Disord,2010,3(2):107-115.
[3]王召平,杨梅,种衍军.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无效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25):34-36.
[4]种衍军,王召平,陈剑,等.三叉神经痛的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J].中国医学创新,2010,7(23):12-14.
[5]简智恒,张喜安,漆松涛,等.神经外科术后炎症指标的变化及意义[J].中华神经医学杂志,2013,12(4):415-418.
[6] Rajshekhar V,Chandy M J.Tuberculomas presenting as isolated intrinsic brain stem masses[J].British Journal of Neurosurgery,1997,11(2):127-133.
[7] Parney I F,Johnson E S,Allen P B.“Idiopathic” cranial hypertrophic pachymeningitis responsive to antituberculous therapy:case report [J].Neurosurgery,1997,41(4):965-971.
[8] Rajshekhar V,Chandy M J.Validation of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solitary cerebral cysticercus granuloma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seizures[J].Acta Neurologica Scandinavica,1997,96(2):76-81.
[9] Rajshekhar V,Haran R P,Prakash G S,et al. Differentiating solitary small cysticercus granulomas and tuberculoma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J].Journal of Neurosurgery Publishing Group,2009,78(3):402-407.
[10] Selvapandian S, Rajshekhar V, Chandy M J.Predictive value of computed tomography-based diagnosis of intracranial tuberculomas[J].Neurosurgery,1994,35(5):845-850.
[11] Gupta R K,Jena A,Singh A K,et al.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MR)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ntracranial tuberculomas[J].Clin Radiol,1990,55(1):120-127.
[12]马玉召,王延伟,孙兴,等.微血管减压术后脑脊液外渗皮下20例治疗体会[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3,16(16):3.
[13] Young-Hoon K,Han J H,Chae-Yong K,et al.Closed-suction drainag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leakage following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 a retrospective comparison study[J].Journal of Korean Neurosurgical Society,2013,54(2):112-117.
[14] Mahanta A,Kalra L,Maheshwari M C,et al.Brain-stem tuberculoma:an unusual presentation[J].J Neurol,1982,227(4):249-253.
[15]赵杰,刘志雄,刘劲芳,等.蛛网膜下腔保护在开颅手术中的应用:附156例手术体会[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35(10):1112-1114.
[16]陈登奎,庄进学,方宏洋,等.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主要并发症临床分析[J].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2006,11(3):135-136.
[17]丰育功,姜元培,唐万忠,等.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手术技巧及并发症分析(附34例报告)[J].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11,16(11):653-655.
[18]王锡温,姜绍红.颅内面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并发无菌性脑膜炎一例[J].中华耳科学杂志,2014,12(3):429-430.
[19]常洪波,田增民,卢旺盛,等,后颅窝开颅手术应用不同冲洗液预防感染研究[J].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2014,13(1):47-50.
第5篇:微观经济分析法范文
与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明显相反,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上升趋势,构成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的基础,而这的确是经典的由交换而获利的斯密式增长。在中世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严重限制了英格兰所能养活的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虽不是全部??在前近代时期仍是如此。但随着英国农业的转变,相对于生存所需的剩余增加从而使得养活日益增多的转入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英国工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生产未染色未加工的布??成为着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以适应横贯欧洲的精英们(多为领主)对奢侈纺织品的需求。但在十七、十八世纪,由于人均农业产量使食品变得便宜并使英国人口能把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大众”制造品市场 (e.g., Thirsk, 1978; Jones, 1967, 1968; John, 1965; Eversley,1967; Wrigley,1985)。
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是通过小农家庭多元化,以纺、织来弥补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中的短缺。与此相反,在英格兰它是与谷物生产的日益高度专业化及对家庭制造业更彻底的放弃相伴随并受其促进。在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制造业在英格兰典型的不是由农民着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赖于市场的商业性牧人或奶农作为副业、或是资本主义制造商利用中部适于耕种的地区相对较宽松的劳工市场来进行。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及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不同,英国制造业者于是倾向于与直接占有生存资料的途径相隔分开,因此依赖市场并受竞争的制约。结果,英格兰农村的耕种工业单位被迫通过其生产活动之总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果是制造业为应对市场需求与比较成本的增长与变化而扩展、变化,而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是为了应对小农尽管回报率日益下降仍需生产棉布并将其售往市场以弥补其粮食短缺以确保生存。
最初,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与东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约克郡,其成长与这些地区的养羊业与奶业密切相连。相应地它不见于(虽非完全)中部粮仓地区。但因为农业劳动的地区分工由新作物与技术引进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倒转,也即过去的牧区与垦区交换工业的地点也相应地发生转移。工业生产现在与牲畜饲养和奶业一道移往中部与北部,而离开东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产日益专业化及对劳力使用与之相应的农业区(Jones, 1968)。
从十七世纪前期某一时间开始且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谷物价格的相对下降,交换率向有利于工业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动,以及最终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与9; John, 1965)。消费者于是发现他们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渐减少,并因此能够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开销上。因此而发生的制造业需求的增长将其相对于农业产出的回报率提得更高,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别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与某一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化模式。而且出现了发育完全而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里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
综合而言,英国农业劳动力在1500年仅只养活占总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万人以上的城市劳力以及可能总共18.5%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农业人口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为农业长期转化的体现及由于农业生产率不可阻挡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万人以上的城镇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以外。1800年时这些数据分别达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兰从真正意义上说已不再是农业国。
经济演化结果
彭慕兰相信直到约1800年时长江三角洲与英国经济追求的发展轨迹基本相似。然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路径导致的是衰退与危机,而同期英格兰经济则遵循了亚当斯密式轨迹。
长江三角洲
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长江三角洲经济演化在十八世纪已经表现为日益增加的马尔萨斯危机症状。如果不是十七世纪内朝代更替的战争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胀而使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与其在1620年时相同,这很可能会发生得早得多。彭慕兰忽视了这一巨大的对人口增长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于是得以从更有利的角度描绘十八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见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实是,在整个十八世纪,尽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麦,长江三角洲人均粮食产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见表三; 亦见张仲民, 1988: 163, 表4.3)。农业确实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追加的劳动力也无法再提高产量,表明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点。人口增长在长江三角洲于约1750年时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这是一个经由溺婴、向外移民及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所带来的趋势。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长率压低了大约75%,从1690年至1750年间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间的每年0.18%(见表二)。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越来越依赖市场而从事家庭制造业以勉强维持生存的长江三角洲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区域外边缘地区运来的粮食。这样边缘地区有一个受人口增加推动的集约增长过程,与在核心地区经由人口驱动的劳动集约形成的集约增长型式相平行。通过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粮食,这在长期内有助于在长江三角洲减缓人口压力。然而由于这些边缘地区的经济演化大致追随人口增长、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相同的轨迹,即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满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断下降。
自明中叶起,中国农民开发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云贵)、西北、东北(满洲)、台湾岛、以及包括长江三角洲自身在内的各处闲置的山坡、丘陵(郭松义, 1990)。在开发并占有大块土地之初,他们即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出售并能以较有利的条件提供粮食以交换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和长江三角洲一样也经历了田产规模与单位劳力投入粮食产出无可阻挡的下降,并最终象长江三角洲一样需要转入原始工业生产。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些趋势因人口增长加快及殖民步伐达到空前高峰而加剧。到了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曾是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占其总量高达三分之一的长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剧削弱,而这正是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之时(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类似的发展也可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当地粮食剩余下降了多达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张国雄1993,45,表; 蒋建平1992, 55-56)。的确,把全国作为整体来看,每人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粮食总产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该数字继续下降至19世纪,亦即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同一时间(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义 1994,47)。
长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长导致劳力集约的发展途径达到极限的表征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换条件急剧恶化,与之相伴的似乎是边缘地区粮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义,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长江三角洲小农尽其所能来增加棉布产量。但所导致的棉布供应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粮的价格下降得更低。长江三角洲明显已进入彭慕兰非常恰当地指称的“原始工业的困境”。
彭慕兰认为长江中游家庭安排妇女劳动力到家庭原始工业上是繁荣增长的象征,对他而言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过接受妇女劳动力的低回报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织”社会模式的能力;我们则认为,农民对因土地资源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及因此直接生产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彭慕兰声称“虽然参与任何一种出口品的劳动的物质回报不断下降,原产品价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够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报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织’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时会被现实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见它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当长江中游在十八世纪后期变得更富庶时更多的家庭会愿意采用。(很有点象在某些西欧国家有些时期当男人挣的钱足够可以把妇女限制于只做家务那样)”(2000:249)。很难相信长江中游地区的妇女会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妇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业相对于稻作的低回报。除非在人口压力下分田产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对家庭劳力需求降低、同时为勉强维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业中家庭劳力需求的情况下被迫如此去做。这样,整个十八世纪两湖地区农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手工业及其它非农生产上只花极少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张建民1987,58; 蒋建平1992,56),湖南农民则似乎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大量从事棉纺织业(Perdue 1987,36,246-47)。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可是当这种转移的确发生时,它所表现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识选择,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英格兰
当长江三角洲以农民为基础的经济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步入自我持续的增长。在前近代时期,曾严重困扰中世纪经济并在早期近代时期欧洲大部地区继续产生作用的生存危机被抛在后面。同时,结婚年龄提高与独身率提高的结果是生育率增长减慢,有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增加。
彭慕兰怀疑有机经济“同时继续扩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费、和增加一地工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所达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农业外劳动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实际工资增加约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这是一个同期欧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联省部分地区外)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并且为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下面将会看到,1750-1850年间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业与服务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会持续增加,生活标准及人均收入将更为提高。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1750-1850)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
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也即大致为古典工业革命时代,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演化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它们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与彭慕兰所声称的正好相反,长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严重的马尔萨斯式危机表明了其在整个十八世纪业已显示的衰落趋势已达到顶点。同时,尽管彭慕兰试图缩小此期内英格兰农工业的进步,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的确是革命性的。
工业革命时代相反的经济轨迹
长江三角洲: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型式是十八世纪期间业已显示之趋势的延长及其达于顶点??即农业生产率衰退、农业中由劳力集约提高产量从而弥补低生产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业中劳动集约以弥补农业报酬迅速递减的能力下降。约在1800年或更早,长江三角洲似乎已达到了追加劳动投入不再能够增加农业产出的临界点。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整个中国时所说,“所有可耕地到那时都已开垦,靠传统生产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明显增长”(1984:12,亦见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认为1780年以后,中国农业产量从整体上开始下降(亦见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结果是经济急速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其标志是制造业产品相对粮食的交换价格下降及随之而来作为农民维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业发生危机;那些截至当时向长江三角洲提供粮食的新近开垦的较边缘地区的土地陷入生态衰退;预期寿命的持续下降;以及地主和佃农之间为土地和剩余的争端剧烈化。
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李嘉图式扩展途径接近最终极限在该地区的主要输出物棉布交换条件的急剧恶化上表现出来(张仲民, 1988:206)。彭慕兰承认长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粮食购买力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从实际上讲,这意谓着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农家为维持相同的粮食消费水准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时间。可以断言,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原始工业家庭勒紧腰带、延长了工作时间、并试图最大限度提高棉布产量。棉作带的农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纺织,被迫通过提高棉布产量来弥补其相对价格的下降,而这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达到,直至棉布成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行为过程只不过是加剧棉布的过剩并增加价格下降的压力,直到有时(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张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农民开始生产劣质纺织品以通过欺骗商人而增加其边际利润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民开始生产能得到较高价格的精致棉布,但这要求比一般标准大得多的劳动投入。男人也转入织布、接管织机、并只让妇女纺纱 (Bray, 1997: 225)。通过从外地购买较贵的原棉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边际利润,或通过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并接受更低的综合劳动报酬,松江农家得以获得足够的原棉去延长其棉纺织的时间以维持生存。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小农甚至开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锭纺车来寻求提高总产,因这一方法缩短了纺纱时间而使更多劳动力可被用于织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随着妇女用新锭纺纱、男人接管织机、以及购买来自华北已轧的棉花,一个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内所织之布的总匹数并因此确保生存。但为了继续用这种方式维持生存,农民在棉花产品交换价值恶化的压力下被迫减少高价大米的消费,而日益大量地以来自该区之外的粗粮为生。与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对照,到十八世纪末粗粮在一般长江三角洲农家粮食消费中占达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长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马尔萨斯式危机。
当十八世纪接近尾声、农业与工业中的劳动集约所产生的回报均趋于消失时,长江三角洲隐然更加依赖于从边缘地区的输入。但不仅是通过劳动集约和农业向新土地主要是长江中游地区拓展以确保进一步输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趋向终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获也不断显示是以地区生态稳定性为代价取得的。十八世纪中期边缘地区低地被填充意谓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此后转向丘陵与高地。农民们首先用尽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们即在其土地上种植玉米、土豆及蓝靛,由于这些作物迅速耗尽土壤肥力,农民们除了放弃已有土地另行开荒外别无选择,可预见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坏随之而来。随着森林覆盖层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层消蚀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与灌溉系统不可避免的淤塞,这又开始导致下游水稻产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赵冈等, 1995: 136-42)。生态破坏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最为严重,也扩展到长江下游与三角洲地区,损及浙北及长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况尤其严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总之,十九世纪完全体现出来的生态危机不仅有其十八世纪的根源,而且应被视为是该地区经济的集约与广泛性增长的整个过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积产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预见,始于1690年而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750年以后对原始工业生产者而言不断恶化的交换条件、以及截至当时为止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的地区陷入生态危机,都造成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人口损失。这种趋势导致农民逐渐放弃价格上涨的米类而依赖于粗粮。明代,江南农民的主食主要依赖于米饭,至十八世纪中期,1/3主食被粗粮及薯类所代替(洪焕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个迹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顿的人口,它看来部分可以解释为溺杀女婴的增加,及农民迫于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下维持粮食消费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机制。由于进一步分产明显是越来越不现实,农民终于不得不开始严格控制其家庭规模。权衡确保家庭生计的当务之急与养老的长期需要,农民夫妇必须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选择,以减少分家??即把儿子赶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数量以求减少分家。长江三角洲的溺婴与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兰暗示的代表了为支持经济专业化与扩展而行的“最优化抉择”,而只是在长期的人口膨胀过程达到顶点时出现的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准的反应。
最具有表症意义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也许更早)时预期寿命下降。在长江三角洲各处,十五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从世纪中叶之后下降了22.3-29.6%(刘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没有试图估计从出生开始的平均寿命)。 [3] 在边缘区安徽,男性预期寿命自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期间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个毗邻长江三角洲的类似的“繁荣”区,相应地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大灾难期间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总结说,“我们可以将男性平均寿命的持续恶化视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清代中后期儿童与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上升……平均寿命下降与婴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来在太平浩劫推动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形成”(1990: 133; 亦见Liu, 1995a:120)。
最后,随着地价与粮价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急剧上升及平均田产规模下降至维生水平以下,长江三角洲的地主与中国许多其他核心区一样寻求“重新谈判”租佃条件,他们在削弱佃农土地安全性的斗争中寻求政府的支持以便从谷价上涨及农民对土地需求增长中攫取更多的收益。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某一时间开始,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的地主特别成功地削弱了??尽管从没有废除??佃农对田面权的拥有权利。虽然地主从未确保随意辞佃的法律权力或能力,他们成功地减少了田面权拥有者将其出卖的权利、抓住了此前归田面权拥有者与售出者的卖田费、并强化了他们自己在驱逐欠租佃农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从佃农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过压榨那些因田产缩小到低于生存的水准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劳力去支付较高地租的小农,而得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事实是这些所得存在时间很短,因为在1860年对江苏的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毁灭了新出现的状况,并留给佃农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兰:工业革命
彭慕兰主张,如果英格兰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产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与木材,而且如果其国内没有煤资源则英格兰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拖跨长江三角洲相似的劳动集约、劳动生产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态危机。但他的论点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因为,首先,与彭慕兰所说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事实上英国农业继续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内得以供养农业外和工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高为任何(至少规模与英格兰相当)其他地区无法比拟、其人口增长率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因为,不存在生态危机的证据。因为英格兰并没有潜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兰所说,它可以从欧洲内部通过贸易获得足够的基本原料供应??因此无法将其视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国农业的成就
彭慕兰关于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濒临转向劳动集约生产之论点的中心是他认为英国农业“很少……继续开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国农业生产率看起来在1750年至185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2000: 216),结果“英国自己的粮食与肉类总产变得不足”(2000:217-18)。但这种断言毫无根据。事实上,英国农业支持整个此一世纪英国狂热的工业化过程的能力??包括总人口与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长??或许是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也即经典阶段的标志性成绩。
1750年至1850年时期对英国农业的要求之大是无以伦比的。英国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长,此期内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胀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从控制前近代时期的低密度人口体制到一个全新的高密度人口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变得普遍的较低的结婚年龄与更强的结婚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内能靠常规工资雇佣过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则是雇佣工作总额中工业和服务业比例上升的结果。在日益易于由工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劳动而获得抚养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纪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之间,女性结婚年龄从约26岁下降到23.5岁,而独身率(不结婚的比例)则从约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时,在1750年至1840年间,农业外人口/劳力占总人口比例从约55%增加到75%。最后,尽管有由人口增长与非农就业增加所含的劳力过剩的巨大趋势、以及由歉收、爆发战争、及欧洲范围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间)所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庞大压力,名义工资仍能在此期间保持与生活费用同步增长。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实际工资增加约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1750年至1850年间,当长江三角洲农业陷入危机时,英国农业中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了60%,而单位土地总产出(单产)则至少增长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结果,至1850年,英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据估计已经是欧洲大陆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两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见表5下)。
表五 1750年与1851年间欧洲农业生产率水平比较
国家|1750|1851
英格兰|100|100
法国|52|44
德国|36|42
荷兰|96|54
比利时|79|37
资料来源:1750年的指数来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数来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尽管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一倍且非农人口比例从55%增加到约65%,进口到英格兰的小麦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计。即使到了1837-46年间,进口小麦也只占总消费量的12%。而且这一进口量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三分之二来自俄国与普鲁士,基本上没有从英属美洲进口小麦。换句话说,在英国成为完全现代农-工业经济的工业革命经典时期,没有统计数字基础来支持彭慕兰的如下中心论题:一、英国农业有不足之处;二、由于农民生产者为生存的生产导向以及其农业更趋向国内市场,“欧洲大陆没有不断增加的剩余出售给英格兰”(2000:217)。事实上,一直到1860年,普鲁士与俄国的农民虽然无疑比美洲奴隶处境略好,可能而且确实被迫生产了几乎英国所有的进口粮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兰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历了日渐严重的食品短缺这看一事实看得很重。实际上,随着谷物法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经济鼓励粮食进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竞争性的工业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粮食进口毕竟是其经济强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显然如彭慕兰所强调的那样,英国不能与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进行糖贸易。几乎所有英格兰的糖消费都依赖于从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而且极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为糖的供应地。但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糖只占英国食品总消费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总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许要附加说明的是糖是一种可能有负营养价值的消费品。假如糖的供给被断绝,英国人毫无疑问会失去一项其极为喜爱的食品。但英国通过结合国内生产与海外进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养自己的能力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因为从面包确保供应一定数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证供应1000卡热量的面包价值为1.32克白银,而用以保证供应同样热量的糖价值为其两倍以上,达3.0克白银(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号给罗伯特·布伦纳的个人通信; 参Allen, 2001: 431, 表7)。
资本积累与技术变迁
除英国工业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国内煤供应所得优势之外(见后),彭慕兰 (2000: 44-67)主要通过极度缩小英格兰对中国的纯技术领先,来试图贬低英国工业在约1800年之前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工业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与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认已发生的突破(如在棉纺织业中)的广泛意义,声称其中含有大量幸运因素,并坚持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使英国领先于中国工业的发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争论方法没有抓住要点。使英格兰工业比长江三角洲工业及欧洲工业具有优势的并不是它的技术创造性,虽然这在事实上相当丰富,而是它在技术进步发生后有能力去实行。
英格兰对长江三角洲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优势因此首先是表现在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在长江三角洲,棉业扩展主要出自农民在小块田产上直接以农业生产维持生存能力的不断下降,及随后尽管其相对于农业的回报低仍必需进入家庭制造业的推动。在这一情况下,由于整个经济日趋贫困,工业单位无法超越棉业,且很少有进行投资的资源。他们因此在生产日益过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劳动接受更低生活标准为基础而承受更低的回报以求生存。这是一种对新近发展的技术吸收能力最为有限的环境。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业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是对因可支配开支额上升而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而扩展。这使得工业回报率特别是与至当时为止一直与之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相比上升(见前述)。由于其开始即依赖于市场,工业单位于是仅凭其在竞争压力下确保获得满意利润的能力得以继续生存:通过从一个行业换至另一个行业以取得最佳回报、将剩余再投资、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产效力的技术。结果是高度多样化的工业部分,其特点不仅表现为非常高水平的技艺,而且表现为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与技术变化速度。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与此同时,与彭慕兰暗示的相反,重要变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几个行业内,而是横跨广阔的范围,常常是经由采用首先在欧洲大陆形成的发明??不仅发生在棉花、钢铁以及能源技术行业,而且在机械工具制造、制陶业、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及一系列化学品制造业领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态危机
正如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英国食品供应没有出现潜在问题一样,那里也没有由开始出现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态危机。这里彭慕兰完全错误领会了瓦格利的观点。与古经典经济学家相同、瓦格利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人口增长所加在土地上的压力迟早会将英格兰的无机经济带进停滞的状态。换一种方式说,瓦格利认为如果没有向无机经济(煤、蒸汽等等)的转变,英格兰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样的人口增长又取得其在整个十九世纪所达到的人均总产增长。瓦格利没有试图证明的是,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持,??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格兰处在原材料短缺的边缘,如果没有断断续续增加煤的使用,这一短缺原本将会迫使英国走上劳动集约的途径。彭慕兰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煤,英格兰就不会有它确实经历了的向无机经济的转变??而将其变为他自己的论点,即是英格兰在十九世纪前期急剧增加对煤的使用将其从经济内卷或生态危机中挽救出来 (2000: 218-19, 263, 276)。与彭慕兰之说相反,1800年英格兰远未“濒临[与长江三角洲]同样的悬崖”(2000:12)。
当然,无可否认,煤确实如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兰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煤在整个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确实比在其它任何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刚好与彭慕兰的相反:英格兰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不是代表一个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劳动集约度与内卷转化的非连续性发展,而实际上它本身表现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机的出现(至十八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现在对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广泛的工业行业产生的对煤成本的负担能力。瓦格利自已认识到了此点,他承认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并未等待工业革命而是始于他称为“有机经济的高级价段”亦即英国经济独一无二、迅速发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纪(1998:34-57,特别是54-56)。人们只要留意长江三角洲可资利用的巨大的煤矿资源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尚未得到认真的开发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极彻底的理解。 [7]
无论如何,不管对瓦格利关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观点作如何解释与评价,都很难看出它能够支持彭慕兰独特的关于美洲作用的论点。彭慕兰断言英格兰“利用源自矿物能源而来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种新大陆资源的流入”(207)。但他从未解释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用说提供证据了。事实上的确难以看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实是,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成功地沿着十七世纪较早时就开始的途径前进,从根本上加大了其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距离。当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中陷得越来越深、并且人口膨胀结束时,英国经济继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尽管急剧加速的人口增长对其构成巨大的抵销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几乎高三倍,GDP则可能增长约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结果:生活标准问题
考虑到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历程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极为不同,如果它们在生活标准方面没有歧异的结果则反倒真会令人惊奇。
消费的商品
彭慕兰其实作了许多努力,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承认了英格兰生活水平较高,尽管他最后却断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兰对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高得多。毕竟,中国农业中几乎没有畜牧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全为谷豆的缮食结构中(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长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摄入量来自非肉及非奶资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兰也承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住房质量比长江三角洲或实际上全中国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争辩说中国的水质量较好,但结果他的证据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对明治日本水质的描述)及某种程度上的东南亚 (2000: 36),根本不是中国或长江三角洲。 [8]
彭慕兰的确号称在一系列他所谓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费上在两地水平相当。但他自己的证据反驳他的观点。据彭慕兰自己承认,1750年英国人均消费的糖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国人均茶消费量已比184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国人消费的茶比中国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们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数字而非彭慕兰所引施坚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数字,比较之下英国人均茶消费量更大。事实是,1800年英国人人均茶的消费比中国人在1980年代末还要大(Note?)。茶与糖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兰承认荷兰在十七世纪可能就有比中国1930年代还精致的家具,而英国在约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已超过荷兰的生活水准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兰提出英格兰的人均布产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与 Cole 1962) 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布产量相当,并暗示这可能转化为相同的消费水平(2000:138)。然而,为了使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人均消费水平相似,彭慕兰必须得出长江三角洲棉布总产达到(3亿匹)的结论,这一数字要比此问题上的权威学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亿匹的数量估算高三倍,而他们的估算已经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数字7.8千万匹(1998,30)要多出2.2千万匹。要达到彭慕兰所估计的数字,江南所有年龄介于10岁与50岁的妇女每年要纺织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仓、苏州北部之外棉纺织业并没有达到彭慕兰所说的这样普及。即使江南纺织中心,迟至十八世纪末,棉纺织业才达到如此繁荣水平(张仲民,1988)。彭慕兰自己对人均消费的估计甚至假设所有三角洲所产棉布都就地消费了,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地不得不大量输出所织之布以换粮食维持生计(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兰承认,如果将棉布输出考虑进去,江南的消费水平将非常可能会比英格兰的消费水平低。而长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费的确是低于英格兰。彭慕兰还大大低估了长江三角洲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种棉花的耕地面积,因此也过高估计了可用于纺织的原棉数量。在水稻栽培面积的计算中,彭慕兰未能将粮食生产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虑进去,而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时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种子、肥料、牲畜等项的部分。总和起来,地租和生产成本将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相当大的增加,并相应地降低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棉布产量和消费的估测而使其更为低于英格兰的水平。
最后,彭慕兰只选择了极少数的消费品进行比较。1770年英国的制造业经济为工农业中的消费者生产了种类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属制品、陶瓷器、镜子、蜡烛、鞋、钮扣、带扣等等,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当数量的这类商品。虽然彭慕兰提出欧洲的消费激增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限于狭窄的领域,他不能也没有对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兰用同样的观点。工业革命前(1625-1725年间)的英国工资劳工与小农场主已经极常规性地拥有桌子、壶与锅、白蜡器皿及陶器,以及较少常规地拥有书、钟、图画、梳妆镜、餐巾桌布、窗帘、瓷器、甚至银器。自耕农更经常拥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还加上图画、刀叉及喝茶之类热饮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对这些及许多其它物品的拥有在英格兰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纪在烟草、肥皂、蜡烛、印花织品、烈酒、廉价布、钮扣、陶器、带扣、烛台、钉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带、假发、鞋、衣服、炖锅、青铜与黄铜厨具、椅子、桌子与桌布、门把手及门环等方面消费兴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这一“消费革命”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终是建立在食品价格不断下降与实际工资持续上升的基础之上,这些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预期寿命
最后,彭慕兰被迫将其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生活水平相当的论点几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寿命的基础上。他争辩说,任何英国在消费上超过长江三角洲的明显优势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国人“更健康、长寿、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为真正的优势。在彭慕兰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寿命跟英国人一样长。
彭慕兰引用的研究显示中国人预期寿命在安徽从39.6岁降到34.9岁 (Ted Telford)、在东北是男子35.7岁与女子29岁(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员的40岁(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对这其中的一些数字的意义作限定,因为它们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个月(满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无论如何,除了皇族外,作为其基础的人口记录是相当不完全的,即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婴孩。二十世纪有关预期寿命的数据更为可靠,而所得出的数字明显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发现在华南40%的婴儿与幼孩在满五岁之前死亡,50%的婴儿与儿童在满十岁前死亡,并且总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岁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台湾更好的数据显示十岁以内的死亡率为40%(Barclay, 1954:172,附录)。 [9] 这些高婴幼孩死亡率转化为很低的预期寿命。Barclay和Coale(1976)对1929-3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24.6岁,在华南为21.5岁(620,表12),而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拥有比十九世纪时更多的土地。就台湾来说,Barclay发现甚至在日本统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预期寿命在1906年还是27.7岁。 [10] 日占以前的预期寿命当然要低于27.7岁,因为到1906年它已经上升相当快,1909-11年达到32.4岁、1921-30年达到34.5岁。只有在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介入卫生与学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让大量的孩童登记入学——及持续经济增长——1910年至1940年间总产增长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况下台湾的预期寿命才出现急剧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当然,用这一时期的数字去说明十八世纪的情况会有一些问题,但考虑到1920年代台湾肯定较好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很难想象十八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怎么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的预期寿命。
总之,很难看出十八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能够大大高于30岁,而1800年至1810年间英格兰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是44.8岁(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释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棉价太低以致一个长江三角洲妇女70天纺织所得仅够买一石米(见Huang, 2002)。这暗示自1750年起购买力全面下降了约60%(参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过长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区的垦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县份均依赖粮食进口。为增加当地粮食供应,某些移民或 ‘棚民’ 开垦山地种上红薯与玉米,但开垦山地造成水分损失与土壤侵蚀,并因此常被政府与当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刘翠溶有资料的九个地区(总共49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地区,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早期预期寿命均下降 (刘翠溶, 1992; 亦见Heidjra, 1998: 437)。在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在1600年至1800年间从54岁下降到38岁; 在长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1700年至1825年间从46岁降到31岁(刘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与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绍兴府)发现了类似的下降(Harrell与Pullum, 1995:148)。彭慕兰不接受这些发现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家谱记录中漏掉了的资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补 (2000: 37)。这样家谱中前几代预期寿命当然会有偏于上升的趋势,但五代左右之后这种偏向看起来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结果是相当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兰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现出来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兰注意到预期寿命从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时下降得更厉害、降至31.1,亦即总数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从这里争辩的观点出发,则英格兰在(大致的)中世纪、早期近代、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成功地从农民占主导转换到依赖市场生产者为主导、到工资劳工为主导地位的人口体制。
[6] 英国的情况当然与长江三角洲通行的情况完全相反,长江三角洲类似的以越来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换边缘地区的粮食,因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力以购买任何既定数量的粮食。
[7] 美洲当然提供了工业革命在棉花生产上所需的原棉。但在这样做时,它并没有满足任何严重的、且曾拖英国经济后腿的纤维短缺;因此难以看到它与彭慕兰观点的相关性,彭认为美洲在让英格兰克服“土地制约”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兰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原棉之需的事实当作英国市场没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国棉市场对美洲的准垄断完全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国南部一样如此有效或廉价地生产原棉;它并不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提供原棉。毫无疑问生产成本会高些,价格因而也会高些。但考虑到棉花制造业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这种降低经由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得以保证,难以相信市场没有能够吸收终极产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价格。例如纺棉的价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间下降了90%,反映出纺棉所需操作时间的减少:纺一百磅棉花的时间从用印度手纺车所需的50,000小时(十八世纪)到Crompton精纺车所需的2,000小时(1780年)、到动力驱动精纺车所需的300小时(约1795年)、到罗伯特自动精纺机所需的135小时(约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在1861年,随着美国内战开始,尽管美国棉花仍能有办法到达英国市场且仍占该市场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价格上(仍有限)的增长(超过1860年价格),突然向英格兰出口接近美国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内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数基本上是通过把“已经存在”的、否则会销往其它市场的棉花转运到英国市场(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东南亚的情形也不是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在人口凑密的地区水质量很差,只有煮开后才能喝(Reid, 1988:37)。
[9] 如果晚期帝国人口研究的发现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得出十八世纪死亡率可与1920年代早期台湾(日占后二十五年)的死亡率相比(约每千人二十五人死亡)的结论。
第6篇:微观经济分析法范文
关于绩效的概念,OECD(1994)认为绩效是有效性,既包括实施该项活动的效率、经济性和效力,还包括活动实施主体对该项活动过程的遵从度以及社会公众满意度。普雷姆詹德(2002)认为绩效包含了节约、效益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容。陆庆平(2003)认为绩效实际上是一项活动实施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投入资源的合理性、结果的有效性,以及实施这项活动所投入的资源与获得效果的对比关系。丛树海等(2005)认为绩效是效益、效率和有效性的统称,包含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两个层面的内容。就行为过程来说,主要是指投入是否最小化,过程是否合规;就行为结果来说,主要是指产出与投入相比是否有效率,行为的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等内容。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绩效指标和事业成本为核心,以绩效目标、绩效拨款和绩效评价为基本环节的政府理财模式。预算绩效管理突出强化了政府预算为民服务的理念,是预算改革和深化的必然要求,目的在于切实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它强调了政府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要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尽可能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努力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切实做到政府行为的务实、高效。
二、预算绩效管理理论基础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需求也变得多样化,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时代变化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种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西方经济学、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工商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原则、方法及技术融合进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之中,于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便应运而生。该理论寻求高效、高质量、低成本、应变力强、响应力强、更健全的政府运行机制,遵循“顾客导向”、“市场导向”和“结果导向”三个原则。“顾客导向”的原则重新界定了政府与纳税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市场导向”的原则强调政府应该多运用市场机制,利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提高政府效率;“结果导向”的原则强调对于政府的考核,应该改变过去过多关注过程控制和监督的理念,应将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政府活动的结果和产出上,以克服政府工作的僵化,更加灵活地提供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政府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变革,在政府制度设计、运作方式、理财模式方面都深深烙下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烙印。可以说,预算绩效管理,既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新公共管理理论转化为实际制度安排的重要工具。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领域中,政府公务人员和市场领域的主体一样,同样也是“经济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将应用于市场领域的“成本—效益”这一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引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政府行为经济化或市场化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客观选择。根据这一思路,政府公务人员的身份是“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的 “顾客”或“客户”。 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衡量和考虑的是政府应当花多少财政资金提供某项公共劳务,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将政府行为经济化,这既是市场经济关系在政府行为中的体现,同时也是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最佳方案。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不断强化政府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观念,关于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恰恰是公共选择理论在财政预算领域的最好应用。
(三)财政支出的边际效用理论 财政支出效率与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财政支出是否有效率,衡量的标准是:财政支出所取得的各种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总和,是否大于在聚财过程中对经济所形成的代价或成本,也就是说要取得效益剩余或净效益。如果净效益值越大,则说明财政支出越有效率。社会资源是在财政部门和民间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实现社会资源在财政部门与民间部门的优化配置,按照边际效用理论,就必然要求用于财政部门的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益等于该资源用于民间部门时所取得的边际效益。如果财政部门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益大于该资源用于民间部门的边际效益,这就说明财政配置资源是不足的,可以增加财政部门对资源的使用,以便获得更大的效益;反之,则应减少财政部门的资源配置规模。当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满足了上述条件,则不仅资源配置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且此时财政预算决策也是最优的,财政支出也是最优效率的。根据此理论所形成的财政支出项目“成本—效益”分析法,已经在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三、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意义
(一)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以人为本。公共财政是民主财政和服务财政,在财政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实现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要节约而又有效地用好税收,向社会公众提供高效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要想做到这一点,在财政支出的活动中,必须要充分注重绩效,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把纳税人的钱用好,使得支出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二)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是实现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财政事业的健康发展,是新时期财政工作的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必须要依靠财政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对于实现财政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理念上,预算绩效管理体现的就是财政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通过对财政支出活动的绩效评价,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从财政资金分配的源头上进行规范,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安排,体现的是以结果为中心的理财理念。在操作层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通过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和特定方法模型的运用,衡量、监测、评价支出活动的经济性、有效性,为财政支出决策提供依据,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三)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是建设“高效、责任、透明”政府的客观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政府的绩效情况和纳税人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要大力推行行政权力的公开透明,建设“责任政府”和“阳关政府”,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以此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预算绩效管理关注产出的效果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理应为“高效、责任、透明”政府建设尽份内之责,同时也是“高效、责任、透明”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对于化解地方财政困境具有现实意义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由于财权层层上移,事权层层下移,导致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财政面临困境。再加之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实施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跟上对财政资金需求的增长,从而造成了强劲的财政支出压力。有限的财政资金在分配上也缺乏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在各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争预算、争项目的现象,预算资金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的博弈来进行的,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导致了预算资金的平均分配,难以实现财政资金的有效率使用。目前,在财政体制没有办法进行大的调整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推行绩效预算管理,强调财政支出的效益,将支出控制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或结果,从根本上改变“重分配、轻管理”格局,制定科学的财政资金分配决策机制,从而达到“少花钱、多办事、办政府应该办的事”的目的。
四、预算绩效管理目标与评价指标设定
(一)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定位 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组成了竞争性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和办得好的,就不应该交由政府承担。公共财政应该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活动的基本着眼点,公共财政的职能在于提供必要的公共性基础条件,维持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进社会公众福利,这是财政运行的基本取向,同时也是国家财政活动应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因此,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定位,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要更多的评价财政支出成本既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预算绩效管理目标设定依据 预算绩效管理目标的确定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起点和核心内容之一。预算绩效管理关注的重点在于财政支出的结果和效果如何,也就是政府花了钱,老百姓最终得到了什么,而不是政府的钱够不够花,怎么花。在实践中,设定绩效目标有不小的难度,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据。一是绩效目标的设定要与部门的战略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部门的战略目标是部门绩效目标的基础,根据部门战略目标的阶段性,并将其分解到每个预算年度,并在此基础首先提出本部门的绩效目标,在总体上,确保绩效目标与部门的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二是绩效目标的设定要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在设定绩效目标的时候,由于不同部门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存在着如何兼顾可比性和独特性的问题。此时,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设定绩效目标,确定一个总体上相对一致的而且又能充分体现部门个体特征的绩效目标原则,就显得比较重要了。三是绩效目标的设定应当采用部门申报和财政部门组织审核相结合的方式。第一步,绩效目标首先由部门申报,在申报的同时提交项目可行性方案以及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第二步,由财政部门对部门提交的可行性方案进行严格的审核,一般项目按照例行程序进行审核,重大项目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三)预算绩效管理中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 按照公共财政的思想,财政支出的目标就是为了提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社会福利水平很难量化,在实践中必须要找到能够量化的特定概念和具体数值,以衡量、监测和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即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对于绩效评价活动的实质性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具有的强烈的价值取向,对于评价对象未来绩效的改进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认为,建立科学、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是进行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在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践中,由于财政支出的类型繁多,不同类型的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指标又各不相同,导致在绩效评价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集中在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上。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如何设计层次齐全、类别丰富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摆在各级财政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的划分,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一是从评价对象的适用性上来划分,可以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共性指标是每个评价对象都要采用的指标。具体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资产配置、使用、处置、财务管理状况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指标。个性指标是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特点和目标,通过了解、收集相关资料、信息,来设置特点目标。二是从绩效评价的目标和全过程方面来划分,可以分为初始指标和终极指标。初始指标具体包括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产出类指标以及效果类指标。投入类指标,用于反映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时,所投入的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等指标;过程类指标是用于反映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工程中,质量控制和执行预算计划的程度等指标;产出类指标是用于反映政府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或完成的工作量等指标;结果类指标是指用于反映一项计划或一种工作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度的指标。终极指标包括经济类指标、效率类指标以及效果类指标。经济性指标,主要用于反映财政支出项目的成本是否最小化。这主要通过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和相应的标准进行比较得出。效率类指标,是用于反映一定的财政资源投入是否获得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最大产出,它往往是通过投入类指标和产出类指标进行比较得出。效果类指标,是反映财政支出项目的产出结果满足和实现社会公众的需求、偏好和价值观的程度。它要求政府不仅要做正确的事,并且做的结果要与社会公众的预期需要相符合。
五、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构建
(一)强化认识,树立绩效评价理念 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绩效评价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建立与公共财政框架相适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要树立绩效理念,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并把绩效评价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改变原有的“重投入、轻产出”,“重分配、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树立“要钱不能随意,花钱要讲绩效”全新的财政理财观念。财政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对绩效评价工作重要性的宣传,让财政绩效评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让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和履行职能的效果为纳税人所了解,努力打造让社会公众满意的“责任政府”和“阳光政府”。
(二)建立专门的预算绩效评价机构 要使财政绩效评价成为一个经常性、常态化的工作,必须要有专门的预算绩效评价机构。结合财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财政监督检查机构改设为财政绩效管理机构,承担绩效评价的具体工作。各部门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组织开展本部门、所属单位以及财政支出项目的具体评价工作。同时,为了便于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应该赋予绩效评价机构和人员在信息查询、资料获取、独立取证以及行政处罚建议等方面赋予必要的职权。
(三)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制度 为了避免在以往绩效评价工作存在的为评价而评价的弊端,发挥绩效评价工作实效,必须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总体上,要科学制定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具体规定评价结果的运用目的、运用范围、程序以及权限等内容,从而对政府各项财政支出活动进行指导和规范。具体包括:一是要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公示制度。有关绩效评价结果要提交人大、政府等部门,以供有关领导决策时参考。同时,还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接受监督。二是要建立问题整改机制。各部门应根据部门的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结果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优化本部门未来年度预算支出的规模、方向和结构,提出整改措施并报财政部门备案。三是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现预算项目与事业发展目标完成情况挂钩。对绩效优良的,在下年度安排预算时给予优先考虑;相反,对绩效差劣的,在下年度安排预算时要从紧考虑。
(四)探索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信息体系 由于财政绩效评价涉及面广,数据信息量比较大,时效性又比较强,在推行预算绩效管理的过程中,就对预算绩效管理信息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保证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有效运行的技术基础。结合我国财政管理的现状,预算绩效管理信息体系的建立要尽快适应财税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金财工程为基础,开发、完善进行预算绩效评价分析的系统软件。二是建立健全预算绩效评价的数据库,并要做好数据信息的分类管理。三是要建立绩效评价信息库。这包括专家信息库和中介机构信息库,实现绩效评价工作所需信息的资源共享和互通。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