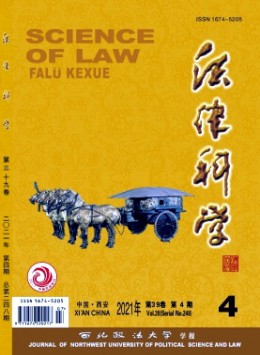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范文
中图分类号:D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2-0185-08
一、商业道德在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定位及其不确定性
不正当竞争行为一直以其行为多样且变化多端著称[1],故有学者将其喻为模糊且幻变无穷的云彩。而发生于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快速迭代性更为显著。近年来国内外互联网领域爆发的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即为明证①。鉴于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迅猛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可能也无法对各样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周延、具体的类型化规定。于是,当涌现一些全新样态、反不正当竞争法未予具体规定且实质性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行为时,该法第2条(即“一般条款”)则成为司法机关判定这些新型竞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不二选择[2]。然而,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是其显著特征[3]。究其原因,一是法律概念的不确定,表现在不正当竞争概念外延开放且内涵不确定,以“公平竞争”为例,其概念本身的含义极为抽象,可从哲学、法律、政治学等多个视角阐释②;二是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最典型表现为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这些规则虽作为客观的强行性规范,然其内涵甚为概括抽象,其内容可能因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而赋予不同的意义。一般条款以诚实信用原则、公认的商业道德作为核心内容,便也表现出显著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条文抽象宽泛、实施起来无所适从,难以为市场行为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合理的行为预期,可能减损竞争法作为市场秩序基本法的指引和预测功能,贬损竞争法的权威,阻滞市场竞争领域内对有效规范的探求。如何具化一般条款的核心内容,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予以重大关切。
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作为一般条款的核心内容,评判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取决于行为是否侵害了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鉴于诚实信用原则更多是以公认商业道德的形式予以体现[4],故如何勘定公认商业道德则成为司法认定涉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之关键。据前述可知,商业道德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其表述过于空泛且边界模糊,也未能涵摄任何权利义务内容,其具体要素可能因各异社会经济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甚至可能基于对各不同要素的不同强调比重而改变评判结果[5]。若无法给公认商业道德认定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困局。科学界定公认商业道德是合理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有效规制一切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逻辑起点。
伴随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不断涌现,学界逐步重视对一般条款核心内容——商业道德的研究。从既有成果看,学界对公认商业道德的研究聚焦在:(1)公认商业道德在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中的作用和地位[6];(2)商业道德司法适用中面临的挑战与相应的细化规则[7];(3)商业道德适用中的局限[8]。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对商业道德不确定性的克服有所助益,然仍存在以下不足:(1)多数局限于单一正当性判断标准,欠缺从整体视角认定商业道德;(2)大多拘泥于商业道德的认定细则,即仅从微观视角予以修补,未能上升到较高层面的认定思路做出反思,从宏观视角阐明商业道德整体认定思路和认定流程的研究可谓阙如;(3)虽提出一些关于商业道德认定的初步解决方案,但所提建议多数流于空泛,未能最大限度保障个案中商业道德认定的确定性。而司法部门虽绞尽脑汁,基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商业道德的认定规则,然其要么过于微观、精细,要么仍然陷入另一种不确定性、空洞化的困境,无法在实质意义上克服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
通过审视学界研究和司法认定细则,发现过于微观、精细的司法认定细则和理论观测点均难以从根本意义上具体化商业道德。明智而务实的做法是将视角投掷商业道德的认定思路上,这是通往商业道德确定性的必然之路。既有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所提规则难以真正达致商业道德的客观认定,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规则背后的认定思路存在弊端,难以承担商业道德可感知化、细致化、具体化的重任。是故,本文从商业道德现有认定规则出发,提炼、审视这些认定规则背后的认定思路并予以反思、批判之,基于此重构商业道德认定的新思路——法律论证分析框架,以及阐明其具体运用。
二、商业道德现有认定规则的检视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海带配额案”中指出,如涉诉行为无法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列举的规制行为,则以行为是否有损公认商业道德做出评判③。其虽肯定了商业道德在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然其仍未提供如何勘定商业道德的答案。商业道德具有明显的概括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厘定商业道德的内涵异常艰难。庆幸的是,立法者和实践中逐步摸索和提炼出商业道德的认定规则。经归纳发现,关于商业道德存在如下两种认定规则:
(一)规则一:以行业惯例认定商业道德
所谓行业惯例,意指行业自律组织基于行业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保障该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而颁布的对行业全体成员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是行业自律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规范性文件。考虑到行业惯例与商业道德源起一致[9],且两者的内在表征、核心指向高度重合,故有学者坦言,公认商业道德作为商業惯例与行为规范另一种形式上的表述[10],因此可以行业惯例来辅佐认定商业道德。最高人民法院在“3Q大战”的终审判决也力主行业自律惯例在认定公认商业道德的作用,认为在市场竞争活动中,相关行业协会及自律组织为规整该领域的市场竞争行为、保障市场竞争秩序,有时会结合该领域的竞争需求与行业特点,在归纳总结其行业竞争现象的基础上,以行业自律公约的形式制定该领域的从业规范,旨在为行业内的企业行为提供指引或约束。这些行业自律规范常常体现该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及行为标准,故可作为法院认定行业公认商业道德与行为标准的重要渊源④。类似案件还有“百度与360违反robots协议不正当竞争纠纷案”⑤、“百度与3721不正当竞争纠纷案”⑥等。
(二)规则二:司法创设具体细则认定商业道德
个别法官结合自身对公认商业道德的理解与实际案情,提炼了一些具体认定规则。如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百度诉奇虎插标案”中,提出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⑦;而在“百度与奇虎robots案”中,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总结了“协商通知原则”⑧;还有法官分别创设了“最小特权原则”⑨及“一视同仁原则”⑩。
后续审理某类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时,有法官径自将目光移至这些规则。如在“爱奇艺与极路由不正当竞争纠纷案”B11,法官则径自借用“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论证:“经营者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和商业创新获取正当竞争优势,但非因公益必要,不得直接干预竞争对手的经营行为”。无独有偶,在“优酷与UC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B12,法官也以该规则论述行为的正当性:“经营者应当尊重其他经营者商业模式的完整性,除非存在公益等合法目的,经营者不得随意修改他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影响他人为此应获得的正当商业利益”。对司法实践创设的商业道德细化规则,有学者认为:这些规则的创设一方面丰富了判决书的论证说理,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面临的道德资源贫瘠困境。
三、对商业道德现有认定思路的反思
从商业道德既有认定规则看,主要采取以认识为主、强调立法主导作用的决定论立场和以裁定为核、强调法院主导作用的决断论立场。其中,以行业惯例认定商业道德类似于一种立法决定论立场,而司法创设具体细则认定商业道德属于司法决断论立场。
(一)决定论立场在商业道德适用中的检讨
所谓决定论立场是一种法律形式主义的立场,其侧重立法的周密规定,认为法律作为由规范组合而成的无缝隙体系,法官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体系找寻合适规范,并采用既定程序将其与事实结合起来,这意味着立法对案件的事前概括认识已然决定事后纠纷的最终解决方案。决定论的立场承认立法者的万能理性,否认裁判者的创造性。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道德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存在唯一、事先可把握的绝对标准,立法难以提供统一明确、封闭的标准,这限制了决定论立场的发挥空间。具体言之,行业惯例的立法决定论立场之所以不适应于商业道德认定,其原因有二:
一是以行业惯例认定商业道德的立法决定论立场奉行一种从前提到结论的简单推导,然“现存的市场惯例不一定是良好的”[11],行业惯例的形成可能因欠缺不同类别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而未能证成其本身的正当性。若仅以决定论思路进行,依靠简单的逻辑演绎,未经利益平衡审查而径自借助现有的行业惯例来认定商业道德,未免显得草率。即便是经过共同体内成员的普遍确认而形成,但未能符合行业通行实践,也可能有违市场竞争[12],不可作为认定公认商业道德的参考。从这个角度看,决定论立场的推导过程过于简单,忽略了个案中商业道德的“特质性”。
二是不同领域的行业惯例通常不具有通约性,特定行业领域具有特定的行业惯例,有的行业惯例正在修订,有的行业惯例还未形成。若仰赖于既有发生效力的行业惯例来认定商业道德,容易显得无所适从。比如,在互联网领域,产业升级换代迅速,商业模式更迭速度尤快,创新程度极高[13],相关行业的自律惯例也正在形成和不断发展中,甚至在某些时候这些行业惯例呈现阶段性特征,难以保证始终存在效力稳定且内容明确的行业规则,如此时以行业惯例认定商业道德,可能引发同案不同判的困局。而其他一些新兴领域可能未形成可视化、稳定的行业惯例,也无法给商业道德的客观认定提供合理答案。对于商业道德认定而言,重要的并非行业惯例的大量制定,而是始终具有稳定可靠、经过全面利益衡量的行业惯例。即便行业惯例制定多缜密,数量如何繁多,也难以保证行业惯例本身的稳定性,无法始终如一、源源不断为商业道德认定输送养料。这种基调决定了立法决定论立场难以适用商业道德的认定。概言之,不正当竞争案件所涉领域的广泛性、丰富性决定了,以行业惯例认定商业道德的决定论立场很难站得住脚。
(二)决断论立场在商业道德适用中的批判
决断论的主要视线是关注法院的司法审判,其有别于上述提倡立法理性万能的决定论,表明“法律不过是对法官行为的预测”,且在个案中充分尊重利益与价值权衡。不得不说,与决定论相比,决断论的立场更契合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实际审理。商业道德的认定复杂模糊,为保证个案的实质理性需要法院的有所作为。并且,商业道德的判定也并非事先有既定规范可仰赖,而需在特定具体情势下经利益权衡与价值判断后做出认定。以决断论立场认定商业道德,体现了对实质理性的追求。然这种从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同样可能引发新难题:
一是如何在个案中把握商业道德的“不唯一性”?商业道德内涵多元且抽象性极强,这可能意味着个案中法官的主观道德正义与市场经济中商业道德的客观正义并不完全吻合。商业道德作为白纸规定,乃授予法官的“空白委任状”,个案中法官对商业道德的把握见仁见智,其所提炼的商业道德细化规则不免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甚至是渗杂过多的价值判断,如未能考察特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竞争规则”,这种基于法官个人的主观道德正义而提炼的商业道德认定规则,极有可能背离市场的客观道德正义。
二是失去立法的事前约束,如何确保法官所做裁判基于客观性要求而非恣意?决断论立场并未为达致商业道德的客观认定提供答案。裁量的运用,非但有正义,亦有非正义;非但基于通情达理,亦可能基于任意专断[14]。商业道德是一个暧昧、滑动尺度较大的概念,包含不同射程的谱系,其具体内容因时展而异,也因所处特定行业领域而有所侧重,甚至因各經营模式而呈不同概貌,如单方地将商业道德的认定权授予法官却欠缺制度性的约束,难以确保这种创设行为基于合理、有效的约束,无法杜绝法官的恣意裁判。“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治可言”。虽然,“国内法治建设正处于转型期,司法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15]。赋予法官享有一定裁量权认定商业道德,是立法有意设置的留白,然如果这种创设未能基于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则只能不断偏离确定性和稳定性的方向,进一步强化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如法官未能坚守谦抑态度,过于随性提炼商业道德的细化规则,长久以往,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将演变为判例法。可见,商业道德认定中决断论的立场也不尽妥适。
四、商业道德认定思路的重构
经由前述得知,决定论立场和决断论立场在商业道德认定中较难发挥效用。法律论证立场(被视为“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超越决定论和决断论立场的困境而产生。商业道德的特性决定了以论证为核心的法律论证分析框架更契合商业道德的判定。
(一)法律论证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
法律论证“被看成是一场关于某种法律观点可接受性对话的组成部分。论述的合理性取决于商谈程序是否符合可接受性的某些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16]。推崇程序正义的法律论证理论的诞生,标志着对既往各种立法和司法模式的反思,重视综合性程序正义的法律论证理论逐步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范式。正如学者所言,“在当代社会中,法治提供了正当性的来源,但是法治需要新的论证,即规范意义上的民主程序。法治的正当性,在于以道德论辩,以制度构建,以程序反思。弘扬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可能出路”[17]。
法律论证分析的主旨在于确保参与商谈的各方主体以程序交往的方式达致某种共识、合意,且最终结果的获得正是构筑于该合意的基础之上。具言之,法律论证的过程并非呈现单一方向的简单线性逻辑推演过程,而毋宁是一个由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对话、协商的论辩过程、一个不断促成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可见、外向性的程序为保障,整个程序的进行包括通过试行错误而逐渐摸索出妥适的解决方案,以及与之相关的相互作用和不断的对话、论证、商谈,最终达成的共识或者表现为罗尔斯所言的“重叠性共识”,或者表现为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暂时性共识”,但其共同的前提是:这些由程序合成的共识均不存在所谓的先验价值、真理或大一统的意识形态[18]。
法律论证理论的分析框架包括逻辑方法、修辞方法和对话方法。其中,对话方法为其他两种方法提供了总体的运行框架,在整个法律论证理论中意义最为突出。事实上,整个法律论证的分析、证立结果能否接受取决于对话方法是否获得良好运用。而对话方法所彰显的所有价值均来源于其对交往理性与程序正义的推崇。对话方法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转化为一个程序性问题,其核心主张是:任一正当且正确的法律决定无不立基于理性民主的商谈、对话和交流机制而形成,建立在程序正义基础上的对话才能联结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藉由理性形成的共识[19]。
(二)法律论证分析框架应用于商业道德认定的优势及其定位
既有研究以及前述司法所提认定细则,不仅面向过于微观,无法在整体视角把握商业道德,而且都试图从实体角度认定商业道德,最终结果只能是以一种不确定代替另一种不确定。而法律论证分析框架的运用,恰从程序的视角并以对话方法克服了立法决定论和司法决断论立场在商业道德认定中的局限性。
相较于以行业惯例认定商业道德的决定论立场,法律论证分析思路的优点体现为:第一,是由多个论证理由相互印证、组合而成,而非限于以行业惯例认定,法律论证分析框架通过不断论证,是一种永远均可借助新证据以及正当论证程序去不断逼近终极观点的论辩式真理[20]。第二,法律论证分析框架充分考量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不推崇从前提到结论的简单推导的蕴含和涵摄过程。商业道德认定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并非一个可以事先能直接把握住的封闭的绝对真理,无法通过直线式、单一方向的逻辑推演即可得出答案。任一规则的正确性无不需要来自另一规则的证立,当然,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元规则”。如只是简单套用现有的行业自律惯例来认定商业道德,论证链条不但比较单一,也囿于已有的且具有效力的行业惯例之数量。法律论证分析框架不拘泥于机械套用既有的行业惯例,对于适用的行业惯例本身进行审查,还予以相应的利益衡量,整个逻辑推导过程思路缜密,由层层链条组合而成。
而相较于创设商业道德具体细则的决断论立场,法律论证分析思路又独到地彰显其在商业道德适用中的优越性:
首先,最大限度限制和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为:其一,法律论证分析框架要求法官进行严密论证,以程序确定性的形式规则和技术规则来约束法官,要求法官基于理性做出符合普遍实践论证的判断,并且要求其广泛结合客观的市场竞争规则,避免其主观道德正义与客观道德正义不吻合。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黄茂荣先生所言,“他(法官)应依共认的价值标准作客观的价值判断。同时这些共认的标准必须是可以验证的,而且为既存之规范模式所支持,而不该仅仅是政策上之合目的性的偶然考虑的结果”[21]。商业道德带有较强的时代属性,永远处于一种演变的姿态,为避免法官对商业道德的认定忽视客观市场背景而渗入过多主观因素,需对法官科以充分论证的义务,防止出现背离市场客观道德正义之情状。其二,纳入当事人的视角,对法官的诠释提供了一种背景约束。案件两造对规范的阐释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利益应走到前台并创建一个由法官、诉争双方共同论辩、寻求真理的“场域”。而法律论证分析思路正是体现所有参与主体视角的制度结构,法律论证分析思路不仅锁定法官的视角,还纳入了案件两造的视角,即同时体现法官和当事人的视角,体现了公民间的公共交往理性[22],从而对法官的阐明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约束。从这个视角看,法律论证分析思路可有效限制法官在认定商业道德过程中过于恣意的裁量权。
其次,以程序可见的方式最大限度确保个案的确定性。整个法律论证分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对话论证的过程,也是一个以推崇程序正义和交往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同于以往结果确定性的追求,而将视线置于程序确定性的追求,是以一种程序看得见的方式把握商业道德的认定。商业道德的确定性追求应落实到程序确定性的追求上,才能保证开放性判决结果的合理性。这种对商业道德认定结果确定性转化为认定程序确定性的过程,是一种肯定“知识共识论”和追求“知识真理论”的过程,是一种依赖于利益相关者通过充分论辩、获得所有人共识而保障確定性的过程。
商业道德的认定并非交由某种简单的逻辑推演便可获得确定无误的规则,也非借助纯粹的经验事实验证即可获得唯一正解。关于商业道德的认定,欲获得一个合理可接受的答案,“不可能通过直接诉诸经验证据和理想直觉中提供的事实,而只能以商谈的方式,确切地说通过以论辩的方式而实施的论证过程”[23]。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商业道德的认定关涉多元价值,难以直接从价值判断中抽离出来,次之其涉及多方主体利益,这些不同、不可通约的主体利益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致力保护的,而这些不同主体利益不存在顺位差异,也无法基于位阶的优越性进行直观判断。此时,借助法律论证分析框架可巧妙趋避这些难题。
法律论证分析“将对法律实质正义的追求转换为一个程序问题,”而程序不存在预设的真理标准,也不与特定的实质内容固定在一起,而呈现出很强的技术性,故得以较好避开商业道德认定中的价值多选难题。法律论证分析重视对话式的讨论,藉由在讨论中不断论证,通过实质推理方法为法官、诉讼当事人给定一个论证规则和论证程序,提供讨论框架并引导讨论秩序,从程序角度设定了约束以达致程序确定性的答案[24]。其既非直接寄希望于立法者,也非将选择唯一正确规范的权力交由法官。而是植入论题学取向的思维方式,强调诉讼主体间性,倚赖论辩这一中立的交涉方式,强调以对话方式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通过论辩程序不断逼近商业道德认定的“终结观点”。
“一个正当的也是正确的法律决定必须通过民主的理性的协商、交流与对话制度才能形成,把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通过沟通理性形成的共识联系起来”[25]。商业道德认定经由植入法律分析框架,各方话语权得到充分保障,任一方主体均可参加论辩,也可质疑其他主体所提任何主张(如图1),并在论辩中提出主张和表达态度(需求),且有权确保不受论辩内外的某种因素之强制性阻碍。即言之,商业道德认定适用法律论证分析框架,得以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以平等机会参加谈判,并且这种谈判平等地对结果施加影响。唯有奠定于真正平等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协商与交流,否则仅有命令及权威。即便获得参与主体的服从,也无法得到尊重,而毋宁提正当性了。反之,在平等基础上经由充分的讨论和协商而获得的共识,才称得上真正的合意,以及获得当事人内在的遵从。
五、法律論证分析框架在商业道德认定中的具体运用
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商业道德认定中具体如何适用法律论证分析框架,亦即如何构建商业道德认定的程序性框架。法律论证理论对法律裁决的证立结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诠释,体现为在证立时需要区分出哪些层次和多少个论证步骤。商业道德认定植入法律论证分析框架,也具化为不同论证层次和论证步骤。
由于商业道德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存在唯一的构成要件作为前提,故难以从简单的三段论逻辑推演直接得出认定结果。而正如阿列克西所言,如推导展开的步骤极少且跨度非常大,则无法清晰展现这些步骤的规范性内涵[26]。欲提高商业道德认定结果的支持力度与论证强度,不妨尽可能细致地还原商业道德的推导步骤。由于商业道德认定涉及多重主体、多方利益与多元因素,不存在绝对、单一、封闭的认定理由,应尽可能对商业道德的认定理由进行多元分解。
鉴于“同一论证方向的两个理由强于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理由”,应尝试以论证链的形式对这些多元理由进行分层论证。其中,每一推导步骤作为一个层级,每一层级可能存在若干个支持理由,第一层级认定商业道德的各个理由又分别需要来自第二、第三层级等次级理由的支持。链条的长度决定了论证的强度。在论证链条中,每一理由的论证强度伴随其支持理由的增加而增加,“其他条件不变,支持一个命题的论据链越长,这一命题的论证强度就越大”[27]。其具体论证思路如下(其中A代指商业道德,Bn代表商业道德认定的各种理由,Cn、Dn、En、Fn、Gn、Hn分别代表各不同层级的次级理由):
商业道德认定理由据个案可能是符合行业自律惯例(B1)、遵循商业模式(B2)、促进技术创新(B3)、保障消费者利益(B4)等。当事人可以其行为符合行业自律惯例、遵循商业模式、促进技术创新、保障消费者利益,从而证明其行为未违背公认商业道德而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至此,当事人需分别进一步证明,为何行为符合行业自律惯例则不违背商业道德、为何行为遵循商业模式则不违背商业道德等。这就是说,以行为符合行业自律惯例等为理由还需要其他层级理由的支持,当它与其他理由结合形成链条结构,这个论证才可靠,才具有说服力。
不妨以行业自律惯例(B1)为例,行为人为论证其行为符合行业惯例而未违背商业道德,行为人需首先证明行业自律惯例与商业道德的源起一致(C1),并且证明行业自律惯例的正确性(C2)。如何证明其正确性?据考夫曼的洞见,可用同意的程度来衡量内容的正确性。故此时行为人可以行业自律惯例的制定立基于行业共同体内多数成员的合意(D1),来证立C2。但论证链条还不能就此止步,并非任一种同意均可作为正确性的评价指标,还须确保据以形成合意的程序是理性的,即还需要证明行业自律惯例的制定基于理性程序(D2),等等。同理,符合商业模式(B2)、促进技术创新(B3)、保障消费者利益(B4)等理由的证立也需要遵循上述论证思路。
在一方当事人论证过程中,另一方当事人均可质疑对方所提理由并表明自身态度与需求,但也需提供相应理由并以论证链条的形式来证立其主张,以确保这些论据的融贯性。而法官的主要任务一是组织和引导整个论证过程的开展,二是权衡这些论证观点并做出最终决断。该决断的得出也需不断进行论证。法官应尽量使论证的理由链更长,但并非局限于单纯的数量追求,而是最大限度确保不同理由之间的支持关系。理由之间的融贯程度决定了其对结论的支持程度。于此对法官的权衡或判断能力也是极大考验。法官不能“孤独地”考虑自身观点,而是要确保其结论得以为相关主体所认可、易被公众接受,以及结论的社会实效性[28]。法官应向当事人公开其论证商业道德的思路,并在判决书详细阐明判决理由以及其形成原因。“任何规则必须公开,且是普遍可传授的”。
至此,应该说商业道德的整体认定流程已基本明晰。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无法设计一个完美的程序并确保通过该程序证立的命题必然正确,也无法一一列举商业道德可能的认定理由,我们所能为者,就是给商业道德认定设定一个程序性框架,并就商业道德认定中的不协调观点“调整之以达成理性同意”,则足矣。
六、简短结语
第2篇: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范文
关键词:司法三段论 法律解释 法律论证 法律方法论
Abstract : traditional legal methodology represented by judicial syllogism has been challenged from variousaspects and is becoming less acceptabl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major theoretical trend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deep transformation is going on in contemporary ethodology , thatis , judicial syllogism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legal methodology characterized by such dimensions as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argumentation.
Key words :judicial syllogism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argumentation legal methodology
一、趋向衰落的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以来在科学领域获得极大成功的逻辑三段论就一直主宰着法律推理的思维。可以说, 近代法治理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严格逻辑。[1]依照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 (1) 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实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对象。(2)因而只有感官经验为人类认识的源泉。(3) 必存在着本质上互有区别的认识方法。(4) 将非描述性陈述———在它们不是逻辑—陈述的范围内———从知识和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这种做法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价值判断被驱逐出知识的范围。[2] 司法三段论即立足于这种哲学认识论。经典的司法推理(即涵摄subsumtion) 就是在法律规范所确定的事实要件的大前提下,寻找具体的事实要件这个小前提,最后依三段论得出判决结论的过程。从学理上,一个法律规范通常被分为“要件事实”和“后果”二部分。只要一个具体事实满足这个规范所规定的所有事实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因而其突出优势在于,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二分格局下,法律适用之操作过程极为清楚。并且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3]故如此似乎足以消除法官的恣意裁判,从而保障了判决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实际上,这种推理模式早在二十世纪初就遭到美国霍姆斯、弗兰克等人的挑战。不过,这种批判乃出于对传统法律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本能的反叛,缺乏论证的系统性和严密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往往只“破”不“立”的一般立场往往易威胁乃至颠覆近代法治的根基。只是到了当代,西方法才不仅从理论上全面省思了司法三段论的利弊得失,而且提出若干解救其弊的理论策略,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善了法律适用理论。当然,这跟1970年代以来西方法学界开始普遍关注法律推理问题的背景有关。在阿尔尼奥、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那篇著名的《法律推理的基础》文中,他们认为,法律推理问题成为近年来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界探讨的中心课题的原因有三:第一个涉及到当今法律理论的状况;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一般的科学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状况;第三个原因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具体分析。尤其是第二个原因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实践理性的复归;分析哲学和诠释学传统差异和对立的式微;科学哲学中社会和因素的纳入以及分析哲学和批判理论的接触。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使得法律理论易于独立地采取不同哲学背景的思想观点。[4]
针对传统的司法三段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德国法学家普维庭认为,经典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认为“, 这种逻辑推理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如有人认为,那种推理模式无法正确地描绘法律适用的过程,掩盖了真正的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实际上就是对大前提和生活事实进行处理和比较。甚至有些学者(如Esser) 则完全放弃了推理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要进行判决,首先要进行不受规范制约的纯粹的认知活动;然后进行第二步———依据法律规范和方法论对第一步的认知进行检验。[5] 考夫曼从解释学的视角认为,[6] “法律发现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包括着创造性的、辩证的、或许还有动议性的因素,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法官从来都不是‘仅仅依据法律’引出其裁判,而是始终以一种确定的先入之见,即由传统和情境确定的成见来形成其判断。”然而传统的形式主义却对此视而不见。针对三段论,考夫曼指出:“我们绝非能够分别独立地探求所谓法律推论的‘大前提’或‘小前提’,法律发现绝非单纯只是一种逻辑的三段论??。”拉伦茨[7]则对三段论涵摄模型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案件事实不能划属特定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尚未必导致该法效果的否定,因为同一法效果可以另一构件为根据。” 从语言学的立场,拉伦茨认为:“如果精确的审视就会发现不是事实本身被涵摄(又如何能够呢?),被涵摄的毋宁是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不过尽管如此,拉伦茨仍然坚持认为,在法条的适用上,涵摄推论模式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相比之下,凯尔森的法律适用理论颇为独特。在他看来,司法判决既是法律的创造又是法律的适用,“法院的判决永远不能由一个既存的实体法一般规范决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法院所适用这一一般规范,仿佛只是由判决的个别规范加以仿造而已。”因此,在判决内容永远不能由既存实体法规范所完全决定意义上,法官也始终是一个立法者。不过凯尔森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即认为上述“授权”是经过一个虚构的方式———法律秩序有一个间隙(gaps Lacunae) ———给法院,结果:一方面,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余地太多,另一方面,凯尔森认为这一虚构也限制了对法官的授权,尤其是这种间隙虚构公式“只具有心理学上的而不是法学上的性质”。[8]而晚年的凯尔森侧重于对规范理论的,更是提出了令人惊异的结论:逻辑三段论(Syllogismus) 并不适用于规范。[9]荷兰法学家Hage 则认为即使在简单案件上,规则适用三段论模式也不正确。[10]其实,二十世纪的实证主义法学均承认法律的未完成性(Unfertigkeit des gesetzes) 或如哈特所言规则的“空缺结构”。在此情形下,法律实证主义以为法官应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因如此,这遭到德沃金的批判并提出法律推论中规则和原则的区分问题。他认为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并且规则表达越明确,其效力也越分明;而原则则带有较大的弹性与不确定性。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分量和重要性的程度,因而带有“权衡”的性质。并且当规则和原则发生冲突时,原则的效力高于规则。更重要的是,当德沃金确认了原则等准则同样具有法的性质时,法官在裁判中就无须行使如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德沃金还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法律的语义学理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其法律推理理论进行了反驳。[11]在世界,波斯纳法官主张区分三段论的有效性和它的可靠性。“其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个别三段论的有效性,而且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三段论的功能只是表明某个推理过程是正确的而不是确定这一过程的结果的真理性。此外,不仅小前提的确定即发现事实不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且法官将规则适用于事实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种不断地对规则的重新制定。波斯纳更注重实践理性诸如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等的作用。总之在他看来“, 在法律推理上,科学方法几乎没什么用,故与科学相比,法学与神学和形而上学更为接近。”[12]
不过,在批判的热潮中,也应当看到某些法学家依然对涵摄三段论的肯定立场。除了上文提到的拉伦茨以外,德国法学家Koch 和Russmann 就回头转向———已经被一些人宣告死刑的———“古典的”方法论。Pawlowski也认为,在说明裁判理由时,不能弃置涵摄模式。但是对正确地做出裁判一事,其帮助不大。[13]Hage 自以为提出的“基于理性的逻辑”(RBL) 是“初级断言式逻辑”( FOPL) 的一种延伸,所有演绎性论辩皆可同样适用于基于理性的逻辑。[14]美国法学家Branting 也提出一个综合了“基于规则的推理”(Rule -based reasoning)和“个案推理”(Case - based reasoning) 的法律分析模型。[15]
从总体上可以说,传统的科学方法论正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法学家对传统的三段论又提出若干替代性和修补性的主张。其实,早在拉德布鲁赫就曾提出借助“事物的本质”在法的发现中架起从应然通向实然的桥梁。还有人提出一种由演绎和归纳组合而成的推理形式:类比和设证。考夫曼认为法律发现是一种使生活事实与规范相互对应,一种调适,一种同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二方面进行: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产生关联,必须符合规范。并且在此,“涵摄”的类推性格完全表露无遗。“涵摄”在此不能被理解为逻辑的三段论方法,而应理解为规范观点下对特定生活事实的筛选。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解释”: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在此基础上考夫曼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普通的概念思维的思想形式:从“事物的本质”产生的类型式思维。[16]Hage 提出的法律推理理论也颇具启发。[17]针对传统的将规则于论辩(arguments) 所产生的诸多缺陷,hage主张最好将法律规则理解为产生于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目的。然后他拓展出一种根据原则和目的推论的模式。最后将这一模式整合进一种较传统“初级断言式逻辑”更为完善更具说服力的“基于理性的逻辑”。
二、哲学上的反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上述科学三段论的重大转变必须置于更深的哲学层次上予以解释和阐明。正如朱庆育博士所论:[18]不与科学分享其本体论的法学,如何能够在方法论上有效的援引科学推论方式?倘不从包括本体论在内的整个法学理论来重新检讨法律推理问题,而一味的希望科学方法论能够支撑起法学的学术品格,那么,法学家们无论表现得如何殚精竭虑,或许都不过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式的幻觉。实际上,当今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的巨大进步已经为法学领域将科学方法论重新置于牢固的本体论框架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哲学向现代哲学迈进中,哲学家们对于“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或理解和说明的关系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一种是以卡尔纳普、纽拉特、亨普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为代表的“统一科学派”(或科学一元论)观点,大多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他们主张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的行为等社会现象作出因果说明。另一种是以德雷、P·温奇、泰勒、冯·赖特等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派”(方法二元论)的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所采用的说明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需要采用理解的方法。所以他们主张把理解和说明区别开来。他们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观点出发,把这二种概念形成的语言游戏区别开来,一种语言游戏讨论那些严格的可以观察的事件及其原因和性。另一种语言游戏说明人的行为和那些人的行为相关联的意义、意向、理由和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和规范等等,[20]他们致力于后一种语言游戏。而这种精神科学派的主要观点“与韦伯的看法很接近:社会行为具有一种”意义性“(Meaningfulness) ,它不是由观察者设想或设计的,而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行为本身;正是这种意义性使得其他人能够理解该行为。意义性与受法则支配有关;但是,理解支配某现象的法则并不等于是赋予该现象一个原因。”[21]而P·温奇竟然极端到主张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学科而是哲学学科。“这种‘理解性的社会学’(这是在德语中得到广泛使用的名称)。最近,它往往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名目之下得到倡导??。”[22]相对于这两种立场,美国哲学家罗蒂的观点也值得注意, [23]在基础认识论撤除后,罗蒂并非提出解释学来作为认识论的一个“继承主题”,作为一种活动来填充曾经由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填充过的那种文化真空。不过他同时也区别了哲学家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博学的爱好者、广泛涉猎者和各种话语间的苏格拉底式调解者所起的作用;一种是起文化监督者的作用,他知晓人人共同依据的基础。前者适于解释学,后者适于认识论。解释学立场上,谈话不以统一诸说话者的约束性模式为前提,但在谈话中彼此达成一致的希望绝不消失,只要谈话继续下去。而认识论则把达成一致的希望看作共同基础存在的征象,这一共同基础也许不为说话者所知,却把他们统一在共同的合理性之中。不过罗蒂同时也反对那种认为解释学特别适用于精神或“人的科学”,而客观化的实证的科学方法则适合于自然。罗蒂从其实用主义立场认为“情况仅仅只是,解释学只在不可公度的话语中才为人需要,以及,人需要话语,事物则不需要。”于是,解释学就不是“另一种认知方式”———作为与“说明”对立的“理解”。最好把它看成是另一种对付世界的方式。总之,西方哲学上的对科学认识论的反思和讨论其实印证了哲学家鲍曼的看法,即“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而“阐释者”的角色的隐喻则最适于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24]相应地,在法学领域,皮尔斯(Pierce)迈出了这一大步,即“从仅仅认识特征评价的亚理士多德和康德逻辑学,发展到了关联评价必须在法哲学和法律理论中才可以理解。”[25]上述哲学争论及转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哲学诠释学之为人文科学对抗传统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合法性地位日益牢固,同时也为法学尤其是法律推理理论摆脱传统科学认识论走向作为自身学科的存在论提供了重大契机。
另一方面,基于近代科学认识论上的法律实证主义在伦理学上通常坚持一种不可知论立场。法律和道德相分离的根本立场使之放逐对价值(善恶)的探求,而在法律适用的形式逻辑三段论思维模式下,法官只需做是非、真假的形式判断而绝不能做价值判断。否则即超出这一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框架和理论初衷。可以说,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严重背离乃是基于主客体二分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到后来趋于衰落的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法律和道德是否分离,而在于人的理性如何来判断伦理价值问题的对错。其实,实证主义分离命题无非是希望正本清源,维护法律本身的体系自足,防止法官专断。达到这样的目的未必非得采取这种思维进路。肯定认知者在价值问题上能够有所作为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路径。在西方法学史上这就涉及“实践理性”的问题:[26]有实践理性吗?实践理性如何作用? 通过实践理性能够得到实质性的价值命题吗?亦或只能解析价值命题之逻辑关联?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法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归”。法哲学家们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再审思,为法与道德哲学寻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27]在英国,实践理性的再发现,推动了法学家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推理、法律和道德等问题的探讨。在德国、奥地利等国,一种新的理论趋向———法律论证理论也逐渐兴起。这种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人的商谈理论或实践商谈理论(practical discourse theory)的。该理论旨在确证、道德和法律论辩。从这种意义上,它取代了古老的自然法理论。所不同的是,自然法关于道德和法律理论的实质内容在这里等而下之,而程序成了最基本的正当性根据。亦即,这些实质性命题或规范只有经过理性的商谈过程达致合意始为有效。[2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推理”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科学方法论上的用法,而是“成了一种说服或反驳对手,并根据一个决定的正当性与对手达成一致的讨论技术。”因此“,实践推理使人的动机、意图具有一种规范或一种价值的特征。”[29]
不过,如哈贝马斯指出,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强烈现代意义,以主体哲学为基础的概念。它在理论上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具有一定负面作用,所以建议以“沟通理性”来取代实践理性的地位。在其交往行动理论中,法律和道德就可以通过言说原则(diskursprinzip)加以联结。[30]哈贝马斯认为“真理”不是超验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类经验中的并且是由理性的、自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成员经过讨论和对话获得的知识。“其理论的目的仅仅是要保证理性探讨的前提,而不是要预知这一探讨的结果。”[31]所以,哈贝马斯批判德沃金理论乃一种出于独白的观点“,由于Hercules是一个孤胆之英雄,缺乏对话的层面的考量,因此其整体性最终仍将落入法官具有特权地位之认识。” [32]为摆脱这种理论困境,应将其理论导向一种商谈式程序性的法概念,探讨一个理性判决是如何作出的。这就需要一种法论证理论。[33]因此,从知识论上,法律论证理论已然摆脱了仅局限于逻辑和语义的层次,而延伸到语用学(pragmatics)的领域。[34]另外,法律论证理论更凸显出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因此,它不仅依赖于法律论据的品质,而且依赖于论证过程的结构。在解释规则时,在各种可能解释当中选取一种之后,法官尚需对其解释作出充分的说明即对其判决进行确证。而法律论证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近年来人们对法律论证可接受的标准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阿列克西认为,法律论证必须成为法学理论之根基。“论证理论并不仅限于法律领域,论证理论研究者试图拓展一种对论证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一般模式,并且这也适于特殊领域。”[35]总之,法律论证理论是在西方法学“解释学转向”以后,学者们在实践理性、商谈理论等知识基础上拓展出的法学新的领域。同时,这一研究触角兼及当今西方逻辑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
三、解释学转向背景下的法律论证初探
在法律方法伦上,无论是近代自然科学还是实证主义法学都不脱离司法三段论的思维模式。“二者对法律发展或适用的过程的理解在方法上是一致的。二者均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法体系的理念。”[36]随着近年来本体论转向后的诠释学理论和语言哲学大规模的进入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话语被深刻地改变了。其中最重要者,恐怕是解释由最初作为一种简单的方法或技艺,至此上升到法概念的本体地位, 即“诠释学的法律本体论”( hermerneutische rechts- ontologie) .在此背景下,学者主张“在敞开的体系中论证”(阿列克西) .此时,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开始普遍被区分为法律发现的脉络(context of discovery) 与确证的脉络(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37]前者关涉到发现并作出判决的过程,后者涉及对判决及其评价标准的确证。一如科学哲学上区分所谓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发现的逻辑和证明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罗素所说的熟而知之者和述而知之者。英国哲学家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提出了区别两类知识范畴的一种有用分法:知道如何 (Knowing how) 和知道是何( Knowing that)。很好地说明了发现和辩护的关系。[38]这一区分同样对于理解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论证的作用十分关键。因为它提出了评价法律论证规格的标准。判决作出的过程固然是一个精神的心理过程,但也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它也成为另一种研究的对象。无论判决是如何作出的,为使其判决能被人接受,法官必得对其法律解释予以充分阐明,由此确证其裁判的正当性。而法律论证即关系到这种确证的标准。至此传统司法三段论模型从整体上被具体化为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推论模式。这在西方法律解释思想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近代西方法哲学传统固有的关于民主和法治、合法和正当等叙事的对立和紧张,由此至少从理论上得以缓解乃至克服。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结合能够有效地克服科学与人文、理性与经验、逻辑与修辞、[39]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此类的二元对立。解释和论证的关系可以套用考夫曼关于“诠释学”与“分析学”的公式:[40]没有解释的论证是空洞的,没有论证的解释是盲目的。
相较于传统的三段论,诠释学和法律论证在新的基础上运用更为广泛的和手段,如论题学、修辞学、逻辑哲学、符号学等。法律推理过程也摆脱了那种严格、呆板、机械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而呈现为全方位、立体式和动态化的结构图式。法律诠释与法律论证对上述知识的运用也不尽一致。如关于修辞学方法,在法律论证理论产生中,修辞学是其重要思想来源。法律论证理论所注重的可接受性即取决于论辩本身对受众(Audience)所产生的效果。而修辞术是就每一事物觅出所有可能的说服方式的技能。“他既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Episteme ,也不是Techne ,而是技能Dynamis.”[41]而修辞学与解释学关系也颇为密切。加达默尔即力倡“解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说”。[42]哲学解释学在形成之际就十分关注语言,因为语言同时关系到解释学的存在论维度和实践哲学维度,而修辞学则是一种说服技能。加达默尔强调解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目的就是为了将语言中这些禀赋再度结合起来。不管这一观点能否成立,解释学和修辞学确实在不少方面有共同之处。相比之下,解释学与逻辑方法就较为悬殊。魏因贝格尔批判解释学依然是个没有完全的科学分支。它虽然已经拓展出一种类型学的推理模式(typology of models of reasoning),但没有分析不同推理过程的相关性。虽然已经确定了不少规则,但对规则在逻辑和认识上的多元性未予注意。[43]为此,他提出一些矫正意见。从解释学看,所有解释都是主张某规范具有法律上效力的言说行为,而后者又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实际上,在法学知识共同体经过长期论述已经逐步形成一套基本的、共同的概念和规则体系,此即法学中法教义学(Rechts dogmatik)的作用。若无法教义学的指引,那么法制度运作之论述将极易陷入浪漫的修辞,而无法产生合理的说服力和共识。从这种意义上,法律解释学和修辞学虽然共同有利于致力语言之自然禀赋,但法律裁判毕竟旨在达成合理和有说服力的结果。法律解释必须遵循某种逻辑的制约。在批驳三段论形式逻辑时,切不可矫枉过正。所以解释学与逻辑学还应当携手并进。当然,法学又不能仅限于法教义学的操作,“因为规范性概念之联结主要不是透过逻辑而是透过提出理由(论据)之论证来加以支持。”[44]而在法律论证理论中是否应包含逻辑,一种看法是将法律论证跟逻辑或逻辑分析区分,因为他们担心,逻辑的严格将伤及法律的适应性,妨碍法官在个案中发现公正的解决办法。不过许多论者还是肯定逻辑在论证理论中的地位。“论证理论主要源于分析学,这仍为今天几乎所有的论证理论家们所确认。”[45]如魏因贝格尔认为,作为现代法学理论的两个标志,其一是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的法律结构理论,其二是法律理性论证理论。二者都涉及将逻辑于法律的问题。逻辑论辩部分是逻辑演绎,部分是佩雷尔曼意义上的修辞论辩。[46]季卫东认为:“虽然有一些学者站在反对决定论的立场上否认法律议论(即法律论证———引注) 也具有三段论的结构,但是一般认为,既然合乎逻辑是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合理性的法律议论很难也没有必要拒绝法律三段论的帮助。实际上,在有关法律议论的新近中,人们所看到的却是三段论的复兴。当然那是按照法律议论的要求改头换面了的三段论。”[47]
不过,论证理论和解释学并不尽一致。如考夫曼曾经谈到二者的差异,“论证理论是反诠释学的??论证理论是反本体论的??论证理论并不赞同诠释学对主体-客体图式的摒弃,而是坚持客观性”。[48]当然,考夫曼也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
按照荷兰学者Feteris对当今西方法律论证研究所做的一个概览式的综括:主要涉及托尔敏的论证理论、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麦考密克的裁判确证论、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确证论以及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理论(ory of t ransformation in the law) .[49]当然,其中有些学者也涉及其他领域,如托尔敏就涉及伦。七十年代,法律论证被视为法律逻辑即一种法学方法论或法律判决的制作,而不是法律论证本来的意义。自产生后,法律论证理论获得很大发展。学者研究的具体领域涉及如立法过程、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等。法律论证一词有不同说法,Neumann 认为当今日本、德国法学界使用“法律论证”这个用语时,其含义尚未确定,但可以归为三大类:逻辑证明的理论、理性言说的理论和类观点-修辞学的构想。 [50]法律论证理论研究适用于对作出理性裁判予以确证的条件问题,而对法律论证合理性之研究具体涉及对法律判决进行理确证的方法、用于法律判决进行重构或评价的方法及其适用的合理性的标准等。法律论证理论乃法学中一门独特的学问。跟其他法教义学、法学和法哲学等研究路向不同。[51]总之,法律论证理论是一种以论证为基础的法律解释理论,其主张以事实和逻辑为论据,在主张-反驳-再反驳的“主体间”的论证过程中,通过说服和共识的达成来解决法律争议问题。因此“,法学之理性在于它的论证之理性,或具体说,在于依据理性论证的标准去考察法律论证的可能性。于是,法学的科学理论遂汇入法律论证理论之河。”[52]
[1] 当代英国哲学家Hare 对实践三段论(practical syllogism) 的界定是:由一个规范性前提与非规范性前提推出的一个规范性结论之推理。芬兰哲学家冯·赖特(G. H. von Wright) 则认为实践三段论跟意图(intentions) 和行动(actions)相关。见Robert Alexy , A Theoryof Legal A rgu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8. 荷兰法学家Hage将传统司法三段论依据的逻辑称为“初级断言式逻辑”(first order predicate logic) ,以与其主张之“基于理性的逻辑”( reason - based logic) 相区别。见Jaap C. Hage , Reasoni ng with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130。
[2] 参见[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18-19 页。
[3]参见[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 页。
[4] Aulis Aarnio ,Robert Alexy and Aleksander Peczenik , The f oundation of Legal Reasoni ng ,该文发表于德国的《法律理论》(Rechtstheorie) 12 (1981)。
[5] [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71页。
[6] [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 - 22 页;[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5 页。
[7] [德]Larenz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8 - 174 页。
[8]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 - 168 页。
[9] 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280页。颜厥安进而评价说:“Kelson的这种规范反逻辑主义并非其独创,也并非毫无问题。但是晚年Kelson规范论的作品则为法理学研究开创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规范存有论及规范逻辑,其与法学方法论及法论证论的结合更成为当前法理论界最为重要的课题。”同书,第281页。
[10] Hage , Reasoni ng with 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2。
[11]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 [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12]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55-90 页。
[13]参见[德]Larenz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46 页。
[14]前引Hage , Reasoni ng with 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158。
[15] L. Karl Branting , Reasoni ng with Rules and Precedents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16]参见[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五、六章。
[17] Hage , Reasoni ng with 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130。
[18]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哲学解释学-修辞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
[19]参见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 页;另见王巍:《 科学说明与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5期。
[20]在法学上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即是一典范。“必须用解释学或内在的观点来理解的东西就是与规范有关的行动的概念。”见[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 页。
[21] [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春、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8 - 209页。郑戈博士也曾作过这方面的理论努力。见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2] [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 页。
[23] [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七章:从认识论到解释学。
[24]参见[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5 - 6页。
[25] [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 页。
[26]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227 页。
[27] 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 年第4 期。有那么一段时期,许多哲学家似乎忽略了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然而只是到了现代逻辑和逻辑哲学兴起以后,哲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道德推理和道德以外的实践推理的关系。人们对实践推理的兴趣还因人们日益意识到它在解释人类行为的特殊性。另外,许多数学和心理学在“决策”问题的研究也是其一重要原因。参见Raz, Practical Reasoni 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
[28] 跟传统自然法不同,通过程序达致正义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重大贡献。其思想在德国也颇有。1993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已经明显意识到并重视社会多元化的事实,正义原则被限缩到只适用于康德式的个人理想社会。而越来越强调政治正义是多种合理的广泛的议论的“交叠共识”。参见何怀宏: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6 期。
[29] [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春、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20 - 421 页。
[30]颜厥安:《法效力与法解释》,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 卷第1 期。
[31][美]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 页。
[32]见颜厥安:《法效力与法解释》,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 卷第1 期。
[33]在大陆法系法学谱系中,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由于涵摄模式对法律解释学的支配,从而视论证理论“没必要”;另一方面,决断论则强调法律决定的非理性主义,从而视论证理论为“不可能”。关于决断论,见颜厥安:《规则、理性与法治》,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2 期。
[34]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即立足于人文主义立场,力图修正科学主义的传统,消解形式语义分析和实践语用分析之间的隔阂并构架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为意义和真理问题提供了一种语用学的解决路径。见郭贵春:《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 哲学研究》2001年第五期。
[35] Eveline T. Feteris , 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 6.
[36]郑永流:《法哲学是什么》,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37] 这一区分最早由Reichenbach 于1938 年提出,后来被普遍接受。见Eveline T. Feteris 上引书, p. 10 ;Alexy 前引书,p. 229 ;Maccormick and Summers , Interpreti ng Stat ute : A Comparative Study ,Dartmouth ,1991 ,pp. 16 - 17 ;另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 页。
[38]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64 - 365页;关于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的区别,另参见沈铭贤、王淼洋:《科学哲学导论》,上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 - 108 页。
[39] 在波斯纳看来,“我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说,只存在两种形式的说服方法:一方面是逻辑,它不能用于决定困难和重要的案子;而在另一方面是修辞的伎俩。并非如此。在逻辑说服同感情说服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取得合理真实的信念??这就是实践理性的领地。”见[美]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 页。这种实践理性相当于宽泛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修辞”。
[40]参见[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 页。
[41] [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8 页。
[42]张鼎国:《经典诠释与修辞》,“中国经典与诠释研讨会”(威海·2002)论文。当然,加达默尔的观点也受到哈贝马斯等人的反驳。
[43] Ota Weinberger , L aw , Instit ution and Legal Politics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p. 89. 而在西方哲学史上,“诠释学一直曾被隶属于逻辑学,成为逻辑学的一个部分。”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9 页。
[44]见颜厥安:《法效力与法解释》,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 卷第1 期。
[45]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 页。
[46] 见Weinberger , L aw , Instit ution and Legal Politics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p. 70 - 71。另外有学者以为,“法律推理逻辑的性格为实践话语领域中形式化限度的讨论,提供了极好的检验标准。”而“法理逻辑是义务逻辑支持者(卡里诺斯基,冯·赖特)和‘新修辞学’支持者(佩雷尔曼) 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地盘。”见[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春、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19 、423 页。
[4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5 - 106 页。
[48][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 页。
[49]见Eveline T. Feteris , Fundamentals of Legal A rgumentati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50]张钰光:《“法律论证”构造与程序之研究》,http :/ / datas. ncl. edu. tw。
第3篇: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范文
普通法的核心原则是遵循先例(staredecisis):曾经在一个适当案件中得到裁决的法律问题,不应在包含同样问题并属于同一管辖权的其它案件中重新加以考虑,除非情况有某种变更,证明改变法律为正当。因此,既定的法律点是有约束力的,并被作为此后案件的判决依据。类比法律推理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识别一个适当的基点即判例。普通法系中在一个特定管辖范围内最高一级法院的判决的案件具有一种特殊的基点地位,即在此管辖范围内最具权威。第二步是在确定的基点情况和一个问题情况之间识别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当一个判例的事实与一个问题案件的事实相似到要求有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就说一个判决依照判例。而当一个判例的事实不同到要求有不同的结果时,我们就说一个案件区别判例。同样案件同样判决这一理念意味着如果在某种情形下不同点更为重要,那么不同的案件应该有不同判决。一个判例应该被依照还是被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与问题案件事实相关的判例事实的细致分析。一个案件的事实由对世上发生的事的描述所构成,这些事确定了纠纷的阶段,握手当事人如何发现自己处于纠纷之中,以及在有的时候当事人曾做过什么以试图自己解决纠纷。在这一步骤中,应该收集整理问题案件中的尽可能多的事实,进而应该确定表面上相似的判例并分析它们的事实,这里同样需要对事实的把握理解。只有在上述工作完成后,你才能列出每个判例和你面临的问题案件之间在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三步是决定在某种情形下两种情况间在事实上的相同点更重要,还是不同点更重要。两种情况不可能完全一样,普通法程序只要求对重要点进行比较并判断,因此,首先要判断,哪些是重要事实,哪些不是重要事实,一个判例是被依照还被区别,取决于重要事实在两种情况下的相似度。但重要事实和非重要事实之间区分的判断,不能事先定一标准,也不取决于判例所表述的普通法规则。普通法规则是法官在那些由普通法调整的案件的判决书中宣布的规则。由普通法规则出发做出的判决,其推理是典型的演绎。在普通法中,规则产生于审判过程,通过比较事实情况来创制,并随判例的适用而改变。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院有权决定它所受理的案件,也只能决定它所受理的案件,法官无权制定权威性的一般规则以支配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的案件。因为即使法官在前例中制定了一般规则,他也不可能考虑到后来案件的情况,后来案件的当事人有权在法院中享有自己的机会。
二、演绎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不同于类比法律推理,首先,它是以规则而非案件为起点。其次,立法至上原则一般要求法官扮演一种从属于更具民主特色的政府机构的角色。第三,对制定法律规则的稳定陈述,使得从这样一些规则出发的法律推理严重关切规则的解释问题。因此演绎法律推理的步骤与类比法律推理存在重大区别,主要由以下三个阶段构成:第一步是识别一个与当前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法律规则本身描述了它所适用的案件的基本特征,在找到可用的规则之前,法官不得不先从讨论事实开始,从这里出发,寻找合用的法律规则。合用的法律规则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个规则群。这个规则群中的各个规则按一定效力秩序组合在一起。但是规则的识别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即使确定了适用的规则序列,各个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规则识别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澄清案件争议的法律焦点。第二步是以允许推断出一个有效结论的方式陈述事实。任何案件的事实都能以多种用语加以描述,关键是要确立与判决相关的事实,并用规则语言进行表述。但案件事实并不是事先包含在规则语言中的,规则甚至都不可能包含其自身的适用标准。因此,案件争议往往表现为两种貌似合法的事实陈述并存。第三步是判断重要程度。大多数语词的意义缺乏清晰性,可能具有二种或二种以上的含义,法律术语的定义本身也会因为遭遇语言问题而需要解释。在规则语言与案件事实的相关度存在争议的场合,需要对某些特殊事实的法律重要性做出判断,以便把问题案件置于一类法律案件中,并证明这一归类为正当。对重要程度的判断,要求我们超越法律规则、法律定义和其它类似表述所固有的语言问题,三段论在这种争议案件中不能保证其必然性。
第4篇: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范文
关键词:形式推理;三段论;许霆案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97-02
1 形式推理的概念明晰
博登海默使用了“分析推理”一术语,意指解决法律问题时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归纳方法和类推方法。分析推理的特征乃是法院可以获得表现为某一规则或原则的前提,尽管该规则或原则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调查事实的复杂过程必须先于该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活动中的形式推理主要是演绎推理,即著名的三段论推理。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有可疑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小前提是经过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体现在具有法律效力的针对个别行为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即判决或裁定。
2 形式推理的理论争鸣
2.1 法律推理的历史沿革
形式法律推理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第一种法律推理理论。这一理论以英国法学家J.奥斯丁开创的分析法学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以法治为基础,第一次确立了作为制度心态的法律推理的自主性。第二,在法律推理标准上,法律推理要求使用内容明确、固定的规则,追求形式正义和正当性。它把一致的使用普遍的规则看做是正义的基石,并认为只有独立于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而选择的标准或原则,其推理结论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第三,在推理方法上以逻辑推理为主导形式。这种观点认为,一切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应用明确的、不变的规则而作出决定,因此,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唯一可用的法律推理方法就是逻辑的演绎三段论。然而以弗兰克和霍姆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派拿起经验为武器对形式主义推理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霍姆斯大法官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成为这一理论最鲜明的旗帜。该理论认为,所谓的法律就是法官的行为和对法官行为的预测。法官的个性、政治因素或各种偏见对判决的影响比法律要大。现实主义法学派强调的法律只存在具体的判决之中,根本不存在法律推理所必须遵守的标准的思想。
到了新实用主义法学派,波斯纳对法律推理的“实践理性”的解释更被人们所熟悉,波斯纳充分肯定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推理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波斯纳认为形式主义的法律推理方法只有在简单案件中才起作用,对于疑难案件和一些涉及伦理问题的案件,逻辑推理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在对立的主张中哪一个是正确的,这一问题需要实践理性的方法来承担。实践理性是人们用以作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
之后以哈特、拉兹、麦考密克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再次兴起,哈特认为虽然语言所表达的法律规则具有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特点,并且,语言本身的含义随同在不同的中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确定的语境中会有相同的理解,那么,人们就有必要遵循这些规则,而不是以法律规则的模糊性为借口规避法律的要求。拉兹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普遍存在着,在不存在着适用任何法律规则的义务的情况下,法官的行为是不可捉摸的,将会导致极端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法律将成为一种绝对的自由裁量系统。”,麦考密克将法律推理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法律推理,即演绎推理;第二层次的法律推理,即实践理性的推理。
2.2 被抛弃的“三段论”
在关于法律的实质推理研究中,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备受关注,但多数是批判之声。这其中包含着对形式逻辑的轻蔑,即使是被称为法律论证的研究,形式逻辑所强调的论证方式也基本被抛到一边,人们都忙着在形式法律之外探寻法律。三段论一直是批评的靶子。但批来批去,遂形成了一种轻形式逻辑的思潮。
笔者认为即使演绎推理存在缺陷,但抛弃形式推理的观念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坚持形式推理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陈金钊教授说过:“在中国语境下,我们的法治刚刚起步,人们对法治的信念还没完全树立起来,这时候采取挖祖坟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的法治进程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的想法是严格法治治而不是放纵‘活’法横行,不是丢掉基本的法律思维方式去搞范式转换,而是把严格法治当成主旋律,把‘活’法当成严格法治的特例来处理,即在一般情况下反对过度解释,多数情形下应用推理而不是本体论的诠释。试想,法官的判断行为如果不是取决于推理,而是取决于各自的“自由”选择,那么我们在哪里还能看到法治的影子。
其次,形式推理是法律推理最基本的形式。形式推理从推理形式上保证了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它是人们从众多的思维现象中总结出普遍适用性的思维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法律推理也不例外,否则,就有可能违背逻辑思维规律,而思维形式的错误必然会导致整个法律推理的无效,即使是霍姆斯也相信在多数案件中可以用简单的演绎推理对案件做出裁决,法律思维离不开形式逻辑作为思维的基础。麦考密克直言某种形式的演绎推理是法律推理的核心所在。形式推理,尤其是“三段论”作为法律推理的基石,一旦被我们抛弃,我们能否像极端的现实主义法学那样去实践,或像部分法社会学者那样去构建无需法律的秩序,或像自然法学那样把希望都寄托给“自然”的正义?
再次,形式推理能满足人们对法律推理明确性、必然性和一致性的要求。法律的规范作用在于人们能够根据法律规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效果作出明确的预测,并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基础之一是同样的案件有同样的判决,即判决的一致性。霍姆斯提出的“预测理论(坏人理论)”,强调了认识法律“一定要从一个坏人的角度来看法律,……因为坏人只关心他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能使他预见的实质性后果……。”笔者认为尽管霍姆斯强烈了批判了形式推理,但从“预测理论”看来,一个“坏人”如果不是通过认识法律,并且参照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能得出行为的后果呢?
最后,形式推理有助于保证执法公正。形式逻辑是作为平等、公正执法的重要工具而起作用,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法官擅断。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是从一个模糊地形成的结论出发,然后试图找到将证明这一结论的前提。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可能不是按照证成、法律寻找、解释、规则适用、评价、阐述这样的思维路线运行的,而可能是从结论到前提的反向运动。法官与律师不同,法官应遵循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活动规律,从规则出发,将它们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结论。
形式推理,具体到三段论作为一种常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并不存在着对与错的问题。在法律思维活动中,由三段论运用所练成的思维形式只是思维的工具。从推理的有效性来说,形式推理保证了推理的形式有效性,形式有效为推理结果有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 是非功过――形式推理的实证分析
3.1 成也萧何――形式推理维护司法判决
2008年的许霆案引发了法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在许霆案两次判决前后,从专家到民众进行了激烈得辩论。许霆案中的法律推理如下:
推理一:大前提――法律规则:凡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就是盗窃罪
小前提――法律事实: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了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结论一判决结果:许霆犯了盗窃罪。
推理二:大前提:“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
小前提:ATM机中的款项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
结论:许霆犯了金融盗窃罪。
推理三:大前提:凡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小前提: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ATM机,数额特别巨大
结论:许霆应当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重新审理,多出了推理四。
推理四:大前提: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小前提:许霆案存在特殊情况,银行明显存在过错且违法程度和责任程度较轻,
结论: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
在两次审理中,法官均严格遵循了演绎三段论这一证明式推理与论证的模式。无论我们赞扬其坚持法治的原则,或贬斥其明哲保身和机械法治,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的确满足了一种严格限制于法律体制内部进行论证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许霆案最终以盗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非仅仅是无期徒刑和无罪的妥协,其得到相对多数民众认可和许霆本人的服从应该归功于演绎推理三段论的严格论证。
3.2 败也萧何――形式推理留下了法学界的迷失
许霆案爆发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在同一刑法的框架下,面对无可争议的事实,进行的演绎推理为何能有如此大的争议。形式推理是推理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推理有效的充分条件。形式推理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具体到许霆案而言,即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造成这个的原因诸如(1)语言自身的不确定性;(2)法律本身概括性所产生的模糊、间隙和隔阂;(3)法律的滞后性等。
为何推理四一开始并未出现,形式推理并没有给出答案。法定刑以下量刑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这项权力也未被轻易开启。对于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基层法院法官选择了“忽视”,他们倾向于在自己的权力内推理,因为这是最为安全的策略。正义如同一张普罗透斯的脸,因为个案变化无常。严谨形式推理无法将其刻画定型。悲观地讲,下级法院法官的最优且通常的决策只能是预测并实现上级法院法官的正义。
4 结语
形式推理,尤其是三段论本身对于我国法治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形式推理基于这种认定制定法律完整无缺、法律和事实严格对应、法官如同“自动售货机”的法治观念,来看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法律神话”。加之形式推理本身始终无法解决前提的真实性这一困扰。固然形式推理仍然有着诸多的缺陷,在疑难案件中,如何在法治统一和个案正义中实现平衡,我们需要实质推理。但有了缺陷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坚持形式推理的地位不动摇,对于我国这一成文法国家仍然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张传新.论法律推理[J].法律方法(第一卷),2002.
[3]李桂林,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陈金钊.推理与解释:寓于其中的法律思维[J].政法论丛,2005,(06).
第5篇: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范文
【关 键 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 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博弈、难题求解和智能机器人;70年代开始研究语言理解和专家系统。1971年费根鲍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学家系统”之后,“计算机数学家”、“计算机医生”等系统相继诞生。在其他领域专家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师提出了研制“法律诊断”系统和律师系统的可能性。(注:Simon Chalton,Legal Diagnostics,Computers and Law,No.25,August 1980.pp.13-15.Bryan Niblett,Expert 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p.2.)
1970年Buchanan & Headrick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拉开了对法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认为,理解、模拟法律论证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许多知识领域进行艰难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规则和论证等几种知识类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识,其中处理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难题。其次,要了解如何运用各种知识进行推理,包括分别运用规则、判例和假设的推理,以及混合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审判实践中法律推理运用的实际过程,如审判程序的运行,规则的适用,事实的辩论等等。最后,如何将它们最终运用于编制能执行法律推理和辩论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区别和不同的案件,预测并规避对手的辩护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设等等。(注:Buchanan & Headrick,Some Speculation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23 StanfordLaw 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沿着两条途径前进:一是基于规则模拟归纳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二是模拟法律分析,寻求在模型与以前贮存的基础数据之间建立实际联系,并仅依这种关联的相似性而得出结论。Jeffrey Meld-man 1977年开发了计算机辅助法律分析系统,它以律师推理为模拟对象,试图识别与案件事实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考虑到律师分析案件既用归纳推理又用演绎推理,程序对两者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包括了各种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专家系统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研究者探索将其当作法律适用的实践工具,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责任案件的赔偿价值,并论证了如何模拟法律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注:'Models of LegalDecisionmaking Report',R-2717-ICJ(1981).)
我国专家系统的研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注: 钱学森教授:《论法治系统工程的任务与》(《管理》1981年第4期)、《主义和法治学与技术》(《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和法制建设》(《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章,为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发起了思想解放和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七五”研究课题,它在建立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数据库开发方面,1993年中山大学学生胡钊、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师办公自动化系统》。(注:杨建广、骆梅芬编著:《法治系统工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页。)1993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主持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注:赵廷光等著:《实用刑法专家系统用户手册》,北京新概念软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询检索系统、辅助定性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组成,具有检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
专家系统与以往的“通用难题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它要解决复杂的实际,而不是规则简单的游戏或数学定理证明问题;(2)它面向更加专门的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域,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表达和运用特殊的知识,而不强调与问题的特殊性无关的普适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专家系统在法规和判例的辅助检索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师一部分脑力劳动。但绝大多数专家系统只能做法律数据的检索工作,缺乏应有的推理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进入了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开发时期。知识工程是指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以能在机上表达和运用知识的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知识型系统的设计、构造和维护的一门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注:《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知识工程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几个推理定律再加上强大的计算机就会产生专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识工程为技术手段的法律系统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获得突破,将会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法律实践自身的要求。随着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实践需要新的思维工具,否则,法律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法承受法律日积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负。其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的全部思维活动为目标,但又必须以具体思维活动一城一池的攻克为过程。它需要通过对不同思维领域的征服,来证明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精确描述并制造出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此外,人工智能选择法律领域寻求突破,还有下述原因:(1)尽管法律推理十分复杂,但它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案件)、相对明确的前提(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及严格的程序规则,且须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这为人工智能模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法律推理特别是抗辩制审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确的规则、理性的标准、充分的辩论,为观察思维活动的轨迹提供了可以记录和回放的样本。(3)法律知识长期的积累、完备的档案,为模拟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4)法律活动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精神,对法律程序和假设进行检验的传统,为模拟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条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价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方法论启示。P.Wahlgren说:“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创造性方法上的法反思。这个信仰反映了法理学可以被视为旨在于开发法律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动。从法理学的观点看,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方法论的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开展从法理学观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探讨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非常细致的技术方面。”(注:P.Wahlgren,Automation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模拟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学家通过与工人智能专家的密切合作,可以从其对法律推理的独特理解中获得有关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例如,由于很少有两个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实践中,总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运用假设来分析已有判例与现实案件的相关性程度。但法学家们在假设的性质问题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设计者,在无真实判例或真实判例不能充分解释现实案件的情况下,以假设的反例来反驳对方的观点,用补充、删减和改变事实的机械论方法来生成假设。这种用人工智能方法来处理假设的办法,就使复杂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假设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论证产生于一个经过修正的老的论证的过程。总之,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法学家跳出法理学方法的思维定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法学问题,从而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是提供了思想实验手段。西蒙认为,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思维在头脑中是怎样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们知道这些处理在数字机中是由电子作用完成的。给计算机编程序使之思维,已经证明有可能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认为:“通过编制有关思维活动的程序,就会加深对思维活动具体细节的了解,并将这种程序送进计算机运行,检验其正确性。这是一种思想实验,有助于我们研究人脑思维的机理。”(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系统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获取、表达和法律知识,软件工程师为模拟法律推理而编制程序,必须先对人的推理过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和的独特解释。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拟开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结构之前,首先从功能上对法律证成、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动进行数理,将法、诉讼法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实现法律推理知识的机器表达或再现,从而为认识法律推理的过程和提供了一种实验手段。法学家则可以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推理过程、方法和结论与人类法律推理活动相对照,为法律推理的法理学研究所借鉴。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法律推理,深化了人们对法律推理性质、要素和过程的认识,使法学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的敏锐透镜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ryan Niblett教授说:“一个成功的专家系统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径对法理学作出更多的(理论)贡献。”(注:Bryan Niblett,Expert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note14,p.3.)
三是辅助司法审判。按照格雷的观点,法律专家系统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国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烟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没有计算机编纂、分类、查询,这种法律制度简直就无法运转了。(注:Pamela N.Gray Brookfield,Artificial Legal 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 Co.,1997.p.402.)其实不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师和法官往往也要为检索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由于人脑的知识和记忆能力有限,还存在着检索不全面、记忆不准确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强大的记忆和检索功能,可以弥补人类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帮助律师和法官从事相对简单的法律检索工作,从而极大地解放律师和法官的脑力劳动,使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更加复杂的法律推理活动。
四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推理虽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法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个体,所以在执行统一标准时会产生一些差异的结果。司法解释所具有的建构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如果换了钢铁之躯的机器,这种由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这当然不是说让计算机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说,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推理标准和评价标准,从而可以辅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贯性的判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物质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像计算机录取增强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电子监视器提高了纠正行车违章的公正性一样,智能法律系统在庭审中的运用有可能减少某些徇私舞弊现象。
五是辅助法律和培训。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凝聚了法律家的专门知识和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如果通过软件系统或计算机实现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训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学院教学中发挥模拟法庭的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专业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知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模拟的审判实践,从而较快地提高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2)帮助新律师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迅速获得判案经验,在审判过程的跟踪检测和判决结论的动态校正中增长知识和才干,较快地接近或达到专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律师和法官及时获得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建议,弥补因知识结构差异和判案经验多寡而可能出现的失误。(4)可以为大众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六是辅助立法活动。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对辅助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完善立法也具有实用价值。(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of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伦敦大学Imperial学院的逻辑程序组将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形式化,帮助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在预见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The Yale 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辅助系统如能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有可能事先发现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个法律内部各种规则之间以及新法律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
三、法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想来源
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之法理学思想来源的追踪,不是对法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所产生的一些直接。
第一,法律形式主义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的法律形式主义强调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认为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以J·奥斯汀为代表的英国法学的传统,主张“法律推理应该依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解决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假如法律能如此运作,那么无论谁作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注:(美)史蒂文·J·伯顿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页。)换言之,机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逻辑,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样的判决结果。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与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注:朱景文主编:《对西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页。)如果法官违反三段论推理的逻辑,就会破坏法治。这种机械论的法律推理观,反映了分析法学要求法官不以个人价值观干扰法律推理活动的主张。但是,它同时具有忽视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学家比埃利希将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推理说称为“自动售货机”理论。然而,从人工智能就是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的意义上说,法律形式主义对法律推理所作的机械论解释,恰恰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实际过程来看,在其起步阶段,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法律形式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前提,首先选择三段论演绎推理进行模拟,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被机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机器法律推理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
第二,法律现实主义推动智能模拟深入到主体的思维结构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推理主体的性。法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所从事的法律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其社会体验和思维结构的影响。法官在实际的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机械地遵循规则,特别是在遇到复杂案件时,往往需要作出某种价值选择。而一旦面对价值,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决定论便立刻陷入困境,显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点。法律现实主义对其僵化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页。)的格言。这里所谓逻辑,就是指法律形式主义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一定的道德和理论、公共政策及直觉知识,甚至法官的偏见。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强调,促使人工智能研究从模拟法律推理的外在逻辑形式进一步转向探求法官的内在思维结构。人们开始考虑,如果思维结构对法官的推理活动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若要达到法官水平,就应该通过建立思维结构模型来设计机器的运行结构。TAXMAN的设计就借鉴了这一思想,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协调程序、说明程序分别对网络结构中的输入和输出信息进行动态结构调整,从而适应了知识整合的需要。大规模知识系统的KBS(Knowledge Based System)开发也注意了思维结构的整合作用,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小规模KBS子系统,在分别模拟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证成、法律查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评价、理由阐述)的基础上,又通过联想程序被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体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
第三,“开放结构”的概念打开了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拟的思路。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疑难案件的存在。疑难案件的特征表现为法律规则和案件之间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对应关系。有时候从一个法律规则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它们往往没有明显的对错之分;有时一个案件面对着几个相似的法律规则。在这些情况下,形式主义推理说都一筹莫展。但是,法律现实主义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否认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存在,试图用“行动中的法律”完全代替法学“本本中的法律”。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是使法律推理摆脱机械论束缚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现实主义法学所说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具体判决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标准或因人而异,那么,受到挑战的就不仅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且还会殃及法治要求实现规则统治之根本原则,并动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存在的基础。哈特在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争论中采取了一种折中立场,他既承认逻辑的局限性又强调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预感来随意判案的见解,又承认直觉的存在。这种折中立场在哈特“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律概念既有“意义核心”又有“开放结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法官发现的阳面,而根据政策、价值和后果对规则进行解释则有助于发现问题的阴面。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规则的法律推理模拟在受到概念封闭性的限制而对疑难案件无能为力时,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过逻辑程序工具和联想技术而建立起来。Gardner博士就疑难案件提出两种解决策略:一是将简易问题从疑难问题中筛选出来,运用基于规则的技术来解决;二是将疑难问题同“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联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识如规则、控辩双方的陈述、常识来获得初步答案,再运用范例来澄清案件、检查答案的正确性。
第四,目的法学促进了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目的法学是指一种所谓直接实现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他们认为,以法治为标志的自治型法,过分强调手段或程序的正当性,有把手段当作目的的倾向。这说明法治社会并没有反映人类关于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因为实质正义不是经过人们直接追求而实现的,而是通过追求形式正义而间接获得的。因此他们提出以回应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张。在回应型法中,“目的为评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地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制度屈从的危险。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美国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对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前者要求使用明确、固定的规则,无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不能适应复杂情况和变化,追求形式正义;后者则要求放松对法律推理标准的严格限制,允许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抽象标准,迫使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追求实质正义。与此相应,佩雷尔曼提出了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法律。他认为,形式逻辑只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对问题加以说明或论证的技术,属于手段的逻辑;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可以帮助法官论证其决定和选择,因而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他认为,在司法三段论思想支配下,法学的任务是将全部法律系统化并作为阐释法律的大前提,“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就成为对法律的三个要求。而新修辞学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示下履行义务,必须考虑哪些价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公平的”。这些价值构成了判决的正当理由。(注:沈宗灵著:《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页。)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统最终需要解决价值推理的模拟问题,否则,就难以实现为判决提供正当理由的要求。为此,P.Wahlgren提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5种知识表达途径中,明确地包括了以道义为基础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引入道义逻辑,或者说在机器中采用基于某种道义逻辑的推理程序,强调目的价值,也许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统的关键。不过,即使把道义逻辑硬塞给机,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生理需要,也很难产生价值观念和主观体验,没办法解决主观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为由对法律家对法律的机械忠诚表示了强烈怀疑,并辩证地将其视为法律的动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够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发现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价值。因此,关于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拟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2.法对人工智能系统研制的指导作用
Gold and Susskind指出:“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专家系统必须适应一些法理学理论,因为一切法律专家系统都需要提出关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质的假设。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专家系统都必须体现一种结构理论和法律的个性,一种法律规范理论,一种描述法律的理论,一种法律推理理论”。(注:Gold and Susskind,ExpertSystems in Law:A Jurisprudential and Formal 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不仅需要以法理学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为知识基础,还需要从法理学获得关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论,如法律推理实践和理论的,法律推理的标准、主体、过程、等等。人工智能对法律推理的模拟,主要是对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知识进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机程序,从而在智能机器上再现人类法律推理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学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成果。
随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从低级向高级目标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认识不足已成为人工智能模拟的严重障碍。P.Wahlgren指出,“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开发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许多潜在的法理学原则没有在系统开发的开始阶段被遵守或给予有效的注意。”“法理学对法律推理和方法论的关注已经有几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诞生只是本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情,这个事实是人工智能通过考察法理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一个有效动机。”(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动化的目标,“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过把计算机的应用与模型相结合)来支撑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应用法理学理论来解决作为法律推理支撑系统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问题。”(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充当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的问题。后一方面,则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学研究成果直接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所应用的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法理学在真实和假设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为几种人工智能法律装置借鉴而成为其设计工作的理论基础。在运用模糊或开放结构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法律解释的形式化等问题上,法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已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所借鉴。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难点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它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一,关于法律解释的模拟。在法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释的研究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起着关键作用。法律知识表达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法律规范在一个法律论点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实原意和适合当时案件的原则通过法律解释予以确认的,其中包含着人类特有的价值和目的考虑,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识表达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德沃金将解释过程看作是一种结合了法律知识、信息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能够应变的思维策略。(注:Dworkin,Taking Rights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的法律专家系统并未以知识表达为目的来解释法律,而是将法律整齐地“码放”在计算机记忆系统中仅供一般检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识工程系统中,法律知识必须被解释,以满足自动推理对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建构的需要。麦卡锡说:“在开发智能信息系统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任务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专家意见的重建,而是建立有关法律领域的概念模型。”(注:McCarty,Intelligent legalinformation systems:problems and 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须以法律家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识为基础,但不同的法律家对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策略。凯尔森甚至说:即使在国内法领域也难以形成一个“能够用来叙述一定法律共同体的实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尽管如此,法理学还是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认为,法官在“解释”阶段,要通过推理论证,为自己在“前解释”阶段所确定的大多数法官对模糊法律规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总的理由”。获取这些总的理由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则,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这种法律原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证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则为依据反向推出具体的法律结论,即用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某一法律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该法律原则来解释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统装置已吸收了这种方法,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使计算机根据案件事实来执行某条法律规则,并在新案件事实输入时对法律规则作出新的解释后才加以调用。不过,法律知识表达的进展还依赖于法律解释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第二,关于启发式程序。的专家系统如果不能与启发式程序接口,不能运用判断性知识进行推理,只通过规则反馈来提供简单解释,就谈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启发式程序要解决智能机器如何模拟法律家推理的直觉性、经验性以及推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即人可以有效地处理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在必要时作出猜测和假设,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活性。在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 L.Rissland运用联想程序对规则和判例推理的结果作集合处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学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将启发式程序于系统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人工智能模拟法律推理的一个难题。选择哪一个答案,往往取决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标准和推理主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但智能机器没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机器法律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第三,关于法律语言理解。在设计基于规则的程序时,设计者必须假定整套规则没有意义不明和冲突,程序必须消灭这些问题而使规则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法律概念的含义可以争论不休,但输入机器的法律语言却不能互相矛盾。机器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规则来模拟严格责任并实际损害时,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确的自然语言进行推理。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法律家对某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可根据上下文关系作多种解释,而且辩论双方总是寻求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智能法律专家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语言理解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学的一个程序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语言的理解问题,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是连法学家们自己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专业术语规范。所以Edwina L.Rissland认为,常识知识、意图和信仰类知识的模拟化,以及自然语言理解的模拟问题,迄今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对于语言模拟来说,像交际短语和短语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会在较窄的语境条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拟、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模拟则距离非常遥远,而像书面上诉意见的理解则是永远的终极幻想。(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证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从检验标准上看,这主要是法律知识在机器中再现的判定问题。根据“图灵试验”原理,我们可将该检验标准概括如下:设两间隔开的屋子,一间坐着一位法律家,另一间“坐着”一台智能机器。一个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机器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如果提问者不能从二者的回答中区分出谁是法律家、谁是机器,就不能怀疑机器具有法律知识表达的能力。
依“图灵试验”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统检验标准,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机器和法律家解决同样法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个是钢铁结构、哪个是血肉之躯。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础,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实现之功能模拟。
从功能模拟的观点来确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策略,可作以下考虑:
第一,扩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主体。现有人工法律系统的幼稚,暴露了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从事系统研发工作的局限性。因此,应该确立以法律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三结合的研发群体。在系统研发初期,可组成由法学家、逻辑与认知专家、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为主体的课题组,制定系统研发的整体战略和分阶段实施的研发规划。在系统研发中期,应通过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级产品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意见,使研发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形成反馈,将开发精英与广大用户的智慧结合起来,互相启发、群策群力,推动系统迅速升级。
第二,确定与相结合、以应用为主导的研发策略。国外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领域,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统包括相对简单的软件系统,如果不经过用户的长期使用和反馈,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将初期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产品,我们也难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必须走产研结合的道路,坚持以应用开路,使智能法律系统尽快走出实验室,同时以研究为先导,促进不断更新升级。
第三,系统研发目标与初级产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是制造出能够满足多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学家)多种需要的机型。初级产品的定位应考虑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别是价值推理的功能远远超过机器,但人的记忆功能、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又远不如机器。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有12万律师,23万检察官和21万法官,每年1.2万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初级产品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与机厂商合作生产具有强大数据库功能的硬件,并确保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网上及时更新;同时编制以案件为引导的高速检索软件。系统开发的先期目标应确定为:(1)替律师起草仅供的起诉书和辩护词;(2)替法官起草仅供参考的判决书;(3)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模拟法庭审判的通用系统软件,以辅助学生在起诉、辩护和审判等诉讼的不同阶段巩固所学知识、获得审判经验。上述软件旨在提供一个初级平台,先解决有无和急需,再不断收集用户反馈意见,逐步改进完善。
第四,实验室研发应确定较高的起点或跟踪战略。国外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开发已经历了如下阶段:(1)主要适用于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2)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3)运用判例和假设的推理;(4)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们如确定以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为初级市场产品,那么,实验室中第二代产品开发就应瞄准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同时,跟踪运用假设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国外先进的KBS和HYPO的设计思想,将功能子系统开发与联想式控制系统结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装置具有如下功能:(1)评价相关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贴切;(3)并区分判例;(4)建立假设并用假设来推理;(5)为一种主张引用各种类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证概要。HYPO以商业秘密法的判例推理为模拟对象,假设了完全自动化的法律推理过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来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许多要素的存在,如商业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虑,法律概念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开,被告是否使用了对方设计的产品,是否签署了让与协议,等等。一个系统设计的要素列表无论多长,好律师也总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样,律师对案件的分析,不可能仅限于商业秘密法判例,还可能援引侵权法或专利法的判例,这决定了起诉缘由的多种可能性。Ashley还讨论了判例法推理模拟的其他困难: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样本,因此,要通过要素等简单的法律术语使模糊的法律规则得到澄清十分困难,法律原则和类推推理之间的关系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这说明,即使具有较高起点的实验室基础研究,也不宜确定过高的目标。因为,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水平。
第五,人-机系统解决方案。人和机器在解决法律时各有所长。人的优点是能作价值推理,使法律问题的解决适应的变化发展,从而具有灵活性。机器的长处是记忆和检索功能强,可以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一贯性。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立足于人与机器的功能互补,目的是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为主,机器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决策参考。律师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机器处理大批数据,并参考机器的起诉和辩护方案,再做更加高级的推证工作。法官接触一个新案件,或新法官刚接触审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机器法官”的判决建议或者审判思路,作为参考。法院的监督部门可参照机器法官的判决,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某种监督,如二者的判决结果差别太大,可以审查一下法官的判决理由。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司法腐败。在人-机系统开发的第二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简单案件的判决与电脑推理结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简单案件可以机器为主进行审判,例如,美国小额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国法庭可用简易程序来审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为“产品检验员”监督和修订机器的判决结果。这样,法官的判案效率将大大提高,法官队伍也可借此“消肿”,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第6篇: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范文
关键词:法律的实践理性;法官职业化;法学教育;法官培训模式
在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各级法院对法官培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培训的实际效果却令人扼腕。反思这种现象,是对职业化建设过程中的法官培训目标定位不准,对于职业法官培训的教育理念、模式、方法与法学院教育的本质差别缺乏明确的把握的结果。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初,立足于中国法官来源大众化的实际,将法官培训的目标确定为完成法律学历教育或法学知识培养,采用法学院教育模式是十分英明而且正确的。但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今天,继续沿用“法律业大”式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却是有问题的。笔者以为,以职业化为理想的法官培训,必须以实践理性的养成为目标,建立符合实践理性培养规律的法官培训系统。
一、法律的双重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
法律与理性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有法学家断言:“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1]由此表明,法律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他掌握了法律。“今天的现实与人类产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人类的产生只不过是世界又多了另一种动物,这种动物也许既不懂哲学也不懂玄学,但却拥有一定的法则。”[2]今天,法律之所以被认为既是约束人类兽性与暴力的“枷锁”,又是彰显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花环,正因为“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存在。”①如果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必须以空气和阳光等为生存的条件,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则是以法律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人性中的恣意、贪婪、自私等缺陷无法通过道德说教予以规训乃至改造,只能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予以刚性的遏制;法的内容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秩序,回应着世俗生活的需要;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始终具有权威依赖性,离不开对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依赖。因此,服从法律的规则治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3]
由此可见,法律理性是一种世俗的实践智慧。[7]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首先是人类实践理性的要求,因而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法的这种实践理性血统决定了它是“行动而不是设计的产物”,由此也规定了法的第一重身份,即作为实践理性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现代法律制度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浸透人类的智慧,法律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一部法律作为纯粹知识体系的形成和传播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同时还具有作为纯粹理性的知识身份。②法律在知识谱系上的二元性,决定了法律人的任务也必须是双重的。前者使其必须不断的认识社会生活运作的新要求,从而将社会生活贴切的翻译成制度语言。后者决定了其在对法律制度进行以实践为标准的价值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对已有法律知识体系的梳理和整合,以实现法律作为纯粹知识的传播和继承的要求。正是因为法律的双重理性,才出现了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出现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分工。
法官是一个将普遍、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职业,是典型的法律家,其最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完成法律从知识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转化:把条文的法律转化为生活的法律,把抽象的法律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把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转化为诉讼技术和程序。这个职业本身要求法官既要掌握充分的法律知识,能够熟练的运用法律的概念、原则和理论;又要良好实践智识,能够自如的将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转化成为“法言法语”并做出裁判。在此意义上,法官成长的基础是法律的知识理性;但仅有知识理性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践理性。
近年来,我们对国外的法学教育和法官培养机制有了充分的了解,介绍性的、研究性的成果已经有许多,这些论著对于国外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官教育的形式、内容、特点都做过充分的阐述,不乏精辟之作。我以为,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与法学教育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官的培养从法学院开始,目标在于养成预备法律人的法律双重理性。①
我们知道,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中,由于历史与传统而形成了两类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在实践中它们也呈现着不同的外观:一类是以欧洲大陆对罗马法的普遍继受、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大陆法系成文法理性,其以法学家阶层理论架构和学术主张为主,强调法的一般性、抽象性、系统性、万全性,认为可在概念化原则支配下实施]绎推理机制。另一类是被认为“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5]”的普通法理性,在英美法系中,没有法律学术化和法典化的研究传统,学者们对于法律的分类以及体系化没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找不到一丝精心分类的迹象,正如萨尔蒙德所言:普通法是一个“最能容忍混乱(tootolerantofchaos)的法系”,[6]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据信是因为英美法发展的内在机制,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其实践目的是为了使争执获得解决。
对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学者们做过许多的评价与比较。我以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同品格的产生来自于其内在逻辑性,均是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保证法律有效和公正实施的理性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哪种品格的法律理性的形成,法学家和法律家的工作都是紧密相连的:在大陆法系中,从概念法学创立到今天的各种法学流派与理论,法学家们都在为司法提供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与法律适用的工具、技术和方法,预备法律人通过学习,可以充分理解法学家构筑的法律理性,准确的适用由法学家用概念和逻辑家精心构筑的法典,成为“自动售货机”②式的法律家;在英美法系中,法学理论不产生于主流哲学家或法学家,而产生于长期积累的司法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而发展成的完善理性,[7]因此,许多法官本身就是伟大的法学家,他们兼具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身份,这样的法学理论对于司法实践的作用不言而喻,预备法律人也是以司法实践培训的方式理解法律理性。至此,我们看到,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共存于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工作之中,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更进一步,我们还发现两大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与他们的法律理性形成模式直接相关,与之相联系的法官培训模式也是由此而决定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将英美法系的法学教育称之为职业指向明确的模式,将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喻为通识性的模式,而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短期的知识更新为主、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较长期的系统的司法技术学习与实践为主,莫不是为适应两大法系不同的法律理性传统而建立的。③因为,他们坚信:“不论哪个时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各种阐释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力量。”[8]
由此反观我国的法学理论、法学教育、司法实践,在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割裂、法学院教育与法官教育脱节、预备法律人学习与法律职业精神的养成无关。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第一,我国的法官培训是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与美国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类似;但是,我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并不具有像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第二,我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同属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职前训练”,这种在大学中进行的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9]这就表明:无论是我们的法学院教育还是法官培训,都忽视了法律实践理性对于法律人的意义。法学院不考虑法院的需要,法院不考虑法学院教育的特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法律实践理性的认识不足。
以上还只是考察了接受过法学院教育的预备法律人进入法官队伍的状态,至少他们已经具备了较系统的法律知识理性,缺乏的仅仅是法律的实践理性。而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大多数人并不是来自于法学院。来源的大众化使得法官队伍的文化素质背景差异巨大、法律知识严重不足,处于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缺乏状态。正如肖杨院长在分析法官队伍现状时所指出的:“我们法官队伍比较缺少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10]虽然近二十年来,全国法院系统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特别是通过“法律业大”方式,基本完成了在职法官的法律学历教育,最近三年,又通过对一定年龄以上的法官采取专项培训方式,完成了部分法官的法官资格确认。不可否认,“法律业大”作为一种应急式的教育模式,虽然对于中国法官队伍建设乃至中国法治建设意义巨大,但它对于法官的法律知识理性培养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法律业大”式教育最多只能缓解在职法官法律知识欠缺状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的法律理性养成问题。所以,“法律业大”的存在必然是阶段性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法官均来源于法学院,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背景,即使法学院没有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在司法实践中也会较悟法律的实践理性并加以总结。经过一批又一批法官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法官思维、法律方法、司法技术并加以传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学院教育的不足,为新入门法官提供一定的法律实践理性基础,也可以为法学院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促进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的沟通,加速法律实践理性的形成,使法学院课堂上的声音与法庭上的声音逐渐趋向一致。但是,中国法官来源的大众化,客观上加剧了中国法律实践理性形成的困难:法院既不能为预备法律人提供司法经验与技术资源,也不能为法学院提供立足于司法实践的理论研究资源。在这种情形下,法学院与法院、法学教授与法官“各唱各的调”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法学院教育模式还是法官队伍状况,都决定了必须将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措施,并不能仅仅只在法院系统内部或者是在法官队伍中寻找。
二、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职业化
早在17世纪初,英国首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为反对英王詹姆斯一世插手司法,与国王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詹姆斯一世说:“依朕意,法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故尔朕及他人与法官具有同样的理性。”柯克法官回答:“不错,陛下具备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常识。但是陛下并没有研读英格兰领地的各种法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所有物或金钱等诉讼的决定,不是根据自然理性,而是根据有关法的技术理性(artificslreason)和判断。对法的这种认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art)。”[11]这段对话被认为是将法律实践理性的概括为技术理性的起源。①学者们对法律的实践理性提出了各种观点。一般认为,实践理性是人们在共同交往的活动中形成的以共同经验、共同理论为基础的指导行为的相同的或类似的理解与共识;狭义的实践理性侧重于群体的实践经验,认为具有共同经验背景的群体,同时具有共同的或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和理解结构。[12]也有人认为实践理性是一种方法或方法论。[13]
事实上,实践理性是指人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首先表明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同时还表明存在着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标准。[17]法官培训实际上是对这种评价标准的灌输或传授,以实现对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评价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此意义上的法律实践理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思维理性与行为理性。[15]而这两者恰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或基础。
1.思维理性。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人的基本特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的思维能力不仅促进了自身发展,而且形成了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行业。不同行业的人在实践中又形成各具特色的行业传统和规范,不同的行业技能和行为方式。其中有一些行业经过长期的实践,不仅技术和技巧日臻完善,而且逐步形成了高度抽象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不仅是一种理性,更是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评价标准——一般的思维规则,正是由于一般思维规则的存在,一些行业才成为了职业。在此意义上,思维理性是职业形成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相互区别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标志。正如波斯纳所言:“职业是这样的一种工作,人们认为它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般的‘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因此,经济学是一个职业,而商业不是,理由是你无须掌握一套抽象的知识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却不能如此。木匠也不是一个职业;尽管其所涉及的训练要比商人更为专门,但是它并不要求有很高程度的智识训练,没有能否胜任的问题。”[16]
法律思维就是这样一种由法律人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基于法律理性的视角和传统来观察社会现象、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或习惯。法官是典型的法律人,其基于法官职业视角和传统的法律思维我将其称之为法官思维。法官思维是法律思维中的一种,它是指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针对具体讼争案件,按照司法认知规律,认定案件事实,寻找适用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和技术解决法律纠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过程。[17]
法官思维首先是一种职业思维,是法官在履行法官职责过程中的工作方式,因而具备法官思维能力是法官从事司法裁判工作基本要求。
其次,法官思维的对象是具体讼争案件,司法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法官思维的对象只能是具体案件,离开具体案件,法官思维不具任何实质意义,其思维结果亦不具任何法律拘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官思维必然不同于以探索法律一般规律为目的的法学家思维,也不同于以制定法律规范为目标的立法者思维。“如果对法律职业者思维方式作细致划分,律师、检察官思维与法官思维具有一定区别。律师、检察官一方当事人,其思维特点是攻击、防御。原告人攻击,被告人用法律技巧防御;而法官居中立地位,他要比较攻、防的理由作出判断。因此,法律职业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官,法律思维的最典型形态是法官思维。”[18]
第三,法官思维涵盖审判的整个过程。法官思维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方式,更是一种实践技术,存在于解决法律纠纷的各个环节,从程序问题到实体问题,从事实问题到法律问题,从法律方法到司法技术,从开庭审理到文书制作,从司法理念到具体操作,都是法官思维的具体化。
我们必须承认,思维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个体特征,不可避免地要体现作为思维主体的个人的主观个性,即思维者的自我意识,如个人的嗜好、习性、直觉、偏好(甚至偏见)等主观、非理性的东西,或多或少地体现思维个体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这些不同的存在是正常的,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在存在个体思维差异的情况下,要形成社会秩序,首先需要具有差异的思维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商谈”,在反复的“沟通”与“商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思维理性——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或普遍的标准。因此,思维理性是一种群体性思维,是职业特性和职业传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个体形成共同知识背景、共同职业语言和共同职业伦理的过程。
法官思维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性思维,是法官形成共同知识背景、共同职业语言和共同职业伦理的过程。法官职业表明,法官的智慧不仅要体现于个案的裁判结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司法裁判的全过程中保持法律思维的活力和张力。因此,法官不仅是一个法律实务操作的技术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解决疑难问题的智慧者。法官对社会和法律的认知和理解是建立在独立判断基础之上的,思维理性保证了法官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草率了事;但却能做到“同样问题同样对待”,维护法律的确定性,能够通过个体化的思维作出正确的法律判断和英明的裁判决策,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所有的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都要依赖自己的一般认识能力和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所以。公民的行为与法律职业者的工作都是以他们对法律以及通过法律可能到达的目的的认识为前提的,都依赖理智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行为才可能是理智的,才可能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19]
司法认知活动表明,法官要想将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个案,至少要同时完成两种逻辑思考: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对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和价值追问,这是一个将“形而上”的思考与“形而下”思考结合的过程。只有在完成这两种思考的结合之后,法官才可能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与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之间进行逻辑涵摄,然后依据司法推理规则,得出案件处理的结论。这是法官审判案件的基本思维过程。对于一些法律规范不明确或根本缺乏法律规范以及存在法律冲突的案件,法官的思维过程则更加复杂。待这些思维活动完成后,法官还要通过书面形式将其思维过程以裁判文书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最终的裁判结果。法官思维过程的曲折性和思维内容的复杂性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决定了法官的审判活动必须形成共同的、科学的认知模式,并遵循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以避免法官思维因巨大的个体差异所导致“同样案件不同处理”的结果,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同时,也可以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少走或不走弯路,工作思路顺畅,思维结论正确,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和思维理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思维理性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官培训最重要的任务。
2.行为理性。“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伦理品质;相应地,法律从业者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其职业实践、志业担当和天职践履,从应然与实然两方面而言,都应当是或已经是法律理性的落实与体现。因而,正像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形式、法律语言等等是法律理性的逻辑外化,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与世俗信仰,作为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理性的内化,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20]如果说法官的思维理性仅仅存在于法官头脑中,是一种内在的素质,那么,这种内在的东西需要有外在的表现形式——法官的行为。行为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体现着行为人的意志和理性程度,法官思维指引下的行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法律实践理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为理性。行为理性是思维理性的外化形式,也是法官具体的工作内容,没有行为理性,法律的实践理性是不完整的。
行为理性是指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对于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运用。法律方法表现为法官思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司法认知,而司法技术则表现为法官思维在实践论意义上的司法操作,它们指向的是同一问题。如法律解释,我们既可以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法律方法,也可以从实践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司法技术。由此表明,当我们谈论某一法律方法时,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某一司法技术。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对于法官的意义,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清楚,法律是普遍性规则,“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规定性和明确性而使法官能够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对有关条款妄加解释。依此种观点,宪法只是一个空瓶子,法官可以任意地倒进任何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为‘反复出现的噩梦’。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令人不寒而栗的。”[21]审判活动不是赌博,可以仅凭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法律的含义或案件的裁决。事实上,也绝对没有人认同法官采用这种方式或方法来裁判案件。人们凭什么相信法官?法官获得权威和尊重的前提在于他们具有法律理性,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了解决法律问题的专门方法和技术。因此,法官是否掌握了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决定了法官的裁判行为是否具备理性。对专门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运用,成为法官职业化的外在标志——专职从事司法活动,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或自治性。
行为理性对于法官的工作,至关重要。“法官基于职业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学者更能具体地、直接地了解现行法律中的问题,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内,通过技术化的方法平息纠纷,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使社会平稳发展。”[22]法官也只有采用共同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才能够实现司法公正。就司法实践而言,法官的行为理性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23]
第一,程序的遵守。法律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具有反思性整合的功能。[27]这四种功能对于审判都是十分重要的。从第一方面看,诉讼程序作为恣意的限制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诉讼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而明确其权利(权力)义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从而减少恣意发生的余地,实际上是对诉讼中公民绝对权利和国家绝对权力的一种限制。从第二个方面看,诉讼程序通过其固定化的处理流程,将当事人对不确定结果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对确定过程的关注,并以结果的拘束力来巩固这一选择的确定性,增强了审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从第三个方面看,公正化的程序通过其类似过滤装置的设置,将审判中的出现的各种情况通过法律程序的沉淀和反馈,而最终为成为未来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事实状况,使法律不断低成本的渗入现实生活。从最后一个方面看,诉讼程序实际上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通过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反复交涉,在“反思性整合”的基础上形成法律决议,既可以发挥诉讼程序的灵活性,解决形式法功能之缺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程序法定,防止和消除因司法的过度自由化而导致的法律过度开放和确定性消弥的危险。正如威廉·道格拉斯所言:“权利法案中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25]因此,人们将法官对程序规则的严格遵守,称之为理性选择的基本保证。
第二,法律方法与司法技能的运用。法律方法是法律人司法经验总结和积累的结晶,它不仅是法律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官担任该职业的基本要求。法律方法既包括理性内容,又包括具体技能;如果说法律方法中的理性内容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法学理论修养有直接关系,那么它的技能部分则需要长期的职业训练才能把握。法学院的普通教育、法官的专门培训、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都是法官获得和掌握法律方法的一个基本过程。“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技术的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26]法律方法对于法官而言,犹如手工业者的技艺,是立身、取胜之本。因此,法官能够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自觉地、熟练地运用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来处理案件,既是法官行为理性的表现,也是案件得以公正处理的重要保障。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一文中,对中国和西方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之所以自晚清以来一直落后于西方,结症在司法这一环节的缺失。[27]与此观点相映证,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英国近代史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模式;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向市场经济,与英国法律尤其是司法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环境是分不开的。[28]而司法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则是法官的职业化。法律人从实践经验中发展了赋予法律普遍性的独特推理技术和发现法律的方法,把法律发展成为自治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必须经过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学识化艺术与技巧,而这不仅为法律职业、尤其是司法独立及排除外来干涉提供了合理性要求和基础,并且为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因为这表明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不是来源于国家强权,而是来源于司法自身的品质,来源于法律人的学识、地位和荣誉。[2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官职业化是司法制度发挥社会功能的前提,而法律实践理性是法官职业化的内在要求,是法官职业品质的基本内涵。将其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三、法律实践理性与法官培养方式改革
通过以上的初步理解,不难发现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与法官培养的关系:法官思维作为一种群体理性需要传授与灌输,法律方法与司法技能作为一种实践经验需要积累、传承与培训,换句话说,法律的实践理性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由此,我们再来认识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制度与法官培训制度就没有了那么多的不解与疑问,法学院的高起点、长学制也好,学徒式教育、国家统一考试也罢,都是因为法律实践人才需要具有法律双重理性的学习与训练。而各国的法官培训模式无不与法学教育模式紧密相连,目的无一不是为了解决法律实践者的双重法律理性养成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以知识理性为主兼顾实践理性基础,法官培训选择了以培养拟任法官或在职法官的实践理性为主的模式,如日本、德国、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以实践理性或者职业指向教育为主,法官培训模式则相应的以法官法律知识更新与实践理性的发展为基本内容。我们考察国外法官培训体制、制度与方式,不能仅仅只看到法官培训本身,还必须将其与该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法学院教育模式结合起来,才能发现个中缘由和必然性。我们的借鉴也只有在全局的[光下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但在我国,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法学家与法官、法学院与法院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法学家将法律理论变成了握在手中把玩的藏品或者是不知所云的玄学,醉心于纯而又纯的理论架构与宏大叙事的论述,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严重脱节;法学家潜心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不断在创造新的法律概念、法学理论,却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实际调研过案件,有的甚至不知道实际的司法程序,不清楚法官的思维与教授思维存在的差异,不知道法官的工作状态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法学院的教育仅仅是法律知识的灌输和法学家的思维方式,教给学生的东西基本上与司法实践无关,或者仅仅是对司法实践隔靴瘙痒式的批评。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加之我国过去的法官来源大众化的背景,法庭上和教室里所进行的各种理论阐释大相径庭,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这种状态长期存在,将会使法律失去力量!可以说,中国法官法律实践理性培养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法官职业化的诸多困难,由于法官们都是“自学成才”,缺乏共同的司法理念、共同的职业价值、共同的职业道德、共同的职业技能、共同的职业行为是必然的结果。
种种迹象表明:各方面都在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并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着努力: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法学家们开始了法律方法的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法学理论对司法的影响,一些法学教授开始进入法院做法官,等等,都是这些努力的实际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双重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明确定位,没有对法官这种典型的法律职业者法律素养构成的清醒认识,有些努力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如统一司法考试,考试的内容及方式基本上还在法律知识理性的范围内,对法律实践理性或者法官思维的内容很少涉及;因此,从统一司法考试合格到职业法官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有些已经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不一定能够成为称职的法官。法学家们开始高度关注司法领域的各种问题,但却很少深入司法实践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更多是坐而论道,提出的批评多、指责多,借鉴或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多,提出立足于中国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少,以解决司法实践问题为目的的研究成果对于司法实践的帮助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
至此,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法律理性的形成具有大陆法系的传统,法学院教育基本上也沿袭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以法律知识理性的传授为主,法律的实践理性的培养主要不是由法学院完成。但是,中国却又没有建立起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法官培养模式,如日本的司法研修所、法国的法官培训学院那样系统的培养法律从业者的法律实践理性的教育制度,于是,法律实践理性从哪里获得,在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中找不到答案。如果我们承认,职业法官必须具备法律的双重理性,而这种理性又不可能先天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养成,那么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制度予以跟进,在法学院法律知识理性教育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法律实践理性教育。如果说,中国有建立专门的法官培训体系的必要,以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是支持它的最充分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在中国特有的法学理论研究传统、法学家与司法实践隔绝的情况下,学生在法学院学习中,基本上得不到法律实践理性的信息,使得学生对于法律的理解单一、机械、片面,只是概念、原则、制度、部门、体系的罗列,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毫无关联。本来是为弥补这一不足设计了实习课程,但因为短学制①而使实践课程的数量有限,再加上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法律实习形同虚设,把学生十分可怜的一点接触司法实践的机会也挤占了。学生进入法院时对于法律的实践理性基本一无所知,需要靠自己的悟性,逐步摸索,积累经验,因人而异,因案而殊,“同样问题同样处理”几乎是一句笑话。
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现状,就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而言,有一些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如何建立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相互衔接的法律实践理性培养机制;二是法官的实践理性培训采取何种教育方式,伸言之,法学院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是否应与法官培训完全相同?如果不同,它应该是怎样的?三是需要由什么样的教师来完成法官实践理性的培训。说到底,依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基本问题——大学、大师、大作。
就建立法律实践理性的培养机制而言,必须有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首先,必须对现在的法学院教育模式与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增加法律方法、司法技术与法律实践的课程,使法律预备人在法律知识理性的养成过程中,不仅能够初步了解法律的实践理性,而且能够感悟法律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其次,必须对现行的法官培训模式进行改革,彻底改变临时性、应急性、知识性培训的思路;对现行的法官培训内容进行改革,摒弃完成任务、追求数量、流于形式的培训计划,真正按照职业法官司法能力结构的要求,制定与法学院教育相互衔接的教学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设定培训课程、决定培训方法。为此,需要对统一司法考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论证,进一步提高司法考试对于法律实践人才选拔的合理性。我以为,要使司法考试真正成为选拔优秀预备法律人的“大考场”,必须充分考虑法律家职业所需要的双重法律理性。司法考试理应成为连接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桥梁和纽带。
就教学方法而言,同样存在着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衔接与配合。有人会说,法律实践理性也需要灌输,需要以一定的方法让学习者接受,因此,也少不了课堂讲授、论文习作等知识性的教学方法,这也是预备法律人在接受法学院教育时已经熟悉的教学方法。我以为这种说法并无大错,只是不够细致与深入。我们已经知道,法律的实践理性可以区分为思维理性和行为理性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便不难发现两种理性的养成应该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说思维理性更多的应采取类似于法学院的课堂教学方式,那么,行为理性则应有与法学院教学基本不同的方式,主要为情景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实际操作式教学。或者可以这样描述:法学院与法官培训学院都设有模拟法庭,法学院设模拟法庭主要是为了给学生以感性认识,让学生知道法庭的形式与基本程序,因此,学院里的模拟法庭更象是在“]戏”;而法官培训学院设模拟法庭则是为了给学生以理性认知,让学生在这里学习实际的操作与应用,使他们进入法院后能够应用这些技术处理案件,所以,法官培训学院里的模拟法庭更多的是“实战]习”。
就教学内容而言,法律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对于法学院教育和法官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需要有对法律理性深刻认知的理论成果支撑与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这对于法学家与法律家都提出了挑战,过去的隔绝与对立必须打破。法学家应从丰富的法律实践中获得知识理性的原始材料,更多的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方法与法律技术,为法律家提供可资实践的理论支持;法律家则应将法律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总结,从法律的知识理性中获得创造的源泉与动力,并为法学家提供可以上升为理论的实践基础。如果没有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司法应用理论研究的共同发展,没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一批能够胜任法律双重理性教学任务的教师,要完成法律双重理性培养的任务是渺无希望的。
法官培训是需要教师的,我并不完全赞成法官培训必须法官教法官说法,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因为教育是有规律的,也是一门职业,并非好法官就一定是好教师。现在的问题是,法学院有大量的精通法学教育规律的教师但缺乏司法实践经验,而法院有大量经验丰富的法官却不懂教学规律与方法。为此,应该采取双向选择的方法来解决,一方面将法学院中教师通过各种方式选派到法院任职或者挂职,使他们在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司法实践经验,既有利于他们利用法学理论研究专长准确的适用法律,提升审判水平与质量,也有利于他们迅速形成应用性法学研究成果、丰富和充实法学院与法官培训的教学内容,还有利于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衔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可以成为法官培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法官中选拔一批既有法学理论功底、又有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进行专门的教学法训练,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与能力,使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对自己司法实践经验的理论性总结,还能够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大家。只有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才能完成法官双重法律理性培养的任务,实现法官职业化的目标。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专门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法律是经验之谈,是人生法则。法律为成年人所制定,也要求成年人所践行,必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要求大众化、通俗化。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告诉人们为人处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此,法律必须生活化、世俗化。法律只规定人们能做到的,不要勉为其难,远离人们生活的法律必然为人们所离弃。法律的智慧不是玄思妙想,而是深入浅出。因此,法律要极度高明,但更要中庸;要穷极思辨,但也不能远离日用常行;要求真,但更要寓俗。法律要大智若愚,法律要平易近人。[30]“法律理性表现出求稳、求妥、求衡平的职业色彩,而类如法官这样的法律公民,一如法律本身,势必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强烈的现实性等职业‘特征’。也正因为此,法律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教导预备法律公民按照法律理性来进行思考的实践。”[31]我们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来重新认识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关系、重新认识各自的特征与规律、重新构建符合法律理性的教育模式与培训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官培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法官培训真正成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与保障。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文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19.
[2][美]约翰·梅西·赞恩(中文版)[M].法律的故事,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5.
[3]刘武俊.假若人类失去法律[N].法制日报,2000-9-10.
[7][31]许章润.法律理性:一种世俗的实践智慧[N].法制日报,2003-1-9.
[5]Maine.EarlyLawandCustom[M].1861.389.
[6]JohnSalmond.Jurispudence(10thed)[M].1777.505.
[7]周沂林.默示权力与司法理性:马歇尔如何审判美国银行案[EB/OL].中国私法
[8][美]德沃金.法律帝国(中文版)[M].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82.
[9]张志铭.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A].信春鹰.公法(第三卷)[C].法律出版社,2001.
[10]倪寿明.法官职业化任重而道远[N].人民法院报,2002-7-16.
[11][27][2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15-19、3.
[12][17]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7、97.
[13][16][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文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1、77-75.
[15][17][23][30]王纳新.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M].法律出版社,2005.290、67、302、299.
[18]郑成良.法律思维是一种职业的思考方法[A].葛洪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1)[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7.
[19]葛洪义.法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J].法学研究,2001,(2).
[20]许章润.论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EB/OL].西北政法学院网络与信息中心[21][美]JamesE.Bond.审判的艺术(中文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
[22]李楯.法官培训与司法改革[A].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86.
[26]苏力.送法下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
[27]贺卫方,魏甫华.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A].葛洪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3.
- 上一篇:施工单位投资控制措施范文
- 下一篇:家庭经营的概念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