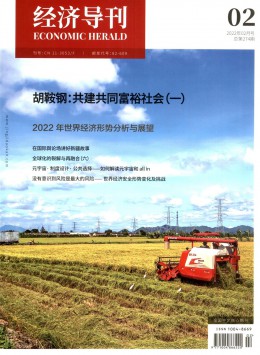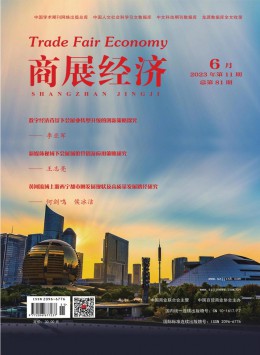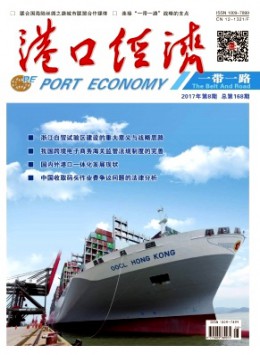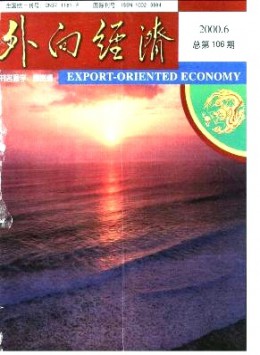经济增长要素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增长要素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第2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关键词:林业要素林业经济增长概况与对策
一、林业要素投入的基本概况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了北方一些地区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部门加强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对林业要素的投入。
1.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在林业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资源。至林业产业发展的中期,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林业的可控能力变强,所需的人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赖人力转变为“半人工半自动化”的现代林业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极度适用于现代林业的发展需求。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其节省的劳动力自由流向社会中更缺乏劳动资源的其他产业,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劳动力方面的优化条件。对于林业经济来说,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也代表着林业产业中科技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林业科技进步的一种体现。
2.产业管理方式的变化
经过不断的发展,林业的经济管理系统不断完善并趋于现代化,同时林业的产业总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随着国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林业产业的总产值在持续增长,通过这种增长变化,传统的林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化林业生产的基本需求。经过现代新型林业管理模式的革新,当代的林业工程建设更加趋于科学化管理,林业的发展也能够按照科学的阶段规划逐渐推进,完成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需求。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带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林业产业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体现。
3.林业面积增加的变化
随着林业产业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国的林业产业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业的公益行为也为我国的造林面积增长贡献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等,市场上的经济型企业对于我国林业发展的无私帮助,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植被面积,对我国的环境绿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近年来的合理规划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国的经济性林业产业不断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森林植被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西北地区的戈壁与沙漠,其植树造林的作用更加明显,近年来西北沙漠地带发展的红杉产业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北沙漠中红杉能够有效的实现防风固沙,同时能够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础性的强化作用,这也是林业为我国实现“绿色增土”的阶段性胜利。
二、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1.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林业产业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林业产业的资金储备是其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发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门保持对林业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应对林业产业的融资渠道也合理的放宽,以吸引民间资金流入,这样能为民间资本进入林业产业提供基础性的助力。民间资本的流入能使社会更加重视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林业经济带来一定的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林业企业也要有实质上的帮扶,例如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等,这也是提升林业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更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调控的优化整合。
2.强化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
林业企事业单位应该加强对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培养创新型林业人才,对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术予以淘汰。在林业经济发展中,科技是企业进步的象征,也是企业在市场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基本核心,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科研技术创新力度,科研部门应对林业产业给予一定的帮助。林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国土环境和生态保护,国家要对此产业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项目扶持,对在林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与人才国家应予以鼓励及资助,政府与企业应积极的将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实现其科研技术的生产价值。
第3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积累;结构变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17-04 收稿日期:2009-05-11
一、引言
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长率由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9.8%(1978~2007),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3%。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是否有可持续性?对这些问题,结构主义和古典主义观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结构主义观点从产业结构转移、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等方面追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古典主义(还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下省略)观点认为要素积累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促进生产率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因而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结果。吕铁(2002)采用1980年~1997年全国及各地区的制造业样本数据经转移一份额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劳动投入并没有明显地向生产率高增长的行业转移,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尽管存在但并不明显。王德文、王美艳、陈兰(2004)以辽宁省560家工业企业1991年~2001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来观察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企业效率和劳动配置的影响,其结论表明,中国工业结构越来越符合我们的资源状况和要素禀赋,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不断发挥,即结构变动促进了生产率增长。李小平、卢现祥(2007)通过扩展的shin-share方法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在1985年~2003年间的结构转移与生产率增长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南于在制造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并没有向高生产率的行业流动,因而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结构红利假说”现象。李小平、陈勇(2007)实证检验了1998年-2004年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Verdoorn效应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总贡献较小。干春晖、郑若谷(2009)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1978年~2007年期间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在此期间日趋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比较平缓,中国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内部的要素流动产生的进步效应。
与结构主义观点不同,关于经济增长的古典主义理论假设经济活动在竞争均衡的条件下发生,部门间要素的边际收益相同,因此部门间生产要素的转移不能够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据此,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部门间的要素流动被认为相对不重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出我国1979年~200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我国1979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较低,仅为9.46%,而要素投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90.54%。汤向俊(2006)首先在生产函数中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计算表明中国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83;引人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后分析表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仍高达0.67。郑京海、胡鞍钢(2008)对中国1978年~2005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观察到了在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总体下降趋势,资本的平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3.13个百分点,资本投入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67%。
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动因的古典主义、结构主义二分法显得过于绝对。其中。古典主义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确实发生了;而结构主义观点忽视要素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也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相悖,如对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成因的分析就认为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积累和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之一(林直道,1995)。实际上,推动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可能涵括了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全部主要要素,即要素积累和要素转移推动的结构转变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只不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类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力有所不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案例而言,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在产出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实证来分析。
二、要素积累、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
1 数据选择与处理
实证分析的样本区间为1979年~2007年,共28个样本,数据见表1。应变量为当年GDP(y),选择物质资本存量(k)、就业人数(f)、劳动力流动(cf)、物质资本流动(ck)和对外贸易出口年增量(e)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过程为,将基年定为1978年,选用徐现祥等(2007)的估算结果即6054亿元,以当年资本形成总额为当年资本积累增量;以当年资本增量与上年资本存量之和为当年资本存量,不考虑折旧;以当年年底就业人数为劳动力变量;劳动力流动变量为当年由第一产业转移出去的就业人数,即当年在非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村人口,计算方法为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剔除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而农村经济活动人口数为农村总人口乘以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于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工业化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反映资本结构变动的变量选择为第二产业当年新增资本积累,数据选自干春晖(2009)计算的中国第二产业资本存量;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将当年出口变量也纳入模型,所有变量值均剔除了价格因素。为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除特殊说明外,各相关基础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建立模型时数据稳定性的要求,对所有变量作了取对数处理,分别得到ly、ly、ll、lcl、lck、le。
2 参数估计
(1)增长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要素积累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我们采取了逐步回归的策略,即将要素积累变量和结构变动
变量逐步纳入回归模型。以上述策略先后得到4个回归方程,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只包含要素积累变量的基础上,每一次纳入新的结构变量均较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这表明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要素积累因素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表现出对产出增长的很大影响作用,回归方程1表明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分别拉动产出增长O,73和0,57个百分点;纳入结构变量后,回归方程3、4均表明物质资本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下降至0,47,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更大幅下降至0,04~0,06。回归方程3显示劳动力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一产业劳动力转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产出增长0,28个百分点,这个影响力在所有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中仅次于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回归方程4显示资本积累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为0,015。
回归分析表明,在综合考虑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和外部需求因素的情况下。要素积累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63%。特别是物质资本积累贡献了产出增长的61%,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外部需求拉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位重要因素。当前来看,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还较小,不过劳动力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略小于物质资本积累而稍大于对外贸易出口对产出增长的弹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为负,成为制约产出增长的因素;计算期内,劳动力转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为12%,资本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因此综合来看,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0%。
(2)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虽然能够在总体上了解各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何种影响,但由于回归分析得来的参数是静态的值,因而不能反映各因素发挥影响作用的动态过程。为了理解这一动态过程,需要得到动态的参数,因此需要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要素积累特别是物质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第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增长的弹性在过去30年中变化很大,由改革开放前期的显著影响转变至近期几乎为零,这表明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可能即将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作出改变;第三,劳动力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但近期其影响力增长开始趋缓,这显示了当前因劳动力结构变动产生的效率改进已经达到一个极限,劳动力结构变动有待进一步优化;第四,资本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为负,究其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中资本积累过度扩张且过于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内部的某些部门,而没有流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和部门。
对发达国家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这些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积累因素对增长的贡献约为30%~40%,资了改革开放以来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动态影响,其中svl、sv2、sv3、sv4分别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变量对产}H的弹性。从图1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对产flJ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出逐期增长之势,但自从2000年以来增长的势头已趋缓,不过仍是影响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投入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较显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明显的下降,长期来看影n向力呈下降趋势,至近期已接近为零。资本结构变动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中表现出促进产出增长的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发生转变,不仅促进产出增长的力度迅速下降,而且转变至制约产出增长。相反,劳动力结构变动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产出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但1992年之后表现出较快的增长,直至近年转为相对平稳,因而长期来看呈现为上升势态。本、劳动力转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20%(Chenery et al,1968;Chenery,1970;Robinson,1971)。但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检验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的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很小,因为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60%以上,而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合计仅为10%,特别是资本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甚至为负数。这确实表明当今发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曾经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折在中国迄今远未完成,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还是通过粗放型增长方式得以实现的,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也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要素积累方面转向要素结构变动方面,结构变动因素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索积累因素仍是重要的一方面)。不过,为了这一增长途径的顺利实现,推动资本、劳动力结构变动的优化为当务之急。
第4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投入产出
作者简介:王沙沙,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周勇,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3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3-92-03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于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1]其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安排、经济结构、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
投入产出模型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基本思想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投入产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投入产出表;二是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两者密不可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由于投入产出表反映了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由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状况、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把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是投入产出模型应用的一个新发展。
一般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多用“索罗余值”法、Malmquist方法等方法。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见。李斌(2003)基于投入产出的行模型 X=(I-A)-1Y, 认为总产出的变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部分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另一部分由技术进步解释, 并据此测算了全国1995-199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2];李景华(2007)应用投入产出行模型 X=AX+Y, 采用国家统计局的1987年和1995年以1990年当年价格作为基期的可比价基础价格的30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1995年间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胡振华(1995)在研究和实际编制企业劳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测度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4]。而用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几乎没有。本文应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从中间流量矩阵出发,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的设计与解释
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的基本关系:
AX+Y=X(1)
其中,表示总产出列向量,表示最终使用列向量,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的元素a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产品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量,将aij称为第j部门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它反映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第j部门与第i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又将直接消耗系数称为技术系数、投入系数,用它可度量全要素生产率。
由(1)式可以推导得到:
(2)
其中,(I-A)-1称为列昂惕夫逆系数矩阵,也称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通常记为B 。该矩阵中的元素b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部门产品的完全需要量,这里既包括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又包括对最终产品本身的需求,即对总产品的完全需要。
用B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下面式子中1,0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
(3)
可见,总产出的增量X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项为B1Y,可视为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的总产出的增加;第二项为BY0,可看作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引起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增长。
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视为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生产技术联系是通过矩阵A,即直接消耗系数来建立的,并且通过计算B来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间接联系。在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中,A除了受生产技术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到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因此,若能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则不同时期的A所反映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从而BY0代表的便是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A的影响之后,通过(3)式,我们知道BY0表示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令, ,则W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n表示第n个经济部门)。
(4)
λ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
λ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与《2007 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原始数据。由于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针对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收集到1997-2007年间上述部门的价格指数对《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以1997年为基期的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针对部门构成的影响,我们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基准,将1997年、2007年两张表中的部门均调整为相对应的30个部门,并对调整所涉及的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处理,达到尽量消除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影响的目的。
(二)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与贡献率
通过(3)、(4)式对处理后的数据计算,我们得到表1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23个部门带来正影响,其余的7个部门带来负的影响。这个实证结果基本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使一些部门的产出率提高了,也使另一些部门的产出率下降了,并且正影响的部门数多于负影响的部门数。
表1 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之所以会出现部分经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广义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为负值,是由于(3)式是由投入产出行模型(1)式推导出来的,投入产出行模型侧重于经济部门 i(i=1,2,…,n)作为产出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对于投入产出表的中间产品矩阵来说,每一个经济部门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产出部门也是投入部门),而经济部门 i(i=1,2,…,n)分别作为产出部门与投入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往往具有反向的作用(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A的反向变动来反映的)。因此,如何综合考虑经济部门的双重身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作用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根据(5)式,计算得到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为57.93%。在《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中测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7.13%,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的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这也与新疆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
四、结论
本文考虑部门之间的完全消耗关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分解方法、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新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实证研究,利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7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考虑价格因素和部门构成因素的影响,对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得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57.93%。综合分析,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新疆经济的实际状况。
参考文献:
[1] 王沙沙.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企业导报,2012,(22).
[2] 李斌.基于投入产出表对技术进步的测算方法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2).
第5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空间计量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2-0019-10;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决定产业结构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地区所拥有的各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某一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改善,会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如果一个地区或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得不到改善,则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使其偏离发展阶段的最优结构状态,经济增长趋于缓慢。新结构经济学中把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认定为最重要的变量[1]。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要素禀赋的界定范围所包含的要素不断增多,由起初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本,逐渐加入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新结构经济学指出基础设施也应属于经济的禀赋的一种,产业升级要伴随其相应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否则会产生x-低效率,而使得产业偏离其同时期最优的产业结构[2]。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需要通过各省份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来实现。而一些地区选择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或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有所忽视,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
本文建立要素禀赋结构指标体系,通过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的全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并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以研究地区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与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不同时间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结果证明,随着时间点的推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阻碍因素是不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趋向于复杂化和高级化。
二、文献综述
对于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早期集中在对外贸易、专业分工方面,后逐渐转向国内产业与经济增长方面。鞠建东、林毅夫、王勇[3](2004)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贸易结构的决定在于要素禀赋与技术比较优势。徐康宁,王剑[4](2006)以要素禀赋及地理因素为视角,通过双边贸易引力模型,证明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共同决定了新型国际的贸易格局。刘修岩、何玉梅[5](2011)通过我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分析要素禀赋与产业空间集聚的关系。而覃成林[6](2011)、李超[7](2011)等研究了黄河流域要素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指出要素禀赋不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分异。徐春华[8](2011)通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三者关系,证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决定产业、贸易结构的升级。张纪[9](2013)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要素禀赋,分析产业内分工的动因。2012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全面阐述了要素禀赋和禀赋结构的最新定义,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吴勇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要素成本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10]
关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巴拉萨[11](Balassa,1981)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说明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国家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贸易出口,但是随着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加、技术创新等使得比较优势增加,会推动整个经济体的产业不断升级。在我国,以林毅夫(2003)、孙希芳[12]、李永军[13](2003)等学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战略,认为经济发展要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内生于决定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来实现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业转变,同时在外部冲击下,产业政策的取向必须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减少金融风险。林毅夫、陈斌开[14]、刘培林[15]研究了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城市化、收入差距以及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经济因素影响。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2012)中指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地区或国家比其他地区表现要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Anselin[16](1988)认为空间单元之间存在相关性,必须在估计过程中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进而更有效地进行复杂经济系统的计量分析。在我国,林光平[17](200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78-2002年我国28个省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进行了测度,发现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吴玉鸣[18](2004)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表明各地区之间存在经济空间依赖型。潘文卿[19](2012)研究了1988-2009年我国各省人均GDP空间分布情况,发现省际人均GDP相关性越来越明显,且地区经济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增长问题,并认为短期可变要素禀赋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禀赋、科技禀赋,还应考虑基础设施和制度影响。其中制度禀赋的测度方面,相比较以往大多数使用的财政支出规模作为测度标准,以衡量地区是否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技术选择指数(TCI)作为测度指标更准确。本文把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与发展战略同时作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发展战略选择关系到地区要素配置效率以及科技创新性,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升级,需要合理的发展战略进行战略定位与引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逐渐成为主要经济调控手段,市场外部性问题增多,这需要地区不断完善自身要素禀赋结构,以保证地区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化发展。
三、变量测度
(一)要素禀赋测度
在要素禀赋指标建立方面,结合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理论,引入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方面的禀赋类别,由于本文研究禀赋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而自然禀赋在中短期处于相对静态,因而没有涉及。各禀赋指标测度方法如下:
1.物质资本禀赋。由于流动资本很难测度,本文通过永续盘存法[20],对1990-2011年间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计算,计算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各省人均资本存量,作为物质资本禀赋的测度标准。
2.劳动力禀赋。从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两方面对劳动力禀赋进行测度。借鉴何枫和陈荣[20]的方法,通过计算年初从业人数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值作为年劳动力投入量。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方面,通过年均受教育年限,引用国内广泛认同的Psaeharopoulos (2004)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数据,设定小学教育阶段回报率为0.18,中学教育阶段为0.134,高等教育阶段为0.151,以此计算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3.技术禀赋。技术禀赋可以从科研投入、科研产出、科研规模三方面进行测度,但由于全国各省级相关统计数据不全,现用万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职工数作为技术禀赋的测度标准,因为该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地区科研投入、产出和规模。
(二)基础设施测度
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多以研究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来研究其经济的外溢效应。基础设施越完备的地区其投资环境越优越,本文把基础设施作为投资环境禀赋。基础设施通过外溢效应,起到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劳动力及技术传播、联通和扩张地区市场、促进地区经济集聚等作用,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基础设施的测度方面,本文借鉴刘生龙、胡鞍钢[21](2010)的方法,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三个核心设施的量化计算对基础设施进行测度。交通基础设施的测度,加总铁路、公路两大基础设施长度除以各省国土面积;能源基础设施以人均能源消费总量为标准;信息基础设施以各地区邮电业务总量为标准。
(三)发展战略选择测度
通过技术选择指数[1](TCI)对地区发展战略进行测度。一个地区的制度决定该地区产业发展是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是否以市场为基础制度。如果地区产业发展不能与同一时期本身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相符合,那么TCI将比其他情况更高。因为如果违背比较优势,忽视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对于其他情况下由于垄断价格导致的垄断利润,同时政府提供补贴贷款和优惠政策以降低扶持产业的运营成本,使得增加值上升,但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没有显著提高,导致TCI计算公式中分子变大,TCI值增加。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发展偏离现阶段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越大,违背比较优势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下,影响产业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成为主要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这种发展战略容易使地区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源过渡投入被选择产业,配置效率低下,同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使其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作用减弱。另外,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方式可能导致业结构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偏离,结果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长期要素禀赋结构无法得到优化,非选择性产业面临更多的市场外部性问题。未来落后地区发展应以市场为主要基础制度,注重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先发带动优势,加大生产业等制造业配套产业扶持力度,增强制造业与配套产业的依存度,同时通过深加工、制造业服务化等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对于资源垄断行业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合理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要素的投入,促使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减少经济运行的外部性问题。地区应施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产业升级的加快,这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以降低结构性失业,使经济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社会总财富增加;对于基础设施,不应盲目投资,盲目投资导致资源浪费,经济效益差等问题的发生,最后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性增大。应重点建设经济效益快、对产业发展作用明显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保障产品与要素流转与经济运行流畅,减少地区企业的外部性问题,加大地方企业外部性补偿;当前发展阶段,提高整体要素生产效率,需要更深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171.
[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研究[J].现代产业经济,2013(3):234.
[3]鞠建东,林毅夫,王勇.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4(10):28.
[4]徐康宁,王剑.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与新国际分工[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67.
[5]刘修岩,何玉梅. 集聚经济、要素禀赋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自制造业的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11(3):16.
[6]李敏纳,蔡舒,张慧蓉,覃成林.要素禀赋与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1(1):20.
[7]李超,覃成林.要素禀赋、资源环境约束与中国现代产业空间分布[J]南开经济研究,2011(4):33.
[8]徐春华.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促进产业链延伸:走出“比较优势陷阱”[J]经济研究导刊,2011(35):183.
[9]张纪.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产品内分工动因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5):9.
[10]吴勇.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6):92.
[11]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65(33) : 99-123.
[12]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13(12):16.
[13]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03(7):30.
[14]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91.
[15]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7):25.
[16] Anselin, L,1988a,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
[17]林光平,龙志和,吴梅.我国地区空间收敛的计量实证分析;1978-2002[J]”转轨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4).
[18]吴玉鸣,徐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J].地理科学,2004(6):18.
[19]潘文卿.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12(1):130.
[20]何枫,陈荣,何林. 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及相关分析[J].经济学家,2003(5):31.
[21]李海峥,等. 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8):53.
第6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 人力资源 素质要素 分析
1 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关理论
“世间万物,人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是对人力资源重要性的精僻论断。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一些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ALμKр
其中Q为产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存量,A, u,p为三参数,其中0
2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2.1 一国经济增长方式受人力资源数量的的影响 一国经济增长需要有多种资源的投入,而任何一种物质资源的投入都要求有适当数量的人力资源与之匹配。同时人力资源在创造社会财富时也要消耗自然资源,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处理好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协调关系。
2.2 一国经济增长方式受人力资源质量的影响 人力资源质量的内涵就是人力资源的素质,包括人力资源的身体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人力资源素质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培训和其它手段加以提高的。一国人力资源素质高,劳动生产率就会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会加快,从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3 一国经济增长方式受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可以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受人力资源的数量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质量受人力资源的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受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因此,人力资源在数量、质量、配置等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均产生影响。
3 辽宁省人力资源素质要素现状分析
3.1 辽宁省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 表1列举出2006年北京、上海、辽宁三个地区的从业人员素质状况。辽宁从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占到76.5%,高中教育人口占到13.77%,大学专科人口比例为6.05%,从业人员中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占3.31%,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仅占0.28%。与辽宁情况相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比例北京的为39.82%,上海为44.1%;高中受教育比例北京为24.47%,上海为27.50%;大学专科教育比例北京为16.30%,上海为13.39%;大学本科教育比例北京为15.99%,上海为12.45%;研究生教育比例北京为3.41%,上海为1.92%。
虽然同期辽宁各层次人员比例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明显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相比有较大差距。说明辽宁省从业人口的整体素质要低于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说明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素偏低,也就是从业人员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3.2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 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辽宁教育发展速度较快,但经费投入水平偏低,预算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能力较弱,致使办学经费短缺,进而势必极大地影响辽宁教育水平即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版。
据统计年鉴显示,2004年至2008年,辽宁省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2.99%、11.81%、11.73、14.07%、12.45%,同期北京的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3.51%、13.78%、13.51%、14.38%、14.67%,天津的分别为14.77%、15.2%15.2%、14.74%、14.75%。全国同期的投资比例分别为11.82%、11.71%、11.83%、14.31%、14.395%。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辽宁的教育事业费支出与北京、天津存在较大差距,虽经过努力差距在缩短,尤其是2007年差距只剩下0.3、0.7个百分点,但在2008年这个差距又扩大了,扩大为2个百分点以上。辽宁作为教育大省,仅仅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3.3 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较低 辽宁人力资本在1980-
2003年时期的贡献率是17.01%,固定资产的贡献率是77.28%,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远小于固定资产的贡献率。从1980-2003年期间辽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人力资本的投资。
4 辽宁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人力资源素质要素的对策
4.1 加大国民教育的投资力度,建立三结合的人才投资模式 政府在国民教育中是主要的投资主体,要加大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在教育投资上要舍得下本钱。企业领导者要从教育、培训的投资能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角度认识人才投资的积极作用。员工个人要从提高自身素质,加快个人发展,完善职业生涯角度认识教育、培训投资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建立政府、单位和个人三结合的人才投资新模式。
第一,政府要加大初等义务教育的投入,防止新文盲的产生。在农村和城市较偏远的地方政府要加大义务教育的宣传,让所有的家长都认识到送适龄儿童上学的重要性。同时,对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采取减免学费的政策措施,减少家庭的教育负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在扫除文盲、提高人口素质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提高重点学科建设质量,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目前辽宁省的25个高等学校制定的89个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包括9个共建重点学科)进行了规划审核,明确了学科发展的重点投入方向,促进了学科的快速、稳定发展。遴选出的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项目也已经举行了授牌仪式。在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的申报组织工作中,全省共申报增列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2个、博士点6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16个,硕士点412个;申报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个,学士学位授予专业50个。
第三,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为了严把本科专业建设的质量关,组织专家对辽宁省80个试办期满的本科专业进行评估。为进一步推进学分制教学改革,组织专家对全省30所进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学校进行现场指导和研讨。为了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组织了36名大学本科外语系主任到英国牛津大学进行培训,学习国外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先进的教学技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还组织大学生进行科技竞赛、机械设计竞赛、广告艺术大赛等活动。另外,还对全省22所独立学院进行专项检查,为制定独立学院管理的有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4.2 建立人才市场,实现市场导向的人才资源配置 建立人才市场,使人才的产权明晰,保证市场导向配置人力资源功能的发挥。建设人才市场体系,在完善辽宁省区域人才市场的基础上,考虑建立国际、国内人才市场,全方位吸引人才,以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政府在人才市场上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实现人才与社会资源的有序化结合。
4.3 政府在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在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一定要把人才规划作为一个中心任务,要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为基础对人才进行宏观布局、层次结构、发展规模的系统预测和规划。结合经济发展目标,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作出合理规划。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全方位引入竞争机制,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帮助员工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使员工早日作出成绩。
参考文献:
[1]王宇,焦建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2005.18.
[2]周亚,,姜璐.人力资源素质与经济增长――一个模型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6.11.
[3]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经济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左玉辉,邓艳,柏益尧.人口环境调控[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第7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利用单元调查评估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坏”产出指标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1993-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29个省份农业TFP增长,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①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考察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该增长主要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但是各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②从地区差异来看,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增长的同时呈现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减;③当不考虑环境因素时,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业TFP平均增长率分别比考虑环境因素时提高0.88%、1.71%和2.35%,但是东部地区却比考虑环境因素时降低1.01%;④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都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是σ收敛趋势并不稳定,σ值呈现出显著的波动特征。
关键词 单元调查评估方法;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环境约束;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3-00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3.011
第8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 劳动力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51-05
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和约束条件。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我国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三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预测达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1] 这个预测和现实也表明,“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出现转折点,有利的“人口红利”决定劳动力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因此,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与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因相关联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 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是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资本是用于投入生产或经营、用货币表示体现在物质方面上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国民产值函数的“残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人们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前苏联曾经一段时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并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水平低下而产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开放后,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大大提高。在这一期间,我国逐渐步入世界市场资源配置轨道,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贸易依存度。如,从1978年贸易依存度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735.23亿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和贸易扩大,逐渐提高技术层次,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世界银行报告》(1999)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9.5%的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此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为16%,全要素生产率为30%。10年后,国内学者李善同等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较为客观,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5年,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测算出我国1978年以来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果如下。
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是资本投入与资本积聚。1978-2003年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2%,导致GDP年均增长9.3%中近6个百分点。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减弱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速明显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继资本之后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虽然部分时期较低,但整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基本接近30%,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过去20多年,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产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体生产效率的改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等等。
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提升空间有限;面临“人口红利劳动力结构即将结束”以及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劳动力质量提高具有发展潜力空间。由此,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中“从技术层面上加大自主创新、从劳动力层面上提高劳动力质量”成为现实的必要。
二、 GDP产值与劳动力结构的非均衡分析
据资料,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达到20.9407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从经济增速上看,10.7%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但是,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
(一)三产产值与劳动力构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产业的GDP比重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基本趋于一致。从GDP分布结构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比重均在3%-5%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般为3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多为65%以上。相应地,劳动力结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与产值结构基本相似,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均衡的、先进的结构水平。目前,我国约有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在从事传统而低产值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尽管50%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5%左右,却为中国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50%的劳动力仅创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产值略超过50%,但它所吸纳的劳动力却仅占22%左右,即“22%劳动力创造50%GDP产值”。这既不是我国工业总产值虚高,也不是工业生产效率和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是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国三产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均衡”(见表2)。
有关专家称这种现象为“产值工业化”。[3]“产值工业化”最现实的注释为,工业经济增长中数量扩张大于质量提升,主要为资本要素的增加而带来的GDP增加;GDP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先进性没有凸现和劳动力质量需大大提高;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产值工业化”的背后劳动效率、节约能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问题。产值工业化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的准备阶段,直接关系到技术层次升级、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反向变化
在技术与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劳动力数量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加,劳动力质量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呈反向变化趋势,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逐渐扩大。经济增长的劳动弹性系数是可以测量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关系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劳动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即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劳动增长的百分点。用公式表示为:E=L′/G′,其中E为劳动弹性,L′、G′分别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人们可以用劳动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间接反映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
据统计资料,我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红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数量。1953-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弹性系数达到0.397的数值,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有限,劳动力增长贡献大。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渐减低;90年代后减低趋势明显,减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为9.58%,但劳动弹性系数仍在减低,达到0.078的水平。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在技术装备陈旧落后和资本缺口大的情况下,劳动增长率增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装备的进步、资本集约度的提高,提高劳动力质量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三、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劳动力质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应用存在差异。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反作用,存在着高劳动力质量与高经济增长质量均衡与递进关系,如出现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GDP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相对“均衡”,三大产业产值与劳动者就业结构一致;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和劳动力质量也相应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一)资本投入与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结构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这些技术升级和技术层次的变迁,由物资资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观看到发生的变化。从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所占产出份额来看,高技术产业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20%,增幅达到14.9个百分点。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份额则有大幅的下降,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从28.7%下降到23.1%,下降5.6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从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份额则变化不大,略微下降1个百分点。① 见表5。
表5说明,资本投入不同,技术层次的变化趋势是高技术与低技术比重的变化,低技术资本投入持续降低,高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高,中技术资本投入基本维持不变。与此相关联的,以物质资本投入的变化带动技术层次的升级,带动对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市场需求。
(二)资本投入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同理,一般低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拥有中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维持投入,因为它涉及面广,这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关键;同时需要不断加大对高端技术蓝领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质资本投入与产出是直接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是间接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进程看物质资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效果看物质资本投入的“政绩”要直观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但从社会效益看人力资本提高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关键。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他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口质量投资,是一种能力资本、人力素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其三,“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在经济社会中,劳动力质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态度和技能应用等。无论是社会或个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既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也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系统接受教育、岗位与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和企业文化的认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质量。
在对深圳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问题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数量增速与经济总量、工业总产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现为对数曲线。1978-1989年深圳经济总量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41劳动力;1989-1994年为0.288劳动力;1995-2003年为0.175劳动力。1979-199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07劳动力;1994-1999年为0.233劳动力;2000-2003年为0.140劳动力。从总体上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逐渐下降的,这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机资本与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的表现。否则,深圳GDP总量的增加与劳动力数量的同步增加,将是深圳各项资源条件难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说明,人口、劳动力数量与国民经济产值呈现对数曲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反映,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要求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中变劳动力数量为劳动力质量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蔡P.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Z]. 中国经济报告,2006-11.
[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第9篇: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