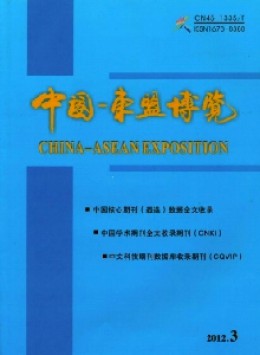中国近代史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国近代史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进士,1838年12月道光帝先后8次召见,商讨禁烟事宜,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禁烟。就是这个时候,这位“天朝上国”的士大夫开始直接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对话、斗争。他表现出了中华民族高贵不屈的品质,充分显示出了一位伟大爱国者的素质,这种高贵的爱国心不仅表现在中,而且贯穿了他整个一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保护民族权利
当英国及其它国家商人大量向中国贩卖鸦片,直接损害人民利益时。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鸦片泛滥将使中国数十年后出现兵弱银涸的严重局面。反对白银流向国外。中国的财富,宁可“损上益下”,也决不可“漏向外洋”。这种初步的民族意识,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突出的特色,也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鸦片泛滥以后,他曾亲自向江苏苏州、湖北汉口一带“禾闾聚集之地”的“行商铺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民族经济遭到破坏和商人破产的现实之后,他指出:“行商铺户…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反二三十年以后,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货何售,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这种认识,初步了解并且触及到了中国的近代问题,即利权问题,这是后来一切爱国主义者所要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口号即是根据这个事实提出的。所以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决,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这说明,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初步触及保护民族权利的内容。同时,他反对鸦片泛滥较多地着眼于大多数百姓遭受毒害的后果,这些都是他在当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二、寻找富国之路
林则徐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努力寻找祖国富强之路,使整个民族富强起来。当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引起清政府财政严重困难时,林则徐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和战舰图式的资料,并建议设立新式国防工业,“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以粤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来制造新式大炮”,“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借此以保卫海防。后来,林则徐在谪守新疆期间,针对沙俄向外扩张对我国西北边疆造成的严重威胁,主张实行“屯田”、“耕战”,采取“兵农合一”的措施,增强边防的防御能力。到了晚年,他还提醒:“终中国之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这些言行,表明了他已从单纯的军事反侵略发展到寻求富国强的道路,不愧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已经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爱国者(这里指诸如顽固派和处于顽固派与林则徐思想之间的中国人,当然,他们都是爱国的,只是思想、主张不同罢了)。林则徐所要求的是改变中国旧有的经济、军事制度,代之而起的是运用西方先进的科技使中国富强起来。
三、重视执法
林则徐为维护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突出表现在他重视执法上。当然,就封建大法而言,他执行的大法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与外国关系而言,他执行的大法在于违法在华外商,就具有维护国家的意义。当鸦片泛滥时,林则徐坚持“大清律例”,不但适用于“华民”,而且同样适合在华“外夷”,“夷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与华民同照新律一体治罪。”坚持执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政策,他还明确地向英国政府宣布:“凡在六个月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林则徐反复强调,“夷商致内地”,必须遵“天朝法度”,犹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一样。这反映了林则徐维护我国和法律的鲜明爱国思想。
四、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爱国主要义思想在近代史上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失败后,中国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对长期以来“天朝上国”至善至美的思想开始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把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作为自己的理想,当作外御强敌的根本道路,纷纷寻找独立富强的方案。近代资产维新派先驱冯桂芬认为,中国“屈于西国之下者”是莫大耻辱,但是“耻之莫如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他看来,应从林则徐提出的魏源总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而得知。明确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了使清廷“中兴”的,可以这样说,林则徐的思想无不在左右其中。
林则徐,这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当时封建官僚集团中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以往民族主义思想的伟大总结,又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开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林则徐和许多志士仁人追求国家富强的真诚的愿望和可贵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所继承。今天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为了实现中国梦这一宏伟的蓝图,还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外抗强敌,内求振兴中华的可贵精神。
参考文献:
[1]宁靖主编:《史论文专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第2篇: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教士;耶稣会;史学东渐
《瀛环志略》是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馆藏书为同治癸酉(1873年)云楼刻本,略如32开本,六册,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本,八册,均十卷,书中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还从地球开始介绍各大洲的风土人情,对其他地区文明也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全书四十多张插图,除了关于清朝、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他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这些与19世纪初开始的西方史学的东传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纪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时期,而位于东方的清朝廷还处于大国迷梦之中,传教士作为西方各国的先驱首先来到中国,打破中国封闭的坚冰。这个世纪前期,传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动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广州和南洋一带(1),西方史学也就在这样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开始了艰难的东来之路。
一、西方史学传播的方式及原因
这一时期,传教士传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译书籍、举办医疗慈善事业、办报刊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传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学传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
刘耕华在《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本土回应》中讲到,从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康熙初80年多年间,是以认同儒士身份在社会行为上遵循儒士礼仪习俗,在传教著述中认可儒学思想并借助欧洲的科技来佐证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取得中国士人的心理认可为特征的“附会期”,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占优势情况下,不可避免采用附会中国文化为主,辅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纪初西方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国,但受“文化传教”传统的影响,仍采用办印刷所、译书、办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潜在的仍是附会中国文化的传教心理。
另外,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传教法”不仅仅受来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强大的排外群体,他们自身知识储备积极的反应,可以说传教士同时拥有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其行为不可避免有一种超越宗教传播即文化传播的倾向。
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华夷之辨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用夏变夷”的沾沾自喜心态,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教,为中国之子民,既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思想界经世思潮盛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接触西方的知识,了解西方的情况来拯救中国。于是出现颇为戏剧的一幕,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却又接受传教士的西学,在这一夹缝中以“知识传教法”传教是传教士的不二之选。
二、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
据英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华传教十纪念录》为例,1810年至1867年来华传教士中文著述目录统计,在约760种出版物中,绝大部分仍属宗教读物,严格意义上的史地译著仅20余种,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编,为最早较系统介绍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简述美国地理疆域、历史、居民、人口、自然状况、经济、政治、宗教、语言、风俗、国防等。《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是这一阶段传入的史学著作中最为系统的一部。
(2)《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达维亚,1829年石印本,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编。书中将中国史书某些记载与《圣经》记载比附排列。
(3)《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页,附一海图。郭实腊编译。叙述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以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
郭氏另有《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万国地图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译著,出版后均几经修订重印。
三、西方史学反映的主要史学思想
以上的历史著作既非专门史学理论著作,也不是体现西方主流史学理论观点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书于西方史学最辉煌的19世纪,经过传教士翻译修改,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的史学观念主要有:
首先,极力宣扬宗教神意史观,如慕维廉在《大英国志》中便一再宣扬:“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开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开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时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3)这类著作中出现的神学史观与西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史学观念极不协调,传教士认为万事皆决于上帝,这与中世纪的史观很相似。
其次,西方与东方平等论。这一时期史学作品多以叙述介绍性质为主,目的让中国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识。1833年6月,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创刊计划书》中写道:应通过出版物的宣传,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以“消除他们高傲的排外思想”(4),次年11月广州成立的有传教士参加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也设想以这种方式,使中国人在“智力炮弹前让步”(5)。但是这一时期传到中国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对历史泛泛介绍的作品,史学理论介绍涉及较少。
四、中国人对西方史学的回应
19世纪前半期传教士对西方史学的介绍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它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大量传入的序曲,给中国史学反省与重建提供了机会。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他更是为国人敲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开阔了知识分子眼界。
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历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6)。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国史地研究都处于发展阶段,西方史学的传入推动这些史学研究活动的开展。道咸年间,研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姚莹的《康纪行》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外国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环志略》姐妹篇《》的出版。《》是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之上广搜中外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强调《》与前人记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书中引录最多的资料,便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人著作,如选取英国人理哲的《地球图说》34处,马礼逊的《外国史略》60处,《每月统纪传》26处,又选取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编译的《美理哥图志略》的部分内容等等(7)。地图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给清朝广州地方官府的“洋图”。内容上,详述各国史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8),对日本维新变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其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纩,其不然哉”(9)。
这一时期清王朝还处于“天朝大国”迷梦之中,对国内外危机束手无策,史学传播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由传教士进行的,它不仅带有基督教文化传教的传统特点,又由于时代特征及历史文化的传播特点而区别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传播。
注释:
(1)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刘小枫:《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
(3)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6)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报》(杭州),2004,(6),第37-38页。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页。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