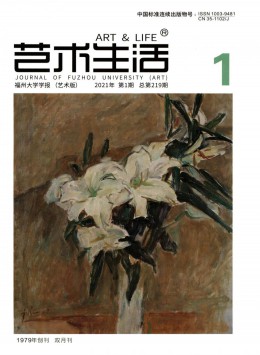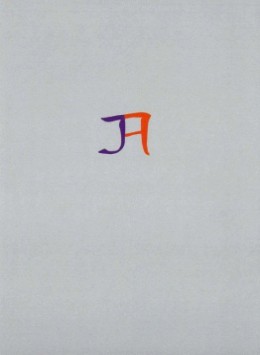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民俗翻译;安徽民俗
一、民俗与文化翻译
翻译除了是源语言文字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包含了意象传递、交谈和融合等活动。吕亚娟在《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一文中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翻译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翻译观则是试图研究和探索这三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逐渐步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尤其是尤金・奈达对于翻译,与文化关系论述的理论在我国翻译界的时兴,以及王佐良先生积极倡议把翻译研究与文体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学学派”一度成形。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佛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在合编的论文集《 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也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延伸并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走出形式主义的框框,应考虑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延伸。
二、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民俗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国民俗学家查理・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正因为民俗和文化的共性,研究民俗翻译要置于文化翻译学范畴内;而民俗的特性又要求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翻译策略来解决民俗文化翻译问题。
1.安徽位于我国东南部,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长江下游,深居华东腹地。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春秋时称为“吴头楚尾”。这里自古是南北文化汇集碰撞之地。文明悠久的安徽人杰地灵,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影响的思想、学派诞生在这里,使安徽成为中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受风土的影响,民俗习惯南北迥异;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安徽名山胜水遍布境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特别是独树一帜、充满地方特色的黄梅戏、花鼓灯、徽剧和傩戏等,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安徽民俗文化要走向世界,多语种的翻译活动必不可少。为符合安徽民俗翻译的诸多特点,安徽民俗翻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征。
2.安徽民俗文化翻译策略,以直接音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出现在较多的地名、人名及约定俗称的民俗表达的翻译中。这一部分的民俗相关文化表达较为简短,口语化和本地化,不乏一些方言掺杂其中。译者通常为了贴近当地民情采取直接音译的方式固然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坦率且不加注释的直译却给译出语读者增加了不少理解困难。而有些民俗术语包涵多种文化暗指,并不源自音韵的模拟,这部分民俗术语的翻译就需要谨慎处理。例如以安徽籍艺人为主的四大徽剧戏班之一的“春台班”,译者译成“Chuntai Troupe”。春台,是一个典故名,典出《老子・道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指春日登眺览胜之处。因此,在翻译这类名词时适当地加入注解或许更有助于译出语读者了解安徽的民俗文化。
3.安徽地区有其独特的发展史、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负载着相关文化的词汇、成语、典故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实写与虚写相互掺杂,句式参差错落,大量的修辞手法融汇其中,译者往往无从下手。比如安徽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叫做傩戏,流行于安徽贵池和九华山方圆百公里的地区,是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的请神送祖的祭祀活动。演出前后有隆重的“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朝庙”等傩事活动。在旅游英语中,傩事活动的过程被译成“The ritual procedure includes 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 Following the solemn ritual,Nuo drama is performed to entertain the spirits.”显然,“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与原文“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相比在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上出入较大,而对于文化意义的传递又存在变差。傩戏以祭祀祖先的目的为主,“神”则应被理解为“forefathers”而非“spirits”。
三、民俗文化翻译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言环境
许多译者为了避免民俗文化因素被忽略和篡改常常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仔细调研反复琢磨后的译法,即便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也会得到认可。而囫囵吞枣的翻译态度则会带来误解。例如,戏钟馗是盛行于安徽徽州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除煞祈福的一种形式,民间对他有“除恶状元,镇邪将军”的美名。译文“the protector against evil spirits and demons,the hero capturing ghosts”中将“状元”译成“the protector”,“将军”译成“hero”似乎有些信手拈来,天马行空。毕竟“状元”所包含的“top”的含义以及“将军”所包含的“status”的含义完全在译文中被忽略了。
总之,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或异化,每一种翻译策略都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孤立的,而是应该互补长短,相辅相成。民俗文化翻译是两种文化移植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其翻译过程必然充满艰辛,这要求译者除了精通译出语语言文化,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语言文字也要有深刻了解,真正做到令译本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对话。
民俗翻译研究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研究民俗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诠释策略以及在译出语读者群中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文化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传播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至关重要。
注:本文是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项目“从文化翻译学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译”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Nida,E.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蒋红红.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
[3]吕亚娟.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J].科技咨询,2009(15).
[4]王慧杰.新疆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剑南文学,2012(11).
[5]李建军.文化翻译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第2篇: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第3篇: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J20-02文献标识码:A
老子的道法自然,顺任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及庄子的天地有大美、与物为春、与物有宜、身与物化的思想,老子的虚静寡欲、无为不争及庄子的“心斋”“坐忘”的人生态度,构成中国人的自然哲学观之基础,并对中国山水画创作及其理论与批评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老庄及其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魏晋时期自然景物及山水已经作为艺术对象和审美对象进入诗人与画家的视野,并成为独立的创作题材,中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得以产生。这使中国诗画中独立的自然意识或自然山水风景作为独立的题材早出西方一千多年。德国文学理论家W・顾彬在《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一书中说:“在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中,便已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在西方,自然当作风景,就是说当作被单独注意,感受到的部分,在绘画中,直到十七世纪(荷兰)而在文学中,直到十八世纪才确定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在此前的若干世纪里艺术中就没有自然的介入,但它起的只是衬托作用,既非可单独认识的现实部分,又非自然意识当作什么独特之物的发展。” [注:参见[德]W・顾彬著,马树德译《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第2页。]中国人比西方人早一千多年用诗画的形式来观察自然并审美地享受自然,和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和的审美关系。
中国山水画从东晋顾恺之等人的作品开始,到南朝刘宋时期宗炳王微,经隋朝展子虔,再到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王维、张b而迅速发展起来,宋元明清山水画逐渐占了中国绘画的主导地位。中国山水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中国山水画以蔚成大观,其思想基础是老庄的道家哲学。老庄的道家学说并对中国山水理论与批评精神产生深刻影响。从宗炳的“含道映物”到郭熙的“林泉之志”,再到石涛的“归于自然”,道家精神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根红线。孔子的礼乐观成为儒家批评精神的核心,儒家思想帮助形成中国美术批评中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批评标准与传统,对中国人物画的道德价值和思想内容起了规范作用,促使人物画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政治伦理功能。而老庄的道家学说则成为山水画创作与批评的精神源泉,正是老庄的道家学说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的恣肆,也促成了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的丰富多彩。
中国的山水画及其画论发展到宋代,可以说已蔚然成大观,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王希孟,南宋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大家辈出,各种技法与皴法更趋完备,宋代可以说是山水画集大成的时代。山水画理论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是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
中国的山水画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东晋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是记述自己创作一幅山水画的构图布局的过程,南朝刘宋时期宗炳的《山水画序》和王微的《叙画》讲“含道映物”“澄怀味象”和“畅神”等功能,此外亦对山水画构图透视规律从总体上加以总结。梁元帝萧绎的《山水松石格》开始对画山水松石的具体技法提出要求,以“格”的形式加以固定,成为画此类景物的准绳。唐代王维的《山水诀》《山水论》,五代刑浩的《笔法记》都是重要的山水画理论文献,荆浩将谢赫《古画品录》主要针对人物画提出的“六法”,而发展为针对山水画的“六要”,即“气、韵、思、景、笔、墨”,还提出笔有“四势”,即“筋、肉、骨、气”,荆浩的《笔法记》在山水画创作思想及评价标准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贡献,同时在具体技法方面也时有论到。
到北宋中期,郭熙《林泉高致》是山水画理论的集大成者,既有对人与自然山水之审美关系论述,亦有对具体绘画技法的探讨,且分章分节论述,篇幅大增,可谓长篇巨制,《林泉高致》是中国山水画理论最高成果之一。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人。好道学,喜游历。曾临摹李成山水画而受到启发,笔法大进。受到神宗赵顼的赏识,授书院艺学,后升至待诏。成为宫廷画院最重要的成员。代表作有《早春图》《关山春雪图》《窠石平远图》。《早春图》表现寒冬刚过,大地回春的早春景色,作者以富有层次的墨色和圆润的卷云皴塑造了雾气升腾阳光浮动下的初春山水景象,并运用高远、深远、平远的构图与视觉处理方式,将山水景色表现得广阔深远。郭熙关于绘画的一些思想,经他的儿子郭思整理成《林泉高致集》一书,共分《山水训》、《画意》、《画诀》、《画题》、《画格拾遗》《画记》六篇。前四篇为郭熙的艺术见解,系统而深刻地表述了郭熙的艺术思想,后两篇为郭思所作。《林泉高致集》前有郭思所作“序”。郭思在“序”中说,他跟随其父游历山水,而将郭熙所谈艺术话语加以记录整理。“侍先子游泉石。每落笔必曰。画山水有法。思闻一说。旋即笔记”。又说“先子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于此以成名”。这告诉我们,郭熙创作十分严谨,并经常思考山水画理论问题。郭熙“少从道家之学”而又“本游方外”,说明郭熙少年就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至于他喜欢游历,既是受老庄热爱自然,遁迹山林思想的启示,也是一个山水画家的基本条件。这说明在中国古代,有成就的山水画家或多或少要受到老庄思想的一些影响。郭熙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对山水画产生和存在根本原因的看法上: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己而长往者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鄢。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暄夺目。此且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注:参见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
郭熙从“人情”本质上看待自然山水,“尘器缰锁,此人情所常厌”,而“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人情即人性,从人性的本质上来看,人人都厌恶繁锁的世俗生活,向往清静怡人的烟霞圣境,所以“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鄢”。人们不能常在这些自然胜境中观览,“所常愿而不得见”,“耳目断绝”,但能用画笔将这些山水胜境表现出来,“今得妙手,郁然出之”,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这和宗炳所谓老之将至,不能再返山林,而“披图幽对,坐究四荒”很相近。“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这都是人的本性所至,虽然不能直接观赏自然,但面对山水画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暄夺目,山水画成为真山水的一种替代物,依然能引起观者对自然的审美联想和审美享受,山水画也可以使人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感。此且不快人意而实获我心,郭熙说到山水画的功能是“快人意”和真山水使人愿“常处”“常乐”是一致的。郭熙对山水画功能的看法与宗炳的“畅神”论是一脉相承的。在郭熙看来,人们之所以爱夫山水和喜欢山水画,其根本原因就是人的本性中有“林泉之志”。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其思想基础是老子的顺应自然和庄子天地有大美的观点,正是天地自然之中有“大美”,所以观赏自然或山水画才能怡悦性情而“快人意”。庄子虚静和心斋的思想还影响郭熙对山水画创作与鉴赏态度的看法,《林泉高致集・画意》写道:
西方的透视学主要是线透视发展得较早。在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那里就有论述。线透视即利用光线沿直线进行这一基本原理,阐明物体为什么愈远显得愈小的透视学。文艺复兴初期,透视学在建筑家布鲁尼斯奇和画家佛兰切斯卡等人的研究下,已发展得较完善。意大利艺术大师达・芬奇曾认真研究过透视。达・芬奇将透视学看成绘画的基础,看成绘画的“缰辔和舵轮”。他将透视学分成三个分支,即线透视、色透视和隐没透视。线透视研究物体远离眼睛时看来变小的原因,亦称为缩形透视。色透视研究颜色离眼远去时变化的方式。隐没透视阐明物体何以愈远愈模糊。[注:参见戴勉编译《达・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7页。]透视学对于绘画来说其根本性质是使平的画面显出物体的立体感或凹凸感。达・芬奇认为这是绘画的最大奇迹。他的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就是严格按透视规律画的。基督处于中心点上,十二个门徒分两边向中心点排列,近大远小,按焦点透视画出。
西方的透视学是从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光学、色彩学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其中还包括对眼睛的生理特点研究。西方的透视学可以说是理性与科学的产物,将透视学引入绘画,画面的景物安排严格按透视学原则处理。正是由于线透视、色彩与光的明暗表现手法的运用,使西方绘画在定点透视原则指导下,在独立单幅画面中,创造了一个虚幻的几乎令人进入其中的空间世界。如十七世纪荷兰风景画家霍贝玛的《林间小道》就是如此。透视学成功地运用到绘画中。可以说是艺术的胜利,使艺术在二维平面中征服(表现)三维空间,从而也为西方写实绘画打下了技术上处理空间问题的基础。但西方绘画中的这种焦点透视比较呆滞而不如中国画中“三远”丰富灵活。看定点透视的西画的人的眼睛视角必须和作画者的眼睛位置相同,否则就会发生形变。西方的透视学和中国的三远等透视规律都是中西艺术家们根据自己民族的艺术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处理空间问题的视觉规律。如果说西方的艺术透视学更富有理性和科学意味的活,那么中国的“三远”论等艺术视觉原理则更富有艺术与情感表现意味。
郭熙在中国画理论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郭熙本人既是北宋一流山水画家,同时也是精妙的鉴赏家,皇宫中的绘画真品都经过他鉴识。这样他对绘画问题的思考起点很高,视野宽阔。他“少从道家之学”使他打下了道家精神中亲和自然的思想基础,帮助他形成“林泉之心”或“林泉之志”。《林泉高致集》一书的确贯穿了所谓“丘园养素”“烟霞仙圣”的道家精神。另一方面,由于郭熙受到皇帝恩宠,授给他书院最高职衔即待诏。神宗将秘阁里所有汉唐以降的名画全拿出由郭熙鉴赏并详定名目,凡是宫廷中重要的地方以及难度较大的画都要郭熙去画。所以郭熙的成名及生活还算是顺坦的。郭熙绘画并无家学,“游艺于此”更加勤奋。所以郭熙多少也应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如《林泉高致集・画题》中引世说所载戴安道学画一事,“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这种影响可能主要表现在他的处世态度比较舒平和畅这方面,因此郭熙并不是在山林中寻仙找药的道家仙人,也不是玄对山水的玄学家,更不是仕途不得志而遁迹山林的隐士,而是具有道家精神念念不忘林泉之志,又以平和之心来观看自然山水的一位大画家,这使他以正当的真正审美眼光来看待这个自然,所以他觉得山水与山水画都是可爱的,可亲近的,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再加上他“本游方外”,使他观察到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深厚。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岫。这是他作为一个山水画家的基本素养。他对自然山水观察之细令人惊叹。如《林泉高致集・画题》中谈到以春景为画题时可画出无数春色风光画:
谓如春有早春云景。早春残雪。早春雪霁。早春雨霁。早春烟霭。春云出谷。满溪春溜。春雨春风。作斜风细雨。春山明丽。春云如白鹤。皆春题也。
只有抱着庄子的“与物为春”的自然审美态度,觉得自然是可亲的,是怡悦性情的,才可能产生仔细观察、体味与表现自然的欲望和行动。《林泉高致集》不仅是中国山水画理论与技法的百科全书,而且也是中国人包括画家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一块心路里程碑,它记载了中国人到十一世纪时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与精神活动。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研究自然美,研究人与自然的精神审美关系的一部重要的著作。此书由于郭熙的儿子郭思帮助整理,也可能包含了郭思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是父子二人几十年的思想总结,因此也显得更加成熟。
当十一世纪中国北宋的山水画与山水画理论及技法相当成熟时,西方的风景画还未见踪影,即使到了十五世纪末达・芬奇对透视学作了深人的研究后,也只画了有风景背景的人物画《蒙娜尼萨》和《岩间圣母》。到十六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乔尔乔纳画出《暴风雨》,才实现了由有风景背景的人物画向有人物的风景画转换,直到十七世纪荷兰画家雷斯达尔、霍贝玛出现,才产生了真正独立的风景画。西方的风景画比中国山水画要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此外在西方美学史上和美术理论史上很难找到诸如郭熙《林泉高致集》这样系统而深刻的风景画论著。这说明像《林泉高致集》这样的著作在世界美学史上也是独特的。
刘纲纪教授早在198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美学概观》一文中就指出:“自宋代以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儒、道、禅三家合流的趋势。元代的倪云林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这恰好可以用来概括宋代以来中国美学发展的大致的情况”。[注:参见刘纲纪《中国古代美学概观》一文,见《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357页。]在中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中,儒、道、禅精神,有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唐代王维的朋友苑咸评价王维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王维的诗画中确有禅的空寂境界。但他在隐居之时,亦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而在做官时多少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北宋郭熙少从道家之学,培养林泉之志,但他在受到皇帝重用后,对绘画功能的看法:“画之有益如是,然后重画,然则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虽然郭熙认为山水画的本质是“丘园养素”,主要用道家精神加以阐释,但他所受儒家中绘画“有益”于世的观点影响也很深刻。这说明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精神虽以道家为主,但儒、禅常常以互补。而元代的倪瓒在《良常张先生像赞》中写到:
诵诗读书,佩先师之格言。登山临水,得旷士之乐全。非仕非隐,其几其天。云不雨而常润,玉虽工而匪镌。其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者欤?
说明儒、道、禅是可以合一。他在《立C像赞》》还说到,宋灭亡后,一些文人与画家理想破灭,虽还抱有儒家理想不愿放弃,但又“黄冠野服,萧散迂徐”,“或颓然净名方丈之室,或悠然庄周冥漠之区”。可谓元代文人与画家于儒、道、禅三家思想兼而有之。
清代的石涛是受道家和禅宗影响的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他的《画语录》十八章及部分题画诗,是中国画论与画评以及山水画理论发展到清代后所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如果说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集》从审美角度对山水画的理论作了全面透析,那么清初石涛的《画语录》则从哲学角度对山水画作了深刻的本质概括。
石涛(1642―1707),姓朱,名若极,明朝靖江王朱赞仪之十世孙,广西人。他法名原济,字石涛,号有苦瓜和尚,瞎尊者,大涤子,清湘老人,靖江后人等。他青少年时期客武昌,曾涉潇湘,泛洞庭,登匡庐,屡游敬亭山和黄山。登山涉水,为他“搜尽奇岭打草稿”作了准备。他中年时期住南京,并到过北京,晚年定居扬州。石涛幼年被迫削发出家,二十多岁投奔禅宗大师旅庵本月门下,四十岁左右曾以一代禅师的身分领众开堂传法,说明他在禅林还有一定地位。1699年前后,石涛脱下袈裟,脱离佛门而志道士,“自托于不佛不老间”。他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年)写的一首七律也表现了他老年时的道士生活:
画家掌握一画后,运用一画之洪规或一画之法则于绘画中,就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石涛这里所述实际上是画家掌握创作规律后,就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和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很相近,都是掌握对象的规律后,达到自由无碍,游刃有余的化境。“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所谓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是说掌握了一画之法,万物皆明,创作就可以进入“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石涛借孔子的话说“吾道一以贯之”,其意是指石涛从对万象之根的理解到创作中具体法则的运用,都是以“一画”之“道”加以贯通。进人“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境地。并可消除法障,法自画生,障自画退。“法障不参,而乾旋坤转之义得矣,画道彰矣,一画了矣”。画道彰的创作目的达到了,一画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石涛的一画论主要是解决山水画的创作与评论问题。如“境界章”讲分疆三叠,一层地,二层树,三层山,千峰万壑该可纳入画的境界。《画语录》还分“林木”“海涛”“四时”专章对景物描绘作了论述,至于“远尘”“脱俗”章则讲创作心态,要脱除物与尘的局隘,要“心不劳”,要进入“至人”的“达”与“明”之境地。“达则变,明则化。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尺幅管天地山川万物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只有心淡若无,才能俗除清至,这正是庄子所说的“至人”的人生境界。
石涛在《画语录・山川章第八》中集中表现了他关于山水的美学思想。石涛以“生活”(生是动词,“活”即活现、生动)的态度来看待山川自然,将山川自然看成是具有生命力的博大载体。他将山川,看成是“天地之形势”,而将风雨晦明,看成是山川之气象,纵横吞吐,则是山川之节奏,山川成为一种天地之中有生命的博大机体。“风云者,天之束缚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跃山川也”。山川形态变化是“天之权”“地之衡”安排的结果,但要把握山川的“形神”,必须一画贯之:
且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里,罗峰列峙,以一管窥之,即飞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测山川之形势,度地土之广远,审峰嶂之疏密,识云烟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万重,统归于天之权,地之衡也。天有是权,能变山川之精灵;地有是衡,能运山川之气脉;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
――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
石涛认为山水是天地间之大美也,广土千里,结云万里,若用肉眼看是难尽收眼底。但若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此处所说的一画,实则是用心灵来感悟自然,凝神遐想,这样才能避免一管之见,达到如陆机《文赋》中所说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就是石涛所谓“参天地之化育”“贯山川之形神”。所以一画是帮助画家认识感悟天地万物和自然山水的一种精神源泉,一种心灵工具。以一画观山水,则可突破一管之见的局限,而达到心与物融,神与景合。因此一画乃画家宝贵的大“法”。在山川章中,石涛还有一段广为影响的论述:
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
石涛说在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即山川与他是分离的,五十年后,他终于体悟到山川在精神上融为一体,“神遇而迹化,”用神与心来彻悟自然山水之特质,主客体交融而合为一体,山川和我已不可分,“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身与物化,我即山川,山川即我。这和庄周梦蝶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为物化。”(《庄子・齐物论》)庄子的身与物化观对中国人观察自然、体悟山水的确发生无限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人观察自然的一种心理结构和思维贯性,特别是对山水画家认识自然山水的表现性特征,以情观物而创造情景交融的山水画更是发挥重大作用。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