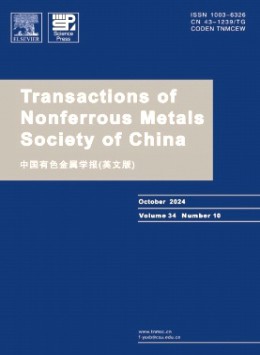英国本科毕业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英国本科毕业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英国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在卢老师的办公室,他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大学生》:从您发表的文章看,您认为我们的大学生学习量,也就是学分要求普遍过大。
卢晓东:2014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晓宇、朱红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的“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调研中,受访的275名专家中有240名专家提供了本校本专业毕业总学分要求,均值165学分。总学分数分布于150~180之间的高校占65%,其中160~170学分的比例最高,达到31%。22%的专家表示其所在学校规定的本科毕业总学分数超过180学分。这反映出我们大学规定的学习量确实过大。
《大学生》:境外高校的学分要求是怎样的?对学生的教学效果如何?
卢晓东:美国高校本科生学习量要求为120~128学分之间,1学分意味着课堂教学1小时加课外2小时,学期教学周数13~15周。美国本科生的规定学习量确实较少,但培养出的学生一般被认为富有创新精神。
就学分而言,日本在1931年颁布了《大学设置基准》,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学生如需毕业,经在大学学习四年以上,取得124以上学分”。由于是国家立法,84年来没有大的折腾和变化。日本在2000年之后诺贝尔奖取得突破,几乎平均每年一位。
英国本科教育基本是三年制,学习量世界最少。但我们看到,英国在创造性人才产出方面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进化论和DNA双螺旋结构、卢瑟福和原子模型、青霉素、图灵和计算机、石墨烯、试管婴儿……英国在现代文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在创造性人才培养方面也很成功,其本科学习量为128学分,也很少。香港之前的学制学习英国,为三年制,学习量很少,培养出的典型创造性人才包括菲尔茨奖获得者丘成桐。2012年香港完成学制改革,大学学制由英制的三年改为美制的四年,学习量有所增多,但四年制大学本科基准学习量也定为128学分左右。
《大学生》:为什么学习量与创造力之间不一定成正比,甚至学习量太大反而影响创造力?
卢晓东:法国古典哲学家蒙田在其《随笔集》中专门论述过“学究式教育”,他对学习量过多举过两个精辟的比喻。他说,“我们公主中的公主提到某人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把其他那么多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放在头脑中,自己的思想为了让出地方就挤压得很小了”“我想说的是植物吸水太多会烂死,灯灌油太多会灭掉,同样,书读得太多也会抑制思维活动。思想中塞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清理,这副担子压得它萎靡消沉”。
从认识论上来讲,如果认为学得越多就越有创造力就存在一个悖论:创造新学科的本质是突破旧学科范式,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遵循旧的逻辑会导致一种情况,如果学生对旧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范式产生某种信赖,甚至信仰而非怀疑,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范式呢?事实上,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早就指出了这种危险: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曾经是并仍然是常规科学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学就会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进步。
“范式陷阱”这个概念可以描述学习量过多的后果。在旧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范式陷阱越深,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创造。经济学家斯特芬在《创新经济学手册》中专章论及“科学经济学”,他指出:“存在轶事证据表明,过多的知识对于研究者的创新发现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多的知识阻碍了研究者。这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暗示。例如,许多超常规的研究常常由年轻科学家完成,因为年轻科学家相对年长者知道得更少,因而在选择研究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时不会被阻碍”。
《大学生》: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以前普遍的做法敲了警钟。
卢晓东:我们是该思考,在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是否存在严重缺陷。我们的大学(加上中小学)让学生学那么多东西,是否会把学生自己的思想都挤压得没有地方了呢?没有自己的思想,创造性何来?我们的学校教育让学生学了太多东西,是否抑制了学生的思维活动,从而使得学生难有创造力呢?
比如有的高校要求的学分总量竟超过180分,尤其在许多大学中,成立的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改综合班”,竟然规定了超高的学分要求。如一个学校规定:“前两年集中强化数理、计算机和英语基础,共修学分达125学分。”这意味着该校综合班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很可能达到250学分!
另一个大学对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强化学院”,其学分制实施方案(2004年12月)规定:“毕业最低总学分(含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及其他实践教学环节的学分),文科类185学分;理科、工科类188学分,其中要覆盖所选专业主干课程。课堂讲授原则上17学时计1个学分”。
上述两校的做法并不是个案,从中看出潜在逻辑:“强化出人才”,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让学生了解和熟悉既有学科范式。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创造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只有把旧学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练和深刻,学生才能创造出新的学科范式。也许一般学生没有很强的学习动力和智慧潜力,但选的优秀同学有这样的潜力,因而让这些优秀的学生学习很多知识,他们就能够成为创新者。
实际调查也证明了这样的做法是无效的,“高等理科本科教育改革”调研专门针对学生完成了“全国大学生调查分析报告”,从学生角度了解学分总数对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学分总数在回归分析中,没有发现对学生学业能力、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大学生》:学得太多未必好,当然不学也不对,大学生的学习量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在您看来,适度的学习量应是多少?
卢晓东:大学生确实需要适度的学习量。经由教育制度比较,如果以120~128学分为参考基础,考虑大陆另外有12~16学分政治理论课学分,我们大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应当在130~140学分之间,上限不建议突破140学分。以15学时等于1学分计算,总学时大致可以把握在2200~2400学时之间。
《大学生》:现在有没有大学的先行者,已经按这样适度的学习量来做?北大能否给全国大学带个头?
卢晓东:北大从10多年前就已经把同学的学分总量要求降到140个学分以内,这些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总量要求,没有因为一些因素而改变。其他也有一些大学已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数,如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对本科生的学习量进行调整,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育改革路线图”中第一条就是:学生的学分要求降到最低129分,最高157分。这在高校中算是非常低的。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等都非常大比例地减少了学习量要求,为学生疏离范式陷阱以及更深入地自主学习给予了可观的空间和时间。
建议修订高等教育相关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习量固化在130~140学分之间,以让大家有个共同的遵循,也防止在实际中出现反复的波折。
《大学生》:可以想象,学习量减少后,大学生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来做自己喜欢的,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学校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给他们提供更便利的学习环境和更多的选择途径?
卢晓东:学校可做的很多。
一是通过通识教育给学生选择背景和原则。
二是自由选课。在全校范围内任意选课意味着,当学生在电脑上打开选课系统,他可以看到全校所有院系的课程,并跨越院系藩篱选择所有课程,甚至跨越本科课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篱选择课程。在必修与选修的维度上,可以给予学生30%~40%选修课比例,将必修的比例控制在60%~70%之内。这样的自由选课会带来许多“意外”,一个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会选择攻读哲学硕士,之后又选择“石油工程”专业博士;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会报考化学专业硕士并且如愿以偿;一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选择了生物学本科课程,竟然“意外”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如程和平院士)。这些都是北大学生中的真实故事。
三是以住宿学院和文理学院去除学生的专业身份束缚。
四是发展个人专业。所谓个人专业,是指个人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不是由教师组织完成,而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全校(甚至更大范围)课程中自行组织完成。
五是自由地转专业。
六是自由选择辅修或双学位。高校应按照学分制模式,为每一个专业构建一个辅修/双学位专业供学生自由选择。人数较多时,可以单独开班;人数较少时,完全按照学分制管理。如塔里木大学主修历史专业的同学可以辅修“枣科学”;西北工业大学主修会计专业的同学辅修“3D打印”;西南师范大学主修“儿童心理学”的同学辅修“古典音乐作曲”。
《大学生》:这些力度不小了,让我们再放飞设想,还能给同学们哪些尽可能宽松的成长环境?
卢晓东:比较大的政策改变还可有一些。
一是大学间转学。转学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转学是普遍的激励。麦可思2014年对大学新生的调查表明,六成大学新生对学习缺乏动力。转学就是当下亟需的新动力。第二,转学是新的学习机会和环境。实现大学间转学需要“985”和“211”高校系统调整不同年级的学生人数结构。
二是开放的暑期学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实践表明,开放暑期学校具备实践可能并已产生重要作用。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