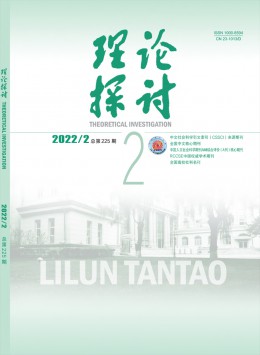后理论时代中西比较文学探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后理论时代中西比较文学探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西方文学理论蓬勃发展、影响极大的时代,但进入21世纪,文学理论已经失去推动文学研究的活力,在西方尤其美国的大学里,甚至有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取代的趋势。于是文学理论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进入了后理论时代。传统的比较文学以“事实联系”(rapportsdefait)为比较的基础,研究作家和作品之间实际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种比较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理论框架,在20世纪显得陈旧过时。二战后,以民族传统和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被学界所摒弃。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文学理论的勃兴,而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打破了实证式的文学影响研究,在理论概念方面寻找比较的理由。这一改变有助于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前,中国与欧洲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联系很有限,所以中西比较文学就缺乏比较的基础。文学理论对东西方比较尤其重要,就因为比较的基础不再是事实的联系,不再是作家或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理论概念上的可比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文学理论为东西方比较文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尤其在比较诗学方面,可以让我们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理论带有普遍性,但也带有概念的抽象性。具体就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而言,文学理论的主导会产生至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的抽象。脱离开文学作品和具体文本的细节,理论的探讨往往从概念到概念,或割裂文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地歪曲文本,使之为理论概念服务。研究者对文学理论缺乏深入理解,也就不能真正把握理论概念,无法用自己清晰的语言来表述和讨论比较文学的具体问题,于是以晦涩冒充深刻,写的文章故弄玄虚,让人读来不知所云,而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是文学理论基本上是西方理论。如果说从美国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德国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都还是以研究文学为主的理论,那么随着西方社会本身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和性别研究等,就更多与西方社会和政治的环境相关,与文学文本则渐离渐远。因此,西方文学研究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带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色彩,最终引起很多文学研究者不满。这种西方理论,尤其是与西方社会政治环境关系密切的文化理论,如果机械地搬用来讨论中西比较,往往方凿圆枘,格格不入。与此相关,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常常讨论的“失语”问题,即当代的文学研究,从理论概念到研究方法都来自西方,中国学者好像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但随着我们对中西文学、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了解越来越多,也就有以扎实的知识和修养为基础、建立更大的自信、获得更多研究和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就会认识到,中西文学和批评理论可以相互发明,只要我们思考清楚了,就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来表述我们思考的过程和结论,而不会有“失语”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在这后理论的时代,不再简单挪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去重新思考什么是比较的基础。
二、以文本为支撑,重建中西比较的基础
譬如诗的概念,东西方各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相互启发。在西方,古希腊有模仿(mimesis)的概念,认为诗是以模仿来描述一个外在的行动。柏拉图把诗之模仿理解为像镜子那样简单照出事物的影像,对诗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之模仿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事物表面,而是可以用想象的虚构来揭示事物的本质。他把诗与历史相比,认为“历史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人则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具哲理,更严肃;诗叙述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叙述的是个别的事物”。无论柏拉图贬低诗,还是亚里士多德褒扬诗,都以古代希腊的模仿概念为依据来讨论诗的性质。但中国古人认为诗不是模仿外在世界,而是表现人内在的思想和感情,即《尚书·虞书·舜典》所谓“诗言志”;《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古印度,7世纪的婆摩诃(Bhāmaha)所著《诗庄严论》(Kãvyālankāra)提出“诗是音和义的结合”,而这就“成了许多梵语诗学家探讨诗的性质的理论出发点”。婆摩诃又进一步认为“‘庄严’是诗美的主要因素。而‘庄严’的实质是‘曲语’(即曲折的表达方式)”。对诗的起源和性质,东西方存在几种很不相同的观念,而且在这几种观念之外,还有如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其他传统里的观念。虽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所谓事实的联系或相互影响,但在比较之中,这些不同观念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诗或文学的起源和基本性质,丰富我们对诗的认识。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用语,有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象征、夸饰等,通过个别具体的意象,表现超出具体事物的普遍意义。在不同的文学传统中,作家和诗人们都会普遍运用修辞手法。有时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一些具体意象有意外的相似,会使人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欣喜,甚至令人不由得思考这些相似是否超出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等种种差异,透露出一点消息,让我们瞥见在人类思想和意识深处或许存在的某种超出偶然的普遍意义。苏东坡《红梅三首》其三有句云:“幽人自恨探春迟,不见檀心未吐时。丹鼎夺胎那是宝,玉人頩颊更多姿。”“玉人頩颊”有宋人赵次公注云:“頩,怒色也,玉人怒则颊红,故以此比红梅也。”用美人的面颊来比喻绽开的花朵,在中国文学里可谓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但东坡此诗特殊之处,不是用美人的笑脸,而是用美人生气,有怒色而发红的脸,来比喻盛开的红梅。《庄子·外物》早有“春雨日时,草木怒生”之句,用“怒”字来形容经过春天雨露的滋润,万物复苏,勃发生长之态。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描写红色的山茶花:“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花,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在作家诗人的想象中,“怒”不仅有一种遏止不住的生机和动力,而且表现为艳丽的红色。说来凑巧,英国17世纪诗人乔治·赫伯特(GeorgeHerbert,1593—1633)在他诗中,也用了十分类似的比喻:“Sweetrose,whosehueangrieandbrave/Bidstherashgazerwipehiseye”(甜美的玫瑰,你怒色娇艳/使冒失的窥探者拭目相看)。这诗句里的“angrie”即“愤怒”一词,注者直接说就是“red”即“红色”。这说明在一般读者看来,用“angrie”即“愤怒”来描写“甜美的玫瑰”颇不寻常,需要解释,而作注者直接说这个词在此的意思是“红色”,就省去了其间的缘由。东坡所写的红梅和赫伯特所写的红玫瑰,在东西方各自的传统里,都颇具代表性,两位诗人都用美人的怒色来比喻盛开的名花。中西不同传统里的两位大诗人,不约而同地使用它,其诗心文心,真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然而把这两首诗再作比较,在各自的文本环境里看起来,其间的差别又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东坡的《红梅诗》写梅花盛开,第三首全诗如下:幽人自恨探春迟,不见檀心未吐时。丹鼎夺胎那是宝,玉人頩颊更多姿。抱丛暗蕊初含子,落盏浓香已透肌。乞与徐熙画新样,竹间璀璨出斜枝。东坡所写的梅花充满了生机。最后两句说,如果请善画花竹的画家徐熙,用墨把这株梅花勾画出来,略施丹粉,在翠竹之间斜伸出一枝红梅,那必定会是一幅生气盎然的梅竹图。但赫伯特的“Vertue”(美德)一诗,写红玫瑰只是诗中一小节,其用意和东坡诗的用意全然不同。我把赫伯特的整首诗和我的译文也引在下面:赫伯特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诗中所写的红玫瑰虽然娇艳,但只是作为陪衬,突出整首诗的主题,即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皆为虚幻,无论是晴朗的白日、娇嫩的玫瑰,或是快乐的春天,都短暂存在于一时,最终都将化为尘土,而唯一永生的是具有美德的灵魂。与东坡诗中如“玉人頩颊”的红梅,与《庄子·外物》描绘的“草木怒生”那种蓬勃的生机完全相反,赫伯特诗中前面三节,结尾都落在一个“死”(die)字上面,最后一节才抬出主角来,那就是基督教神学强调的灵魂之永生不朽。所以赫伯特这首诗是以世界末日景象(apocalypticvision)为背景,带有基督教神学所谓生活在最后时刻(eschatology)的想象。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可以说完全不同。在思想文化背景上,东坡之诗与赫伯特之诗固然大不相同,但这两位诗人都以“发怒”和美丽的红色相联,用“怒色”来描绘艳丽的红梅或玫瑰,则在巧思和妙语的运用上,又有不期而遇的契合。尤其因为中西思想文化传统有巨大的差异,这种诗思与文心的契合就更使人觉得可贵,在超乎那些差异之上,为我们揭示出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用具体文本的例证来支撑中西比较,就不会流于空谈,也就可以使比较研究具有说服力。其实在西方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例如库尔裘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方法。这本书讨论了许多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重要观念,他所说的topoi即主题。另一部西方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奥尔巴赫的《论摹仿》同样以丰富的文本证据来支撑他的论述。此书开篇即讨论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9卷,描述奥德修斯在离家多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回到家里,却并不急于露面,而先乔装打扮成一个陌生人,但他的乳母尤瑞克莉娅为他洗脚,从他脚上的伤疤认出了他。荷马对这整个过程描写得极为细致,而且由倒叙过去,又回到现在,似乎故意放慢叙述的步伐。奥尔巴赫认为,造成“步伐缓慢”这个印象的真正原因,是在于要满足“荷马风格的需要,即凡是诗中提到的,都不会半明半暗,而一定要充分的外在化”。他继续描述荷马风格的基本特点说:“以充分外在化的形式再现某一现象,使其所有部分都历历如在目前,完全固定在其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之中。”然后奥尔巴赫说,取同样古老、同样具有史诗风格而其形式又完全不同的《圣经·创世纪》中一段,与荷马史诗相比较,就更能见出其风格特点。他选取的是《创世纪》第22章第1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让他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读过荷马史诗之后,再看《圣经》这一节文字,其简约实在令人吃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从哪里来,在什么地方对亚伯拉罕说话,为什么要这样试验他,此处全无交代。“上帝直接说出他的命令,但他的动机和他的目的,却完全没有说出来。”接下去亚伯拉罕也完全没有犹豫,直接按照神的命令,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带到山上,设立一个祭坛,而且准备举刀杀他献祭。这样非同小可的重大事件,《圣经》里只用了极简炼的语言写来,与荷马史诗那样细致入微的描写,真有天壤之别。奥尔巴赫对比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描述,就说明在西方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经典文本,一种是充分完整的叙述,另一种则是尽量简约的暗示,让读者去发挥想象来使之圆满,而这两部经典和两种风格,就形成了西方文学传统再现或模仿现实的基本模式。
三、结语
中西比较文学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比较研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明确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写一篇文章要讲出什么道理来,又如何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某一个文学或文学理论问题的认识,加深我们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和鉴赏。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论证,而论证必须基于文学文本的证据,不能缺乏证据或不经过论证就信口开河,否则就经不起严密的逻辑和文本证据的检测验证。说到底,我们需要多读书,多思考,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现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时才可能联想到各类相关的文本,列举丰富的例证,也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作出自己的一点成绩和贡献。这就是我们在后理论时代,做中西比较文学应当采取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作者:张隆溪 单位:香港城市大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