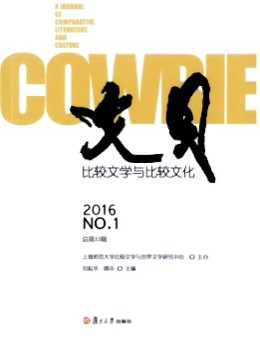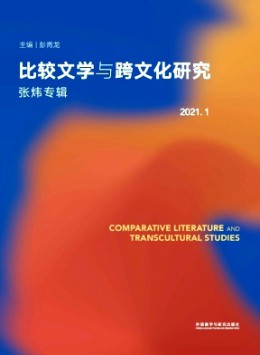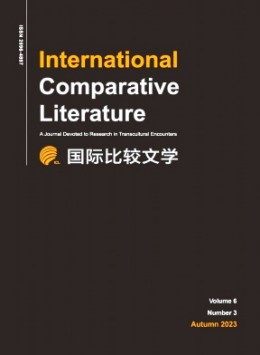比较文学合法性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比较文学合法性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一、比较之辩
一旦谈到比较文学的合法性,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做一个专题式的考察,这样以来首先应该纳入我们视域的即是“比较”一词。接下来的问题是,何谓比较,或者说,如何能完成比较。这一考察,作为奠基性的工作将为我们澄清“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的问思路径。比较首先有其哲学维度,而历来大哲学家们都不乏对其讨论,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已触及到这一问题了,他在《斐多篇》中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应该拒绝这样的说法: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一头是因为[高出一个]头",而那个比较矮的人之所以比较矮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可以]接受的惟一观点是,任何事物比其他事物高的原因只是因为高本身,比其他事物矮的原因只是因为矮本身。”显然,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进一步说,在柏拉图的哲学视域中,比较是无法完成的,而他的结论首先在于对流俗化比较观点的澄清,即,比较是自然而然之事,这一命题乃是自明的真理,不需任何反思。而在柏拉图的探究中,比较这一行为之所以呈现,事实上是分享了“高本身”“矮本身”这样的理式。那么问题是,凭借高本身,我们只能得出:甲比乙高。而凭借“矮本身”又只能得出甲比乙矮的结论。因为比较当中定然只能有一个标尺,也就是只能有“高本身”或“矮本身”这样一个理式。但是如果我们只凭借其中一个标尺的话,那么只能找到受比较二者的共同点,而无关差异。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形形色色的同一性理论粉墨登场,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增添所谓的利器,比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而它们无不是逻各斯主义同一性诉求的产物,只是诉诸于某种共在的标尺,而不能,也不可能找出差异的标尺。因为如柏拉图所述,既然是标尺,那么它只能是共在性的,所以,这只能是个悖论。而这些在共在标尺的先在前提下构建的比较理论,无疑是逻各斯主义同一性诉求的产物,在单方设定的标尺中,只能求同,而不能辩异,实际上不能完成比较,它们已陷入比较悖论而浑然不觉。
二、现象学式的境遇比较
那么,这岂不是说,比较本无可能?当然,如果把这一专题诉诸于常识的话,我们可以自然的说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怀疑主义。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不假思索的说,A比B高,C比D大,那么这种生活世界中的比较是否合法呢,我们已经提到,在同一性标尺的设定中,实际上无法区分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否能在一种境遇中完成比较呢?在现象学式的比较中,比较实际上是在一个境遇中完成的,比如我们坐下来看球赛,面对某一场景,会很自然说,A的跑动速度比B要快,这种比较,不需要先在任何共同标尺的设定,只是处在一个共同的比较情境之中,是这个具体的情境使我们顺利完成比较。这种比较是自然而然的,它自身有其自在的自洽性,也就是说在这种现象学的视域之下,它悬置了预先设定的同一性标尺,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悬置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当然,现象学本质上也是本质主义的高峰。在这个情境中,一切都变得明晰了,不必诉诸与外在的外在的逻辑设定,不必求助于高悬与比较者之上的标尺,而这个比较的完成,只与情境有关,与我们的意识结构有关。但是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我们需要诉诸于一个具体的情境,那么毫无疑问,在这个情境中,我们的判断肯定已经包含了我们之前习得的经验,这里也就自然包含了辨识能力的习得,但是,在现象学的视域之下,这些都是不成总是的。因为现象学本身的霸道在于,它在经验和先验之间的回溯。如果做一回答,那么可以说,我们可以设想,越向幼年经验回溯,越没有理想模型与标尺的地位,比较情境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这种境遇比较中,境遇就是在参与比较的A和B之外的不可或缺的第三者,它是非课题性、非对象化的,从而回避了同一性标尺的主观设定,而使比较顺利完成。在比较这一论题中,现象学路径的追随者不可谓不多,比如张祥龙等人。抛开此哲学论题不言,我们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内部也可以看到现象学式的比较方法,比如余虹,他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当中,把语言作为比较中的一个共属区域,在语言这一共属区域中,并非审美论或是工具论的,而是“后者能划定前者的范围和限度”但是,问题是,面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第三者,我们能否找到这样的第三者呢?这个第三者的设定有谁来设定,又如何设定,这都是其症结所在。吴兴明先生在评述余虹此书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但事实上,不仅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纬度不能向此所谓的共属区域归并,自古以来西方哲学的诸多纬度也不能归在语言学之维中,关键是,如此“强行归并”,还是通过还原达到的,我们在理解上就会产生歧义,你无法理解他究竟是陈述知识史还是在伸张自己的主义”所谓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尤其要面对这一问题,即,中西文化各自由其特定的历史和地域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分殊性的结构性,对此,有人把这个第三者设定为语言,即中西文化的“共属之域”,但显而易见的,这种比较显然与简单陈述A比B高不同,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同的结构性的总体,而在设定语言为第三者的同时,又已陷入同一性设定的泥淖中了。要研究作为观念历程的不同文明的思想史,我们依赖的,还是研究者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这些仍旧是思想者作为个人的主观视域,这样现象学意义上的向“纯粹意义”的还原便在文明总体研究和抽离中成了典型的乌托邦。归根到底,现象学式的自身意识回返仍然是主体哲学的形式,它的同一性场域寻求仍然是单一主体的诉求,从而无法兼顾到异。
三、比较之不可能
比较,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的事情,它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或是我们在比较中浑然不觉,但又对其完成。但这是生活境遇,而如果将其设定为专题,就此一维划定学科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一个学科本身必须观照成一个总体,而这个总体正如前文所言,是一个差异性和个体分殊性构成的混杂的整体,它绝对不是同质的。所以,如果任何人想要从总体中抽离出这一标尺,或是所谓的共在视域来完成比较的话,那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个在,作为单一主体,不可能渗透到主体间性的纬度,而如果提到主体间性,那么比较事实上同样是无法完成的,因为个在的分殊性正会因我们个人的逻辑结构,知识背景,先在经验等诸多层面的差异而不可能。在现代哲学和思想史的进程中,事实上,一些哲人已经取消了比较的可能性,而在对思想和立场悬置的同时倡导一种“知识社会学”式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在思想史梳理中,在其它相关的领域也大行其道,主体要悬置,要诉诸于问题,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引言中就谈到“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经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开始多样化,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这就是说,要突破认识论的现在框架,使知识的线性梳理和不确定中的合并关闭,而开启出一个新的空间,那就是,要把认识从他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解放出来,把他们从主观设定的圈套中澄清出来,而我们能面对的,只能是“位移”和“转换”。那么,毫无疑问,在这种对“位移”和“转换”的承认中,在主观的先在视野的有效悬置中,比较是不可能完成的,就以中国学派的跨文明比较为例,它必须设定两个文明整体,而这种设定本身已已经隐含了其先在承认的差异性,也就是设定了价值和标尺,而这个标尺是有谁来设定的,那就是问题了。比如,法国汉学家于连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更可靠,还是中国思想家葛兆光的梳理更准确,这事实上只能称之为个人的判断引发的论述总体。
四、结语
可能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逻各斯冲动,寻求一己的秩序总体,即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系统。恰恰是从这个意义上,比较是不可能的。进而,比较文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比较”总是意味着双方共同逻辑域或背景域的同一性设定,而这种设定是由单方完成的。而且就文明总体来说,即使从单方的历史性总体抽离出什么一二三特性来,也是颇值得怀疑的。特洛尔奇的《自然法理论与人类共同体》一文的最后一节(斯宾格勒主义与社会主义)说,我们应该在一边是海妖(她以动听的歌声诱惑过往的航海者,使他们丧命)居住的海岛,一边是危崖的狭窄的海峡小心翼翼地穿行。尤利西斯事先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免抵抗不住海妖的诱惑而前去送命。现代先知式话语如同海妖的歌声,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恐怕也应该像尤利西斯那样把自己事先“绑起来”。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