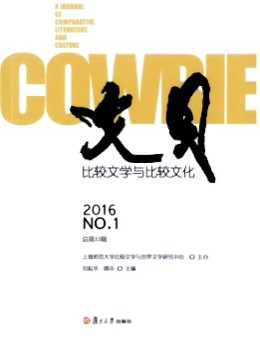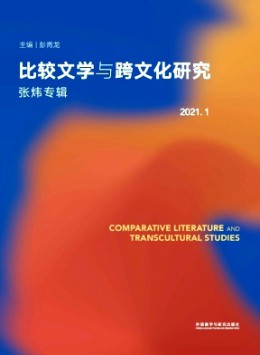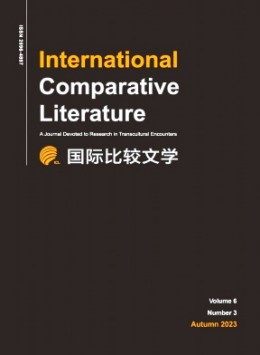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前史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前史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一、《诗学》中的比较思维
有关《诗学》的比较思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还是《诗学》的主体内容:摹仿说、悲剧论和艺术的功用。我们认为,《诗学》的言说方式贯穿着比较的思维,这是一种侧重于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张尚仁在讨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后认为:“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史,在欧洲认识史中属于对主体、课题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开始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这一认识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成果的集大成者。”[4]94文学研究隶属于哲学认识,从方法论上看,《诗学》在进行文学比较时,主体已经不做情感的投入,所分析的概念纯粹是从对客体的比较中抽象出来。马强据此认为,《诗学》是纯理论的思维,“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运用逻辑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这一切推动了西方科学的长足进展。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5]34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诗学》的比较思维走在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路途中。朱光潜先生对这一思维概括说:“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用的都是很谨严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出规律、下定义。”[6]66这一概括更为准确的说明了比较方法在《诗学》中的运用。《诗学》以比较的方法确定摹仿艺术的种差。亚里士多德给事物下定义贯彻“属+种差”的定义方式,诸多艺术门类在“属”上都是创制艺术,而在种差上存在着区别。种差上的区别就是艺术分类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从种差上为艺术分类:“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3通过三方面种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划分,比如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凭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7]4
这是从摹仿的方式确定画家、雕刻家与游吟诗人、颂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区别。前者用颜色和姿态摹仿事物,后者用声音摹仿事物。在论述悲剧、喜剧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所摹仿的对象:“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7]8-9可见,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创制知识这一“属”内的诸多种差依据摹仿的媒介、摹仿的对象与摹仿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表现为绘画、颂诗、史诗、喜剧、悲剧等艺术门类,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艺术门类的特点也随之得以展现。《诗学》在论说悲剧定义与创制方法时也贯穿着比较思维。《诗学》的主体部分是论述悲剧的定义与创制方法,这是古希腊戏剧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就戏剧而言,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在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前一年逝世,因此,在戏剧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阅读到古希腊最为优秀的所有戏剧家的著作。《诗学》作为指导学生艺术创制的秘传学问,亚里士多德当然也要对悲剧的创制方法作详尽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7]19这一定义是通过比较摹仿方式、摹仿媒介和摹仿效果三方面内容而确定,这一比较性的定义囊括了悲剧的六大要素,同时也确定了悲剧创制的技术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安排就以是否能够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为标准,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7]31为了达到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情节安排的“突转”、“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在情节“突转”上,他要求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只能写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由顺境转入逆境。在布局上,亚里士多德要求单一的布局,他通过比较单一布局与双重布局说:“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局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也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7]41-42
从这些言说方式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非常理性的。首先他通过比较种差确定悲剧的定义,然后以悲剧所要达到的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的要求确定悲剧的情节安排。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情感与客体保持着距离,他论说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诗学》在批评方法上也运用着比较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诗学理论是在其老师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反思的对象。《诗学》中一些经典的论述往往来自与柏拉图的比较。例如,在论述诗能否摹仿真理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7]28-29这段论述表面上看,是诗与历史的比较,实际上是对柏拉图诗是“摹仿的摹仿”,“诗与真理隔着三层”的观点的反叛。在对悲剧效果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与其老师对举。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引发了群众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了控制,因此破坏了“正义”。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的认为,悲剧能够净化情感,从而逆反了柏拉图的悲剧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构成了对比关系。陈康先生说:“在亚里士多德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影响之广是惊人的。在这项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以柏拉图哲学为背景。”[8]406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比的方法更为集中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柏拉图哲学的反叛。通过比较,诗的特性得以确认,其地位得以张扬。
《诗学》的比较方法是理性的思维方法,祛除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开始,逐渐摆脱了神话思维的影响,运用了概念、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这是人类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的飞跃。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希腊哲学史》探讨了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关系后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将这种想象性的猜测转变,飞跃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维,就产生了哲学。所以,古代希腊神话应该说是希腊哲学的史前史。”[3]84飞跃是一种质的变化,哲学斩断了神话的脐带,以新的姿态开辟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亚里斯多德是这次文化飞跃的集大成者,在思维方法上吸取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智慧,祛除了原始思维的想象性、以己度物和以象见义诗性痕迹,开创了抽象高蹈的形式逻辑思维。《诗学》中的比较方法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体现,比较可以是三段论的辅助,也可以是走向归纳结论的桥梁,因此,《诗学》灵动而又深刻的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许多结论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诗学》隐喻理论的理性诉求
比较的思维在《诗学》中有另一层面的运用:隐喻。隐喻是比喻的一种方式,即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事物。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看,隐喻原是远古先民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和以己度物的诗性特征。维科在《新科学》中论述了先民想象力旺盛、推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思维特征,指出处于这一阶段先民的思维方式为隐喻,他说:“根据上述来自玄学的这种逻辑,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的来源。……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9]176在维科看来,原始时代,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薄弱,词汇的积累也比较贫乏,因此,先民表述较为抽象的事物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比如以具体的“头”指示抽象的“人”的概念。可见,隐喻是原始先民出于本性的表述行为。隐喻到了亚里士多德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一种原始的思维方法发展为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法。语言学家埃科认为,“隐喻这个论题,是亚里士多德首次在《诗学》中提出的。”[10]179埃科所谓的首次,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运用理性思维论述了隐喻的理性运用。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原始人如何理解物我关系,在城邦注重演说能力的时代氛围中,亚里士多德更加注意语言运用的技巧。汪子嵩等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描绘了古代希腊修辞学盛行的状况后,说:“在古代希腊修辞学早有创立和研究,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活跃,演说和论辩是政治上谋进取、法庭上舌战取胜的重要手段,智者修习修辞术风靡一时。”[3]
316
早熟的城邦民主制催生了修辞术,从而使隐喻的诗性披上了理性的外套。亚里士多德论述隐喻,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智者的学说,顺应时代氛围,将隐喻限制在修辞技巧的范围内。埃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时说:“隐喻被定义为是使用另一种类型的名词,或被定义为由一对象的真正名词到另一对象的转移,通过由类到种或类推作用可以出现的一种行为。”[10]179-180这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能力与技巧,亚里士多德说:“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1]8可见,理性思维遮蔽了隐喻的诗性智慧,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取代了隐喻所蕴含的诗性温情,人及其利益开始在文化生活中凸显,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上帝”。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隐喻思想正是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探讨了隐喻的运用,其具体的论述贯穿着理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字的一种类型,他说:“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7]73隐喻既然是用其他事物的字借来表述这一事物,它必然涉及到甲事物(别的事物)、乙事物(所表述事物)和隐喻字三方面的关系。隐喻字原用于表述甲事物,现在不表述甲事物,而用来表述乙事物,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其目的就在于以熟悉的甲事物替代听众不熟悉的乙事物,从而使人们更好的认识乙事物。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隐喻的类型: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借种作种说明了甲乙事物之间构成了种与属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借用往往是一方比较容易感知,一方难以认识,所以隐喻是人们学习陌生事物、知晓陌生事物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12]176
隐喻所产生的愉悦效果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快感,其理性色彩非常强烈。亚里士多德还论述到了隐喻的类同性,这种类同布莱克称之为比较理论。亚里士多德说:“类同字的借用:当第二字与第一字的关系,有如第四字与第三字的关系时,可用第四字代替第二字,或用第二字代替第四字。有时候诗人把与被代替的字有关系的字加进去,以形容隐喻字。”[7]73-74类同字的隐喻是最受人欢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隐喻能够“使事物活现在我们眼前”[11]187隐喻的四种类型都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只不过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和借种作种三种类型是借语词的形象性使事物活现于眼前。比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俄底修斯曾作万件勇敢的事”、“用坚硬的铜火罐割取血液”,语词之间的换用增加了句子的形象性。类同性的隐喻则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似与类似关系,是相似性基础上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关系。隐喻词实际上就是事物之间类似关系的体现,因此“隐喻关系不能太远,在使用隐喻来称谓那些没有名称的事物时,应当从切近的、从属于同一种类的词汇中选字,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该让人明白这种切近的关系。”[11]167类同性隐喻的比较在词语的聚合关系中进行,第二字与第四字之所以能够相互替代,就是词语的聚合关系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修辞学家布莱克据此说:“如果一个作者认为隐喻就是把一种业已存在的类似或相似性呈现出来,他所持的这种看法我就称之为比较理论。”[13]146布莱克从比较理论的角度论述隐喻,他着重的是隐喻所体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布莱克,隐喻背后的诗性思维已经完全消失,隐喻成为诗人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法。《诗学》中的隐喻首先是一种悲剧的修辞技巧。亚里士多德是在论述名词的种类时讲到了隐喻字,它应该隶属于双字复合名词。隐喻字在悲剧中的运用可以形成高雅而不平凡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说:“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克勒俄丰和斯忒涅罗斯的诗风格即是如此。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7]77
选用隐喻字避免风格的平凡,是针对悲剧的写作技巧而言,通过这一修辞技巧,悲剧避免了平淡,增强了审美价值。将隐喻作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修辞技巧,体现的是理性的技术思维。隐喻能够赋予平凡的语言以表现力,从而引起观众的注意,煽动起观众的感情,获得观众的认可,这正是法律演讲、议政演讲和宣德演讲所要达到的目的。隐喻就是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技巧性修辞方法。法国哲学家利科曾对亚里士多德分别在《诗学》与《修辞学》中论述隐喻感到惊奇,他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修辞学与诗学的这种二分,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喻就属于这两个领域。”[14]利科还只是从修辞学看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没有体会到隐喻所蕴含理性思维。亚里士多德是将隐喻作为一种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表达技巧加以分析,《修辞学》服务于演说的效果,《诗学》服务于悲剧风格的塑造,因此,两者之间的隐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隐喻的方法、构成、内容必须顺应使用隐喻的目的,因隐喻目的的转换而改变,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主要特点。《诗学》中的文学比较与隐喻理论是希腊轴心期理性精神的文化成果。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期”,是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集聚能量的突破,奠定了以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标准。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孔孟时代均属于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期文明。然而,中西轴心期文明所奠定的基础却有着内在的差异,中国文明保存着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的诗性智慧,希腊文明则断裂了与诗性智慧的联系,将诗性智慧导向了理性思维。
张光直认为“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的,主要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15]17-18轴心期这种文化转变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比较思维的不同形态。中国比较思维保留着诗性智慧,是诗性智慧“以象见义”特征在文明时代的延续,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诗性关系的持续存活。西方比较思维则斩断了与神话的联系,诗性智慧转变了理性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类似性想象被理性的逻辑、冷漠的利益算计所取代。《诗学》中的比较思维与隐喻理论正是文化断裂后新的文明形态的文化成果,其运思方式迥异于中国比较思维。可见,尽管中国学者将西方littératurecomparée翻译为比较文学,但中西文化在轴心期的“比较”还是有着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甚至影响到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形态,形成了中西各具特色的文学比较研究。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