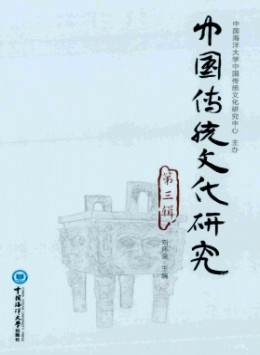传统建筑构件门槛浅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传统建筑构件门槛浅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门槛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极富文化与象征意蕴的小木作构件。本文以门槛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和实例分析的基础上,从概念辨析、类型划分以及功能与形式的复杂化发展方面,对门槛的历史沿革、内涵意义与发展演变进行解读,从中得出可供当代建筑传承与发展的3点启发,即“动态的”空间观、兼具界面与空间双重属性的外围护结构以及“过渡空间”的重要作用,以期应对建筑与城市日趋隔绝、地域性消失的局面,避免建筑沦为非人性化的“居住机器”。
关键词:门槛;传统建筑;建筑构件;界面与空间;过渡空间
0引言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门既是划分不同属性区域的分界,也是沟通、联系内外的枢纽,有着特殊且重要的意义。李允鉌先生在《华夏意匠》一书中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门堂之制”[1],即充分体现了这种重要性。传统建筑的门槛是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飞檐起翘的屋顶、结构繁复的斗拱、精美绝伦的彩画一同成为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文化建筑的特色构件,其所蕴含的实用功能、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赋予门槛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关于传统建筑门槛的关注较少,既有研究主要针对门槛的尺度、形态的历时性变化[2],门槛的构造、材质、安装方式等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差异[3],以及古代文献中关于门槛的释义称谓变化及其原因[4]等方面,但大多停留在孤立的建筑构件层面,尚未将门槛与门、台基的形式演变以及建筑装饰的发展过程作为整体考虑,同时也缺乏对门槛现代意义的探索。由此,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在对有关门槛的古文献和现存实例进行整理归纳的基础上,从功能与形式的发展及其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方面,对门槛进行重新解读,以期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1门槛的概念与类型
1.1门槛的概念
门槛,探其肇源,有“户限”“门阀”“门阃”等多种称谓[5]。《辞海》将其解释为“门下之横木”,即指位于门扇下部紧靠地面的横木(或长石)。史前时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门槛的雏形。当时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墙体与屋顶尚未区分,门设于屋盖之上,其下设有土脊状矮墙,以遮挡风雨、尘土的侵袭(图01)[6]。随着建筑形制的不断发展,成熟时期的门槛通常由柣(通读zh)和地栿板两部分组成。其中,柣为起支撑、稳固地栿作用的构件,《尔雅》有言:“樗……为柣为枨且不可,况为负任器耶?”柣具体可分为卧、立两式(图02)。卧柣为横于两颊之间带槽的枋,后世较为常见;立柣则为紧贴立颊带槽的枋,仅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萧照的《中兴祯应图》中可见此形象。地栿板在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中具体指固定于门扇下方、嵌入两柣之间的横向枋材[7],即通常认为的门槛。清代称其为“下槛”,用以连接相邻柱脚,本身并不承重,可随意放置或抽离。
1.2门槛的类型
门槛一般可分为木、石、铁3类。其中,木质门槛最为常见(图03)。《营造法式》中对其尺寸有明确规定:“门限长随间广,其方二寸,若柣断砌,即卧柣,长二尺,广一尺,厚六分。立柣长三寸,广厚同上。”“地栿长、厚同额,广同柣”。元代民间木作匠书《梓人遗制》中也有类似规定:“地栿长同额,广厚同柣。若断切,不用长地袱。两柣之下,安短限(即卧柣),下入立柣木之内。”[8]清代因多用隔扇门,构造简化,故《清式营造则例》中对门槛的规定也相应简化,仅规定其宽度是柱径的五分之四,厚度是柱径的十分之三[9],又出于车马通行安全的考虑,在门槛两侧增加了抱框,作为门槛的组成部分,其宽度规定为柱径的三分之二,厚度为柱径的十分之三[10]。另外,亦可见石质或铁质的门槛(图04、图05)。古文献中也有相关的描述,如:韩愈在《谴疟鬼》中有“清波为裳衣,白石为门畿”的描述,即指以白条石制作的门槛;文震亨《长物志》卷一中所说的“(门)若用石梱,必须板扉”,也是使用石质门槛的意思;张怀瓘《书断僧智永》中有“人来觅书并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的记载,说明也有用铁皮包裹的门槛[5]。
2门槛的演变
与其他中国传统建筑构件一样,门槛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逐渐多样而不断发展变化,总体呈现复杂多元的趋势。在功能方面,由实用性逐渐向精神性与象征性发展;在形式方面,则类型丰富、灵活多变,出现了既是等级象征又出于通行考虑的移动式门槛,以及更加强调装饰性和纪念性的双(多)重门槛。
2.1门槛功能的变化
2.1.1实用性功能。初期,作为建筑构件的门槛具有较强的实用功能,可起到地圈梁的作用,使建筑底部结构相互连接为封闭的整体,增加结构强度,对提升建筑稳定性和抗震性能有一定帮助[2]。另外,受限于木工工艺和材料性能,中国传统建筑的门扇通常无法完全闭实,与地面之间常留有一段缝隙,而门槛恰好可以将其遮挡,起到封闭空间的作用,阻挡从底部吹入的灰尘、雨水,或防止蚊虫、野兽进入[3],同时对门扇也是一种保护。2.1.2象征性功能。后期,门槛的结构意义与实用性质淡化,精神与象征意义逐渐成为主导。一方面,门槛的高度、材质与装饰程度成为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高度为例,通常情况下门槛的高度为五寸,因“五”数主五行,可防财气外泄。也可以是三寸六分或一寸二分,与一年365天或12个月数字相契。另一方面,门槛超越了普通建筑构件的范畴,被赋予伦理意义,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蕴含了民间传统对尊卑、利弊、吉凶的心理暗示。如《论语乡党》中有“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一语,即指在进入官府时要避免踩踏门槛,从而规范人的行为活动。一些古代医书记载门槛附近的“门限土”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具有攘灾辟邪、驱鬼除疫的作用,体现了对门槛所代表的神灵与祖先的敬畏。
2.2门槛形式的发展
2.2.1移动式门槛。普通的门槛是将地栿板固定于柣槽内,无法随意移动,高度较低,可一步跨过。唐宋时期出现了“绰楔门”,其两侧立柱下端安装有斜切的木条,内部开出插槽,可将梯形的活动门槛向下插入或向上提起,专为有身份的官宦车马进出通行服务[11]。相关文献如《宋史孝义传》中记载:“旌郭义家,于其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下广上狭,饰以白,间以赤。盖亦沿五代之制,皆官为建造也。制或设于门,或别建他所,或四柱,或二柱,其上亦有用乌头者,盖合唐、宋、五代之制而参用之。”后期逐渐演变为仅供特权阶层使用的“乌头门”(也称“棂星门”),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代表(图06),如《唐六典》中明文规定:“凡六品以上,始用乌头大门。”大门。”除此之外,鉴于商贾活动、车马通行的需要,民间建筑中出现了“断砌造”(俗称“将军门”)的特殊类型(图07)。其主要特点是其台基并非整体,而是分成左右两半,中间开辟道路,以供车马通行。因此,这种门槛(也称“门挡”)同样可以灵活拆卸,通常高至70~80cm,以金属或竹片贴面,起到保护与装饰的双重功能,俗语称之为“高槛倍之通月兔”“门槛拔去迎达贵”[12]。在《清明上河图》中亦可见到此类特殊的台基与门槛形式。2.2.2双(多)重门槛。明清时期,礼制渐弛,出于纪念性与装饰性考虑,部分特殊建筑中的固定式门槛逐渐向层层递进、装饰繁复的双重乃至多重门槛发展。有“民间故宫”之称的福建客家培田村久公祠,其大门前所建的一座三开间廊庑即采取双重门槛形式(图08)。外槛石质,配合四根雕琢石柱,两方两圆,内槛木质,于正中开设大门。门槛上方的五重斗拱结构雄健、出檐深远,颇有唐代建筑遗风[13]。
3门槛的现代意义
门作为内外衔接与转换的关键部位,由台阶、门扇、门槛、照壁等构件组成完整的空间单元,起到界定并区分公共与私密两种性质空间的作用。其中,门槛部分体现了一种“动态的”空间观,即通过略带强迫性的抬、放腿动作和人体重心的升降变化,配合空间的收放、光线的强弱,欲扬先抑,将进入的过程延长。其作用或意义有两个方面:首先,心理层面的过渡与社会/个人身份的转换,与日本建筑师筱原一男(KazuoShinohara)在“上原的住宅”中故意裸露混凝土树状斜撑一样,“并不是让建筑直接服务于住户,而是让居住在里面的人去努力适应建筑,正因为有了这种适应,反而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14];其次,在由单纯的“一层皮”式的外围护界面向有“厚度”的空间转换过程中,门槛赋予建筑入口部分层次性、连续性和多义性,包含了门槛实体、空间与人的活动,具有界面与空间的双重属性,成为一种“复合界面”(multiplexinterface)[15]。类似的空间思想在西方语境下也有所表现。20世纪50年代,第十次小组(Team10)成员、荷兰结构主义建筑师凡艾克就提出了“门槛”(或译为“门阶”)理论。他认为,在建筑中门常常作为界定内外的分界,同时又是两者的连接,属于“中性空间”,并具备上升到人的意象经验(即“领域感”)的可能,是建立个体与空间、环境认同的关键,可用于对抗现代建筑中将地域文化差异与人类情感需求抹杀的所谓“通用空间”或“均质空间”。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门槛与之意义相近,甚至比门更为准确地扮演着内外空间转换的角色,其所体现的“过渡空间”(transitionalspace,或称“灰空间”)价值是当代建筑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换言之,建筑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之间”(in-between)的部分[16-17]。
4结语
门槛因其处于建筑内外之间的关键位置,被赋予重要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随着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逐渐被视为落后无用的封建糟粕而遭淘汰。客观地讲,门槛形式的消亡实属必然,但其空间意义、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仍给当代建筑以诸多启示:其一,以“动态的”空间观念对抗现代建筑空间的过分简洁与平铺直叙,反思将地域文化和人类情感抹杀的所谓“通用”“均质”空间,为建筑空间赋予体验感和文化性;其二,建筑外围护结构应兼具界面与空间双重属性,重视人在其中的活动与交往,营造“场所感”;其三,对建筑“过渡空间”的重视,避免内外割裂或独立,强调城市环境与建筑空间应该相互渗透、交融,进而形成连续的统一体。
作者:宋晋 于家兴 张玉坤 单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