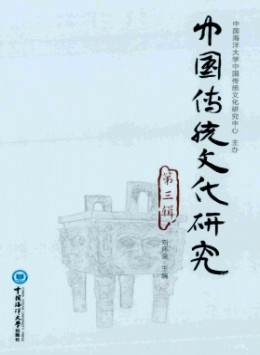传统建筑的经验理性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传统建筑的经验理性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在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中国传统建筑在为人提供物质功能需求方面,存在非常恰当的经验理性。中国传统建筑的经验理性,体现在营造过程各个环节中,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归纳总结,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思想。
建筑环境的经验理性
查阅中国古代的大量文献,无不都表达着“因天材、就地利”,顺应自然的经验理性内涵,这首先体现在城市规划方面。《管子》载:“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就表达了经验理性的精神。与城市及建筑营建中“象天法地”的拘泥于形式的伦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互补机制。在城乡聚落和建筑活动中,中国古人表现出重视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意识。但古人对于这种环境意识的理论,概括阐释得一直不够充分,有关环境意识的论述,大量混杂在浩如烟海的风水书中。尽管风水书中夹杂了大量的荒谬的故弄玄虚的迷信活动,但其中颇为丰富的、理性的、基于相地实践经验的“因地制宜”的环境调整意识,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藏风聚气”的理想模式中,取得负阴抱阳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坐北朝南的方位。若受地形的高低限制,风水师往往会依地势走向,偏转建筑的朝向角度。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以子午线的正南轴为基准,在南偏西30度和南偏东30度之间,这恰恰与日照的最佳朝向相吻合,从而取得了建筑朝向与“日照”的天时、“地形”的地利的双向协调。再如村庄的出水口以“巽”位为吉位,这是因为中国地形地貌的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是自西向东,以东南向为出水口,是符合河流流向规律的。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民居村落的布局大都反映出风水中依形就势的规划意识,民居聚落的形态既配合山川形势,又强化山川形势,使得建筑景观所散发的人文美与自然美得到完美的结合,相互的统一。[2]在这个过程中很注重实用功能需求,从而使功能与美观得到统一。
建筑选材的经验理性
中国传统建筑在构筑选材上,注重经验积累,表现出很强的务实性。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要构筑体系,但又不拘泥于木构架的约束,常常是就地取材,根据所选材料的材性采取合宜的营造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相济的木构架建筑体系为主体、建筑选材多样、构筑形态多元的特点。土木相济的木构架建筑体系,之所以能从远古时期长久地延续下来,取材方便、构筑体系的合理是重要的因素。从取材上讲,中国古代的土材和木材资源都很丰富。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地区,有着很厚的黄土层,这深厚的土层不仅生长出多样的作物,也以其优良的材性从一开始就成了构筑房屋的材料。土材不仅是易于挖掘,而且保温、隔热、防火和隔音性能优良,这些都使得土材成为木构架建筑中重要的组成成分。中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纯熟的用土机制。首先来看夯土台基,这一技术出现得很早,夏商时期的“茅茨土阶”表明在当时已广泛使用夯土台基。其二,就夯土高台来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这一方式盛行一时。木构建筑依附于高台组成庞大的组群,形成了远胜于木结构单体的宏伟体量。其三是版筑土墙,这是一种长期使用的木构架建筑墙体,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有时会在土中加入草根、竹片或碎瓦片,用以提高版筑土墙的力学性能。其四,土筑坯墙,就是将土和泥注入模范,拓成砖块形状,晒干后叠砌成墙体的做法。有时,土坯墙不仅起围挡作用,它还可以稳定柱网,提高建筑的整体性,增加建筑刚度。[3]此外,土材还用于地面和屋面。上至屋面,下至台基,土的身影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随处可见。土材在木结构体系中广泛使用,使得承重结构和维护结构相分离,从而使木材和土材各得其所,这就大大提高了木结构建筑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在中国传统建筑木构架承重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以穿斗式和抬梁式两种基本形式的木构架互补的机制。中国古代匠人对木材很早就有“横担千,竖担万”的说法,可见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木材力学性能上各向不同性的特点,其中以纵向的抗轴压能力最强,木材的抗弯性能犹弱。抬梁式木构架体系是梁柱支撑体系。梁作为受弯构件,虽可以达到六步架的跨度,但同时也要付出增大梁柱截面积的代价。穿斗式木构架体系则是檩柱支撑体系。穿枋起拉结作用,不受弯,木柱间距缩小,上部荷载不需要经过受弯的梁即传入受纵向力的柱,且由于分配到每根柱上的荷载减小,柱的截面也可缩小。由此可见,穿斗式在力学性能方面比抬梁式更趋合理,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由于柱子过密而不能适应大空间要求。因此,抬梁式建筑在官式建筑和大材较易得的北方地区使用得较多,而穿斗式建筑在民间建筑和大材难觅的南方地区使用得较普遍。[4]从明清以来斗栱的力学作用不断消减而趋于装饰的趋向来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对木构架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匠人对木材力学性能运用,走向经验理性。纵观中国古代建筑木构架体系中抬梁式和穿斗式的互补运用,就能充分说明这种体系机制的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从木构架体系后来的木材力学性能的合理化趋向,也无疑说明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经验理性特点。
建筑组群的经验理性
由于木构架体系的局限,中国古代单体建筑体量上不能做得过大。中国古代建筑都是由几个建筑单体围合成院落,再由若干个院落组合、连接而成为建筑组群,从而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的。[5]这种与西方建筑迥异的离散型建筑布局特点,从其诞生时就显露无遗。而经过几千年的岁月考验,在不断的工程实践中,这种离散型布局形态一直贯穿始终,经久不衰。这种布局形态是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农耕文化最合适的组合方式,也符合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需求。除此之外,这种布局形态能够贯穿始终地存在,必然有其使用功能上合理和普遍适应的一面。首先,这种闭合而中间庭院露天的院落,具有气候调节机能,可以明显地改良气候条件,将不良自然因素排除在外。有院墙和屋宇围合的封闭空间,可以有效地阻挡寒风和狂沙的侵袭,而天井和屋檐的结合又可以满足遮阴和采光等要求。其次,与底层独立式建筑布局相比,围合式的庭院布局有更高的土地利用效率,用地效益较高。其三,土木共济的木构架建筑相较于西方的砖石建筑,坚实程度和防护性能较差,而庭院式的布局形态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这些由单体建筑组成的院落,由坚固的砖石和厚厚的围墙包裹起来,有时再在围墙上布置角楼,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线,提高了建筑组群整体的防御性,防护戒备的功能较强。其四,有利于防火安全。木结构建筑本身的防火性能很差,虽然中国有高超的木结构使用经验,也可以构建出很高的木结构楼阁建筑和恢弘的集中式建筑,终因其很差的防火性能逐渐趋于离散型的布局。通过建筑之间的防火山墙,可有效地延缓火势的蔓延。离散型建筑布局最大限度地减小了火灾对建筑的破坏。其五,中国古代建筑不论是建筑单体还是建筑组群,都呈现出一种“通用式”的设计理念。这就如同中国古代的服装、衣服和人体之间并不会要求完全吻合,而是做得都比较宽大,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灵活性和普遍的适应性。建筑组群的普遍适应性,体现在建筑功能的普遍适用性和地域的普遍适应性。其一,功能的普遍适用性。对于围合着的庭院,既是建筑组群的内部空间,又是建筑单体的外部空间,它可以根据建筑组群的用途呈现出不同的用途。在宫殿、寺观建筑中,庭院可以放大到极广阔的尺度,成为各种礼仪祭祀活动中大流量人群的聚散场所;在民居建筑中,各种家务活动、副业生产、休息闲聊和婚丧嫁娶等各种活动,都可以在庭院中进行;在园林建筑中,院落中的掇山、理水、置石、种植花木,又将院子变成了园主诗意的栖居之地。其二,地域的普遍适应性。同样是庭院式布局,在不同地域会根据当地的环境特点,对庭院做出相应的调整,表现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北京长期处在封建王朝政治中心,受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限制。北京四合院就俨然成了等级礼法的物化形态,展现出分明的等级制度。同时,北京四合院的空间尺度,又与当地自然气候和使用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契合。庭院空间宁静、安全又生机盎然,院落严整、端庄而内向性强。晋陕窄院的庭院狭长,厢房间数较多,常做成一层半的阁楼,上面半层不住人,仅用于储藏。晋陕窄院分布于山西晋中、晋南和陕西关中地区。这是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对四合院作出的改良。这些地区夏季炎热,窄院可以使庭院的阴影区域扩大,而较高的阁楼使东西厢的住屋避免了阳光的曝晒。这些地区风沙较大,两厢的靠拢可以使房屋之间相互遮挡,避免风沙的直接侵袭。由于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用地紧张,所以增加院落进深无疑更加经济。[6]东北民居常常是采用“一正四厢”的形态。东北地区冬季严寒,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保暖、日照和御寒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礼制约束较弱,加之土地辽阔,从而形成了相应的“一正四厢”的形态。[7]东北民居庭院宽大,日照充足。正房中,梢间和次间常设有炕,明间集中有做饭和烧炕合用的大锅,成为厨房兼御寒挡风的过渡空间。为了防寒、保暖,将厚厚的墙体包裹住木构架,墙体有砖墙、土坯墙或砖墙与土坯墙混用。天井院是南方地区院落的主要形式,四周用建筑围合,仅在中间留下犹如井口一样的小院。南方地区气候湿热,这种天井院既可以遮阳避暑,又有效地改善空气流通状况。
建筑单体的经验理性
台基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避免水湿和虫害。高高抬起地面的台基,可以很好地保持其上土木构件的干燥,避免水湿和虫害的侵扰。中国木构架之所以可以长久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赖于夯土技术的发展。土基的夯实有力地阻止了地下水的毛细作用。一方面,给木柱和土墙提供了相对干燥的环境,能有效保证土木结构的工程寿命。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古代早期喜欢席地而坐的中国人可以避开潮湿的地面,有益于人的舒适和健康。二是台基发展到后期,基础用磉墩取代了满堂夯土,台基起到了稳定基础的作用。作为台基的附件,台阶和栏杆都是从实用功能出发来考虑、设计和规定的。比如说台阶的坡度选择就是这一理性推敲的典范。宋代喻皓所著《木经》里说:“阶梯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图1)[8]这样,在保持轿身水平的同时,前后的轿夫都可以保持很舒服的姿势,正好体现了现代基于人体工程学的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在古代勾阑和须弥座形式的演变中,可以看出,从木材权衡向石材权衡的过渡。“阑干”一词,在古语中意思是横木为阑,纵木为干。这说明阑干是木制的。而由古代壁画和考古研究发现,中国历史早期的阑干确实是木制的。由于露天木构件在长期的日晒雨淋中极易损毁,后来过渡为石阑干。木材向石材过度的阶段,石阑干是以仿木的形式出现的。较之于清式石阑干,宋式石阑干看上去可以分解成更多的小分件,而小分件之间似乎是榫卯结合的。宋式石阑干的望柱间距大,寻杖细长,万字板很薄,常有镂空雕饰,这些都呈现出一种轻灵、修长、纤薄的特点。这种气质更适合于木结构,而用于石构件上无疑增加了雕刻的难度,构件的耐久性也很难保证。反观清式石阑干,每隔一块栏板设一块望柱,栏板更加整体,已看不到细小的分件;望柱间距缩小,寻杖变得短粗,荷叶净瓶变得肥硕;枋板更加厚实,取消了镂空雕刻,仅有浅而规整的浮雕。这些都呈现出厚重、沉稳、有力的气度。这显然更符合石构件的气质。在宋、清两代须弥座的比较中,同样可以看到从仿木向石权衡完善的变化。须弥座最初用于寺庙佛像的底座,由木头雕刻而成。后来受佛教文化影响,须弥座转而被用于建筑台基,由木材作改为砖作和石作。宋代正处于须弥座的仿木时期,这时的须弥座的层次多而密,雕刻细腻、繁复,这都是对木制须弥座的效仿。这显然既费工,又影响构件的耐久性。清代的须弥座已经在石权衡的完善之下,显得更加合理:层次被大大简化,雕刻趋于肥硕、厚实,体现出沉稳和庄重的品格。这种勾阑和须弥座形式的由木权衡向石权衡的过渡、演变是如此的漫长。因为在中国述而不作的传统下,在形式背后文脉的延续过程中,建筑结构和构件的每一次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显得是那样的步履维艰,都要经历漫长的岁月考验和时代的打磨,在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和许多败笔的总结之后,才作出艰难调整。建筑上很多看上去不起眼的变化,其实是在匠人们悉心经营和精心推敲之下,出色匠心的运用。如木须弥座上原有的几根易于积水的线脚,在最初移到室外时,室外雨水的积存,在室外冷热骤变环境下,很容易出现冻胀现象,因此这些线脚很快就会裂开、脱落,石构件中这些细小的线脚,在其他雕饰还完好的时候就已经坏了。匠人们在长期的实践后,总结了线脚的这一弊端,进而改变了石构件的样式,使雕饰更加符合石材的材性。又比如石栏杆中勾阑栏板两侧的“素边”,它是之前木栏杆中许多小分件的概括和整合,它的妥帖、自然正是石质材性和石作形式的契合。中国木构架建筑结构逻辑十分清晰,在彻上露明的殿屋中,无论是从外部造型还是从内部空间,都可以看出这种结构逻辑。木构架的荷载经由椽、檩、枋、梁、柱到基座,层层传递,清晰明了。采取这种结构外露的方式,也是经验理性的体现,本身就是长期的经验总结。木材在封闭、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腐烂、朽坏,而木构架任何部位的损毁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因此,为了尽量延长木构架的使用寿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暴露在流通的空气中,这是匠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的。柱子是由天然的树干加工而成。树木经过一万年的进化,其形态本身就具有非常合理的力学性能。树木都是圆形截面,通过计算得出,各种正多边形中在保持截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圆形截面的刚度最大,而且圆形截面不论受来自哪个方向的弯矩,它的刚度是不变的。将柱子选择为圆形截面,是有多方面优点的,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树干而使横截面积最大化,增强抗压和抗剪性;可以使柱子取得各向均匀的刚度;方便木料加工,节省人力。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方形截面、八角形截面等多种尝试,但圆形截面的柱子,终因其力学和加工多方面的优越性一直是木柱的主流。木柱常常作“杀梭”处理,使柱子由粗到细形成优美的过渡曲线,使木柱看上去挺拔、秀美、亲和,符合树木下粗上细的生长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杀梭”处理的别具匠心,既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木材,避免砍去过多的树干,造成浪费;同时也使建筑具有了有机的自然形态。木材沿纵向的受拉和受压承载力,远大于它的受弯承载力。木桁架体系恰好将木材的受弯转变成木材承受轴向力,正是发挥了木材的优势,相信有丰富木工经验的古代匠人也一定能意识到这点。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木桁架承重体系呢?而在西方民居建筑中,木桁架屋面的运用十分普遍。这是因为多数西方建筑是砖石承重墙结构,雨水的侵蚀对其影响不大。屋面只需要挂瓦以保护木屋架不被雨水侵蚀,而不需要用它来保护墙面。中国木构架建筑就不同了,屋面需要伸出深远的挑檐来保护墙柱和台基。要想将挑檐深远,桁架体系是达不到的,只能是用抬梁式和穿斗式承重体系。对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屋面反曲的由来,有许多种说法。我们先不论其由来,分析一下这种反曲屋面的实际优点。首先,这一反曲面可以接纳更多的阳光,空气流通更好,同时又可以更有效地遮风避雨。在审美上,消除了大屋顶的压抑、沉闷感。同时,在木梁截面高宽比选取上也十分合理。用现代材料力学理论分析清式大式做法中对于梁截面尺寸,发现它十分接近最合理的高宽比。在一定半径的圆木中加工矩形截面梁,这一高宽比可以带来最大的受弯刚度。
建筑装饰的经验理性
中国传统建筑重视装饰,却并没有给人以堆砌、牵强之感,其奥秘正在于选择装饰载体的合理性。概括起来,装饰主要是存在于以下几个部位。首先是关节点。就是结构或者构造上的连接点,这些个连接点经过美化处理,成为建筑装饰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在大门中,门板上的门钉,中槛上的门簪,都是在原有构件基础上,加以美化的结果。驼峰、角背、雀替在一开始时,都有其明确的力学功能,是构架节点的附加件,其优美的曲线轮廓表达出清晰的力学逻辑,是轮廓线和内在力学影响线的高度契合。其次是自由端,构件的自由端常常不承受任何力。因此,这就给自由端的美化处理带来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于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就有了形式丰富多样的各种“头”。如斗栱中的蚂蚱头、菊花头、麻叶头及各式的昂嘴、昂形。额枋搭角上的霸王拳、三岔头,山墙面的博风头等等,不一而足。建筑在逆光下或者是光线照度较差的情况下,常常呈现给观者的是建筑的外轮廓线。建筑的外轮廓线的形象因此也常常成为观者对于某个建筑或者某一类建筑映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留存观者心底中最美的图式。中国的匠人们投入很大匠心和精力放到对建筑的外轮廓线的塑造和装饰上。屋顶的鸱尾、垂兽、戗兽、仙人走兽,斗栱中的角科,石栏杆上的各式望柱,这些无不是倾注了匠人们匠心的美的凝结。这使得原本乏味和呆板的轮廓线变得生动、有机和合宜。此外,建筑中的门、窗隔扇、挂落,花罩中的各种棂栅格网,以其透空的图案赋予建筑内外空间的流动和渗透,给建筑以轻灵的美感。还有各种板、扇的表面层,也同样是装饰的重点所在。中国古代匠人对于装饰载体的选择是理性的分析和实践下的结果。“一般来说,构件的装饰是多余装饰的构件的。”[9]重要的传力构件往往不施雕琢,仅施以油漆对木结构加以保护。如果对传力构件加以雕琢,势必会减少构件受力的有效截面,甚至造成局部的应力集中,木构件在受到重复荷载作用下承载力大幅降低。装饰主要施加在对所受承载力要求不高的构件上,比如构件的自由端,这些部位是建筑形体的边缘,对建筑造型影响极大,但又不承受太多的力,自然成为装饰的重点并表现出极大的自由度。可见,正是这种对装饰载体理性的选择和对装饰理性的节制,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质朴但不粗俗,精致而不淫巧,厚重却不沉滞的美学特质。
结论
“经验理性”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强调“务实”和“实用”,不重视纯粹抽象的逻辑。更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不赞成非理性的直觉,主张“以理节情”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它更执著于人际,带有为人服务的功利性,所以缺乏西方对自然探索的无限热情。正因为“经验理性”的这种理智和理性,它少有宗教中非理性的情感因素。这种特性使得中国人善于吸收一切对现实生活有益的事物,舍弃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用和过时的事物。“经验理性”将人伦秩序与宇宙系统的和谐作为最高理想,所以不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经验理性”所体现的这种务实性,使其具有了一种开放性,它不仅善于接纳和吸收外来事物,而且还会改造和同化外来事物。在此过程中,外来事物同自己文化相一致的地方被吸收进来,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和价值体系相矛盾的东西则被消融,将它逐渐变成自己体系中的一部分,为自己原有的体系服务。中国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包容性和同化性,使得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权更迭和外族统治之后,不但依然屹立不倒,还使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综上所述,“经验理性”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上,体现得更为充分。(本文作者:王金平、郭贵春 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