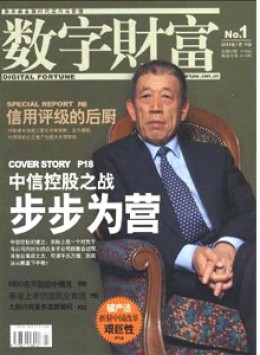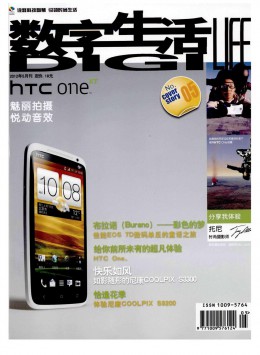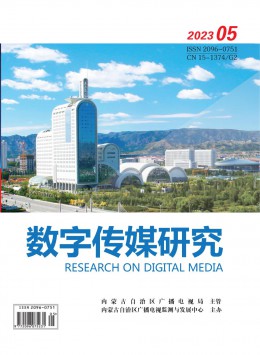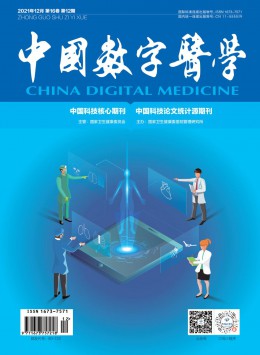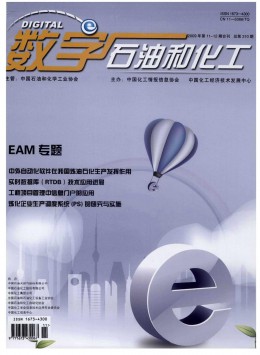数字时代传统艺术原创性神话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数字时代传统艺术原创性神话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绝地即生处,最为衰减的地方往往潜伏着最强势的反弹,反之亦然。立足于辩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即可发现,传统艺术及美学的流变及重构的历程其本质就是一场充斥着否定之否定、对立与统一、颠覆与鼎新的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和传播技术得到了爆发式的蓬勃发展,为传统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曾经在传统艺术中盛行的创作技艺和理念在当代数字及传播的技术语境下呈现出不足和窘迫,但又充满着拓展的生机。作为数字媒体技术与传统艺术相整合所产生的全新的艺术形态,数字媒体艺术还很稚嫩,但它对传统艺术的创作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力度之大、传播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数字媒体艺术不仅是由数字和传播技术在传统艺术领域引发的现象性变革,审美体验的新、奇、特,或是艺术形式的加加减减,它是通过对艺术创作工具和创作规律的改写、对艺术生产和传播流程的重构、对艺术存在方式的刷新,最终引发传统艺术在内容、形式、理念以及审美等诸多方面的重构。就其本性而言,数字媒体艺术是当代新艺术精神的集中呈现和传统艺术当代重构的直接原因和动力。
一、传统艺术原创的“破”
借助数字技术或数字媒体,将传统艺术作品中的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构成元素,通过挪用、拼贴、复制、模仿、改写等创作手法处理成易于重组、合成、传播和存储的信息碎片,从而将传统艺术解构为现代数字艺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数字化完全打破了艺术原创的传统和美学要求。对于这种解构,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对传统艺术作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其意义在于通过数字技术把传统艺术作品中具有独创性、唯一性和原先的不可重复性的元素进行拆分、修改、重构甚至多次重复重组使用,从而打破了传统艺术原创性的神话。
1.数字化解构
数字媒体艺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形式,它是以数字技术为创作手段,以数字、网络平台为展示空间,根据作品的来源可分为两类解构方式:第一类是已存在的艺术作品经过扫描、人工输入等方式上传到数字平台。如将书籍、绘画作品等扫描后为电子图书的形式;或者直接采取人工输入的方式,将文字类作品录入数字平台。第二类是通过专业的数字软件,创作出原先不存在的数字艺术作品。如矢量插画、二维动画、3D动漫游戏等。其中,第二类解构形式在创作上是具有个性化的,而且在传播上具备公共性,可以自由修改、无限复制与传播。无论是多么令人着迷的数字作品,就其解构的本质而言,构成要素都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数字艺术类型实际上使用的是同一种创作“语言”,其构物的本源是一样的。因此,不同艺术类型的界限在数字化艺术创作语境中会产生模糊甚至消除,各种艺术类型将易于交融,取长补短,从而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样式。
2.创作非物质化
作为艺术创作工具和创作手法的变革,数字技术完全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中对物质材料的依赖,这种非物质性的创作方式不仅让艺术创作具备了非物质性,更为现代艺术工作者们开辟了一个数字化的、虚拟化的创作空间,大大提高了艺术工作者的效率及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整个艺术创作过程可以自由地分解为若干个单元模块,各模块交由不同功能的创作团队独立去完成,各创作单元模块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实时沟通,有效的突破了时空和地域条件的限制,所有这一切些都大大缩短了艺术创作的周期和艺术作品的流通,同时也加速了艺术风格和艺术潮流的新陈代谢。
3.“互文性”的兴盛
数字化的艺术作品具备了“互文性”。从个人创作的视角去看,任何创作都是从接受者转化而来,正如没有学习过写作的人无法进行文字创作;没有学习过绘画的人无法进行绘画创作,当然前提是汲取借鉴没有流于抄袭。“互文性”模糊了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分界,将艺术活动视为创作和接受递相转化的过程;数字化后的艺术作品具备了“个性化”和“自由民主性”,使人们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喜好、灵感、需求通过建立、修改、重组创作出开放性的艺术作品,那个“艺术作品一经创作便无法更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艺术走向民间,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前行,真正实现了“艺术服务于大众”、“艺术完成后进入公共场所或公共媒介”的普及理念。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艺术走向个人,实现了代表“草根文化”特质的“个性化”和“自由民主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
二、数字解构后的“立”
任何艺术作品,其本质上都是对既有艺术作品的再写,包括转移、拼接或者参照,甚至包括模仿、认同与遵循。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艺术自足的密封整体的观念,代之以艺术生产是在其他艺术作品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念。
1.再塑书写方式
数字技术能够将传统艺术整体消解为关系与联系、解释与片段、局部图形与整体图像的无界、无限的艺术编织品,彻底颠覆了传统艺术的书写方式。在书写形态上,数字媒体艺术呈现为对现有艺术资源的移接和拼贴,并且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创作出一种混同的文本形态。每件作品不再是单品,而是存在于涉及多样文本与媒体技术的文本海洋中。在书写理念上,对数字技术来说,任何艺术文本都是可塑的,各类艺术文本在彼此交织形成的网络空间内生存,通过主题处理的不同或方法处理的不同来突出艺术特征。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拼贴和移接是后现代艺术家津津乐道的独创之举,它通过文本之间的隐喻、模仿、假借、偷换直接铲平原有的价值中心,并和已有文本形成互文关系
2.拓展艺术创作的空间
几乎每一种新技术的问世都会产生某种新的创作特征,数字技术为传统艺术带来了创作“空间”的无限拓展性,这个“空间”包括创作主体、领域、手法及理念等。其中,虚拟是最为核心的空间拓展品质,其本质是在艺术作品中生成由各种艺术形态构成的虚拟的视觉盛宴。1994年的影片《阿甘正传》中,有一根从天飘落的白色羽毛分别出现在影片的开头与结尾,借助数字技术设计生成运动轨迹和飘落的形态与观众真实的生活体验毫无二致,出色地暗示了主人公神奇的一生。影片《木马屠城》在表现两军对峙的场景时,把只有1000多名群众演员的场面虚拟成数万人的战争大场景,达到以假乱真的视觉效果。正是由于虚拟影像合成等CG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原先不可能的题材变成了可能。植根于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艺术形式提供的虚拟与传统艺术中的虚构完全不同。虚拟首先属于技术范畴,应当被视为一种技术行为,尤其是一种成像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现代广告、电影工业、工程学等领域。虚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模拟,对物质世界已经存在的对象形态进行模仿;第二种是创造,将物质世界中不存在的对象形态创造出来,使其具备直观化和真实感,如虚拟场景、虚拟人物等。
3.改写艺术审美标准
由于艺术创作工具的解放,数字艺术不仅可以创造物质世界原本不存在的对象,能够极尽夸张传统艺术环境中无法看到的细节。凭借数字技术,人们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将数字效果推向极致,艺术创作随之发生了观念上的的变化,“陌生化”和“独创性”被视为等同。只有那些能够激发受众新奇感的作品,才被视为具有吸引力和创造性。越来越多的数字艺术家出于对新技术的探索与尝试,乐此不彼的创造着现实世界里从未存在的形象,以新、奇、特作为出奇制胜的标准。“特异化”正在成为数字审美的标准,使数字艺术的世界变得无奇不有,美丽的更加美丽,丑陋的更加丑陋,恐怖的更加恐怖,可爱的更加可爱。过度化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畸态,它并非畸形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异形,而是指非自然标准的、非日常的、非常规的,它总是大于或小于自然的标准。以形态的“过度化”引起人们的视觉兴奋,在这种“过度化”标准的追求下,从视觉到意义的传达,数字技术让艺术体现出过度的效果美学。在数字技术推进和商业效益的驱动下,数字技术掀起了受众追逐对现实不存在或者无法实现的对象的痴迷,“过度化”审美被推向极致,它不再是艺术创作的标准,而是成为艺术创作的目的。传统审美活动带来的身心愉悦、精神的解放在这里被异化了,这些过度化的审美标准以极端化的形态对人的感官浅表刺激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审美标准,传统艺术美的自然属性发生了改变。电影《指环王》中的咕噜、《侏罗纪公园》的恐龙等便是例证。
三、亘古不变的情感脉络
以畸态作为艺术审美的标准和追求,是新事物发展初期出现的情形—摄影、电影等艺术形式都曾出现过因陶醉于新兴技术带来的无所不能而无法避免走弯路。当我们还没有对数字技术及其带给艺术的改变形成成熟的认知,而数字技术的无所不能又令人留恋和迷醉时,过度化的审美必然是数字技术与传统艺术碰撞后需要经历的必要阶段。数字艺术的兴盛带引发了传统艺术的落寞,数字艺术凭借技术的运用所呈现出的虚拟性、自由性、交互性等特征都是传统艺术无法实现的。然而传统艺术在历史长河中慢慢积淀下的情感凝聚和文化的精髓是不能忽视的宝贵财富。数字技术归根结底要服从于艺术整体的需要,要表现人,反映人、表达并丰富人的情感世界,才是数字技术作为技术本质应该做到的本源。美学家李泽厚在谈及审美感受时,提到了几个层面,第一层是悦耳悦目,这是最低层次的感官享受;第二层次是悦心悦意;第三层是悦神悦志。单纯依靠数字技术给人以视听感官的刺激是暂时的,数字技术带给传统艺术最终的归属依然是情感,毕竟,人要在艺术中感受到的始终是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以及人的灵魂。这就是艺术创作永当追随的情感脉络,与技术无关。
作者:宋蔚 单位:安徽大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