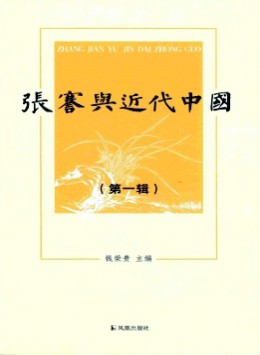近代町村财政的变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近代町村财政的变迁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民费财政具有“来源狭窄”、“公私不分”、“国政委任事务费所占比重高”[3]等特征,这在最基层的町村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民费的收支最初只由府知事和区户长等专断,并不同民众进行协议,由此不可避免地酿成种种纷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府县就自主地召开民会,包括府县会、区会和町村会等。[4]1876年,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各区町村金谷公借共有物处理土木起工规则》,规定实行村内不动产所有者对町村财政的协议,这也被称为日本近代町村会的起源。这一规定的出台,使民费财政表现出“从封建的地方财政开始向近代的地方财政过渡的特色”。[3]
协议费财政1878年7月明治政府进行地方制度改革,了《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统称为“三新法”。《地方税规则》的出台,结束了民费财政,确立了新的地方税财政制度。但这种地方税只是原来民费中的府县的费用,将其“作为人民的义务,进行强制的征收”,并由府县会对预算进行议决;[5]而原来民费中的“各町村及区内的入费”则“任其区内人民协议”,承认其协议、自治的性质,原则上不加干涉,因此这一时期的町村财政“被称为协议费财政”。[6]391880年政府《区町村会法》,各地开始设立正式的町村会,对协议费的赋课征收和支出等进行议决,这在町村财政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町村费财政1881年松方紧缩财政实行后,谷价暴跌,农民极度贫困。与此同时,国库和地方税的财政补助减少,因此町村协议费年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必要的国政委任事务的费用,1884年政府决定对《地方税规则》进行修改,明确以区町村费支付的项目及征收区町村费的课目,对于区町村费怠纳者,适用于租税未纳者的处分。[2]110这实际上赋予了一部分町村费以租税的性质,对其征收进行公法的保护。经过改革,协议费进一步分化为区町村费和协议费,“原来性质不明确的区町村财政被赋予了公共财政的性质”,[2]111成为町村财政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变。
近代的町村财政制度的形成明治政府在确定了1889年宪法的日程表后,各项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也开始了。在地方制度方面,在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主导下,1888年《市制町村制》,在形成了市町村自治制度的同时,也完成了其财政制度的近代化。法律对町村的费用、收入、财产、公债和预算决算及出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主要内容是:(1)町村为公法人,其町村民有分担町村费用的义务和使用町村财产和公共设施的权利;(2)町村的费用由町村费负担,没有具体限定町村的费目,但国政委任事务和必要的固有事务的费用实行强制预算,承认代议决制;(3)收入主要是财产收入、使用费、手续费和町村税等,町村税以国税和府县税的附加税为中心;(4)町村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基本财产的处分及町村有不动产的买卖、转让、置换等都必须由町村会议决;(5)町村有公债募集权,但设置了相关的限制,确定其偿还办法;(6)财政的运营实行预算决算制度,并由町村会议决,进行公告,其出纳定期接受检查和监督。《市制町村制》的颁布,标志着20年左右的町村财政的探索期走向终点,近代的町村公共财政制度形成了。
明治后期町村财政的初步改革
近代的町村财政制度开始实行后不久,日本便迎来了两次对外战争———日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争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同时,也使町村财政的疲敝开始初步显现。到明治末年,政府对町村制度进行初步改革,加强了町村的财政基础。
1.町村财政制度的初期实行新的町村财政制度实行初期,主要出现了如下问题:(1)在町村自治实行前,政府首先对旧町村进行合并,形成有一定财政基础的“不要公课”的新町村,但是因为旧町村的内部统一性很强,所以其原有财产(如林野)没能实现统一。导致新町村财产收入有限,不得不主要依附于町村税;(2)町村中重要的财源都被国家和府县所收夺,町村税主要为国税和府县税的附加税,不仅来源有限,而且缺乏自主性;(3)町村岁出主要为国政委任事务费,在完成委任事务后,町村很难有财力再进行自己的自治事务。特别是随着小学教育制度的整备,小学教育的费用全部由町村负担,它作为町村最大的委任事务费,成为町村最沉重的负担。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作为战胜国,获得了清政府大量的战争赔款,开始了所谓的战后经营,由此导致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同时急剧膨胀。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1896年明治政府《国税营业税法》,规定把“原来府县税营业税及杂种税的一部分编入国税”,[7]19同时规定町村可以对其征收不超过50%的附加税。政府同时出台了对地方团体的教育、土木等事业由国库进行补助的法令(如1899年《小学校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等等),但其补助额度极为有限,而且必须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督和接受国家的广泛指令,在减少了地方团体的自主性的同时,并没有缓解地方财政、特别是町村财政的紧张。
2.日俄战后的征税限制法案与部落①有财产统一日俄战争爆发后,为了筹措战费,政府制定非常特别税法,在进行了大规模的临时征税的同时,为防止地方对国家财源的剥夺,对地方税课税也开始进行限制。政府还向各地方长官发出通牒,命令中止或延缓地方上的各种土木事业等,严格控制岁出。“日俄战后的国家财政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其主要特征是以军事费、殖民地经营费、产业助长费、社会政策费及公债费为中心显著地膨胀。”[8]88-89为继续保障国家的财源,1908年,《关于地方税限制的法律》公布,对地租附加税、营业税附加税、所得税附加税等继续实行限制,虽然额度比战时有所缓和,但“这是将战时应急而设的对地方税的限制作为恒久的制度确定下来”。[7]142战时与战后的课税限制对町村岁入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另一方面,在日俄战后的经营中,国家又了一系列新的法令,推行以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产业政策等,因此地方上的国政委任事务激增。这在町村主要表现为教育费和保健卫生费等的急剧增加。特别是教育费,根据1907年的《小学校令改正》,小学的修业年限从原来的4年延长到6年,教员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本来就是町村最沉重负担的教育费进一步增加,导致町村的债务开始急剧上升。缓解町村财政的紧张成为日俄战后政府直面的紧急课题。为此,1910年,政府开始实行部落有林野统一政策,把町村制实施初期仍然保留在旧町村的林野,强制统一到了新町村。这一举措消除了町村行政和财政上的障碍,增加了町村的基本财产。而且客观上它彻底地消除了旧町村的“私经济”,进一步推动了“町村行政财政的近代化”。[8]98
3.1911年町村制改革1911年4月,明治政府以法律第69号公布了新的《町村制》。新法扩充了町村委任事务的范围,并强化了町村长对町村议会的权限,加强了对町村的行政监督。[9]在财政制度方面,新法主要目标是强化町村的财政力,充实了基本财产的规定,对居民租税征收进行强化,扩大了征税的范围和对赋课征收规定进行整备以及使用费、手续费及特别税滞纳者的制裁强化等。但是这些不是“从根本上扩充町村的财政力,只不过是町村所有的财政力的利用度比原来更高了而已”。
大正时期町村财政的民主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与国家财政的积极政策相对应,地方财政也以“积极政策为基调”而急剧膨胀,教育费、社会事业费和公债费等急剧攀升。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重工业化、城市化也飞速发展,由此导致地方发展的极度不平衡,特别是町村财政出现极度贫乏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大正民主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不仅放宽了日俄战后的地方课税限制,[8]128还出台了一系列町村财政民主化的新举措。
1.町村义务教育费的国库负担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小学校费一直是町村的沉重负担。“小学校费强烈地压迫着市町村的财政,成为其财政贫乏的最大原因。”[6]133因此,民间要求小学校费国库补助的呼声一直极高,并多次进行请愿、建议和提出法律案等。1918年3月,政府《市町村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规定:市町村立普通小学校的正教员及准教员的薪金费用的一部分由国库负担,其支出额每年不少于1000万日元;其交付方法半额按教员数量、半额按就学儿童数的比例交付;文部大臣可以在不超过国库支出金1/10的范围内对资力薄弱的町村增加交付金额。[6]142不过,虽然实现了小学教育费用的一部分由国库负担,但是其额度有限。1918年市町村岁出总额为3.38708亿日元,其中小学校费0.90542亿日元,占岁出总额的27%,其中教员的工资总额为0.49365亿日元,占岁出总额的15%,1000万日元以国库负担金支付,其数量是很少的。[6]144但是此后,国库负担金一路增加。1923年,国库负担金增加到4000万日元;1926年增加到7000万日元;1927年增加到7500万日元;到1930年5月增加到8500万日元,占小学校费的34%,教师薪金的53%。[6]160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的出台,虽然最初的目标是为了改善教育,但随着町村财政的恶化,减轻町村负担,缓解町村财政就成为主要目标了。它是大正民主时期町村财政改革的最重要成果,堪称“改革的顶点”。
2.1926年町村税改革1926年,政府还进行了地方税制的改革。其关于町村税的主要变化是:(1)把户数割从道府县转移给市町村作为独立税,同时对其课税标准和赋课方法进行了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封建的人头税的性质”;[8]131(2)废止原来的所得税附加税,增加府县家屋税及特别地税附加税。经过改革,原来以附加税为中心的町村,独立税占收入的比重上升了,在1927年达到了57%(见表1)。而国税和道府县税附加税的比重明显下降,特别是府县税附加税从占74.2%直降到25.7%。但町村独立税是以户数割为中心的,占町村独立税的87%,反映了这次改革并没有创设新的税源,而只是“税目的再编成”。[10]1不过客观上它使日本“税制的近代化、合理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地租委让的失败政党内阁成立后,特别是在大正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疲敝,两税委让问题成为当时的焦点。所谓两税,是指作为国税的地租和营业税,政党主张把营业税委让给道府县、地租委让给市町村,以增加地方的财源。1923年,政友会最先提出地租委让建议案,主张把地租委让给町村作为财源。这一提案在议会上获得通过,但由于关东大地震的发生,最终未能实行。[10]71927年,政友会以两税委让为中心的税制改革案在第56次议会上再次提出,但提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在贵族院遭到否定。政府准备在下次议会中提出,但是1927年的金融恐慌后,国家财政也出现了问题,已经没有能力弥补两税委让后产生的缺口,加之政友会下台,最后两税委让案不了了之。地租委让的失败,反映了大正时期町村财政民主化的局限。
昭和战争时期的町村财政
发源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30年波及日本,给日本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挑起“七七”事变全面侵华,1941年又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1930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国内体制向准战时和战时体制发展,町村财政也逐渐被纳入到战争的轨道中。
1.临时町村财政补给金的诞生和发展30年代初期,德英等国的财政调整制度和交付金制度等被介绍到日本后,[6]215内务省官僚中也出现了“国家为了确保财源,需要进行自治体间的财政均等化,为贫穷的地方自治体填补财源的所谓财政调整制度不可缺少”的思想。[11]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农村的疲敝和战时军需工业畸形发展导致的地方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均衡,更使地方财政调整问题成为当时的焦点。1932年,内务省提出了《地方财政调整交付金制度要纲》,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1934年开始,各政党相继向议会提出地方财政调整相关法案,但均未在议会获得通过。直到1936年10月,《临时町村财政补给金规则》终于得以通过并,规定作为追加预算,政府拨出临时补给金2000万日元,交付町村使用,国家对这些补给金的使用计划和预算编成加以监督。虽然这只是“小规模的、临时的应急措施”,但却标志着“日本最初的地方财政调整相关制度的创设”,[6]529也是地方财政中央集权化的重要一步。此后,全国町村会、帝国农会要求把这一制度恒久化。因此从1937年开始,临时町村财政补给金变成临时地方财政补给金,广泛交付给道府县和市町村,按各地方自治体课税能力进行反比例的交付,同时其额度一举增加到1亿日元,市町村获得7250万日元。[6]232-2331938年度补给金又增加到1.3亿日元,市町村获得9200万日元。[6]2351939年总额达到1.48亿日元,市町村获得1.03亿日元。[6]236-237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全面侵华后,急需对农民进行监管,因此此时的财政调整制度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自治体间的财政均等化”,其性质更多地倾向于对战争的配合了。
2.1940年税制改革在实行地方财政调整制度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开始探索税制的根本变革,以适应战争状态下激增的以军费为中心的国家和地方财政支出。“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广田内阁开始实行“积极的战时财政”政策,[8]203并以马场锳一为财相,提出马场税制改革案,欲图对税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但这一尝试直到1940年才真正实现。1940年3月,政府了《地方分与税法》等38个法令,对国税和地方税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把具有张力的所得税和法人税等所得税由国家独占,废除地方上的所得税附加税;(2)把地方税体系改为以国家的地租、家屋税和营业税的附加税为中轴的物税本位;(3)实行地方分与税制度。地方分与税由还付税和配付税组成。还付税是国家把作为国税征收的地租、家屋税及营业税的全额还付给道府县,而配付税是把所得税、法人税、入场税和游兴饮食税等按比例交付给道府县和市町村,进行“地域间的财政调整”;(4)町村的独立税户数割被彻底废止,新设町村民税。[12]34-35这种新的课税体系,把地方税分为直接征税和间接课税的地方分与税两大部分。分与税的出台,从表面上看实现了大正时期的两税委让,但在性质上,它作为国税,由国家统一征收、分配,实际上加强了中央集权,是战争体制下国家对地方进行监管的重要一环。配付税的62%给道府县,38%给市町村,根据各道府县和市町村的课税能力、财政需要及其他特殊的情况进行配付。“地方分与税制度带来了日本地方财政制度的一大转换”,标志着以往“作为临时措施的财政调整制度恒久化”。[8]266改革给町村财政带来了重大变化,从此配付税占据了町村收入的重要位置。地方分与税制度具有某种“地方财政现代化”的特性,[13]55在战后日本广泛实行,[14]但是日本在1940年实行的分与税制度,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改善“由于日中战争的进展抑制地方税、地方债而产生的新的地方财政的窘迫,在现实中是为了确保全体町村的‘战时民族’的机能”。[13]54因此改革后的町村财政被完全纳入到法西斯国家的战时统制中,“町村自治明显后退”。[12]37此后经过1943年的町村制度改革,町村自治名存实亡。
总结
通过上述对近代日本町村财政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近代日本通过法律,在形式上形成了近代的町村公共财政制度。1888年《市制町村制》的,赋予了町村财政以公共财政的性质,对町村的费用、收入、财产、公债和预算决算及出纳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规定,特别是预算决算制度的确立和以町村会为中心的财政运营,具有重要的近代意义,也为近代日本实行的町村自治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撑。此点也足可资至今还没有建立完备的乡村财政制度的我国参考。
其二,尽管近代日本形成了町村公共财政制度,但是从町村的财政收入上看,财源已经被国家和府县所收夺,因此财政疲敝几乎贯穿町村财政的始终,根本无力支撑起町村自治。也即,无论是制度初形成时的附加税中心主义,还是大正民主改革后的独立税居于主要地位,都没有改变町村财源有限,财政窘迫的局面。到了经济危机和战争爆发的昭和时期,政府出台了地方财政调整制度,1940年的地方税改革实行配付税制度,更把町村财政彻底地纳入到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中。
其三,从近代日本町村财政的支出看,国政委任事务费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导致町村根本无力进行地方固有事务,自治能力极其虚弱。制度实行初期町村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公务费和教育费,而公务费以承担国家委任事务为主,自主的费用很少。在后来的战争时期,支持战争的军事费支出增加,成为战时町村财政支出的重要特点。总之,近代日本町村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近代的公共财政制度,但是财源枯竭导致的财政疲敝和以国政委任事务费为中心的支出模式,是其贯穿始终的特点,严重影响了町村自治的自主发展。考察近代日本的町村财政变迁,经验有之,教训亦深刻,值得我们思考和引以为鉴。
作者:郭冬梅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