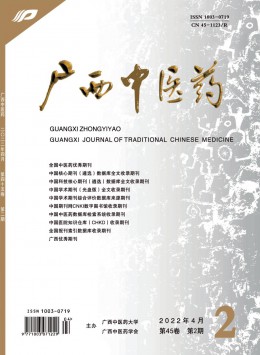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1肠道菌群在心血管疾病中的致病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调及其部分代谢产物在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3]。如部分肠道菌群对动脉粥样硬化有保护作用,而部分肠道菌群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损害;短链脂肪酸(SCFAs)在血压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肠道菌群与心衰之间关系提出的“肠假说”以及三甲胺氮氧化物(TMAO)与动脉粥样硬化、心衰的发展和预后的关系。
1.1冠心病
冠心病是最常见的心脏病之一,是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相关实验数据表明,来自不同种类细菌的DNA存在于同一个体的肠道和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故动脉粥样硬化细菌的潜在来源可能是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因此很可能参与了冠心病的发病机制[4-5]。Jie等的相关实验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中肠杆菌科细菌和链球菌(EnterobacteriaceaeandStrepto-coccusspp)的检出率高于健康对照组[6]。Stepankova等进行的小鼠动物实验证明肠道细菌对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有保护作用[7]。Chan等通过给载脂蛋白E基因祛除的小鼠喂饲高脂饮食12周,添加鼠李糖乳杆菌(Lgg)或替米沙坦(Tlm)建立动脉粥样硬化模型,2种补充剂都改变了肠道微生物区系的比例,并显著减少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大小[8]。此外,5种细菌(真细菌、厌氧菌、玫瑰红菌、示波螺旋菌和脱盐菌)已被证明在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方面是有效的。相反,Kasahara等的研究表明,微生物区系的缺乏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增加[9]。此外,有研究表明Porphyromonasgingivalis(牙龈卟啉菌)和Aggregatibacteractinomycetemcomitans(放线菌)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有关[10-12]。总而言之,某些肠道菌群被认为是促进疾病进展的新因素,对保护动脉粥样硬化发挥一定的作用,而部分肠道菌群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损害。三甲胺氮氧化物(TMAO)主要来源于左旋肉碱、卵磷脂、胆碱,TMAO被认为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成分。在肠道经肠道菌群作用生成三甲胺(trimethylamine,TMA),后者经门脉循环进入肝脏,并被肝黄素单氧化酶(Fmo3)氧化为TMAO[13-14]。Gregory等[15]通过移植C57BL/6J、TMAO高产菌群(动脉粥样硬化易感肠道菌群)和NZW/LacJ、TMAO低产菌群(无动脉粥样硬化趋势肠道菌群)到载脂蛋白E基因敲除的小鼠中,并且用抗生素抑制微生物生长,二者实验结果相比,移植动脉粥样硬化易感肠道菌群的小鼠表现为膳食依赖性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Li等的一项研究表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TMAO水平是短期(30天和6个月)和长期(7年)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16]。其他研究也强调TMAO参与了不同患者队列中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17-19]。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TMAO是肠道菌群影响冠心病的重要机制的一部分,但肠道菌群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所涉及的详细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1.2高血压
在我国,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7亿,控制率仅为13.8%,高血压是促进卒中、冠心病以及心血管意外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20]。近期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Yang等[21]的研究表明,在高血压大鼠模型和一组高血压患者中,发现微生物的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性均降低,这表明高血压与肠道失调有关,改善肠道微生物区系可能是未来高血压治疗的目标。同样,肠道微生物群在高血压形成中的重要性也从一项研究中得到证实,该研究表明,在高血压患者的粪便物质转移到小鼠后,无菌小鼠的血压升高[22]。亦有研究表明,在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中存在较多的机会致病群,包括克雷伯菌属、链球菌属和副结核杆菌属,这些分类群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23]。这些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高血压的发展中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与其他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相比,更多的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SCFAs)在血压调节中的生理功能。肠道内的细菌通过膳食纤维的厌氧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通过与G蛋白偶联受体41(Gpr41)、G蛋白偶联受体43(GPR43)、G蛋白偶联受体109A(GPR109A)和血管嗅觉受体78(Olfr78)的结合,研究了多种生物学效应对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CVD、炎症和肠道内环境稳定的影响[24-25]。Pluznick等实验结果提示,Olfr78可能通过SCFAs介导高血压效应[26]。Pluznick又指出Gpr41和Olfr78在丙酸(一种短链脂肪酸)反应后对血压的调节作用是相反的,即SCFA的降压和降压作用分别是通过与Olfr78和Gpr41的结合介导[27]。总之,血压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丰富性和均匀度密切相关,短链脂肪酸(SCFAs)在血压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改变肠道菌群结构可能成为治疗高血压的潜在方法。
1.3心衰
心力衰竭(heartfailure,HF)是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虽然药物和非药物治疗可以延缓HF的进展,但短期和长期死亡率仍然很高[28-30]。近年来,我们对HF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对其认识从血液动力学变化到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的转变,而肠道微生物群在炎症和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对肠道菌群和HF之间联系的关注[31-32]。Pasini等[33]比较了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heartfailure,CHF)患者和健康人粪便中的细菌和真菌,结果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粪便中的细菌数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念珠菌、弯曲菌和志贺氏菌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78.3%的CHF患者肠道通透性升高,中度和重度CHF患者肠道通透性高于轻度CHF患者,右心房压与肠道通透性呈正相关。在另一个动物实验中[34],心衰豚鼠在压力超负荷下,10种粪便菌群的丰度发生了变化,这些数据表明心力衰竭可以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于是研究人员提出了“肠假说”,即心输出量减少,导致低灌注和胃肠道充血,可导致心衰患者肠缺血或水肿,从而肠道菌群的组成、肠道功能、形态和肠道通透性都发生了改变,继发性肠道细菌移位和循环内毒素水平升高加速了全身炎症反应,而激活的炎性细胞因子促进了心衰的发生[35]。此外,TMAO还与HF的发展和预后不良有关。研究表明,在数百名参与者参与的两项队列研究中,升高的TMAO水平不仅可以预测CHF患者的长期死亡风险[36],还可以预测急性心衰患者的长期死亡风险[37]。Organ等[38]在小鼠实验中,使用主动脉缩窄手术诱发HF,并发现在饲喂TMAO或胆碱饲料的小鼠中,HF的症状和体征比对照饮食的小鼠更严重。服用TMAO和胆碱的小鼠血浆TMAO水平升高,这是因为肠道微生物将胆碱转化为TMA。TMAO可促进左室扩张、心肌纤维化和心室重构的发展。但是,通过调控肠道微生物TMAO通路,是否能降低HF患者的TMAO水平或减轻HF的症状,是否能长期改善预后,有待进一步研究。
2中医“脾胃学说”理论与肠道菌群
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将水谷精微转化为气血濡养全身,与肠道微生物参与机体营养物质消化吸收一致。此外,中医学“脾”生理病理功能的现代生物学基础之一可能是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等产生的作用,即肠道菌群代谢营养功能正常,则脾胃能正常行使其化生水谷精微的功能;肠道微生态紊乱或其代谢异常则脾失健运,容易产生湿热、痰浊等邪实。调节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可防治多种疾病,如冠心病、心衰、高血压及肥胖等,《灵枢》云:“五藏六府,心为之主……脾为之卫”;《金匮要略》中记载“脾旺不受邪”;又有“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说法,中医学认为脾气充盛,可拒邪于外或驱邪外出,可从脾胃调理五脏六腑而防治多种疾病,其机制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免疫防御的生理功能相契合[39]。故“脾胃学说”与肠道菌群的研究有许多契合点。
心脾两脏的重要联系早在《内经》和《难经》中就有阐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提到:“心生血,血生脾”。《素问•玉机真脏论篇》也提到:“五脏受气于其所生……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授气于脾,授气于我生之子也……”。脾胃五行属土,心五行属火,心与脾乃相生关系,又心脾两脏阴阳相通,气血互济。心脾相关理论于秦汉萌芽,宋兴盛于,明清成熟,近现代逐渐完善。在胸痹心痛的论治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提出“补益心气重在健脾”“痰瘀相关”,并强调心脾相关学说,指出饮食不节、七情内伤、年老正虚等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湿浊内生,聚而生痰,日久成瘀,从而出现胸痹、中风。邓老用温胆汤加减治疗冠心病,取其益气除湿化之效,实践证明效果颇佳[40-41]。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共同的病理机制是“痰瘀相关”,脾胃功能失调是关键,且与肠道菌群的功能关系密切,具体是指食用富含胆碱的肥甘厚腻之品,在肠道菌群的相关作用下产生TMA,而TMA被认为“痰浊”的生物学标记物,TMA入血,在肝脏转化为TMAO,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激活血小板聚集,促进动脉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发生,此即为“痰瘀互结”致血脉闭塞的病理基础[42]。路志正教授在临床运用中擅用调理脾胃治疗胸痹心痛,具体包括健脾养血、温阳理中、醒脾化湿、健脾涤痰等法,疗效显著[43]。现代研究也表明,调理脾胃的相关药物能通过促进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改善能量物质代谢,通过调节脂质代谢以减轻血管压力,通过改善脂质过氧化损伤以减轻内膜损伤、脂质沉积,从而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可见基于“肠道菌群”,从脾胃探索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治疗途径是一条可行之路。同时,日益增多的证据也显示肠道菌群参与了中药的心血管药理作用。如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用于治疗脾虚证型心血管疾病的疗效,与肠道菌群结构变化有关。丁维俊等[44]利用大黄灌胃建立脾虚小鼠模型,给予参苓白术散治疗,结果表明参苓白术散能显著提高肠道双歧杆菌含量,降低肠球菌、大肠杆菌数量,对益生菌起到扶植作用;而对条件致病菌及病原菌起到间接抑制作用,对肠道肠道菌群动态平衡的恢复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4小结与展望
近期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失调在冠心病、高血压、心衰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心血管领域肠道微生物组学的研究与新一代核酸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其确切的分子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随着粪菌移植、口服益生元、改善饮食结构等方法的出现,能够较大地改善菌群结构,但需进一步探索干预肠道菌群的精确方法。基于“脾胃学说”“心脾相关”理论,中医药可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从而改变宿主的代谢状况,减慢或逆转心血管病的发生或进展。
作者:曹玉 王立玉 刘睿斯 徐婕 沈雁 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