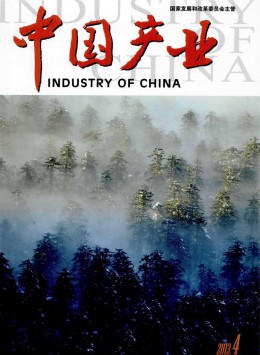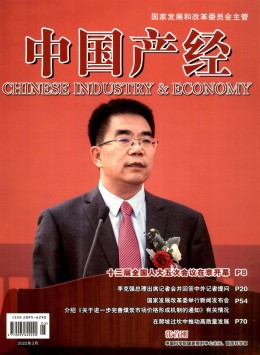国产动画片创作选材问题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国产动画片创作选材问题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影视动画片的首要功能是给观众讲故事,讲好故事的必要条件就是要选择有故事的题材。选材的实质是为主体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的题材,这种题材要蕴含着精神潜流的感性生命体。选材是影视动画片创作过程诸多链环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创作环节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动画作品的经济效益的亏盈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其作用与功能不言而喻,选择好的的题材是影视动画片创作成功的关键所在。概览我国影视动画片的题材选取,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虚幻选材、神化选材、脱离现实选材、过度依赖原著等方面问题。限于篇幅,本文直奔主题,指陈当前国产动画片创作在选材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别提出因应之策,但愿对国产动画片创作实践有所启示、有所裨益。
一、关于选材“虚”
“动画”英语词汇“Animation”原义为“使原本不具生命的东西像获得生命一般地活动”,也可释义为“无中生有”。从动画定义的本意上推演,虚拟性是影视动画片的本质特征之一,这里而言的“虚拟性”主要指的是动画片中人物角色设定与塑造,叙事时空的建置,故事发生的环境与时代背景的创设等都是虚构的。其中也包含动画故事情节的虚拟、故事题材虚拟等等。由此可见,“虚拟”尽管作为影视动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创作中也应当把握虚拟程度,适度而止。国产动画片虚拟尺度普遍较大,一虚全无,给观众留下一片虚无飘渺。在题材选取方面,主要表现在国产动画倾向于选取发生在外太空、外星球、狼村、羊村等的空间中的无厘头的故事题材,并且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一律被虚化掉,故事人物角色与现实人没有丝毫关联。这种全然虚化的动画影片也就无所谓情感、观念的表达,即便有,也无所依。大多数观众在观看了国产动画电影后,所发表的最深刻的感触是:不知道讲的什么?譬如国产影院动画片《魁拔之十万火急》,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元泱境界”的架空世界中,一心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妖侠”的八岁少年蛮吉,与收养他的青年蛮小满一起,克服重重困难,抗争元泱境界中最可怕的灾难———魁拔的故事。该片片名就足以让人摸不着头脑,迷茫糊涂。何为“魁拔”?何为“元泱境界”?“架空世界”是什么世界?什么是妖侠?这些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的、完全虚拟的人物与事物,让观众群体实在感到虚无缥缈!影片的故事题材、人物角色、时空结构等影像元素严重存在虚拟过度,丝毫激发不起观众的观赏欲望,就更加谈不上产生“共鸣”了。据网络报道,该部影片仅仅收获近300万元左右的票房收益,全国仅有387家影院愿意上映此片。[1]显而易见,影片《魁拔之十万火急》商业效益的失败与其过度虚拟化的选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再看号称我国首部全三维动画电影的《魔比斯环》的选材,选择了一个普通大众都不懂的高深数学概念充当片名,也未免过于虚拟化。该片的选材依据也即是电影开篇时候的解说———“内部传输环”的科学理论:当一个三维圆锥环扭转180度时,会变成一个二维的数学形态,成为魔比斯环,然后扭转两个空间的参数,就可以建立第三个参数,即是距离。还有,电影中的科学家西蒙建立了一个魔比斯场的入口,即时空通道,名为“魔比斯环”,穿过这个时空通道,便可以瞬间到达已知的宇宙的任何地方,可以通往宇宙的任何地方的时空通道,这种虚拟可信吗?于情理之中吗?我认为这部电影的选材切入点已经完全脱离了观众视野,使得观众无法进入电影带来的虚拟世界,更是让观众群体无法投射现实情感于其中。这样就出现了观众不能走进影片世界,影片也不能进入观众心中,结果带来的后果便是无人问津。可以说,“过度虚拟化”形如在动画影片与观众之间构筑了一道“屏障”,二者无法逾越。既然,虚拟性作为动画片的本质特性,在选材上就不可避免要选择虚拟的题材,那如何做到虚拟有度,虚实相得益彰呢?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动画片的虚拟特性,尽管虚拟是影视动画的重要特征,也不是无限制、无根据、无尺度的虚拟,虚拟性是为动画片叙事服务的。动画片故事选材还应适度关联现实社会的“实”,才能得到观众群体的认可,使其情感落地。纵观国内外经典影视动画,都能在题材选取方面做到“有据可依”,适度赋予现实元素,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使观众群体能够感受到动画影片故事是从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时空,总能感受到“虚实相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最终让观众得到情感观照。譬如,美国电影《阿凡达》故事发生在2154年,是从我们生活的地球开始的,人物确定为一位双腿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杰克•萨利,这些题材元素充分表明故事是从“真实”开始的,至少故事开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要素是确定的,尽管选定在未来时空,但并不是完全虚拟的。在这些题材元素确定之后,导演卡梅隆把故事开拓到距离地球遥远的“潘多拉”星球去讲述,并与地球作为统一整体进行观照。“潘多拉”星球无疑是一个虚拟的时空区域,在上面发生的故事固然也是虚构的,但主要角色从地球上通过先进的宇宙飞船到达“潘多拉”星球,这在目前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于未来100多年之后,这不免为故事的可能发生设置了真实感觉,因为100多年之后人类对于外太空的宇宙探测是完全可能的事情。《狮子王》、《花木兰》、《点点滴滴的回忆》等经典动画影片也都能找到题材之根、情感之源。可见经典动画影片的创作之道首要的任务是使故事“落地生根”,然后一步步推向虚拟世界,并非一来就虚。题材失去了“根”,故事就失去了张力和定力,就抓不住观众的心。因为,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是源于生活。
二、关于选材“神”
“只见神话,不见生活”是我国影视动画创作的一大通病。一直以来,国产影视动画片的题材选取大多是神奇、神话和神勇等方面,少见以学校、家庭、社会生活作为题材的,这与我国神话故事题材资源丰富不无关系。概览我国早期动画片创作,大部分影片的故事题材不是出自于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是选材于我国民间神话故事资源。从这些选材基点可以窥探出我国早期动画创作界对动画片的理解与认识,他们认为动画是“非神即幻”的虚拟艺术类型,这样的理解与认识也影响了国产动画片“喜神好幻”的创作选材倾向,这种倾向一直影响着国产动画创作选材。比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猪八戒吃西瓜》等动画片选材于《西游记》;选材于我国民间神话题材的有《天书奇谭》、《小倩》、《神笔马良》、《梁祝》、《九色鹿》、《八仙过海》等。这些动画片不仅在题材上选取我国神话故事资源,在艺术形式上实行了创新,巧妙地将水墨画、剪纸、折纸等传统艺术形式与动画艺术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成功,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学派”。但在该学派的影响下,我国影视动画创作“神选材”一发不可收拾,各种神话题材动画片层出不穷。尽管上世纪中后叶的国产动画片的开山之作《大闹天宫》,以及《哪吒闹海》、《天书奇谈》、《九色鹿》等改编自中国神话传说的动画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毕竟有时代因素的成全,民间神话传说属于旧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推移,正在逐渐失去诱人的色彩和感召力,即使作为动画选材,也应当作适时改编。一直以来,我国动画创作群体一味地以“弘扬动画民族化”为旗帜,将神话故事题材生搬硬套地搬进动画世界,缺乏时代感与创新性的改编,结果创作出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作品。这些动画作品无法真正体现民族文化,无法经受住市场与观众群体的检验,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知极其肤浅。如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影院动画片《宝莲灯》改编自我国古代神话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圣母与刘彦昌成婚,生下沉香,圣母之兄二郎神竟盗走宝莲灯将圣母压在华山之下,十五年后沉香学得武艺劈山救母,宝莲灯重放光明。动画片《宝莲灯》基本上完全承袭了神话故事原有情节,结果不能恰当地表达故事主旨,影片的主题也混沌不清,自然无法赢得观众。我们并不一概否认动画片的神话选材,大众需要的是既能传递出中国神话传说的内涵与主题,又符合当代大众审美眼光的民族动画艺术。要达到这种艺术水准,创作者要站在观众角度,走进神话世界,然后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映射现实情感与社会问题,从而回归现实。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通过两个中国的现实题材元素“功夫”和“熊猫”进行故事架构为一个神话题材故事,“功夫”和“熊猫”是一对矛盾体,导演将其放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矛盾共同体,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偶然现象,同时映射了东方的虚无文化现象,在各个层面均引发观众热切期待。《千与千寻》尽管是一部关于魔幻神话题材的动画片,但其所选题材建构的异度空间的神话故事映射了“环保”、“泡沫经济”等现实问题。反观国产动画,《宝莲灯》、《魔比斯环》、《神笔马良》(2014版)、《太空熊猫》等影片选材过于神话、虚幻,没有立足于观众心理现实与社会现实基础,导致讲述的故事仅仅具有神话外壳,没有提升人们灵魂的现实内涵。可见,国产神话题材动画片需要“接地气”。另外,国产动画片神话选材也常常表现于“神勇”角色的设置与塑造,即在动画片中设置一个“神通广大”的角色,其在故事中往往威力无比、无所不能,在危急关头总能化险为夷,如《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哪吒闹海》中的哪咤,《魔比斯环》中的杰克等。这些“神角”在剧作中一个共通的功能是解决“剧情危机”,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遇到情节的起承转合不那么平滑的时候,往往通过这个角色进行衔接,情节曲线也就因此不大自然。从这个角度上,国产动画片中的“神角”为编剧提供了推移剧情发展的途径与方式。不过,受众群体观赏过程中也顺利形成了动画情节理解定势,即在情节发展中的危急时刻背后总会有“神角”予以化解,便不会激起观众群体的“群情”共鸣,进而导致作品艺术性的平淡化。《西游记》中,哪怕是唐僧马上被下油锅,观众却丝毫没有紧张感觉,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要来拯救,这些危机情节的“着陆”太容易,观众心理也较平静、淡定,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没有“神角”的经典动画片在处理紧张危机的情节发展时却相当自然,创作者总是站在观众群体的视点,按照故事情节“艰难”地推移,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理一步步发展,将观众群体“召唤”进作品中来共同“化解危机”,而不是将观众推置于一边。危机化解时,观众也为之捏了一把汗,从中获得了艺术体验。国产动画的“神角”现象导致神通广大的“孙猴子”(孙悟空)“敌”不过美国的一只“米老鼠”,原因在于“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造的一只猴子,离现实太远;而“米老鼠”则是从地上“跑”出来的,与人们很亲近,广受观众群体的喜爱。国产动画片只有将神奇化为平实,才能真正抓住观众群体的心。
三、关于选材“远”
国产动画片选材较“远”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所选题材与现实社会距离较远,与当今社会生活丝毫不沾边,动辄把动画题材故事承载的时空开拓到“羊村”、“狼堡”等虚拟的动物生活时空,甚至随意建置诸如太空、外星球等遥不可及的故事空间。国产动画片之所以把主体心灵延伸至距离现实世界非常“远”的时空,主要是想达到叙述自由之目的,获得艺术生命之自由。但结果往往不如所愿,非但不能获得自由的生命强度,反成故事之羁绊。原因是,国产动画创作主体没有找到能含纳这种空间与时间于一体的有机结构,更没能找到足以扩展至如此广阔时空的内在动力,主、客两方面都成了宏大而遥远的存在,故事、主题、文化等层面都达不到相应的生命强度。比如国产动画《太空熊猫》把故事主角熊猫置放于虚幻的太空世界,尽管叙事自由度获得了张力,但受众群体面对的是一个纯粹陌生的审美时空,缺乏审美理解,审美体验也不能“落地”。观众群体对客观现实的崇拜源于对人生实在性的追求,没有现实,人生就会失去依托和参照。只有双脚踏在大地上的人,才会建立起对自己、对同类、对生活的基本信念。号称我国首部三维动画电影的《魔比斯环》也是一部远离现实的虚空作品,其表现时空选定在一个距离地球数百万光年的菲卡星球,距离现实世界太“远”,并且通过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即片名“魔比斯环”)进入遥远的菲卡星球,将大众生疏的、高深的数学概念“魔比斯环”①置入动画情节,未免离现实社会太遥远,观众群体无法运用已有的经验对其进行审美体验。漠视现实,无异于漠视人生,对现实的皈附,是人的重要本性,是人的理性复苏的主要标志。求实的内驱力,历来是人们审美意识和审美热情的重要动因。[3]因此,让主人公置身于现实之外的异度时空,不应仅仅为了故事情节调度的自由,而应该将“遥远时空”与现实时空放在一起作整体认知与表现。并非“远离现实”的动画题材不能选,关键要找到一种能够拢括虚拟时空与现实生活的艺术机体的内在形式。纵观国内外动画片,远离现实社会的动画题材比比皆是,不乏经典之作。主要由于这些动画片能够做到把异度空域与现实生活放在一起作整体认读与表现,巧妙地联接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使观众的心灵在两个时空之间进行自由的审美游弋。即便是完全虚幻的动画题材,也应该处理应好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做到虚实相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桂青山曾分析:“凡获得成功的科幻作品,基本都体现着一条规律,或遵循着一条原则———就是他们不管怎样闪展腾挪、极尽科幻编排之能事,但总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与当时广大观众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某一层面的共鸣。”[4](P.256)譬如美国动画片《阿凡达》表现的题材时空选取在遥远的潘多拉星球,但影片所推崇的反映现实世界中反殖民主义和环保的观念将异域空间“潘多拉星球”与地球联系在一起,物理空间上则是通过宇宙飞船将两个时空联系起来,观众也基于对神秘玛雅预言的恐惧和地球毁灭后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走进了电影院。动画故事观众越远,观众离动画片也就越远,反之亦然。
四、关于选材“旧”
选材“旧”的现象不是指所选题材时间的久远性问题上,而是指在选定了我国悠久的民间故事与文学资源之后,编创态度方面的问题。国产动画片惯常在动画创作过程中,故事编创技艺严重缺乏,“忠实”原著太过,甚至还有“翻版”已有影视作品或动画作品的“吃别人嚼过的馍”的现象。我国影视剧创作热衷于对同一故事题材进行重复拍摄,比如《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四大名著就在不同时代分别进行过不同形式的“复制”或“多制”。而且,在对原著意义读解、改编技巧与创作创新意识等方面,新创影片没有超越旧有影片,乃至还有下滑的趋势。要说超越,仅仅表现在数字技术手段的运用方面,新创影片在影像画面、音效效果等视听效果上更为生动逼真。选材自我国传统文化的国产动画比比皆是,但鲜有精品产出。主要原因在于动画业界缺乏创作技艺,不能从根本上驾驭传统文化题材,只有“照搬”,并冠以“尊重原著”之美誉。这种“忠实”的“啃老”创作形态的实质上就是缺乏创作创新意识,以至于编创出来的动画片既缺乏文化根基又无意趣可言。动画创作者们误以为选材于史料或文学资源的动画题材,必须趋于忠实、品察原作、如实描绘,而不必有太大的创造欲念,没有达到“改编”的目的。这种死钻表现的题材自身,即便巨细无遗、纤毫必呈,也未必能达到原作的境界。故此,创作出来的动画作品显得有些“旧”,即仅仅改变了题材故事的表现媒介,未能从这些题材资源中开掘出新的意义。如《孔子》、《郑和下西洋》等国产电视动画片基本上采用“因循守旧”方式,没有实行富有动画艺术性的改编,实则是将这些原典或史实以动画影像表现媒介形式简单展示。众所周知,所有表现媒介中,文字媒介传递信息量是最大的。因此,用动画影像形式“忠实”改编经典原著势必会对原著意义大打折扣。此外,“吃别人嚼过的馍”也是国产动画选材的一种比较拙劣的方式,选择已经通过动画艺术形式或其他影像媒介形式表现过的故事题材进行“再”创作,香港意马动画工作室电影以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为创作蓝本的3D版动画电影《阿童木》,结果票房大败,并没能达到意想目标。对于原典或史实的动画题材改编,首要的是创作主体应将自己的思想心灵开拓进原著,对要改编的题材进行充分理解、消化和升腾,然后用动画表现媒介形式伸拓出来,最终形成动画艺术。但是,当代动画创作群体以我国历代经典文学宝库作为创作蓝本,进入思想的历史时空,仅仅是为了故事的猎奇性与叙事的自由性,不具有非原典就不能体现某种情感的依据在作动力性后盾,而这种情感依据,恰恰是艺术家主体心灵的依据。国产动画创作主体在“开不进”原著,更“走不出来”的时候,就只有“照搬”原著,这种改编创作行为便会失去原著本身的思想深度、艺术韵味。如此一来,就大量出现误读原典、戏弄史实的动画片,根本就无法表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这样肤浅的动画片与遭国人唾弃的手撕鬼子式的抗日神剧、戏说历史的狗血剧没有两样。总之,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动画题材,处理上要讲究道法,导演、编剧及动画师等创作主体群体首先得将自己的艺术心灵开拓进讲述的题材,然后“驻守”其中与剧中人物交流、体验虚拟环境等,最后以动画影像形式开拓出来,升腾为艺术,这是经典动画创作的心路历程。通过这种创作理路,动画片便能与现实联接、与观众交心,激发广大观众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达到主客共鸣。如果把动画题材“放到一边”随意讲故事,不与题材“交流”,主体心灵也不能“走进”题材故事,即便技艺再精湛,也不能创作出成功的动画片。
作者:李明 杨洁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