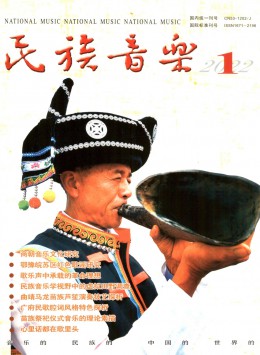音乐学视域下看唐诗中的乐伎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音乐学视域下看唐诗中的乐伎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唐朝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在这一强盛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唐代歌舞音乐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乐伎作为音乐文化的表演载体,为唐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传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活跃于社会的各个文化空间,负载着多种历史信息,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诗则是唐代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在唐朝空前繁荣,诗中不乏描写唐朝乐伎的内容。本文从音乐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诗词中描写唐代乐伎的部分,探究唐代乐伎的歌舞生活。
关键词:唐代;乐伎;唐诗;音乐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乐伎在唐代各个阶层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古时,“伎”与“妓”二字均不表示现代汉语中的“娼妓”之意,在唐代是指擅长歌舞乐器的女艺人。她们是唐代歌舞音乐的传播者,是唐代艺术达到顶峰的见证人。唐诗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是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全唐诗》900卷共收录诗篇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题材广泛,歌颂大唐盛世繁荣的同时,也揭露了现实社会的不公与矛盾,也不乏感叹个人遭遇、儿女之情等。更有许多的唐诗描写唐朝社会风尚时,将乐伎纳入重要的部分进行描述,可见当时社会中乐伎已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乐籍制度下唐乐伎的社会地位
在乐籍制度的影响下,乐伎出生卑贱,从小接受歌舞训练,是唐代音乐文化表演的重要载体。乐籍制度是北魏时期形成的一种户籍制度,是用来惩罚犯人家属、区分等级的一种历史阶级性产物。被纳入乐伎的人所在的家族都会沦为乐籍制度内,成为受人鄙夷的乐户。到了隋唐时期,乐籍制度得到完善,建立了太常、教坊等培养乐人的宫廷机构,于是乐籍中的乐人与平民中的乐人没有了太大的区分,各尽其职。乐籍制度下产孕而出的歌舞机构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存在,宫廷机构中的太常寺、教坊、梨园;地方机构的“县内音乐”和“衙前乐”,以及军营音乐和民间歌舞机构。入了乐籍制度的乐伎已颇具规模,在长安、洛阳等城市中,花街柳巷,乐伎数量惊人。根据等级、机构、类型的不同,乐伎大致可分为宫伎、官伎、家伎和散伎。在唐代,乐籍的概念已经被模糊化,众多善于歌舞的乐伎出现,预示了唐代的繁荣与昌盛。唐代的乐伎出身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因话录》中记载的,“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罪犯的妻子和女儿被判为乐工,视为乐伎。第二个为已沦为乐籍制度的后人,有记载唐代的乐户后人不得改职业。第三种为民间姿色较好的平民女子,可成为乐户落入乐籍。《教坊记》中有记载:“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谓之撐弹家。”沦为乐籍的女子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为世代子女都是乐户,入乐籍之事受人轻蔑,一般女子是不愿意入为乐户。而且乐伎的地位十分低下,常用来买卖与赠送,不得与良人同类,不可以和良人结婚,没有人身自由。初唐时期很难见到乐伎的姓名,通常多为无名乐伎,随着统治者对音乐的推崇,诗歌中的题目和内容都出现了乐伎的艺名。
二、乐伎诗的发展变化
唐诗是中国文学上璀璨的明珠,其中的种类繁多,乐伎诗是非常特别的一类,在唐朝乐伎诗非常受欢迎。在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全唐诗》中,有关于乐伎的诗词竟然多达两千多首。如李白所写的唐诗中,就有约22首描写乐伎的诗,刘禹锡也有约20首描写乐伎的诗。此外,乐伎诗也包括一些乐伎自主创作的诗歌,记录在《全唐诗》“妓女”卷中,著名的女诗人有薛涛、赵莺莺、关盼盼等。之所以乐伎诗如此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唐代的统治阶级喜爱歌舞、精通音乐,统治者的喜好与提倡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在全民享乐之风的倡导中,促使了乐伎诗的诞生与发展。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大唐提倡民族融合,四海一家,使得社会风气自由开放。在如此开明的政治下,为各民族之间创造了积极友好的交流氛围,人民思想开放,诗人们纷纷对许多少数民族的乐伎表演屡有描述。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文学观念得到转变,对于女性的容貌、体态、服饰以及演奏风格、技巧的描述比比皆是。在初唐时期的乐伎诗,通常以客观的角度描写乐伎的表演技巧,诗人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歌咏乐伎技术的高超。诗人一般从乐伎的歌喉、舞姿、穿着、发饰等方面着笔,以观赏者的角度回忆乐伎的表演场景。如陈子良《酬萧侍中春园听妓》:“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一句就是描写舞伎穿着和动作的诗句。初唐时期的诗歌多描写无名乐伎的舞姿和跳舞场景,平铺直叙的语句较多。可见当时初唐的歌舞并非普遍,仅仅视为娱乐活动而非生活的必需品。盛唐之时,文化、国力、科技全面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共享繁荣。一批优秀自负的诗人横空出世,有着如此开放的国风,使他们的诗可以畅所欲言,自由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与初唐的乐伎诗相比此时的乐伎诗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描写乐伎歌舞表面盛世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细腻的情感和细节,比如“仙伎来金殿,都人绕玉堂。定应偷妙舞,从此学新妆。”一诗,对歌舞琴艺十分出色的乐伎艺伎描述的非常细致;“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李白通过对乐伎放荡不羁的姿态,表达对谢安的崇仰之情,从而透露心底的沧桑沉郁。安史之乱以后,人们对唐的统治不再乐观,唐朝由盛转衰,文人墨客纷纷用诗词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批判朝政已是当时常态之举。诗人们开始关注乐伎的不幸命运,伤悼怀念乐伎的陨落。如窦巩的《悼妓东东》所写“芳菲美艳不禁风,未到春残已坠红。惟有侧轮车上铎,耳边长似叫东东。”悼念逝去的乐伎。另外出现了许多乐伎自己创作的诗词,如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锦江集》中流传至今的诗作有90余首,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蜀中四大才女之一。
三、从唐诗看乐伎技艺
在唐诗中,不乏形容歌伎歌声的诗句,如张祜《歌》:“皓齿娇微发,青蛾怨自生。不知新弟子,谁解啭喉轻”中,“啭喉”一词就是描写歌伎的歌声婉转动听、悠扬流畅,深入诗人之心。张祜另外一首诗《听崔莨侍御叶家歌》中这样写道:“宛罗重縠起歌筵,活凤生花动碧烟。一声唱断无人和,触破秋云直上天。”其中描述的是歌伎唱歌的技巧运用的灵活自如,像是冲破了云霄,非常的高亢嘹亮。亦有描写歌伎演唱技巧清亮透彻,诗人均用“清”字来形容歌声,如武元衡《赠歌人》所写:“曾逐使君歌舞地,清声长啸翠眉颦。”在唐代,无论是“九部乐”、“十部乐”,还是“坐部伎”、“立部伎”都与舞蹈息息相关。唐代法曲中最为著名的大曲《霓裳羽衣曲》被白居易誉为“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这样描述《霓裳羽衣曲》的舞蹈场景,“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这句就是描写起舞时的姿态,乐伎的舞姿曼妙犹如仙界的仙女般,震撼人的心灵。杨衡道:“蹑珠履,步琼筵,轻身起舞红烛前。芳姿艳态妖且妍,回眸转袖暗催弦。”用“蹑珠履,步琼筵”描写舞者的舞步轻盈,似踩着珍珠般踱步,身体柔软轻巧,身姿曼妙令人神往。歌舞盛行的唐代,乐器的兴盛和发展与歌舞艺术密不可分。唐代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朝代,上至天子下至臣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接纳异常的宽容。“九部乐”中就将周边藩国的民族乐舞纳入其中,民族乐舞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冲击,更是对民族大融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唐代乐伎十分擅长器乐演奏,唐诗中对她们娴熟的演奏技巧描述甚微,有本民族传统的乐器演奏,也有外来民族所使用的乐器演奏。有如琴、筝、瑟、阮等传统乐器,也有包括琵琶、羯鼓、觱篥、箜篌等外民族乐器。《听崔七妓人筝》是白居易所写有关于乐伎弹筝的一首诗,诗中写道:“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可见当时筝的演奏十分流行,女子坐于玉楼之上,低头弹筝,从筝声中听取了些许愁绪,似十三根琴弦拨弄而出。白居易由乐伎演奏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丝丝哀愁,以物抒情。白居易的《琵琶行》流传千古、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誉为,从《霓裳》到《六幺》(即《绿腰曲》)皆为唐名曲,白居易用短短几言将乐曲的动人之处描写的淋漓尽致。“轻拢慢捻抹复挑”是琵琶演奏中推弦、揉弦、下拨、回拨的动作,可见唐乐伎的演奏技法十分成熟,技巧运用非常流畅。有好似骤雨般的低音扫弦,也有如私语般急切的拨弄,嘈嘈切切相交替,像颗颗大小不一的珍珠坠落玉盘。琵琶声音的多变性使得其在唐朝大放异彩,大部分有关于乐伎演奏的诗词都以琵琶曲作为描写的对象。
四、从唐诗看乐伎形象
乐伎从技艺、职业、社会层面无不渗透着权力,由于他们身处乐籍制度之内,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当权者的支配,无人身自由,唐诗中也透露出了这一点。晚唐名伎徐月英在《叙怀》一诗中感叹自己悲惨的命运,曰:“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她诉说自己常常泪满心底,不愿做这为人不齿的职业,就算日日笙歌,却还是会羡慕穿着布裙朴素的农妇。诗中无不透露一位被迫沦落乐伎的女子,为了谋生活而带来的无尽的痛苦,令人叹息。唐代才女薛涛将乐伎悲惨的生活写入自己的诗中,受人折磨,众叛亲离,因为面色衰败而遭遇唾弃。《十离诗•镜离台》一诗中写道:“铸泻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裴回。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乐伎之人遭到无端的诽谤却无处伸冤,只得默默忍受被政权之人遗弃。“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是一名太远的乐伎女子寄给欧阳詹的一封信,在临终之时仍对情郎牵挂在心。乐伎也为人,她们对爱情是忠贞的、痴迷的,诗中所写动人心弦,情真意切,却亦透着苦涩和遗憾。唐诗中歌咏乐伎追求爱情的诗非常的多,大多为乐伎亲自创作的爱情诗,诉说着对情郎的真心。“与君咫尺长离别,遣妾容华为谁说。夕望层城眼欲穿,晓临明镜肠堪绝。”诗中叹离别之情,思君之意,诗人牵肠挂肚,望眼欲穿,表达作者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勇于追求的情愫。在许多诗人眼里,乐伎在表演时有着光鲜艳丽的外表,诗曰:“翠蛾转盼摇雀钗,碧袖歌垂翻鹤卵”,头戴雀钗的乐伎,身穿碧衣长袖舞于梨园内,甚是优雅可人。“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刘禹锡在《赠李司空妓》中描写乐伎的发饰,盘着云髻,高唱一曲。诗人所写的唐诗中多为描写乐伎服饰、发饰等外表形象,而乐伎本人创作的诗词多为表达内心渴求的愿望,体现乐伎原本的凄苦形象。相结合不难看出,虽然乐伎笙歌于权贵之间,却仍渴望着自由与安定,他们不愿对命运低头,也曾像权贵抗争,但都没有好的结果。他们追求爱情,对爱情忠贞不渝,但由于社会地位、乐籍制度的束缚难以实现,无限的悲凉。
五、结语
乐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时代印记,因为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他们的生活只存在于文学中的只言片语。而乐伎代表着古中国音乐的繁荣,尤其在唐代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如雨后春笋般兴盛,唐代乐伎诗由此而来。无论是诗中所写乐伎和乐伎自己创作的诗,都表现了丰富的唐文化,乐舞的繁荣应运而生。乐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正由于他的独特性在古典歌舞艺术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歌唱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乐器技法的创新与改良、舞蹈艺术的传播与推崇,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唐文化的融合,是华夏音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清•彭定求校点.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
[2]郭海文.唐五代女性诗歌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4.
[3]王晓霞.唐代乐伎诗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0.
[4]何玉.音乐与身份:唐代乐妓的音乐生活[D].西南大学,2012.
[5]项阳.乐籍制度的畸变期考述[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04.
[6]秦晓妍.谈乐籍制度对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J].歌海,2012,01.
作者:王忆南 单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