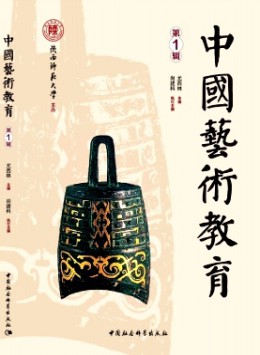中国艺术电影的话语变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中国艺术电影的话语变迁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内容摘要】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艺术电影也在影像表达和身份认同上体现出“文化自信”,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探寻和对自我身份的哲学追问。其影像中呈现出“文化的中国”,而不再只是“镜像的中国”。艺术电影在主体设置、影像表达和身份认同方面的更替性转变,也正是后全球化时代艺术电影的新表征。
【关键词】后全球化;艺术电影;影像表达;身份认同
一、后全球化与艺术电影
在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世界范围内大众文化的流行趋势。尤其是“好莱坞”几乎成为世界电影的代名词,美国电影对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影像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有人认为,在“后全球化”时代,与“冷战”时期以及全球化时代相比,全球化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对中国文化的阻止作用超过了所有的贸易壁垒,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国际文化界一直主张的文化多元化将真正被人们所肯定,②在这个阶段涌现出的中国新生代导演,他们的电影开始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开始进行回归性质的影像探索。尤其是2016年以来的艺术电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艺术电影气质的表现形态,开始致力于对东方文化艺术精神的挖掘以及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化,逐渐摆脱自怨自艾和悲天悯人。关于“艺术电影”的界定,学界说法不一。笔者比较认同的是吴冠平在《艺术电影手册》中所表述的:“正如‘艺术’无法用准确的术语进行定义一样,‘艺术电影’也不是几段话可以廓清的概念。艺术电影的创作,有时候就像一场与常态思维、价值、道德一起进行的智力游戏,最艺术的往往是最出人预料的、无法言说的。”③以时间为分割单位,粗略地说2016年之前中国艺术电影的创作主体基本上是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管虎、娄烨、张元、贾樟柯等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影坛,用“自我言说”的方法拍摄了一系列“成长电影”。他们同时还把镜头对准了生活在当时的社会边缘人,影片中弥漫着无处安放的青春和物质匮乏的窘迫,用纪实性的影像风格还原生活状态的本真。生活已属不易,当时他们还无暇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个体的来源。随着新生代导演涌入影坛,2016年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突破了电影创作的常态。2016年的《路边野餐》《长江图》《冬》和2017年的《冈仁波齐》《七十七天》《嘉年华》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新的电影语言。这些影片摆脱了第六代的“物质”窘态,开始探索心灵的哲学性归宿,在现实主义的影像呈现中融入了“超现实”的表达方式。
二、主体设置——充满诗意的边缘人
第六代导演电影中的主体形象大都是存在生存焦虑的边缘人——小偷、民工等,这些小人物游走在生活的边缘,造成其焦虑的最主要原因是其生存的困境,也就是物质的匮乏。小武(贾樟柯《小武》)因为缺钱,成了小偷,成为街头的“被观看者”;韩三明(贾樟柯《三峡好人》)因为缺钱和生存环境的闭塞,“买”了媳妇,媳妇却跑了;黑道邮递员马达(娄烨《苏州河》)迫于生存的压力,出卖了自己的心上人,最后陷入精神困境。2015年徐浩峰的《师父》,主角是一个民国年间的武术师父,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个师父仍然是一个边缘人,为挤进主流环境而不断努力。这一年的《塔洛》《山河故人》的主体,也依旧是生存于困境中的边缘人。2016年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创作则契合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因为小康生活除了物质上的丰衣足食以外,还意味着精神上的丰富满足。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文化形态的电影,呈现出小康社会相关主体对文化的精神追求。笔者认为,2016年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艺术电影是杨超的《长江图》、毕赣的《路边野餐》和邢健的《冬》。虽然影片的主体依旧是边缘人,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了被物质束缚的生存困境,转而追求生活的意义,是充满诗意的边缘人。《长江图》中的高淳,导演没有刻意表现他的家庭环境,但从零散的信息中,我们得知他没有受到因物质匮乏带来的生活困扰,活得自我而自在。因由一本诗集,他的生活有着诗意魔幻般的色彩,他的行程是一场心灵的涤荡,他就像一个流浪的诗人,徜徉在长江无尽的遐想中。《路边野餐》中的陈升是一个小诊所的医生,母亲过世的时候还给他留了一套房子。他与弟弟的矛盾,虽然有房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情感因素。他在影片中所有的境遇,根本性动因都是因为他自己对情感的价值认定。《冬》中的老人甚至都没有名字,他独自一人生活在看起来“非实在”的环境里,每天吃相同的食物。从画面中看,老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从内在表达上看,老人始终在追寻的是情感依托。《路边野餐》和《长江图》都有诗意外化的部分。《路边野餐》全程贯穿着陈升自己“朗读”诗歌的声音,一个小城镇诊所的医生与诗歌产生关联,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情。《长江图》则通过字幕的形式,展现了高淳拿到的诗集《长江图》的内容,他沿着长江自下而上一路找寻一路诗。《冬》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台词,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行走在风雪飞舞的广袤天地间,更平添一种生命的诗意。在2017年的《冈仁波齐》中,一群生活在藏族地区的普通牧民虽然生活清苦,但是整部影片着重于探寻他们的精神追求,并没有涉及物质困境。他们在朝圣的路上经历了各种困境,但没有哪一种是直接与“钱”发生关系。即便最后抵达拉萨以后,他们已经没有钱去冈仁波齐,在这种境况下,导演让他们“自食其力”,通过打工的方式赢得后续的路费。一路上除了集中念经他们几乎默默无言,没有丝毫对生活的抱怨。从这些影片的主体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后全球化背景下,普通人不再因物质生活的窘迫而展现生命的无可奈何,而是开始追问和追寻生命的意义。在这些影片中,从充满生存焦虑的边缘人到充满诗意的边缘人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因时代特性而赋予电影的不同特质。
三、影像表达——魔幻与写意
爱德华•赛义德指出:“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同样,西方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和评价,也是基于一种“东方主义”,是他们为了确认“自我”而构建起来的“他者”。
(一)表现手法的魔幻性
第六代导演致力于纪实风格表现手法的运用,以展现中国银幕上所缺失的小城镇景观。这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般的镜头风格,客观地呈现了其时其地的生活状态,但却在某些方面,缺失了人物心理情感的表达。2016年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开始探索新的影像表达方式,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交织,表现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其在影片中展示了现实的中国,开始确认“自我”的存在。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这种表达方式置换到电影中,就成为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叙述超越现实的情节和故事。2016年以来的艺术电影,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1.纪实手法的魔幻应用
一是长镜头的使用体现纪实性。备受纪实美学大师巴赞推崇的长镜头,最大的作用就是它的纪实性。巴赞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而最能体现电影这一性能的表现方式就是长镜头。毕赣在《路边野餐》中用这种最具纪实性的长镜头,呈现了一段虚拟时空。影片中陈升因为诊所同事的“请求”和自己要去找弟弟孩子的双重动因,从凯里启程去镇远。在火车穿越隧道之后,陈升进入了“荡麦”梦境。镜头的转场是通过苗人吹笙的画面切入到陈升搭车的画面,画面从稍微有点变形到回归正常。接下来40多分钟的镜头,是一个完整的长镜头,这个部分在整个影片中承担着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核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陈升与自己曾经的“爱人”重逢,讲了从前没有讲的故事、唱了从前没有唱的歌,在虚幻的时空中,生命中曾经的遗憾有了一次补偿。镜头从陈升上了小卫卫的摩托开始,一直跟随陈升的行进路线。中间陈升换乘一个小乐队的顺风车之后再次遇到被人捉弄的小卫卫,他第二次搭乘小卫卫的摩托。这时镜头在跟拍时,突然转到其他的拍摄路线,在一个胡同下坡之后,与陈升汇合。这个片段通过一个连续的画面将镜头从客观镜头转为主观镜头,仿佛陈升在被“第三个人”观看,而这个人就是冥冥之中主宰他命运的隐秘存在。二是360度圆周镜头营造时空的虚幻性。《长江图》因为拍摄环境的制约,镜头的运动受到限制,所以在狭长的广德号上,有很多360度圆周运动镜头。高淳到铜陵和悦州找寻安陆的足迹,在一个摆渡船上,镜头进行了几乎360度的运动,最终画面并没有回到原点,而是切到了安陆所在的住所。虽然从物理学角度讲,360度就应该从原点再到原点,但是高淳并没有抵达他最初开始的地方。影片的结尾部分,高淳在时空交错中看到了对面船上的安陆,接着一个摇镜头从安陆的特写摇到高淳的特写,两人仿佛是在同一条船上。高淳伸出手,镜头再摇回来,安陆把诗集递给高淳,高淳撕碎了诗集,碎片在空中飞舞。镜头再从高淳摇向安陆,画面却空了,安陆仿佛凭空消失了。在这个连续的运动镜头中,导演营造了超现实的时空存在。由此让人们去猜测,高淳所遇见的安陆,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2.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
一般而言,现实主义的电影都会严格遵守现实时空描绘的原则,影片的叙事结构一般是遵照事件发展顺序的线性叙事。而魔幻现实主义则在现实时空中,插入了超越现实的时空叙事和结构。《路边野餐》从时空结构上来看,是从现在时空到虚幻时空再到现在时空。这几个时空存在内在线索的联系,但又不具有常规的因果关系。叙事依靠典型的影像符号来串联,在不同的时空里出现相同的影像符号。比如卫卫(第一段现实时空中的孩子名叫卫卫,第二段虚幻时空中载陈升的摩的男孩也叫卫卫)、理发店的女人(第一段现实时空中,闪现了陈升已故妻子的影像,第二段虚幻时空中理发店女人就是他亡妻的模样)、花衬衫(第一段现实时空中,花衬衫是陈升同事交给他、让他转交的信物,而在第二段虚幻时空中,陈升穿上了这件象征爱情的信物)、望远镜(第二段虚幻时空中,大卫卫把望远镜送给了陈升,而第三段的现实时空中,陈升却拿着这个望远镜看到了放学回来的小卫卫)等。这些符号的贯穿,使影片披上了魔幻主义的色彩。这些在时空交错中出现的人物,就像我们的记忆一样,不可捉摸也无法确定。导演杨超说《长江图》是一部科幻片。高淳不断在长江沿岸的码头遇见同一个女人,为何遇见,女人从何而来,这些都仿佛被一本叫《长江图》的诗集所指引。而在时间流动上,高淳是顺时性地自然生长的,而安陆则是逆时性地非自然生长的。一个去向未来,一个回到过去。安陆是高淳心里所向往的美好,是心底里隐藏的另一个自己。安陆也是长江的化身,她是高淳隐匿和栖息的怀抱。就像诗歌的本质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不可言说的美好和伤痛。无缘由地相遇、无缘由地找寻。从影片的表现上看,他们每一次的相遇都是真实的遇见,触摸了真实的彼此。安陆是高淳这一路找寻的动机和结果,在静美如画的长江里,他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七十七天》也是多线叙事,一条线索是杨独自穿越羌塘无人区,一条是他与蓝天相遇,蓝天送他到阿里的线索。电影叙述中,这两条线索是交织出现的,他们的相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杨一个人在无人区继续前行的力量。
(二)影像风格的写意性
写意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种重要精神,这种艺术精神重神轻形、求神似而非形似,力求虚实相生甚至化实为虚,重抒情而轻叙事,重表现而轻再现,重主观性、情感性而轻客观性,并在艺术表现的境界上趋向于纯粹的、含蓄蕴藉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④
1.“以大观小”“情景交融”
《长江图》号称是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因为出色的镜头画面,获得了第66届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摄影)”。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特征是“以大观小”“情景交融”,其宏观视角的画面蕴藏着生命的情感投射。该片基本上以大景别构成,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长江的意境美。人物在画面中以点缀的形式出现,体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大雾弥漫的长江有一种朦胧美,映射生命的不确定性;江面上孤单的船和渺小的人,传达了生命的孤独性;夜幕下的长江静谧神奇,风雪中的长江孤傲冷峻。《冬》的开篇颇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风雪交加的茫茫天地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冰窟旁钓鱼;光影昏暗的小屋,简朴却不简陋;在风雪中徒步前行的老人,如沧海一粟,却熠熠生辉。《冈仁波齐》中有很多的超大远景,来呈现这群人与藏区环境的关系。尤其是影片最后,在白茫茫的冈仁波齐山间,几个朝圣的人化为黑点,在银幕上留下生活的印记。《七十七天》这部影片最突出的是摄影风格。全片几乎60%左右的镜头都是大远景,呈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不同色彩、不同地貌的藏区风景将主人公完全包围。影片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是杨来到了一片“水天相接”的地方。蔚蓝的湖面和蔚蓝的天空交融在一起,杨骑着自行车穿行其间,仿佛一个自由的灵魂在天空翱翔。在广袤的天地间,人如沧海一粟。冰河、沙漠、石山、洪水、大雪,杨就穿梭在这美丽而又神秘的自然天地间。而这样罕见的景象,却是在无人居住的地方,不禁使我们思考人与自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以黑白影像呈现的。镜头隐忍克制地呈现了那个异常紧张时代里异常紧张的人际关系。摄影机很多时候距离人物很远,我们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就像他自己也看不清自己一样。影片中几处大景深镜头,将人物置于中景,被前景的小溪和后景的大山包围,表明他们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压抑的时代。
2.诗画同体
《长江图》中,高淳在江对面看到缓慢行走的安陆,镜头的前景是高淳飘忽不定的衣服造成的黑影。在这个占整个画面四分之一的黑影上,出现了字幕诗句“新船上水七千公里/发动机不停咳嗽/我压低声音穿过温暖的县城/怕人听出心中怨恨”。画面与诗句交融在一起,充分体现传统绘画美学诗画同体的审美意境。《长江图》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画面布局安排,让本来就意境极佳的画面,更添了内涵丰富的诗意。
四、文化、身份认同——回归与探寻
(一)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性探寻
“文化认同”这个术语指的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⑤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逐步提升,电影作品更加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用更理性的态度去讲述它。《长江图》《路边野餐》《冬》等影片,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探寻已经表现得很明显。《长江图》开篇讲了江边的一个习俗:“父亲去世以后,孝子必须亲手在河里捞一条黑鱼,供在香炉里,不能喂它任何食物。当它自然死亡那一天,父亲的灵魂就安息了。”在这里,黑鱼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个外化符号。《冬》是1984年出生的邢健的第一部电影。影片用无声的风格,表达了依存与背叛的关系。老人因为老伴儿的去世显得异常孤独,每天通过“钓鱼”“放鱼”这种外在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当不断有新的“伙伴”出现在他身边时,可能是出于“新鲜感”,他就放弃上一个同伴。最终,所有的同伴都走了,留下仍旧孤单的他。在茫茫风雪间,他依稀看到了自己的“爱人”拥他入怀,他获得了永久的陪伴。
(二)对自我身份的哲学性追问
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己的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认识与定位,人们对自我的定义来源于身份认同,并且人们对意义的组织常常是围绕其自我认同而进行的。⑥,通俗地说,身份认同就是人们确认“我是谁”。2016年之前的中国艺术电影,在身份认同上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在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都遭遇了不可抗的时代困境。例如影片《老炮》的自我认同与时代背景是错位的,所以最后六爷穿着军大衣、握着军刀一个人“冲锋”的时候,有种无可奈何的悲壮感。影片《师父》中的陈识,一心北上扬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却遭遇“时代变故”,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身份认同发生改变的首要条件就是情境的变化。后全球化时代,艺术电影中的身份认同开始呈现哲学追问的倾向。人物在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不再遇到现实的壁垒,而是可以充分自由地探索,其从确立身份转变为“核实身份”,追求精神自我的满足。《长江图》中的高淳在父亲去世后继续从事“家族事业”,无意间在广德号上发现了一本诗集《长江图》,而诗集中所出现的地点恰巧与自己偶遇女人的地方重合,这在冥冥中仿佛暗示着什么。高淳就这样沿着长江回溯源头,在找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对存在的追问。安陆到底是谁?与高淳念念不忘的潜在自我有关系吗?当最后安陆与高淳隔船相望、高淳撕掉诗集时,他说:“你不需要诗歌,你不需要再去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这一刻,高淳仿佛见证了自己的人生,愿用自我“牺牲”来救赎另一个自己。他从终极存在的意义上,确证了自我。《路边野餐》中陈升在不同的时空里游荡,与过去重逢、与未来相遇,追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因为哥儿们义气,陈升坐牢九年,出狱后妻子和母亲都去世了。生命因为自己的“正义”而留下了巨大缺憾,潜意识里他想回到过去,弥补失去的时间,他也想去到未来,看看年华老去时自己的样子。而在当下,他只是一个小诊所的医生。肉体身躯的存在受时空限制,精神意识却可以无限徜徉。在时空交错中游荡了一次的陈升,发觉一切就像梦一样。不同于高淳的确证自我,陈升质疑存在的确定性。他从更高维度的哲学层面,思考存在。《冬》中的老人,一直在依靠他者来确证自己的存在。“鱼”“鸟”“小孩”,这些意象的变化,体现了老人存在价值的不断提升。老人总是竭尽全力维护现在的陪伴者,为了鸟杀了鱼,为了小孩杀了鸟,而最后小孩罹难了。随着这些陪伴者的不断离去,老人的精神支撑崩塌了。没有支撑自我存在的他者,老人也失去了生命。《七十七天》中的杨,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家庭境况如何,更不知道在进藏之前他有什么人生际遇。可以说,我们除了知道他来自上海以外,其他一无所知。影片通过主人公独白的形式,表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在这短短的一生里,鼓起勇气做想做的事,成为想成为的那个自己。”他之所以要一个人徒步横穿羌塘无人区,就是为了追求自由。《二十二》反映了人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曾经屈辱的苦难,在那些亲身经历过的普通人眼里一些大的时代命题是怎样的存在。经历了特殊年代的特殊痛苦,如今他们几乎处在被遗忘的边缘,而历史给个人造成的创伤,却是这个时代应该警醒的。他们不是自己确证自己是谁,而是通过这个影片让现在这个时代确证他们的存在。《嘉年华》中在酒店打工的姑娘,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很小就逃离原生家庭,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没有办法上户口。对这个社会而言,她是一个不合法的存在。她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但心底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证的身份。于是她冒险“敲诈”一万块钱,希望健哥能帮她办一个身份证。事情败露后,她听着电视机里解救女孩的消息,勇敢地踏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2016年是后全球化时代的开端,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传统文化价值得到不断确证的同时,艺术电影的表达领域也会相应拓宽、表现手段也会更丰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也会更加自觉。总之,后全球化时代开启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时期,也为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作者:郭锐 单位:山西省吕梁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