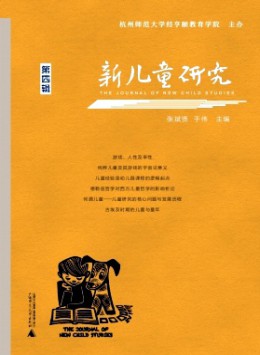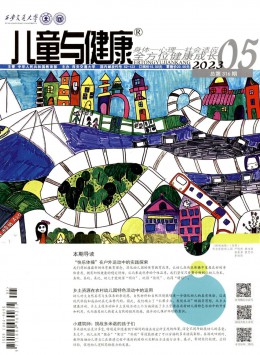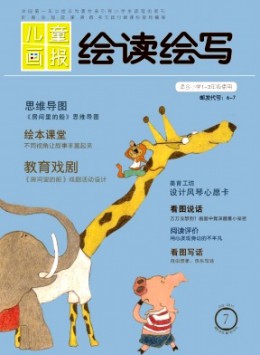儿童动画电影创作叙事伦理建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儿童动画电影创作叙事伦理建构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从接受角度看,作为以儿童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的叙事伦理是创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颠覆、解构、重构是推进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的重要理念,但这种探索在以未成年人为主的电影类型中应当慎用,电影符号的能指承载了儿童对所指的认知与接受过程,动画电影应当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理性与个体价值有机辩证地呈现,将儿童能够接受理解的伦理观念与影像叙事完美融合,使审美内核与儿童成长的情感期待达成趋同。
【关键词】中国动画;叙事伦理;传统文化;文化理性
动画电影的观影对象主要以未成年人和陪同他们的家长为主,虽然近年出现了一些以成人为消费目标而创作的动漫作品,但就国内院线而言,当前以未成年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故事片少之又少,从数量、质量上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进入电影院。因此,从小在电视动画熏陶出来的观看习惯,使动画电影几乎成为唯一能够让未成年群体进入影院的电影类型,这个潜在的极其庞大的消费群体是近年中国动画电影投资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动画电影主要接受群体的特殊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片种来看,动画电影的叙事伦理建构更为迫切、更具有现实意义,当下中国动画电影制作者对叙事伦理的认识不足,影响了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
一、叙事伦理对儿童动画电影的重要性
叙事作为一种必然需要创作主体介入的活动,天然地存在着伦理构建功能,“阅读理论提醒我们,叙述者展开劝说意在对读者的世界观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上绝不是中立的,而是或隐或显地引出一种对世界和读者的价值重估。在这种意义上,叙述以其对伦理判断的要求而从属于伦理领域。”1叙事以文本为中介,给受众呈现了在不同的空间、时间里可能发生的千姿百态的人生遭遇,这些叙事弥补丰富了受众人生经历的局限性,让人们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观摩文本中人物的悲喜人生,将之汇集到自己的人生经验中不断总结反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既有的人生经验、处世理念。电影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电影的银幕更像一面镜子,当观众坐在黑暗封闭的电影院里凝神关注银幕上呈现的影像时,仿佛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说的处于婴儿时期的人,银幕中所呈现的人物故事情境如同镜像一般,延伸了观众的自我想象,观众随着银幕中人物经历或悲或喜,连带着想象秩序中自我的延伸,在这种情感的互动中,将自己与电影叙事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放映发生于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待在里面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得到(或者根本不去认识),都像是被拴住、俘获或征服了”。2儿童正处于身心快速成长的阶段,其个性和对社会性认知在教育、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变化,此阶段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但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直接与感性经验相联系。3现实生活中的见闻直接构成了儿童的感性经验,作为儿童青睐的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动画片无疑是儿童获取感性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动画电影以影像形式与儿童相遇,动画电影中的人物经历、处理事情的方式就会与他们已然建构的经验冲突、融合,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儿童的个性发展、社会性认知的形成。因此,电影叙事伦理对儿童较之于成年人的影响更为深刻。动画电影是公认的具有“全家欢”功能的电影类型,虽然以儿童为主要观影对象,但儿童能否进电影院观影的决定权主要取决于为他们提供消费的成人。与电视动画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可以在家里独自观看电视,而儿童观看动画电影是由成人陪同的。当成人在观看动画电影时感到故事乏味,或者意识到电影中所传递出的伦理价值观与自己对儿童的教育相悖时,观影的不适感会影响成人今后是否愿意继续承担儿童的这种娱乐消费。在市场化经济体制下,一种电影类型是否能够良性发展,经济收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真人版电影与动画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观众对真人版的某一种类型电影厌弃之后,会有大量的其他电影类型供其选择,而动画电影本身就包括了爱情/伦理/奇幻/灾难等各种类型题材,不同题材的故事类型局限在“动画”这一类型之下,形成了动画电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状态。从动画电影的长久发展上考量,绝对不能像一些低口碑高票房的真人版电影那样,以非常态叙事搏人眼球,吸引话题炒作,以“赚一把就跑”的心态来操作动画电影的发行,否则会把一些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观影群体再次赶回电视机前,赶到进口动画电影那里。
二、被利用与滥用的传统文化叙事错位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构成包括外显的物质层面与内隐的精神层面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中国传统文化外显的物质层面纷繁驳杂、包罗万象:民风民俗、方言土语、服饰特色、地域生活方式、各种艺术创作等等,这些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特点的物质呈现,在日趋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景观,区隔了“地球村”同一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显示出有别于他国的差异化色彩。内隐的精神层面主要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儒家元典精神以“仁爱”为核心,提倡人们应当以君子的标准来修身修心,修身、齐家、济世是人们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要秉承的生活准则,只有不慕功名富贵、以强烈的责任感承担社会义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社会的楷模;佛教文化提倡以“无我”的精神普度众生,奉行“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准则,看重善恶因缘的果报对众生六道轮回的影响,从因果报应角度提倡“众善奉行,众恶莫做”的行为规范;道家文化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之“道”,以“无为”为准则修养身心,从而达到身心的绝对自由状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显内容相比,内隐的精神层面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数千年的波折依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许多传统文化的物质呈现是以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为基础而产生的,在外显的物质层面之下包裹的是深邃幽远的精神内涵,表里相互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向来是中国动画电影的资源宝库,其原因在于:首先,这些文化资源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依然广为传播没有断流,许多文化的内核已然内化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强盛的生命力使之具有天然的广告效应;其次,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认知潮流的感召下,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会使电影呈现出独特风格,从而满足观众奇观化的观赏兴趣,因此,电影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掘取人物和素材是长久以来的趋势。从早期引起世界关注的中国动画电影《大闹天宫》《神笔马良》到《宝莲灯》、2015年重燃中国动画电影信心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6年的《大鱼海棠》、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借助网络动漫的粉丝效应而制作的《万万没想到》等电影,情节构思的源头或一些动画形象的设置都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经典名著或寓言故事,甚至美国也借中国传统文化之东风,拍摄了《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电影,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吸引观众已然成为当下诸多动画电影的构思方向。
对于儿童来说,动画电影中表现的传统文化物质层面便是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银幕上传统人物形象、传统故事的传播,既是电影借用传统文化资源提高票房的利用过程,也是传统文化借用电影这个娱乐资源传播的过程,如果运用得当,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在众多动画电影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之名拍摄、宣传并引起观众观影兴趣的表象下,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种热烈场面下的缺憾,这些电影所呈现的大多是传统文化的外显物质层面,对内隐的精神层面的内容触及不多,甚至有的动画电影只是简单罗列了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审美内涵与传统文化精神完全无关甚至相悖,对传统文化资源不走心的滥用现象比比皆是。从电影符号学角度来看,影像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能指即这些在银幕上呈现的人物形象,所指是指这些人物所承载的意义。这些动画形象经由情节叙事而承载了一定的文化理念,观众对动画形象的接受,正是对其背后承载的文化理念的认识与认可的接受过程。当下的一些动画电影只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当作赚取票房的噱头,缺乏对传统文化深入认识的动力,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表现上苍白无力甚至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背道而驰。当前的一些中国动画电影,频繁出现传统人物形象,这些经典形象本身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他们的名字本身就伴随着意蕴丰富的先文本而存在的,但是,一些动画电影中的传统人物形象只是一个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走马灯式的能指符号呈现,却没有形成具有所指意义的后文本。莎士比亚认为,在创作中哪怕一只麻雀的死,也自有天意。电影人物形象的设置应当能够推进故事发展,有益于主题的表现。而这种只是简单的传统文化人物单一的能指符号陈列,因为失去了本可以意义丰富的所指意义,除了能够在电影宣传时增加一点传统文化意蕴丰富的表象,受众在观影的接受环节只觉得动画形象的设置多余,毫无意义,儿童在观看时由于人物形象众多会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这不仅表现出电影编导在叙事能力上的欠缺,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不求甚解的态度。当下中国的许多电影生产者,将传统文化当作电影随用随取、用之不竭的免费资源,既可套用现成的人物或故事展开拼贴、颠覆、解构,不必再费周章寻找素材,降低了编写故事的难度;又可借助这些广为人知的文化资源吸引潜在的巨大受众群,以传播传统文化的噱头唤起受众的文化情怀,降低了传播成本;还可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金字招牌,完全照搬传统人物、情节可说是传承传统文化,随便拼贴解构可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借此提升所拍摄作品的文化品位。而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无论是所谓的传承或反思,电影制作者自身就不求甚解,甚至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些文化资源真正的内涵价值。电影在消费传统文化资源时,创作者应当对传统文化予以充分的认知与尊重。电影将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吸引受众、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途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无节制地滥用,仅仅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吸引受众的有效传播手段,而丝毫没有在故事构思、形象表现上做出了解传统文化的努力,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其文化精神的剥离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仅仅被作为娱乐化、消费化的对象,这既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消耗、对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解构毁坏,也是电影行业涸泽而渔的短视行径,在不断地打着传统文化情怀的幌子吸引受众观影赚取利益之后,过度的消费将引起受众的情怀疲劳,伤害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包括电影本身的发展。
三、文化理性与个体价值认知的叙事错位
理性是人类特有的高级思维能力,人类借助理性的思维,才能够既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也不凭感性冲动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判断、分析、综合、推理等方式理智客观地分析事物,调整自己的认知,确定行为规范;与理性相对的是反理性,反理性主张个人意志的自由,反对道德规范等对人类的约束,认同个人凭借感觉选择行为方向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的传承,经过不同时代主流思想的改造扬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无论儒家对君子修身、齐家、济世的行为规范,还是佛家的“普度众生”、道家的“道法自然”,强调的都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个人的需求欲望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特别是儒释文化,认为个体应当以群体利益为重,应当为了群体、他人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儒家的“舍生取义”、佛家的“以身饲虎”所表达的都是这种理念,凡是不符合这种文化规范的行为都被剔除在理法之外。而一些如“尊贤而容众,嘉善而不能”(《论语•子张》)这样关注个体价值、容许生命千姿百态的传统元典精神被逐渐边缘化,逐渐流落于乡野之中,成为世俗化的民间认知。随着新时期国门的打开,各种文化思潮蜂拥而至,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理性主义的解构,使中国人接触到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迥异的新的文化观念,意识到追求个体利益、个人幸福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在反拨传统文化轻视个体利益的极端认知的同时,一些人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趋于对个体价值的无限认同,忽略了人作为社会群体、宇宙自然中的一员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创作角度而言,艺术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多元化价值选择,不同的文本伦理预设会涉及不同的文本主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叙事,由此会走向不同的价值体系,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不再单一狭隘,能够在一定的范围里对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观念予以理解。“小说之所以为小说,不在于它有能力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小说家流连和着墨。对于小说而言,它要探究和追问的是存在之谜,是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的难题。它所表现的,是永远存在着争议、处于两难境遇的生活。”4这种艺术创作理念正是保持艺术千姿百态、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也是能够吸引众多受众流连于艺术中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创作理念在创作动画电影时应当慎之又慎,作为主要以未成年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的故事叙述应当注意相对单纯的正向的价值观呈现。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我意识的成熟往往标志着个性的基本形成,儿童阶段是确立社会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儿童个体会显著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5在观看动画电影时,动画形象的生动别致、情节叙事的超越现实性,会使儿童沉浸在娱乐的愉悦感当中,而电影中最容易唤起儿童情感认同的,必然是电影创作者浓墨重彩烘托出的主人公,作为电影叙事的中心人物,主人公处于情感组织的核心地位,整部电影的叙事,观众都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去观察、体验、理解,因此,电影中的主人公处于叙事伦理合法化的优势地位。在这种虚构的叙事情境中,儿童会更深地融入银幕的镜像当中,不由自主地与电影中的主人公一起欢乐和悲伤,主人公在不同情境中应对困境的行为方式、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会被儿童不由自主地认同、模仿,内化为自我意识。
如果从相同的事件的不同角度来审视人们的行为观念,与事件有关的不同个体基于自己的角度,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观念赋予必然的合理化解释,然而站在更多个体生存的角度,有些行为的实施就不再具有合法合理性。在个体价值与社会群体价值发生冲突时,从个人角度来看,服从社会群体规范必然会损及个体利益,社会群体价值规范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是不合理甚至是反人性的。但人类的生存是基于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独立生存,在个体的自由意志与行为方式严重危害群体利益时,个体意志与行为必然会受到群体规则的限制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在遭遇群体生存危机时,应当忽略个体利益,甚至褒扬献出个体生命的行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这种基于群体生存的角度对个体意志与行为的约束就是文化理性。文化理性要求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基于一种“共情”的心态约束自己的行为,限制个体在追求个体价值时危害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利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西方社会的“公民意识”,都是为了能够实现人类群体生存延续而形成的“共情”的伦理规范。当前的一些中国动画电影,过于强调人物的个体价值,对电影中不顾社会规则的感性行为赋予合法性叙述,从叙事学角度看,电影的主人公处于故事中的主体地位,作为事件的发言者,具有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合理化改造的先天优势:基于个体角度而言,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那么事件性质就无所谓对错了,遵从自己的感性意识就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跳出这个极端个人化的叙述角度,理性地运用客观视角就会很轻易地发现,无论个人出发点如何无私、充满善意,如果这种行为可预见性地危及社会群体的生存,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反道德伦理的。叙事学家托多洛夫所说:“二百年以来,浪漫派以及他们不可胜数的继承者都争先恐后地重复说:文学就是在自身找到目的的语言。现在是回到(重新回到)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忘记的明显事实上的时候了,文学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话语。”6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正是因为人类具有限制感性冲动的高度理性,理性能够让个体充分意识到个人生存与群体利益息息相关,能够在感性冲动之时预见到个体行为对群体生存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人情或者伦理,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究竟;然而,正是这些‘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共同制造了一个旷世悲剧。”7而当前的一些影视剧,却在不断地强化这种“通常之人情”的“无罪之罪”,用极端强调个体价值的叙事,讴歌以爱的名义毁灭社会、践踏他人利益的合理合法性。这种以权威者叙事的方式讲述的违背社会伦理的故事,对处于心理尚未发展成熟的儿童而言,他们没有足够的阅历理解人类生存的多元化价值选择,更多地是在权威叙事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接受。在儿童确立社会自我意识这个最重要的时期,培养儿童的“共情”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儿童学会换位思考,能够恰当地抑制个人的欲望,学会在群体利益和个体价值发生冲突时理性地判断分析,理解为了整体社会的良性发展,有时会损失个体利益的必要性。这一点,无论是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天空之城》,还是好莱坞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疯狂动物城》,中国动画《大圣归来》《妈妈咪鸭》都反复呈现了这种观念,电影中的主人公在不断克服外部的困难的同时,也跳出了狭隘的个体局限,获得心灵的成长,这种心灵的成长恰恰与儿童社会自我意识的逐渐形成相契合。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社会现实,我们尊重个人价值多元的选择权利,但价值体系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对群体利益的蔑视和个体价值的无限膨胀。因此,在动画电影的叙事中,要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的非成年特征,故事的叙事伦理应当保持充分的文化理性,而不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进行极端的叙事。结语从动画电影的接受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以儿童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的叙事伦理是创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颠覆、解构、重构是推进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的重要理念,但这种探索在以未成年人为主的电影类型中应当慎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传媒方式,必然承载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功能,电影发掘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汲取现念的侧重点的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的文化身份的定位,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认知、处理问题的方式。动画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既是电影为了经济利益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也是传统文化借用电影传三四线城市观众的观影需求变得不仅可见,而且清晰了。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最终的受益者,市场和观众通过这种视角的挪移,或可实现互利共赢的理想局面。
结语
可以说,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差异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据主流。只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阶级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依然存在,这种现状就不会消失。电影文化消费作为上层建筑时刻受到国家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的影响和制约。未来,待到中国发展成为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市场的层级城市格局将有望被打破和重构,中国影市将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到那时,这种空间地理差异亦会在共性和个性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并实现常态化。综上所述,城市等级划分与中国电影市场可谓是息息相关,线性城市在将来可以算作一个重要的区域性视角来作为考察的对象。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对产业和消费的研究迫切需要更加深入的细化手段。线性城市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新现象、新问题给出一种合理的阐释,提供一种新颖的角度,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如今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市场。
作者:徐燕 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