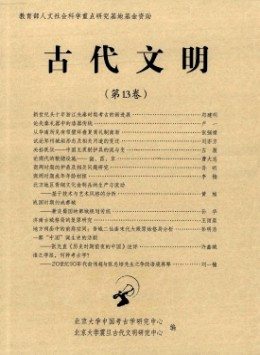古代文学研究价值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代文学研究价值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一、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的中庸
古代文学研究说到底是文本的研究,而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内容意义和形式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以诗、词为最根本阵地的古代文学,其研究更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形式结构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用以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手段的总和。内容意义是作品中所描写的渗透了作家思想情感的社会生活。形式与内容之间体现出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内容,形式无法存在,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法闪现,二者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作为文学研究,尤其是在以含蓄蕴籍著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更是应该掌握好二者的平衡,既要析出其在布局谋篇中的妙处,又不穿凿、拆散“七宝楼台”;既要解悟作品真正的思想价值、审美意义、哲学思考、又不附会诸般“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风貌。举个例子来讲,北宋欧阳修有一首《蝶恋花》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墟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是一首情深意切的闺怨诗,但清代的张惠言却在慎重研究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遽远也。‘楼高不见’,则王又不寐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也。‘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①全词被整体肢解,形式之美荡然无存;附上“微言大义”,又失却词中原原有的闺思闺怨的情肠。现今的诗词研究者也常会做类似的事情,或是一首诗词只剩下起承转合、伏应断续,或是要从一首小小的诗词中“挖掘”出“深刻的哲学思想”、“重大的历史意义”。应该说这样的研究都是有失偏颇的,是对古代文学研究价值的破坏,对读者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阻碍。对古代文学作品形式结构和内容意义的研究,可以有所侧重,也可以作一定的扩展和深挖,但前提必须是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出结论时更应严守中庸。
二、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的中庸
佛马克、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文中,将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研究概念又细致分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两个侧面。前者是一种解释,有客观的操作性,后者是一种阐释,强调主观的参与和制造,强调前见的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也就提出了文本研究中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的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处理好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的关系尤为重要。由于时间的久远和流传中传抄、印刷及时代更迭时的校正等原因,古代文学作品文本的客观性时常会受到质疑,需要研究者的考订。但应当意识到,古代文学研究是为了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并利于它的传播,以便对现代的读者和作家的鉴赏与写作提供指导。这就提醒古代文学的研究者,要把握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的“度”。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客观应更多关注对文本本身的考察,对能够帮助理解作品的作品的生成情况、作家的生平活动、思想状况的一定程度的研究是可行。如对王之涣《出塞》一诗中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远上白云间”,《红楼梦》中黛玉吟诵的是“冷月葬花魂”还是“冷月葬诗魂”等的争论直接关系到研究价值的立足点,无疑是必要的。但绝不能钻牛角尖,像“红学”研究中,对曹雪芹籍贯的考证,今天一块碑,明天一个家谱,然后再大张旗鼓地争论、打擂,除了成就几位“专家”和专家所谓的“事业”,对《红楼梦》研究本身几乎没有价值,甚至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还有的研究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主观,像出于个人的偏见偏好对作品价值的抬高或贬低,自以为是脱离作品实际的“×××的真故事”之类都无益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应该把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统一起来,“中庸”中追求对作品深刻、独到又有价值的见解和认识。
三、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中庸
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在古代社会出现并流传,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旧传播并备受关注的古代文学作品。古代与现代,虽不是完全对立的,但必须承认,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社会的状况、思想意识还是读者的范围、接受标准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文学研究中就出现了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矛盾。如果单纯考察古代文学作品的历史情况,分析作品在其产生时的思想和艺术,就会与现代的读者阅读产生比较大的距离,无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如果一味地用现代的分析方法和视角观点来关照古代文学作品,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却古代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趣味,同时会最终造成读者的厌弃。比如,以下这样的研究就会破坏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三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的是商人蒋兴哥与其妻王三巧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但蒋兴哥出外从商时,三巧奈不住寂寞被人引诱与另一个商人陈大郎通奸的复杂的爱情故事。在对这一篇作品的研究中,学术界出现了若干种区别很大的观点,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文学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关系的界定。美国学者夏至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一书中,称这篇小说是“明代最伟大的作品”,“是一出在道德上与心理上几乎完全协调的人间戏剧”,写的是“商人阶级中三个普通又体面的青年人,他们会爱并且忠实于爱”,“三巧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情人正是她对丈夫的爱和思恋”,“爱既是情感的也是肉体的,具有双重意义,正是这种爱,纯洁了她的意识,以至于与处同样情境的西方女性相比,她的彻底摆脱忧虑的坦然,道德上令人清爽……”②而徐朔方先生《论“三言”》一篇中,则认为,作品强调“少男少女,情色相当”,三巧与陈商之间的所谓爱情,只是“情色之娱”,不配作为爱情看待。这篇小说不是对礼教的否定,而是对爱情的否定。③前者的观点是以现代的角度在考察作品,体现的是当代人对人性的认识,后者则立足于作品当时的道德和思想基础,没有现代接受的参与。两者都失于偏颇,没有能够体现出一篇有着产生于古代而流传于现代的双重性质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应当把握好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中庸,做到既有历史又有现实,掌握好历史与现实的交流与对话。在现实对过去无止境的接受中,既体现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的价值取向,又以当代的标准发掘过去文学的意义。
四、作家与读者的中庸
任何信息的传播都是发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作为文学,它的发送者是作家,媒介者是作品,读者是接受者。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决定于创作意图与接受意识的统一。而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同样决定于其对作家和读者的解读是否是创作意图与接受意识的统一,是否能够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其能够更好地沟通。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这种沟通尤为重要。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能够立足于作家当时的创作背景,从作家角度正确解读其在作品中蕴含和宣扬的意识,而后要关注作品在长时间的流传中意义与价值的转换,然后立足现代体会新的阅读角度、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产生的阅读期待,最终找到古代的作家、古今并存的作品与现代的读者之间的中介点。明确作家与读者因古今时代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差异,以及其间由于共同关注一部作品带来的联系,从而更好地发掘或引导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能使作家的创作意图被充分地理解。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古代文学研究者就应该有既客观又主观的身份定位,在作家与读者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也就是严守中庸。否则,就与一般的读者无异,无法完成作为研究者应该完成的任务。几乎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研究着。尤其是那些优秀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留存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在其流传过程中每时每刻都被研究着。这种研究对作品和作家来讲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是对作家劳动和作品价值的肯定,但对于现代的研究者来说,却实在不算一件好事,再深刻、再宏篇巨制的作品也经不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反复咀嚼。要想不乏味,要想出新,似乎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在某一立场上,钻研到极致。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终极性研究恰恰是一条死胡同,堵住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之路。因为这种方式无疑是为文学研究而研究,在结合作品分析的同时,反而把结论与作品推得更远,实质上与作品本身是完全间离的,也就失去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应当发挥的作用。只有在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作家与读者及其他许许多多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矛盾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严守中庸的研究者,才能够得到真正符合作品实际、作家实际、时代实际和读者实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