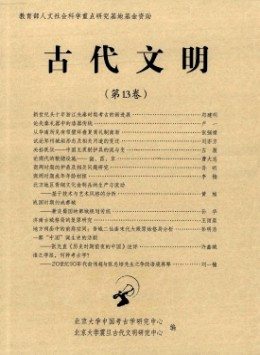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