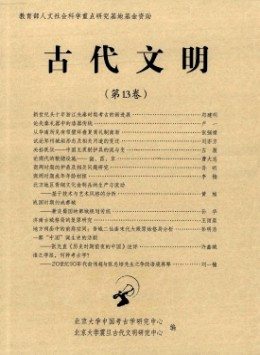古代文学知识转变途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代文学知识转变途径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能否享受文学生活是衡量人生活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小到个人,大到民族,都是如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懂得享受文学生活的民族,文学承载着民族文化,传达着民族的心声,是国人的精神家园,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为建设好这个家园出力。这一道理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懂。但是如何出力,很多人可能没有思考过。我想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人提供新鲜而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用理工科学者的话就是“注意知识的转化”。知识是生活前提,没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就没有某一方面的生活。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人致力于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教科书上的知识。结果是,古代文学研究日新月异,进入教育系统和公众传播系统的古代文学知识却陈陈相因,甚至存在许多不准确之处。首先说不新鲜。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特殊意识形态作用下,古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阐释模式,以人民性为内容标准,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艺术标准来评价所有的作家作品。“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成了不可移易的经典描述。那个时代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种特殊的阐释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已被彻底抛弃,但是在众多中小学教科书中(包括部分大学教科书中),在中国中小学教师的传授中,李白仍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仍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次说不确切。笔者几年前偶尔翻女儿新发的初中语文课本,是苏教版的(很权威的版本),课文选有柳宗元的《黔之驴》,心里很高兴。
我在1984年考研时就是靠这篇初中时背的课文而答上“默写唐宋八大家一篇古文”一道大题的。可再看一下课文所归入单元,就高兴不起来了。单元名称竟然是“动物世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语文读本3》对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赴河陇》、《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作背景交代是“:唐代开国以后,西域边关战事不断……”这一描述对第二首诗比较合适,对第一首就不是那么合适了。“河陇”虽然在西部,但毕竟不能和“西域”混为一谈。再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语文3》中对“秋兴”的解释:“就是借秋天的景色感物抒怀之意。”解释未必错,但很不贴切。“秋兴”是因秋景引发的诗思,强调秋景的兴发感动,而非先有诗兴再借秋景以抒怀。造成上述知识陈旧和错误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很少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现有的编写者多是学习现代汉语的、现当代文学的和语文教学法的。由于知识结构所限,或是没有能力到众多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中找寻新知,或是不愿去寻找新知,有的甚至对教材中选不选古文都产生了质疑。一位曾主持中学教材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就公开表示没有必要把古文选入中学课本。理由是课本使用者是现代人,用的是白话文,何必要学古文?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心编写的,由开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读本》,共有六本,就一篇古文也没选。细碎的学科设置造成学者通识贫乏固然是形成上述局面的一个原因,但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知识普及和转化方面意识不强,努力不够,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非常重视创造新知,却不太重视将新知转化为常识。而常识作用是巨大的,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大多数人对众多领域的了解仅限于常识。
如果你和一个不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讲:宋以后也有好诗,甚至不比唐诗差,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其实费多少口舌,讲多少道理,都不如编一本《宋诗三百首》,或《元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如果选出来的诗真比《唐诗三百首》中的作品好,甚至超过那三百多篇唐诗,就会大大改变人们对这些朝代诗歌的印象。在很多人那里,五万首唐诗就是三百首唐诗,二十五万首宋诗就是三百首宋诗。文学史从来都是选家的文学史。但近些年来学者很少把精力花在选注选讲上。人们完全可以再选出一本与《唐诗三百首》不重复的水平丝毫不降低的《新编唐诗三百首》,但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大众了解唐诗还在使用清人的选本。既然大众所需古代文学知识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知识选择好,更新好,传播好,就十分重要了。当你知道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生都需要了解这些知识时,当你知道需要这些知识的读者数以亿计时,难道你还能说这是不值得花费精力的小事吗?广大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发起一个“重读名篇,清理常识”活动,以几十年研究古代文学积攒起来的功力,把常见的名作重新读过,把积非成是的说法翻过来,把最新获得的知识加进来,把精彩动人的地方讲出来。常见的东西不见得没有问题。刘禹锡《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是否表现男女调情的欢歌?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否表现了一个女子苦闷的情思?李商隐《登乐游原》是否在感叹唐帝国将要灭亡?都有问题。刘禹锡善唱《竹枝词》,白居易《忆梦得》诗题下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欢快的情歌如何能唱入令人愁绝的曲调?“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定是在使用南朝乐府的双关手法吗?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明明是写一个新嫁娘晨起刻意打扮,怎么就成了表现闺中女子的愁绪呢?更何况这首词是被人以“中吕宫”的欢快曲调演唱的。李商隐《登乐游原》写诗人因心绪不佳而登乐游原,登上后欣赏夕阳美景留恋不舍,怎么就成了感叹唐帝国将要灭亡呢?要注意把那些得到学人公认的成果转化成知识。例如关于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就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韦应物家族墓志的发现,我们就知道了韦应物的字是什么了。类似这样,孟浩然的字是什么?《菩萨蛮》是不是李白所作?学术界都有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应该成为可以传播的常识。要注意把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经验传达出来,以提高民族的语文能力。例如发掘唐人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写景,如何抒情,如何叙事,如何议论,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如何使学生学会读诗,把诗歌的好处读出来,进而能以恰当的语言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如何使唐诗的名言警句成为今天生活的话语,为我们今天人们的生活增加艺术的品味等等,都是需要学人花大力气琢磨的。由于考试的需要,中小学语文教材和教参的编写者一贯的想法是力图使语文变成一门他们所认为的科学,要在具有高度个性化和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类似于数学公式的东西来,结果眼睛只盯在字、词、句、篇(主要是层次结构)上,至于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审美韵味则说不好,也压根儿不想说。完整的艺术品被拆碎得不成片段,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变成了兴味索然的东西。
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教会人们应该如何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研究者要积极宣传新的知识,自觉维护已有的常识,积极参与到各层次的教材和普及读物的编写当中,通过各种手段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施加影响。例如袁行霈主编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里的古文选取眼光就明显高于以往同类教材。《文学遗产》应该开辟专栏,发动学者监督大中小学教材中古代文学知识的使用情况,发挥权威刊物的批评和引导作用。批评可以避免知识上以讹传讹,引导可以使师生在教和学中有所归依。古代文学研究者要进一步改进古代文学知识的宣讲方式。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很吸引人,但讲古代文学时多爱讲故事,成了另一种“说书”,没有达到宣讲的最高境界。宗教界人士特别注意宣讲,历史上曾留下“石点头”、“天花乱坠”的故事。星云大师一场演讲下来,很多人立刻跟着出家。这种能触动人心的宣讲经验值得借鉴。应该把众多优秀作家作品的真精神讲出来,讲得令人心驰神往。古代文学研究界应该出现一批这样的宣讲家。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