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与狂飙突进运动异同探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典主义与狂飙突进运动异同探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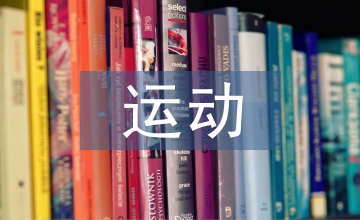
【摘要】西方戏剧经历两千余年的发展,因古希腊戏剧的繁荣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等戏剧理论的创立而拥有了耀人的光辉,相比之下,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作与十八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则难以与前者相提并论。不过,在这一时期涌现出高乃依、席勒等天才戏剧家,他们具有追求“情感”“道德”“美”的自然本性。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对爱情进行了一次残酷的试验:人们究竟能让爱情走得多远,它此刻会陷入何种内在的矛盾。它不仅受到来自外部的抵抗和威胁,同时受到自身的局限。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熙德》相比,其中包裹着“责任与爱情”,父辈的仇恨施于子女,一方面是高尚而严厉的责任,一方面是可爱而专横的爱情。它散播着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追求个人主义思想的种子,更多了一份“理性与关怀”。本文将从悲剧与思想性、悲剧与怜悯感、悲剧与宿命论、悲剧与道德观四个方面来分析高乃依的代表作《熙德》和席勒代表作《阴谋与爱情》,浅析法国古典主义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之异同。
【关键词】席勒;《阴谋与爱情》;高乃依;《熙德》;法国古典主义;德国狂飙突进运动
一、悲剧与思想性
受古典主义悲剧思想的影响,高乃依的作品多取材于古代有名的历史或者古希腊、古罗马神话。高乃依曾在《论诗体剧》中提到:悲剧“要以有名的、不同寻常的、严肃的情节作为题材。”这三个要素也表明了其创作的原则,而《熙德》则取材于西班牙历史。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从莱辛的《爱米丽雅·伽洛蒂》中获得了启发,但他创作了某种独特的东西,贵族青年斐迪南与平民少女露易丝的爱情悲剧是具有市民性的、充斥着阶级对立的爱情悲剧。《阴谋与爱情》中没有一个人物是自由和独立的。“这个世界就像一架社会机器,狂热和意向犹如小小的轮子,驱动一个社会的命运程序。”席勒把一个社会的进程搬上舞台,在这个进程中没有舵手只有参与者,没有人能够把握全局。这两部作品的主题思想都在讲爱情结局之悲、父权的影响,与《熙德》不同的是,席勒笔下的青年敢于反抗父权,对爱情怀有渴望与犹疑。同时二者的命运观又有大体相像的地方,都表现了主人公的责任和个人情感的冲突,罗狄克对施曼娜的爱情是矢志不渝的;斐迪南在面对阶级的对立和所谓“门不当户不对”的境况下依然不妥协、不屈服。但两者的结局是不同的:斐迪南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毒死”了心爱的女人露易丝。罗狄克却在国家利益、家族荣誉与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能用理性抑制感性从而获得美满的结局。
二、悲剧与怜悯感
《熙德》和《阴谋与爱情》当中悲剧主角的处境都很相似。乐师米勒一家与宰相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颇像唐·狄哀格和唐·高迈斯之间的争吵;罗狄克像斐迪南一样对爱情忠贞,露易丝则像为了爱情和责任甘愿突破藩篱的施曼娜。两者的差别在于《阴谋与爱情》更能让人产生“怜悯感”。读者在面对露易丝与斐迪南死亡时会产生怜悯情绪,伴随而来的是恐惧感。《熙德》的结尾是和解,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在大致都相同的情形下,不幸的结尾的确能够增强悲剧感。这也是《熙德》作为悲剧的缺陷,这样的幸福结尾好比暴风雨过后透过乌云的一道阳光。观赏悲剧不能没有怜悯。高乃依认为仅有怜悯足以产生悲剧效果,但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作为一种审美同情的怜悯,如果把它孤立起来看,不如斯宾塞认为的“力量的节省”更有道理。舞蹈家在动作轻盈、洒脱自如的时候显得更为柔美,因而我们看到《阴谋与爱情》中露易丝作为女性的柔美似乎更能激起我们的爱怜,《熙德》中的施曼娜刚毅硬派的性格很难让观众产生“共情”。也正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崇高会激起两种不同的感情,首先是恐惧,然后是惊奇。高乃依认为在怜悯和恐惧之外应该加上赞美,也许是正确的。”
三、悲剧与宿命论
命运观念对悲剧的创作和欣赏都很重要。不过,大多数西方学者习惯于将宿命论归为东方的人生观,例如,坎布兰在《论希腊戏剧的命运观念》中,对一般人认为的命运观念在希腊悲剧中最为突出的这种看法进行了强烈的反驳。文中指出:埃斯库罗斯及其杰出的后继者们不是把命运,而是把正义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他判断宿命论在本质上是东方人的观念,欧洲人是不会受到宿命论观念的感染的。狄克逊在《论悲剧》中也指出“东方是疲弱的、活力困乏的失败主义者,不可能产生悲剧。”但如果我们把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和北欧神话的基本精神拿来和中国戏曲、印度梵剧相比较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两位学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昆曲《张协状元》里贫女与张协就像是被宿命安排的“冤家”,张协剑劈贫女后将其残忍抛弃,但因命运的安排,贫女与张协再次相见,最终言归于好;在某种意义上,《熙德》何尝不是通过宿命的安排使男女相爱相杀后而破镜重圆呢?往往宿命论具有共通性,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悲剧或喜剧都以某种相似的形式重演着。宿命论与悲剧感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原始人类对恶的根源的最初解释。追求幸福的自然欲望使人相信,人生来就是为了获得幸福。当不幸的事件接连发生,人的自然欲望就会受阻,当找不到合理解释时,人们大多会滞留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答案,但困惑会导致人们讲不清楚究竟是谁在看似合理的道德秩序世界里“作怪”。《阴谋与爱情》从开始就编织出一张大网,平民乐师米勒坚决反对女儿露易丝与贵族斐迪南来往;身为贵族的斐迪南则被宰相父亲当作政治工具,他被要求与同等身份的公爵情妇完婚。这其中应当注意:除了传统的门第观念之外还存在着对于宿命的妥协和无奈。米勒深知自己的女儿露易丝与斐迪南之间隔着一道结界,露易丝在即将死亡时向斐迪南讲出了真相,她渴望斐迪南看到自己的真实与善良。在斐迪南倒在父亲瓦尔特身旁时,他依然将自己的手伸向父亲,带着善良与憎恨。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缺少了信仰,他们的价值尺度是不同的;贵族信仰权力,平民渴望幸福。虽说悲剧也和宗教、哲学一样,试图解决善与恶这个根本问题,但悲剧的精神与宗教和哲学又是格格不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满足于宗教或哲学时,对悲剧的需要就会消失。信仰消解了人们对于宿命论的恐惧,剧中每个角色都追寻着属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可以理解为“美”。“美”是单纯的,是被渴望的,是被破坏的。正如尼采所说:“受难者最深切地感到对美的渴求,他产生美。”一个人可以相信命运的存在,但在感情上可以完全漠然置之。一方面,宿命论不是信条更不是哲学;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宗教,它深深感到宇宙间有些东西既不能用理智去说明,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的证明。然而,也正是这些“原材料”给予戏剧家们创作的灵魂,也正是这些东西使悲剧诗人感到敬畏和惊奇。
四、悲剧与道德观
对于中国人来说,强烈的道德感代替了对于宗教的狂热。中国人认为,人必须自己救自己,不能依靠鬼神。《赵氏孤儿》里将孤儿养育成人,为其父母报仇,才是上策。孤儿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他的敌人杀害了他的亲属,窃夺了本来属于他的荣誉,他必须复仇。剧作者是要传达一个道德的教训——忠诚与正义。《熙德》中罗狄克受制于父命,他的道德感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罗狄克深爱着施曼娜,他无法违背父亲的命令,杀死了施曼娜的父亲。施曼娜因为强烈的道德感而无法与罗狄克继续相爱,甚至对他产生仇恨,要求侍卫与罗狄克决斗,但因罗狄克在战场上屡次获得战功,结尾国王又再次“授予”施曼娜道德感,让二人再次结合。整个剧情的推进通过“赋予道德感”到“剥夺道德感”再到“授予道德感”将剧情向前推进。《阴谋与爱情》中的斐迪南虽敢于反抗父权但因为自身的矛盾性和敏感多疑为之后的被阴谋所骗埋下了隐患,他的道德感随着剧情的发展是逐渐被压制的。通过对悲剧《阴谋与爱情》的理解,在面对贵族霸权与个人私情时,道德观在结尾得到了纾解,它审判了权贵,彰显出崇高道德感,让人们意识到,这是道德法则的胜利。在生命屈从于道德这一悲剧艺术的要求下,露易丝直到临死之前都还展现着自我牺牲与宽宥他人的道德感:“可怕的误解啊——斐迪南——他们逼迫着我——请原谅——你的露易丝宁肯死去啊!——可是我的父亲——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搞的阴谋诡计。救世主临终时会宽恕一切人——愿你和他也得到宽恕。”道德感通过个人生命的死亡来换得始终,高尚的道德感因牺牲而更有意义。这正如席勒所追求的,读者在悲剧中“体验到道德法则的威力而大获胜利,这给我们的快乐,远远超过自然世界里一切矛盾能使我们痛苦的程度”。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戏剧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但它们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从以上四点浅层的比较可以看出,高乃依的《熙德》和席勒《阴谋与爱情》中悲剧共有的相似性能让观众一见如故,对于这种命运的悲剧颇具亲近,也让读者和观众对两部戏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前者以理性与感情的较量为主题,后者从关注内部精神的角度,展示了席勒自身的美学体系和戏剧作品的良好结合。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究,使之更进一步接近“法国古典主义”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
参考文献:
[1]魏超.共同的爱情悲剧不同的矛盾冲突——〈孔雀东南飞〉与〈阴谋与爱情〉的比较分析[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3,28(06):84-87+92.
[2]金诚诚.浅析新古典主义〈熙德〉悲剧之美[J].戏剧之家,2017,(04):7-8.
[3]席小妮.从〈熙德〉和〈费德尔〉比较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思想[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03):109-111.
[4]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M].卫茂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睢人源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