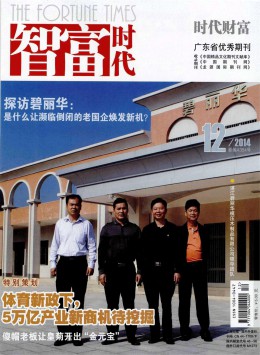智媒时代媒介教育改革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智媒时代媒介教育改革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新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智媒时代的到来,传媒生态的变革给传播学学科学术乃至媒介教育的发展改革带来了新的启示。本文认为媒介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树立媒介生态观念,改革的原动力不仅源于外部环境变化,更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智媒时代的媒介教育改革应当超越经验,既要把握宏观,也需加快研究推进跨域交叉融合的改革思路与策略。
关键词:智媒时代;媒介生态;媒介教育;超越经验
一、改革的前提条件:增强教育观念中的媒介生态意识
媒介教育改革的前提是在媒介教育中培养出一种深刻的媒介生态意识,但目前而言,无论是在传播学学科建设中,还是在媒介教育改革的理念中,此类观点仍未受到普遍重视。“生态”的概念由来已久,并且媒介环境的研究视角也早已存在于传播学研究视野中。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1866年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起初其研究对象主要在生物领域,后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有了“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联”[1]的研究转向。在媒介研究领域,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了与生态相关的概念“媒介环境”。1968年,尼尔•波兹曼认为要“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2]之后,环境研究就正式成为媒介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生态学并没有把传播媒介仅看作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手段或工具,相反,它认为即便是从客观上,传播媒介也扮演了解释和塑造者的角色。任何媒介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或系统,而这种结构或系统通常是由符号按照一定规则和秩序组建起来的。我们在通过一种媒介进行传播与表达时,就必然要遵循其既定规则秩序所带来的内部逻辑与传播偏向,而媒介特征内在偏向引发的对媒介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要素间因果关系的探究,便成为了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关注的重点,“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3]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媒介技术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近年来,网络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贡献明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被放在“互联网+”环境中加以培育。高速率、延时低、大容量、高效率的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机器语言规则秩序主导的媒介生态变革中,不仅给媒介带来了巨大变革,为全社会发展的天平增添了技术砝码,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关注环境中的技术,使关于媒介技术的许多学术研究探讨重新繁荣起来。在媒介生态视域下,如何理解媒介与技术的基本内涵,关乎媒介教育观念中的生态意识水平。这种观念告诉我们,媒介已在社会中变成像空气和水一样普遍存在的自然元素,我们对媒介的考察其实更多是在考察环境对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且,在生态观念中,主体性从人转向了自然,对于这种转变,学者彼得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偏离人类的尺度……自然主义能给我们人文主义已经做过的一切,也能让我们在运行有序的万事万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又不会让我们充满傲慢和自满”。[4]对技术的讨论则是将其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或手段,人类无法避免受到其影响,想要摆脱技术的束缚显然毫无意义。因此,“专业主义”等原始纯洁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问题,面对技术我们根本毫无选择,而且“免于被技术控制的承诺通常只是另一种尚未被认可的技术而已”。[5]
二、关于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在传媒教育改革的趋势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改革的必然性,以证明其必然性不仅来源于外部条件,还有其自身的探索与追求。
(一)重新思考媒介教育改革的合法性从“绿眼罩人”和“卡方人”的争论开始直至今日,传播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社会科学方向就一直从未改变。1955—1956年,施拉姆在斯坦福建立传播研究院时就将传播学定位为“针对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而且研究方法也完全是实证主义取向的。[6]这无疑为后续社会科学方向在传媒教育中被逐渐固定下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这种依据可能是靠不住的。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传播学学科边界被不断延展,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愈发复杂。如果在新的传媒生态下,依然固守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对涉及其他学科内容的相关问题视而不见,显然不是一种合适的态度。另一方面,在未明确传播学学术核心问题的情况下,预设一个发展方向的做法本身也值得怀疑。学者彼得斯在分析该问题时就认为“传播学研究一直受到社会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的驱动”,[6]况且早期的学科设立可能急切于向世人证明其合法性,“为了争夺学科地盘,学术性和理论严谨性”可能因“主观随意、相机而动的行政行为”而受到损失。因此,认识到“传播学学术体制建设的封闭性”与“传播学学术研究范围的广阔性”两者之间的冲突,重新思考传播学学术研究范围,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媒介教育进行改革,既是媒介生态变革的客观结果,也是传播学学术传统发展的自身追求。
(二)媒介教育改革应超越经验既然无法通过自身经验摆脱媒介技术的影响,那么就必须采取一种超越经验的方式重新审视我们周围的“自然”。显然,通过一种新技术来限制旧技术,就必然会被新技术影响。传媒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当使对教育改革的思考深入到超越经验的程度。媒介教育改革首先可能着眼于对学科基础框架的重构,意在摆脱学科建设社科为主的局限性。学者喻国明认为,5G技术的特点会使传播中“媒介”“传播者”“内容”与“受众”4个基本要素发生变革,而学科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实践相统一,主动将传播学的基本学术架构建成一个“人机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符号传播学、电信传播学”自上而下的模型,并希望能使传播学学科边界清晰起来。[5]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弥补学科建设存在的不足,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主观预设、各自为政的尴尬,也实现明晰边界的初衷。因此,我们仍需破除成见,如学者彼得斯从根本上将传播作为领域而非学科,把媒介看作是“必需品、环境和各种数据处理器,是一种处于其他要素中间的元素”,那时“研究者将不再强调人文与科学领域间的边界,并采用任何有益的形式探寻知识”。换句话说,当媒介成为必要的环境元素,边界被环境替代,对媒介问题的探索自然也就消除了学科的界限,学科的基础框架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重构和发展。但坚持人文传统并不代表放弃涉及其他学科范围内的知识。纯粹性超越经验演绎推理式的学术和教育,其结果可能是缺乏实质性内容。因此,对传媒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而言,在继续坚守人文主义传统视野的基础上,既要把握宏观视角,也要努力推进跨域交叉融合的教改思路。
三、结语
智媒时代的媒介教育改革,相比在课程内容与学科边界上的拓展,更需要有人文主义媒介哲学的视野,对改革有更全面、历史和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汉斯•萨克塞(德).生态哲学[M].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3.
[2]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J].中国传媒报告,2003,2(2):4-16.
[3]哈罗德•伊尼斯(加).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
[5]喻国明,曲慧.边界、要素与结构: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8):62-70+127.
[6]约翰•杜翰姆•彼得斯(美).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3+17.
作者:刘振宇 单位:三亚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