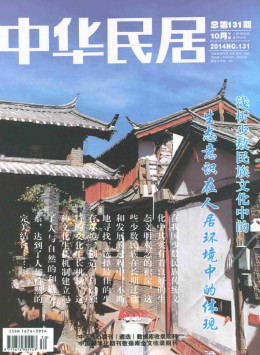民居改建中建筑文化保留状况探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民居改建中建筑文化保留状况探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本文作者:何彪、王伯承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在贵州,民族地区传统民居所用的建筑材料多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泥土、石头、树木、竹子、秸秆等都可以作为建房盖屋的材料。这些建筑材料基本是随处可得,极少耗费能源资源,几乎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例如贵州黔中镇宁、平坝一带的布依族地区盛产优质石料,当地布依族群众因地制宜,以石条或石块砌墙,以石板盖顶,用石料修造出一幢幢颇具民族特色的石板房,冬暖夏凉,防潮防火,美观大方。而且,石料在这些地区是随地可取的材料,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
贵州省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给人一种极强的审美感受。其中尤以“干栏式”建筑的吊脚楼最具特色。贵州山区苗侗人家的吊脚楼大多依山而筑,建在斜坡面上,后部与坡坎相接,前部用木柱架空,像是吊着几根柱子,其造型从纵剖面看,形成了“占天不占地”、“天平地不平”的独特景观,在观察这些吊脚楼的时候,毫无生涩呆滞的痕迹,尤其是在依山傍水的苗寨,那些顺山而建的吊脚楼就像一只只展翅高飞的雄鹰翱翔于苗岭之中,给人一种甜美的享受。
贵州传统民居体现的是农业社会的居住模式,在生产生活资料较为匮乏的情况下,贵州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虽形式多样,但都体现了民居实用性的特点。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的传统民居都为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一般都分两层或三层。底层存放杂物,堆放柴火,存放犁、耙、锄等生产工具,便于存取;中层住人,使人离地而居,既避免了虫蛇猛兽的袭击,又保障了人不受湿气的影响;上层储粮,既可避免粮食受潮,又可随时取用,十分方便。
民居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农村,民居的附属建筑也同时具有生产的功能,譬如饲养家禽、家畜,还有房前屋后空地上开垦出来的菜畦。贵州苗侗人家的吊脚楼建筑或一家一栋、自成一体,或聚族而建———同族的房子连在一起,廊檐相接、互通有无。吊脚楼的主楼一般为三开间,正中一间前有回廊后又偏厦,左右两侧另设厢房。回廊于二层出挑,安装有独特的“S”形曲栏靠椅,苗语叫“嘎息”(ghabxil),民间有一说法叫“美人靠”。这是因为姑娘们常在此挑花刺绣,向外展示风姿而得名。此外“嘎息”还可用作一家人劳累过后休闲小憩,纳凉观景,讲述神话和族群迁徙历史的地方。偏厦多用作厨房或磨房,厢房一般为卧房,或作绣房、织布房、芦笙房等。大多数吊脚楼把在二楼地基外架上的悬空走廊作为进大门的通道。猪、牛圈都在屋侧房后,方便喂养和耕种使用。
信仰、风俗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特质。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不同的信仰和风俗都在传统民居上有所体现。例如贵州的苗族家庭在正对大门堂屋的板壁上安放有祖宗圣灵的神龛。结合苗族吊脚楼的结构,可以看出建筑的空间分割组合是以祖宗圣灵神龛所在的房间为核心,再向外延伸辐射。家庭成员在这样的空间组合下生活,无形中便被祖宗圣灵所在的堂屋的空间引力所凝聚,从而为家庭的团结增强了亲和力,苗族同胞祖先崇拜的信仰在吊脚楼上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来。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使得更多的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类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对自然均衡状态的破坏也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而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建筑,一方面顺应了自然地理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注意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民居与环境的和谐相生。例如贵州的苗族、侗族生活的地方炎热多雨、地面潮湿、瘴气浓重,为适应这种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他们发明构建了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具有通风干燥、安全实用、凉爽舒适的特点。而且苗侗人家的吊脚楼也非常尊重自然,不会盲目地大规模挖山平地建房,根据当地地势、坡度的不同,吊脚楼的形式因地制宜地分为单吊式、双吊式、四合水式、二屋吊式和平地起吊式,顺山就势而建的吊脚楼很好地避免了水土流失并维护了生态平衡。
危房改造中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出现的问题
我国全面启动危房改造试点工作的第二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农房设计建设要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体现民族和地方建筑风格、传承和改进传统建造工法,推进农房建设技术进步。尽管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过程中,思想上很重视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工作,坚持“能避则避、修旧如旧、适度调整”的原则,尽量保护传统民居的风格不受破坏,然而改造实践过程中政府部门过分强调风格一致、整齐划一,加之危房改造开展多服从于行政安排,从而影响了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传承。
过分整齐划一,忽略了传统建筑文化。我们调查中发现,伴随着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逐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实施了许多扶贫开发项目,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居住条件、生计方式等。但是新建的水泥房或式样统一的民居房,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些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反而使民族传统建筑文化遭到破坏。国家危房改造政策下的安居工程,把居住在深山老林中生存条件恶劣的村民们,集体搬迁到新式住宅,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但村民们也被迫改变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民居的彻底更新,依附在民居建筑上的民族生产生活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被忽略或摒弃。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的杨中村,把居住在石山区、交通不便的群众集体搬迁到公路沿线,从外观上看,新式建筑整齐划一、非常美观,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传统的布依族建筑文化却已经不存在。
政府行政命令,忽略了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危房改造不仅仅是一项民生工程,它也体现了政府的经济目标。2008年底,中央出台了《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将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列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点举措;2010年的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贵州省在危房改造中除了解决村民的住房安全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乡村旅游———如农家乐的形式———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危房改造工程改善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拉动了内需,推动了乡村文明建设,但却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1]P171-187。作为危房改造首个试点的贵州省在危房改造的面积上有严格的控制标准,对政府补助的困难户,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40平方米以下,而且,式样统一,建筑材料也基本一样。这种有限的居住空间和统一的模式,使民族传统建筑得不到保护。
民族地区危房改造中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保护难的原因
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民居建筑文化在内的“传统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文化的积累性和变革性,……传统文化是历史沿传下来的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体系中既可以传承,也可以变异”[2]P204。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也已经纳入了全球化的范围。贵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逐渐从小农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苗族传统民居中的“美人靠”和用于置放碓、磨的偏房等已逐渐失去其功能。随着外来文化不断涌向民族地区,各种新鲜事物不断充斥着少数民族群众的眼球,农村民居的建筑样式也在不断更新,新式、美观的建筑样式不断涌现。我们调查发现,在当前的危房改造中,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对传统木质、石质、土质民居的认同度大大减弱,他们几乎都把拥有一套新式的砖混结构住房作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笔者曾到苗区调查,部分苗族群众说:“不能只让我们住木房,你们住砖房!”
搬迁环境的改变。贵州民族地区传统民居的重要特点就是与自身所处的环境相得益彰。脱离原建筑的环境,要保护传统建筑就十分困难了。例如在我们调查的苗侗地区,政府把居住在交通极为不便的高山密林里、生活贫困的少数民族群众集中安置在公路沿线的平地或坝上,传统吊脚楼建筑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建筑条件。
建筑材料的欠缺。近年来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对砍竹伐木进行了严格规定。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许多民族地区已很难建盖传统的全木结构房屋。其次,就算获得了林木的采伐权,也还得交高昂的育林费。再加之木质房屋每隔几年都要整修,所以许多村民认为非常麻烦,纷纷用新型建筑材料对老屋进行改造,并大量吸收外来的新式建筑风格。建筑材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先后经历了天然材料阶段、人工材料阶段、有机材料阶段,直到现在的新型建筑材料阶段。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建筑所依赖的天然建筑材料,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就显得十分困难。
投入经费的不足。虽然国家关于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民居改造要体现民族和地方建筑风格,尽量保护传统民居的风格不受破坏”,但是我国危房面广、数量多,改造资金本已非常紧张,很难再承受保护民族传统民居需要支出的额外费用。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危房改造是用有限的资金,解决最困难农户最基本的居住安全问题,不能搞扩大化,要注意在建设标准上不能走过了头。如果建设标准要求过高、改造费用增加都可能导致农民借债,使贫困农民更加贫困;而民族地区危房改造中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却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需求。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做好资金倾斜与平衡,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传统建筑人才的匮乏———能工巧匠后继无人。贵州民族地区传统建筑之所以能够因地制宜、经济实用,从根本上来讲是源于建筑工匠们精湛的技艺。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苗、侗族的吊脚楼和布依族的石板房等传统民居建筑形态各异,建筑技艺也是各不相同,传统的工匠技师并不靠图纸来完成建筑的每一道工序,他们依靠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熟能生巧。例如吊脚楼的整个构架均以榫穿铆相连,无钉无栓,工匠从构思、设计、建造到完工,对作为建筑材料的数百根梁枋的大小长短和开铆作榫的部位以及复杂的力学估计等数据皆胸有成竹。然而,随着群众对民族传统民居认同的趋弱、甚至淡化,传统工匠早已被新式工匠所代替。伴随着传统民族能工巧匠的老去和离世,传统建筑技艺也在慢慢作古,传统建筑艺师后继无人。
贵州民族地区危房改造中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保护问题的思考
危房改造中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流失。是一种客观事实,保护需量力而行民居建筑是地形、气候、建筑技术、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社会生产力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更新有其自身演变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伴随着危房改造的推进,民居的结构形式和风格取向,自觉不自觉地发生着变异、调整和重构,这是时展下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的嬗变是自然而然的,民居建筑文化不必要进行原原本本的保护,也不可能在危房改造中实现全面有效的保护,传统民居变迁作为一种客观事实,保护需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选择传统民居建筑较有特色的民族村寨,实施重点保护。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仅是传统建筑文化,而且整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异和退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民居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特殊的文化意义。[3]P29如果“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必将很快流失。特别是人口数量在10万以下,甚至1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它们几乎没有能力对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实事求是讲,所有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在危房改造中都要按传统来修建,实行全面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可以选择一批有特色的民族村寨进行重点保护。例如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的郎德苗寨,吊脚楼建筑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配合风雨桥、芦笙场等公共建筑彼此呼应,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民居建筑文化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整个村寨至今古香古色、风韵犹存。
危房改造中可以多途径获得资源支持,扩大保护覆盖面。危房改造中的传统民居建筑保护,单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在危房改造过程中,多途径解决资金、资源问题,在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建筑保护的面上获得突破。针对民族地区危房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民居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可以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首先,可以从制度上保障危改资金来源,例如“创设农村危房改造公积金贷款法律制度是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重要渠道”[4];其次,可以吸收社会福利、慈善资金,例如可以利用福利彩票资金每年拿出一定资金支持困难农民盖房,加大福利彩票资金投入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危房改造的比例等。第三,政府的相关部门落实优惠政策,也可以解决改造户经济困难的问题。在开源的同时,做好节流,各相关部门都应该相互协调从服务民族地区危房改造工作的大局出发,简化项目审批手续,针对危改工程提供各种优惠措施,减免相关行政性、服务性收费。国土部门可以在宅基地的审批上简化手续,同时给予特殊照顾,减免土地占用费;林业部门可以对危房改造林木使用减免育林费;建设部门可以免费提供改造户型的图纸资料;供电部门可以减免电表安装费;金融部门可以负责帮助危改户解决急需的建房资金,加大小额贷款的力度等等。针对危房改造过程中,劳动力难以为继的现象,政府部门可以发动民兵、人民武装部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临时组建危房改造建设兵团,以解决民族地区危房改造和整治工作施工劳动力不足问题。[5]
传统民居建筑适应时展的潮流,双效合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传统民居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生存与发展、解体与重构、衰落与再生等许多矛盾冲突。[6]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应当以实用和民族情感为导向,在保留原有民居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建造出具有现代要素的新型民居。全球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传统文化的自我防卫机制的发挥,使民族传统文化丧失自我保护的机会陡然增多,极易沦为被动的一方。[7]P29面对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少数民族只有在传承自身传统优良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各种先进的外来文化,才能获得立足之地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民族地区很多传统民居建筑的传统技艺、方法已被实践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当前的危房改造工程,并不是彻底推倒重来,当然也绝非传统样式一以贯之。我们要做的是结合现代先进的建筑工艺和传统建筑工艺的精华部分,双效合一,在致力于改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传统民居建筑所孕育的民族传统文化。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