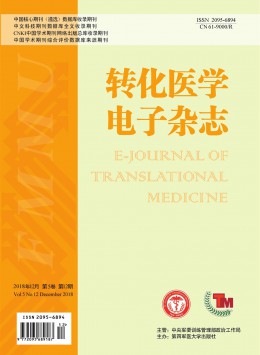转化医学的现况及困难探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转化医学的现况及困难探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纵观国内外的各种基础医学研究,很大一部分在向临床实践进一步转化的过程中,难以将基础研究成果再次重复。因此,基础研究成果缺乏可重复性,是目前转化医学失败的首要原因[3],使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脱节,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难以为临床实践服务。尽管在转化医学实施的过程中有许多经典的案例,但从国内外对疾病诊治的相关转化医学应用效果来看,应用现状仍不容乐观。
1转化医学应用现状
1.1肝细胞癌的转化医学研究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属于较为常见的肿瘤,是恶性度较高的肿瘤之一。据统计,在我国,肝癌是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就全世界而言,则位于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三位[4]。近10年来针对肝癌治疗研究的技术领域不断扩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使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肝癌发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和关键分子方面也取得了较为领先的地位[5-7]。但是,从临床对肝癌诊治的过程中看,肝癌的总体预后依然很差,难以与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相平衡。2004年,Mankoff等[1]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就全世界而言,肝癌的发病率仍持续上升,年发病和死亡人数较10年前明显增加,由10年前年发病56.4万人上升到74.8万人,年死亡人数由54.9万人上升到69.6万人。目前,肝癌的5年生存率仍然不足5%。
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国是肝癌高发国,患者数量占全世界肝癌人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对肝癌诊治的相关研究较为突出,但治疗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仅就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而言,转化医学在此领域进展颇微,虽然相关的基础医学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不断更新,但是在检验基础医学应用效果时,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肝癌的疾病治疗却进展缓慢,肝癌的基础研究没有达到提高肝癌预后生存率的效果。与国外相比,虽然我国的肝癌人数占世界肝癌人数一半还多,但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没能通过转化医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治疗手段,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转化医学的真正意义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2心肌梗死治疗的转化医学研究
目前,对于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治疗经验的总结,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应用,已经通过转化医学实践验证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一般认为放置血管内支架是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国对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使用心脏支架的态势呈现疯长。据统计,心脏支架的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例,但是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仍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一种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要通过预后的效果来判断,即预后的生存时间。冠脉支架和/或搭桥手术,对心肌缺血性心脏病的病死率下降仅为3%~5%。从上述例子可知,我国应用转化医学的近10年间,在心肌梗死治疗领域仍然属于探索阶段,还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虽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心肌梗死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冠脉支架,因为冠脉支架能快速畅通冠脉,但对于一种临床应用技术的判断不能仅看近期的治愈情况,还应该对临床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做客观评判。但是预后却难以令人满意,转化医学的效果也同样难以让人满意,需要临床与基础研究的相关人士共同努力协作发展转化医学,共同寻求最佳的诊治策略[8]。
1.3实验外科应用的转化医学发展
实验外科是外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用实验医学的方法探讨、验证外科领域的未知问题。首先,是通过动物实验来验证手术方法的效果,通过各种实验技术和方法,验证临床诊治应用的合理性等;其次,是外科疾病的病因、诊断、防治与预后等内容,利用循证医学进行判定。
通过上述可知,实验外科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具体说应该是与外科临床医学相联系的重要枢纽,应属转化医学的范畴。在外科临床诊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实验外科的基础医学的相关内容来判断或验证这种问题可解决的办法,进而通过临床实践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诊治。
近30年来,虽然我国的实验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主要表现在[9]:(1)在国际上有标志影响力的先进成果不多;(2)每年在SCI具有影响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真正能将基础研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重复验证的却寥寥无几,多数是为了基础研究而进行基础研究;(3)对疾病进行诊治的临床知名医生很多,但能真正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进而转入实验外科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匮乏;(4)临床外科手术创新不够,高新技术成果及应用较少,多为国外新技术的跟踪引进和重复应用,一些重要的技术和设备仍受制于人,临床研究的创新指数和证据级别也有待提高。比如,外科手术技术最先进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因临床中难以达到精细操作应运而生的,从2000年首次应用,到2010年短短10年的时间,全世界范围内,欧美国家的装机数量迅速增长[10]。截至2010年12月底,全球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装机数量为1753台。其中,美国1285台,占73%以上;欧洲316台,占18%;亚洲及其他地区152台,占8.7%。亚洲国家和地区共有96台,其中,韩国34台;中国大陆10台,仅占0.6%;中国香港6台;中国台湾7台;日本20台;印度7台;其他国家共12台[11]。由此可见,我国外科学的发展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竞争力,因此,作为转化医学范畴的实验外科应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医学科学内部学科间的相互转化,提高我国医疗的整体水平,合理运用转化医学,培养“实验室-临床-实验室”综合型人才,使我国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强国。
1.4转化医学资金投入及其成果发表情况与转化医学初衷相悖
美国国家肿瘤研究院在过去30年间共耗资2000亿美元,用于基础医学的相关研究,最终发现80%的经费涉及小鼠、果蝇与蠕虫等的基础性研究,共发表学术论文约156万篇,但肿瘤死亡率却未见明显改善[12]。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长期以来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人员往往将作为主要的研究成果,只要能在Nature、Science、Cell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视为科研的最高成就。而临床医生则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大多不善于基础性研究,对临床上发生的难题缺乏敏感性,往往习惯于凭经验解决问题;即使在教学医院,临床医生与基础医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也常表现为形式多于实际,缺少有效的沟通与整合,所有这一切都制约了转化医学的发展。对临床工作者而言,实现转化医学的新模式必须改变传统临床科研的思维方法,要以迅速发展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结构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从系统生物学角度,对疾病的本质展开研究,以寻找疾病诊断、分型的新方法,提供疾病治疗新的药物靶点,探索靶向治疗的新手段,这是实现转化医学的关键所在[12]。
2转化医学发展的重点与困境
综上可知,全世界的转化医学发展似乎存在一个瓶颈,虽然在20世纪中叶就提出了转化医学,但真正意义上的转化需要用时间来判定,需要远期的效果观察来最终做出结论。可以认为,转化医学在世界范围内仍处探索阶段,虽然相关的针对临床实践基础医学研究不断更新,但真正意义上能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应用的却微乎其微。与国外相比,我国对转化医学的提出和研究起步较晚,相应的投入和对高精尖技术的关注亦较少,与国外差距较大。而转化医学的重点并非“转化”的本身,其真正意义是通过这种转化的过程,使有意义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真正成为临床医生得心应手的诊治疾病的工具,而且在今后的效果评价中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目前转化医学发展的重点和困境如下。
2.1“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形式多于实际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转化医学实施的困境。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就是诠释从实际出发的最好例子[13]: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胃溃疡是由于长期食用辛辣食物、饮食不规律及工作压力大等原因造成的,而在1982年4月,临床医生Marshall与病理学医生Warren合作从胃黏膜活检样本中成功培养和分离出了幽门螺杆菌,并认为这种细菌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相关。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细菌就是导致胃炎的罪魁祸首,Marshall和另一位合作者Morris不惜喝下含有这种细菌的培养液,结果大病一场。在1984年4月5日,他们将研究成果发表于TheLancet上,在国际消化病学界引起了轰动,通过人体试验、抗生素治疗和流行病学等研究,幽门螺杆菌在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所起的作用逐渐清晰,科学家对该病菌致病机理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于是,世界各大药厂投资开发治疗疾病的药物,并且临床试验成功。这是转化医学实践从临床中来最后应用到临床的典型例子。但是当前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脱节的原因在于大多基础研究者为了基础研究而研究,没有真正到临床中去调研,查看临床医学实际的需要,盲目进行基础实验,最终实验结果难以达到临床实际需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转化医学难以实施。同样,临床医生往往不屑于基础研究,认为治好疾病就是好的临床医生,却没有认识到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达到对疾病诊治的需求。
2.2基础医学研究对象的简单性与临床疾病诊治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基础医学的研究往往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对于研究对象(包括小鼠,细胞等)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培养,也就是追求一种简单性、效率性和因果性。因此,无论实验的方法和技术如何,这对事先已经预定结果的实验而言,往往能获得成功。但是,基础研究的目的是要转化为医学实践所用,而医学面对的是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富有感情色彩的人,因此,在把基础医学实验结果放到临床进行验证时,很难达到可重复性[3]。也就是说,基础研究产生的结果,是基于事先预定好的实验对象进行实验而得出的,而要将这种方法转化为临床应用,要面对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性别等的复杂人体,需要多次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因此,二者研究对象的矛盾,注定加剧了转化医学的困境,基础研究对象的简单性与临床实践的人的复杂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临床医学只有经过大量资料的积累,长期的临床效果观察,对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人群的反复验证,才能达到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实践的真正转化。如同上述肝癌转化医学研究的困境,即使基础医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临床试验需要大样本及长期的临床观察,而面对复杂的人体时,就会产生上述矛盾,阻碍转化医学的顺利进行。
2.3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各自为政
人类进行基础研究之初,实验室是在医院之内,随着临床工作复杂性的增加,基础研究人员逐渐从医院分离出来,将基础医学研究放到医学院校之内,这样,基础医学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分离,从而也导致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基础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各自为政,他们之间的沟通较少,没有交流就难以互相提出各自的需求,阻碍基础医学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也阻碍了临床应用需求反馈给基础研究。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是转化医学难以实施的关键。
实验外科的发展如火如荼,从传统手术到目前手术机器人的发明,可以看出外科学中的实验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但反观我国的实验外科向临床外科学转化的实际,对于先进的手术设备却少有人问津,虽然有手术技术不成熟、治疗费用高昂等因素存在,但多数的医院包括临床实践者,没有将这种尖端的技术提到引进的日程,使实验外科新技术难以在我国大范围应用,实属转化医学的又一困境所在,实验外科的基础研究已经完成,但临床的实施者却将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医院效益等进行权衡,最终可能由于难以广泛开展而延缓新技术的引进。因此,对于高新技术的研究,临床医生应与基础医学研究者共同协商,在对高新技术开发之前,明确其今后使用的效价比,以避免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不符合临床的实际需要,而这种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各自为政,是转化医学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
2.4明确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目的性:为患者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的挑战》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是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而应当是以人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目的。因此,无论是基础医学还是临床医学,都应明确实施的目的是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只有目的同一,才能为了相同的目的而共同发展。为患者服务,不但是对患者疾病的治愈,还要节约患者的治疗费用支出,提出最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预后的生活质量。只有基础医学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从“为患者服务”的目的出发,节约医疗成本,才能使转化医学最终达到为临床所用之目的,走出困境,实现发展。
3转化医学的未来展望
3.1相关疾病的转化医学研究展望
纵观全球近20年的转化医学发展,有较多的转化医学研究的成功案例,如胃肠间质瘤(应用情况)(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GIST)是近10年来被重新认识的消化道间叶源性肿瘤,在2000年以前,这一少见肿瘤发病机制的发现未能转化到治疗干预中,这时患者的生存率只有10个月~20个月,2000年以后,由于临床研究者注意到伊马替尼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作用,进而转向到胃肠间质瘤的治疗当中,通过基础研究,使伊马替尼成为治疗胃肠间质瘤的有效药物,这使患者的生存率延长至57个月。使其生存率从只10个月~20个月延长到了57个月。但是,临床中仍然有许多疾病有待通过转化医学的研究和应用被攻克。
未来转化医学研究的临床疾病中传染病将是重要的一方面,其中亟待通过基础研究解决临床治疗问题的传染病包括:艾滋病、丙型肝炎、乙型肝炎、流感等。而关于这几种传染病转化医学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内容:艾滋病产生的致病机制;预防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效果;针对丙型肝炎病毒(HCV)的抑制剂的发现[14];治疗乙型肝炎的蛋白酶抑制剂药物的抗性如何;H5N1流感的相关致病机制;流感与脓血病(sepsis)之间的相关性[15];H5N1疫苗的免疫效果可否通过MF59免疫佐剂增强;流感疫苗的相关研究,等等。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变异性较大而且变异速度较快,最近已经发现了H7N9型流感病毒,这又为转化医学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此外,转化医学未来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代谢性疾病、精神疾病、运动系统疾病、视网膜疾病、遗传病、器官移植等。而相应的研究内容包括:糖尿病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人造胰脏治疗1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联合治疗新方法;通过恢复控制多巴胺传递的蛋白(GRK6蛋白)改善帕金森病症状;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后的运动障碍;保护具有骨质增生的Wnt蛋白的作用;脊髓损伤之后病情恶化与Surl蛋白的关系;基因治疗脊髓性肌萎缩;先天性失明的治疗;提高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移植存活率;失眠的致病机制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等等[16]。可见,转化医学的未来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仍然有许多疾病亟需转化医学研究解决相关的临床诊疗问题,这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者的有效沟通,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多学科交叉理念的推广,转化医学研究必将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未来攻克各种疾病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但是,转化医学应用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建议:首先,对于基础研究者来说,在进行基础研究之前,明确研究目的,到临床中进行调查,验证该研究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临床诊治困难,应用前景是否乐观,对医生和患者是否适宜。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诊治手段的精确与多样性,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一项利好消息,但诊治费用必将提高,患者的医疗负担也会相应提高,等等[17],这些都应该是在进行基础研究之前需要做的工作。其次,临床医生要培养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的习惯,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在完成临床疾病知识充实的同时,要重视基础医学理论的学习[18]。只要二者相结合,利用转化医学理念,就能找到临床实践中需要的基础医学知识,找到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方法,使得转化医学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使得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为患者服务。
3.2转化医学研究的政策支持
3.2.1建立转化医学研究机构,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深度合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在2003年描绘的路线图计划中,明确了所谓的双向、开放、循环的转化医学体系[1],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NIH路线图计划一经确立,就得到了全球的各大机构及制药公司的大力支持,相应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及其研究的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扶持转化医学的研究。在2006年,NIH成立了由20多所大学和机构协同合作的一个协作组织,专门负责对临床和转化医学的推动发展,并使其他学科加入到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中来,通过合作、协助等方式对研究进行创新。包括各种研究的项目设立、新式计划和手段的应用、技术的介绍,而这些项目和技术均与临床癌症防治相关,目的在于找到相应的组织工程技术,癌症防治技术的临床转化,干细胞技术对临床疾病治疗的方法和转化。鉴于此,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对恶性肿瘤的防治应该能够达到降低死亡率的目的,但通过调查,肝癌的年死亡率升高,5年存活率未有改观,因此,应成立相关的转化医学机构,必须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提供相应的资金,将基础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临床,对于费用较高的问题加以解决,使临床医生和患者没有后顾之忧,使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者密切沟通,全身心地投入到转化医学研究中;另外,鼓励临床的研究者发现临床应用的问题,尽快反馈给转化医学研究机构,通过机构与医学院校基础研究者联系,达到信息的传递通畅,保证转化医学顺利进行。
3.2.2鼓励医药企业投入,国家对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给予支持
全世界对转化医学的重视,无论是资金的投入还是研究的广泛程度,均超过其他学科的发展,从医学角度看,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将向注重转化医学的目的和效果转变。例如,外科机器人的发明,极大地解决了临床手术操作因精细问题而出现的事故,使外科手术接近于完美。但由于技术的不熟练,临床应用费用高昂,我国难以普遍应用。因此对于先进的手术技术难以为患者服务,使我国转化医学遇到瓶颈。在国家政策方面,首先要对高新技术效果加以肯定,鼓励医药企业加大投入,对于引进设备的医院等医疗机构,在使用初始阶段应给予相应补助,使患者尽量能承受经济支出,使开展技术的医院避免大的损失,使其产生应用的动力,将转化医学研究中的高新技术在临床实践中顺利应用。
3.2.3提高转化医学研究者的临床和基础知识、技能,为转化医学的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叶青海[19]指出,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严重脱节,使得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没有转变为临床可用的诊疗方法并使患者真正从中受益。如何打破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药物研发之间的巨大“鸿沟”,将基因组学时现的大量分子生物学医学信息变为临床可用的技术、方法,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也是进一步提高诸如肝癌治疗效果的关键。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应建立健全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并将这种理念遍及全国范围,开启转化医学研究方便之门,使转化医学的理念深入基础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的内心,使得临床工作者要加强基础思维技能的训练,基础研究者了解临床疾病诊治现状,只有将临床知识与基础研究相结合才能达到转化医学研究的目的。
作者:高 峰 赵明杰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杂志社 医学与哲学杂志社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