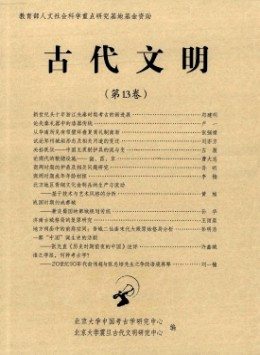古代外民族音乐传播对汉族音乐的影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代外民族音乐传播对汉族音乐的影响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中国古代汉族音乐的形成源流、外民族音乐的传播历史、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对汉族音乐的影响,三部分来具体阐述了古代外民族(少数民族、外国)音乐的传播对汉族音乐形成的影响,以及对它的贡献,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传播;汉族音乐;外民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
一、中国古代汉族音乐的形成源流
具体来说,汉族音乐之所以形成今天这种局面,归功于它的三大源流;即中原音乐、以及伴随着历史上若干次人口大迁移而来的外国音乐以及四夷音乐。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传来的佛乐,隋唐时期传来的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是两国音乐文化交流的结果。外国音乐传入中国的历史,从正式史料记载来看,应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说起,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音乐、唐朝时期的天竺乐、高丽乐、清朝时期欧洲音乐的传入。
二、外民族音乐的传播历史
据史料记载,早在周代,一些统治阶级酷爱音乐,经常带领乐队或歌者到各国游历,将我国的音乐带给别国,同时也将别的国家的乐器、乐人引入我国。史料记载,周穆王早在公元前10世纪,在中国边境游历过程中,用音乐感动傀儡戏艺人,并将外国傀儡戏艺人带入中国。这为我国汉代百戏的发展起到大的影响。汉代,航海家张谦出使西域,带回乐曲《摩珂兜勒》[1],汉乐府领导人李延年,根据这一西域音乐,创作了新声二十八解,最后列入军乐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西域音乐的元素注入汉族音乐中,新声二十八解的曲式结构后来大量的出现于戏曲结构中,比如杂剧与南戏中。秦末西北部少数民族牧民班壹,躲避战乱,到山西接近少数民族地区,应用鼓吹乐,乐器配有笳以及萧、角,羌笛。羌笛这一少数民族乐器,后来经过京房改造,逐渐融入汉民族音乐生活中;而在音乐曲调方面也大量将少数民族音乐引进来,随着后来鼓吹乐在宫廷的盛行,汉族音乐元素更多的参与其中,最后两者融合。汉代最著名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2],是由蔡文姬在匈奴生活12年之久的基础上,参考少数民族胡笳这一乐器的音乐曲调而创作的,可以说在琴曲吸收少数民族音乐方面开创先河。在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因此在音乐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汉族与外国音乐出现了大交融的场面,汉族音乐融入了新的血液。在北魏时期,出现一种新的音乐品种,叫做《真人代歌》,也叫《北歌》,实际上是鲜卑族风格的《鼓吹乐》,即将鲜卑族音乐文化融入汉族音乐中。同时更是出现了具有说唱性质的鲜卑族大型叙事音乐《木兰诗》,当时流传于汉族各地,对说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更是之后戏曲音乐崛起的先声。印度音韵学的传入,可以说为我国音韵学的正式创立奠定了先决条件。建立了平上去入,新的四声体系,这对以后中国的声乐艺术以及作曲技术起到深远的影响;同时佛教徒来中国宣传教义,早在第四世纪也将大量的印度音乐带入中国,与中国汉民族的音乐相结合,到唐代出现的带有说唱性质的变文,即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演变的,以及现当代各成体系的佛教音乐。且在南北朝时期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于汉族中原地区的音乐即有鲜卑乐、西凉乐、龟兹乐、高昌乐等;而外国音乐则有高丽与安国乐。而这些外民族音乐最终都被唐大曲吸收,无论是在乐器上、外民族音乐家的输入、音乐元素上还是曲式结构上,都对汉民族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质的材料。而最具影响力的当数这些各地区音乐传入的同时,带来的乐器,而乐器里的琵琶,在几千年的汉民族发展历程中,已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族乐器之一(在下章详述);而在曲式结构上的影响,可以唐代的《霓裳羽衣曲》为例。到了唐代正是因为这些外民族音乐的冲击,使得传统宫廷雅乐日渐衰微,燕乐一跃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品种。《立部伎》八部、《坐部伎》六部,可以说是多民族音乐大融合的典范;同时它在宫廷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雅乐,甚至于雅乐也逐渐交流融合;在名称上,这主要通过官府正式的将这些带有民族标记的音乐名称去掉,而改换曲名,且将一些曲名刻在了石头上,以示郑重。[3]大概都是将通过汉文音译的外民族音乐,改成了意译,这时通过朝代的更迭,人们已经不能将两者分离;而在乐器方面,一方面对它进行改进,如琵琶,另一方面将它原汁原味的吸收,更甚者,将汉族与外民族乐器混合使用,或者,两种乐器互相取长,进行改进;在歌词内容上,将之前多讲述征戍生活的鲜卑族音乐改成内容上讲述宫廷宴请之类偏重于娱乐情节的;同时为了配合,内容的改变,一些乐曲在情绪方面的要求也出现,因此,配合此种情况出现了移调,最著名的要数,佛教音乐家与外民族音乐家,康昆仑与段善本的《羽调绿腰》,因此也才有二者斗琴的千古传奇。唐朝体现各民族音乐文化大融合的两个极具典型代表的作品,即《霓裳羽衣曲》、《凉州大曲》两个大曲。前者为外国音乐作品与汉民族音乐的融合体;而后者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结合体。凉州大曲一方面吸收中原旧曲、另一方面吸取龟兹音乐的精华,同时融合凉州地区音乐文化而出的精品。《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所做的法曲,即大曲的一种,是大曲中情感较细腻,音乐较委婉的一种。是根据印度《婆罗门曲》的声腔的基础上,融合自己所创的,带有清商大曲风格的《霓裳曲》而创作的全曲。这些大曲都是融合器乐、声乐、舞蹈为一体的,曲体大型、音乐结构完整、结合复杂的一些大型曲体结构,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戏曲音乐发展埋下了伏笔。唐朝乐人之间也在各国、各民族进行交流,最著名的要数龟兹音乐理论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理论,这些新的理论的出现,催生了对调式体系的大探索。一直到宋元时期胡琴乐器才随着戏曲音乐的大发展,在中原大地火速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无论是南方剧种还是北方地方戏曲都少不了这种起始于少数民族的原始名为火不思的乐器,到了近现代经过著名音乐演奏家、作曲家刘天华[4]的发展与改制,就发展成我们如今的二胡;由此可见这一乐器已经根深蒂固的与汉民族人民生活连接在一起。
三、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对汉族音乐的影响
通过种种列举音乐史实,汉族音乐的发展史,追根朔源,原来是一部多民族音乐大融合、大交流的音乐史,因此我们明白,我们民族的音乐并不是故步自封式的自身对自身的发展,尽管顽固的雅乐派音乐家们盲目的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民间音乐、外国音乐、四夷音乐,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正如音乐这一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它自身的发展,人为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它经历过了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吸收优秀的相邻文化,俨然将自己发展的更加完善,日臻成熟。
(一)它民族器乐的传播对汉民族器乐发展的影响在器乐方面的影响要数从外国传来的琵琶,与少数民族传来的胡琴(现的二胡)。琵琶这一乐器,从三世纪-五世纪,曲项琵琶与五弦琵琶,陆续从印度传入我国北方。经过唐代,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音乐,琵琶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乐器,当然它在汉族发展的历程中,也吸收我们民族乐器的特长,以及为了表现我民族的音乐情感,所以技法方面大为改进,而技法方面的改进,就激发了它形制的改制,比如为了旋宫转调方便而做的弦数的改变、相的改进,以及曲项的改进;到了近古,与戏曲音乐的进一步磨合,才使得它真正发展成熟,明清时期,大量的琵琶名家、名曲涌现。无论是琵琶这种乐器本身,还是琵琶曲都成为了,我们民族人们心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二胡[5],这一乐器,从唐代的二弦擦弦乐器,到近现代的二胡,它的发展,可以说是音乐文化中的一件大事件。从最初的拨子弹拨,到最终的拉弦,经过一代代音乐家的努力,最终成型。当然二胡的最大发展时期还要说到近现代时期的阿炳与刘天华[6]。阿炳在发展器乐文化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二胡名作《二泉印月》,在对二胡弓法的开发上做了大量研究,也可以说,整个作品即是对这一乐器改革的一个尝试性范例,无疑这一范例已经成为典范。而刘天华,更多的是参考西洋乐器,小提琴的顿弓、力度、节奏,以及西洋乐的十二平均律、有利于旋宫转调等反方面对二胡进行改革;于此同时还专门创作二胡练习曲,将这一乐器真正推向成熟。
(二)它民族音乐传播对汉民族音乐品种发展的影响1、说唱音乐众所周知,唐代的变文一类说唱音乐,最初是由印度传来的佛经文,为了通俗易懂,就出现了将佛经与音乐相结合的形式,同时又由于佛经篇幅长大,逐采取说唱这一形式,因此,说唱艺术才广泛被推广。在唐代,寺庙中常常定期举行音乐会,当然涉及的多是这一种说唱形式的变文,而内容方面逐渐改编为一些传奇、演义。一直到宋代,街头出现的叫卖调、嘌唱、小唱、唱赚等都是唐代变文世俗化的结果,最后这种叫卖调愈演愈烈,直到包容性更大的大型杂剧、南戏音乐的出现,此种叫卖性质的说唱一并被吸收,最终演变为我们现在听到的曲艺音乐。2、佛教音乐宗教音乐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但不是自发形成的。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音韵学的传入,到佛教音乐的传入,到它与汉族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寄托。各种法事都有固定的仪式,而固定的仪式又配合相应的音乐模式,这些音乐模式大多是一个固定的高度程式化的形式,开场用哪首音乐,音乐中要用到哪些乐器,队形如何排列,它们又具体包含何种意味,何种内涵都是有规律可循。总之它的高度完整化与成熟化,并逐渐成为单独的一个学科。[7]
(三)对律学的影响十二平均律,它的精密计算方式,虽然在明代已被我国乐律学家朱载堉已近完美的计算出来。但众所周知,我们民族的乐器大多用纯律与五度相生律[8],十二平均律[9]虽最早在我国被计算出来,但由于一系列原因都被忽视,直到康熙年代欧洲大小调体系以及由十二平均律体系制作而成的钢琴(当时称为管风琴)的传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音乐体系,虽然这一次的传入只在宫廷之内流行,但它对近现代大量的欧洲音乐涌入中国打下了基础,因此到了鸦片战争后,才有了我们的学堂乐歌,从学堂乐歌又普及到每一个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到现当代,十二平均律已经是与纯律、五度相生律并驾齐驱的一个律种。
参考文献
[1]柯琳,高乐.中国汉族传统音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4]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5]王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6]袁静芳.民族器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7]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8]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初稿).1983
[9]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作者:曾真 单位:衡阳市艺术研究所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