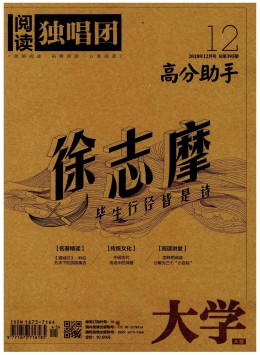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分册专辑出版的考察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分册专辑出版的考察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追溯晚清民国期间综合性大学文理综合版与中英文混合版学报历史的背景,考察1949年至今70年来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分册专辑出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认为1951年的《厦门大学学报》和1963年教育部主导的《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专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读者群体未能细分的缺点,达到了准专业期刊或准专辑出版的效果,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建议推广分册专辑出版,以便弱化大学综合性自然科学版数量过多、规模过大、与科学和教育发展规律相悖、与期刊传播规律相悖的不利态势,变劣势为优势,变优势为特色,进一步发挥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在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大学科技学术期刊;综合性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分册专辑出版
1百年历史沉淀而成的文理综合版与中英文混合版
1.1晚清民初的中英文混合版与文理综合版
我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在萌芽时期,表现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沌不分的状态或中文与英文杂处的状态,我们称其为“文理综合”与“中英文混合版”。1889年创刊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的《约翰声》(《TheSt.John’sUniversityEcho》)文理综合版和中英文混合版,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与中英文混合的大学学报。这种文理综合性的模式,至1909年的《金陵光》(《TheUniversityofNankingMagazine》,中英文混合版)、1915年的《清华学报》(《TsingHuaJournal》,中英文混合版)和1919年的《北京大学月刊》(中文)趋于鼎盛。然而,不同于《清华学报》的是,《北京大学月刊》创刊伊始,就是以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分册专辑出版的形式面世的。其编辑出版方式是由“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每册之总编辑,则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其临时增刊之总编辑,校长任之”[4]。即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主编,按学科分册的编辑出版形式出刊,像陶孟和(哲学)、朱希祖(国文)、马寅初(经济学)、胡适(英国文学)、陈启修(政治学)、黄右昌(法学)、秦汾(数学)、张大椿(物理)、俞同奎(化学)、孙云铸(地质学)、刘慎谔(生物学)等,均曾担任过分册的主编者[5],蔡元培校长也担任过第7册的总编辑和增刊的总编辑。这使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一炉,按研究领域或按学科出版月刊成为一种制度。
1.21931年的《复旦季刊理工专号》
20世纪30年代,文理综合与中英文混合版出现分化的迹象。复旦大学出版委员会于1931年3月创刊的《复旦季刊理工专号》就表现出这种迹象。该刊“每年要另出四期,就本校文、理、法、商四学院分配,每学院每年须担任一期”[6]。这与此前1926年7月出版的第2卷第2期《复旦(土木工程专号)》和复旦大学理工学会学生于1928年6月出版的《理工学报》两刊不同:一是《复旦季刊理工专号》为校方主办,且按年统筹规划,与《理工学报》和《复旦(土木工程专号)》均系学会临时主办不同;二是《复旦季刊理工专号》为学校按四大学院分配专号,更近似于1919年《北京大学月刊》按研究所分配专号,同时,这也不同于此前1930年第6卷第1期的《清华学报》文哲学号与第2期自然科学号的做法,更类似今人文社会科学版与自然科学版的分化。
21949年后的文理分化、分册专辑出版
2.1综合性大学学报专辑出版
1949年至1965年是大学科学研究发展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1949年至1953年,经过学习改造,以及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经验,高校教师的科学研究热情普遍有所提高;1953年至1957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高校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1958年至1965年,形成了较大发展,仅仅南京大学,就“在文科各系完成1104篇论文、理科各系试制2700种新产品”。[7]于是,《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于1959年选择44篇论文,印成一个专刊(四本)。稍后,又以1963年第1期、第2期的封面,另编了No.1—No.16+Z1的期次编号(每个学科占两期),分别出版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专辑。其中数学专辑后来演化成为《南京大学学报(数学半年刊)》。这表明,学校科学研究规模的扩张,是形成学报专辑、分册、增刊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专业化、特色化扩张的内在动力。这一时期,厦门大学的海洋生物研究也渐成特色,1952年9月复刊的《厦门大学学报》基于此,将学报分为数学版、生物版、海洋生物版、自然科学版、财经版等交替出版,至1956年始分别为社会科学版与自然科学版。这种分学科分册出版,突出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学科优势的做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科技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创造,是今天综合性大学学报特色化办刊的先声。《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1958年至1959年,出版了“基本粒子结构理论专辑”“自然科学增刊”。《同济大学学报》1959年全年均为铁路、桥梁等专辑。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综合性大学学报出版专辑,并非个别现象。
2.2教育部主导的专辑出版
20世纪60年代,除高等学校自身分册专辑出版的应变举措之外,教育部也因势利导,采取了组合全国高校科研优势出版系列专业期刊的重要举措。1963年5月2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出版“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的通知》[8],委托相关高校创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相继出版的有8个分版,包括:(1)数学、力学、天文学版(委托复旦大学主办);(2)物理学版(委托北京大学主办);(3)化学、化学工程版(委托吉林大学主办);(4)生物学(委托武汉大学主办);(5)地质、地理、气象学(委托南京大学主办);(6)机械、动力版(委托西安交通大学主办);(7)电工、无线电、自动控制版(委托清华大学主办);(8)土木、建筑、水利版(委托清华大学主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系列刊物除生物学及地质、地理、气象学版为半年刊以外,其余均为季刊。该刊具有较高的起点,主要“以择优选载各高等学校学报上已经发表的上述各学科的科学论文”和“选载全国性学报(或相当于学报水平刊物)上高等学校师生所发表的论文文摘”,后来才发展到发表原创论文。为此,教育部专门成立“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委会”,并《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征稿暂行办法》。这些分版,对集中反映高校高水平成果有积极意义,也反映了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科技学术期刊专业化发展的引导。
2.3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化和特色化系列刊物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学术期刊规模有较大扩张,校内期刊的作者队伍渐以研究生为主,另外由于关键词等搜索方式在某些程度上降低了综合性期刊和专业化期刊的检索差异,加上SCI的引导,大多一流稿件外流,出版专辑的条件和热情有所降低。这时的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出现了教育部主导的大学科系列期刊新引领,高校也在合校潮中对以综合性为主的期刊布局作了某些调整,综合性期刊特色化也逐渐成为主流。然而,高校综合性期刊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并无根本性改变。教育部主管并委托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于1980年主办的《高等学校化学学报》,1986年全国直属高校应用数学学术与工作会议委托浙江大学主办的《高等学校应用数学学报》,教育部主管、全国高校地质院校于1995年联合创刊的《高校地质学报》,2017年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分为中文版、英文版两刊)又一次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一种专业化引导。1986年以来,《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始按学校优势学科分为三大版块、12个方向,并重点向电机与信息科学(含计算机、自控等)和机械(含精仪、热能、力学、航空、航天)等方向倾斜,大致形成专辑,走出了一条准专业化和特色化的新路子。[2]2006年,教育部再次出台引导性举措,支持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公司合作创刊《Frontiers》(《前沿》)系列英文学术期刊,包括《FrontiersofEnvironmentalScienceandEngineering》(《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等29种。其初期运作,与1963年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相似,都是从大学学报择优选稿,以后才逐渐发展到发表原创论文,并采用了在线优先(OnlineFirst)等多种出版方式。它是依托高等学校的国内第一个成规模的英文期刊群,力图凝聚国内顶级科研力量,反映最新学术成果,形成品牌,同时也反映了对高校科技学术期刊专业化发展的一个引领。另外,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合校潮中,不少大学将综合性学报改为专业期刊。比如:浙江大学有了《浙江大学学报》A辑、B辑及《浙江大学学报》之理学版、工学版、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医学版等准专业期刊。长安大学有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等专业期刊。给人以启迪的是,《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因合校后的新增学科而变得更为综合,结果不为读者接受,但及时恢复了原来的公路交通运输特色,之后逐渐成为一份有影响力的刊物。这说明在国际专业化潮流和读者市场细分以后,特色化办刊、分册或专辑出版是综合性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切实有效的选择之一。
3讨论与建议
大学科技学术期刊是随着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故科学的分化与综合、大学的院系划分、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是期刊类型生成或制定期刊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理工农医师范院校,均应按学院、系科、专业、社团现状,以主办专业科技期刊为主和主办少量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为辅。纵观我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的演化进程,逐渐实现了期刊类型从文理综合性向文、理各自独立的进化,从史地不分,走向史学与地学的分化,也实现了从地学向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的进化,或从博物学向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或生物学的进化,以及从物理学向力、热、声、光、电、磁的进一步分化。目前,一些专业期刊已经很难归入6000余个自然科学二级学科,出现了《细胞》《质粒》这样细小的期刊类型。看来,文理综合期刊→自然科学综合期刊→专业期刊,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规律。70年来的大学科技学术期刊,特别是以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刊名的一批期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哲学社会科学版与自然科学版的分立以后,无论是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版(甚至很多理工院校的学报也以自然科学版为副刊名),还是综合性的工程技术版或综合性农学版、综合性医学版,似乎并未继续跟进全国或世界期刊类型的进一步进化。2014—2017年认定的全国6449种学术期刊中公办高职高专院校主办的153种学报[9],甚至仍然处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理综合的形态。据调查统计,截至2004年底,在全国高校1494种科技学术期刊中,综合性自然科学版就有474种,占总数的31.73%[10]。如果将综合性工程技术期刊(238种,占总数的15.93%)、综合性医药科技期刊(393种,占总数的26.31%)、综合性农业科学期刊(88种,占总数的5.89%)也计入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则其总数达1193种,比例高达79%。这不仅高于中国科协系统、中国科学院系统中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和专业性期刊的比例,显然也远高于《乌利希期刊指南》(ULRICH)中世界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仅占3%的比例。[11]李玉红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为例,指出综合性大学学报“学科分布杂,检索不便”“扩散范围有限”“作者群相对狭窄”,缺乏对一流稿件的吸引,“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故“发挥特色优势”应为发展选项之一。[12]朱崇业也以《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指出:国内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类学报都处于进退维谷、极其尴尬的局面。学报的综合性、多学科性和本身的封闭性,又是当前形势下的致命弱点,所以自然科学类学报必须改革、兼并,走专业化、国际化的道路。[13]由此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由《厦门大学学报》和《南京大学学报》,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传承民国时期传统出版的做法,逐渐形成一种综合性学术期刊分册专辑出版模式。它既保持了综合性大学学科众多的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读者群体未能细分的缺点。从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出版形式问题,但实际上它反映了大学科技学术期刊遵循科学分化规律以及适应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发展需要的一个编辑出版应变模式。因此,这一模式当具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保留少量有历史、有影响的综合性学报的前提下,可以借鉴《厦门大学学报》和《高等学校自然科学报》分册专辑出版方式,参考英国的《自然》杂志按稿件多寡创办27种系列刊物以及《中国科学》分为17个分辑出版的方式,推广分册专辑出版,以弱化大学综合性自然科学版数量过多、规模过大、与科学和教育发展规律相悖、与期刊传播规律相悖的不利态势,变劣势为优势,变优势为特色,进一步发挥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在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作者:姚远 单位: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