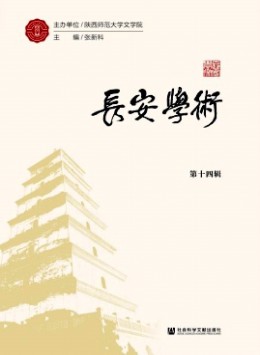学术成果分级目录图书情报类期刊分层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学术成果分级目录图书情报类期刊分层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本文以高校实际使用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为视角,探讨中文图书情报类期刊的分层结构,为图情研究人员确定成果发表渠道、图书馆员调整期刊订购方案、高校管理人员制定学术成果分级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网络调研,汇总整理了国内63所有图书情报类硕士点(含专硕)高校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提取了24种图书情报类期刊,统一编码、整理,对数据聚类产生期刊分层结果;发现图书情报类期刊的层次区分比较明显,处于上层的期刊多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高校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明显受CSSCI来源期刊遴选和北大核心期刊评选结果影响,表明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桶”分类系统对高校学术成果分级政策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期刊评价;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期刊分层;图书情报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图书情报类学术期刊数量不断增长,对学术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两批认定的学术期刊中图书情报类共有40余种[1],大致可分为偏图书馆学、偏情报学和图情综合3大类。但这些期刊在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随着期刊数量的快速增加,如何从众多期刊中筛选优质期刊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期刊评价不仅有助于学术期刊提升办刊质量,而且也帮助研究人员、图书馆员和管理人员了解期刊的质量变化。研究人员通过它确定发表渠道,决定在哪里发表研究成果,学术新人可以集中阅读某几本最重要的期刊尽快熟悉某个领域[2];图书馆员会根据期刊评价情况调整订购方案,以有限预算购买那些最有价值的期刊;高校管理人员会根据教师在优质期刊的发文情况,制定与薪资调整和考核晋升有关的决策。更广泛地说,院系和高校师生在顶级期刊上的发文情况也会影响人们对该机构的整体看法。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在探讨学术期刊的评价问题,学者们采用了多源的评价数据、丰富的评价方法和多样的评价技术开展研究,为期刊评价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贡献。分析图书情报领域期刊评价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主要存在引文分析评价法、感知调查评价法和混合评价法3类方法。引文分析评价法是以期刊影响因子(JIF)和h指数以及由二者衍生的一系列引文计量指标对期刊评价[3]。此类方法的优点是指标易量化、易计算、数据易获取,但引文作为一种仅能衡量影响力的计量指标,并无法全面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因为引文具有学科和领域差异,不具可比性,评价者也无法确定施引者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引用一篇文章,甚至少数期刊还会操纵作者的引文行为,部分指标用于评价的准确度和区分度也有待商榷。感知调查评价法是同行评议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一种基于受访者的感知判断给期刊打分的方法,可代表受访学者群体的累积意见。其优势在于可以反映熟悉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的群体感知意见,缺点包括主观性太强、受访者样本代表性不足、认知偏差影响以及时间久、成本高等,说明该方法也有待继续完善。混合评价法是对上述两种方法的整合,将引文分析法与感知调查法结合,或将引文计量指标与基金论文比、Web即年下载量(率)、作者集中指数等加权汇总产生期刊排名。此外,基于博客、社交媒体、网站下载等参考资料的Alt-metrics指标也被建议作为一种期刊评价信息来源[4]。
学术界普遍认为,只关注单一指标、单一数据、单一方法的期刊排名是有风险的[5],不足以客观反映学术界对期刊质量的整体看法。混合评价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仅使用引文分析法和感知调查法的偏差,但如何保证指标选择的全面性、数据聚合方法的科学性和减少权重设置的主观性等问题同样影响此类方法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以上3类方法都可以对期刊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质量特征进行评价,但这些方法均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足,单独依靠某一排名判断一本期刊质量的好坏是非常武断的。出于各种原因,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的期刊排名结果褒贬不一,同行对结果的普遍认可度较低使其无法广泛用于期刊评价决策。本文从目前高校正在使用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入手,探讨图书情报类期刊的分层结构,帮助研究人员、图书馆员和管理者全面了解图书情报类期刊的评价情况。如今,从学校层面的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学位点申报,到基层研究人员层面的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甚至是研究生的毕业要求等都离不开对期刊的考核,各高校均会制定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明确衡量标准,表明学校对期刊质量的认可程度,以指导本校师生的发表渠道。在高校管理者合理、科学决策的前提下,这些高校学术成果分级目录的出台,一般是靠领域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实现的,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校各学科研究人员的同行集体意见。如果对这些学校的图书情报类期刊目录进行整合,可以合理认定为领域同行对期刊的一次大规模同行评议,可以有效减少个人评价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法超越了对期刊质量的主观感知和客观计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个别高校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偏见对期刊评价结果的影响。一所高校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中的表现和是否存在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对判断其在某一领域学术实力和师资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可以认为这所高校从事图情领域研究的人员相对较多,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学术水平相对较高,据此,可以作为选择高校样本的依据。为扩大调研规模,本文选取我国(未调研港澳台地区)具有图书情报类硕士学位(含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授予权高校开展调研,获取数据。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网络调研阶段;第二阶段为数据整理分析阶段。
2网络调研作者
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研招网)”查询2020年硕士专业目录中学科类别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和专业学位“图书情报(1255)”的招生单位名单,去重后共得到73个机构,去除7家科研院所和军队院校后,余66所高校。这其中包括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级的全部26所高校(不含国防大学)和11所具有博士授予权高校,其中图书情报学硕士点高校50个,只有专业硕士点的高校16个。这些高校分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发现,我国有图书情报硕士点(含专硕)的高校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其中华东地区(20所)、华中地区(13所)、华北地区(12所)、东北地区(10所)高校数量占总数的83.3%,尤以江苏和北京两省市更为集中。随后,笔者陆续对这66所高校开展网络调研,主要了解以下问题:该校目前是否使用学术成果分级目录、主要用于什么用途、这些分级目录是否可以获取、目录中对图书情报类期刊是如何分级的。笔者主要采用4个步骤获取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文档:(1)依次根据高校名单,访问其社科处(或人文社科处、科研处、科技处等)官网查询,因为根据作者经验和高校职能管理部门分工,普遍由此类机构负责制定并经学校授权该校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文档或文件。(2)若无法在社科处网站查询,则通过站内搜索引擎等工具以“权威期刊”“重要期刊”“一流期刊”“期刊目录”“奖励期刊”“期刊分级”“成果分级”“核心期刊”“成果认定”“论文奖励”等关键词检索。同时,在该校人事处、学术委员会、研究生院以及图情相关学院的官网招聘或考核文件中查询期刊目录线索,以确定新的关键词。(3)考虑到部分学校设置内网,一些网站内容无法访问的情况,在百度、必应等搜索引擎中以“学校名称+关键词”检索文库或论坛中由个人上传的期刊目录,对不同版本迭代,确保获取最新版。(4)通过QQ、微信、邮件、电话等联系部分学校职能部门、教师或博士生,对部分年代久远的期刊目录进行确认,同时解决了部分高校由于文件在内网存储无法获取的情况。经过调研,笔者掌握了66所高校的学术成果分级政策情况,有一所高校目录中未明确写明期刊名称,另有两所高校未制定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故有效期刊目录数量为63个。这些目录整理后,可以发现以下几项特征:(1)绝大多数高校均制定了学术成果分级目录,并根据期刊地位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主要用于成果奖励、人员考核等目的;多数高校以校发行政文件形式目录,可见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2)在这些目录中,期刊通常被分成不同的层级,不同高校的划分层级以及各层级的名称多样,包括权威期刊、重要期刊、奖励期刊、一流期刊、Top期刊(T0、T1、T2、T3)、A类期刊(A1、A2、A3)、B类期刊(B1、B2、B3)、C类期刊、学校认定期刊、优秀期刊、核心期刊等。期刊目录一般划分为2-5级,以3级和4级居多,极少量学校划分为5级,或者只列期刊名称,不分级。(3)从多数文件说明中可以发现,期刊层级划分依据主要以同行评议为主,包括领域专家咨询、全校师生讨论、学术委员会认定后确定期刊名称、级别,部分高校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期刊评价机构的最新排名,如南京大学CSSCI、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社科院A刊等。
3数据整理
笔者提取了目录中涉及图书情报类的期刊,统一进行了编码、整理。部分高校在某一层级中只写明采用最新版CSSCI期刊或北大核心期刊,考虑到此类情况属于将该级评价权转由评级机构的结果决定,不属于同行评议范畴,故对这些层级不作统计,只统计那些明确罗列出期刊名称的层级。由于多数目录中期刊分成3级或4级,笔者统一按照前4级统计。以某图情期刊在中文期刊目录层级中的出现位置,依次设置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有些学校中英文期刊目录在一起,中文期刊从第二级或第三级出现,则以中文期刊最先出现的层级为第一级。对于那些在一个层级中又细分了二级层次的情况(如在A类下再分A1、A2),根据图情类期刊的整体出现位置,酌情确定层级。如所有图情期刊均出现在A级,则按照A1、A2分别对应第一级、第二级,如部分在A级,部分在B级,则将A1、A2全部归为第一级。
4数据分析与结果
笔者对63所高校目录全部统计完后,根据图书情报类期刊的被提及频次,整理得到了右表的数据。从表中可以发现,共有24种图书情报类期刊被各高校列入期刊目录,均为近几年曾被南大CSSCI(含扩展版)和北大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过的期刊。根据期刊质量、影响以及学术地位,它们在各层级中出现频次有明显差异。除《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图书情报知识》6种期刊在第一级出现外,其余多数期刊均分布于第二、三、四级。利用SPSS24.0统计软件,对24种期刊的统计数据进行层次聚类,得到图2的聚类谱系图。如图2,当用1号线来切割谱系图时,24种期刊分成了两个层次:第一层为《中国图书馆学报》,第二层为其他23种图情期刊,足以说明《中国图书馆学报》在图书情报类期刊中的绝对顶刊地位。当用2号线来切割谱系图时,24种期刊分成了3个层次:第一层为《中国图书馆学报》。第二层为《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共3种期刊,说明这些期刊都被各高校广泛重视,在图书情报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第三层为其余20种期刊。当用3号线来切割谱系图时,出现了4个层次:第一层依然为《中国图书馆学报》;第二层为《情报学报》;第三层为《图书情报工作》和《大学图书馆学报》;第四层为其余20种期刊。当用4号线来切割谱系图时,24种期刊最终被划分为5个层次:第一层《中国图书馆学报》;第二层《情报学报》;第三层《图书情报工作》和《大学图书馆学报》;第四层为《情报资料工作》等14种期刊;第五层为《现代情报》等6种期刊。其中前四层全部为CSSCI来源库和北大核心目录中目前或曾经收录的期刊,第五层均为CSSCI扩展版收录或近几年曾被CSS-CI来源库收录期刊。总体来看,在63所高校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中,《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4种期刊处于图书情报类期刊层级的上层,CSSCI收录的其他期刊会因被核心版和扩展版收录以及收录时间长短等因素而呈现两个比较明显的层次。
5讨论
5.1期刊的地位变化
笔者将本文的期刊分层结果与刘宇(2011,2019)[6]研究中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虽然与上述研究结果在个别期刊上有细微差异,但总体上呈现一致趋势,印证了图书情报类期刊层级固化的状况。近10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4种期刊已牢固确立了其在图情学者心目中优秀期刊的地位,其余期刊的层级差异则越来越小,且明显受CSSCI来源期刊遴选和北大核心期刊评选结果影响,表明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桶”分类系统对高校期刊分级政策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这种评价惯性和“路径依赖”的状况不利于图情类期刊质量的整体提升,因为即使期刊的质量在短期内发生了变化,个人或组织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对期刊的看法,容易使部分期刊丧失努力改善学术质量、获得期刊声誉地位改善的动力。
5.2地区差异
为了解不同地区高校对期刊分级的差异,笔者以《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4种期刊为样本,提取了这些期刊在不同地区分级情况,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各地区在期刊目录中对4种期刊的分级总体上相对一致,但也存在部分明显差异。首先,东北、华东、华南、华中地区的多数高校倾向于将《中国图书馆学报》列在期刊目录的第一层级;西南地区多数高校则将其列为第二级;华北地区将《中国图书馆学报》列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的高校各半。同时,《中国图书馆学报》也出现在东北、西北、西南少数高校的第三级或第四级列表中。其次,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地区的多数高校将《情报学报》列为第二层级,华东地区高校对《情报学报》更加青睐,有8所高校将其列为第一层级。该刊在西南地区高校的第一、二、三级目录中均出现一次,而在西北地区,《情报学报》仅在一所高校的第三级列表中出现。再次,东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多数高校将《图书情报工作》列为第二层级,而华北地区多数高校将该刊列到了第三层级。华南和西北地区高校在第一、第二、第四层级中均有提及《图书情报工作》的情况。最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地区多数高校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列为第二层级,西北地区仅有一所高校提及该刊并将其列为第四级,可见全国各地对《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评价相对比较一致。各地高校期刊分级的巨大差异也会给图书情报领域的校际或跨地域合作研究带来一定障碍,因为研究人员往往会以自己学校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指导成果发表,一种在本校列为第一级的期刊,在其他高校可能被列为3级或4级,这会对两校合作成果的发表渠道选择提出巨大挑战。
5.3专业设置影响
Haslam(2010)[7]和Serenko(2018)[8]在其研究中发现,个人研究兴趣和学科领域对期刊评价结果有影响,受访者倾向于给自己感兴趣或自己学科领域的期刊打高分。为了检验收集到的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是否受各高校研究领域或专业设置的影响,笔者进一步调研了63所高校的专业设置情况。图书情报类期刊涉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二级学科,两个专业的设置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校在图书馆学或情报学领域的师资配置和优势科研状况。调研发现,有52所高校具备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或者同时具备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或者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点,仅有7所高校只设置情报学专业,4所高校只设置图书馆学专业。笔者重点对这11所高校的期刊分级列表进行了审查,结果并未发现明显的期刊分级偏见,即只设置图书馆学专业的高校并未给予图书馆学期刊更高的评级,只设置情报学专业的高校也并未给予情报学期刊更高的评级。所以,可以认为,高校图书情报类专业设置情况并未对期刊分级产生显著影响。
6结语
笔者对我国66所有图书情报硕士点(含专硕)的高校开展网络调研,获得了63所高校的有效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提取了目录中涉及的图书情报类期刊,统一编码、整理,共得到24种图书情报类期刊数据,全部为南京大学CSSCI(含扩展版)和北大核心期刊。利用SPSS24.0统计软件,对24种期刊的统计数据进行层次聚类,可以发现:首先《中国图书馆学报》以绝对的优势确立了本领域顶级期刊地位;其次是《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最后其余期刊层次并不明显。高校学术成果分级目录明显受CSSCI来源期刊遴选和北大核心期刊评选结果影响,表明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桶”分类系统对高校期刊分级政策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期刊评价惯性和“路径依赖”的状况不利于图情类期刊质量的整体提升,因为即使期刊的质量在短期内发生了变化,个人或组织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对期刊的看法,容易使部分期刊丧失努力改善学术质量、获得期刊声誉地位改善的动力。以《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4种期刊为样本,笔者发现各地区在期刊目录中对4种期刊的分级总体上相对一致,但也存在个别明显差异;重点对只设置情报学专业的7所高校和只设置图书馆学专业4所高校的期刊分级列表进行了审查,结果并未发现明显的期刊分级偏见,专业设置情况并未对期刊分级产生显著影响。
作者:胡绍君 孙玉伟 郑彦宁 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