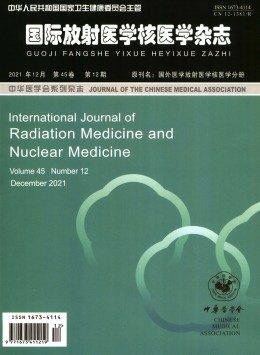医学社会学下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困境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医学社会学下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困境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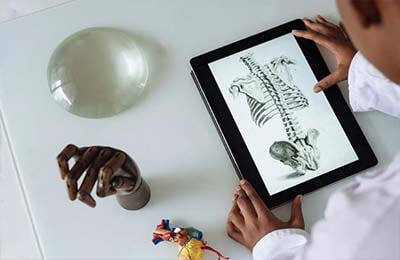
摘要:社区康复是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改善社会功能、回归家庭和社会的重要环节,深受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家庭环境等多因素影响。本研究从医学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及焦点小组等质性研究方法,从污名化所造成的排斥、隔离与自我身份认同挣扎,病人角色、照顾者角色和医生角色的交织影响,以及政府政策与资源受限所带来的社区康复公共路径受损3个方面,分析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区康复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消解路径等相关措施。
关键词:社区康复,医学社会学,污名化,病人角色,制度区隔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困境主题,本研究共选取3类对象:(1)选取2016年6月~2018年3月上海市H区8个街道的社区精神疾病患者38人,患者家属9人。患者入组符合国际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且出院居住在社区3个月以上,家属入组标准是与患者共同生活半年以上,两者均需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可进行基本交流,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2)从事社区精神康复的医生4人,精神科社工5人。(3)政府部门中负责精神卫生相关工作人员5人。
1.2研究方法
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运用参与式观察、个体访谈、焦点小组方法收集资料,从3个不同视角了解精神疾病患者面临的社区困境,具体包含:(1)康复亲历者视角,患者和家属的直接经验、感受和态度;(2)康复提供者视角,专业技术人员对于社区康复的态度、思考;(3)政策制定与执行者视角,政府部门如何看待社区康MedicineandPhilosophy,Feb2019,Vol.40,No.4,TotalNo.61551复的制度化建构以及法规政策层面所遭遇的康复困境。
2结果与讨论
医学社会学关注疾病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后果,将“患病”视为“越轨”[6]3,建构出了“正常/健康”之于“异常/疾病”的权力和权威[7]。谢夫强调精神疾病是一种无法用一般标签定义的“剩余越轨”(residualdevi-ance),最终形成了社会污名和患者的自我认同[1]。因而,精神疾病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生物学疾病,关于患者的社区康复,除了药物治疗促使的生理症状缓解外,更与其家庭关系、社会网络、公众污名、自身耻感及社会文化制度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的精神病学模式缺乏社会和心理支持以及医学人文关怀,社区康复面临诸多困境。
2.1污名化:影响患者社区康复的社会表征
关于精神疾病的污名自古有之,但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戈夫曼[8]3-5提出,将其定义为“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克里根(Corrigan)[9]进一步强调了污名本质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身份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定义了谁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并决定了某一特性在某一既定背景中是否受损。因而,精神病人是一个充满隐喻的社会身份,精神疾病污名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对于心理和行为疾病患者以及残疾人群而言,其身心康复和社会融入的最大阻碍就是社会施予他们的污名和与之相连的歧视。”[10]精神疾病污名的长期存在,造成患者不仅面临疾病症状引起的种种问题和困扰,还要应对公众对他们的偏见、歧视和排斥,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伦理压力和道德困境,社区康复与社会融合进程缓慢。污名阻碍患者的社区康复,其客观后果体现在一旦做出精神疾病的诊断、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公众便因刻板印象而对患者及相关群体产生歧视、排斥与隔离,导致社会网络断裂、社区康复举步维艰。医学社会学认为“污名化是影响患者生活的核心力量”[6]124,精神疾病的社会属性体现为一种污名化的符号暴力,导致患者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社区是患者康复的主要场所,但公众由于社会刻板印象对患者充满恐惧,普遍认为应将患者加以隔离,不愿与患者交往,导致社会网络断裂、社区康复举步维艰。一位患者讲到自己出院后经历:“从精神病院回来后邻居都躲着我,见面也不会与我打招呼,如果我因为别人的冒犯生气了,也会被人说‘是不是又发病了!’现在真的过得太痛苦……精神病这顶帽子再也摘不下来了!”职业康复是患者回归社会、实现真正康复的重要环节,但污名与歧视导致职业康复停滞不前。工作前发病的患者,即便康复也甚少获得工作机会;工作中发病患者也面临被企业辞退、即便康复后也难以返回职场的处境。“作为一个社工,我们针对社区康复状况良好的人组建了职业康复俱乐部,希望帮助他们走入职场真正回归,但还蛮受打击,之前我帮一个患者介绍了份共享单车搬运的工作,已经和工作人员联系好了,也通过了面试,但最后审查时听说患者以前住过精神病院,他们就找理由拒绝了,作为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职业康复实在太难。”一位社工讲到患者由于污名化在职业康复中面临的巨大困境。污名化的主观后果体现在:一方面患者由于恐惧污名带来的伤害和歧视而拒绝精神科的诊断与治疗,社区患者经常通过拒绝服药、拒绝社区康复、拒绝医生随访等行为否认精神疾病诊断和精神疾病患者身份,其结果是社区治疗和康复难以持续进行导致疾病复发,反向加重污名。同时,社区患者因担心遭遇来自社会、社区等多方面的污名与歧视而不敢把病情告知亲属,或因恐惧周围人知道其诊断而躲避社区康复资源,面临内心苦闷、情绪低落却无处述说之情境。“作为H区最大的街道,目前生活在社区的患者有800多人,但是我们街道阳光心园(注:精神疾病患者日间康复机构)却只有7个人,我们也积极动员社区里状况不错的患者来这里康复,可是大部分患者和家属都拒绝了,生怕来这里会被周围邻居知道生了这个病,怕被人瞧不起。”一位负责社区康复机构日常运作的工作人员无奈表示。另一方面患者在精神病院和精神科医生的权威规训下,在社会交往世界的实践中、在社会大众的污名评价中,强化了关于精神疾病标签的自我认知,内化成自我耻感与患者身份的自我认同,将“真实自我”与内心需求与感受隐藏起来,以一种“假象自我”和“分离自我”与外界世界接触[10],影响其权力意识的形成和自我话语的表达,形成社会性身份的恶性循环,导致社会退缩和功能受损。
2.2不同身份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社区康复的内在因素
帕森斯提出“病人角色”理论,指出患病不仅是体会患病的生理状态,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个社会角色,涉及一系列程式化的期待,这一期待能够定义与病人身份相适应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既为病人本身,也为与病人互动的其他人[6]112-114。围绕着精神疾病患者的病人身份,主要有三种角色。一种是病人角色,精神疾病患者病人角色的主导性与病人身份的固着性,严重干扰患者的日常生活,一旦被确诊很难消除精神病人的身份标签,在其角色丛中处于主导地位,定义了他当下的价值与意义,并相应管理着他人所形成的印象[7],使得患者被排斥、被孤立、社区康复困难。大众普遍认为“精神疾病难以治愈,甚至有人将精神疾病描述为绝症,认为根本无法治愈与彻底康复”;“精神疾病患者都是暴力的、恐怖的、难以靠近的,都是肮脏的、邋遢的、懒惰的”等社会化印象与期待。对于患者而言,往往会将这些外在期待转化为内在想法,因为精神疾病是难以治愈的,所以52MedicineandPhilosophy,Feb2019,Vol.40,No.4,TotalNo.615缺乏康复动力;因为患者是暴力的,所以逃避社会交往;因为患者是无能的,所以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同时“继发性获益”使得康复者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保持病人角色,从而获得正常责任的豁免和病人通常获得的其他特权[6]112,利用病人身份,按照与角色相期待的社会规范行为,将自身失败合法化,不愿进行社会康复。二是照顾者角色,照顾者在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时,呈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是“包揽”,把已经回归社区的患者仍当作病人和无法自主生活的孩子看待,即所谓的“依赖性儿童状态”[6]114,容忍患者不成熟甚至幼稚行为,包揽患者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通过访谈,了解到造成患者社区康复缺乏动力,既有客观上长期服用精神科药物会导致患者思维迟缓、行动缓慢、精神状况不佳;也有主观上的因素,照顾者一方面心怀愧疚而对患者过分宽容,包揽其康复过程所需掌握的各种事务,“生了这种病是老天在惩罚我,只要孩子开心,我做什么做多少都愿意”是许多照顾者面对康复者时的愧疚心态;另一方面,患者的不佳状况使得他们经常被看作是无法自理的孩童,“我担心哪天走了孩子怎么办,也希望他能学着烧饭,照顾自己……但是他有一次差点把房子给我点了,哪敢还让他再弄”,许多照顾者因担心出现纰漏不敢也不愿为其提供康复机会和路径。另一种是“放任”,就家庭外部来说,戈夫曼[8]43指出污名具有从污名携带者向其近亲传播的趋势,“连带污名”使得家属在照料患者的过程中亦遭受耻辱而拒绝承担照顾者的角色或拒绝患者接受社区康复服务,“觉得精神病人的家人也都是精神病人”是许多照顾者在社区中经常遇到的情景;就家庭内部而言,照顾社区患者是一项长期的、极耗费人力财物的活动,但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使得病情反复、康复周期漫长而成效不显著,导致家属陷入无止境的照顾负担中而放弃患者的治疗与康复。三是医生角色,帕森斯指出医生的角色就是把病人送回到正常功能状态,社会还把社会控制的功能注入到医生的身上[6]113-116,关于精神科医生的社会控制功能更为明显,社会对精神科医生的期待就是控制患者症状,确保不发生肇事肇祸事件。在对精神科医生的访谈中,有医生这样描述自身角色“既要能文又要能武,‘文’指的是对患者的精神症状充分了解并进行治疗与康复指导,‘武’则指在患者发病期间进行必要的约束保护”,由此可见,精神科医生在医患关系中不仅承担着治疗者的角色,同时也是控制越轨和执行规训的手段。社区康复中医患关系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情境是患者和家属由于拒绝精神科医生的控制与规训、否定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拒绝社区医生提供随访与康复指导;另一种情境是患者对医生权威的情境性依赖,医患关系的“主动—被动”模式压过了“双向参与”模式[6]127,患者过于遵从医生权威,缺乏主动康复意识。医患关系的这两种状态均不利于患者的社区康复,随着现代精神医学和康复技术的发展,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方法和途径不断完善,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就精神科医生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精神医学诊疗模式与心理-社会模式发展的不平衡,过分关注药物治疗而忽视心理和社会康复;过多承担社会控制者的角色,关注患者是否发病、是否需要紧急送治,而忽视日常康复,“保证患者在社区稳定,发现患者病情不稳定的情况及时上报,尽可能住院”是社区医生对自身工作的普遍定位;照搬国外康复技术、康复理念落后,如在社区康复中引进程式培训法和森田治疗法,但并未做出本土化改良,亦没有做到“以患者需求为中心”开展康复活动,导致患者参与康复活动意愿不强,社区康复效果不理想。
2.3政策与资源受限:阻碍社区康复的公共路径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逐步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网络,为患者营造“无缝化”的精神卫生服务,社区精神病人的防治与康复已从最初的原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为主管单位三部门合作到残联、民政、教育、综治等部门相继加入,由医疗卫生人员以治为主、公安部门以管着手到现今吸纳职业康复师、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等群体参与,逐步为患者提供多部门、多元化、多人员的社区康复服务。但是受传统精神医学影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面临康复力量与管理力量、康复力量与社会对患者的污名这两种张力,其中政府管理、社会对患者的污名这两股力量极大影响了康复力量[11]。首先,精神卫生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其一,政策制定层面,管控与康复的博弈中管控力量仍发挥主导作用,不仅缺乏法律政策对患者康复进行保障,而且仍以“院舍化”思维为主,以“社会管控”的角度介入社区康复。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制定时具有浓重的管理色彩,相较于其他国家立法进程缓慢,直至2013年才正式实施第一部关于精神卫生的法律,相关法规关注对象仍以严重精神障碍者为主,对如抑郁、焦虑等心理行为问题和常见精神障碍患者关注较少。其二,政策执行方面,政策制定的导向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时管控和区隔想法盛行,且部门间各自为政,职责尚不清晰,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和发挥各自优势,社区康复的连续性难以推进。“国家对我们上海精神卫生的考核是一票否决制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是否发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如果发生不要说社区康复,所有工作都是白做,我们的首要职责将社区患者肇事肇祸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一位负责精神卫生的政府官员强调对社区精神病人管控和维稳的重要性。其次,我国精神卫生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平均2.03名/10万人口),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12]。政府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投入不足,导致其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投入经费不足、康复机构不完善、康复场地短缺、康复人员数量少且能力参差不齐、康复理念与设施落后、康复活动受限等。H区的社区康复方式主要呈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日间康复机构中康复,H区目前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约4500人,但日间康复机构只有8个,负责日常运行的工作人员16名。参与式观察过程中,了解到日间康复机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首先,管控逻辑主导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导致康复学员真实需求难以满足,机构中的许多课程设计并非从学员角度出发,也没有做到个性化康复服务的提供,同时对于学员需要的工疗、农疗等职业康复服务因社会污名、资金不足、资源短缺等原因被阻断。其次,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日间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残联指派的躯体残疾人士,政府对其工作职责的定位是看管机构中的精神障碍人士,社区医生到机构主要是了解学员药物服用情况,关注点是患者躯体症状的改善,而提供心理与社会康复服务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则主要是通过志愿者、实习生身份进驻,康复活动缺乏连贯性、康复技术缺乏先进性。社区康复的另一种形式是居家康复,居家康复服务提供者主要是由社区精神科医生及精神科社工组成,根据患者疾病评估等级决定上门随访次数。一位精神科医生描述道:“我们也知道社区康复是患者回归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没办法,我们人太少,不可能所有有需求的人都访视到位。”居家康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由于服务人员限制,有社会康复需求的患者因病情稳定无法获得专业服务;二是家庭系统介入难度大,康复情境受限;三是康复内容上主要关注患者服药情况,忽视患者其他方面康复需求。
3结语
我国目前的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体系尚不健全,仍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精神疾病的社会偏见与排斥使得患者的就诊、治疗和康复更加困难[13],患者承担着精神症状、心理压力、社区疏离的三重压力。随着我国社区康复体系的完善,精神卫生领域从服务理念、服务场域和服务方法渐进式改变,逐渐关注精神病患者的能力发掘和社会功能发展,强调患者优势和个人能力的发展[14]。但精神疾病的社区康复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对于患者而言宏观的社会环境、中观的家庭系统和微观的自我认知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入和融合。推进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道路险阻且漫长,个体层面需要注重患者的增能与赋权,打破以疾病为中心视角,注重患者个体化需求,转变康复理念,走出固有社会角色定位,增加自我效能。但只是致力于改变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够的,必须伴随着社会中机构和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导致收入、教育、权力和医疗不平等的因素的改变[15],才能破解消除精神疾病污名与歧视的迷局,推进法制化进程和调整政策导向,从而构建多部门间的联动合作,打通患者社区康复的桥梁。
作者:谢迎迎 汪作为 范明林 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