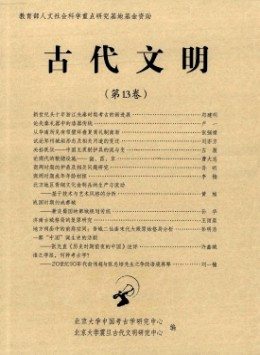古代扇器审美演变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代扇器审美演变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关键词:中国古扇;器;物;观念;美
中国古代的扇子历史悠久,不仅浸润着中国的传统思想,还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千百年的历史中遗留下了许多与扇子有关的轶事,如周王喜执雉尾扇、孔明手摇羽毛扇、班婕妤寄情合欢扇、秦少游与黄谷扇上斗诗、苏东坡书画咏扇等,这些历史风流人物引领着时代的风尚。此时手中的扇器,俗称扇子,它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作为消暑纳凉的器物,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文化、思想的观念物,这个观念物已经超越“器”“物”之限,成为一种有形的无形物,通过器形和扇面,进行移情寄托,并衍生出审美方式和艺术样式,使该器物不断倾向美的精神追求,最终升华为象征精神品质的文化之器。
一、古扇作为引风遮日的器具
在中国,扇子最早是作为引风遮日、消暑纳凉的器具来使用的。器,通常指具有实物之形的象,所谓器者,乃物之象,何谓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可以说,世间万物,只要有形象,都可谓之器,故清代学者段玉裁指出:“器乃凡器统称”。中国最初的扇子,只是为驱赶炎热而出现。史书记载:“尧时曾做物,吊于室中,动摇生风”,可见尧时已有了扇子,说明中国古代扇器历史的源远流长,这也是扇器出现最早的记录。在《淮南子•人间训》中则记载了周武王利用扇子招风纳凉的功用来救助中暑之人的实例,“武王荫喝人于抛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1]。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羽扇,“楚襄王时始用羽做扇”,又称“翟扇”,说明战国时扇器已经有了多种变化。扇器作为古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不但记载于史书中,还出现在实物器皿上,如四川百花潭出土战国时期的“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上面记录着贵族生活的场景,其中第二层发现有手持长柄大扇的侍者,面前有两人举觯进献,这也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扇子图像。在中国,扇子的器形种类样式繁多,略统之,从其形制上,可以分为团扇、折叠扇(又名折扇)等,它们形制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举或握。从其制作材料质地上分,可以分为竹扇、羽扇、纹扇、鹅毛扇等;在扇面材料上,有布、纸、绢、丝、蒲等;还有一些雅好者,在丝扇或布扇上,编织、刻画或上漆,经常于扇面上绘以装饰图案,以画山水寄托野逸之情,以竹梅抒写心志理想,更有甚者,在扇柄的制作上不吝成本,素则竹木,贵则象牙金石,形成不同类型的竹扇、玉版扇、羽扇、团扇、福寿扇、蝉翼扇、折叠扇等。这些扇子的使用功能,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说文解字》中“器”的定义:“器”者,释为皿也,而走向了“象征物”的概念。
二、器的神化与物的象征
物,与器相比,常作为对应物出现在中国儒道思想的文化观念中,通常指代自然之物。而“自然”常常意味着一种“天人合一”道的最高境界。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因此,无论在儒、释、道中,都有把“物”尊为“神灵”的传统,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导致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以致于人们认为,自然百物背后自有神灵,而这些神灵实际上组成了“物性”。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物”实际上有一股神性的和谐统一,正是由于这些万物神性的和谐相处,“物”超越了“器”的机械性和无机性。这种“物”的神性的潜在性,形成了“器”的道德礼制,以器物的形状和纹饰来象征特定的礼制内涵。如青铜时代后母戊方鼎是由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腹壁内铸刻有“后母戌”三字,作为祭祀旌功记绩的礼器,是对物“神性”的模仿,它已脱离了实用功能,折射出“别上下,明贵贱”身份等级的天然决定性。其实,在中国古代扇器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物”的神性象征,扇子在古代社会,除了用来引风遮日、消暑纳凉的基本功能,还有一些扇器已经演变成了“礼器”象征。如有学者认为,扇子最初称为“五明扇”,由虞舜所制,晋代崔豹在《古今注》中记载,“五明扇,舜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2]。从秦至汉都在沿用,此时扇子已作为向外界吸纳贤才的主张,到了魏晋时期,开始作为帝王或贵族的仪仗之用,在唐朝社会制度里就有关于“其人君举动必以扇”的记载,以此来象征帝王尊贵威仪。如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唐太宗在众侍女的簇拥下,端坐在步辇之上,宫女举着“仪仗扇”在其身后,画中扇形巨大,占据画面很大的比例,画家通过这种方式把大唐王朝的威严、仪制外化于大扇之中。到了宋代以后“掌扇”[3]作为装饰,被放置在宝座后的架上,演变成了汉族民间婚嫁时使用的仪仗用具。在古代文献中还有关于扇器被作为丧葬之用的记载,在《礼记•檀弓上》中的“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塑周,殷人棺撑,周人墙置霎”,而“霎”就是礼仪之扇,在中国的儒家礼仪思想中,强调丧葬之礼,必须符合与生前身份相当的礼制规范,这些都能从礼扇的仪制中反映出来。
三、观念作用下扇由器向物的转变
扇子由实用性转向象征性的过程中,显现出古人通过扇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也是传统伦理道德投影下的观念思想,如清代诗人、戏曲家孔尚任的《桃花扇》,这里的扇子不是讲述扇面是如何绘画而成的,他实际是把“桃花扇”作为一个象征物,以爱情故事为引子,来写家国兴亡,如研究者所言:“来引述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4]。“同时也揭露了弘光政权衰亡的原因,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5]。实际上,从中国古扇形制与扇面内容的发展,也可以看到观念在其中的作用。如在唐代之前,多以礼仪为尊的“礼仪扇”,随着儒、释、道家的观念和审美发展,到唐时,扇子开始出现在各个阶层中,特别是团扇更是广泛流行,诗人王昌龄在《长信怨》中写道“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7]。而团扇,因其形状似团圆明月,暗合中国人合欢吉祥之意,又名“合欢扇”。折扇在宋元之际的朝鲜已开始出现,明代永乐年间,朝鲜进贡折扇,成祖皇帝十分喜欢,命工匠仿造,从此折扇也在文人志士中流行开来。折扇又称聚头扇,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故又称“撒扇”,它携带方便,出入怀袖,扇面书画,扇骨雕琢,是文人雅士的喜爱之物。随着宋、明、清文人画的逐渐兴起,折扇扇面画开始蔚然成风,折扇扇面上宽下窄的形制要求艺术家必须精思巧构,笔随意转,化有限于无限之中,追求一种自得其乐的心学方式,来表现文人雅士闲适自由的生活艺术,备受推崇。除折扇外,据学者考证,还有一种折团扇,也被称之为高松扇。其是一种打开如团扇,折叠如折扇的器形,在北宋时,由高丽传入中国,元丰六年,高丽国王王徽卒,宋神宗派遣杨景略、王舜封、钱勰、宋球前往高丽吊祭,派遣使团于元丰七年归来,松扇即此行所得。钱勰归来后,将松扇分别赠友朋,首先得到高松扇的是张耒,还有黄庭坚、苏轼等[8]。
四、观念由扇子的美来体现
对于中国古扇的形制,如团扇、折扇生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书画艺术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正是中国宫廷绘画和文人思想成熟的关键期。此后古扇以一种“形制较小,物象不多,精微含蓄,寸瑜胜尺瑕”的方式传达出“宋人穷理,格物致知”的追求,中国书画与扇面的结合,成了中国艺术宝库中别具一格的艺术样式———扇面书画。扇面书画艺术在构图上突破了以往立轴、卷轴的形式,既不失严谨法度,又意趣生成,并通过题写诗文能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其注重艺术性与诗意性的表达。通过这种书画美,也可反映当时的社会观念及审美趣味,如五代时“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的艺术风格,体现在黄筌之子黄居寀的扇面画中,《晚荷郭索图》描绘了三四枝芦苇、荷叶、莲蓬、一只河蟹爬盘于残荷之上,让原本秋意萧瑟冷寂的气氛中多了一丝诙谐的生动感,动静结合不乏趣味;如赵佶《桃鸠图》中,一桃枝上栖一鸠鸟,花枝细墨钩勒,栖鸠自然生动,以生漆点睛,亦具神采,整体设色华丽,即在方寸之间感受到春意盎然的生命之趣,用自己的独特“美”感来营造理想世界。明代中期不论是出于创作还是欣赏,吴门人士引领着折扇的审美趣味,如文征明《桐荫小憇图》所绘石树苍雄,高士论道而坐,小童归来,画面空远,风格高雅;清代王翚《松壑云泉图》扇面设色,高山浩瀚、烟云缭绕、丛树茂密、泉溪奔流,呈现朴茂静穆、情景交融的天然意境;恽寿平《国香春霁图》扇面以“没骨”绘兰竹,敷色清新明丽,笔墨灵动洒脱,既生动又雅致,寥寥数笔却活色生香,隽雅脱尘。明清文人画家通过在凹凸不平的扇面上抒写林泉之志,寄托一种隐逸淡然的人生态度和表达自我的精神追求,在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美学之间,笔墨创造了意境,意境激活了笔墨,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美的形态。
五、结语
贡布里希说:“整个艺术史不是技术成熟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9]。在中国古代扇器的发展中,随着文人画家、职业画家的加入,使得扇面绘画成为绘画艺术中独特的门类形式,完成了从“书画之于扇面”到“扇面之于书画”的演变,扇子也逐渐从一种实用“器”转向文化意义和审美功能。时至今日,作为权威象征的礼扇已经进入博物馆,而作为使用功能的扇子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中国古扇的这种“器以藏礼”的方式,将扇子文化深深地纳入中国传统思想的体系中,并且被赋予了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在当代,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兴起,如何把抽象的中国文化理念经过不断的实践与调适,通过阐发与再阐发,赋予其更深的思想内涵和找到展示其精神需求的视觉呈现方式,扇器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其独有便利性,生活的实用性,文化的象征性,器、物、观念和美的统一性,将会使具有千年传承的扇器重新散发出中国文化的璀璨之美。
参考文献:
[1](汉)刘安编,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05.
[2](晋)崔豹.古今注(卷上)[M].四部从刊.三编景宋本。
[3]汪思源.一生要读的国学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17-318.
[4]徐宁.编南京历代名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60-61.
[5](宋)程大昌,周翠英注.演繁露(卷十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6]诗词名句网[EB/OL].
[7]鄧淞露.以高麗松扇與北宋士人相關唱和为例[J].新国学,2018(1).
[8](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故事[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44.
[9]王志强.山水寄情笔墨抒怀明清文人山水题材折扇画[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7):30-37.
[10]吴彦颐.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研究[D].东南大学,2018.
[11](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上、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9.
[12]钱公麟.扇子[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13]杨祥民.中国扇面书画艺术的历史演变[J].书画世界,2007(4):84-86.
作者:孙文娟 单位:上海大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