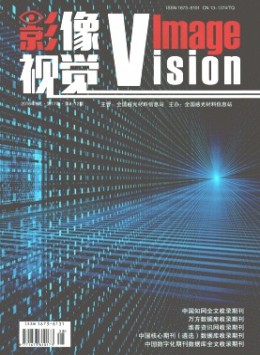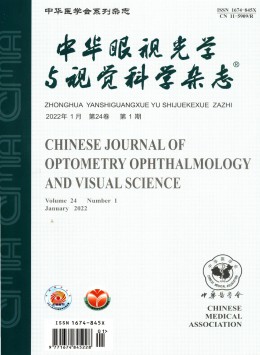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扁担舞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扁担舞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广西壮族扁担舞因其以扁担为道具而得名,古代称为“打舂堂”,现在称之为“扁担舞”,壮语俗称“谷榔”、“打榔”。扁担舞主要是模拟人类生产劳动的场景,它流行于广西红水河畔的都安、马山和桂西的百色、巴马一带,尤以马山、都安最具代表性。扁担舞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插秧、收割、打谷、舂米、织布和打布头等,也展现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欢乐情绪。每逢年节,当地妇女们便手持扁担,涌向街头巷尾、晒谷场,跳起扁担舞。他们两人一对,围在长凳或舂米木槽旁,边击、边歌、边舞,用扁担两端互相撞击或敲击长凳,发出咯嗒咯嗒的和谐音响。这种节奏强烈有力,声响清脆高亢,舞姿变化多样,富有浓郁的劳动生活气息。
舞蹈视觉人类学作为舞蹈民族志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可以用来描述或解释舞蹈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
(一)壮族扁担舞的视觉色彩艺术效应
根据托马斯•杨和赫尔姆霍三原视觉理论,“将红、绿、蓝三颜色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实际上,人类眼睛主要有三种感色细胞:第一种主要是对红色作出反应;第二种主要是对绿色作出反应;第三种主要是对蓝色作出反应”。[1]这些感色细胞体系活动的不同方式可以使人类感知到不同颜色。这一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科学家证明了人类视网膜中主要含有三种类型的视锥细胞,一种主要是对长波红色的反应,其次是对中波绿色的反应,第三种是对短波蓝色的反应。如果我们把“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混合在一起,那么显示出来的是白色。如果我们只选择其中三原色红、黄、蓝的话,其结果也是白色”。[2]
如果我们只选择三原色中的两种颜色的话,那么我们就能见到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颜色。“三原色视觉理论解释了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所发生的变化”。[1]视觉与大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眼睛对各种光波和视觉图像产生反应,并把它们复制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破译神经信息,即通过感知舞蹈服装颜色、道具形态,服装与道具质地和舞蹈运动形式及动作技巧,形成视觉神经感色系统。壮族扁担舞演出者的服饰道具均以红、黄、蓝三原色为主色调,分别再在服装上镶嵌以白色和黑色;道具底色是一种深板栗色调,目的是以三原色为主色调对观众能产生一种直观的视觉反应,即视觉心理反应。扁担舞的表演道具由舞蹈者手持一根扁担,扁担多用毛竹削制而成,长短各异,一般长约1.5米,两端较窄,中间较宽。男女分别身着黄色和红色服装,手持黄色扁担相向而立,围着一条长一丈多、宽一尺的板栗色为底面的木槽或板凳(凳长250厘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在木槽和板凳上绘有一种原始狩猎巫术祭祀图案,男女同声呼喊,上下左右相互打击,边打、边唱、边舞,时而用扁担两端互击,时而敲击长凳或长方形木箱,时而敲击地面,模拟农事活动中的耙田、插秧、戽水、收割、打谷、舂米等农耕劳作姿势或动作。
在扁担舞中,男性舞者以黄色调为主,女性舞者以红色调为主。舞蹈者使用扁担道具则以纯黄色调为主,木槽和板凳的颜色以深板栗色作为底面,上面绘有原始狩猎巫术祭祀的动物图案。在表演过程中,扁担舞出场用鼓、锣、镲、竹筒等打击乐作为伴奏,节奏明快、气氛热烈。如舞蹈者一出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这种铿锵的打击乐,无论是扁担舞的单打节奏,还是男女双打节奏,其舞蹈运动节奏感明显,并配以红黄两色服装相对应,说明颜色是运动的,它能把观众带到不同时空场域。因此,色彩视觉效应成为自由视觉空间运动的流变形式。在舞蹈视觉色彩图像中,是以“追求色彩振动”为视觉空间主题的,包含了不受特定视点约束的流变空间造型。但西方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把三原色视觉理论解释清楚。“神经生理家和心理学家尤恩•海瑞从纯色彩学理论方面进行考祭,并把三原色视觉效应理论作为色彩理论的基础”。[1]观众在观照舞蹈者服饰和道具三原色过程中,尤其是在自然光线下能产生不同舞蹈视觉效应。严格地说,它是处在舞蹈视觉色彩效应不断变化的时空流变状态之中,而不是一种恒常的舞蹈视觉现象。三原色“这种色彩的动感并不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个人感觉,它们和现实之中显示出色彩物体形态表情相吻合,并且各自都具有一种能被普遍理解的性质和一种普遍的适应性”。[3]210
“扁担舞”的板凳和木槽极类似于后现代绘画艺术,以红、黄、蓝三原色作色彩基调,结合绘画平面艺术手法来表现舞蹈立体流变于运动空间所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舞姿,展示出一种绘画色彩与舞蹈动作相结合的后现代审美艺术的心灵观照。“关于色彩艺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歌德的色彩研究就已经超出了他的同时代学者。在色彩感受过程中,色彩对事物的美感能产生审美艺术判断和审美价值取向”。[3]210尽管这种判断是一种趣味性的,抑或是一种艺术性的,但是这种趣味性或艺术性是可传递的,并非是自我封闭的。我们强调趣味性或艺术性审美判断与艺术审美价值取向表明了艺术主体性和创造性。如果色彩图像不能在观众的主观条件下设定视觉图像的“同构性”,也就不能说明视觉图像传达可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壮族扁担舞的视觉时空艺术效应
扁担舞在表演过程中,根据壮族农业生产活动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耙田插秧、戽水耘田、收割打场、舂米尝新。就如农民“犁地打牛”节奏一样,生动地表现了壮族劳动人民耙田农耕动作。“从美国学者格尔兹解释人类学角度来理解舞蹈视觉空间构成的视觉艺术图像,它具有实证性和多样性”。[4]
舞蹈者把“耙田插秧”、“戽水耘田”、“收割打场”和“舂米尝新”等不同劳动的自然场景作为视觉三维空间艺术的认识,通过不同舞蹈视觉空间主体动作的延续性和色彩的流变性,构成一个三维空间主体行为艺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交织在其中的话,就会构成一个四维时空流变,这才是艺术行为空间更为真实的性质。所谓艺术的时间性,即指艺术表演的历时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和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可复制性。“在艺术中是一个强化的过程,它是由个别向普遍、由主观向客观、由事物向自我本质的转化,这一事实的发现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3]
壮族扁担舞高度集中地表达了壮族农民四季劳动生产过程,也表达出人们欢庆丰收的喜悦心情。打扁担是以扁担和长凳为主,参加活动者是以妇女为主,甚至全部是女的。打法轻巧,花样也较多而舞姿轻盈美观,使人观之有五彩缤纷之感。扁担舞的基本动作是舞伴互击扁担,舞者以扁担敲击板凳或舂槽。起舞时,舞者成双,两两相对。有4人击打节奏,亦有6人、8人,10人、20人不等的“翻天覆地”的节奏等。
从壮族扁担舞的视觉空间结构分析来看,这里包含有两个时空层次的内涵:一是指扁担舞的舞蹈者时空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二是指舞台为舞蹈者提供静态时空艺术审美观照。前者是指舞蹈者运动所构成的一种流变的时空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研究者假想中的一种不同形态的时空艺术说明舞蹈艺术价值的存在;后者作为舞台静态时空艺术为舞蹈者提供一个客观实在的固定表演的艺术空间,或者说是一种静态时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审美艺术观照。当然,把扁担舞作为时空艺术,可见这个静态艺术时空与时空艺术运动相叠合所产生的强烈的艺术冲击效应。扁担舞在各种打奏法交叉进行时,发出的“咚咚、嗒嗒”、“得得”、“棒棒”的和谐音响;舞者时而双人对打,时而四人交叉对打,时而多人连打产生错落有致、此起彼伏的动作,使整个舞蹈节奏明快、舞姿矫健、优美清新,富于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表演者在高潮动作时发出“嗨!嗨!嗨!”的呼喊声,伴随着打击乐器的强烈声响,形成独特的节奏,激发人们热烈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一个民族的艺术震撼力,同时也说明壮族人民勤劳勇敢、性情豪放,体现出壮族人民乐观奋进的民族精神。
二、舞蹈视觉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的物像并不是一个平面的二维图像,而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图像。它具有高度、宽度和深度。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通过舞蹈艺术的“移情”作用,使这些具有高度、宽度和深度的立体艺术形象产生某种位移,这样便于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壮族扁担舞的艺术移情机制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审美感受。当这些图像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玫瑰形象时,或者说是一朵红色玫瑰形象时,它能使你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艺术移情作用,它使你无法用一种语言来描述它的香味和色彩以及这朵玫瑰身上锋利的锥刺。虽然作为玫瑰形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清晰的概念,但“玫瑰”作为现实事物是绝对具有显著特色的。舞蹈民族志田野观察本身就是一个视觉艺术过程,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田野“视觉文化”或“视觉艺术”过程。在这里我们避开“田野观察”一词,改用“视觉人类学”或“视觉民族志”一词,这样避免了民族志田野观察中所谓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某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来自欧洲殖民主义时期不平等的权力格局的重要表现。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蒋浩副教授首先提出:“舞蹈视觉人类学”和“舞蹈视觉民族志”并非是原有西方的“视觉主义”至上的历史产物。[5]
我们所揭示的舞蹈视觉文化,是将民族传统舞蹈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视觉艺术进行田野深度观察,或者说我们运用舞蹈视觉人类学对民族舞蹈进行深度描述或者作为一种深层内在结构来解释。自然界中的色彩同样是一种最具有美感的分形,赤、橙、黄、绿、青、蓝、紫,就表现出一种色彩分形。如果说我们把不同大小空间嵌塞进不同的颜色,就会产生不同的色彩空间分形,同时也就构成了视觉色彩分形。色彩分形和图像分形是产生视觉美感的主要物质基础。舞蹈作为视觉艺术,除了身体动作的视觉动态外,服装、道具、化妆等都丰富了舞蹈的视觉美感和文化内涵。
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把“舞蹈视觉艺术”或“舞蹈视觉文化”作为获得知识理念的正确途径来加以解释,并着重强调舞蹈视觉民族志模仿客观对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舞蹈视觉艺术”或“舞蹈视觉文化”与“艺术模仿”使两者拉近了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时也避免了人类学者想象中的“田野观察”。舞蹈视觉艺术消除了人们对田野观察与“监视”的歧义,结束了田野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不平等的对话。虽然“观察”同样包含了“视觉文化”或“视觉艺术”的意思,[6]但是观察有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之分,有“局内”和“局外”之分,有观察对象和被观察对象之分,人类学家往往容易忽略“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深度观察,[7]尤其是对舞蹈、音乐和美术之类的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内部结构的分析,总是容易使观察者对被观察者带有某种歧视或歧义的理解。这就要求舞蹈家和人类学家之间要缩短原来田野观察与田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不平等的距离,要求我们提出“舞蹈视觉人类学”方法或者说“舞蹈视觉民族志”的概念与方法,并对当代人类学参与式观察进行必要的反思。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放弃对“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观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参与式观察在舞蹈人类学中的局限性和歧义性。所谓局限性是我们对“扁担舞”的动作节奏理解很难达到“文化持有者”的深层结构,即从“文化主位”到“文化客位”、从“局内”到“局外”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舞蹈视觉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调查对扁担舞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仍然是有限的。舞蹈视觉人类学者在进行参与式田野调查时,对“扁担舞”会生某种歧义性。这种歧义性是参与者或局外人对“文化持有者”所产生的某种文化距离,或者说是文化偏见,从而导致对异质文化的歧义。因此,局限性和歧义性是局外人对文化持有者的一种理解屏障并由此产生某种认知障碍。这种理解屏障和认知障碍将会直接影响“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的融合,也就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问题。
结语
壮族扁担舞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壮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扁担舞同其它舞蹈一样有着自身的演变轨迹、表演系统及其发展规律。它是壮族人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并健康地顺应其发展规律向前演进,使广西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和全面发展,以至繁荣昌盛。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