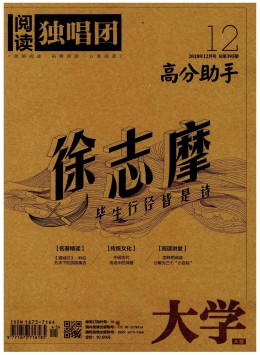大学跨学科组织创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大学跨学科组织创建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纵观当今生物医学领域跨学科组织,公认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先驱和典范当数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合作成立的“哈佛-MIT健康科学技术学部”(TheHarvard-MITDivisionorHealthSciencesandTechnology,HST),现又称为怀特健康科学技术学院[2]。HST是哈佛大学和MIT在生物医药工程等学科方面进行合作而成立的跨学科组织。哈佛大学充分利用MIT交叉学科的优势,以通过跨领域合作改善人类健康为研究宗旨,主要在生物医学成像、生物医学信息与综合生物学、再生和机能生物医学技术等研究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领域的合作研究将对生物和健康知识的进步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MIT自20世纪60年代进入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时代,如今已拥有70余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组织,如雷达研究组织、HST、计算机系统生物学研究所(ComputationalandSystemBiologyInitiative,CSBi)等[3],并在5个学院内部以及学院之间构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相互交叉的跨学科研究体系,为美国重大战略性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2003年成立的CSBi,作为MIT最具代表性的虚拟跨学科组织,是MIT最大的跨学科组织之一,其教育与科研成果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达到了领先地位。CSBi主要通过特定的技术平台把MIT的三个关键学科领域,即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三者交叉融合而展开大型跨学科项目合作研究,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复杂的生物现象进行系统分析与计算机建模,同时培养相关领域跨学科人才。在世界大学跨学科研究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又名“Bio-X”跨学科研究计划),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开启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生命科学跨学科研究领域已成为一个著名“品牌”[4]。
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创立于1998年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项目,主要涉及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生物科学三大领域,跨越文理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三大学院。其实质就是一个由生命科学与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机构[5]。Bio-X研究中心将基础、应用和临床科学中的边缘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从分子到机体各个层次的生物物理学研究,以实现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新的发现和技术创新。发展至今,研究中心已取得包括成功破译人类遗传基因密码,发展观测人体细胞在人体中如何活动的技术等众多的开创性成果,使硅谷的这所名牌大学在科学发现和教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欧洲,英国1990年已设立了包括牛津的分子科学与分子医学等17个研究中心[6]。2001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牵头成立了由英国政府的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生物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国防部共同组成的纳米技术跨学科研究伙伴机构(IRC),开展了前沿生物纳米技术方面的研究。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以工程、自然科学、生命与食品科学、医学与运动科学等优势领域,建立了与生命科学、营养和食品科学、生命技术学、生物信息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强有力的跨学科合作。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与管理,具有以下共性特点:①政府、学校宏观政策的支持是跨学科组织发展的保障基石。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2004年发表了《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报告;哈佛大学就曾明文对该校跨学科动议项目的政策扶持作了规定。②组织结构与管理合理,强调多学科组织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组织合作,如MIT与哈佛大学共同合作的“哈佛-MIT健康科学技术学部”。③注重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协同发展,如美国的HST就是主要通过研究影响疾病与保健的基础原理,开发新的药物与仪器,致力于培养医师-科学家,通过跨领域合作改善人类健康。④提供跨学科研究经费,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强调对多学科、跨学科和多机构联合的医学研究项目的资助,如2007年就给9个科学研究联合体提供了2.1亿美元的研究经费[7]。⑤多样化的激励措施,重视奖金发放和提供实践机会等。
2我国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组织建设与发展
我国学科交叉研究萌生于20世纪50年代,而80年代初召开“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基本就被认定为我国跨学科研究的全面展开。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学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建制开始引人关注。特别是我国“985”二期工程,为突出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问题引导,凝聚了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开展跨学科研究,着力建设了一批创新平台。目前“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是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中就包括大批生物学与医学创新平台的实体机构。2000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多年来,该中心将基础科学、技术应用和临床科学的前沿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单细胞原位实时微纳米检测与表征研究,数字化诊疗仪器技术研究,医学信号与图像分析研究,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生物学效应及医学应用研究等四大主要研究方向,建立了跨学科的实验室和研究平台,组织了30余个跨学科研究项目,取得了系列跨学科研究成果[8]。
同时,该中心注重各有关学科优势互补、相互合作,对来自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基础医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来自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等众多应用和工程学科的研究生,开展生物医学工程跨学科前沿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形成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培养出了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新型人才。200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至此成为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研究中心之一。2010年,基于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建立了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该研究所注重复杂系统的研究和学科交叉,并且与环境因素相结合,主要针对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研究领域作为重点和突破点进行系统生物学研究[9]。2004年,清华大学顺应跨学科研究趋势,改革科研体制,通过将分散于全校各院系的有关生命科学、医学及相关的工程学科统一组织和协调起来,重点支持和建立了包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在内的若干研究所(或研究平台),加强和促进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发展及其与其它工程学科间的交叉合作[10]。
同年,复旦大学组建生物医学研究院。作为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目前研究院以“转化医学”为目标,形成了包括疾病系统生物学、出生缺陷与发育生物学、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创新药物和结构生物学等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建设了功能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癌症研究、心血管研究、分子与细胞生物学、药物与结构以及公共技术平台等10个技术平台,建立了基础科学与临床需求的紧密联系,为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1]。此外,研究院重点把学校所属上海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化学系、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相关附属医院等院系等有机地穿插在一起,在疾病蛋白质组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肿瘤学、干细胞生物学、分子药理学等专业培养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研究生教育。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Bio-X生命科学研究基地”。2005年,与神经生物与人类造化学研究室重组成立“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现改为研究院),是继美国斯坦福大学后的世界第二个、中国第一个Bio-X研究中心[12]。2007年,学校又成立了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集生物、医学、物理、工程、数学、信息、计算等不同学科,集研究、教育、开发及服务于一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与开发的公共技术平台。中心立足于以系统生物学的方法为基础,致力于在生物整体水平、细胞和发育生物学以及单细胞分析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生物医学研究。同年,随着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Med-X研究院。Med-X研究院主要依托学校临床医学学科和理工科优势,涉及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四个研究领域,以解决临床医学问题为目标导向,进行前沿性医学科学研究,开发高尖端领先性医疗技术产品,构建国际化、多学科交融、多资源共享、多方位服务的开放式医学应用研究平台,建立医疗技术产品研发-技术转化-临床应用体系[13]。
3我国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组织建设困境与借鉴
从建设与管理实践看,我国依托大学建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正在遭遇重重困难和种种挑战,并突出体现在跨学科研究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障碍与缺失,跨学科研究的组织结构障碍与冲突,学科文化障碍与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缺失,跨学科研究的资源配置障碍与冲突,跨学科研究评价(利益)的障碍与冲突等方面。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大学教师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还不强;大学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跨学科研究缺乏支撑力和推动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竞争与合作的失衡,缺乏系统的执行架构和机制;缺乏跨学科研究改革与创新的切实措施和效率最大化的管理模式。在组织结构上,各学科仍相对封闭,跨学科研究的合作机制与条件缺失,学科间未能实现协调发展,跨学科组织内各要素尚不能完全产生协同作用,妨碍了跨学科组织系统的有序运行。在研究资源上,资源投入的主体和方式较为单一,力度小,持续性差,分散度较高,
忽视无形的“软”资源积累等等情况,学科建设没有形成开放大平台,学术队伍、实验设施、科研用房、学科组织及教育教学等学科构成要素尚未形成大规模、集团化攻关形态,资源配置的非效率问题尤为突出[14]。在研究评价上,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个体,轻集体”、“重智商,轻情商”等问题。综上,由于跨学科研究本身的性质及其组织管理环境如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评价体系、学科范式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导致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一直在困境中前行,徘徊于非可持续的发展困境之中,已经成为困扰大学跨学科研究与管理的瓶颈。进入21世纪,基因组学生命大科学的出现,脑与认知科学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和人类健康科学的热点与前沿,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融合,都将对涉及人口健康领域的生物医学带来重大变革。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解决生物医学领域重大问题的必然趋势。
对此,针对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存在融合不够多、研究领域不够宽、规模不够大等现实问题,我国应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关于跨学科组织建设经验:首先,需要立足研究与发展需求,科学定位组织的模式;其次,注重整合资源,强化制度保障,构筑实质可行的科研平台;再次,种子培育,精英领衔,协调管理,实施跨院系协调机制;最后,加强沟通,信息共享,构筑合作网络,建立完善灵活合理的组织运行机制。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