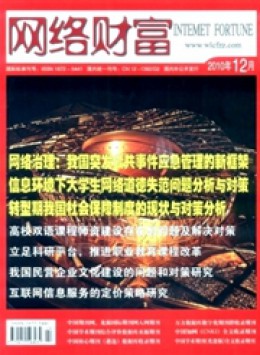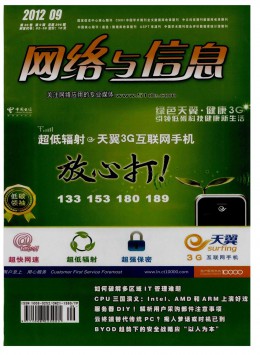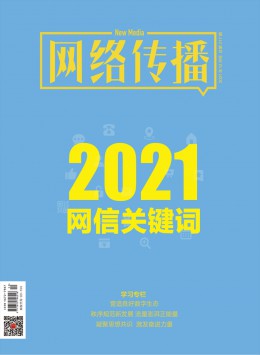网络传播中的言语活动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网络传播中的言语活动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视角,网络传播中的言语活动可以分为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分别指向符号(意义)的两端,关联不同的叙事方式,构成了网络世界的众声喧哗。从概念上厘清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有助于更清楚地掌握网络言语活动的传播规律,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述方式,进而为提高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效的语言学支持。
关键词:网络语言;网络言语;符号;能指;所指
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几乎每年都会有网络热词出现。它们不仅在网民中间广泛传播,有些还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所使用,甚至被收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三版)。这种语言现象,既让我们感受到了网民的智慧,也让我们看到了网络对语言的巨大影响。当然,网络热词也给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带来了挑战。而网络舆情的引导过程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一边是主流媒体苦口婆心地劝说,另一边则是自媒体中网民七嘴八舌的“众声喧哗”。这种情况,客观上形成了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网络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构成了一幅奇特的网络语言景观。本文从语言学、符号学和传播学等三个层面,对网络传播中的言语活动进行剖析,探讨网络言语活动的传播规律,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述方式,进而为提高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效的语言学支持。
一、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言语活动进行了二元划分,将语言现象分为语言和言语。索氏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则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一般来说,语言是稳定的,具有相对的静止状态;而言语因为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1],所以往往是异质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因此,言语相对于语言显得千变万化,无限丰富。李幼蒸教授将语言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性、同时性、结构性、形式性、自主性、齐一性、内在性、系统性、规则性、关系性、潜在性、静态性;将言语的特征概括为个人性、历时性、事件性、实质性、受制性、多样性、外在性、过程性、实事性、个别性、动态性。[2]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指的是传播主体共有的交际工具,是约定俗成并共同遵守的符号系统;网络言语指的是网民为了交际而使用语言的结果,更加注重语法、词汇的使用。语言和言语的上述特征在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对某一事件的叙述,网络语言更多地关注事件本身的结构和造成的社会影响,因此内在的逻辑比较严密、体系比较完整,篇幅也比较长;而网络言语则更多地关注个人在事件中的体验,因此叙事的形式比较自由活泼,看起来较少逻辑思辨。在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以前,网络传播活动因为没有网民的广泛参与,基本上处于单线传播状态,网络语言处于“霸权”地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网民在传播过程中的主动介入和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网络传播慢慢转向多项传播的状态,网民经常会发表一些具有即时性、碎片化和无深度性特征的言语,表达对网络语言“霸权”地位的反抗,有学者将这种反抗称之为对符号(意义)的恶搞和狂欢,认为他们以内容的多元化、语言的叛逆性和意义的拼贴来凸显其反理性、反本质、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特征,这种狂欢表现为炫耀性、碎片性、黑色幽默性和白色幽默性四种类型。[3]网络言语的形成并非全是偶然,某一词句之所以能成为网络流行语,除了简单形象、生动有趣外,更多地在于反映了某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在海量的信息中,只有那些最能触动公众心理的话语,才能迅速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和认可,进而爆炸性地传播开来。这一现象与后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不无关系。后现代主义否认真理及本原的存在,认为所谓的崇高事物和信念都是从话语符号中派生出来的短暂产物。实际上,索绪尔在晚年非常重视言语的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一部分接近语言,另一部分接近言语,是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被渗透到语言中去的那些现象的真正源泉”[4]。在索绪尔看来,言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语言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从网络言语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它在慢慢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尤其是在高校大学生中间,他们喜欢创新、追求时尚,“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5]因此,网络言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另一方面,网络言语又在丰富着我们的语言,如《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就收入了“晒工资”“房奴”等网络热词。由此可见,一些发展成熟的网络言语已被社会大众完全接受,由虚拟网络走进了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推动与丰富着我们的语言,这也正回应了索绪尔的初衷。
二、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的二元关系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推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学者赵毅衡指出:“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任何意义都必须要符号才能表达、传送和解释”[6]。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由所指和能指两部分组成。该理论认为就意义的传达而言,语言的所指面指涉意义的内容,包括符号所阐述的实在事物、符号使用者的心理概念,为符号的不可见部分;语言的能指面指涉意义的形式,包括声音、音响,是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层面。语言符号是概念和声音形象的结合体。符号学理论的首倡者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最初是任意性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任意性慢慢演化为约定俗成性,因此语言和言语在传统语境下,呈现为比较稳定的二元关系,如作为概念的凳子和作为言说的凳子。从符号学的视角来讲,网络传播中的网络语言更多地侧重于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主要指的是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和逻辑系统,讲究规则、秩序和严肃性,注重传播主流的、一元的价值;网络言语则更多地侧重于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主要表现为言语简洁、时尚、自由、犀利,具有无厘头的特征,注重传播非主流的、多元的价值,更打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社会化过程。当然,从理论上对能指和所指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揭示意义的生成过程而进行人为的区分而已,在实际的符号运用过程中,是不存在这种划分的,正如中国传统哲学里常说的“得意忘象”。在网络环境里,网络语言与网络言语之间不再是稳定的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关系,虽然所指在符号意义的传达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能指在网络环境里显然比在传统语境下更加强势,经常以一种链条的形式,对所指表现出强烈的殖民和覆盖,能指和所指之间呈现为拉康式的S/s。[7]在这个表述中,S表示能指,s表示所指,中间的横隔线则表示能指对所指的覆盖,让所有对意义的探寻只能在能指与能指之间周游,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8]。比如“豆你玩”“向前葱”,这种来自于网民口中的网络言语,对传统语境中的豆、葱等所指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解构,并且还衍生出了许多新的意义符号,给人一种此豆非豆、此葱非葱的感觉。尽管网络语言也一直努力捍卫自己的所指地位,但是以网络言语为代表的能指链,则在不断地挑战网络语言的权威,几乎每天都会有网络新词出现,不管多么严肃的话题,都可能被网络言语解构得体无完肤。虽然这也是当下互联网信息文化的真实写照,但是较之于传统语境,网络语境下所指与能指的游离关系由于缺少社会化的过程,可能暂时会因为能指的强势而带来新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的生成也深深地带有时代(事件)的烙印,或者说是一种短暂的社会现象。网民编织的各种网络热词,往往伴随着一些热点事件。这些词虽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网络事件的升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又会被人们遗忘。所以网络热词与网络热点事件之间几乎是同生同无的关系,故而其对网络语言的殖民,也只是暂时的。这种能指对所指不断殖民的文化景观,从学理上可以追溯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在网络文化世界中的映照。[7]继索绪尔提出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符号学以后,以德里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索绪尔符号学里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进行了破题,开展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和解构,以为能指腾出足够的位置和地位,并赋予能指足够的能量,让所指日益从能指的殖民中退出,因此在网络世界里才会出现“能指膨胀、所指丧失”的文化景观。网络上虽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网络言语,但是其究竟有何所指,意义何在,经常让读者无所适从,带给读者的却是内心的虚无,大家称之为信息快餐,后现代主义者则称之为荒诞。[9]
三、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关联的叙事方式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关联的是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网络言语关联的是以网民为传播主体的网络叙事或者碎片化叙事。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以宏大叙事为表征的网络语言,注意锤炼语言,讲究自己的语汇系统和逻辑系统。宏大叙事是指基于网络传播的个体化叙事,以网络叙事为表征的网络言语,注重网络词汇,讲究个体的情感体验。宏大叙事因为逻辑严密的缘故,容易给人一种死板的、老套的印象;网络叙事则比较随意,排斥一本正经的面孔,也不需要死板地恪守规则,抗拒主流价值和精英文化,对一切宏大的、神圣的、主流的叙事传统进行解构。我们通过一个禅师体对话,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两者的显著不同。禅师问:“一根鱼竿和一筐鱼,你选哪个?”施主说:“我要一筐鱼。”禅师笑道:“施主,你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吗?鱼吃完就没了,鱼竿可以帮助他们钓很多鱼,可以用一辈子!”施主说:“我要一筐鱼之后把它卖了,再买很多鱼竿。然后把鱼竿出租给别人收租金,再自己留一根竿。”禅师生气地说:“贫僧不想和你说话!”实际上,网络上像这类禅师类的对话很多,而且还会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在印象里,与禅师对话就是与智者对话,禅师说的往往都是一些人生的哲理和大智慧,但是在网民的调侃下,禅师竟无言以对。对此,已无法再简单地判断孰是孰非,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以网民为使用主体的、碎片化的网络言语对以宏大叙述为特征的网络语言的抗拒和解构,这也是网民为什么比较抵制诸如大道理宣传等宏大叙事的一个原因。宏大叙事和网络叙事分别构成了两个传播主体的话语表述模式,也建构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场。我们经常把传统媒体形成的叫官方舆论场,把网络媒体形成的叫民间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是大一统的体系,它有一个主旋律,一个意识形态,一个价值观,它的背后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更有数千年来承袭下来的文化;民间舆论场实际上比较散乱,由各种网络自媒体组成,一些人为了吸粉,提高点击率,往往采用夸张的表达,甚至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去叙事。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以宏大叙事为旨归的官方舆论场,其语言表述呆板、叙事方式单调、内容空洞无味。以网络叙事为旨归的民间舆论场,其言语表述灵活、叙事方式多元、内容鲜活有味,二者形成鲜明的反差。从阅读的视角来看,宏大叙事侧重于深阅读,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阐述,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去表述,而网络叙事更加侧重于浅阅读,不需要高深的哲学思考,所以网络叙事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旨在打破和颠覆传统的宏大叙事。在网络世界里,宏大叙事变得似乎与这个社会毫无关系,解构与嘲笑似乎成了网络世界的主旋律。对于解构,我们也要辩证地分析。事实上,就连解构主义思想家们也承认,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解构,比如德里达就曾提出“正义的不可解构性”,因为正义是对他者的无条件的义务或者说是责任,是一种“非对称的责任”[10]。因此,从逻辑上说,如果一切都可以被解构,那么解构也将归于虚无。所以,网络世界里不仅需要个体式的网络叙事,也需要集体式的宏大叙事。二者虽然话语体系不同,但在对意义的传达上却殊途同归,对于一个健康的网络叙事生态而言,缺一不可。实际上,就传播的效果来看,在互联网传播世界里,我们不仅需要有完整的宏大叙事,更需要大量的微言大义式的网络叙事,比如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拍摄的《老爸的谎言》等大量公益微视频,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来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方式,不仅赢得了市场,更赢得了口碑,这应该成为主流媒体提高话语权的新形式和新方向。
四、结语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既不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主体并不直接地与客体世界打交道,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去认识、理解和改变客体世界的。[11]因此,对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界定,与其说是个基础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命题。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作为人类言语活动在网络上的两极,对之进行辨析,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网络传播规律,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广大网民公民理性精神的慢慢培养,网络语言的使用会更加灵活、丰满和实在,将会涌现出更多建设性的网络言语,两个舆论场由此逐渐走向融合,我们的网络叙事生态一定会更加和谐与理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也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创新与完善。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52.
[2]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20.
[3]董燕,杨劲松.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符号学阐释[J].教育评论,2016(5):51-55.
[4]胡亚敏,闵建平.回到索绪尔[J].江西社会科学,2013(6):184-189.
[5]熊澄宇,孙晖.从符号学理论看网络传播[J].当代传播,2002(4):64-66.
[6]赵毅衡.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J].学习与探索,2015(1):54-55.
[7]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79.
[8]欧阳友权.网络叙事的指涉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04(3):23-29.
[9]方海涛.论自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价值嬗变[J].新闻界,2013(5):54-57.
[10]周志雄.网络叙事与文化建构[J].文学评论,2014(4):185-193.
[1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作者:方海涛 姚金兰 单位:嘉兴学院党委组织部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