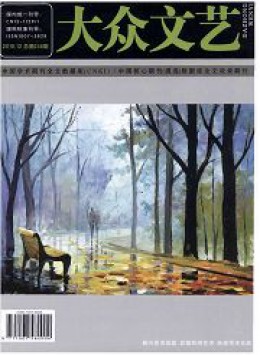大众文化理论下的网络文学IP热现象传播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大众文化理论下的网络文学IP热现象传播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随着《花千骨》、《择天记》、《甄嬛传》、《盗墓笔记》、《琅琊榜》等大批网络文学IP剧改编的热播,让大众对网络文学IP格外关注。这些网络上流行的知名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漫画、动画、游戏,都能在网络上吸引大家足够的眼球,原著粉丝的“自来水行为”更是为制作方炒热话题度,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话题度、受关注度高,以及本身受众众多,“网络文学IP”改编市场已然成为一个典型的大众文化传播现象。一方面网络文学IP热,其实是影视剧市场的商业资本为迎合大众口味,获取商业利益的结果;另一方面网络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文本属性、受众属性以及观感体验,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迎合低层次的文化需求,这是网络文学IP能够持续火爆的一个基础。
关键词:网络文学;IP;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传播学
一、网络文学IP的概述
网络文学,普遍被认可的概念是——以网络为载体发表的文学作品。最早以台湾作家痞子蔡在网络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是: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借助超文本连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段来表现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的网络艺术品。[1]IP,英文全称IntellectualProperty,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现在我们普遍认为IP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游戏或者漫画,它在网络上拥有足够的人气,已经具备有可开发的价值和持续影响力。以网络文学作品为例,它在网络上,首先已经积累相当大数量的读者,其文本的价值也同时具备可以后续衍生出电影电视、游戏、动漫,及其他周边创意等文化产业相关产品。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因此其本身自带网络属性,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而“网络文学IP热”现象主要归功于网络文学文本的趣味性、读群的普遍性以及观感的娱乐性,对于长期只能看日韩电视剧或欧美大片,抑或是重复播放令人审美疲劳的国产剧《西游记》、《还珠格格》等,本身具有一定的受众群体的网络文学改编剧会给大众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和娱乐体验。当大众愿意为网络文学IP消费时,商业资本就会对网络文学IP进行大规模投资,而这也使得《花千骨》、《择天记》、《甄嬛传》、《盗墓笔记》、《琅琊榜》等大批网络文学IP剧改编的热播,“网络文学IP热”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基本观点
约翰•费斯克(JohnFiske)是当代西方社会有关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家和实践者,在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继承并发展了以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School)为代表的英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作为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修正并超越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学者对于大众文化单一的研究思路,从大众与大众文化的现实本质出发,强调大众文化的参与性、娱乐性、趣味性与反抗性,从而进一步突显大众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力以及潜在的进步意义。约翰•费斯克全新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模式,主要着眼于文本、受众和文化的功能三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1.能动型文本观,即生产者式的文本建构;2.能动型受众观,即积极、主动的生产型受众;3.媒介文化的功能观,即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传统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相比,约翰•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更注重受众自身的作用,他认为大众在文化传输过程中,不仅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也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大众在文化生产中具有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他相信大众通过生产者式的文本建构,可以实现生产型受众向生产型作者的转变,并通过文化的创造能够在微观政治层面促成社会体制循序渐进的改善和进步,最终促进社会的革新。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学ip热”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众文化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是当代社会大众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以现代科技为文化生产的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传播的形式,以现代工业化大众文化为传播的内容,以普通的社会大众为主要的传播对象。在此背景和条件下,我们的受众不仅是文本的消费者和传播者,更是文本的改编者和生产者,受众与受众之间的文本传播方式也将对传播的效果和意义产生重大影响。
三、基于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视角的网络文学IP研究
(一)生产者式文本的生活与艺术对话
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写到:“大众文化只存在于其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而不是存在于静止、自足的文本中。”[2]他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3]在这一个过程中,文本的传播具有互动性,文本传播的主动权逐步发展转变,由原来文化的生产者逐渐倾向于文化的接收者,文化的接收者也在大众文化的消费中逐渐占据优势。简而言之,受众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subjectivities),即是:受众能够在社会不同的分层中自由穿梭,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消费也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文本形式应该是生产者式的文本”。[4]“生产者式的文本”一方面能够实现“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作者性文本”的开放包容。网络文学在创作的时候恰恰重点考量了易读性与开放性的文本设想,在情节设定和任务刻画方面更加“场景化和典型化”。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有着爱情、亲情、友情,更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文本的创作时,假定读者就是作者,并以同等的注意力代入阅读全部文本,使其具有相应的角色视角同情性。以《琅琊榜》为例,故事具有强烈的叙事主观性,故事从梅长苏的视角观察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特点,通过大篇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回忆,使得读者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和“视觉同情”。这里所谓的“视觉同情”指的是: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作品,通过某个主要人物的视角进行叙事,以主要人物感情或命运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铺陈,使读者对持有这个视角的人物产生人物代入,并产生道德和情感的同情。梅长苏身上发生的背叛、爱情、友情也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因为这些人物的遭遇或是经历的感情,恰恰也是普通大众能够经历的。而他为了复仇的步步为营的心理变化以及通过超凡智慧设计的复仇桥段,又是大众对于生活平凡的一种“破壁”,是一种对生活的改造和再生产,是升华的艺术。网络文学这种根据受众的需要,将受众视作大众文化的真正生产者从而赋予他以主动性的文本创作方式,使得网络文学既有“读者性文本”的易读性,又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文本就像是一个“菜单”,是大众日常生活情感的体现,也是大众对于生活之外精神世界追求的艺术,受众可以从中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探寻文化内容中的快乐,创造出具有自己精神意义的“菜肴”。大众文化文本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更像是一个意义上的“超市”,受众可以在这里面根据不同的喜好和观念,自由选择所要接收的内容。而这也就是一些好的网络文学IP具有强大粉丝群体的原因所在。这群庞大的读者群体,恰恰又是网络文学IP衍生成影视剧、游戏等的根本所在。
(二)从生产型受众到生产型作者的身份建构
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认为,受众不只是文本的消费者,也是文本的传播者,甚至是文本的创造者。受众与受众之间的文本传播方式也将对传播的效果和意义产生重大影响。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不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赋予的或强加给他们的,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兴趣、爱好、价值观、生活阅历以及文化消费目的等在大量的文本中不断发现、甄选、挖掘和提炼出来的,甚至是通过自己文化生产直接创造而来的。大众文化中的受众是“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的”。[5]在大众文化文本的生产过程和传播过程之中,创作的过程往往是一个作者与受众互动的过程。大众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消费,同时也产生着各自的见解和不同的意义,甚至产生了文本再创作的过程。因此生产型受众到生产型作者的身份建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大众文化文本的再生产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大众同样也是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就没那么清晰,编码和解码的双方随时也发生着角色的颠覆。诸如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的走红,各类改编自两者的盗墓题材的网络文学、电影电视剧层出不穷;随着《诛仙》的走红,玄幻文学也迎来了创作热潮,各自同质性创作或同人文章等也迎合了不少人的口味,而这些文本的创作,很多是原著小说粉丝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再创作。另外“网络文学IP热”催生了粉丝社群,并形成粉丝经济,小说的读者往往会通过阅读平台区、QQ群或微信群等传播渠道形成相应的自媒体,与作者就小说的文本框架、写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进行提问或讨论,给予作者更多的想法和构思,直接或简洁地参与作者后续作品的创作。作者与受众的角色互动,也催发了网络文学的粉丝经济,激发了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网文爱好者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工作,使得更多网络文学的草根富豪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网络作者有数百万人,按收入和粉丝数可分为5级。多部知名网络文学IP,诸如《择天记》、《何以笙箫默》、《翻译官》、《芈月传》、《盗墓笔记》、《花千骨》等的作者均来自“草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网络作者有数百万人,享誉网络的知名作家猫腻、唐家三少、辰东、天蚕土豆等大部分也是“半路出家”,最早也是网络文学的读者。许多资深网文粉丝也在蠢蠢欲动打算重新投入网文写作中。这种生产型受众到生产型作者的身份建构,使得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的受众,在享受网络文学的同时,也不断参与网络文学的创作,甚至最终成为了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传播过程中的编码者和解码者界限并没有那么明显,有时候还发生了转变或者互换。大众文化信息化的今天,受众一方面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资讯,并根据自身的喜好和价值判断主动获取有用的文本,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样的选择、萃取、吸收和融合,不断塑造出了更多新的大众文化,成就了更多的网络文学IP。
(三)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文化体验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因为其自身种种原因的限制,同时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限制,不可能在宏观的政治层面发挥作用,只能是在各类微观的政治水平层面上产生影响。“大众文本可能是进步的——在它们鼓励有助于改变或动摇社会秩序的生产的意义上,但永远不会是激进的——在它们永远不会直接对抗或推翻那个秩序的意义上。”[6]网络文学更多的是构建在一个虚拟的社会环境之上,可能是架空的历史也可能是历史事件的改编。不论是仙侠、玄幻还是盗墓、权谋,文本总是充满着受众对于现实乐观的投影和想象。因此,大众之所以能够主动地、灵活地使用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并从中创造性地发现自己的意义,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在文化产品与日常生产生活之间发现积极的联系。这种联系取决于观众的日常经验与社会语境,但无论如何,这种联系所产生的文化体验,绝非是悲观主义的,也非少数人的精英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生产式快感”,“生产式快感”能够不断激发大众的创作热情,将不同的文化体验逐渐变成网络文学IP创作的养料,并通过不断的文化生产塑造出更多具有自身文化标签和意义的文化作品,最终实现大众对于个体身份的进一步认识和升华。因此保留受众自己所开创的文化场域,增强受众文化快感的变革潜能,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文化体验是网络文学IP的重大使命。而这个使命约翰•费斯克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微观政治”,即在符号抵抗中实现受众的自我身份认同,“最为微观的微观政治是幻想的内在世界”。[7]以《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作者塑造了一个“幻想的内在世界”,这个世界有强权(如天帝、长留上仙),有反派(如杀阡陌、素锦),有朋友(如折颜)、有爱人(如夜华、白子画),有权谋,有背叛,有生死之恋,有离别之苦,有反抗强权的斗争,也有对抗邪恶的战争,各式各样的“幻想的内在世界”构成了作者显现给受众最为实际的文化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幻想的内在世界”是大众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精神力量,它通过文化的感染力,不断鼓励大众以不同于统治阶层精英文化所设计的方式去思考,从中找寻自我的身份定位,以及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另外亲情、友情和爱情永远是网络文学IP不变的主旋律,无论主角经历过多少次的挫折、背叛和苦难,各种虐心的情节设计始终是读者“意义创造的质料”,营造一个为爱付出一切的现实意义。而这种现实意义是普罗大众的,是乐观主义的,是大众文化进步性的表现。与我们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精英文化不同的是,大众文化总是在统治结构的内部形成的,通过微观的、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文化体验。“网络文学IP”属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所秉承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核也深受我们主流文化的影响,这也使得大众文化不可能是激进的,而只能是进步的。“网络文学IP热”不仅仅是传播学现象,我们主流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大众文化及大众快乐之中,是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表现。这种转变是大众积极向上、主动乐观的文化探索,是一种超越了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文化体验。
四、结语
大众的能动性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网络文学的生产和传播离不开大众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效应”。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8]“网络文学IP热”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体现,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得利于互联网科技的普及与创新,得利于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更是得利于普通民众对于丰富多元的大众文化的迫切需求。如今网络文学生产者的文本与阅读者切身的社会情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因此如何创作出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同时能够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和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则需要我们广大网络文学创作者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生活、贴近大众,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正如所讲“人民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坚固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9]只有以丰富和改善大众文化生活为目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传递正能量,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网络文学IP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补充,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热爱和珍视。
参考文献:
1.彭伍新.约翰•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2.石雯.理想大众与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3.胡疆锋,陆道夫.文本、受众、体验——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学术论坛,2009(3):79-84.
4.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J].学术交流,1998(6).
5.滕守尧.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J].北京社会科学,1997(2).
作者:沈培辉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