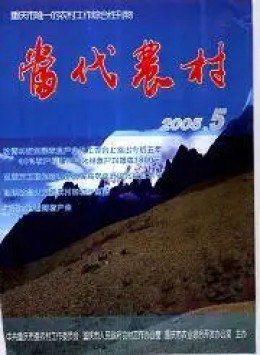农村社区文化建筑对孝文化的传承影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农村社区文化建筑对孝文化的传承影响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通过对农村社区新型文化空间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不仅继承了传统祠堂孝道功能,也产生了新的孝文化表达方式。从表层上看,它为村民提供一种精神文化生活场地,实质上它借助新型建筑空间为孝文化提供实践手段,构建出村民文化精神与现实实践的交往,传承与延续孝文化。本文从新型空间的实体性器物、仪式的操演两个方面探索孝道意识如何濡化到村民的内心,诱导村民孝行,使孝文化在新型文化空间内完成文化的再生产过程。
一、引言
随着时代变迁,现代化进程推进,农村社区内许多承载传统文化的建筑空间遭到严重破坏。像祠堂这种具有体现中国孝道观念,承载孝道文化的空间载体(冯尔康,1996),也面临着巨大消失风险。甘满堂(2014)认为导致风险产生的关键在于祠堂建筑空间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不断消失,“在福建,村庙可以申请登记为道教或佛教活动场所,拥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护身符’;哪怕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村庙也会得到一块地而异地重建。而祠堂除了‘文物’之外,再无其他‘护身符’;若未被登记为文保单位,那它通常只能是消失。”。显然,祠堂在农村社区的存在空间已经被压缩,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与祠堂之下的孝道象征意义也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那些已经消失了祠堂的村庄,怎样才能更好传承孝道文化。如何通过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来补充祠堂孝道传承功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众所周知,历来朝代都对“孝”做过阐释。早在《尚书》中,曾把“孝”解释为“厥养父母”。《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显然孝是以围绕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关系的展开为前提,但敬养父母仅仅是一种狭义层面的孝(肖群忠,2002)。广义的孝则应为“慎终追远的意识,以及延伸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里、扩展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教育、文艺、民俗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传统儒家所要求的亲亲、尊尊”。也就是说,孝不仅是针对个人对父母的敬养关系,更是个人对社会生活表现的一种精神气质。沿此逻辑,朱岚(2010)对广义孝的概念做进一步延伸,广义的孝是立身处世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是对所有长辈、亲贤一种尊、敬、善的行为。本研究是以传统祠堂中孝文化继承与发展为基点,来探讨长幼有序、尊老、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在现今阶段新型建筑上的社会性延伸。因此本研究中所强调的“孝”将特指广义层面上的“孝”,及社会对老年人的敬老、养老行为与长幼有序礼制准则将统称为“孝文化”。目前国内有关乡村社区内孝文化传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它包括:传统孝道文化空间如何传承孝文化(冯天瑜,2005)、乡村社区内组织村民进行孝道实践来传承孝文化(朱启臻,2015)、利用家庭日常教育传承孝文化(李小燕,2006)、依靠乡村学校以及借助传统艺术开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去传承孝文化(周亮,2009;陈瑞生,2011)。但以往研究出现这样一个空白,便是承载孝文化的旧文化空间消失基础上,如何构建新的承载孝文化的空间载体。大量有关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又表明,一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建构对文化的形成、保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公社集体主义解体后,福建乡村社区村庙的复兴,以及围绕村庙展开的祭祀仪式,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多元文化的产生(甘满堂,2008)。随着基督教会所在传统村落的兴起,乡村文化空间发生了变迁,使原本维持乡村秩序的宗族与祠庙的公共空间地位交付给了基督教会所来完成(李华伟,2008)。同时,乡村文化空间的发展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周尚意、龙君2003),以及一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起又助推了村民自治的产生与发展(王春光,2004)。这些研究都说明,农村社区新型空间对当地文化的变迁作用。因此,以农村社区中新的文化空间样式探讨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成为一种可能。最重要的是,“空间——行为”理论同样指明,文化空间在依靠建筑空间表达观念精神的前提下,对个人观念形成,以及行为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舒尔茨(2005)曾对建筑做过如下的论述,“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自远古以来,它已使人类的存在变得富余意义,并使人类在自身之中寻找到一个立足点。所以建筑不能用几何或符号概念来完满表达,它应是一种象征,并可以成为表达和传载人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理解的象征形式。”吴良镛(2011)指出:“任何建筑空间除了自身的居住、实用功能之外,它既含有物质内容,但更应该注入精神上的内容。”而这种承载精神观念的空间,又会作用到个人的意识之中。耿海燕、朱滢、李云峰(2001)也认为任何一种无意识的信息在反复的刺激后,都会形成特定的思维意识。再进一步讲,文化空间又会构造一种场域。让村民在无意识下,把身体动作转变为一种生活习惯。正是空间与意识的关系,让一些学者关注到空间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徐从淮(2005)系统的探讨了建筑空间与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建筑空间对主体的心理影响,从而产生行为的影响。建筑学家与人类学家的拉普卜特(2004)认为,建筑空间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诱导建筑空间内的主体行为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会被带入到一个人的习惯当中,形成一种文化特质。以上的分析已经表明了本研究的前提假设,同时也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乡村社区下的文化空间建筑对个人意识与行为将产生影响,而承载孝文化建筑的新型文化空间将对村民的孝意识行为发生作用,进而传承孝道文化。基于此,本文将选取一个已经具有承载孝文化空间建筑的农村社区,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选定农村社区中新型文化建筑的考察,弄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建筑,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或者转化而来的?第二,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建筑,是依靠什么方式影响村民的孝道意识的?第三,如果村民已经具有孝道意识,又是如何展开行为实践?希望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追问,理清乡村中新型文化空间对孝道文化传承过程与对孝文化的传承作用。
三、传统公共空间承载孝文化的两个维度
“祠堂”这一文化建筑空间起于汉朝,最早被用作供奉祖宗牌位。那时的祠堂称为家庙,与墓地合为一体成为后人祭拜祖先之地。直至南宋朱熹在《家礼》中明确提出祠堂之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至此“家庙”才被改称为祠堂。这时的祠堂从建筑与文化内涵两方面发生转向,从建筑角度讲,祠堂与墓地分开,单独成为祭祀祖先的建筑。从孝道文化内涵角度讲,它被赋予新的功能,“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开业传世之本”。由于祠堂是满足家族需要得以产生与发展,它也成为家族主义的重要的空间地理标志与家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家族依靠它把区域内分散的宗族成员、把过去的祖宗与现实的后人整合在一起,并以“孝道”作为维护家族网络关系的基本法则。正是在此情况下,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祠堂的家族性特征决定了其建筑空间对于本村村民的“内”与“外”之分、决定建筑空间的认同性与排它性,这赋予它成为一种指针对本宗族的公共建筑。由此空间生发出来的孝道准则,起到对本宗族的成员起到规范与惩戒作用。浙江下宅村的朱氏祠堂在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据《潭溪朱氏宗谱》载,朱氏祠堂始建于明初。由于元末明初常年战乱灾荒,下宅村朱姓始祖为躲避灾祸便带领带族人从义乌县赤岸迁于此地,在此发家,兴朱姓一族。后人感念祖上之恩,而建朱姓祠堂。朱氏祠堂作为朱姓家族的公共空间,它在“孝”的表达上具有两方面维度:一方面它是国家实行孝道教化的工具,强化家族中个体成员的家族身份认同的空间性纽带。另一方面它又是传播孝道观念,通过惩戒与奖励的机制维护家族内部的正常运转秩序的重要场所。从第一个方面看,传统下宅村借助祠堂把国家、家族、个人置于同一个文化网络之中,在三者间建构一种孝道观念的纵向下渗的文化通路。朱姓宗族与宗族个人之间在展开孝道关系的同时,代表国家意识的道德观念——即儒家孝道,借助祠堂把国法礼数渗入到村庄内的宗族成员中间。“乾隆二十五年(1706年),清廷颁布的《颁胙条例》规定对老年人在祭日时获得的待遇以及忠义孝悌之人享受的待遇等条例,就利用祠堂公布给村民”(王克俭,2012)。祠堂作为传播媒介把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孝道观念传达给了家族中的个人,并以国家名义对个人进行教化,让人养成尊老敬老的孝道意识。同时,国家又在规定中体现长幼有序的秩序,表达对于老年人的尊敬礼爱。从第二个方面看,在传统下宅村社会,祠堂还作为扬善惩恶的文化空间载体,“孝”与“不孝”则是褒扬与惩治的重要内容。在朱氏族人看来,不孝是违背伦常,大逆之罪,因此必须严处“孝悌不敦: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子弟当尽之职分。有忤逆犯上及重服违制者,祠族分别重罚”(王克俭,2012)。那应如何惩戒?在传统下宅村祠堂内以藤条鞭打不孝者以此作为一种重要惩戒措施。作为朱姓氏族权威的祠堂“藤条”,便为孝道精神延伸的物质化符号。因为,它不仅代表着权威与势力,它还代表着一种让族人臣服的道德要求,它与道德、年龄、地位紧密连接在一起。而这种道德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孝道伦理。当然,祠堂除了以孝观念为基础,发挥惩恶的作用规范族人外。还具有扬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主要借助文化空间内的实体器物,它们作为孝观念的物质性延伸。传统朱氏祠堂大堂正上方就挂有许多匾额。这些匾额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记述功名的如“左丞相”“状元”“进士”。第二类是记述道德的如“孝义”“忠慈”。只有在功名上、道德上有成就的人才能以匾额的形式被挂到祠堂内,享受族人的敬仰。而“孝道”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敬仰最直接、简便的方式,也成为大家得以遵循、恪守孝道的动因。这样祠堂除了与宗族中的功名产生联系外,祠堂也与孝道精神产生关联,通过祠堂起到激发、褒扬族人重孝的意识。让族人在祠堂内的交往中,养成重孝的习惯。显然,传统朱氏祠堂作为一种家族建筑,它以孝道为连接点把国家、家族、个人构连在一起。作为一种文化空间,规范了族人的孝道要求与秩序。并以空间内的物质实体延伸孝道文化,使孝道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这里,个人的家族身份得到认同,并以此为展开进入到家族的日常生活中。祠堂凝聚起整个朱姓家族,同时也使孝道观念通过祠堂在家族内部绵延接续。直至近代,由于的产生使下宅村的祠堂彻底离开了历史的舞台,朱氏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彻底消失在了下宅村的村域之内。随之而来的是,祠堂赋予朱姓族人的家族凝聚传统与孝道劝诫作用随之消失。国家权力在这个时期,替代了下宅村传统的村落秩序,国家意识取代了下宅村的宗族观念。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权力在下宅村的撤出,下宅村村民出现道德真空,这时市场化、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填充物占据了下宅村村民的道德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下宅村中传统孝道观念开始逐渐湮没。朱氏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它承载着村民的道德理想与孝道观念。承载着孝道的惩罚、规训与秩序。它的消失,使这一切失去了落脚点。对老年人讲,祠堂是尊老敬老的场域,是老年人权力得以照顾、承认的发源地。对年轻人讲,祠堂是培养老幼秩序的训练场,是树立孝道观念的大讲堂。时至今日,社会变迁,原本承载孝道文化观念、表现人际秩序的祠堂固然消失在下宅村内。但孝文化像种子一样,只要为它提供适当的土壤、合适的气候,它又会生根。文化礼堂建设就像为孝文化重新提供土壤,为孝文化这粒种子提供生根的机会。因此,伴随着文化礼堂在浙江兴起,作为一种新型建筑样式对孝道文化承载作用,接续很多传统祠堂功能,成为传统祠堂延续。文化礼堂对孝文化的传播与承载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新型文化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延续与转化
“文化礼堂”作为一种乡村文化空间样式,起源于2012年的浙江省,它的前身是“文化大院”,之所以由“文化大院”变为“文化礼堂”,主要突出对“礼”的承载作用。根本目的则是通过乡村内特有的文化空间保存本地文化资源、普及传统文化以及宣扬优秀的现代文化,达到教化育民,培养村民道德价值观念的目的。由于文化礼堂与传统祠堂都具备道德教化功能这一特性,因此浙江省各村的“文化礼堂”多是基于传统祠堂的文化空间发展起来。例如金华市琐园村的严氏祠堂、澧浦镇的王氏祠堂都在保存祠堂原本的结构样貌下转化为本村“文化礼堂”。而一些已经消失了祠堂的村庄,如下宅村。则利用本村的沿袭下来的文化特色,借助物质承载物把本村的文化特质注入到新兴的文化礼堂中,并在此文化空间恢复礼俗仪式完成对村民的道德教化,弥补祠堂消失所带来的不足。(一)文化礼堂对传统祠堂空间孝道理念的继承在这里,有必要从空间上,把下宅村承载宣传文化与文化活动场所称为“文化堂”,以此与文化礼堂概念相区分。下宅村的文化堂从整个文化空间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堂的外部空间,另一部分则为文化堂的内部空间。文化堂外部空间表达孝道含义是由三个元素构成。其一,环绕文化堂的廊道,廊道上的本村孝道故事凸显着孝道文化。其二,为文化堂门口的一副楹联,上联为“文化礼堂传今古佳话”下联为“精神家园承世代文明”,直接表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其三,为挂在文化堂外部强上的“孝心榜”。通过村民为老人捐款的记录,直接宣传孝道行为。这些物质化的象征符号直接反映出生活中的孝道文化精神,起到告诫与引导村民行孝。文化堂的廊道上所除了呈现的是下宅村民间艺术、传统孝道故事外,更注意对个人孝道行为的文字与图像记忆。这些长廊不同于传统祠堂上方所挂起的“进士”“状元”“忠孝”等匾额,它已突出日常生活中的行孝方式为主题。它记载着儿媳如何孝顺公婆、子女怎样孝敬父母的日常行。孝德廊把真人真事记录下来,教育村民效仿行孝,孝顺儿女的相片被放在孝德廊内,人人口碑传颂。孝心榜,则是历来村内、村外企业和村民为本村孤寡老人捐献行为的记录,是人们表达爱老敬老的方式。文化堂外部的要素从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寻找到出发点,一面是传统故事、古老楹联。另一面是现代的相片、现实的事迹。这些符号是人们真实生活中孝道表达的写照,文化堂通过它们把个体日常的孝道行为形塑成一个形象,并把这个形象带到了公共场域,每一个形象又会作用村民的意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并非是毫无关联的符号,它们构成一个象征符号群,是敬老爱老增强村民对孝道的认识效果不可缺少的一环。文化堂内部则分为前厅与后堂。前厅与后堂的空间划分,实则内在的规定一种空间秩序,空间秩序的安排则是以老幼的年龄差距为基础进行区分。尤其当文化堂内举行有老年人参加的敬老仪式时,文化堂内的空间表达会非常明晰。空间内的秩序规定了老年人的位置与权力,明确了村民的敬老爱老意识。一方面,敬老仪式依照老人的年龄规定就坐次序,年龄较大、村中地位较高的老人会座在前堂,小辈们按照辈份次序依次分坐于大厅或站立前堂两旁。座次顺序的安排暗含一定的老幼尊卑孝道秩序观念,其意义在于,使村子里的老人和年轻人都具有准确的辈分与长幼标记。文化堂重新以礼俗社会的空间规范来指导人们道德,加强个人敬老观念。另一方面,文化堂以敬老仪式的“身体实践”来规训村民的身体记忆。首先,孝道观念在子辈村民中的记忆,是孝道仪式操练的展示场所。行礼作为一种身体实践被看做是表达敬老爱老的标准。一般来说,不同时代表达敬意的方式不尽相同,文化礼堂内敬老礼仪实施时,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用不同礼仪方式表达孝义。自文化礼堂出现之时起,如今每年夏季举行的四世同堂家庭进行敬老礼时,子辈会给老人磕头,孙辈则要向老人鞠躬,并在此基础上向父母鞠躬,重孙辈则需要给所有长辈行礼。每逢重阳节都举行孝道仪式,此习惯促使孝意在村民间的长久留存。“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沉淀在身体中。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虽然不留痕迹,但却避免了在所有话语实践中可能遭受到的侵扰与冲击”(保罗康纳顿,2000)。因此,文化礼堂成为承载仪式的现场,人们在仪式过程中用身体实践重复过去的历史传统,最终把孝道观念封印于村民头脑当中。下宅村的文化礼堂建筑通过内部方位安排体现对老年人的关照,秩序规范依然以敬老行为的操演渗入到村民意识中。文化礼堂尊崇传统尊老道德习惯,接续传统祠堂建筑的孝道功能依靠孝道秩序。总之,作为文化堂建筑中的一种孝道象征符号——孝心榜、楹联、廊道构成孝德展示,文化堂内部空间秩序规定和村民在文化堂内部实行的仪式操演,构成村民敬构成村民敬老爱老的孝道精神的物理空间与肢体性的延伸。(二)文化礼堂补充传统祠堂空间对养老实践的现代需求居家养老中心是“文化礼堂”中的另一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文化堂孝道的精神性延伸。一方面是以日常生活入手,从实际入手解决老年人吃、住、养的问题。下宅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过高(下宅村总人口1039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234人,比例占到百分之22.3%)①,且村中孤寡老人较多,因此全村有20多名孤寡老人需要解决吃、住、养的问题。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便利,建筑为单层结构,在建筑外的中央处挂着百善孝为先的匾额。除了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外,居家养老中心还设置保健室、棋牌室、图书馆等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尽管从物质功能上看,居家养老中心与城市的敬老院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但实质上,居家养老中心打破由于城市敬老院中老人因互不相识与习惯差异而导致的精神隔阂。以遵循“离家不离村”的理念,填补老年人的“思乡”情感,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通过对文化空间上的分类描述与两则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成为蕴含孝道观念祠堂的替代形式,它生发了原有祠堂所具有的情感性力量。假若没有任何建筑形式来接替祠堂孝道功能意义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维持村落秩序与激发情感力量的建筑形式,在村落地域内将不能出现。最重要的是,下宅村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在空间上的结合,有效的强化了孝文化的传承,满足老年人的内在需求。(三)文化空间功能发展与孝文化变迁下宅村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体现出两种不同功能,就文化礼堂来说,它是承载孝文化教化功能,是传统孝文化仪式、礼仪教育的操演场所,也是现代孝行的宣传阵地。通过孝文化仪式和尊老爱幼模范事迹的不断上演,加强人们对孝文化的理解,不断丰富着人们敬老养老的精神。居家养老中心则是一个孝行为的实践场,人们在文化礼堂认识孝文化、树立尊老敬老观念的同时,在居家养老中心得到了实践的操演过程,认识与实践的空间整合,使敬老理念与养老实践结合在一起,有效强化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加上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孝文化得到了有效发扬,从而真正做到孝所要求的“敬与养”的融合。卡特勒曾对建筑空间的教育功能有过这样的评价:“教育的复杂性,即影响教育的因素很多,其中有许多变项,而教育建筑是教育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项”(秦红玲,2006)。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的空间整合,发挥了建筑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赋予了学孝与尽孝的双重含义,对村民们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孝文化的教化功能。根据心理学揭示的文化传承原理,孝文化规范的养成要经历服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服从是孝文化规范培养的开始阶段,有自愿的服从,也有迫于某种压力的服从。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孝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对社会整合、形成一致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化阶段是人自觉自愿地接受孝文化的理念,愿意根据角色要求规范自己行为,以便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这个阶段,宣传和示范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示范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同化效应的发挥。内化是在同化的基础上把接受来的孝文化观念变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稳定的观念和行为,甚至发展为一种信仰,而且还会影响、教育其他人。在农村社区具有潜移默化地从服从到同化的天然优势,下宅村的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整合了孝文化资源,突出了这一优势。居家养老中心使文化礼堂所弘扬的“孝”被赋予一种实际上的行动与真实,人们在此体验,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其它领域,进而影响孝行习惯。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空间上的整合,增强孝文化从理念到行为的实践过程,它扩大了孝在当前社会下的文化转变,相较于传统祠堂空间只承载孝道理念来讲,更具有实践行动。
五、结论与讨论
文化礼堂作为农村新型文化空间,承载了祠堂的孝道功能。但相较于祠堂,文化礼堂更被赋予居家养老中心的孝道实践功能。二者的结合为乡村孝道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就是把孝道的宣传教育与孝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以空间建筑的整合为载体。一些乡村在新农村建设中由于没有意识到宣传与实践的结合意义,常常出现二者分离或其中一个缺失的现象,造成仪式性宣传与实践的脱离,弱化了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我们调查过的村庄中,有的建设了文化中心,其中也有敬老的内容,但是没有类似敬老中心的实践条件,使敬老文化的宣传效果打了折扣。也有的村庄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相隔距离较远,二者的空间隔离出现了一边是热闹的文化礼堂,另一边是被村民遗忘的老人们。无论村民在文化礼堂内如何操演,形成“孝”的记忆如果远离孝道实践,就很难与敬老行为建立密切关联,孝行因此得不到及时强化最终削弱其教育效果。对于除了孝文化之外的其他乡村文化来讲,使得以“文化礼堂”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空间真正发挥作用,达到教化育人的目的,除了重新恢复并构建文化空间内承载文化的物质实体,并通过仪式操演强化其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外,孝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表明了应建造相应文化实践场所的必要。
参考文献:
[1]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8.
[2]甘满堂.[乡村!乡村]福建祠堂=世界遗产[J/OL][2014-05-22].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4]朱启臻.留住美丽乡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7.
[5]李小燕.从族谱的家规家训看客家人的价值观念[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77-80.
[6]周亮.试论贤孝的艺术价值、社会功能和传承发展[J].科学•经济•社会,2009(02):20-23.
[7]陈瑞生.基于孝道文化传承的养老教育实践[J].上海教育科研,2011(08):82-83.
[8]甘满堂.福建村庙酬神演戏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J].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58-63.
[9]李华伟.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J].民俗研究,2008(04):72-101.
[10]周尚意,龙君.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J].河北学刊,2003(02):72-78.
[11]王春光,孙兆霞,罗布龙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J].浙江学刊,2004(01):137-146.
[12][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M].李璐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
[13]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6.
[14]耿海燕,朱滢,李云峰.错误再认:仪式、注意和刺激特性[J].心理学报,2001(02):104-110.
[15][美]阿摩斯•拉普卜特.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M].黄兰古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2-45.
[16]徐从淮.行为空间论[D].天津:天津大学,2005.
[17]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94-99.
[18]朱岚.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5.
[19]王克俭.文昌武曲写春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77.
[2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90.
[21]秦红玲.建筑的伦理意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45.
作者:孙大伟 任超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